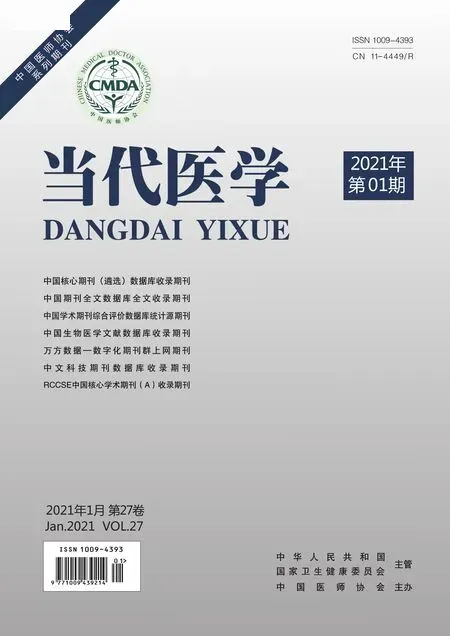體檢人群中體重指數與血壓、血脂、血糖及血尿酸的相關性分析
程臻,胡瑜,劉雨濛
(1.山西白求恩醫院綜合醫療科,山西 太原 030032;2.山西國信凱爾生物技術有限公司,山西 太原 030000)
世界衛生組織認為超重與慢性疾病發展風險和死亡率增加有關,且認為肥胖也是一種慢性全身疾病[1]。脂肪不僅是哺乳動物能量的來源,也是作用于體內平衡和病理條件的生物活性分子,也是導致臨床肥胖狀態的個體出現低度系統性炎癥的誘因[2]。研究發現,由于體脂增多,肥胖個體脂肪細胞分泌的趨化因子可能啟動脂肪組織中的白細胞浸潤,進而介導建立慢性免疫激活[3]。脂肪組織具有固有的巨噬細胞,當該組織失去功能時,脂肪細胞釋放促炎趨化因子招募的活化巨噬細胞會增加,活化的巨噬細胞釋放炎性因子,促炎趨化因子有助于巨噬細胞誘導炎癥的正反饋[4]。超重和肥胖患者的血清中TNF、IL-6、C 反應蛋白等炎癥標志物水平較高,超重增加炎癥介質循環,這些炎性標志物與心血管和代謝危險因素密切相關[5]。人體內的高脂肪分布與肥胖有關,與高血壓、糖尿病、呼吸系統疾病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病因密切相關[6]。本研究以2014 年1 月至2017 年12 月于本院接受體檢的7 004 名為研究對象,對其高尿酸血癥與其他體征之間的相關性展開分析。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2014 年1 月至2017 年12 月于本院接受體檢的7 004名為研究對象,其中男3 860名,占55.1%;女3 144 名,占44.9%;年齡18~85 歲,平均年齡(44.55 ±8.54)歲。
1.2 方法 受試者在體檢前禁食8~12 h,對受檢人群的體質量及身高進行測量,以坐位形式測量血壓。采取外周血,利用全自動生化分析儀對血液甘油三酯、總膽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谷丙轉氨酶、血糖及血尿酸進行測量。
1.3 代謝異常的診斷標準 體重指數(BMI)的劃分根據《中國成人超重和肥胖癥預防指南》,BMI<18.5 kg/m2為消瘦,18.5 kg/m2≤BMI<24.0 kg/m2為正常,24.0 kg/m2≤BMI<28.0 kg/m2為超重,BMI≥28.0 kg/m2為肥胖;血壓(BP)標準根據2010 年《中國高血壓治療指南》,收縮壓(SBP)≥140 mmHg和/或舒張壓(DBP)≥90 mmHg 者判斷為高血壓;血脂依據2007 年《中國成人血脂異常防治指南》,總膽固醇(TC)≥6.22 mmol/L,甘油三酯(TG)≥2.26 mmol/L,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4.14 mmol/L,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1.04 mmol/L 及≥1.55 mmol/L,以上4 種情況中出現任意1 種即判定為血脂異常;血糖(FPG)依據2010 年《中國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診斷標準,FPG≥7.0 mmol/L為高血糖;血尿酸(SUA)依據男性及絕經后女性SUA>420 μmol/L,絕經前女性SUA>350 μmol/L判定為高尿酸血癥[2]。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7.0 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以“±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 檢驗或方差分析,計數資料以百分數(%)表示,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高尿酸血癥危險因素分析采用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隨后進行Logistic多元回歸分析,并采用95%可信區間及比值比等表示結果。
2 結果
2.1 基本情況和各指標異常率 調查人群平均BMI 為(26.42±3.54)kg/m2,其中男性(26.36±2.76)kg/m2,女性(26.49±2.85)kg/m2。受試者中無消瘦者,超重和肥胖檢出率分別為61.29%和23.80%;BP、血脂、FPG及SUA異常率分別為25.71%,27.35%,12.24% 和41.39%。BMI 正常范圍上述指標異常率為12.45%,17.34%,4.48%和11.83%;超重者上述指標異常率為25.20%,28.72%,6.22%和38.23%;肥胖者上述指標為33.59%,36.71%,8.82%和36.41%。
2.2 不同性別、年齡段指標水平比較 體檢人群中女性和男性BMI指數在不同年齡段顯示均為超重,且其血壓隨年齡的增長均有升高趨勢,血脂、空腹血糖和血尿酸在男女各年齡段間未見異常,除血尿酸外,各年齡段間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1。
2.3 不同性別、年齡段指標水平比較 體檢人群中男性女性超重率和肥胖率隨年齡增長有升高趨勢,男性肥胖率在60歲后呈降低趨勢;高血壓、血脂異常檢出率和高血糖檢出率均隨年齡增大有增加趨勢,其中男性45 歲血脂異常達峰值;血尿酸異常在男性女性體檢呈年輕態勢,女性因缺少停經信息,未能有效計算45歲后血尿酸異常率。除血尿酸外,其他指標異常率與年齡段間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2。
2.4 BMI 與各指標的偏相關分析 控制年齡和性別,BMI除了與HDL-C呈負相關外,與其他各項指標均呈正相關(P<0.01);控制年齡,男性BMI與HDL-C無明顯相關性,女性BMI與TC、LDL-C無明顯相關性,見表3。

表1 不同年齡、性別體檢者BMI、BP、血脂、FPG及SUA水平比較Table 1 Comparison of BMI, BP, blood lipid, FPG and SUA levels in different ages and genders

表2 不同性別年齡體檢者BMI、BP、血脂、血糖及SUA異常率比較(%)Table 2 Comparison of abnormal rates of BMI, BP, blood lipid, blood glucose and SUA in different genders and ages (%)

表3 高尿酸血癥組、正常尿酸組與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的關系Table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yperuricemia group, normal uric acid group and hypertension, hyperlipidemia, and hyperglycemia
3 討論
由于現代久坐不動的生活方式和高熱量食物攝入,肥胖等相關疾病患者與日俱增,肥胖是一種基礎慢性炎癥性疾病,是多個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的危險因素,已成為危害人類健康的重要公共衛生問題[8]。由于社會屬性及分工不同,男性工作壓力大以及生活習慣等,男性健康受到日益關注。近幾年健康體檢中發現本市男性健康體檢者的健康問題不容忽視,對2017年本院健康體檢者進行調查,本市女性人群超重和肥胖率分別為57.68% 和22.70%,男性人群的超重和肥胖率分別為62.55% 和21.06%,超重率與肥胖率均高于2011年報道的本市社區人口隨機抽樣調查結果[9],女性和男性體脂、血壓和HUA 異常檢出率最高的年齡段為45~59 歲,以中年人群為主;在18~29 歲女性中SUA 異常率最高,其次是30~44 歲,45 歲之后SUA 異常率有所下降,可能因為高年齡段女性處于更年期,絕經前后血尿酸的異常判斷標準不同,未能有效計算該年齡段血尿酸異常率;男性人群各個年齡階段呈現無明顯差異,但在高尿酸血癥檢出率高于社區男性人群比例檢測率(19.00%),且男性在18~29 歲SUA 異常率為32.63%,男性高尿酸異常年齡的提前與不健康的飲食習慣、生活方式及社會壓力等因素有關。
對2014年和2015年在本院進行體檢的成人體重指數和血脂異常關系研究發現,BMI 指數>23.8 kg/m2可以作為判斷高脂血癥、高三酰甘油血癥、HDL-C及LDL-C異常的危險因素[10],我國判定承認BMI超過24 kg/m2時即判定為超重,本研究對男性BMI研究發現,各年齡段BMI均超過24 kg/m2,且通過相關性分析可知BMI與血脂血糖血尿酸均有相關性,提示在各個年齡段本市男性女性超重肥胖不容忽視。
高尿酸血癥(HUA)是與心血管疾病、代謝綜合征、高血壓和腎病相關的常見疾病。在以往研究中,與高尿酸血癥相關的共病,包括肥胖、高血壓、糖尿病、腎功能衰竭、高脂血癥呈亞穩態上升。高尿酸血癥(和/或痛風)可能是一種病因或一種并發癥的結果,盡管流行病學數據表明高尿酸血癥與共病之間存在聯系,沒有產生足以證明高尿酸血癥引起心血管、代謝或腎臟疾病的證據,但與高尿酸血癥相關的共病治療值得注意,特別是當高尿酸血癥呈現無癥狀[11]。無癥狀高尿酸血癥的治療首先要確定引起或導致高尿酸血癥的因素(生活方式因素,如飲酒、肥胖、提高尿酸水平的藥物)。識別所有共病(體重指數、腹部屈曲、血壓、心血管風險評分),并確保每種疾病都得到最佳治療。
BMI 對多項健康指標的異常有較好的預警作用,控制BMI在正常范圍內,可以較好的預防血壓、血脂、血糖和血尿酸出現異常。本研究結果提示,加強控制體質量,預防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及高尿酸血癥等疾病的發生,對肥胖、有不良生活習慣和飲食習慣的人群應進行健康宣傳和教育,加深對肥胖所致其他疾病的風險認知,做到早期預防。此外,老年人和中年男性人群應視為超重和肥胖重點防治對象,尤其注意控制飲食和體質量,加強體育鍛煉,同時應定期進行體格檢查,及時采取相應的防治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