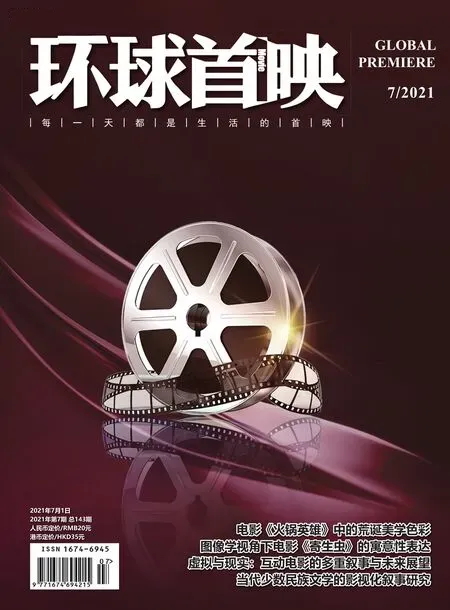淺析電影《末代皇帝》的敘事手法
熊英強 天府新區航空旅游職業學院
一、平行剪輯的巧妙運用
何為平行剪輯?它指的是幾條故事線可以是同一空間,不同時間發生的事情,將它們交替呈現在觀眾的眼前。相比較于平鋪直敘或者是“羅生門式”的剪輯方法,這種敘事相對難度較大,用好了將會使得電影非常具有節奏感和設計感,稍有不慎則會使得電影鏡頭在組接過程中比較混亂。而《末代皇帝》這部電影,則是電影史上平行剪輯手法運用的典范。
電影的開場,就營造了一種肅殺的氣氛。時刻放在了1950年。溥儀從一列悶罐火車下來,被共產黨軍隊押回了遼寧撫順戰犯管理所。溥儀自覺不堪受辱,于是在廁所拿出了一塊小刀片割腕,鮮血彌漫了整個水池,溥儀的眼神開始迷離。隨即進入了紅墻壁瓦,光線卻又昏黃的紫禁城宮中的畫面。在電影伊始,首先就是倒敘的手法,給觀眾制造了強大的視覺沖擊力。不僅畫面上,在人的心理上,也通過這種手法制造了強烈的反差感。
角色的互換,時空的變幻,在富有邏輯的蒙太奇平行剪輯手法之下,將溥儀人物的復雜性展現得淋漓盡致。在6分26秒到6分30秒的,監獄發現了溥儀自殺的跡象,大呼開門(“open the door”),6分37秒,時間突然從1950年的撫順監獄轉回到1908年(清光緒三十四年)的紫禁城的宮門。具有意味的是,太監打開了宮門,八旗兵勇騎馬進入。這兩個鏡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是又通過“門”這一象征,將二個畫面巧妙的聯結起來,構成了生命循環的平行時空。
在21分08秒,門最終被監獄長用腳踢開了,他救起了失血過多而昏迷的溥儀。溥儀這時候問他:“我在哪?”監獄長回答道:“這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溥儀又說道:“我是萬歲爺。”在19分56秒,內閣大臣卻在登基大典時對年僅三歲的小溥儀說:“您瞧,它給皇上叩頭呢。”溥儀這種身份的落差,無疑制造了一種絕望和唏噓。
二、電影的特定語言
Taylor Wills認為,敘事是無所不在的言語說詞,它將是現在是過去與現在的素材,組成敘事結構的動力,進而造就我們的言語文化。
中國的語言歷史,在世界數千年的語言文明歷史進程當中,是唯一沒有“斷過流”的,文化遺產之豐富,令世人嘆為觀止,因此從中國語言本身而言就具有獨特的文化色彩。
當溥儀的帝師,來自英國的莊士敦來到北京之時,他漫步在街上,耳邊此起彼伏的是街攤小販的叫賣聲,舉著旗子喊著口號的愛國大學生,滿嘴之乎者也的清朝的旗人。這些聲音和語言構成了莊士敦對中國社會的基本印象,也成其為電影當中敘事的主線之一。
新皇帝的登基大典,是中國皇權社會的集中反映,也是電影當中特定語言的集中呈現。而在清朝,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跪!一叩首,二叩首,興!”,再輔以萬人齊跪的畫面和漫天蔽日的儀仗,三歲的溥儀依舊有著君臨天下的氣魄;慈禧太后去世之時,在一旁祈福的喇嘛,聲音一直循環著藏傳佛教的《平安經》。縱觀歷史,中國在短短幾十年時間中語言的特質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無論社會是進步抑或者是倒退,特定的語言反映了特定的時代,從一定程度上來說,特定語言也是歷史時期的表征。
三、符號象征
藝術是人類情感符號形式的創造符號象征,是電影當中獨有的視覺語言。而在《末代皇帝》這部電影當中,對于敘事手法的闡述,其精妙絕倫的符號象征手法的運用不可或缺。
(一)門(door)
門的符號元素,在電影當中屢次出現。
a.在影片的伊始,監獄長對溥儀大喊:“開門。”
b:八旗兵勇闖進了醇親王府,大喊:“開門。”隨即抱走了奶娘懷中的小溥儀。
c.溥儀騎著莊士敦送的自行車,想要闖出紫禁城里的“小朝廷”,看看中華民國的世界,大喊:“開門。”
d.在長春的偽滿洲國皇宮,婉容被關東軍帶走,他絕望地呼喊:“開門。”
令人唏噓的是,溥儀的每一扇“門”都沒有被打開。溥儀一次次地進入“門”背后的世界,這一扇“門”永遠沒有被打開。“門”既是現實世界實際的自然物,卻又是溥儀絕望的心結,門佇立在那里,每一次的阻擋,既隔絕了世界,也隔絕了溥儀的肉身和靈魂,讓他充滿著束縛。
(二)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的變化,是反映時代特征的重要抓手之一,也是電影當中一道“獨特的風景”。
在紫禁城中,皇上和格格坐的是人力驅動的轎子和馬車,抑或者是騎馬;溥儀和弟弟溥杰翻墻看到民國大總統乘坐的汽車之時,不禁感到暗暗地震驚;老師莊士敦送給溥儀一輛自行車之后,他馬上拋卻了轎子,每天騎著自行車穿梭在宮中。交通工具,讓溥儀看到了中國和西方文明社會巨大的差距,他有著對于自由和社會變革的渴望。
(三)標語
標語,是電影中新中國時期的符號象征。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和溥儀回歸普通公民生活之后,標語多次出現。在審判溥儀之時,書記員和審判員背后,寫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從這個角度,聯系《末代皇帝》電影拍攝制作的年份,1986年,這個背景之下,正好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這一時期,也是中國民間歷史反思運動的高潮期。將真實的歷史畫面重現在電影之中,這充分證明了,我們對這一時期錯誤的深刻理解,和直面恥辱的勇氣。
四、隱喻
何為隱喻?隱喻是在彼類事物的暗示之下感知、體驗、想象、理解、談論此類事物的心理行為、語言行為和文化行為。
在電影當中,隱喻包含之處很多。16分06秒,三歲的小溥儀乳臭未干,坐在太和殿的龍椅上焦躁不安。這時溥儀的父親,攝政王載灃對他說道:“快完了,快完了。”此言一出,就暗示了清王朝最終的結局。短短三年之后,享國268年的清王朝被推翻了。
有意思的是,在后面的畫面中,溥儀和溥杰站上高墻,看到坐著小汽車的民國大總統,車旁邊居然跟著皇帝本人才能使用的華蓋。這里的鏡頭,則隱喻著走向“共和”的中華民國,行“共和”之名,卻名不副實,仍舊是封建帝王的排場和模樣。
在影片的97分25秒,溥儀的妻子之一,文繡在雨中丟掉了雨傘,說道:“我根本不需要這些!”雨傘在這里,則成為了文繡重獲自由的隱喻象征。在歷史上,文繡也成為中國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與皇帝辦理合法離婚手續的女性。這個故事,也讓文繡本人成為了新時代女性掙脫束縛和自由的代表。
經典之作為何可以使觀眾重復多次地觀看,除了明確的結構和優秀的內容之外,隱喻則是為電影增光添彩的重要手段。同時,隱喻的運用和解讀,也是電影是否經得起時間的淘洗和世人反復評價推敲的恒定因素,它使得電影更加富有意蘊,更加彰顯智慧的光芒。
五、矛盾對立
巧妙地使用矛盾的沖突對立,有助于電影的敘事過程的推進。《末代皇帝》不僅在敘事結構上采用了非線性敘事的手段,在矛盾沖突的設計上,它也是多線并舉,二元對立的。
(一)從微觀角度看
在電影當中,主人公溥儀的心理活動和周遭環境形成了非常鮮明的二元對立。32分49秒,當溥儀看到袁世凱的汽車從紫禁城耀武揚威地經過的時候,他從心里就意識到,這個國家和政權已經完全不屬于自己,溥儀也并不明白民國政府的《清室優待條件》對他有什么好處,只知道自己似乎終身會被這偌大的皇宮所圈禁;當馮玉祥的士兵沖進皇宮將正在打網球的溥儀趕出去之時,太監太妃的落寞和一旁狂喜的士兵又成了鮮明的對比;除此之外,學生和警察、溥儀的軟弱無奈和日本人的強硬,通過二元對立的形式,將溥儀本人的無助刻畫得入木三分。
(二)從宏觀角度看
一個故事的完整敘述,總體是處于一個“均衡”的狀態,即“開頭”“中間”以及結尾。為了故事不斷地向前推進,則需要打破均衡狀態,造成一定程度的失衡,再通過正面的反對力量進行解決,從而恢復均衡狀態。莊士敦,象征著西方現代文明的傳入,他的到來,讓溥儀對封建禮制和文化極度反感,甚至下令將自己的常用語言變為英文。從宏觀上來說,這其實是文化上的對壘和“失衡”。但是從另一面來看,在冰冷無情的皇宮當中,因為莊士敦的到來,溥儀感受到些許的溫暖和關懷,又將這一失衡拉回到了平衡的狀態。當溥儀正式成為偽滿洲國的“康德皇帝”之時,日本人后期對他的蔑視和侮辱將整個“失衡”的狀態達到了一種極點,戰后溥儀被押進了撫順戰犯管理所,監獄長讓他“用眼睛來觀察自己”,隨著時間的推移,溥儀逐漸完成了社會主義的思想改造,從溥儀的內心出發,他又是感激監獄長的,這再次將敘事推回到平衡的狀態。
六、結語
《末代皇帝》作為20世紀80年代最負盛名的關于中國題材的影片,通過多種富有技巧性非線性、非典型的敘事手法,將溥儀命運多舛,矛盾無奈的一生得以充分的展現,堪稱影像視覺藝術的典范。四千年的皇朝史,溥儀無奈地作為“句號”結束。任何人似乎都是歷史的過客,任何人隨著時間推移,無非是宇宙觀下宏大敘事的驚鴻一瞥。在命運的反抗斗爭中,有人成了勝利者,有人卻成了“悲劇演員”。總之,《末代皇帝》的探索和分析,時至今日,仍值得我們去探索和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