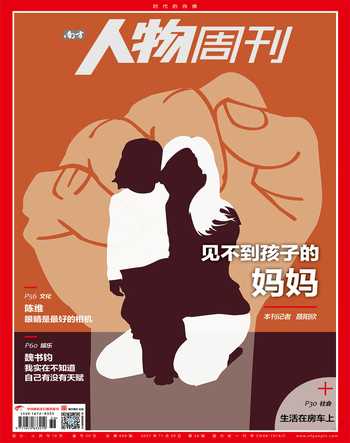一生棱角磨不平
鄧郁
1979年,袁運(yùn)生參加改革開放之初的國內(nèi)第一次大規(guī)模壁畫創(chuàng)作——首都機(jī)場壁畫繪制,他極為自然地選擇自己熟悉的潑水節(jié)故事,借助神話傳說與傣族人的真實(shí)生活面貌,呈現(xiàn)人性自由的美妙境界。據(jù)說壁畫出現(xiàn)后一個(gè)多月,首都機(jī)場門前的廣場上停滿了大巴,包括遠(yuǎn)道而來的藝術(shù)生,不僅是為欣賞壁畫本身,更想對傳得沸沸揚(yáng)揚(yáng)的畫中裸女一睹究竟。
《潑水節(jié)》令袁運(yùn)生達(dá)到前半生的名譽(yù)巔峰,也成了他一輩子擺脫不掉的標(biāo)簽。但他的藝術(shù)底蘊(yùn)、人格魅力與復(fù)雜性,其實(shí)早就逾越了這幅作品。
結(jié)合其時(shí)的社會(huì)背景和意識(shí)形態(tài)來看,袁運(yùn)生的出現(xiàn)以及命運(yùn)走向,既特殊,又典型。他身上有源源不斷噴薄而出的才華,敏感、執(zhí)拗,激情四溢,但在多個(gè)節(jié)點(diǎn)上和主流發(fā)生激烈碰撞:要么是眾人皆避“西方XX主義”時(shí)他大膽呈現(xiàn)自己汲取的營養(yǎng);要么是舉國開放后,他又開始倡導(dǎo)對傳統(tǒng)藝術(shù)造型的重視。不管是油畫還是水墨,抽象抑或?qū)憣?shí),還是晚年一心推動(dòng)的教育課題,不隨時(shí)而動(dòng),“言為心聲”,這是袁運(yùn)生。
做耄耋老人的采訪,總會(huì)遇到相似的困難:年事高,記憶力減退,敘事容易重復(fù)。如果帶著問題試圖還原一個(gè)個(gè)現(xiàn)場,很難得到細(xì)致而準(zhǔn)確的“拼圖”。于是只好通過大量的周邊采訪來實(shí)現(xiàn)。從袁運(yùn)生的央美時(shí)期,東北,云南,再到1996年回國后,每個(gè)階段都不難找到見證人。一圈采訪下來,一個(gè)高度自信又高度自覺的形象逐步清晰。
只有14年的美國旅居生涯這段,有些遺憾。我很想了解,他在美國的若干年,如何面對創(chuàng)作語言的突破、文化沖突、與西方藝術(shù)圈之間可能存在的“隔膜”、生活的窘境,以及能否順利歸國的糾結(jié)等等。遠(yuǎn)隔千山萬水,袁運(yùn)生的心緒與藝術(shù)思考很難有暢通的出口,外界對他抱有的期待與想象,也與他本人大相徑庭。
兩次采訪袁運(yùn)生,他最感懷和愿意聊的話題,一是恩師董希文,一是他的“中國傳統(tǒng)雕塑的復(fù)制與重建當(dāng)代中國美術(shù)教育體系”課題。這兩者延綿下來,正是一種精神上的傳承與延續(xù)。
他說,1960年代以后,許多人去研究中國古代和民間藝術(shù),發(fā)現(xiàn)也希望那里有一座橋梁,可以名正言順地通向現(xiàn)代藝術(shù)之路。敦煌藝術(shù)大廣為人們所稱道,像董希文先生以實(shí)踐去追索這條崎嶇而又充滿吸引力的道路的人并不多。
到了1996年回國之后,他更感慨,西化的觀念、方法、審美趣味“統(tǒng)治”日久,國人已經(jīng)很難意識(shí)和欣賞到自己的藝術(shù)根源。他希望沿著董希文的路繼續(xù)生發(fā),改變以央美為首的傳統(tǒng)高等教育體系,但卻更像“一個(gè)人的戰(zhàn)斗”。不喜他挑戰(zhàn)既有框架的,或者同意其觀點(diǎn)、但認(rèn)為他欠缺溝通和執(zhí)行之道的,比比皆是。即便他申請到了國家的專項(xiàng)資金,本人知名度也高,卻很難調(diào)動(dòng)足夠的資源來推進(jìn)這件他認(rèn)為最急迫、最有意義的工作。
“好好地畫畫不是更好?袁先生藝術(shù)上絕對還會(huì)有更高成就。干嘛非得往這個(gè)泥潭里扎?”說這話的不乏其人。
而這大抵才是袁運(yùn)生之所以成為袁運(yùn)生的最寶貴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