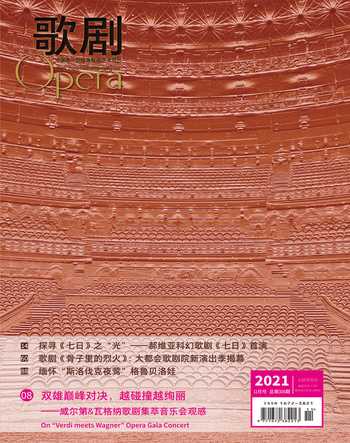平淡中的《張富清》
蔣力

10月23日,山東省會大劇院,觀中國歌劇舞劇院的《張富清》。方石作曲,文新國編劇,朱亞林、李世博導演,劉新禹指揮。毋攀、王一鳳主演。
我在看戲時,想到蘇東坡的一句話:燦爛至極,歸于平淡。(“至”字多寫為“之”,我更喜歡“至”。)
張富清的燦爛,主要燦爛在戰場上,那是青春的燦爛。隨著他的復員轉業,平淡幾乎隨之而至。可以說,他在平淡中度過了大半生,但他創造了平淡、平凡中的燦爛。這是更加感人的燦爛。
也許是受了張富清其人其事的啟發,這部歌劇大膽采用了音樂會歌劇這種更接近平淡的形式。這樣的呈現,與它所表現、謳歌的這個老兵、這位共和國的功臣是十分吻合的。音樂會歌劇《張富清》的成功,包括了它的感人度和可信度。當然,感人度中也包括了“可信”。說實話,直到看戲之前,我對這個題材、這種表現樣式,都是抱遲疑態度的。觀后,我的看法發生了陡變,音樂會歌劇《張富清》足以讓我們相信、確信:中國歌劇,既可以有燦爛的一類,也可以有平淡的一類。看似平淡的這一類,照樣可以表現出燦爛的一面。當然,這類歌劇對作者、創造者們的要求,并不低于燦爛類歌劇的創造者們,甚至要求更高。
之所以成功,我認為有三點至為重要。一是編劇文新國與作曲方石兩位湖北同鄉,長年搭檔的默契配合,最大限度地減少、避免了一度創作環節的內耗,語言和音樂都盡可能地運用了湖北的民間元素,為其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是毋攀對“張富清”舞臺形象的成功塑造。他很注意細節的表演,如:開場時對自己那只搪瓷杯子的愛護,瞬息即過,他卻認真地處理。面對副縣長的斥責、施壓,他帶著堅定信念的輕聲答復,耐品耐回味,從而令人信服。
三是職業化的樂隊和指揮。樂隊在臺上,指揮在臺上,一覽無遺。我算了一下,十年里不經意間,我已看過劉新禹指揮的多部歌劇:《青春之歌》《松毛嶺之戀》《辛夷公主》,直到這次的《張富清》,其間或許還有,這次印象最深。站在臺上,他很注意收斂,很多時間左臂都不動,去表演化的意識、去自我陶醉的意識都很強,更強的是他對樂隊的掌控力。
樂隊首席是我的老同事曹歡,這些年我四處觀摩歌劇,不止一次發現曹歡坐在樂池里的首席位置上,雖是客座,他仍極盡主人的職責。幾年前,曹歡轉入中國歌劇舞劇院,任樂團首席,對樂團整體的技藝提高起了重要作用。今觀《張富清》,樂隊因在臺上,不能不引人多予以關注。作曲家溫中甲說:跟十年前相比,變化太大了!十年前,恰逢首屆中國歌劇節,中國歌劇舞劇院只有《紅河谷》一部劇目參演(另有一臺歌劇GALA);這次,該院的參演劇目多達四部:《白毛女》《小二黑結婚》《江姐》《張富清》——了得了得了不得!
幾點不成熟的看法,不成建議,僅供參考。

張富清和老年張富清的第一個高音,不要出現得那么早,早到他們各自的第一個唱段。固然,兩個高音唱出來后,都有掌聲,也就是說有現場效果。但是,這個效果只是聲樂的,不是歌劇的,也不是人物的。
老年張富清的敬禮,從面對三五九旅的軍人,到面向觀眾,持續的時間雖長,顫抖的頻率卻不宜過密,微微顫抖與長時間的顫抖,達到的效果一定不一樣,建議導演與演員一起再切磋。
“張富清”這個角色,是由張富清、戰士張富清和老年張富清三個男高音共同完成的。老年張富清是否可以調換聲部,改為男中音?現在由男高音扮演,聲音中缺少蒼老感。如改為男中音,仍然重復一些毋攀飾演的那個張富清(男高音)懷念戰友唱段的旋律,會因聲部的改變而增加厚度。
合唱的聲音偏美,少變化,唱的是歌頌或敘事的不同內容,聲音卻沒有變化,旁觀感太強,戲劇感有欠。這主要該是合唱指揮的責任。

村民們張傘為張富清送行那段,燈光打在傘上,很搶眼,略感奪戲。我期待看到一條由傘湊成的廊橋式的傘棚,由疏至密,漸漸在斜坡上形成。短時間里,張富清一家四人都隱沒在傘棚下,而后在傘棚的那端出現,告別。
多媒體影像中的圖片,尤其是歷史圖片,如:報功書、立功登記表、解放大西北人民功臣獎章等,盡量完整地、多一點時間地展現,以造成更強的視覺沖擊力。
謝幕處理建議增加張富清、老年張富清、戰士張富清三位“張富清”扮演者單獨謝幕的環節。
節目單。建議將首頁(劇院簡介)移至最后,劇情簡介頁的六幅劇照與分幕介紹各自對應,或擇一幅放大,以突出本劇而不是本院的分量。
本以為謝幕時能見到文新國和方石,未料,23日那天從始至終都未看見。經微信聯系,二位分別給我發來劇本(第十稿)和以“用音樂為老兵塑像”為題的創作談。不止一次地通讀之后,我必須承認,在觀劇中我忽略或印象不清的一些地方,在這里得到了強化認識和感知。如:第一場,年輕的張富清與四個伙伴(后來都是他的戰友)在山坡放羊時唱的《放羊嘹得很》(意即“好得很”),因用了陜西口語,編劇就提示這里應是秦腔起句的男聲表演唱。這段演唱的旋律很快就再次出現,不同的是換了唱詞,成了《當兵嘹得很》。又如:富清娘唱的《五更響》,是陜南民謠,陜南是張富清的家鄉,這樣的選擇非常貼切。富清娘去世后的閃回戲,《五更響》旋律再起,唱詞有變,母子之情得到進一步的升華。再如:張富清的愛人孫玉蘭唱的《葵花花》,也是陜南民歌,兩次出現,表現了他們的夫妻情。全劇的結尾,落在張富清對70年前永豐大血戰的沉痛回憶、對戰友們的深情回憶、向他們致敬的軍禮中,又一次表現了戰友情。他的信念,他的人格魅力,也由此得到極大的凸顯。
方石的創作談中,強調了四個“把握”,一是把握歌劇的質感,二是把握本劇的骨感,三是把握人物的情感,四是把握音樂的美感。他認為,“骨感”方面,一是把握好音樂語言,二是把握好地域特色。依據張富清的身份,為其定位的音樂語言,一是單純、質樸、接地氣的基調,二是彰顯陽剛、豪爽、執著的軍人本色,三是對黨和國家的赤膽忠心,對戰友、百姓、親人的俠骨柔情。因此,他也對唱詞的寫作提出了基本要求:盡量口語化,盡量不用形容詞;思想要深入,語言要淺出。
張富清的主要生活環境,一是大西北,包括他的家鄉陜南漢中,二是鄂西。陜南民歌《花鼓調》和鄂西來鳳縣的土家族民歌《直嘎多里嘎多》成了方石主要選用的音調元素。幾年前,方石參考土豆食法,摸索出一種“土豆寫法”,包括:塊狀式、嵌入式、整合式、包裝式等。其本質就是利用各種手段有效整合民歌這個“土豆”,形狀可變,本色與味道不能變質。他的“土豆寫法”,在本劇中得到了得心應手的運用。音樂情緒上,力求準確、得當、豐滿、統一,要將張富清極具個性的情狀揭示、表現出來,從而呈現出鮮明的音樂形象。
在真善美和旋律美的前提下,方石采用了混搭、混融、混血的手段,嘗試營造了部隊與地方、陜南與鄂西、親情與友情、忠臣與孝子、凡人與英雄及宣敘與詠嘆、土調與洋腔、人聲與樂隊的混合狀態。這應當是音樂會歌劇《張富清》貌似平淡、實則并不平淡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