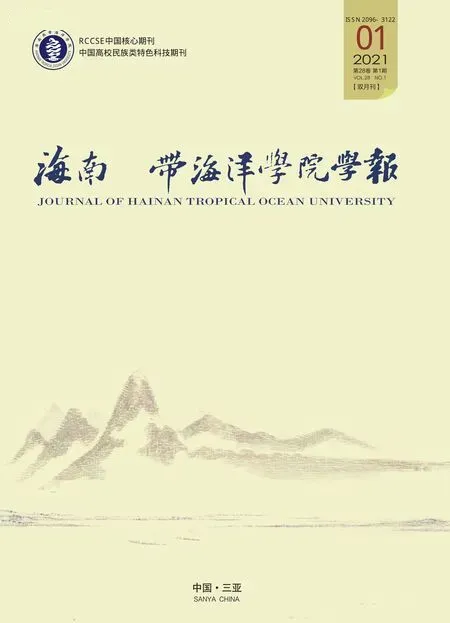民國時期關于南海諸島問題的社會輿論
劉玉山
(溫州醫科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浙江 溫州 325035)
中國人民在南海活動已超過2 000年,南海諸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神圣領土。中國人民最早發現、命名和利用南海諸島及相關海域,最早并持續、和平、有效地對南海諸島及相關海域行使主權和管轄,確立了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相關權益。目前學界對民國時期南海諸島問題的研究成果豐富,但多從國民政府的視角進行論證,關于民間社會輿論對維護南海諸島貢獻的文章卻不多見。事實上,民國時期中國民間對維護南海諸島主權參與的人員眾多,有引入最新國際法原理進行理論論證的,也有進行著書撰述的,也有繪制地圖進行位置確認的,更有就南海問題而生發出的一系列中國邊疆危機乃至中華民族危機預警的。這些都是為維護國家領土主權所做出的努力,其精神不僅為后世所學習,其所保留的各種撰述也為我們打贏南海問題“信息戰”提供了第一手的歷史證據。
一、 關于南海諸島問題社會輿論的特點
民國時期關注南海諸島問題的社會輿論構成繁多,政商學界都有參與;所依托發聲的載體有教科書、期刊與報刊等,而且在時間分布上也呈現一定的規律。
(一)參與人員的構成
參與人員的社會構成有知名專家、知識分子群體,如著名地理學家張其昀、我國現代人工珍珠養殖創始人熊大仁、地理學教授王光瑋和冼榮熙、著名地層古生物學家穆恩之和李毓英、地質學家席連之、圖書館學家袁同禮等。介入的媒體,如北平時事日報社、《申報》和《大公報》等主流媒體。有政府官員如前清官員李準、前國民政府鐵道部部長葉恭綽、廣東省地方官員黃強等。有各級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如國民黨省、市、縣黨部如河南省、寧夏省、汕頭市、寧洱縣、蕭山縣、皋蘭縣、紫金縣、會同縣、安仁縣、儋縣、楚雄縣、安鄉縣、文昌縣、大定縣、中山縣、上海法租界納稅華人會、上海市總工會、上海市商會、寧波市商會、中華海員上海黨部等。此外還有大量的愛國學生乃至高中生,如后來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外交工作的俞沛文等。
總體來看,民間參與論述的“陣容”沒有二戰后參與琉球論述的知名人士多、波及范圍廣。這也可以理解,琉球論述是二戰后伴隨著國民政府因應對日和約而產生的,未來的對日和會的核心議題之一就是琉球歸屬問題,所以在社會力量的資源動員方面,肯定是吸引了與之相關的各方面專家的“協同會診”,有官方的積極推動因素在里面,而南海論述由于時間跨度更長,大致有1933和1947年兩個高潮(下文會有比較)階段,雖然社會關注度不低,但并沒有國民政府的積極推動,因而總體來看,專業人士參與相對較少。
(二)民間社會輿論參與的載體
首先,教科書。如林紓1913年《重訂中學國文讀本》、王鈞衡1933年《初中本國地理教科書》、張其昀1935年《本國地理》、江蘇省教育廳編1936年《小學教師文庫?第一輯(下)》、葛綏成1945年《新編高中本國地理》等。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江蘇省教育廳在編寫的小學各學科教材指針中,特別將南海九小島列為“社會科學臨時教學事項”[1]。
其次,學術性期刊。如《邊事研究》《邊疆》《國立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年報》《國立中央大學農學院旬刊》《地理學季刊》《國立中山大學校報》等。
再次,專業性質的期刊。如《水產月刊》《氣象年報》《上海市水產經濟月刊》《農聲》《廣東農村月報》《土壤》《農報》等。還有海事方面的報章雜志,如《中國海軍》《海軍雜志》《海軍公報》《海事(天津)》《海事(武昌)》《海事(臺北)》《海事(天津)》《航業月刊》等。
最后,國內大報刊如《申報》《大公報》給予持續關注。國內報刊輿論的記載,完整地記錄了我國政府機關、各行各業對南海諸島行使管轄權的過程,這就構成了國際法上證據鏈的完整性,這些社會輿論資料與政府如外交部門所保存的檔案資料一起構成了南海諸島屬于中國的充分證據鏈。
(三)時間分布特點
可以發現,我國新聞輿論界在歷次南海諸島危機事件中都不缺席,為探尋南海諸島屬于中國在資料搜集方面做足了功課,責無旁貸地完成了報道事實真相的任務。通過比對發現,社會輿論對南海諸島的關注有兩個時間段較為集中,一個是30年代初,尤其是1933年,占全部的近三分之一。第二個是二戰后,尤其是1947年,接近全部的五分之一。出現這兩個高潮的原因也顯而易見,1933年正是法國政府炮制“南海九小島”事件的年份。1946年底,國民政府派遣軍艦分別進駐西沙武德島(改名永興島)和團沙(今南沙群島)之長島(改名太平島),緊接著1947年面臨占領西沙、南沙其他附屬島嶼及公布收復范圍諸問題,同時本年還發生了法占西沙白托島(珊瑚島),國民政府與之外交折沖之事件,因而1947年也成為社會輿論關注南海諸島問題的又一高潮年份。
二、 關于南海諸島問題社會輿論的主要內容
社會輿論對南海諸島主權維護的表現形式是多樣的,面對法國侵占“南海九小島”的惡行,曾在清末帶兵巡閱南海諸島的李準拍案而起,向主流媒體《大公報》投書,從而昭告天下。還有很多人翻譯當時的國際法最新著作,或對南海諸島主權屬于中國進行理論撰述,表現出了民間輿論的集體智慧與敏銳性。
(一)《李準巡海記》在《大公報》發表
1933年4月,法國乘中國內憂外患,占領了中國南海的九座島嶼,這就是“南海九小島事件”。國民政府一籌莫展,對“九小島”的名稱、地理經緯度、歷史沿革皆無概念,以至于“舉國濁濁,無一能道其真相者”[2]。針對這種情況,寓居在天津的清末廣東水師提督李準拍案而起,向天津《大公報》投稿,將他于1909年率領170余人的“琛航”和“伏波”二艦,對我國南海諸島進行考察,探明島嶼15個[3],并用隨行人員的籍貫進行命名,有效宣示了中國政府對南海的主權,符合國際法程序。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中日東沙島紛爭出現,李準“親巡其地、鳴炮升旗、勒石命名,并測繪地圖,作巡海記事”[4],擊破了日本人的東沙島為“無主荒地”之狡辯,日本被迫退出東沙島。《李準巡海記》在《大公報》發表后,各大報刊爭相轉載,比如《申報》1933年8月15—16日兩天以“特刊”的形式連載《李準巡海記》。《大中國周報》1933年第3卷第8期、《珊瑚》1933年第3卷第6期、《中央周報》1933年第273期、《國際現象畫報》1933年第2卷第9期、《新世界》1933年第34期、《國民外交雜志(南京)》1933年第2卷第5期、《國聞周報》1933年8月21日第十卷第33期在《李準巡海記》的基礎上又補充了李準所撰的《東沙島》。實際上,李準就南海諸島撰寫的文章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就是上文提到的《東沙島》,而另一部分則是各大報刊所轉載的《李準巡海記》,而《李準巡海記》的原名叫《西沙島》,是為第二部分,將這兩部分文章拼接在一起才算完整。
(二)出版專著或譯著,論證南海諸島主權在我
專著如鄭資約1947的《南海諸島地理志略》、馮承鈞1936 年的《中國南洋交通史》、凌純聲1934年的《中國今日之邊疆問題》、楊秀靖1948 年的《海軍進駐后之南海諸島》等。其中《南海諸島地理志略》還有人做了書評。資料匯編類如陳天錫《西沙島成案匯編》、杜定友《東西南沙群島資料目錄》等。
翻譯如胡煥庸譯《法人謀占西沙群島》、黃莫京譯《西沙群島》、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續編》和《昆侖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何健民譯《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馮攸譯《唐宋元時代中西通商史》等。
報紙雜志及時登載日本國際法學家橫田喜三郎有關“先占”著述和其他日本學者相關文章。日本著名國際法學家橫田喜三郎在“九小島事件”發生后給予了關注,并撰寫了論文《無人島先占論》。當時我國的部分報刊及時進行了翻譯轉載,如《南方雜志(南寧)》1933年第2卷第8期、《國際美日文選》1933年第58期、《中央時事周報》1933年第2卷第38、39期分上、下連載。值得注意的是,這三種雜志發表的《無人島先占論》分別由梁佐燊、易野、何鼎三人各自獨立翻譯,可見當時的社會輿論對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重視,知識階層不遑多讓,利用自身的文化優勢積極貢獻心智。
根據當時的國際法,橫田[5]8在《無人島先占論》中提出了符合先占的四個要件:土地是無主的土地;國家自身占有這土地;占有是實效的;通知其他的國家。基于此,日本所謂在該數島嶼曾有拉薩磷礦公司的開采、日本學者在那里研究過地震等“都只是錯誤的與國際法上的先占毫無關系的事實”[5]2。《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規定,法院對于陳訴各項爭端,應依國際法裁判之,各國權威最高之公法學家學說,作為確定法律原則之補助資料者裁判時應適用。當日本政府“突兀”地卷入中法“九小島”爭端時,其國內國際法權威立刻進行“學說”撰述進行反駁,這應視為日本“先占說”不成立之有力證據。
1931年“克利珀頓島(Clipperton Island)仲裁案”為“南海九小島”爭端提供了現時的極好的案例。該島1855年被法國占領,次年美國立法列為國土,1897—1917年為墨西哥軍隊占領并駐守。作為仲裁官的意大利國王維克托·伊曼紐爾三世1931年1月28日在羅馬做出裁決,他認為:“克利帕倘(克利珀頓)島,乃法蘭西于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為法蘭西所正當先占,法蘭西于其后并無可以認其有拋棄權利而喪失其權利之根據,而且并未嘗有欲拋棄該島之意思,所謂法蘭西未嘗積極地行使其權力之事實,可不惹起既確定的完成取得之失效。依此等理故,予為仲裁裁判官,對于克利帕倘島之主權決定為從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已屬于法蘭西。”[6]張覺生將橫田喜三郎論文中的這段判決結果做了翻譯,登載在國內報刊。
日人金子二郎發表在《外交時報》1933年第67卷第5號有關“九小島”的文章也被新聞媒體第一時間翻譯介紹給國人。翻譯者楊祖詒“譯出以供國人參考,亦以覘日本之野心”[7]11,該文為日本張目,認為“至今尚留有足跡,不問問題之歸結如何,僅此亦足為日本同胞之榮”[7]13。可謂強詞奪理到極致。不過該文的直接矛頭對準了法國,認為“法國對該島嶼毫無實跡,僅為夢里世界之占領手續,頗使吾人難以諒解”[7]13。這篇譯文一方面讓國人看透了日本人對我領土的覬覦,另一方面戳到了法方的“痛處”,即法方雖然“形式上”似乎完成了當時國際法意義上的“先占”,實質上卻構不成國際法“先占”要件。
(三)撰寫論文,多視角闡釋南海諸島主權在我
1.針對“南海九小島”事件的論證
(1)強調“九小島”的軍事價值
蔣震華認為“從地理上分析,南洋九小島,真可說是太平洋上航路的樞紐。我們看,無論自菲律賓至夏威夷,香港至新加坡,或者日本海岸至歐美各國,廣州灣至西貢的船只,航輪往返都必經過這個地方。這一地帶對于海軍關系之重要,尤其他在太平洋均勢局面之下將發生很大的作用的重大性,我們可想而知了”[8]13。張靜民認為“九小島介于太平印度兩洋亞澳兩陸之中,東控菲律賓,南制婆羅洲,西達南洋群島,北逼安南兩越,誠交通便利,東亞之要地也。若加以嚴密之建設,巽日面積擴大,以之為工,則原料四集,源源而來。制品暢銷,無所不知,以之為軍,則軍港機站無所不適,故是地若終為法所有,法人筑之,則大赫的島與安南聯成一線,非特太平洋之勢力,不為日美英之所獨有,即日之臺灣及代管德屬太平洋諸島亦有被脅之勢,至我中華,則更無論矣”[9]13。靜植認為,法國又多了一項根據地,“不特西沙群島全部隨時有危殆的可能,即瓊崖海疆也大感威脅”[2]。有人拿九小島比作德國黑爾戈蘭島(Helgoland),歐戰前卻是該國重要的海軍基地;本太平洋委任統治地被視為海上重要的生命線;南極圈內各荒島,英法挪各國爭奪激烈[10]16。
(2)論述先占與時效
1933年“南海九小島”事件發生后,社會輿論已經開始充分利用最新的國際法“先占”概念對法、日的無理證據進行批駁。王英生提出國際法“先占”必須具備的四個要件:被占的土地必須是無主的土地;國家占領;有實力的占領;必須通知其他國家。即使日本最先發現“九小島”,但這純屬私人發現,“若要先占成立,則日本政府必須于斯人發現華南九島后,立即樹立權力,而作有實效的占領,然而日本政府并未在華南九島樹立任何權力”[11]5,針對日本人可能辯解的“九小島”是無人居住的荒島,沒有設官駐軍的必要,王認為“就是在這種特殊的情形下,亦需在其鄰近毗連的土地上設置官吏,駐扎軍隊,以謀對于華南九島得意行使監視和保護。但是日本屬地的臺灣距華南九島有七百五十海里之遙,不能說是與華南九島毗連,更不能說日本能以臺灣為根據地,對于華南九島行使權力”[11]6。王敬熙從先占和時效兩個相關聯的國際法理出發認為,明末清初,鄭成功舉事不成,即入此土,清政府也派遣官吏置守,屬瓊崖管轄,華人往來打魚者甚多,依時效言“實為中國所有,即依先占言,亦不虞他人之責言”[12]。錢彤對于時效的時間斷限考證最具學術價值,他認為,“我們知道隨便占領并不是一樁合法的事,日本公法學者江木翼認為‘如此無所屬土地之經營,除取事實上殖民地占領之形勢外,全無適法之形式。’又雖在國法時效之規定,有一定之年限,而國際法則無之;但在一八九七年二月二日英委條約,其第四款中所云‘對方領有,經過五十年,視為合法諸語尚不失為一種有限制之先例’;又公法家斐爾黎亦曾主張以二十五年為期,無論時期為長為短,有人出而辨正,就應終止侵占,此卻也是國際應有之美德。日調查諸島,固已發現了有我國人在島;法四月六日有軍艦至斯巴得來,亦見有華人居住在島”[10]17,錢提出“國人皆應迅速收集證據,調查事實,準備抗爭,謀所以防止列強瓜分中國事實之擴大了”[10]17。
(3)保留了大量的南海九小島位置地圖
1933年第1卷第1期《江蘇省小學教師半月刊》[13]、1933年《南海九小島位置圖》[14]、1933年《南海九小島位置圖》[15]、后來成長為我黨優秀外交官的俞沛文在1933年手繪的《南海九小島圖》[16]、1937年《中華省市地方新圖》[17]等都非常精準地將“南海九小島”位置標示出來。聯想到1947年前后,國民政府為團沙群島(今南沙群島)、日人命名的新南群島之間的關系而一籌莫展,殊不知,30年代的很多輿圖都已經將南海諸島的位置標識出來,至少資料來源上絕對是豐富的。同時,白紙黑字,也為南海諸島屬于中國提供了國際法地圖上的證據,現實價值重大。
(4)從國際關系角度論述南海九小島之重要戰略地位
胡墨宣從國際關系的角度論述“九小島”事件時認為,現在的中國與1850年的意大利相似,意大利在完成統一的過程中,“沒有打過勝仗,而且參加普奧戰爭是弄得全軍覆沒的,但實際的勝利卻屬于打敗仗的人,意大利就在打敗仗的聲中一天天健全,統一起來,這無他,由于能利用別人的拳腳而已。”中國怎么做呢?中國可以“照樣葫蘆地做”,“有賴由我主動地促成并參加鷸蚌相爭以收漁翁之利的原則,即欲中華民族掙脫次殖民地的厄運,也是舍此別無他法。”[18]
梁庭棟從中日法三角關系出發認為,南海九小島為西沙群島之屏障,我西南海防之第一道防線,“今一旦為法人所領,則廣州灣以南之海南島受其包圍,攻之取之,惟其所欲,而侵滇之滇越鐵道,得一助手矣;倘為日人所有,則其在太平洋之勢力,猛烈增加,我國過去受其侵略,雖失滿洲,猶曰江南一隅可守。茲后如其大陸海洋,兩策并進,吾人恐無立錐之地矣,觀此知可九小島實為我國之生命保存地也”[19]。
2.闡述中國人最早發現、利用南海諸島,并有充分的統治痕跡
中山大學地理系教授王光瑋從歷史學的視角將中國人民在南海諸島棲息、生存的歷史脈絡做了系統介紹,并且從國際法的角度闡述了中國人最早發現、利用南海諸島,并且已經行使了主權,如1883年德國政府派員測量該諸島,經清政府嚴重抗議而罷,“是我國在南沙群島行使主權之充分表示,亦即通告各國當尊重在南沙群島之主權”[20]。1932年我國西南政委會對華南三年建設計劃,亦規定開發南沙群島,“又有實施統治權之表示,此非我之領土而何”[20]。王的這篇文章還被1948年葉恭綽主編的《廣東文物》[21]收錄。
3.關于公海與領海事實之辯
20世紀30年代日本經常有人在東沙島附近灘嶼采集海人草,針對日人所謂“系在公海,而非在中國公海”[22],梁朝威經過大量的國際法案例比對,認為“所謂公海者,宜從距離海岸最遠之灘嶼往外量算,三英里以外之海面,然后可以謂之為公海,若在三英里以內之海面,則為中國之領海也。此一群灘嶼在水漲時,雖有被海水淹沒,然于潮水落時,則露出于水面,故自以潮落時露出水面之灘嶼量起,以決定三英里領海之寬度焉”[22]。基于此,日人“若在東沙島附近灘嶼三里以內之海面耶?則亦顯然地為在中國領海私采。若在距離海岸最遠之灘嶼三英里以外之海面,然后可以謂之為在公海采集”[22]。
1946年8月4日和5日上海《大公報》連載曾達葆的文章《新南群島是我們的!》,該文章論證縝密,證據確鑿,各個島嶼的名稱都位列其中,讓人感嘆文章作者背后做了很多調查研究工作。作者給出的新南群島的位置在“臺灣省高雄市南南西約七百五十里處,當南中國海之中央偏南。正在西沙群島、菲律賓、婆羅洲和交趾半島的中間。群島的水域面積約七萬五千六百平方浬,介于北緯七度至十二度,東經一百十七度至一百十四度的海上。這些群島是十三個大小不同的島嶼組成的,各島的面積都很狹小,其中以長島的面積比較大些,但其周圍亦不過二千八百公尺。”文章還稱,根據昭和八年(民國二十二年)九月號的《世界知識》,日人福島丈雄的記錄,這十三個島嶼有日人所定的名稱和英文。這兩篇文章并附有新南群島位置形勢圖、新南群島主要島嶼分布圖,通過對比二圖,可以發現該文章所稱的新南群島就是當時的團沙群島(即今天的南沙群島)之一部分。這篇文章可謂來得及時,作為剪報,至今仍夾在《外交部檔案》中。
三、 關于南海諸島問題社會輿論的歷史評價
民間輿論對南海諸島主權的維護所留下來的撰述,保留了大量歷史證據,在今天看來,這些社會輿論不僅討論的問題有一定的理論深度,最關鍵的是,社會輿論往往其敏銳度或者說“先知先覺”于政府,而官民之間也沒有形成一定的良性互動和溝通交流模式,更不用說達成一定的默契,這是一大遺憾。
(一)保存了南海諸島主權在我的歷史文獻證據
國與國之間要想在領土爭端中占據有利的地位,大面積搜集、整理和研判自身及對方的“證據鏈”非常重要。這種“證據鏈”必須豐富、完整和具有系統性,形成一定的“證據鏈”閉合。南海諸島是中國人民最先發現、命名和利用的,根據近代以前國際法“誰發現誰擁有”的原則,中國已經擁有了南海諸島的主權。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大國及周邊國家的介入,近代以來南海問題日趨復雜化,將原先并不存在爭端的島嶼問題演化成國際“爭端”。這種情況下加強自身原始檔案、歷史文獻資料的搜集與整理就迫在眉睫了。民國時期中國民間社會輿論蘊藏了豐富的歷史文獻證據,這些證據是中國人民自發在第一時間維護祖國領土完整、維護中國南海領土主權所做出的努力和貢獻,構成了南海諸島主權屬于中國的原始歷史文獻證據鏈重要的組成部分,誠如郭淵所言:“為后來中國政府的維權奠定了基礎。”[23]
(二)社會輿論“先知先覺”,惜官民之間未形成合力
1933年“南海九小島事件”后,大家普遍覺得“交涉起后,我國方面很有臨事慌張的情形”[1],從1934年出版的1933年度《中國外交年鑒》專辟“法國占領九小島之交涉”一節,然從論述看頗為吃力,甚至有“(九小島)并非西沙群島,亦無從證明系我國之領土也”[24]之結論,這就頗讓人感覺意外。1933年7月15日法占九小島后,日本反而最先提出抗議,甚至連日本民間都開始行動起來[15]7。又比如針對1933年國民政府對于“南海九小島”昧暗無知,張覺生不僅及時翻譯了日人關于“先占”的最新國際法案例,而且極力提倡成立邊政機構,在張看來“(吾)于民元以前民元以后,曾屢上書政府當道,請設墾殖部以重邊政,不幸頻年國內多故,當局無暇及此,至今未見實行,今政府已有見及,深望此早日成立,并于部中設置移民屯墾及界務諸廳,急起直追,鞏固配實邊防,則誠大局之幸也”[7]94-95。《申報》1933年7月15日即以《法國占據太平洋島嶼:向為我國漁民居住地》為題,提出“西貢與菲律賓間有小島九座,住于北緯十度,東經一百十五度左右,向為中國漁民獨自居住停留之所,頃據西貢電,現有法差遣小輪亞勒特與阿斯特羅勒白兩船,忽往該島樹立法國旗,要求為法國所有”[25]。而有人造訪南京外交部探尋國民政府之因應對策,外交部則“尚未接到正式報告,僅于報端閱及”[25]情報訊息之滯后可想而知。
事實上,如全文所述,民間輿論(也包括低級官員乃至極少數高官)已經就南海諸島從各個方面全方位做了深入研究,這些成果就刻印在著作中或期刊里,但外交部似乎并沒有留意。歷史有著驚人相似,1946年外交部在為日人所謂“新南群島”究與團沙群島是何關系而焦慮時,殊不知在1933年南海九小島事件之時,已經有很多文章提到了“新南群島”,如1933年顧秉麟《成為問題的南海九小島》對日人福島丈雄所作“新南群島事情”所述11島之英文名稱、面積等數據都有摘錄。1933年《九小島實況:遠眺九小島之一:[照片]》、1933年錢彤《九小島事件》、1933年俞沛文《中國南海九小島問題(附地圖)》、1938年干城《日本占據新南群島與遠東局勢》[26]等都有記載,雖然筆者翻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外交部檔案時看到外交部檔案中保留有剪裁的1946年8月4日和5日上海《大公報》連載曾達葆的文章《新南群島是我們的!》(上、下),曾文也提到了十幾年前福島關于新南群島的論述,顯然外交部對于十幾年前的民間論述甚少關注,而僅及于眼前。
民間輿論力量蘊藏了強大的理論力量、民意力量,但南京國民政府并沒有有效利用和善待這些民間力量及其研究成果,官方與民間難以形成合力,這的確留給我們深刻的教訓。與強勢的官方話語體相比,民間社會輿論是處于劣勢,這就更需要政府善待。帶有民間和自發性質的民間輿論先于政府“先知先覺”,希望政府善待民間輿論,重視來自底層的社會體驗。帶有民間和自發性質的民間輿論是公民社會唯一能與強大的公權力對峙的力量源泉。只有二者在一定層次上協調、對話、平等地發出聲音,才能有效地形成合力維護國家領土主權。
(三)參與面廣,尤其是學生階層也廣泛參與
如1936年衡湘學校高二班張靜民、卄六班汪敬熙、梁庭棟等從歷史沿革、國際法先占與時效、中日法三角關系等角度對南沙群島屬于中國做了學術價值較高的論述,理論運用之強,似乎超出了學生階層的認知范圍,反映了他們“事事關心”,對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認真準備資料的愛國主義精神。這也給我們提供一定的經驗,即加強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邊疆歷史文化教育等,一方面可以增強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操,另一方面也可以塑造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通過本文對民國時期民間輿論對南海問題的關注,愛國主義教育從小抓起,堅持不懈,迫在眉睫。
結 語
本文對民國時期中國民間社會輿論對南海問題關注群體的構成、載體與時間分布和社會輿論對維護南海諸島主權所做出的貢獻等做了深入的論析,“尤其是民國學者在九小島事件后對南沙漁民和地理景觀進行了歷史場景的敘述和勾勒,為深入研究南沙歷史保留了珍貴資料”[27]。誠如本文第三大部分談到的,民間輿論對于南海問題的關注與撰述其實非常豐富且具有一定的深度,但這些研究成果或行動如何能夠為政府所熟知,并與政府間達成一定的合作,從而形成全民族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合力。很可惜,國民政府都沒有有效利用這一點,誠為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