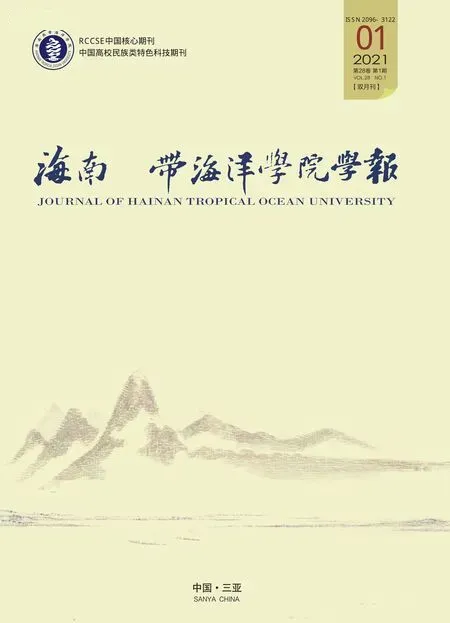古典詩詞英譯中的情感效度
謝艷明,范 咪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外國語學院,武漢 430073)
情感是詩歌的靈魂。詩歌之所以能有“驚天地,泣鬼神”的藝術魅力,就是因為其中飽含濃重的感情色彩。盡管中國詩學的開山綱領是“詩言志”,但它并沒有將中國的詩詞引向純粹的理性說教,而是側重于情感的書寫。《毛詩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63中國的詩詞是“情動于中而形于言”的結果,“情”是其中重要的元素。魏晉文論家陸機在《文賦》提出“詩緣情而綺靡”[1]171的觀點。鐘嶸的《詩品》開篇就強調“情”:“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行諸舞詠……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2]15在中國詩詞中,“志”是情感的儀式化和儀式表達,“詩言志”論也是關于情感問題的理論[3]。“詩歌由于用語言來建立情感的秩序和情境,就有了某種固定情感的力量——能再現詩人依附在感性事物和清晰觀念上的情感。感情不僅作為一種動力,存在于詩的孕育和創造過程,它還是詩的直接表現對象。”[4]中國古代是沒有寫詩這個職業的,詩人們寫詩也并不是為了謀生。他們為什么要寫詩呢?很多時候詩人們有感于情,有結于心,以至于不得不抒發出來。清代學者況周頤在《蕙風詞話》中說:“吾聽風雨,吾覽江山,常覺風雨江山之外,有萬不得已者在。此萬不得已者,即詞心也。”[5]10況周頤的“萬不得已者”就是華茲華斯所說的“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6]。既然情感是詩詞的生命,在翻譯時就必須突出情感的表達,要使得譯文像原文一樣在讀者的心靈中產生情感的共鳴。根據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數據庫的檢索,有關詩歌情感研究的論文超過52篇,有關詩歌翻譯的論文多達637篇,然而研究詩歌情感翻譯的論文為零。不僅這方面的研究存在嚴重不足的現象,而且許多詩詞譯者過于注重語言形式,忽視了情感傳達。詩歌翻譯講究“傳神達意”,“傳神”的核心就是“傳情”,情感傳達到位了,“神”就出來了。也就是說,譯文要達到原文的“情感效度”。
一、 情感效度及其判定
奈達提出的“功能對等”[7](functional equivalence)強調譯文接受者和譯文信息之間的關系應該與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間的關系基本上相同,要求譯者著眼于原文的意義和精神,而不拘泥于語言形式。“功能對等”理論在我國翻譯界引起了很大反響,金隄認為它對“直譯和自由譯之爭,提供了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8]15。根據這一理論,翻譯不是逐字逐句的死譯,而是在忠實于原文的基礎上,對原作的一種解釋和再創造。因此,金隄指出:“翻譯中需要的對等是一種綜合性的關系,不是機械地綜合語言學、語義學、語用學等方面的對等,而是依靠藝術的眼光和文化語言素養,全面細致地考慮各方面因素。效果上的對等就是這樣一種綜合性的對等關系。”[8]22“效果上的對等關系”就是“等效”,其主要原則是原文和譯文用不同的語言表達同一信息,但要產生基本相同的效果[8]27。中國古典詩詞很講究運用簡潔的詞語表達深重的情感,力求“言有盡而意無窮”,將“人生意趣”與“物外意象”深刻交融起來。詩歌的譯文要讓讀者感受到一種特殊的情感體驗,這種情感在原文中就存在,而且譯文讀者和原文讀者對這一情感沖擊的反應應該是基本一致的、等效的。詩歌翻譯也是一種移情的過程,將情感從一種語言移進另一種語言,而且要求是等效的,即“情感等效”(affective equivalence),也就是譯文實現了與原文基本對等的效度(validity)。
所謂“效度”就是有效性,它本是一個測試學的概念,其意為“使用測量工具或手段準確測量出某一事物的程度”,即“所測量到的結果反映所想要考察內容的程度”[9]。本文提出的情感效度是指詩歌譯文的情感反映原文情感的程度,也就是原文的情感傳達到譯文中的程度,譯文的情感越接近原文的情感,其情感效度就越高。當然,沒有一種科學儀器能夠精確地測量譯文的情感效度。情感是純感性的東西,雖然譯者可以通過問卷的形式調查讀者對原文和譯文的感覺是否相同,是否最大限度地達到情感等效,但在具體的翻譯實踐中邊做問卷調查邊翻譯實踐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譯者往往通過假想的讀者去感知譯文的情感。要判定譯文的情感效度,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考察。
第一,譯文的情感表達是否做到了“真”。這里的“真”有兩方面的含義,其一是情感之“真”,譯文要讓讀者感覺是“真情流露”,而非虛情假意的無病呻吟;其二是敘述的自然流暢,而不是故作矜持、曲筆跌宕,即情感的表達要顯得自然,不露人工雕琢的痕跡,否則就會讓譯文中的情感顯得不真實,因而也達不到譯者所需的效度。《蕙風詞話》論詞的創作中說:“真字是詞骨,情真意真,所作必佳,且易脫稿。”[5]6“真”也詩歌譯文之“骨”,無“骨”而不立。《惠風詞話》也說:“詩筆固不宜直率,猶切忌刻意為曲折。”[5]5譯詩也是這樣,詩句固然不能像日常語言那樣直率,但不可因為詩歌的形式因素(如押韻和節奏)刻意將句子顛來倒去,使得情感表達不自然順暢。在翻譯中國古典詩詞時,很多翻譯家們十分認“真”地注重情感的錘煉。比如,漢代蘇武寫過一首《別妻》詩(一說是假托蘇武寫的),描寫了一位剛烈節義的男子,在出使臨行前,告別自己深愛的妻子。這首詩最后六句為:“握手一長嘆,淚為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將夫妻離別的無限悲愴、難以自持的情景展現在讀者面前,催人淚下,震撼人心,表現了男子對愛情忠貞不渝的赤誠和生死相依的決心。對這六句詩,Henry H.Hart的譯文是:
How tight you held my hand!
I can see yet
The tear that fell upon it,
And those words you whispered last
I treasure still:
“Do not forget the hours of life and love
That we have shared.
If I live,
I shall surely come back to you.
If I die,
Remember
That all my thoughts have always been of you.”[10]88
Arthur Waley的譯文是:
I hold your hand with only a deep sigh;
Afterwards,tears-in the days when we are parted.
With all your might enjoy the spring flowers,
But do not forget the time of our love and pride.
Know that if I live,I will come back again,
And if I die,we will go on thinking of each other.[10]88
兩位譯者對原詩采取了不同的處理方式,Hart將妻子作為敘述的主體(第一人稱是“妻子”),用直接引語的方式引述了丈夫臨行前的愛情誓言;Waley的第一人稱是“丈夫”,也有臨行前的囑咐和誓言。在Hart的譯文中,妻子感受到了“你緊緊地握住我的手”,“看見了你的眼淚流下來”。通過觀察者的內心感受和觀察,描寫了“丈夫”難舍難分的情感。“丈夫”的述說生動地再現了他臨行前向“妻子”表示出的生死相依的情感。Waley的譯文直接描述了“我握著你的手,深深地悲嘆,然后淚流滿面”,通過敘述者的內心悲慟表現臨別前的凄慘景象,接下來的四行像戲劇獨白一樣,是“丈夫”向“妻子”的愛情宣誓。兩個譯文都十分注重情感的渲染,讀起來情真意切,自然流暢,毫不矯揉造作。
第二,譯文的情感表達是否恰到好處。《蕙風詞話》說創作詞要“恰到好處,恰夠消息,毋不及,毋太過”[5]6。這句話也適合翻譯詩歌,譯者在用詞和情感渲染方面要把握好一個度,不能表達不到位,也不能表達太過,能做到“恰到好處”便是取得了最佳的效度。例如,有人將李清照的《一剪梅》的第一節英譯如下:
紅藕香殘玉簟秋。
輕解羅裳,獨上蘭舟。
云中誰寄錦書來,
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From lotus to bed,aroma does blow.
My silk robe’s lightly doffed.
The lone canoe I row.
Who would send me a letter from the clouds?
When the wild geese come back,
The rail’s moonlit to glow.[11]
李清照寫這首詞時,她和趙明誠結婚不久,趙明誠便負笈遠游,她不忍離別,便寫下這首詞以傾訴相思、別愁之苦。第一句是說秋天到了,天氣轉涼,荷花的香氣變得殘敗微弱了。而譯文卻說“荷花的香氣吹進到了床上”,譯者使用了blow一詞,力度很大,可見荷花的香氣不但沒有殘敗,反而依舊濃烈。此詞用在這里就不是“恰到好處”,而是“太過”。“玉簟”是精美的竹席,枕席生涼,既是肌膚間觸覺,也是凄涼獨處的內心感受。譯文沒有渲染這一情感,因而有傳情“不及”之嫌。“月滿西樓”不僅僅是一幅“月亮照在房屋西面”的靜態畫面,而是在敘述詞人思念丈夫,輾轉反側,直到月亮偏西的后半夜仍然無法入眠。譯文卻將“西樓”隱去,因而無法傳達詞人的相思之愁苦。
當抒情述懷恰到好處,譯文一定是耐人尋味的。許淵沖在翻譯中國古典詩詞時十分注重情感的錘煉,他的許多譯文“用情”之深,動人心弦,感染了許許多多的讀者。比如,他的杜甫《春望》的譯文不僅做到了“音美、形美、意美”,而且在遣詞造句上凸顯了情感的美,且看前四句: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On war-torn land streams flow and mountains stand;
In towns unquiet grass and weeds run riot.
Grieved o’er the years,flowers are moved to tears;
Seeing us part,birds cry with broken heart.[12]
許淵沖將這首詩每行譯成十個音節,構成五步抑揚格,并精心設計了行內韻,譯文的音韻極美。在傳達原詩的“意美”時,譯者運用了情感沖擊力很強的詞語,十分扣人心弦。他將“國破”譯成“被戰爭撕裂的國家”,將“草木深”譯成“雜草長得狂亂”,具體化的處理,畫面感增強了,情感也加深了。接下來的傷感在譯文中處理成“多年的痛苦,花都感動得流淚”,雖然沒有原文“濺”的力度,但在前兩句慷慨激昂之后,稍稍抒情一下,更好地引導讀者的情感波動。最后一句譯成“鳥都苦得心碎了”,將情感的書寫推向高潮。在翻譯詩詞時,譯者除了在遣詞時要考慮詩歌形式上的適應性,如押韻、音節數量、構成詩歌節奏的重音位置外,還要在詞義方面仔細比對兩種語言相關表達方式的詞匯含義和聯想含義,找到最為貼近的表達方式,以取得對等的情感效果。“情感對等”要求譯者做到和原作者心靈相通,要全面而又細微地感受和領悟原作的情感,“調動譯入語中最適宜的手段,用恰如其分的譯文,使讀者也獲得同樣全面而細致的理解和感受”[8]8。
第三,譯文的情感表達是否合乎原文的文化規約。詩歌的情感即為“審美情感”,而“審美情感”又來源于“有意味的形式”[13]27,體現著特定文化群體的“文化心理結構”。情感是主觀感性的,看起來是個人的心理表征,實際上“積淀了人的理性”,也“積淀了社會的價值和內容”[13]10。可以說,情感雖然是詩人的“生命沖動”,它具有文化的符號性質,受文化的規約,體現著傳統的文化價值觀。例如,《關雎》的第一節:“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詩以關雎鳥相向合鳴,相依相戀,興起君子對淑女的思戀。
汪榕培英譯為:
The waterfowl would coo
Upon an islet in the brook.
A lad would like to woo
A lass with nice and pretty look.[14]
理雅各(James Legge)的譯文為:
Hark! From the islet in the stream the voice
Of fish hawks that o’er their nest rejoice!
From them our thoughts to that young lady go,
Modest and virtuous,loth herself to show.
Where could be found,to share our prince’s state
So fair,so virtuous,and so fit a mate?[10]3
從抒情層面上看,理雅各的譯文比汪譯情感充盈得多,呼語“Hark!”一下子拉近了文本與讀者的情感距離,讀起來更加生動親切。從意義層面上看,汪譯要簡潔明了,有“言有盡而意無窮”的韻味;而理雅各的譯文則闡釋過多,略顯啰唆。從文化層面上看,汪譯不如理雅各譯文接近原作的情感效度。這首詩所寫的男女雙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這是一種與美德相聯系的結合。“君子”在《詩經》的時代是對貴族的泛稱,是兼有地位和德行雙重意義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說體貌之美和德行之善。汪譯將它們分別譯為“lad”和“lass”,在文化上顯得貴氣不足,有些輕佻。第一節沒有敘述“君子”如何追求他心儀的“淑女”,而是說“君子好逑”,即這個美麗善良的“淑女”是“君子”好的伴侶。這里為什么不能理解為“君子喜好追求該女子”呢?《毛詩序》在解釋這首詩時,主張“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1]63。這實際上給出中國傳統男女關系的一個文化規約:普通民眾都是有情感生發的,但有德行修養的人會控制情欲,不讓它僭越禮義。因此,“君子”對“淑女”產生愛慕之情,但不會一開始就展開追求(woo),他縱然思念若渴,輾轉反側,不能入眠,也要在禮義規約的范圍內,用“禮樂”去取悅心儀之人。理雅各將“君子好逑”譯成“該女子美麗、有美德,是君子的適合的伴侶(So fair,so virtuous,and so fit a mate)”更合乎中國文化的情感效度。
二、 情感效度的翻譯策略
既然情感效度關乎詩歌翻譯的是否“傳神”,關乎翻譯的成敗,那么怎樣在翻譯實踐中達到或捕捉到理想的“情感效度”呢?
第一,盡力縮小敘事距離,將敘述者和主要人物盡量融合起來,讓敘述者“親臨”故事場中,這樣的譯文會給人一種真切感,能取得良好的情感效度。敘述距離是布斯在《小說修辭學》中提出來的重要概念,指故事敘述主體(隱含作者、敘述者和人物)之間的距離。中國古典詩詞的故事敘述主體和人物通常比較模糊,敘述視角呈多樣性。例如,杜甫的《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
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
香霧云鬢濕,清輝玉臂寒。
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干。
像絕大多數中國古典詩詞一樣,此詩沒有明確的敘述視角,盡管讀者一般都解讀為第一人稱視角,“今夜里鄜州上空那輪圓月高照,我不在你身邊,你只能在閨房中獨自欣賞了;我遠在他鄉憐惜起幼小的兒女,還不懂得為何思念長安”,但是此詩也可以解讀為第三人稱。不過,當敘述者和詩中人物融合一體時,讀者會感到情真意切些;若敘述者和人物分離,距離產生了,感染力就隨之減弱。王宏印在翻譯此詩時,采取了縮減敘述距離的策略:
This night,at Fuzhou,my wife,my dear,
Do you alone come out and look at the moon?
And does our daughter,so young,so little,
Remember and mention her father in Chang’an?
Take care.Your hair should be wet with the fog,
And your arm,so cold—so deep in the night.
When shall we meet and sit together by the bed,
And our tears be dried by the same moonlight?[15]
王宏印的譯文讀起來就像在聆聽敘述者兼人物“我”對妻子說著情意綿綿的悄悄話,三個問句表達了對妻子及兒女的深切牽掛。譯者十分注重情景和情感的錘煉,一開頭就充滿情感,“my wife,my dear”,親切的呼語讓人感到一股暖流。在問到小兒女時,譯者似乎重復了“so young,so little”,但充滿了情感和關切。原詩雖未著一個“我”字,但抒發的全是“我”的愁苦和思念。譯文將第一人稱突出出來了,情感距離拉近了,更顯得真情實感。
第二,由靜態表達轉譯為動態敘述,讓“情感”動起來。中國古典詩詞傾向于使用靜態的意象來展示一幅意境深遠的圖畫,常常呈現一種狀態(state)。比如柳宗元的《江雪》中的“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將讀者帶到一個幽靜寒冷的境地,是一個靜態的、“極端的寂靜、絕對的沉默”[16]的景象。這樣的詩句在中國詩詞中比比皆是。很多的詩句是靜態的情感描述,表現一個人內心的情感狀態。英語詩歌比較傾向于使用動詞來表達一種動態的事件(event),通過事件來體現人的情感。因此,在翻譯古典詩詞時,譯者可以使用動態的描述來再現靜態的情感。
例如,五代時期詞人牛希濟(生卒年不詳,913年前后在世)寫有《生查子·春山煙欲收》,用清峻委婉的語言,生動形象而又細致入微地刻畫了一對情人分別時難舍難分的場面。這對有情人在離別前傾訴了一夜的戀情,直到天明仍然依依不舍,總有訴不完的情:
語已多,情未了,
回首猶重道:
記得綠羅裙,
處處憐芳草。
They’ve talked too much,but with more love to pour,
Turning her head back,she urged him once more:
Keep in mind the green satin skirt I wear,
And feel tender to green grass everywhere.[17]158
縱然訴說了一整夜,但心中的戀情仍然滔滔不絕。“情未了”是對戀情的情態描寫,譯文使用一個動感很強的“pour”,敘述了戀人之間訴說了一整夜的情感,依然很濃烈,猶如“傾盆大雨”在心中泛濫。
宋代女詩人朱淑真在《秋夜聞雨·其二》中寫道:“獨宿廣寒多少恨,一時分付我心頭。”她在一個下著雨的秋夜想起了獨自守著廣寒宮的嫦娥,嫦娥的處境和心境實際上是詩人自己當時的情感狀態,詩人同樣感受到了廣闊無邊的孤寂和幽恨。這兩句詩可以翻譯成:
How many rues She’s paid for staying in the Cold Palace?
She has hurled all those rues upon my mind,so strong.[18]84
“分付”到“心頭”是一個相對靜態的描寫,動作感不是很強烈。譯文運用了“hurl”(投擲)一詞,動感極強,讓讀者感受到原文中的“孤獨”和“幽恨”很有力度地沖擊著內心的情感。
第三,動態的情感轉譯為靜態的表達。雖然中國詩詞傾向于靜態的抒情,但這并不是說動態的事件完全被拒之門外。實際上,很多詩句像“僧敲月下門”運用“敲”字一樣將動態的事件描寫得出神入化。在多數情況下,動態的事件仍然譯為動態的。但在一些詩句中,動態轉譯成靜態也可以達到相同的情感效果。例如,南唐中主李璟(916-961)寫的《攤破浣溪沙》第一節:
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
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Gone is the lotus’ fragrance,and withered its leaves;
Among green waves,the west wind brings sad heaves.
Our life is on the wane,as time goes by.
A cruel sight to our eye.[17]161
荷香消散,荷葉凋零,深秋的西風拂動綠水,使人愁緒滿懷,美好的年華也在凋謝,。與韶光一同憔悴的人,自然不忍去看到這一景象。“不堪看”譯成“a cruel sight to our eye”(殘酷的景象),將動態的動作“看”轉譯為靜態的“看”的對象,并且運用“cruel”一詞進行情感渲染。
再看看朱淑真的(《恨春五首 其二》):
淚眼謝他花繳抱,愁懷惟賴酒扶持。
鶯鶯燕燕休相笑,試與單棲各自知。
Thank Heaven in tears for flowers’ cheerful embrace,
And when in sorrow,wine becomes my sole soul mate.
Orioles and swallows do not laugh at my poor case;
You will know how you suffer if you’re separate.[18]15
盡管時令是花繁錦簇的春天,但因心上人的離開,詩人感到無限的惆悵,她內心的愁懷只有酒才能消解。“扶持”一詞具有動感,顯示她已悲凄得支撐不起自己的身體。若譯成“My sorrow is only counteracted by wine”或“supported by wine”,不僅詩意沒傳達出來,情感效果更沒到位。譯成“when in sorrow,wine becomes my sole soul mate”,把“酒”比作“心靈伴侶”,從身體的依賴到內心的寄托,由外而內,詩人憂戚的情感躍然紙上。在孤獨無助、人生不如意、憂傷悲凄的時候,中國古代詩人往往借酒澆愁,酒成了他們的心靈伴侶和情感慰藉。所以,在這首詩里,朱淑真的“酒扶持”不就是“心靈伴侶”嗎?由此可見,靜態的表達雖然不如動態那樣給人以栩栩如生的感覺,但其定性式的描述同樣能達到情感效度。
第四,將原文中情感話語具象化。具象化(concrete)翻譯就是將原文中總結性、評價性、抽象化的話語由面到點地轉譯成具體的意象或事件,使宏大的、概括性的敘述變成細節性的話語,通過細節來再現原文的情感功能。具象化的翻譯可以使譯文的情感表達更為細膩、豐滿、有力度。例如,《詩經·邶風·擊鼓》的第一節:“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戰鼓擂得隆隆響,校場上士兵踴躍練兵。有的在修路筑城墻,我獨自從軍往南行。“戰鼓雷動”和“士兵操練”在這里都是籠統的狀態描寫,是“總結性、評價性、抽象化的話語”。筆者將這一節翻譯如下:
Beat! Beat! Beat! Bong the drums out.
Charge! Charge! Charge! We’re busy about.
They are building walls far and near,
But I go to the south frontier.[17]9
回譯過來就是“敲啊敲啊敲啊,戰鼓隆隆響;沖啊沖啊沖啊,我們忙操練。他們到處修城筑墻,我獨自去南方的邊疆。”三次重復“Beat!”和“Charge!”將士兵緊張訓練的情景具體展現出來了,表現有力度,讀起來很有節奏,似有雷霆萬鈞之勢,讓讀者感受到士兵們斗志昂揚的樣子。再如朱淑真的《牡丹》一詩:“嬌嬈萬態逞殊芳,花品名中占得王。莫把傾城比顏色,從來家國為伊亡。”
Unique scents it shows with many a fetching pose,
And wins among others flowers a fair from fairs.
Don’t compare it to beauties who can e’en ruin cities;
For them,many kingdoms have met their nightmares.[18]171
此詩歌頌牡丹花的美麗、獨特、妖嬈,具有高貴的品質,是“花中之王”。將“占得王”譯成“a fair from fairs”,巧妙地借用了莎士比亞的Sonnet 18中的具體意象。在許多詩詞中,詩人們一般將美女比作花,而在此詩中,朱淑真將牡丹與傾城傾國的美女相比擬,并說不要將牡丹比作這些美女,因為美女會引起國家滅亡。將“為伊亡”譯為“met their nightmares”雖然改變了原作的內容,但其意象更為具象化,起到了對等的情感效果。
第五,走進詩人的情感世界,圍繞原文創設語境,以達到情感效度。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和原作者達到了一種心靈上的契合,這種契合超越了空間和時間的限制,打破了種族上和文化上的樊籠,在譯者而言,得到的是一種創造上的滿足;在讀者而言,得到的是一種新奇的美感經驗”[8]34。朱淑真的《清平樂·夏日游湖》一詞記述了她與情人在湖上約會的情景。上片寫他們倆相約游湖,先是“攜手藕花湖上路”,不料遇上“一霎黃梅細雨”。游湖賞花而遇雨,卻給他們造成了一個幽清的環境和難得親近的機會。接著下片寫道:
嬌癡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懷。
最是分攜時候,歸來懶傍妝臺。
在他們小駐的地方,應當沒有第三者在場。于是他們便摟摟抱抱,未免輕狂起來。詞人不管許多,“不怕人猜”,打破了“男女授受不親”一類清規戒律,遂有了相戀以來第一次甜蜜的體驗。正因為是第一次,感覺也就特別強烈而持久。“最是分攜時候”,多么依依不舍:“歸來懶傍妝臺”,何等心蕩神迷!兩筆就把一個初歡后的女子情態寫活了。這兩筆要想翻譯得像原文一樣情感充盈是具有相當挑戰性的。
I didn’t care I was thought to be girlish and silly;
With my dress on,I slept in your arms straightway.
But the time when I parted you was really chilly;
Back home,at my dressing table I was lost in idle gaze.[18]199
此譯文圍繞原文創設了一個情感語境,兩情相悅的人相約游湖,他們陶醉在二人世界里,相依相偎。可是,相聚越是甜蜜,分別越是難舍。所以,分別的時候一定是冰冷的(chilly)。獨自回到家里,她坐在妝臺前,悵然若失,她什么都不想做,只是癡癡地坐在那里,眼睛一定在凝望著。雖是凝望,其實什么都沒有看,所以是“lost in idle gaze”,這不就是活脫脫的、約會歸來的、心蕩神迷的女子情態嗎?
結 語
詩詞是以情動人的文學形式,情感是詩詞翻譯中重要的參數。如果譯者不注重于情感錘煉,即使言辭精美,其譯文就像鐘嶸批評玄言詩那樣:“理過其辭,淡乎寡味。”[2]17“情感效度”強調“真實性”,讀起來像是蓄積在詩人內心的一種不可抑制的情緒沖動,而非矯情、偽飾,或無病呻吟。只有“情投意合”的譯文才能真正地讓讀者“知之,樂之,好之”。翻譯詩歌除了要求譯者具備很高的智商外,還需要很高的“情商”,譯文要努力做到“情不動人誓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