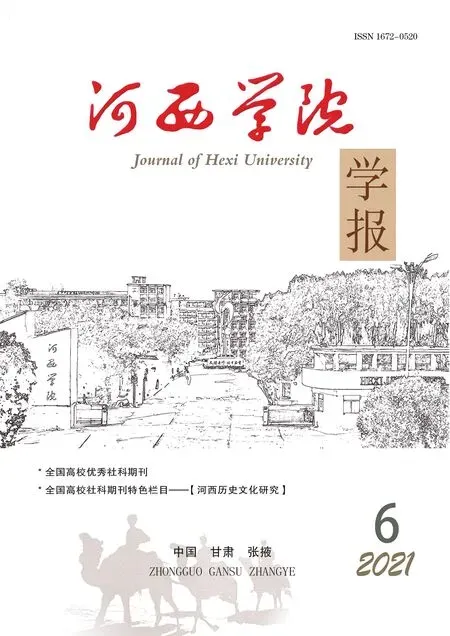《漢語大詞典》人名疏誤類舉
何 茂 活
(河西學院文學院,甘肅 張掖 734000)
《漢語大詞典》(以下簡稱《大詞典》)雖然不直接收列人名類條目,但在援引書證時會涉及著作者,所引文句中亦常出現人名。而這些人名的引錄和標注,難免會出現錯誤,從而影響辭書質量,造成相關知識的訛傳。筆者在編校該詞典修訂稿的過程中,發現初版中即已存在一些有關人名的訛誤,修訂稿中或因襲舊誤,或者又產生了新的問題。今試分六種情況予以解析,以圖引起相關編輯、學者的重視。
一、作者或注疏者不確
《大詞典》有些字頭或詞頭下援引書證時,因各種原因導致將著作人張冠李戴,從而造成了作品及語句“權屬”的錯謬。如:
例1.“毋”字條下引清戴震《汪河發墓志銘》:“嗚呼,我死毋憾,但我主人聞之,病又加甚耳。”按:該文實見于清戴名世《南山集》卷十(有光緒二十六年刻本)。[1]《大詞典》“入粟”條、“紈綺子弟”條均引《汪河發墓志銘》例,所標作者無誤。“毋”字條下出現這一疏誤,不排除編撰者誤將“名世”當作了戴震表字的可能。
例2.“有頃”條引《戰國策·秦策一》“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蒞政有頃,商君告歸”姚宏八十首”。正文中該詩確在許承欽名下。[3]但查清康熙刻本《遺民詩》卷十一,許承欽之后有紀映鍾,許氏名下有詩44 首,紀氏名下有36首,自《城邊路》之后屬紀氏所作。再查紀氏《戇叟詩抄》,在其卷四確見此詩。又據《明詩紀事》辛簽卷十二,該詩作者亦為紀映鍾。[4]據此可知《明遺民詩》整理本誤漏了紀氏之目,將其詩作統歸在了許氏名下。
例4.“火樹”條引宋張憲《鵲橋仙》詞:“星橋火樹,長安一夜,開紅蓮萬蕊。”按:初版作“宋張憲”,修訂稿改為“元張憲”,俱誤。實為宋張先。詳見《張子野詞·補遺上》,又見《歷代詩余》卷二九等。[5]另,據上述諸本,“紅蓮”前有“徧”字,當補。
例5.“炕”字條引張天民《死不著》詩:“二畝地的谷穗沒見黃,掐回家來鍋底上炕。”按:“張天民”實為“張志民”。詳見《張志民詩選》。[6]《漢語大字典》“炕”字頭下亦引此例,無誤。
例6.“炎光”條引《文選·曹植〈王仲宣誄〉》:“會遭陽九,炎光中蒙。”張銑注:“炎光,謂漢也。”按:實為呂延濟注。詳參《新校訂六家注文選》。[7]
例7.“神王”條引《莊子·養生主》:“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成玄英疏:“心神長王,志氣盈豫。”經查《莊子注疏》,“心神長王,志氣盈豫”之語已見于郭象注,成玄英疏中又轉述了此語。[8]按照征引書證的慣例,應當引用時代在先者。
例8.“神交”條引元劉南金《和黃溍卿客杭見寄》:“十載神交未相識,臥淹幽谷恨羈窮。”按:據《全元詩》,此詩作者當為元吳師道。[9]據《吳師道集》,有《和黃晉卿客杭見寄》三首,此為其三。[10]另詩題中的“黃溍卿”,多作“黃晉卿”。二者當為同一人。
除《大詞典》外,《漢語大詞典訂補》也有作者或注疏者不確的問題。如:
例9.《漢語大詞典訂補》“炎溟”條引明陳文彬《寄懷徐聞陳公文彬舊游》詩:“雷翥天飛海色青,一時風雨滯炎溟。”按:據《湯顯祖詩文集》,該詩作者實為湯顯祖,系湯氏“寄懷”陳文彬之作。[11]茲將作者誤為“陳文彬”,便變得不合情理。
二、作者及書名、篇名不確
作者及書名、篇名不確,實即書證出處不準確,在《大詞典》中大致表現為三種情況:一是所標出處與實際不符;二是所標出處并非原始出處;三是書名、篇名有誤或作者稱名不合常則,造成詞典內部歧異。
例1.“祖生鞭”條釋義:
語出《世說新語·賞譽下》“劉琨稱祖車騎為朗詣”劉孝標注引晉虞預《晉書》:“劉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指祖逖)先吾著鞭耳。’”
按:“晉虞預《晉書》”應為“晉孫盛《晉陽秋》”。詳參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12]244-245《大詞典》征引之誤,蓋因劉孝標注先引晉虞預《晉書》18 字,后引《晉陽秋》200 余字,引者失察,誤將后者混為前者。查《晉陽秋輯本》,在其卷三確有上述文句。[13]
例2.“神女”條引明楊珽《龍膏記·買卜》:“朝云暮雨連天暗,神女知來第幾峰。”按:查楊氏雜劇《龍膏記》,第四出“買卜”煞尾詩:“巫嶺岧峣天際重,佳期宿昔愿相從。朝云暮雨連天暗,神女知來第幾峰。”受文體限制,作者在這里并未注明此系前人創作,因此很容易被人誤解為系楊氏自作。其實此詩出自唐代張子容之手,題為《巫山》,詳見《全唐詩》。[14]
例3.“豪翰”條引傅熊湘《〈鈍庵詩〉自序》:“涕沾胸臆,憤發豪翰。”按:這里有兩個問題,一是關于作者,據有關介紹,傅熊湘(1882-1930),后改名傅尃,字文渠,號鈍安,有《鈍安集》等。[15]《大詞典》引用傅尃詩文凡90 余例,除此處作“傅熊湘”外,其他均作“傅尃”,應統一為后者。二是文題《〈鈍庵詩〉自序》,“庵”為“安”之誤。
《大詞典》初版書證,全靠手工摘錄,無法像現在這樣進行檢索排查,因此出現上述作者及書名篇名方面的疏誤與不足在所難免。本次修訂中,應充分發揮各類數據庫的檢索功能,最大限度地核實書證及其出處,實現相關信息的信實和協調。
三、史書傳主標注不確
《大詞典》征引歷代史書,有專門的引書格式和相關規定。有些詞條下征引此類文獻時對上述規定執行不太嚴格,按照體例規范衡量,也應視為疏誤。如:
例1.“祖宗”條引《漢書·張湯傳》:“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藩國。”經查,該句確見于《漢書·張湯傳》,但具體見于其子張安世部分,按照《大詞典》引書體例,應標為《漢書·張安世傳》。
例2.“祅道”條引《南史·蔡廓傳》:“宣城郡吏吳承伯挾祅道聚眾攻宣城。”按:此例與上例相仿,應改為《南史·蔡撙傳》。撙為廓之孫。
四、人名文字訛脫
此類訛誤包括兩種情況:一是形、音訛誤導致人名文字訛舛;二是人名文字脫漏。如:
例1.“靈運屐”條引元宋旡《送金華黃晉卿之諸暨州判官》詩:“晚陪靈運屐,早訪董生帷。”按:“宋旡”實為“宋無”之訛。宋無(亦作無),字子虛,著有《翠寒集》一卷。詳見《元詩選初集》。[16]《大詞典》引宋無詩句為證者凡67例,其中44 例標為“宋無”,23 例標為“宋旡”。如引《詠石得天字》句者,“文貝”條下為宋旡,“龜”字條和“彈子窩”“木屐”條下則為“宋無”。引《送金華黃晉卿之諸暨州判官》句者,“杏苑”“孤枕”條下為“宋無”,①“靈運屐”條下則為“宋旡”。經查檢,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版本字形的歧異和詞典編撰者對著者姓名異寫的誤識。中國基本古籍庫收錄有宋氏《翠寒集》的兩個刻本,刻本一為“明刻元人十種詩本”,刻工精良,字形規范端莊,作者自序署名“至元丙子秋吳病叟宋無子虛志于翠寒山隱居”。刻本二標為“明刻本”,但從刻印特點看,似屬元刻。作者自序署名為“至元丙子秋吳病叟宋無子虛志于翠寒山之隱居”,其中“無”字字跡較模糊,作,卷一題署作“廣平宋子虛”。這大概就是《大詞典》所引“宋旡”之名的來由。
那么從命名理據上來說,究竟應該是宋無(無)還是宋旡呢?答案當然是前者。其一,從名與字的意義聯系上看,“無”與“子虛”意義對應,可以互解;而“旡”為氣逆哽咽之義,與“子虛”意義無關。其二,《翠寒集》卷首馮子振序對宋無的取名已有討論:“天詘西北曰‘無’,曠古未有有姓而以‘無’為之名者。吳人宋子虛乃以‘無’為之名。斯名也,殆自‘子虛’始。”(前二‘無’字,刻本二作‘無’)其三,文淵閣《四庫全書》中,《翠寒集》的作者署為“宋無”,紀昀等所作《提要》中也做了十分確定的表述:“《翠寒集》一卷,元宋無撰。無字子虛,蘇州人,嘗舉茂才不就,是集前有自序。”[17]綜上所述,《大詞典》初版中的23 處“宋旡”均應改為“宋無”,以與另外44例相統一。
例2.“毒害”條引明李贄《復鄧在陽書》:“斯言毒害,實刺我心。”經查李贄《焚書》卷一及《李溫陵集》卷一,俱作“鄧石陽”。[18]據中國基本古籍庫檢索,“鄧石陽”之名凡十余見,無作“鄧在陽”者。《大詞典》引李贄《復鄧石陽書》及《答鄧石陽書》計57 次,唯此處誤作“鄧在陽”。②
例3.“有頃”條引明張寧《方洲雜言》:“有頃,姚與尚書胡公濚偕來。”按:經查《方洲雜言》明萬歷刻本,“濚”實作“濙”。[19]據中國基本古籍庫所見之《方洲集》卷二六,亦作“濙”,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亦如此。《大詞典》所引,蓋據叢書集成初編本。[20]當予改訂。
例4.“每每”條引唐歐陽詹《與王氏書》:“今一辭庭闈,而逾半紀,以本心每每,馳戀若此,魂夢昭昭,感發如彼。”按:據《全唐文》及《歐陽行周文集》《文苑英華》等,該文題目中的“王氏”實應為“王式”。
例5.“有意無意”條引茅盾《子夜》十七:“韓孟翔有意無意地又準對著吳蓀莆的樂觀論調加上一個致命的打擊。”“莆”系“甫”之誤。
例6.“祓1”條下引《管子·小匡》“鮑叔祓而浴之三”尹子章注:“祓,謂除其兇邪之氣。”按:“尹子章”實系“尹知章”之誤。《大詞典》引尹氏《管子注》860 余次,除此處誤作“尹子章”,以及“地位”條下誤作“尹之章”外,其他均無誤。
例7.“災福”條引宋沈括《夢溪筆談·樂律一》:“高郵人桑京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按:經查《夢溪筆談》,“京”實為“景”。[21]
例8.“炊爨”條引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德行》:“〔祖訥〕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按:“祖訥”實應為“祖納”,詳參《世說新語校箋》。[12]15并參《大詞典》“行操”條。③
例9.《漢語大詞典訂補》“炎涼世態”條引宋王十朋《湖邊懷劉謙沖》詩:“炎涼世態從他變,生死交情祇自諳。”按:“沖”實為“仲”。今據中國基本古籍庫檢索,王氏《梅溪集》中,“劉謙仲”之名凡三見,而“劉謙沖”之名則無之。
例10.“神王”條引明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懶倦欲睡時,誦子小文及小詞,亦覺神王。”按:經查《歷代詩話續編》所錄《藝苑卮言》,“子”后有“瞻”字,子瞻指蘇軾。其上文曰:“讀子瞻文,見才矣,然似不讀書者。讀子瞻詩,見學矣,然似絕無才者。”[22]1018
例11.“祇樹園”條引唐杜甫《贈蜀僧丘師兄》詩:“我住錦官城,兄居祇樹園。”按:經查檢,該詩題實為“贈蜀僧閭丘師兄”,原注:“太常博士均之孫。”詩中有“世傳閭丘筆,峻極逾昆侖”之句。“均”即閭丘均。《舊唐書·文苑傳中·閭丘均》:“益州成都人閭丘均,亦以文章著稱。景龍中,為安樂公主所薦,起家拜太常博士。”[23]
又,“閭丘師兄”中,“閭丘師”為名,“兄”為敬稱。其證如后:宋計有功《唐詩紀事·杜審言》:“子美贈閭丘師詩云:‘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謂審言以詩,閭丘均以字,同侍武后也。”明楊慎《升庵詩話·閭邱均》:“成都閭邱均,在唐初與杜審言齊名。杜子美贈其孫閭邱師詩云:‘鳳藏丹霄莫,龍去白水渾。’蓋稱均之文也。”[22]856
五、人名割裂
這種情況主要見于外族人名的稱引中。如:
“特勤”條引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特勤當從石刻》:“顧氏《金石文字記》,歷引史傳中稱‘特勒’者甚多,而涼國公《契苾明碑》,‘特勤’字再見。又柳公權《神策軍碑》,亦云大特勤嗢沒,斯皆書者之誤……”按:“嗢沒斯”為人名,不當割裂至上下兩句。《大詞典》“貴酋”條引唐李德裕《〈異域歸忠傳〉序》:“嗢沒斯者,回鶻之貴酋也。”“祛除”條引李德裕《賜回鶻可汗書》:“去歲,嗢沒斯特勤已至近界,邊將憤激,便請祛除。朕念其無主可歸,且令安撫。”另有“虎拜”條引明張居正《擬唐回鶻嗢沒斯率眾內附賀表》等,俱可為證。
六、專名線標注失當
《大詞典》專名線使用方面存在的問題大體有以下幾種情況:一是當打而漏打;二是不當打而誤打;三是所打范圍失當;四是連打、分打處理欠妥。
例1.“祈福”條引清曹寅《祀灶后作》詩:“刲羊剝棗竟無文,祈福何勞祝少君。”其中“少君”一詞應加專名線而未加。據《大詞典》“少君”條,漢武帝時齊有方士李少君。事見《漢書·郊祀志上》。漢王充《論衡·道虛》:“武帝之時,有李少君,以祠灶辟谷卻老見上。”
例2.“有酒”條引元鄭廷玉《后庭花》第二折:“李順,你有酒了,你歇息咱。”按:“李順”為人名,當連打專名線于二字之下。《大詞典》“握刀紋”條引《后庭花》第一折:“若是殺人處,不教別人去,則教李順去。哥也,偏怎生我手里有握刀紋?”所加專名線無誤。
例3.“火辰”條引《新唐書·歷志三上》:“自羲和以來,火辰見伏,三睹厥變。”按:羲和指羲氏與和氏,當分打為“羲和”。參《新唐書》中華書局點校本。[24]
例4.“炎1”條義項⑧引《后漢書·馬融傳》:“自黃炎之前,傳道罔記;三五以來,越可略聞。”宋蘇軾《泛舟城南會者五人分韻賦詩》之四:“南郭清游繼顏謝,北窗歸臥等羲炎。”按:“黃炎”指黃帝軒轅氏與炎帝神農氏,專名線當分打。“顏謝”指顏延之、謝靈運,專名線亦當分打。
例5.“祖襲”條引南朝梁鐘嶸《詩品》卷下:“檀謝七君,并祖襲顏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初版無誤。修訂稿誤將“顏”“延”二字分打了專名線。“顏延”指顏延之,不可分打。
例6.“將養”條引元鄭光祖《伊尹耕莘》第一折:“王留伴哥,好好的抱到家中,便尋覓妳母,好生將養著。”初版未加專名線;二版修訂稿標作“王留伴哥”。據《大詞典》“王留”“伴哥”的釋義,“王留”為“元明雜劇中泛用的人物名稱,猶‘張三’‘李四’,一般屬于插科打諢角色”;“伴哥”是“鄉村中少年的泛稱”。試看《大詞典》中相關書證的征引情況:
元石德玉《秋胡戲妻》第一折:“王留他情性狠,伴哥他實在村。”(見“王留”“伴哥”“牛觔”條)④
明湯式《慶東原·田家樂》曲之三:“東墥沽新釀,西村邀故交,麥場上醉倒呵呵笑,釁都摔腰,王留上標,伴哥踏撬。人說仕途榮,我愛田家樂。”(見“踏撬”條)
元趙顯宏《滿庭芳·耕》曲:“賽社處王留宰豬,勸農田牛表牽驢。”(見“牛表”條)
元姚守中《粉蝶兒·牛訴冤》套曲:“為伍的是伴哥王留,受用的是村歌社鼓。”(見“村歌社鼓”條)
以上各例中的“伴哥”“王留”,《大詞典》中除最后一例在“王留”下加了專名線以外,其他均未加。也就是說以不加為常,基本統一。這樣做的原因,應當是它們已經屬于泛稱而非專名。初版“將養”條中的處理與此一致,本不必改訂。修訂稿標作“王留伴哥”,顯然是因為缺乏對相關問題的綜合了解,從而導致了改正為錯的結果。
以上分六種情況,對《大詞典》中有關人名的疏誤做了列舉和分析。其中前兩類屬于事實方面的舛誤,亦即作者、書名篇名及具體語句之間“張冠李戴”的問題。第三類屬于引書格式方面的疏誤,如果拋開特定的引書格式規定,則可以忽略。第四、五類是稱引人名時出現的文字脫誤及詞語斷連失誤,屬于文字編校問題。這種情況會造成給人“改名換姓”的結果,也可能會導致語句齟齬難通。第六類問題,表面看來只是標點符號問題,但是詞典以及古籍點校本中的專名線有其特殊的解釋作用,它的打與不打、多打與少打、連打與分打,都直接反映了點校者對詞義及詞間關系的分析和認定,因此這方面的疏誤同樣不容忽視。
以上各方面的問題,都會造成詞典內部的矛盾沖突。因為《大詞典》篇幅巨大,材料豐富,本身就是一個難得的信息庫。在校訂時我們發現,很多矛盾或疑問都可以在《大詞典》內部找到解決途徑或正確答案。因此建議在修訂過程中,加強對《大詞典》自身資源的利用,同時加強詞典內部的比證協調,從而盡可能多地發現問題,克服訛謬。
本文所舉上述各類疏誤,絕大多數都是見于初版并沿襲至修訂稿(編委稿或分冊主編稿)中的,但“顏延”例及“王留伴哥”例是修訂稿中新出現的問題。而這兩例的致誤原因又不大相同,前者也許源自重新錄排時的疏忽或者誤解,⑤后者則應當是刻意而為之。另如“火樹”條由“宋張憲”改為“元張憲”(實應為“宋張先”),可謂錯上加錯。類似于上述三例這種尚在修訂、并未定稿的情況,本不應該放在這里討論,但是因為考慮到這些情況頗具警示意義,所以不揣冒昧,還是提出來加以討論,并與相關編輯同仁共勉。希望詞典修訂各環節編輯人員,既要注意改正初版錯誤,又要注意防止產生新的錯誤,尤其要防止在無疑處生疑,將無誤者改錯。由此說來,《大詞典》修訂之初,編委會提出的“訂嚴補慎”的原則的確值得仔細領會和認真貫徹。以上討論可以看作筆者對這一原則的粗淺領悟和實踐心得。謹此芹獻,敬請方家批評教正。
注釋:
①《大詞典》“孤枕”條下引為《送金華黃晉卿之諸暨判官》,“判官”前脫“州”字,當補。
②《大詞典》不同詞條下所引文題不同,《復鄧石陽書》或作《覆鄧石陽書》《復鄧石陽》,《答鄧石陽書》或作《答鄧石陽》。修訂時應盡量統一。
③“行操”條引《世說新語》劉孝標注,實系劉氏轉引王隱《晉書》語,應予揭明。
④《大詞典》引此例,所標作者不統一,“伴哥”條下作石君寶,“王留”及“牛觔”條下作石德玉。“君寶”為石德玉之表字。據漢語大詞典編纂處編《〈漢語大詞典(第二版)〉工作用表》,當統一為石君寶。
⑤比如初版“祀堂”條書證中有一處“顏孟”,正好分處上下兩行;修訂稿中錯排成了“顏孟”。這種情況也應引起編校者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