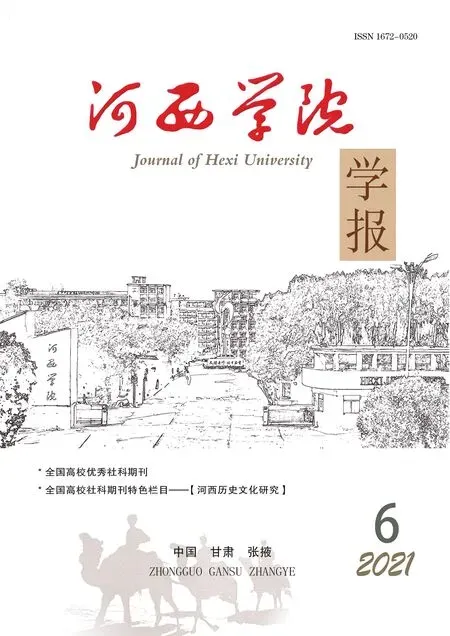上古漢語定語后置的適用語境
程 建 功
(河西學院文學院,甘肅 張掖 734000)
關于古代漢語定語后置問題,古漢語學界的探討相對較少,并且對古代漢語中是否存在定語后置尚有爭議,古代漢語教材一般也不涉及此問題。因中學文言教學常涉及定語后置問題,故中學語文教學界對此問題頗為關注,可惜從使用層面研討的多,而從理論層面探討的少。本著中學與大學學術一體的原則,我們試圖換一種思路,不再探討定語后置本身,而從定語后置的適用語境角度談談這一古代漢語的特殊語序。眾所周知,語言選擇和句式的運用往往取決于具體的語義和語境。從語言形式上看,古漢語與現代漢語一樣,定語置于中心詞之前為常態,適用于正常的語言表達。定語后置作為一種非正常或特殊的語法現象,就一定有其存在的特殊語境和適用范圍。那么從語用角度來看,古漢語定語后置究竟適用于怎樣的語境呢?
據筆者初步考察,對此問題至今尚未見到專文探討,學者們只是在探討語序問題或句子結構移位(或易序)的語用功能時有所涉及。范曉先生認為“語序與句式的關系非常密切,語序的差異會影響句式的差異。……特定的語序對應特定的句式:原型語序、衍生語序、超常語序對應原型句式、衍生句式、超常句式。原型語序是本源語序、母體語序,變化原型語序(主要方法是成分的“移位”)就能生成各種衍生句式和超常句式。語義語序是句法語序和語用語序的基礎,是生成句式的基底語序”,并強調說“語序影響句式是有理據的,這主要表現在:思維的定勢和表達的需要”,同時指出“有些語序及其形成的句式受到語境因素的制約。比如在上下文語境里,為了保持話題或主題的銜接,就得適應語境需要選擇某種特定的句式。”[1]李晉荃先生也指出句子結構的易序和變位,其語用功能一是“適應話題化的需要”,二是“適應突出主要信息的需要”,三是“適應句式和押韻的需要”[2]。范、李兩位先生就語序的“移位”或“易序”問題從理論高度所作的概括可作為本文寫作的基本理論依據。而王锳先生和趙世舉先生關于古漢語定語后置的具體論述則是本文寫作的語言事實依據。王锳先生通過對大量上古文獻資料的考察,認為“定語后置的現象在古漢語中確實不多,但卻是不可否認的客觀存在。其存在形式至少有下面幾種類型:一、名詞及體詞性成分作定語后置,二、形容詞及謂詞性成分作定語后置,三、‘者’字結構作定語后置,四、數量結構作定語后置。”[3]趙世舉先生通過對《孟子》及相關語料的考察,認為“古漢語中存在著兩種性質不同的定語后置:一種是作為遠古漢語遺留模式的定語后置——遺跡性定語后置,一種是出于表達需要的定語后置——語用性定語后置”,明確指出語用性定語后置“這類變異式與常規式是同義結構,結構形式上也只是語序不同,結構關系、語義關系都相同,主要的區別在于語用價值有異。”[4]我們完全贊同王、趙兩位先生的觀點。下面我們依據語用學的相關理論將古漢語定語后置的適用語境大體分為以下三類,并以學界常用的上古漢語定語后置例句作為基本語料對定語后置不同于常規句式的語用價值做一點初步探討。
一、概括與具體表述語境下的定語后置
關于這種語言現象,清代學者稱之為“大名冠小名”格式;學界一般稱之為“名詞及體詞性成分的定語后置”;趙世舉先生認為這是一種遠古漢語遺留模式的定語后置,故將之稱為“遺跡性定語后置”。孟蓬生先生曾對此進行過詳細的語料整理和具體探討,認為夏以前這種格式一統天下,商周時期“大名冠小名”與“小名冠大名”兩種格式并存,秦漢時期“大名冠小名”格式逐漸消亡[5]。這一結論應當說基本符合古漢語發展演變的實際。這一類的例句上古漢語中較為常見。如:
(1)祖己圮于耿,作祖乙·。(《尚書·咸有一德》)
(2)肇牽車牛·,遠服賈。(《尚書·酒誥》)
(3)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周易·泰》)
(4)無逾我墻,無折我樹桑·。(《詩經·將仲子》)
(5)遂置姜氏于城穎·。(《左傳·隱公元年》)
(6)畏其師曠·,告晉侯曰……(《左傳·襄公十八年》)
(7)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呂氏春秋·仲春紀》)
(8)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孟子·離婁上》)
(9)大夫不得造車馬·。(《禮記·玉藻》)
(10)若如臣者,猶獸鹿·也。(《韓非子·內儲說》)
以上各例,前一名詞為某一類事物的概括性名稱,后一名詞則為某一事物的具體名稱。例(1)“祖乙”中的“祖”為先祖的通稱,“乙”則指稱特定的某一先祖,例(3)與此類似,只不過通稱換作了“帝”,只是因為“乙”在商人稱呼其為“祖”,而在周人稱呼則為“帝”;例(2)的“車牛”即指牛車,例(9)的“車馬”即指馬車,其中“車”為通稱,“牛”“馬”則為限制車的類屬的具體稱謂;例(4)的“樹桑”與例(8)的“草芥”用法相同,“樹”與“草”為草木的通稱,“桑”與“芥”則指稱草木具體的類屬;例(5)“城”為城池之通稱,“穎”則指具體的地名,例(6)與此類似,“師”為樂師的通稱,“曠”則為樂師之名;例(7)的“蟲螟”為螟蟲,例(10)的“獸鹿”即鹿獸,其中“蟲”為動物通稱,“螟”則為蟲之一種,“獸”為野獸之通稱,“鹿”則為野獸之一種。
通過以上分析,這一類定語后置是古人在屬種概念并舉語境下所采取的表述方式,是將屬概念放在種概念之前加以表述的,這種屬于原型語序的表述,應當與古人的思維習慣以及對事物的認識水平有關。或許古人一開始只有屬概念一種認識,后來發現同一屬概念之下還有種概念的區別,于是在屬概念之下加上種概念以示區別,久而久之成為了一種用語習慣。這是文化語言學研究的問題,我們姑且不論,僅就一般語言理論而言,這種為區別事物屬種概念的具體語境下產生的語序,客觀上不是并列結構也不是后補結構,而只能是中定結構。既然是中定結構,那么將這種結構理解為定語后置也就順理成章。盡管有學者認為“樹桑”例為詩歌押韻而設,但也當承認正因“大名冠小名”為當時的習用表達,才不致出現因押韻改變詞序而產生誤讀。同時正因這種“大名冠小名”的格式在商周以前為常用格式,商周時期“大名冠小名”與“小名冠大名”的格式才逐漸形成并舉的局面,也正好說明了語序或語用習慣的改變與人的認識水平的提高緊密相關。有學者曾根據后世文獻中尚存一定數量的“大名冠小名”格式,認為孟蓬生先生關于秦漢時期“大名冠小名”格式逐漸消亡的結論有誤。我們認為這種情形應當是后世仿古造成的特殊現象,畢竟秦漢以后,在表述概括事物與具體事物關系時“小名冠大名”已成為通用格式。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后世之所以依然模仿上古“大名冠小名”格式,也恰恰說明這本就是上古漢語在概括與具體表述語境下的一種原型語序。
二、物量表述語境下的定語后置
一般情況下,上古漢語數量詞連用時,名量式和動量式常常不用量詞,直接用數詞表示不僅如此,上古漢語名量式與動量式的用法基本與現代漢語相反。就是說,在上古漢語中,名詞與數量詞結合時,數量詞往往放在名詞后面。看起來這的確是上古漢語的習慣語序,當然實際情形要略為復雜一些。王力先生《漢語語法史》曾對這種語言現象做過細致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在上古漢語里,人、物數量的表示,可以有三種方式:一是數詞直接放在名詞前,這是最常見的方式;二是數詞直接放在名詞后,這種方式較為少見;三是將數量詞放在名詞后,這種方式也比較少見;并強調如果是數詞與度量衡單位詞組合,就必須用第三種方式。[6]可見,上古漢語人和物的數量表示方式以第一種為常,即名詞與數詞的組合以數詞放在名詞前作定語為常式,這與現代漢語語序基本相同(因現代漢語數詞后一般還要帶量詞),這顯然是其原型語序;而以第二、第三種為變,即以數詞或數量詞放在名詞后作定語為變式,這可視為衍生語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種語序下,王力先生所舉的例證均為表人名詞、表事名詞、時間名詞與數詞的組合,沒有一例是與表物名詞組合的;二、三兩種語序下的例證則多為數詞或數量詞與表物名詞的組合,偶爾也與表人、表事名詞相關。由此我們是否可以得出這樣一個初步的結論:上古漢語名量式語境下的數詞或數量詞與名詞的組合一般與現代漢語語序相同;而物量式語境下的名詞與數詞或數量詞(尤其是度量衡單位詞)相組合時,數詞特別是數量詞常常放在名詞后作后置定語。可見這是古人為區別不同事物的差別而在表述上所做的一種慣常處理。如:
(1)獲虎一,豕十有六。(《殷墟文字乙編》)
(2)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城邑,牛一,羊一,豕一。(《尚書·召誥》)
(3)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詩經·伐檀》)
(4)睽孤,見豕負涂,載鬼一車。(《周易·睽》)
(5)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左傳·哀公十五年》)
(6)冉子與之粟五秉。(《論語·雍也》)
(7)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孟子·公孫丑下》)
(8)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于梁。(《戰國策·齊策》)
(9)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莊子·秋水》)
(10)負服矢五十個。(《荀子·議兵》)
以上各例均為數詞或數量詞放在名詞后作定語,特別是數詞后帶上度量衡單位時放在名詞后作定語為其常態。可見這是先秦物量表示的一種慣常語序。這種情形在秦以后的典籍中也還常見,如“吏皆奉送錢三。”(《史記·蕭相國世家》)“令民入米六百斛為郎。”(《漢書·王莽傳下》)其實,不僅表物量的數量詞或數詞可放在名詞后,即使表人名詞的后面也可帶上后置定語,如果例(6)“載鬼一車”里的“鬼”究竟指人指物尚難確認,那么“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無眚。”(《周易·訟》)“吏二縛一人詣王。”(《晏子春秋·雜篇》)中的“邑人”“吏”指人則確然無疑。由此不難看出,先秦典籍在表示物量關系甚至名量關系的語境下,數詞或數量詞尤其是度量衡單位詞常常放在名詞后作定語。換句話說,秦以前的古人在表示名量關系和物量關系時,原本應當是有區別的:即表示名量關系時,數詞直接放在名詞前;表示物量關系時,則數詞或數量詞放在名詞后,尤其是數詞與度量衡單位結合時一定要放在名詞后。只是后來隨著時代的發展,表示名量關系的數量詞也可放在名詞后了,但也僅限于數量詞置于名詞后,若是用單個數詞表示名量關系時是不會置于名詞后的(筆者曾考查過《周易》全文,無一例外)。從思維習慣來看,這應當是古人對人和物在數量關系上進行的有意區分,或許與古人的禁忌有關。從實際語用層面來看,數詞直接置于名詞后作定語表名量關系的用例很少,也恰恰說明了古人在具體使用數詞時,究竟是指人還是指物其表述方式是明顯有區別的。至于數量詞組置于名詞后作定語應當說是古人的一種習慣性表述,由于早期的古人使用量詞較少,既然單個數詞表示物量關系時可放在名詞后,那么當數量詞組合在一起表示物量關系時自然也要放在名詞后作定語。對此,王力先生也曾明確指出:“就名詞、數詞、單位詞三者的結合方式來說,有一種發展情況是非常值得重視的,那就是在先秦時代,數詞在兼帶單位詞或度量衡單位詞時,位置是在名詞的后面。”[7]而大量的實際用例不僅證明王力先生的觀點完全正確,也說明了這確實是古人的一種語用習慣。
三、特殊語境下的定語后置
我們這里所謂的特殊語境,是與習慣語境相對的概念。從語序來看,習慣語境的句式一般表現為常規的定中結構。而當定中結構不能準確表達語義時,就說明所處的語境已非習慣語境,而處于非常規的特殊語境。由于正常語序不能表達特殊語境的內容,所以只能采取靈活變通的方式運用超常語序來解決問題。李晉荃先生關于句子結構的易序和變位,其語用功能一是“適應話題化的需要”,二是“適應突出主要信息的需要”,三是“適應句式和押韻的需要”。[2]將這一概括放在特殊語境下的定語后置上來考察同樣適用。如:
(1)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荀子勸學》)
(2)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云之。崔嵬(《楚辭涉江》)
(3)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詩經桃夭》)
(4)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者汶汶乎?(《楚辭漁父》)
(5)有一言而可乎以終?身行(之者《論語衛靈公》)
(6)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孟子梁惠王下》)
(7)齊人有,馮貧諼乏者不能自存。(《戰國策齊策》)
(8)杞國人有。憂天地(崩墜身無《所寄廢寢列食者子天瑞》)
(9)人之涂,其左體三被濡千衣人而,赴火右者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韓非子內儲說上》)
(10)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時者也。”(《孟子萬章下》)
以上各例,從其外部形式上來看,中學語文教學界一般分為四類[8],許仰民先生分為六類[9]。分類標準不同所分類別自然不同,此乃通理。但由于分類不同,學界對此也有頗多爭論,對前述原型語序和衍生語序所形成的定語后置學界一般是認可的,而對超常語序所形成的定語后置現象有些學者并不認可,甚至因此認為古漢語中不存在定語后置現象。這當然未免偏激,但也從另一側面說明拿具有局限性的固定形式去套用和分析變動不居的超常句式是行不通的。以上例句,從其內容結構上來看,大致可分為形容詞性定語后置和名詞性定語后置兩類,王锳先生將之分為“形容詞及謂詞性成分作定語后置”和“‘者’字結構作定語后置”兩類。由于王先生將“者”字結構視為名詞,所以同我們的分類實質上并無區別,只是表述略有不同而已。從語言理論上講,可作定語的詞類無非名詞、形容詞、數量詞、代詞等幾類,前述習慣語境下的定語后置涉及到名詞和數量詞,而特殊語境下的定語后置涉及形容詞以及名詞或名詞性結構符合語言規律,因古漢語中代詞作賓語常常后置,而代詞作定語則不后置,故不涉及代詞定語后置問題。可見,分析以上例句是否為定語后置還得從其語義、語境入手,方能得到準確的結論。
例(1)為形容詞作定語后置,從上下文語境看,“利”“強”兩個后置定語分別起強調作用,目的在于突出“蚓”缺乏必要的可用于勞作的器官以及自身弱小的程度,其中“之”為結構助詞起聯結作用(下三例“之”用法與此同)。例(2)“陸離”“崔嵬”兩個形容詞作后置定語,不僅起強調作用,以突出寶劍之長之美和帽子之高之美;從詩歌語用角度分析,還有上下呼應、音韻和諧之作用。例(3)形容詞“夭夭”作后置定語同樣具有強調和使音韻和諧的作用。例(4)形容詞“察察”“汶汶”作后置定語,基本作用與例(3)相同,此外二者還有對舉作用。以上四例均為形容詞作后置定語,從語用層面講,都不屬形容詞置于名詞前作定語的原型語序(或常規語序),均屬超常語序,而這種超常語序只適用于突出強調或呼應、對舉、音韻和諧等特殊語境。例(5)“可以終身行之者”為名詞性“者”字結構作后置定語,起特意說明作用,“而”為連詞起聯結作用。例(6)結構與例(5)相同,后置定語作用也同于例(5)。例(7)“有馮諼者”名詞結構直接置于中心語后作定語具有特意說明作用,這種句式上古漢語中較為常見。若與“馮諼者,齊人也”的判斷句相比,明顯可以看出前者為特殊敘述,后者為一般敘述;前者似有“在某地有這么一號人”之義,在上下文語境中往往略帶戲謔意味,后者則為比較正式的人物介紹,在上下文語境中一般具有鄭重意味。例(8)結構同于例(7),“有憂天地崩墜身無所寄廢寢食者”這個后置定語的特意說明作用更加明顯,從語境分析戲謔意味也更濃。例(9)(10)結構相同,均為“者”字結構作后置定語,并用結構助詞“之”與中心詞相聯結。從上下文語境來看,例(9)“涂其體被濡衣而赴火者”特指為了領賞而作出非常舉動的人,例(10)“清者”“任者”“和者”“時者”則指某一方面的才能非常突出的圣人,均有褒揚意味。當然,也有學者將例(9)(10)的“者字結構”內容視為復指,不無道理。我們認為作為超常語序的定語后置起突出強調作用或許更好。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發現,上古漢語定語后置現象,均有其適用的語境,其中既有表述概括事物與具體事物的鮮明區別之語境的,又有用于名量與物量區分之語境的,還有或用于強調、或用于特意說明、或因音韻和諧等特殊語境的。萬變不離其宗,無論以上所述的那種情形,它都與正常的定中結構語序不同,表達的內容也往往是與定中結構不易表達或與之有所區別的內容,這其實正是古漢語存在定語后置現象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