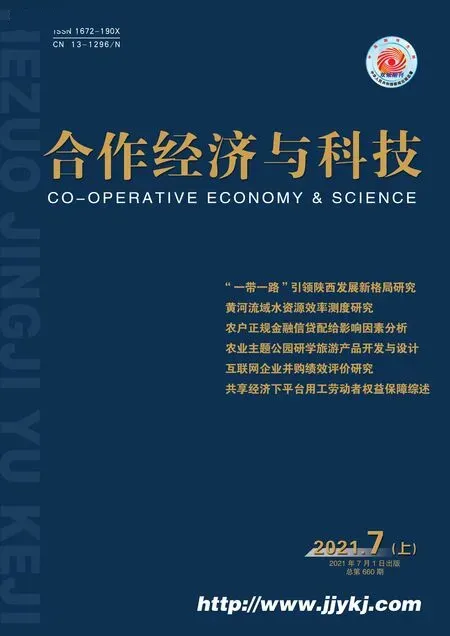農村養老服務有效供給理論與對策
□文/楊雨婷
(南昌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江西·南昌)
[提要]從公共產品理論視角出發,對農村養老服務作為準公共產品的性質進行理論與現實的闡述,并以此說明多元主體供給農村養老服務的必要性。此外,在強調政府承擔農村養老服務有效供給的第一行動者的基礎上,對于政府如何保障農村養老服務有效供給進行深入分析,以期對政府保障農村養老服務供給提供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上的幾點建議。
一、問題背景
民政部養老服務司李邦華于2020年10月23日在新聞發布會上指出,根據相關預測,“十四五”期間,全國老年人口將突破3億,我國將從輕度老齡化邁入中度老齡化。隨著人口老齡化逐漸加重、農村勞動力流失加劇,我國農村地區人口老齡化的嚴重程度要高于城市,但農村養老服務的發展明顯落后于城市。農村地區由于其傳統農業經濟的發展慣性和較落后的思想文化環境,社會資本和社會組織難以在農村地區扎根發展,農村經濟發展水平遠遠落后于更加開放包容的城市。此外,我國為推進社會民主進程而實行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在農村地區表現為村民自治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等,但由于農民普遍文化水平有限,個別“農村精英”也隨著市場經濟浪潮流入城市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因此能力有限的村民自治組織——村委會只能常常依附于基層政府,不能夠真正發揮其為自己謀發展、謀福利的主觀能動性,這使得農村的政治環境和政治資源都存在某些不足。可以認為,政府、市場和社會三大主體的輻射作用在農村地區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席,村自治組織調動力有限且執行力不足使得村自治組織難以充分利用政府資源和推行養老服務,資本的“洼地效應”使得農村地區難以充分享受市場經濟帶來的經濟效益,社會組織的發展受限和資源匱乏使得養老服務機構難以在農村地區充分提供養老服務。因而農村養老服務的提供亟須重新激發、整合這三大主體的影響力和作用力,其中政府在我國“強國家-弱社會”的格局下作為國家統治社會的主要力量,秉承著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理念,掌握著引導決策、分配資源的巨大權力,理應成為推動農村養老服務有效供給的第一行動者,保障農村養老服務的有效供給。
本文試圖從公共產品理論的視角論證農村養老服務的供給需要由多元主體共同支持,為多元主體供給農村養老服務提供理論意義上的現實依據,并且探討政府如何保障農村養老服務的有效供給,為政府承擔農村養老責任、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提供一些建議。
二、理論與現實的闡釋
公共經濟學將社會產品分為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私人產品是為滿足不同的個人偏好需要的社會產品,通常由個人或企業進行提供,而公共產品是為滿足大眾共同需要而產生的,一般由追求公共利益的政府來提供。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是判斷是否為公共產品的關鍵因素。所謂非排他性,是指無論提供公共產品的一方持有哪種意愿,產品一經提供出來就不能夠排除其他人享有產品,公共產品的受益對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性;非競爭性是指公共產品一經提供,增加一個人享有公共產品所需要的邊際成本為零,需要注意的是,這并不意味著增加一份公共產品所需要的成本為零,而是說在一定的公共產品數量下,增加一個人從公共產品中獲得收益的邊際成本為零。
根據以上這兩個標準可以將不同的物品劃分為純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純公共產品既具有非排他性又具有非競爭性,比如國防和法律制度,任何人都能夠享受,無法花費巨大成本做到將某一個人或某一群人排除在享受該產品之外,這就是非排他性,而國防和法律制度并不存在總量的限制,即無論多少人享有這兩種公共產品,都不會影響其他人的使用,這就是非競爭性。準公共產品是只具有非排他性或只具有非競爭性的產品,如只滿足非排他性但具有一定競爭性的義務教育和公園,再比如不具有競爭性卻具有一定排他性的自來水。私人產品是既具有排他性,又具有競爭性的產品。但由于公共產品產生的情境是千變萬化的,以上劃分的標準也應適應實際情況。因此,在確定一種物品是否為公共產品時,必須要考慮受益者人數以及能否將受益者排除在該物品的享用之外。受益者人數眾多且無法利用技術手段將任何一個受益者排除在對該物品的享用之外時,該物品就可被視作為公共產品。因此,農村養老服務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公共產品,我國老年人口數量龐大,尤其是農村地區的老年人,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中提到的“老年人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有享受社會服務和社會優待的權利,有參與社會發展和共享發展成果的權利……國家和社會應當采取措施,健全保障老年人權益的各項制度……”,充分表明養老服務是對老年人全面覆蓋的公共產品,進一步理解為農村養老服務是不排除任何一個農村老年人享受養老服務的公共產品,但由于農村養老服務的提供需要有限的社會資源的支持,而每個農村老人是較為獨立地享受社會資源與公共服務,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競爭情形,這種有限的競爭性可以分別從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上來闡釋。
(一)宏觀:體制資源不平衡引發的競爭。我國城鄉二元體制的實行造成城市與農村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這種差距體現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基礎設施建設、社會資金投入、財政撥款和公共服務覆蓋面等,且隨著市場經濟對農村“自給自足”生活的沖擊加劇,大多數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流入城市奔波打工導致農村人力資源“空心化”,因而養老服務在農村的供給面臨供給不足、供給質量低且需求量龐大的艱難困境,部分老人可能因為子女有較優經濟條件會被遷入城市社區中享受比較優厚、舒適的養老服務,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養老服務資源消費的競爭。
(二)微觀:資源有限引發的競爭。從現實效果上來看,農村養老服務機構的建設的確為解決農村養老服務的需求取得了比較顯著的成果,不僅是養老服務模式從單一養老服務機構發展為“三院合一”、“五院合一”等“多院合一”這種在整合資源、互補優勢、節約成本和提高管理水平方面具有重要進步的運作模式,而且從互助養老的角度出發創新了“集體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務”的農村互助養老新模式——農村互助幸福院。但無論模式如何發展、創新,農村養老服務機構提供的養老服務都是一種公共產品,這決定了其可提供的總量受到限制,一個農村互助幸福院或養老服務機構可提供的養老服務和基礎設施都是有限的,老年人數量增加會影響每個老年人對養老服務和基礎設施的使用,當老年人數量超過養老機構的承載力時就會出現“擁擠”現象,這種“擁擠”會直接造成養老服務質量的下降。此外,另一種養老服務模式——居家養老服務模式是由服務人員到老年人的住所為其提供分散的養老服務,這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老年人同處一室的“擁擠”,但由于居家養老服務也是由有限的服務人員和服務設施支持而成,因此無論是機構養老服務還是居家養老服務,養老服務的享有及基礎設施的使用都會使老年人之間存在一種競爭狀態。所以,無論從宏觀層面還是從微觀層面來看,農村養老服務都具有一定的競爭性,這表明農村養老服務實際上是一種準公共產品。從準公共產品的特性出發,結合現實問題就能夠清晰地理解農村養老服務由政府、社會和市場等多元主體供給的必要性。
三、多元主體供給的必要性
由于政府自身的局限性,現實中的政府不可能有效的、無限的供給農村養老服務,政府所承擔的公共服務不僅僅只有農村養老服務,如果政府全權包攬農村養老服務,由政府主體自身承擔農村養老服務需求的調查、農村養老服務模式的設計與應用、農村養老服務資源的供給以及農村養老服務的落實等等一系列農村養老服務的供給過程,那么政府很可能因為“不堪重負”而成為一個失敗的政府,導致農村養老服務提供的數量、質量都難以得到保證。盡管政府承擔著管理社會各方面的諸多職能,但政府不是萬能的,因此政府必須和其他社會主體進行合作,實現功能優勢的互補。此外,政府因其內部成員或領導在某種程度上充當著“經濟人”的角色,因而現實中的政府并不是時時刻刻都為公共利益著想,政府機構謀求內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謂“內在效應”現象在各個國家中時有發生,這使得政府不能夠在農村養老服務供給的每一個環節都公正、高效且不失偏頗地追求公共利益、提供養老的公共服務。此外,從專業性程度上看,政府相比于市場中的專業主體來說的確處于弱勢,農村養老服務供給的基本前提中所需要的數據調查并不是政府所必須承擔的有意義的工作,而且政府自身的資源是吸取社會的部分資源而構成的,政府所能夠投入到各領域的資源是有限的,因此政府行動就會出現對養老服務這種準公共產品的供給失靈和投資不足的現象。
所以,農村養老服務的供給可以通過引入市場機制來彌補政府在供給養老服務過程中失靈的領域和環節,實現一部分由政府承擔,一部分由市場承擔的互補機制。經濟條件較優的家庭會選擇通過付費的方式將老人托付給一些營利性養老機構,由于這些營利性養老機構與老人是“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關系,而且市場中不止一家營利性養老機構,養老機構彼此之間存在競爭的關系,因此老年人在營利性養老機構中所享受到的養老服務會優于政府提供的無償的養老服務。但是,市場競爭中的“非理性”會導致營利性養老機構之間的惡性競爭,以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擠壓、壓榨消費者(老年人)的利益等情形,因此為了減少市場競爭對農村養老服務的破壞性,農村養老服務除了由政府和市場分擔一部分之外,再引入一個新的主體滿足農村養老服務的需求,緩沖供給服務的政府和市場主體由于自身不可避免的逐利性而降低農村養老服務的質量,這個新主體就是社會組織。
社會組織是因追求共同的美好愿景而成立的非營利性組織、慈善機構和志愿組織等,這種組織機構提供農村養老服務完全是出于道德感、同理心等善的理念,因此社會組織提供的農村養老服務是更高質量、更有情懷的。但社會組織的發展常常不夠理想,由于政策支持力度不夠、資金短缺、志愿人才緊張及組織管理不善等原因無法發揮其潛力。
應當看到,各主體都有其獨特優勢和一定的缺陷,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基礎設施建設、社會提供免費的短期服務、市場提供滿足不同需求的多樣化服務。正是這種互相補充、互相依賴的關系使得準公共產品有限的競爭性得到緩解及非排他性得到擴大。首先,政府、社會組織和市場分別發展農村福利院、非營利性農村養老服務機構、營利性農村養老服務機構三種養老服務機構滿足不同的農村老人的養老需求,能夠通過增加供給類型和供給數量使農村養老服務消費的競爭性得到分散;其次,政府、社會組織和市場分別在農村養老服務供給過程中發揮監督兜底、溝通傳達和專業護理的作用,確保農村養老服務全面覆蓋到農村地區的每一個老年人,并為其提供有效的、及時的農村養老服務,能夠保證農村養老服務的非排他性。
四、政府保障農村養老服務有效供給的途徑
政府作為供給農村養老服務的第一行動者,必須以身作則。農村養老服務的非排他性要求政府引入并引導其他主體進行有序、有效供給農村養老服務,實現農村養老服務的全面覆蓋;農村養老服務的有限消費競爭性要求政府通過財政供給增加對農村養老服務設施和基礎工程的提供,并且減少私人產品的供給,實現資源在公共產品上的有效配置。
(一)協同多元主體供給服務,保障服務全覆蓋。首先,政府要積極吸納其他主體進入農村養老服務供給的體系,降低社會組織注冊、登記的準入門檻,增加各種類型的社會組織以不同的方式、渠道為農村提供養老服務,保證農村養老服務供給的資金來源多樣化、服務覆蓋全面化。其次,通過政策支持鼓勵其他主體提供農村養老服務,可以為發展營利性農村養老服務機構的企業和發展非營利農村養老服務機構或農村養老服務項目的社會組織提供稅收減免政策,并為該企業或社會組織提供優質的人才支持,保證其組織中的成員就業的優先性,對于發展良好的社會組織盡可能提供財政補貼,保障其充分發揮其組織優勢,提高農村養老服務的供給質量。
(二)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保障供給條件。基礎設施建設作為政府追求社會福利最優化和公益性職能最基礎的表現,是政府在保障民生發展工程中重要的責任擔當。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該地區能否有優質的企業和社會組織發展,保障發展營利性農村養老服務機構的企業和發展非營利農村養老服務機構有效提供農村養老服務的前提就是建設方便其提供農村養老服務的基礎設施,從而增加其提供農村養老服務的“機會”。
(三)培育良性的養老服務市場,保障公平競爭。農村養老服務市場中可能會出現欺詐、惡性競爭等市場失靈的現象,因此政府必須發揮好其市場監管的作用,及時到各營利性的農村養老服務機構進行實地調研,檢查農村養老服務供給產品的質量,對于農村養老服務供給市場中損害老年人利益、惡意侵占其他服務機構市場份額的行為予以堅決打擊,保證各服務機構有序、有效進行農村養老服務的供給,保障養老服務的供給市場良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