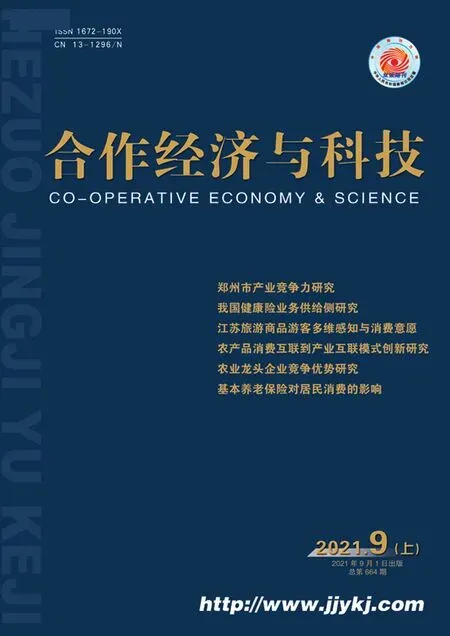市場化城市更新中個別征收法律問題研究
□文/徐 寧
(江西理工大學 江西·贛州)
[提要]深圳是市場化城市更新的典型城市。市場化城市更新中會因為“市場失靈”陷入談判僵局,繼而無法推進產權集中。深圳通過地方立法,確立個別征收模式,在市場化城市更新中介入行政權。對于該模式在程序上還需要完善,如增設公益認定程序、明確程序啟動、適當簡化征收流程。
在市場化城市更新中,產權集中難是近幾年困擾各地城市更新的難題。深圳最新施行的《深圳經濟特區城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更新條例》),《更新條例》中提出個別征收模式。個別征收以剝奪少數人的不動產權來讓城市更新中所需的產權集中,其使這些少數人被迫遷離原先的生活環境,城市的發展不能打著公共利益的旗號肆意的犧牲少數人的權益。本文以深圳市個別征收為例,來研究市場化城市更新的產權集中的相關法律問題,以期引起更多人對個別征收的關注。
一、市場化城市更新與個別征收的內涵界定
(一)市場主導下的城市更新。城市想要在現有基礎上獲得更好的發展,城市更新是不可回避的一個問題。一般認為,城市更新是指由實質上維護、整建、拆除等方式使城市土地得以經濟合理的再利用,并強化城市功能,增進社會福祉,提高生活品質,促進城市健全發展的活動。
深圳的城市更新模式主要是以市場化城市更新為主的,也就是“政府引導、市場運作”。“政府引導”主要體現在政府通過各種管理手段引導、規范更新活動,包括:政策支持、規劃引導、審批管理,一般情況下政府并不會主動參與到城市更新中。重點在于“市場運作”,其主要體現在以市場作為更新主體,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
(二)個別征收的內涵界定。征收是指政府為了促進公共利益,依法定程序,強制性無償取得相對人的財物所有權,并給予當事者相當補償之行為。征收會直接導致所有權喪失,理論上一般將其視為對所有權的最根本限制,征收依據強大的國家權力,對相對人的財產占有、使用和收益權的進行單向強制性轉移。因此,征收關系不是自發形成的,具有不平等性和非自愿性。個別征收是市場化城市更新為背景,主要是用以解決在產權集中時所出現的“談判僵局”,是針對零星的房屋進行的征收,而不是成片的一體征收。
二、市場化城市更新的困境與破解路徑
(一)市場化城市更新中“市場失靈”。深圳采取市場化城市更新模式,本希望通過引入多元主體參與,通過市場化運作來提升城市更新的效率。但是,多元主體的參與,必然伴隨著多樣化的利益訴求。完全交由市場來運作,所產生的后果是不盡如人意的,也就是帶來所謂的“市場失靈”。有學者將造成市場化城市更新中“市場失靈”歸咎于釘子戶現象,這種觀點主要是站在政府視角或是開發商視角去看待這個失靈現象。還有一種觀點,就是將失靈現象視為“談判僵局”,其意指在市場化城市更新的開發商與業主作為平等的民事主體在簽署搬遷協議或是產權購買時,出于對補償不能達成一致,進而陷入互不妥協,導致無法達成民事合同。另外,還有一種觀點就是采用司法權介入的做法,構建強制拍賣制度。
(二)深圳設置個別征收的立法實踐。實踐中,深圳市政府曾做了具體的嘗試,深圳市政府為打破“談判僵局”的回應,在達成一定條件之下,自己組織實施相關更新活動。也就是在《實施辦法》中規定:在達成兩個90%的情況下,相關主體可以申請政府介入,政府綜合考慮項目的緊迫性、可行性及補償方案的合理性等要素,最終決定是否由政府來組織實施。雖然相較于全體介入難度會稍低,其第二款緊迫性等規定出發點是防止政府濫用該條進行介入,但是實際上因為其模糊性、風險性導致政府很少會援用該條而介入相關的更新項目。
2021年3月1日,深圳市實施的《更新條例》正式施行深圳市破局之招,也就是個別征收模式,該模式對征收啟動最低產權限度、事后相關救濟及征收后的處理進行相應的規定。該模式選擇介入的是行政權,通過行政征收的形式打破僵局,以此推動城市更新進行。
立法者對該模式寄以厚望,希望能破解搬遷難的問題,也就是解決市場化城市更新程序推進的關鍵問題,即搬遷難的問題。但是,從立法上來看,僅有寥寥一兩個條文加以規定,對于具有的程序并無太多表述,所以還有諸多地方需要完善。
三、市場化城市更新中個別征收程序的完善
(一)增設公共利益認定程序。市場化城市更新是以自愿、平等為基本原則,正因如此,相較于普通征收,個別征收在公共利益論證上,具有更明確的標準和更高的要求。公共利益是個別征收賴以成立的基礎,是行為合法性和正當性的來源。如果缺乏公共利益,個別征收將被詬病。所以,應當在個別征收中做好公共利益認定的程序設置,政府介入市場行為需要有正當性理由。雖然,個別征收被征收的對象是少數人,但是不能因為被征收人是少數人,就假定征收具有公益性,多數人利益并不等同于公共利益。如果公共利益存在與否有爭議,行政機關又介入市場主體與業主的糾紛,就存在官商勾結的嫌疑,少數人訴求未得到其正反饋,很難保證不會有人走向極端,威脅社會穩定。
對于公共利益認定程序的設置,應當充分保障被征收人的知情權、參與權,平衡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所以,為了更好地規范土地征收程序,應在個別征收程序前增設公益目的認定程序。該程序的設置,筆者認為可以設置在談判僵局發生之后,征地決定程序之前。談判僵局是行政權介入的現實需要,征地決定必須以公共利益認定為前提。未經公共利益程序認定的,其征收決定將違背法律規定的土地征收必須以公共利益為目的之原則。
對其具體設置問題,筆者認為可以進行如下規定:首先,土地征收的決定機關征收申請時,擬被征收方及相關人獲知公共利益認定的,可以向決定機關申請聽證。征收決定機關接到申請,應當組織聽證。在召開聽證十五天前告知當事人時間、地點,對于聽證會的時間、地點,應當遵循便利當事人原則。聽證會的舉行,應該充分聽取被征收方的意見,同時對于各方意見應當載入聽證會筆錄。聽證會筆錄是解決后續產生糾紛的重要依據。征收決定機關在做出公共利益認定時,對于聽證意見未采納的應當書面說明理由。就該認定,被征收方或利益相關人可以就此復議,對復議結果不服的,可以提起訴訟。在訴訟完結時,不得依此認定做出征收決定。對于公共利益認定,應當規定其認定結果的強制性和確定性。可以進行規定“未經公益認定或者未通過公益審查者,不得核準征收。如果作出核準征收的決定,該決定無效”。
(二)明確征收程序的啟動。根據《更新條例》第32條的規定,搬遷安置協議的合法產權比例不低于95%即可對剩余部分進行征收。這一表述是表明在何種情況下可以進行個別征收,是征收程序啟動的條件要求。對于征收程序如何啟動、何時啟動,條例并沒進行明確。政府到底是依申請介入進行征收,還是依職權進行征收;是一經達到95%以上就開始征收,還是在窮盡其他方式后方才進行,當前這些問題尚存在模糊。個別征收程序及時啟動,是個別征收制度發揮打破僵局推進城市更新的前提與基礎。對于個別征收程序啟動者與何時啟動都不明確,會產生不良后果。第一,如果在面對少數強硬的拒絕城市更新的業主時,政府、開發主體、業主三方有可能導致扯皮,都不愿去冒風險,進而致使個別征收的作用難以發揮。第二,一經達到95%的比例,就立馬介入國家權力,粗暴征收業主的合法財產,故此,有必要明確征收程序如何啟動。
筆者認為,依申請啟動征收是一項有效的途徑。個別征收雖然可以實現公共利益,但是其中也帶有私人利益,政府依職權直接介入有違市場主導的原則。應該明確,實施主體或是已經簽訂協議了的業主申請政府啟動個別征收程序。對于何時可以啟動,筆者認為,其應當受比例原則限制,窮盡其他辦法方可征收。即征收是必不可少的,無法以其他方式替代,如果可以用其他非征收方式替代的,就沒有必要發動征收。在還未進行協商、或是調解之前,不得申請啟動征收程序。
(三)適度簡化征收流程。實體權利需要等到程序的保障,沒有程序保障的權利將永遠停留在紙面上。在一個理想的行政程序中都會兼顧“公正”與“效率”二者,但是在實際中對于二者往往會有一個抉擇問題。對市場化城市更新中個別征收所適用何種程序,《更新條例》并沒有進行明確。對于個別征收程序,因為其在數量上的極少性,制度設計的目的也是為推進城市更新的進程。其可以在一定的程序上進行簡化,如果對該程序都不加以簡化,而是采取和普通征收一樣的程序,那個別征收的意義將喪失大半。個別征收應當比普通征收更加追求效率,也更具簡化的基礎。從《更新條例》將個別征收的決定權賦予給區政府可以看出個別征收程序可以也需要是在普通征收程序上進行適當的簡化。
普通征收一般需要以下六步方可進行征收:決定程序、告知、調查、征收補償、訂立協議并搬遷、強制執行。普通征收程序,在程序的設置上較為繁瑣,目的在于保障當事人的財產權不受非法侵害。首先,個別征收程序中公告程序明顯可以進行簡化。因為個別征收程序征收對象相較普通征收的對象,少之又少。以張貼公告的形式加以告知,顯然是多余且耗時的,其不需要通知多數人知道將要被征收,也達不到讓相關人員進行共同商議形成多數意見的能力。所以,對于個別征收在告知程序上,可以采取單獨送達的形式加以告知相對人,無需再行公示。其次,對于補償程序也可以適當簡化,應當充分聽取被征收人的意見,但是不需要進行公告,也不需要進行所謂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最后,對于相應的程序都可以在期限上進行限縮。對于相對人對補償方案等意見提出的時間加以削減。總而言之,個別征收制度應當比普通征收可以也必須進行相應的簡化,否則其對在市場化城市更新中無法成為破局利器。
四、結語
我國城市發展已經進入存量用地時代,城市從追求速度轉向質量、效率,市場化城市更新模式會被越來越多城市所接受。在國家立法缺失的情況下,《深圳城市更新條例》公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深圳市用地方性法規的形式對城市更新加以規范,確定的行政權介入市場化城市更新的道路。在市場化城市更新中通過個別征收的形式,介入國家權力來完成產權集中,如何確保征收的正當性、公益性是需要嚴肅對待的一個問題。對此,未來立法應當加強程序上的細化完善。堅持正當程序,保證少數人的訴求能得到相應的釋放。兼顧公平、效率推動城市向更好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