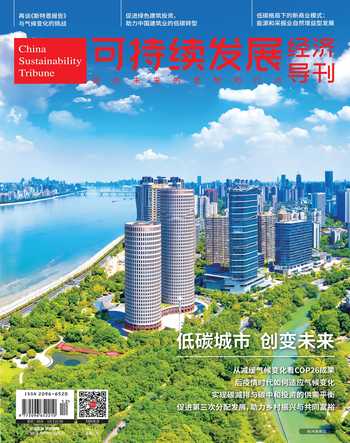從減緩氣候變化看COP26成果
朱松麗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第二十六次締約方大會(COP26)在歷經曲折艱難后結束,一如所有具有某些歷史意義的氣候會議。COP26是《巴黎協定》進入實施階段后召開的首次締約方會議。在約兩周時間內,各締約方共同努力彌合分歧、擴大共識,最終基本解決《巴黎協定》實施細則遺留問題,并就提高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和努力做出安排,為落實《巴黎協定》奠定了良好基礎。
對這次暌違兩年的大會成果,各國和各界的評價兩極分化,有的表示謹慎樂觀,有的表示悲觀失望。這其實再次反映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氣候大會能夠達成“人人都不滿意但人人都能接受”的成果相當不容易。在以《公約》為主渠道的全球氣候治理中博弈和合作并存,博弈的結果是為了合作,為了避免最壞結果出現。縱觀整個會議成果,在兩個目標——完成《巴黎協定》實施細則遺留問題和提高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力度——方面均有所斬獲,適應、減緩和資金技術支持的成果基本全面平衡,并且大大提升了適應的地位,應該說是各國在全球疫情尚未平穩、全球化進程遭遇挑戰的背景下所能形成的“最大公約數”。
在氣候治理中,適應和減緩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在一定意義上,積極有效減緩氣候變化是人類社會面對氣候危機所采取的“最大的適應”。本文即從減緩氣候變化的角度對COP26成果進行評述。
減緩氣候變化面臨的嚴峻形勢
2015年達成、2016年簽署并生效的《巴黎協定》正式確定了本世紀末溫升幅度相比工業革命前“遠低于2℃、力爭1.5℃”的全球減緩氣候變化目標,同時確立了以全面參與、國家自主貢獻(NDC)和全球盤點為核心的減緩機制。根據各國提交的目標年為2030年的第一輪NDC(NDC1)進行測算,本世紀末的溫升幅度大約為2.7℃。
氣候變化并沒有因為人類形成政治共識而放慢腳步。2019年,上萬名科學家共同宣布地球正面臨“氣候緊急狀態”。2020年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呼吁全球所有領導人“宣布進入氣候緊急狀態”。2021年2月,聯合國安理會就氣候變化與和平和安全問題舉行了高級別辯論,指出氣候造成的破壞是危機的放大器和倍增器,氣候變化加劇了動蕩和沖突的風險。如果不努力控制溫室氣體的排放,未來氣候系統變化造成的影響和風險將比預計來得更為劇烈 。2021年8月,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六次評估第一工作組報告發布之后,古特雷斯再一次呼吁“紅色警報已經拉響(a code red for humanity)”。
在基于國情的原則基礎上提升國際集體減緩目標和行動成為氣候治理的當務之急。2019年以來,本世紀中葉實現碳中和成為新的全球競爭賽道,但雄心勃勃的遠期愿景目標并未對中近期目標形成實質推動。如何鼓勵各國提出與遠期目標相吻合的2030年中期目標成為COP26面臨的現實又緊迫的任務。
COP26在減緩氣候變化方面形成的成果和共識
在熙熙攘攘的COP26大會進程中,有兩條關于減緩氣候變化的軌道并行,我們姑且稱一條是“公約外”,一條是“公約內”。
1. “公約外”的減緩宣言
“公約外”指各類氣候治理主體借COP26這個平臺宣稱成立或強化的各種減緩倡議。簡單梳理一下,COP26形成或強化了如下機制:一是東道國英國主導的機制,包括停止新的國際化石能源投資和“煤電清潔轉型宣言”。前者有25個國家和多邊銀行參與,承諾從2022年起原則上終止各自的國際化石能源投資(不僅僅是煤炭投資),后者鼓勵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分別在2030年和2040年前淘汰煤電,同時立刻停止新建煤電站。該宣言在大會上得到了近90個國家、地方政府和公司的支持。越南、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的加入備受矚目,其中后兩個國家為“有條件加入”,即不承諾立刻停建煤電站。與2017年英國和加拿大共同發起的“助力淘汰煤炭聯盟”合并估計,大約有190個國家和地區加入了“去煤”陣營。
二是美國和歐盟組織了“全球甲烷減排承諾”,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加入,承諾到2030年將甲烷排放在2020年水平上削減至少30%。在科學和政治的共同推動下,甲烷減排成為一個“熱詞”。從科學上看,甲烷的短期溫升效應要遠大于中長期(20年內甲烷增溫效應是CO2的80倍),如果能將甲烷排放消滅在萌芽中或排放初期,削減甲烷在空氣中的滯留時間,所獲得的減緩效益要大于減少等量的CO2排放的效益。2021年發布的IPCC報告首次強調了甲烷減排的重要性,闡述了甲烷控排對減緩升溫的作用以及與空氣質量改善的關系。
三是占全球森林覆蓋率90%的130個國家承諾到2030年將毀林排放降低為零,中國和美國是其中的重要成員,同時美國也發布了首個“保護全球森林計劃”,承諾通過保護全球生態系統加強碳匯建設。美國還發起了“第一驅動力聯盟”(First Mover Coalition),聯合25家成員單位(以大型企業為主)成立“綠色采購俱樂部”,目的是通過大幅度提高對低碳產品的需求,推動生產端綠色轉型。
四是一些小多邊和雙邊活動,典型代表美國聯合歐盟、英國、法國和德國與南非建立伙伴關系,共同注資85億美元幫助南非加速能源低碳轉型,爭取未來20年避免10億-15億噸溫室氣體排放。美國還和丹麥聯合發布了零碳航海行動。美國試圖通過以上這些行動恢復其世界氣候領導力的意圖十分明顯。
在COP26召開期間,多家全球性研究機構對以上新承諾帶來的影響進行了快速反饋。國際能源署(IEA)認為,如果這些新舊目標能夠全部兌現,全球有可能實現1.8℃溫控目標。國際社會普遍表示質疑。其中,“氣候行動跟蹤組織”(CAT)相關的研究結果顯示為2.4℃,并指出,如果所有的遠期目標和與之相適應的中期目標都得到不折不扣的實施,實現巴黎目標是有希望的,但目前的最大挑戰是2030年目標力度遠遠不夠。
2.“公約內”的磋商成果
“公約內”的正式磋商要艱難得多。最終呈現在大會一號決定中的關鍵共識顯示:
第一,《巴黎協定》所確定的全球減緩目標得到重申并向前推進了一步。在全文短短的三個段落之間,1.5℃出現了四次,并強調“決心推動溫控1.5℃所需的努力”。與此相伴,《 IPCC 1.5℃特別報告》科學結論“2030年全球CO2排放比2010年降低45%”也被納入決定文本中。相比1.5℃特別報告在2018年COP24上所遭遇到 “阻擊”,此次大會切實提升了科學在各國政治博弈中的分量。
第二,明確了加速能源轉型的重要性和路徑選擇,包括加速削減(phase down)無減緩措施的煤電廠、取消(phase-out)效率不佳的化石燃料補貼。盡管相關文本引起較大爭議,討論持續了很長時間,但這是第一次在《公約》大會決定中提出如此明確的減緩措施。
第三,要求各國在必要和考慮不同國情的情況下重新評估和強化2030年行動和目標,爭取與巴黎目標相一致,相關任務應在2022年COP27之前完成。在大部分國家已經于COP26之前提交了經過更新的NDC1后,依然鼓勵各國再次進行評估和更新,邏輯上與減緩的緊迫形勢一脈相承,但現實可行性必然遭遇挑戰。
對以上成果的初步分析
首先能看到的依然是雄心勃勃的大會決定與現實之間的巨大虧空(Credibility Gap)。綜合結果顯示,現有NDC路徑下2030年排放將比2010年增加13.7%,是1.5℃路徑要求的兩倍。大會成果中重申的IPCC科學結論雖然只具有象征意義,但傳遞出的信號非常強烈。這里可以進行假設性估算:在2030年全球CO2排放比2010年降低45%的理想目標下,假設2030年發達國家CO2排放比2010年降低60%(目前發達國家最高的減排比例也就55%),粗略估算2030年發展中國家也必須整體減排至少33%;如果發達國家屆時減排80%,那么發展中國家需要至少減排17%;即使2030年發達國家就達到凈零排放,發展中國家屆時仍需要至少回到2010年排放水平。這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在這樣的差距面前,各國NDC1都明顯不足,而不是哪一個國家不足。那么,各國是否將如大會決定所鼓勵的那樣再次更新NDC1?從目前看,大部分國家都持否定和觀望態度。決定墨跡未干,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就宣布,不考慮重新更新2030年目標。不久之后,一向積極的歐盟也放出了類似的風聲。美國則強調“如果有必要才更新,不是強制要求”。作為COP26主席國的英國尚沒有表態,英國工商界倒是給首相發出了公開信,鼓勵英國率先更新NDC政策包 。相關智庫則建議各國可以首先將“公約外”的承諾和行動正式化,在COP27前提交《公約》秘書處,將來接受透明度機制所規定的專家評估和多邊進程討論。
從悲觀角度看,COP26在減緩氣候變化、實現巴黎目標面前給各國“畫了一個餅”,可望不可即。從樂觀角度看,在碳中和競賽和持續提升2030年目標進程中,不可避免存在“冒進”和“相互施壓”的成分,但在氣候危機面前,確實需要強有力的政治意愿和國際共識,向企業、市場、金融業、科技研發乃至社區等領域釋放更加積極明確的信號,動員全社會力量向低碳、零碳和負碳方向集中,進一步加速能源和技術變革的進程,使現在看上去的“不可能”在不遠的將來變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