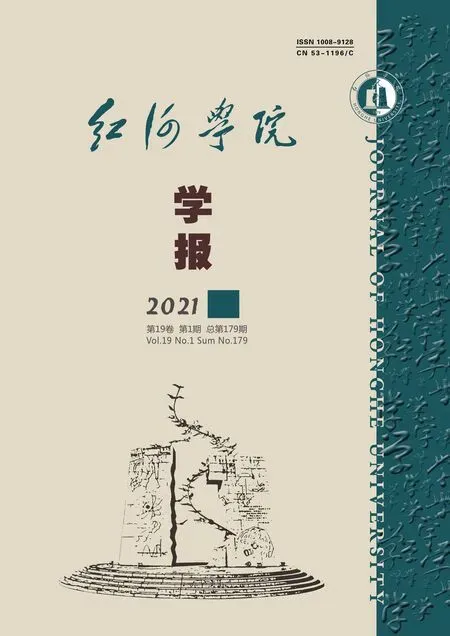從越南城隍信仰內(nèi)涵變遷看中央與地方權利的交流
趙立明
(云南民族大學,昆明 650500)
一 越南城隍信仰的興起與發(fā)展
“城隍”源于中國文化,是指保護一方池城的神,最初是指古代居民點最先修筑的兩種防衛(wèi)設施,即圍墻和壕溝。在古漢語中,“城”是指用土石夯砌而成的圍墻;“隍”是指沒有水的護城壕。中國古代稱有水的城塹為“池”,稱無水的城塹為“隍”。城與隍各位一物,均為居民點的屏障。[1]128據(jù)《禮記·效特性》記載:“天子大臘八,祭坊為水庸,事也。”鄭玄注云:所祭八神也,水庸七。”《侅余叢考》又進一步解釋道:“水則隍也,庸則城也。”由此可見,城隍這一概念是從由“水庸”逐漸演化而來,隨著人口的增長和鄉(xiāng)村城市的聚集,民眾對所生活地區(qū)歸屬感的加強和對社會安定的渴望,城隍信仰便從最初的保護溝渠之神逐漸演變成“城市的保護神”。中國現(xiàn)存可考文獻中最早記載的城隍神祠是建于三國赤烏二年(公元238年)的蕪湖城隍,東漢以降,隨著佛教傳入,道教模仿佛教中的神佛觀念,將仍在民間活躍的社祭活動納入道教信仰體系,開始形成系統(tǒng)完備的城隍信仰體系。[2]及至唐宋時期,隨著封建中央集權制度加強,廣建城隍廟、城隍信仰逐漸成為封建統(tǒng)治者奴役百姓的精神枷鎖。宋代開始為城隍神加賜封號,祭祀典禮也更為隆重。至明代,城隍信仰達到頂峰,明太祖朱元璋主張增強中央集權,加強神權統(tǒng)治,大封城隍。皇帝在封赦城隍時曾言:“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而不妄為。”“朕設京都城隍,俾統(tǒng)各州府縣之神,以監(jiān)察民知善惡而禍福之。俾幽明舉,不得僥幸而免”[3]181-187由此可見,伴隨王權專制加強,城隍信仰已從保護城市之神變成統(tǒng)治者對下層民眾思想控制和教化民風的重要工具。
越南城隍信仰源于中國,并伴隨著道教文化傳入而逐漸在越南興盛。道教作為中國本土宗教,公元142年由張道陵在老子道教和中國地方信仰基礎上創(chuàng)立而成,是融合了中國現(xiàn)實狀況與思維方式的神教。《牟字》序言曾言:“靈帝崩后(公元189年),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為神仙辟谷長生之術。”[3]由此推知,道教在東漢末年即已傳入越南。中越兩國同為農(nóng)耕文明為主,在文化審美和價值觀念等方面也有很大的相似性。道教哲理偏重于人在現(xiàn)實生活中個體生命的完成,對于人生,對于潛藏在人的意識深層的俗望的力量,其采取迎合滿足的方法。[4]因此,源于越南社會下層民眾對生活的渴望和對現(xiàn)實的追求,道教傳入越南之初便在越南下層民眾階層引起了激烈反響,并且呈現(xiàn)出“自下而上”的傳播方式。
公元2世紀左右,交趾地區(qū)屬于中國漢王朝管轄范圍,中央王朝派遣官吏前往交趾地區(qū),整頓兵馬,補充糧草,率兵平定各地,每至一處便建城筑堡,且全盤改革各州郡的政治制。[5]31隨著漢王朝對交趾地區(qū)管理的加強,當?shù)匦纬闪溯^為系統(tǒng)嚴密的政治層級制度,農(nóng)村地區(qū)也出現(xiàn)了類似于中原地區(qū)的村社社會,城隍信仰在越南有了現(xiàn)實的依托物。
唐朝時期,我國官方有了關于云南城隍信仰的最早記錄。據(jù)《交州記》:王姓蘇名百,世居賁度鄉(xiāng)江水側,三世同居。晉時旌表其間,號所居為蘇白村。王初舉孝廉,為龍度令,有忠孝之名。唐穆宗長慶中,都長李元喜見龍城北有逆水,乃相地移府。其地是王故宅,因奉請封王為城隍神,立祠祭之。夜夢王來告曰:“某主此地久矣,君為教導吾民以義,方能久居。元喜許諾。迨高駢筑羅城,聞其事,具澧致祭,尊為:都府城隍神君。李太祖遷都龍城時,夢王來拜謁,具言姓名。帝覺而命祭,封為國都異龍都城大王。[6]從這段引文可以得知,安南都護高駢曾將當?shù)氐奶K瀝江神奉為其都府大羅城的城隍神,號曰“都府城隍神君”。李太祖公蘊遷都河內(nèi),也基本沿用在京城升龍祭祀城隍的儀式。可見,越南上層社會在接受城隍神之初基本沿用了中原王朝對城隍的內(nèi)涵解釋,并且伴隨著越南封建集權統(tǒng)治的加強,開展在這一基礎之上繼續(xù)對城隍神更為隆重的加封和祭祀。但這僅僅是城隍信仰開始在上層統(tǒng)治者階層流行,其在民間的傳播情況尚缺史料。從道教在越南傳播的時間和方式來看,越南民間城隍信仰理應較官方更為豐富,關于這一問題將在下一部分探討。
二 越南城隍信仰內(nèi)涵的變遷
從宗教傳播的角度看,任何一種宗教在傳入其它地區(qū)之后,都需要與傳入地地方信仰相結合,形成具有當?shù)靥厣谋就粱攸c。[7]中國城隍信仰傳入越南過程中也不例外。越南城隍信仰不僅繼承了中國城隍神對加強皇權和思想教化的功用,在傳入民間時,也與當?shù)卦夹叛鲞M行了本土化結合,其內(nèi)涵包括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原始信仰元素,具有神秘主義色彩。民間城隍信仰,有關學者認為,越南民間城隍信仰的傳入采用了上層至下層,城市到農(nóng)村的傳播階段。[8]也有研究人員指出,越南本土信仰中曾存在與城隍神相似的信仰,當城隍概念傳入越南后,當?shù)孛癖姴艑⑦@一名詞用解釋相關的本土文化。[9]但是不論越南民間城隍信仰是由上層傳入下層,還是源自其本土文化中觀念,從民間城隍信仰所保存的元素中可以發(fā)現(xiàn),在越南城隍信仰發(fā)展之初中央和地方保持著相對獨立的狀態(tài),封建統(tǒng)治者認識到城隍信仰對封建王權的促進作用,后兩者才出現(xiàn)了結合。
越南城隍神種類繁多,包羅萬象。由于受萬物有靈和靈魂崇拜觀念影響,村民為求獲得神靈庇護,城隍神往往又成為各種自然現(xiàn)象神袛、動植物神袛和自然神的化身,而且人神和天神相互結合,如傳說中的天神、扶董大王、禇童子、東海大王等;各種自然現(xiàn)象神祗風神、雨神、水神、自然界山川湖泊神祗等;人神包括一些與地方有關的人物,如帝王將相、清官廉官、民族英雄、忠臣義士、以及在當?shù)貕ɑ慕ù暹^程中有功者、在某重大事件中貢獻卓異者等等。[8]越南民間城隍信仰發(fā)展過程中充分吸收了民間信仰的元素,正是由于在發(fā)展之初未受到中央王權過分干預,才得以保留著大量的原始信仰元素,保持著相對獨立性的發(fā)展。后來隨著越南封建社會發(fā)展進程加快,中央王權興盛以及受中國封建王朝的影響,上層統(tǒng)治者開始將城隍信仰賦予了更多的政治功用,將其看作聯(lián)系上下兩級的紐帶,以期達到加強統(tǒng)治,增強民眾對國家歸屬感的目的。特別是到后黎朝英宗時期,中央考慮到民間城隍信仰繁多,開展對民間城隍信仰的審理工作,皇帝把各大城隍神赦封為上、中、下三等:一等神為某些名山大川神祗;中等神為鄉(xiāng)民供奉和祭祀已久、有助于本土發(fā)展并在一定范圍內(nèi)形成重要影響的城隍。下等神為除上等神和中等神外的其他正神,這些神業(yè)績不明,但由民間奉為城隍,朝廷亦遵從民愿奉為下等神。[8]值得一提的是,在黎圣宗時期,為證明其民族正統(tǒng)性和提升民眾對國家的歸屬感,開始將“萬世之祖”雄王作為雒越始祖,雄王開始成為城隍神位中的上等神,并賦予了至高無上的地位。此后雄王附著的民族精神符號不斷地滲透到民間各種信仰中,并在民間社會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由此可知,隨著封建中央集權統(tǒng)治的加強,越南統(tǒng)治者展開了對民間信仰的控制。在對城隍信仰審查和再構建過程中,鄉(xiāng)間城隍信仰被納入到封建王權統(tǒng)治范圍之內(nèi),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規(guī)范的信仰體系。經(jīng)過整合后的城隍信仰內(nèi)涵保羅萬象,不僅包括民族始祖、國家功臣這類有助于凝聚民心的上等神,也包括具有民間原始崇拜特點的自然神。
三 城隍信仰變遷背后中央與地方權力的交流
(一)越南中央與地方權力交流的必要性
越南李朝滅亡之后,越南進入了頻繁的王朝更迭階段。在長達兩個世紀的發(fā)展過程中,越南統(tǒng)治者與國內(nèi)盜寇的交戰(zhàn)和與中國中原王朝的交涉成為首要問題。陳朝建國之初,越南國內(nèi)寇盜頻發(fā),在國威地區(qū),時有芒賊作亂。洪州地區(qū),段尚占據(jù)唐濠之地,自稱為王。北江地區(qū)則有阮嫩稱王于扶董村。陳太宗在奪取帝位之后,才領兵前去平亂。但囿于朝廷勢力孱弱,致使其在與寇賊交戰(zhàn)中頻頻失利,迫于無奈選擇與寇賊求和。這一份妥協(xié)也為陳朝統(tǒng)治者后續(xù)推進統(tǒng)治帶來了重重阻礙。雖然之后在與元軍抗爭的過程中贏得了勝利,但是兩次抗元戰(zhàn)役沉重打擊了陳朝國力。最終陳朝皇位被胡季犛篡取,后與明朝的交涉過程中,其詐稱陳朝宗嗣已絕,無人承繼皇位,便以陳氏外甥之名,代其權理國事。至1404年,自稱藝宗之子的陳添平,行經(jīng)云南抵燕京,向明成祖朱棣揭發(fā)胡季犛僭逆本末。明成祖遣使李锜徹查此事,結果為確系篡奪。明朝出于宗主國對藩屬國的責任,出兵越南,胡朝軍敗后,明朝便張貼榜文訪求陳氏宗室,但陳氏子孫無遺類,越南便暫交與中國管理,于是便開啟了越南歷史上的屬明時期。[5]84-134由此可見,陳朝以來,越南保持著非連續(xù)的獨立狀態(tài),在中國中原王朝的管轄和與國內(nèi)反動勢力的抗爭過程中,越南統(tǒng)治者無暇兼顧地方統(tǒng)治,導致民間社會土地兼并愈發(fā)嚴重,豪取豪強現(xiàn)象頻發(fā),民不聊生。
直至15世紀后,越南步入了后黎朝時期,在經(jīng)歷了長達數(shù)世紀的社會動蕩之后,黎朝統(tǒng)治者在統(tǒng)治之初就強化王權,并以儒學作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太祖黎利“立國之初,祠孔子以太牢,其崇重至矣”,在不斷抬高孔子地位、神化孔子的同時,黎朝大興儒家教育,鼓勵、提倡向全社會灌輸儒家思想,按儒家思想置禮樂,定制度。在京城設立國子監(jiān),于各府路開辦學堂,延請教師教授儒學。此外,統(tǒng)治者還根據(jù)儒家思想制定了一些通俗的教化和條例,用行政手段推行,將儒家思想深入民間,以達成化民成俗的目的。[10]160-161特別是到黎圣宗時期,在其非凡的統(tǒng)治之下,越南文治達到全盛,使其顯赫一方。在政治制度上,封建君主制更為加強。中央設六部,各部設尚書,廢除丞相一職,皇帝獨攬大權。全國分為十三個道,各道長由中央任命,分掌軍、財權和司法大權,設監(jiān)察御史使加以監(jiān)督,并設立私人軍隊,以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10]131伴隨著封建中央集權一統(tǒng)國家的建立,統(tǒng)治者也展開了對大越民族主義觀念的構建。成書于黎圣宗時期的《大越史記全書》曾記載:“大越居五嶺之南,乃天限地北也。其始組出于神農(nóng)氏之后,乃天啟真主也。所以能以北朝各帝一方焉。”[11]越南統(tǒng)治階級在進行民族構建的過程中,通過與“神農(nóng)氏”等中華文化元素的聯(lián)系來證明其民族正統(tǒng)性,但又采用“南北朝各帝一方”“與北朝而抗衡”之類的句子來強調其與中國中原王朝獨立平等的地位。這種民族主義的構建大大激發(fā)了越南人民對國家的歸屬感,同時也強化了中央與地方間的聯(lián)系。盡管在黎圣宗后期,越南再度陷入王權斗爭、割據(jù)對立的狀態(tài),但是這份已經(jīng)構建而成的大越民族主義一直傳承至今,對越南民族團結和民族歸屬感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二)城隍信仰變遷中的中央與地方權力交流的方式與過程
如前述,越南進入后黎朝時期,國家進入全盛階段。統(tǒng)治者以儒學為基礎不斷將權力深入到民間社會。但是以儒學為基礎的漢文化畢竟為一種外來文化,由于其思想晦澀難懂,當其深入到民間社會之時,就極易與地方民間信仰產(chǎn)生沖突。正如本文所論述的越南城隍信仰,由于中央和地方社會對城隍神的內(nèi)涵、功能等解釋存在較大差異,當兩者交匯之時,特別是在統(tǒng)治階級極力推行其政治目的之時,極易與地方權力產(chǎn)生巨大的矛盾沖突。為了避免這類沖突產(chǎn)生,越南中央與地方在城隍信仰交流與融合過程中,采取的是一種更為積極的方式,即在堅守自我原則的基礎上進行一定程度上的退讓。
如城隍信仰成為了國家行政權力下放與民間信仰之間的調和劑,統(tǒng)治者利用鄉(xiāng)紳、儒士階層等地方精英的管理,地方行政單位村亭從之前的“驛亭”轉變?yōu)閲以诖迳缭O立的一個具有政治、文化和社會功能類行政機構,而地方城隍神則依靠這一機構變成了神圣界域中村社的管理者,得到統(tǒng)治階級的認證,并納入到封建官僚的政治象征體系。村亭和城隍神的出現(xiàn)標志著中央與地方間妥協(xié)、讓步的達成,同時也是越南本土文化、信仰與儒家文化相互適應、融合的結果。[12]124-125
此外,隨著以雄王始祖為基礎的民族主義的構建逐漸趨于完善,國家參與的雄王崇拜也成為了民間城隍祭祀中的主要正神。在這一過程中,國家通過循序漸進的方法,起初通過地方官員和精英來管控民間的信仰生活,祭祀儀式則主要有地方社會自行組織。[12]135通過民間社會對雄王祭祀儀式的不斷踐行,逐漸加深了下層社會對統(tǒng)一民族構建的認知,最終民眾開始自覺地將雄王作為城隍祭祀的主神,希望通過祭祀大越始祖的方式來加強與國家的聯(lián)系。美國社會學家保羅·康納頓從集體記憶的角度指出,社會秩序的維持需要預設一個共同的集體記憶,而記憶的載體是通過儀式來操演的。[13]儀式或信仰具有連接過去、現(xiàn)在和將來的作用,當某個族群的人們在參與該族群的大型宗教活動過程中,或多或少地會對所構建的集體記憶具有一定的承襲,這份承襲對民眾的認同感和社會穩(wěn)定性將會承擔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從這個角度看,國家統(tǒng)治者將“萬世之祖”雄王納入越南城隍信仰和祭祀中的上等神的位置,一方面民眾在儀式參與的過程中逐漸加強了對國家民族意識的認同;另一方面統(tǒng)治者也在與地方社會的溝通過程中實現(xiàn)了大一統(tǒng)國家的建構。
從越南城隍神的分類以及統(tǒng)治階級在利用城隍信仰構建國家共同信仰的過程中可以發(fā)現(xiàn),國家統(tǒng)治階級并沒有打擊民間信仰的個性,也沒有一昧地宣傳民眾所不熟悉的上等神中的正神功績。而是在尊重和保留民間信仰的基礎之上,用一些能夠激起民眾民族記憶的始祖類的正神,如雄王始祖及抵御外族侵略的功臣等等,不斷安撫地方民眾的情緒,加強國人對于民族的認同感和榮譽感,實現(xiàn)了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思想層面的交流與融合。同時,統(tǒng)治者也將民間信仰一同納入到城隍信仰大的話語體系之中,使得城隍信仰內(nèi)涵更加的多元、豐富。
從越南中央與地方在城隍信仰的交流過程中,可以發(fā)現(xiàn)良好的交流從來都不是一種單向的壓制抑或是單方面的被動,而是雙方在彼此尊重的基礎上,達到一種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雙向流動,最終形成兩者共同接受、認可與遵守的約定。文化作為一種精神領域的概念,其融合與接受的過程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國家一昧地用暴力強硬的態(tài)度去干預民間文化與信仰,即使最終結果是某一方屈于武力鎮(zhèn)壓而暫時服從與接受,也會產(chǎn)生更大的文化縫隙,為后期爆發(fā)更大的沖突埋下伏筆。更甚者在生產(chǎn)力較為落后的封建時期,在野蠻好勝的思維驅使下,民間權力不會輕易地去遷就和迎合國家統(tǒng)治階級。因此在雙方交流過程中統(tǒng)治者如果繼續(xù)采用強硬的態(tài)度,放棄理性和善意的溝通時,兩者容易激起更多的流血事件,從而加劇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沖突,不利于統(tǒng)一中央王權社會的建立。
四 總結
從越南城隍信仰內(nèi)涵的變遷中可以發(fā)現(xiàn),國家統(tǒng)治階級在規(guī)范城隍信仰的過程中,尊重了中央和地方間的差異,通過有效的溝通對話實現(xiàn)了彼此的融合與發(fā)展。一方面地方順應與迎合了中央所傳達的有效指令;另一方面中央也在保留地方性特色的基礎上做出適當?shù)耐讌f(xié)與讓步,實現(xiàn)了城隍信仰對民族歸屬感和統(tǒng)一民族國家建設的功用,也促進了其信仰內(nèi)涵的多元化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