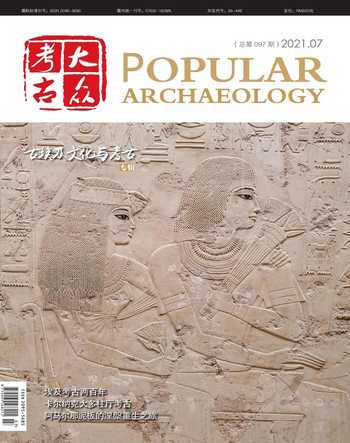卡爾納克大多柱廳考古
李曉東

疑慮,帶我來(lái)到卡爾納克
2016年11月,應(yīng)美國(guó)孟菲斯大學(xué)埃及考古項(xiàng)目負(fù)責(zé)人、埃及學(xué)家皮特·布蘭德(Peter J. Brand)教授邀請(qǐng),我前往埃及盧克索,加入“卡爾納克神廟大多柱廳巨柱浮雕與銘文整理校對(duì)項(xiàng)目”一個(gè)考古季的工作。接受邀請(qǐng)是基于兩點(diǎn)考慮,一是當(dāng)時(shí)尚無(wú)中國(guó)學(xué)者到這個(gè)考古圣地實(shí)地工作過(guò);二是對(duì)這個(gè)項(xiàng)目有些疑惑與不解,想通過(guò)參與其中得到答案。疑惑很簡(jiǎn)單,卡爾納克神廟作為世界上知名度極高的古代遺址,70年前哈羅德·海登·納爾森(Harold Hayden Nelson)就主持了神廟大多柱廳銘文與浮雕的勘查整理,之后威廉·默南(F.William F. Murnane)帶領(lǐng)團(tuán)隊(duì)繼續(xù)在大多柱廳勘查和整理,埃及學(xué)家一直在關(guān)注著這些銘文與浮雕。70多年過(guò)去,大多柱廳129根巨柱上的銘文都已記錄在案,銘文翻譯工作已經(jīng)做完;浮雕圖案都已拍照、描畫(huà)、標(biāo)號(hào);考古報(bào)告編輯成冊(cè)出版發(fā)行工作也已完成。難道還有沒(méi)被發(fā)現(xiàn)的銘文或浮雕留給現(xiàn)代學(xué)者去興師動(dòng)眾設(shè)立項(xiàng)目,并召集美國(guó)、加拿大、法國(guó)還有中國(guó)的學(xué)者每年在現(xiàn)場(chǎng)工作嗎?皮特·布蘭德教授作為默南先生的弟子,主持孟菲斯大學(xué)埃及考古隊(duì)每年在此的工作,連續(xù)多年從不間斷,并聲稱項(xiàng)目要持續(xù)50年。田野現(xiàn)場(chǎng)工作究竟如何進(jìn)行的?
決定前往埃及參與大多柱廳巨柱銘文與浮雕整理勘正工作后,身未往書(shū)已到,皮特·布蘭德教授寄來(lái)《卡爾納克神廟大多柱廳銘文浮雕指導(dǎo)綱要》,厚厚的一本,內(nèi)有大量圖片實(shí)例。相關(guān)內(nèi)容之細(xì)超出想象,僅將書(shū)中第一部分目錄翻譯成漢語(yǔ)列于下,便可窺見(jiàn)其工作之細(xì)膩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