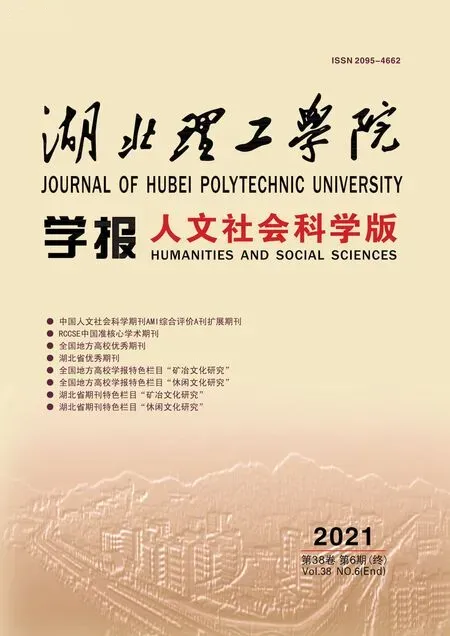萍鄉煤礦早期經營業績探究*
張 實
(湖北師范大學 漢冶萍研究中心,湖北 黃石 435002)
中國近代煤炭工業慘淡經營二十來年,僅剩下開平煤礦一枝獨秀。至甲午戰后,萍鄉煤礦異軍突起、翩然問世,當時就享有“北有開灤,南有萍鄉”的盛譽,于國計民生具有重大的現實作用、深遠的歷史影響。
萍鄉煤礦是為漢陽鐵廠供應燃料而創建的,從晚清至民國早期都是漢冶萍公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近代經濟史領域將它作為獨立企業進行專題研究的很少。中國共產黨成立后,萍鄉煤礦是工人運動的發源地,是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從事革命活動的重要基地,因而它在革命史、中共黨史上的重要地位又遠遠超過了它在經濟史上的影響。
如何估價萍鄉煤礦早期的經營業績,當時就有分歧。盛宣懷曾宣稱:“萍礦開辦以后并未獲利”“萍礦實收實支,虧耗亦巨”。有的專著則認為:盛宣懷“‘求大求全’的創辦思想與實施,自企業內部從根本上決定了近代萍鄉煤礦‘一生’經營不振的命運”。萍鄉煤礦在創辦之初,雖與大冶鐵礦一樣,被視為漢陽鐵廠的下屬礦山,但它一開始就是獨立核算、自負盈虧。上述專著認為,盛宣懷“對下屬三廠礦具體實施的是‘大鍋飯 ’體制”“一切資金均由總公司‘財政’下撥,所有費用也向總公司報銷”“企業的經營與經營的效果完全脫節”,這是一種誤解[1]58-71。
本文以財務數據等檔案資料為依據,結合史料考證、辨析,就評價萍礦早期經營業績的有關問題提出不成熟的看法,供學界進一步研究參考,并請讀者批評指正。
一、萍鄉煤礦早期是盈利的
本文所說的萍鄉煤礦早期,是指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張贊宸以漢陽鐵廠“提調”之職位、受命“總辦”“萍鄉等處煤礦總局事宜”起,至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盛宣懷任命林志熙為萍鄉煤礦會辦,“準于五月初一接事”,以接替因病重離職的張贊宸為止。即從張贊宸正式創辦萍鄉煤礦起,至其將機械化礦山基本建成;又由于主要負責人更替,在財務結算上自成一段落,也可以稱之為“張贊宸時期”。
張贊宸交卸后兩月余仍在安源辦事,并于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二日致盛宣懷電云:“今年正月至閏月帳各處皆已清結,……截至閏月底交卸止,作一大結束,總結盈虧。”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十四日,盛致李維格函云:
萍礦實收實支,虧耗亦巨。而故張道呈送估價單轉得盈余卅余萬兩,以是商情看好萍礦而看壞漢廠,其實不然[2]1174,600。
(一)據《萍礦過去談》提供的賬目,萍鄉煤礦早期是盈利的
盛宣懷提出上述看法之際,正在籌組商辦公司,大張旗鼓地招收股份。此時張贊宸已病故,那份令盛頗不以為然的估價賬單,似不見于已出版的《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和《漢冶萍公司檔案史料選編》,我們卻在不大為人注意的孟震《萍礦過去談》一書內,發現載有萍礦“九年收支總賬”。
孟震,江蘇武進人,與盛宣懷、張贊宸皆是同鄉。自1898年萍鄉煤礦創辦至1909年,在該礦經理賬目,1909年至1911年調往該礦漢口運銷局任稽核。辛亥起義期間,不避艱險,極力保護萍礦賬簿,1912 年6月漢局裁撤稽核處,孟震“辭職后得將十六年經手事實一一編制成表”,匯輯成《萍礦過去談》一書,1914年由漢口前花樓正街汪日升石印局承印。孟震將此書送呈國務院及有關部門、官員,曾受好評,如交通部路政局復函稱:“凡關于該礦之辦事章程,出入款項以及營業盈虧,頗為詳盡”。刊載此書的《近代史資料》編者“說明”亦認為:“內容頗詳,代表了清末民初我國礦業發展的規模和水平,對于研究我國近代礦業史、經濟史均有直接的價值。”我們研究萍鄉煤礦的創建,這件原始資料似不宜忽略[3]78-81。
《萍礦過去談》載有《萍鄉煤礦自光緒二十四年開辦起至三十二年閏四月底止九屆收支總表》,分列為《九年收款》《九年支款》《盤存礦產成本》三表。孟震此賬,截至光緒三十二年四月,正是張贊宸移交之期,盈余30多萬兩也與張贊宸移交時所報相符。
現將《萍礦過去談》主要數據摘要如下:
1.《九年收款》
所列總名目為“煤焦售價及各項收款門”,是萍礦九年的全部產出,計湘平銀867萬余兩。其中分項為焦炭、生煤、制造機件、火磚、材料等產品銷售價值及官錢號的盈余等,包括全部銷售收入和庫存產品,都是自身生產經營的收入。主要有售焦炭價522萬余兩,售生煤價183萬余兩,兩者共計706萬余兩。另有移交現存煤焦、華洋材料91萬余兩。
2.《九年支款》
總名目是“煤焦成本并各項工程機器各料支款門”,實際是兩大塊:產品生產成本和礦山建設所用經費,計湘平銀1 250.19萬兩。其中產品成本開支最大的幾類是:
1)本局各分廠挖煤煉焦價費144.79萬兩,收購各商廠焦炭價107.3萬兩,收購各商廠生煤價17.9萬兩,共約270萬兩。
2)煤焦輪駁運費193萬余兩,火車運費28.9萬兩,共約221萬兩。
3)利息、股息。禮和洋行借款利息合湘平銀86.99萬兩;股息自收股日起至光緒三十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合湘平銀38.44萬兩,共125.43萬兩。
4)另有“各戶往來借款并煤焦價欠款”湘平銀92萬余兩。
表末“總結除收凈支”一項,是將九年支出減去九年收入,計凈支出,即不敷銀382萬余兩。表后說明:有一部分建設經費用于購置礦山、機器設備等,轉化為礦山的固定資產,列入盤存礦產成本。
3.《盤存礦產成本》
計湘平銀418.43萬兩。主要項目是購礦山、機器及工程經費,有的是原價,有的是賴倫礦師的估價。大項如下:
1)“購盡萍境東南各土窿計周圍90余華里,又銀鐵銻錳各礦小花石機器煤礦”,共估湘平銀100萬兩;
2)“機礦窿工內外總機器等處成本”估湘平銀50萬兩,直井成本估湘平銀60萬兩,“穿紫家沖總平巷成本”估湘平銀40萬兩,此三項共150萬兩。
3)大小洗煤機兩座,成本估湘平銀40萬兩,煉焦爐三座、推煤機、壓煤機成本估湘平銀32萬兩,制造廠成本36萬兩,共約108萬兩等。
最后的計算結果是:“總結報告收支兩抵,盈余湘平銀三十五萬九千二百九十六兩六錢五分三厘。”[3]107-111
其計算的步驟是:
1)九年支出(約為1 250萬)-九年收入(約為867萬)=凈支出(約為382萬)
2)盤存礦山成本(約為418萬)-凈支出(382萬)=盈利(約為35.9萬)
按照我們今天的理解,基本公式是:
3)全部產出(約為867萬)+固定資產(約為418萬)-全部支出(約為1 250萬)=企業營利(約為35.9萬)。
我們注意到,孟震賬中的《九年收款》只有萍礦本身的經營收入,未見股本、德國貸款等,也就是說,孟震的賬目只反映了萍礦內部產出、成本和積累的數據,而沒有反映盛宣懷投入了多少資金及其運作的情況。
(二)對于“萍礦開辦以后并未獲利”“虧耗亦巨”應作具體分析
1)盛在光緒三十一年二月三十日《關于萍鄉煤礦借款問答》中曾強調:“萍礦開辦以后并未獲利,是以尚未刊布帳略。”這是應付朝廷調查的一種說法。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張贊宸致盛密函云:“查近三年間土礦擴充至八十余處,……可值銀六十萬兩。而土礦資本,統已賺出。”說明萍礦早在此時便已獲利[2]477,260。
2)盛宣懷所謂“萍礦實收實支,虧耗亦巨”,當指上述九年支出1 250.19萬余兩,除去收入867萬余兩,尚不敷銀382萬余兩;張所謂“轉得盈余卅余萬兩”,系以固定資產總值418萬余兩與超支382萬余兩相抵。有的資產估值是否準確,我們難以鑒別,但一座機械化煤礦作為固定資產已是客觀存在,不可無視,應當計入企業效益是毫無疑義的。盛將此全部認作虧耗,看來未免苛求,有失平允。
盛宣懷經常強調企業困難、虧損,有時是真困難、真虧損;有時卻是企圖掩蓋他已經獲得的實際利益;有時是為大借外債制造輿論。而為了招股,有時又把廠礦前景說得天花亂墜,并為掩蓋虧損而調整賬目。宣統元年三月,盛宣懷在《漢冶萍公司注冊商辦第一屆說略》中宣稱,“萍鄉煤礦產業估值銀一千五百五十萬兩”,則是孟賬418萬兩的3.7倍[4]93。總的來說,盛在不同形勢下,根據需要,強調廠礦某一個側面,賬目也隨之而改動,我們不可一概信以為真,需作具體分析。
孟震所提供的賬目,是他在戰火中“不避艱險”保存下來的;編印此書時,張贊宸早已不在人世,孟震已脫離萍礦,可謂用心良苦。按此賬目,即張贊宸移交時收支的總結算,萍礦早期是盈利的。它的業績不僅體現在賬面有盈余,也體現在客觀存在的礦山已建成的固定資產,更難能可貴的是,這些業績是在白手起家、負債經營的條件下取得的。
二、創建萍礦資金嚴重不足,系負債經營
萍鄉煤礦的創始人張贊宸有《奏報萍鄉煤礦歷年辦法及礦內已成工程》一文,系統記述光緒二十四年起至三十年十一月止,該存款目及工程產業大致情況,是按照盛宣懷的指令、為應對商部查賬而編寫的。原文第一節為《股本來源和收支情況》,所述資金來源主要有:先后股本銀100萬兩,該付股息50萬兩,計150萬兩;禮和洋行借款除陸續歸還外,尚欠庫平銀78萬兩;該漢冶萍駐滬總局153.18萬兩;該招商局20.32萬兩;銀行、各錢莊往來,欠商井廠等106.44萬兩;以上該款合計庫平銀約507.92萬兩。除去結存庫平銀123.57萬兩,該存兩抵,實結該庫平銀384.35萬兩。主要支出:一為“所付莊號及禮和息銀、并老商股息”,共150萬余兩;一為購買機器、礦山、輪駁、建外局基地房棧等實用234萬余兩,共384萬余兩。收支平衡[5]204-206。
張賬的計算公式是:
1)股份(約170萬)+德國欠款(約78萬)+總局欠款(約153萬)+銀行錢莊欠款(約106萬)=結該(約507萬)
2)結該(約507萬)-結存(約123萬)=結欠(約384萬)
3)結欠(約384萬)-已付利息股息(約150萬)-固定資產(約234萬)=0(收支相抵)
這些財務數據很重要,似可彌補孟震賬目的不足,但它是秉承盛宣懷的意旨為應對朝廷調查而編寫的,滲雜著盛的主觀意圖,數據可能有虛有實,虛實夾雜。本節擬結合檔案史料分別進行探究、辨析:
(一)股本原是按盛宣懷的指令編造的
所謂的萍礦創始老股“先后股本庫平銀一百萬兩”,系張贊宸奉盛宣懷之命編造,實為虛報。光緒二十七年五月一日,張贊宸致函盛宣懷,報告其所擬萍礦章程稿內,“有礦本已集商股一百萬兩一語。其實所集股本,并無如此之多”。張一度擬將近三年土礦盈利50余萬作為機礦股本,盛于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三復電,堅持“應仍以創始股本五十萬,一股作為兩股。”“雖當時未收齊,已見奏案。”即仍然按照他當初向朝廷報告的方案編造股本[2,6]。
張贊宸在此賬內也說明了股本的部分真相:
查萍礦開辦之初,并未領有資本,起首用款,即皆貸之莊號。及二十五年,始借禮和洋行德銀四百萬馬克,……至所收股本,乃二十五年以后事,且系陸續零交,指作還款,不能應時濟用,勢不得不輾轉挪移,以為扯東補西之計。
關于招商局的股份,兩次入股共20萬兩,也都是奉盛之命,從萍礦所欠招商局40多萬的舊賬中劃出。 張贊宸此賬云:
查招商局首次入股,庫平銀十五萬兩外,尚應結規元三一〇四〇七.九四七兩,除奉督辦憲行知,二次又入股庫平銀八萬兩,申規元八七六八〇兩外,尚該還規元二二二七二七.九四七兩,折合庫平銀如上數[2]205。
經查對,招商局首次入股萍礦,系光緒二十六年二月間事,十七日盛電令盛春頤、張贊宸:“招商局附入萍股庫平十萬,申規銀十萬九千六百兩,已交漢銀行收萍賬,抵付比款。”二十八日張贊宸向盛報告,“招商局附股庫平十萬已收”。雙方都說是10萬,并非15萬。看來入股,10萬也好,15萬也好,都不過是盛隨口一句話,終究是拆了東墻去補西墻[2]789,791。至于招商局第二次入股8萬兩,據后來光緒三十二年五月十九日盛電通知張,盛與當時掌控招商局的楊士琦剛剛商定:“照廿九年臘月轉賬日期填制股票,另加卅三年前息股二萬八千兩外”,下欠本銀22萬余兩,酌給息銀,按5年分還。說明這次入股8萬不僅仍然是舊欠劃轉,而且為時甚晚,已是官督商辦的末期,在為組建公司作準備了[2]1155。
(二)所欠漢冶萍駐滬總局之款真相難明,實同貸款
張贊宸原件此項下與其他各項不同,并無分類細目,也未作任何說明,留下一行空白。參照相關史料,似存在一些疑點,須要多花一些筆墨。
1.駐滬總局是萍礦的最大債主
盛宣懷接辦初期,漢冶萍廠礦負責人都曾自行籌集資金,分別向錢莊、銀行短期貸款。盛宣懷為了加強對廠礦的控制,于光緒三十年七月前后設立駐滬總局,先是要求下面借款要提前申報,不久即將籌款的職能及支出的審批完全集中到總局。總局即盛宣懷,無可爭議地成為了漢冶萍廠礦唯一的資金供給者,也是最重要的直接債權人。總局設立不到半年,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已是萍礦的最大債主,欠款計高達150多萬兩。
2.所欠駐滬總局的金額是按照盛宣懷的指令填報的
張贊宸領受了提供總賬以備商部查賬的任務后,十月初一致電總局楊學沂詢問:“萍礦九月底止,結欠鐵路總公司若干?”之所以有此一問,似張贊宸雖知萍礦欠有鐵路總公司銀款,但系總局辦理并控制使用,不知詳情,不能自行確定如何申報,必須詢問總局有關人員。初四得到復電:
總局單開九月底止,萍礦結欠規元一百五十六萬四千六百九十二兩四七五。沂。支。宣[2]1016-1017。
此電回復頗不尋常:一是答非所問:問的賬戶是“鐵路總公司”,回答的債主是“總局”;二是復電落款不尋常,大約是楊學沂已經具名并寫下日期代碼后,呈送盛審閱,盛又親自添上署名,可見盛對此電的重視,強調是其本人的指令。如此,張贊宸按盛的指令上報,既承認了此項欠款,也承認了債主是總局即盛宣懷,完全撇開了鐵路總公司。
3.此款疑點甚多,用途不明
1)此款是商部調查重點。商部參議王清穆、楊士琦查賬,曾就萍鄉煤礦借款提出問題,計有“禮和借款”“該駐滬總局銀款”“該道勝往來款目”“每年收支簡明總結賬”等,基本是針對張贊宸所提供的賬目提出的。光緒三十一年二月三十日盛宣懷書面回答,關于“該駐滬總局銀款”稱:“該礦總辦張道與漢廠總辦李郎中會呈,廠、礦、路一一鉤連,相依為命,稟請提日本金錢一百萬元趕應礦路之需,曾奉批準,遵即收入萍礦所欠總局帳上,計規元七十九萬一千一百零七兩七錢九分,余款仍是該局籌墊各等語。” 至于此款系由何處而來,盛則強調:“查弟前因承辦路礦,頭緒過多,為日后交替之計,不容不先分眉目,是以關系鐵路者,歸總公司收支處經理;關系廠礦者,于上年七月另設漢冶萍駐滬總局經理。而漢萍之窘,迥非鐵路借有洋款可比。遇兩處函電請款,概飭總局就銀行短借,莊號短拆,應結月息,應付本銀,概由該局備歸各帳,列入萍礦往來。”[2]477
以上回答,強調都是向銀行、錢莊短期拆借,力圖否認萍礦曾動用鐵路總公司之款。
2)一百萬日元之謎。上述盛所謂“稟請提日本金錢一百萬元趕應礦路之需”曾一再見于有關史料:
在商部調查的同時,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十七日,李維格在致盛宣懷函中報告預借礦價三百萬日元的使用情況,內有“前宮保提用一百萬元”之記載。次年三月上旬,李在向盛提交的《新公司接辦漢陽鐵廠之預算》中,再次說明他經手“支用日款三百萬之大略情形”,其中:“歸還萍礦借款一百萬,又萍洙鐵路購辦車頭、車輛,并萍礦煤磚、機器等運保到漢約三十余萬。”[2]463,487
另有史料顯示: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三十二年八月,盛兩次上奏共報銷萍醴、醴洙鐵路建造銀二百九十八萬兩[7-8]。
上述100萬日元似從漢冶萍預借礦價中提取,由盛掌控使用,既列入萍礦欠款由萍礦歸還,然后又向朝廷報銷,是否有兩頭重復報銷、收款之嫌?
3)萍礦曾否認34萬兩欠款。有時總局在上海向銀行、錢莊借款而計入萍礦欠總局款,或是為漢廠還債,或不是為萍礦所用。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張贊宸、林志熙曾有一電,要求從萍礦欠總局款內除去三筆,合計近34萬兩[2]1199。
萍礦欠總局高達150多萬的借款,究竟真相如何,用在何處,似乎是個謎。
4.漢冶萍駐滬總局確曾挪借鐵路資金
總局設在上海,據楊學沂、金忠贊云“專管帳目,毫無存款”[2]528。有時挪借鐵路總公司的資金,如光緒三十一年五月初五,盛電令金匊蕃(即金忠贊)借用鐵路總公司2萬英鎊代萍礦償還禮和洋行借款,“分別作為漢、萍借用總公司之款,七厘計息”。又于同年的五月初九,令金匊蕃借用鐵路總公司存款3萬多英鎊代漢廠償還比國郭格利廠[2]1062-1063。
(三)萍礦早期實際是負債經營,債務沉重
誠如上述張贊宸所言:“開辦之初,并未領有資本,起首用款,即皆貸之莊號”;后來所收股本,“系陸續零交,指作還款,不能應時濟用”,所謂“勢不得不輾轉挪移,以為扯東補西之計”,實際是負債經營。
首先是德國禮和洋行貸款。張贊宸原賬云:
二十五年,始借禮和洋行德銀四百萬馬克,除四分之三仍暫存禮和,以備代購機器料物之用外,僅只現銀三十余萬兩。以還前欠,尚有不敷,而一年兩期,轉瞬即屆應還息本之日,率又由息借,以為應付[2]205。
向德國禮和洋行借的400萬馬克,主要是用于在德國購買煤礦機械和物料。而歸還德國借款則是萍礦最大的經濟負擔,合同規定至1911年1 月1 日止,應還清全部本息。每年還款兩次,倘有一次逾期三個月不付,則所有未到期之本款均需一次還清,利息照舊收取,并由禮和掌管煤礦所有產業和鐵路,至為嚴酷。還款高峰是1902年,須還本40萬馬克,還息26萬馬克,共66萬馬克,按銀一兩合2.5馬克折算約為26.4萬兩。此后每年還本40萬馬克,還息因本金逐年歸還而逐年遞減[2]96-99。至1905年1月1日止,前11批本息已如數還清,還有12批本息,按時價折合尚欠庫平銀約78萬兩。
此項借款系盛宣懷談判、簽字,款項使用由盛掌握,按時還款亦由盛指定人員辦理,前期曾挪用鐵路總公司資金,后期盛另立小公司為萍礦貸款并收高息,光緒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金匊蕃要求撥款為萍礦還貸,此時盛已交卸了鐵路總公司的差使,令其外甥、盛氏的總賬房顧詠銓另立“新記”的賬戶,為總局撥款20萬,收月息一分二厘的高利。看來盛宣懷個人的資金與漢冶萍廠礦是借貸關系,以高利貸牟利[2]1335。
其次,因缺乏自有資金,日常生產所需流動資金依靠短期貸款。
張賬所列萍礦欠各銀行、錢莊及商井廠之款合計106萬余兩。其中,欠日本大倉銀行庫平銀26萬余兩,欠德國道勝銀行13萬余兩;國內欠通商銀行9萬余兩。欠十多家錢莊之款,除一家13萬、一家8萬外,多則3萬,少則數千。所欠商井廠者系歸并時分期付款之余額。
張贊宸稱:“以故七年之間,所付莊號及禮和息銀,并老商股息,共已有一百五十余萬之巨。”按張賬計算,萍礦早期經營的成果,除用于償還禮和貸款等本金外,償還債務的利息和股息150萬約占四成,化為固定資產234萬約占六成。
三、張贊宸白手起家,功不可沒
萍礦創建人張贊宸,字韶甄,江蘇武進人,與盛宣懷同出身于常州城內著名的青果巷。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初,盛宣懷確定接辦漢陽鐵廠即發電至煙臺,調張贊宸來廠,初任漢廠提調,協助總辦處理廠務。張贊宸是在萍鄉部分鄉紳反對洋人、反對機器開采,文氏家族主持的商號希圖壟斷萍煤產銷,其與漢陽鐵廠駐萍運銷局及其他商戶矛盾錯綜復雜的歷史背景下,來萍礦主持創建工作的。在上述資金短缺、負債經營的艱困條件下,堪稱圓滿地完成了創建任務,白手起家并有盈利,實功不可沒。
(一)堅持土洋并舉,邊生產、邊建設
萍鄉煤礦是以自購土井土窯邊生產、邊收購商戶土煤土焦、邊建設機械化礦山。土洋并舉,銷售土煤焦以輔助機礦建設,逐步過渡,最后以洋為主。因資金緊缺,盛宣懷早在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就曾下令“此后土礦不宜再擲巨款”,為此張屢受盛之責難。如前所引,張贊宸在前三年內將土礦擴充至80余處,“可值銀六十萬兩。而土礦資本統已賺出”,連同前任的虧損亦代還清。對于不愿歸并的商井、商廠,張贊宸仍堅持收購其煤焦。實際至光緒三十二年安源總平巷開通才停止收購[2]76,1188-1189。查孟震的九年支出賬,“本局各分廠挖煤煉焦價費”計144萬余兩,而收買商戶焦炭、生煤價共127萬余兩,兩者規模大體相當[3]109。在此期間,土法煤焦的生產銷售,既保證了對鐵廠的供應,又發揮了支持機礦建設的作用,相對投資少、效率高;而處理好與當地土煤窯、土焦廠的關系則有利于穩定大局,緩和與地方的矛盾。
(二)管理井然有序
張贊宸得知商部要來查賬,光緒三十年十月初二復盛電云:“萍礦開辦至今,均有逐日流水細賬,款無巨細,皆有憑據,可聽部員前往徹查。”[2]1016說明該礦歷來資金管理嚴格,賬目基礎工作做得好。后來提供的賬目包括“施工計劃”“礦內工程”“礦外設備”“產業”各部分,條分縷析,明確具體,可供檢驗。《萍礦過去談》中“九年收支”是張向繼任者辦移交,更是向盛宣懷作交待,匯報了創辦以來日積月累的實收實支,突出的是自身的業績,產出了多少,花費在哪里,留下了什么,一目了然。其中收錄有《張韶甄更定萍鄉礦路辦法稟》就是他手訂的管理章程。戶部侍郎鐵良視察漢陽鐵廠、萍鄉煤礦,系張贊宸接待,隨行十余日。鐵良對他印象很好,回京后晉升為戶部尚書,便要調張贊宸去辦戶部銀行[2]1090。
(三)鞠躬盡瘁,清廉可敬
在生命的最后幾年,張贊宸是帶著重病堅持,至光緒三十二年八月,親眼見到安源總平巷開通,大功告成,年底始赴滬就醫,次年三月初一即不治,實為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盛宣懷在請恤時,稱其操履敦篤、秉性公忠、搘柱艱險、以身殉礦,評價很高。張白手起家,建成如此大礦,每年經手進出數百萬,死后家中卻負債累累,債主紛紛索債。光緒三十三年十月,楊學沂去電“懇各債戶念韶身后奇窮勿索”,盛宣懷以恤薪四萬,又自助六千,一并填寫股票交給家屬,方資了結[2]1334。
四、自1912年起萍礦業績急速下降
(一)自1911年起政局多年動蕩不息
武昌起義后,繼之以二次革命和護國軍討袁,直皖、湘鄂軍閥混戰,工農革命興起,北伐勝利后又有寧漢分裂、夏斗寅叛亂,武漢至長沙鐵路沿線屢屢成為戰場,湘鄂贛又是工農革命運動的中心。動蕩期間,或漢廠、萍礦停工,或交通阻塞,或火車、輪船、煤焦鋼材等被征用,歷年損失,難以算計。1914年3 月《漢冶萍公司第四屆賬略》稱,武昌起義機爐熄火,事后修治經年,甫得開爐,各處損失“初步調查,約有三百余萬之多”。其中萍礦煤焦收入“本屆則驟減至二百七十一萬四千余兩,比上屆少收一百十四萬五千余兩”;至下一年份,礦萍收入更下降到“共一百三十七萬余兩,視辛亥則減收一百三十余萬”。概略地說,辛亥前后三年萍礦收入之比大約是3∶2∶1[5]568,573。
從萍礦歷年煤焦產量來看:歷史最高峰為1911年,111.56余萬噸:1912年突降至24.39余萬噸;此后十多年在60余萬噸至90余萬噸之間起落。1924 年為64.85余萬噸,1925年則下降到51.23萬噸,1926年更狂落至7.57余萬噸[9]509。
(二)漢陽鐵廠、大冶鋼鐵廠相繼停產使萍礦銷售一落千丈
據農商部地質調查所1925年調查,萍礦“往年工作最盛時,每日曾出煤三千噸 ,近年……每日僅出二千噸”,但因戰亂失修,“維萍株路機力不足,難以暢運”。1925年2月季厚堃致盛恩頤函稱,“查該路每日僅能運出三百噸左右”,而大冶鋼鐵廠“一號爐每日用焦約四百五十噸至五百噸”[9]498-499,457。
1924年冬,漢陽鐵廠因焦炭不足而停爐,1925年大冶鋼鐵廠亦停爐。1928年4 月,日本政府考慮到“今后隨國內(包括滿洲)煉鐵爐之增設,將可以適應平時與戰時之需要。漢冶萍公司今后以中止生鐵生產,專事采掘與出售礦石”[10]1041。這一變化,不僅決定了漢廠和冶鋼的命運,也嚴重影響了萍礦的命運。
盛宣懷創建機械化的萍鄉煤礦沒有錯,興建萍株鐵路也沒有錯,錯在依賴日本資金,為適應日本的需要,背離了中國國情而畸形地擴大生鐵的產能。一旦過河拆橋被日方所拋棄,為擴大生鐵規模而先后投入的2 800萬日元付之東流,漢冶萍公司必然倒閉。漢陽鐵廠、大冶鋼鐵廠相繼停產,萍煤失去了最大的銷售對象,尤其是主導產品工業用焦所留下的巨額缺口,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沒有其他客戶可以彌補,萍礦必然衰落。漢冶萍公司是以冶煉為中心的生產聯合體,一旦冶煉停產,這種企業聯合也就解體了。
五、余論
綜合上述,我們認為:
(一)創建萍礦的資金來源應包括鐵路專用資金
創建萍礦的資金,購買德國機械設備,主要是使用禮和洋行的貸款;日常的生產流動資金包括建設施工費用系向銀行、錢莊短期貸款。此時盛宣懷督辦鐵路總公司掌控有巨額鐵路資金,其光緒三十三年七月致張之洞函稿云:“敝處前有輪、電局,后有鐵路公司,故挪墊數百萬不致為難。”[2]617除了自安源至株州的運礦鐵路建設經費全額奏銷外,種種跡象表明,雖然盛在商部調查時極力掩飾,似不能排除動用鐵路經費是萍礦早期建設和生產的重要資金來源之一,不能忽視它曾經發揮過重要作用。
(二)萍礦負債經營,盛宣懷難辭其咎
盛宣懷素以“長袖善舞”著稱,又有人稱他是“妙手空空兒”。這一特點也淋漓盡致地反映在創建萍鄉煤礦的過程中。
1)不僅100萬兩的創始老股是編造的,我們在已出版的有關檔案史料中尚未發現盛本人付款認購股份的記載;據民國九年(1920年)整理的盛氏遺產《估價清冊》,其擁有漢冶萍公司股票創字、優字、普字三種,計13.399萬股,每股面值50元,計669.95萬元;其中創字3.400 1萬股,計面值170.005萬元[11]176。竊以為這些股票只可作為盛氏擁有資產的憑證,而并不能證實創辦萍礦時盛已投入與其股票面值相應的資金。如果當時盛確實已投入百萬以上的巨款,原始檔案中不可能沒有具體而明確的記載,張贊宸也不會叫苦不迭地“輾轉挪移”“扯東補西”,更絕不可能在上報盛氏、以供商部調查審核的書面資料上斷言:“開辦之初,并未領有資本,起首用款,即皆貸之莊號。”
2)史料顯示,盛宣懷個人、駐滬總局與萍礦的資金往來是借貸關系,他所提供的資金,不論從何而來,不論是墊付還是代借,都是要收高息的。西方通行的股票,或贏或虧,原本要承擔風險;晚清的商辦公司根據中國的國情推行“官利”制,使投資者旱澇保收,當初盛擬定的鐵廠官督商辦章程是每年官利八厘到一分;而駐滬總局的借款是收萍礦月息七厘至一分二厘,比股票的官利高十多倍。發展至1912年,漢冶萍公司欠盛家的“六合公司借款已過四百萬兩”[4]240,如此,廠礦負債經營,借債越多,作為最大債主盛家的高利貸收入越豐厚。
(三)虛報投入、虧損既是盛宣懷自衛的手段,又是取得收益的渠道
虛報投入、虧損是盛宣懷慣用的伎倆。如光緒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袁世凱視察漢陽鐵廠,廠方送呈的書面資料上虧損達140余萬兩,引起袁的注意,又詢問商股有多少,得到的回答是50萬兩左右,此外尚有60余萬兩皆盛宣懷經手挪借。這份清單系盛事先布置并親自改寫,事后鐵廠總辦盛春頤向叔父申訴,“結虧一百四十二萬余兩,計相去九十四萬有奇”,即虛增虧損94萬兩[2]298-299,302。這次應付商部調查報稱欠總局150余萬兩,也有可能是對付袁世凱的故伎重演。
在特定形勢下,虛報投入和虧損是盛宣懷對付朝廷或袁世凱官僚集團的自衛手段。在布置接待袁世凱視察時,盛曾強調“該廠虧款數目宜預為他人接辦地步”,這是輪船招商局、電報局被袁所奪后的必然反映。出現巨額虧損,表明此企業是難啃的硬骨頭,期望對方知難而退,袁世凱此次視察后似也無意接管鐵廠;如果商部一旦要接辦萍礦,盛則必然以歸還其投入的全部資金,包括歸還萍礦欠滬局款項為先決條件。
虛報投入、虧損也是盛宣懷獲取收益的渠道。盛所開列的這類欠款,一經正式列入賬戶,廠礦勢必要如數償還,實同上繳利潤。如此,則與股本、短期貸款利息,共同構成了盛從萍礦獲取收益的三條渠道。
(四)萍礦是自負盈虧,沒有吃大鍋飯
萍鄉煤礦早期一般被認為是“官督商辦”,實際既無商股,也無“董事會”等機構和人員,其經營決策、人事、財務管理等高度集中于盛宣懷一人之手,實行的是督辦集權制,形同獨資企業。在財務體制上,萍礦不僅是獨立核算,也是自負盈虧。所謂的股本、德國貸款均未下撥給萍礦,由盛掌控,故孟震賬未見記載。統收而不統支,盛從未承擔萍礦的虧損或債務。包括禮和貸款的全部本息,所有貸款都是萍礦用銷售收入或盈利償還的。上述孟震的九年收付總賬,也說明了萍礦是自負盈虧,盛宣懷并沒有讓它吃“大鍋飯”。
基于上述史料梳理辨析,我們對于萍礦早期的業績有一個總體的、概括的認知:一是在建礦的同時,生產不斷發展,九年產出總值達867萬兩。二是其產品主要是供應漢陽鐵廠,“結至三十年十一月底,萍礦共已運到漢陽鐵廠焦炭三十二萬一千余噸,生煤十九萬一千余噸”[5]207,煤焦共五十余萬噸,基本保證了漢廠的正常生產。三是建成了一座機械化的礦山,固定資產達400余萬兩,可日出生煤1 000~2 000噸,日煉機制焦炭160噸,為萍礦及漢冶萍公司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
張之洞辦鐵廠,未能解決焦炭供應;盛宣懷接辦后建成了萍鄉煤礦,解決了焦炭供應。沒有萍鄉煤礦,就沒有漢冶萍公司;沒有萍鄉煤礦,也就沒有京漢鐵路通車。創建萍鄉煤礦,盛宣懷是決策者,而張贊宸是具體執行者、實踐者。這是盛宣懷的重大貢獻,也是張贊宸的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