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閑 健康 審美:馬斯洛《科學(xué)心理學(xué)》的三個(gè)關(guān)鍵詞*
章 輝 宋麗娟
(1.西南醫(yī)科大學(xué) 健康與休閑文化研究中心,四川 瀘州 646000;2.西南醫(yī)科大學(xué) 心理學(xué)教研室,四川 瀘州 646000)
馬斯洛是美國著名心理學(xué)家,曾任美國人格與社會(huì)心理學(xué)會(huì)主席和美國心理學(xué)會(huì)主席。他發(fā)起的人本主義心理學(xué)成為心理學(xué)界同精神分析理論、行為主義相抗衡的“第三勢力”,至今影響深遠(yuǎn)。
對(duì)于現(xiàn)代休閑學(xué)來說,馬斯洛是一個(gè)不應(yīng)被遺忘的名字。在其早年所著《自我實(shí)現(xiàn)的人》(1950年)、《動(dòng)機(jī)與人格》(1954年)等書中,馬斯洛已初步涉及休閑、健康、審美的話題;而在其晚年力作《科學(xué)心理學(xué)》(1966年)中,馬斯洛針對(duì)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價(jià)值觀的偏頗和心理學(xué)研究的不足所提出的許多觀點(diǎn),從本質(zhì)上完全可以視為休閑學(xué)基本理論的先聲或早期共鳴。休閑、健康、審美及其關(guān)系,是《科學(xué)心理學(xué)》一書開篇便重點(diǎn)加以討論的關(guān)鍵點(diǎn)。
一、“生活的另一半領(lǐng)域”:對(duì)無動(dòng)機(jī)行為的重視
在《科學(xué)心理學(xué)》一書的第一章《動(dòng)機(jī)與行為的控制》中,馬斯洛首先反思了動(dòng)機(jī)與無動(dòng)機(jī)的問題。動(dòng)機(jī)理論是心理學(xué)基本理論之一。弗洛伊德的主要理論建立在這樣一個(gè)假設(shè)的基礎(chǔ)上:動(dòng)機(jī)無處不在。而馬斯洛在其早期著作《動(dòng)機(jī)與人格》中就反駁說:不是所有行為或反應(yīng)都是有動(dòng)機(jī)的,成熟、表現(xiàn)、成長以及自我實(shí)現(xiàn)等現(xiàn)象都不符合一般的動(dòng)機(jī)理論。在《科學(xué)心理學(xué)》中,馬斯洛進(jìn)一步認(rèn)為:從弗洛伊德開始,“有動(dòng)機(jī)”和“有決定因素”這二者被混淆了,而精神分析學(xué)家們卻一直沿襲這個(gè)錯(cuò)誤,機(jī)械地為各種生理變化、生理疾病尋找動(dòng)機(jī)。但馬斯洛敏銳地看到,很多生理變化只有決定因素而沒有動(dòng)機(jī)。比方說,物理運(yùn)動(dòng)或外界刺激造成的體質(zhì)變化,男性女性的生理成熟,以及心理改變(如倒攝干擾、前攝干擾、隱匿學(xué)習(xí)等)。故而,馬斯洛重視無動(dòng)機(jī)行為在心理學(xué)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認(rèn)為僅僅從有動(dòng)機(jī)的行為來研究心理問題是片面的。
一般來說,西方文化是以猶太教和基督教為基礎(chǔ)的,這種文化精神重視勞動(dòng)、拼搏,主張以嚴(yán)謹(jǐn)?shù)膽B(tài)度完成清晰的目標(biāo)。馬斯洛認(rèn)為,在這種文化的影響下,美國的心理學(xué)研究也呈現(xiàn)了過分實(shí)用、過分清教徒化和過強(qiáng)的目的性、功利性的缺點(diǎn),這明確體現(xiàn)于“休閑”這一非工作、非勞動(dòng)的領(lǐng)域被忽視的狀況:
在教科書里,沒有論及嬉戲的歡樂、閑暇的沉思、閑逛和游蕩,以及無目標(biāo)、無用處、無目的的活動(dòng)的章節(jié)。這就是說,美國心理學(xué)僅僅忙于從事生活的一半的研究,卻忽視生活的另一半領(lǐng)域——也許是更重要的一半的領(lǐng)域。
或許有人說,這是只注重手段價(jià)值卻忽略目的價(jià)值。這種哲學(xué),幾乎包含在整個(gè)美國心理學(xué)中[1]2。
不難看出,馬斯洛所謂的無動(dòng)機(jī)、無目的的行為,無疑很大程度上就是休閑活動(dòng)。馬斯洛看重休閑的價(jià)值,認(rèn)為它是“生活的另一半領(lǐng)域”,是和工作等量齊觀,乃至比工作更重要的一極。顯然,馬斯洛間接肯定了工作是手段、休閑才是目的,而這正是現(xiàn)代休閑學(xué)的基本原理。因此,馬斯洛認(rèn)為,美國心理學(xué)長期存在的誤區(qū)就在于:過分重視行為的外在目的,只眷注、研究帶來明顯效用、結(jié)果的活動(dòng),而基本上忽略無功利、無目的的活動(dòng)以及由此帶來的內(nèi)在體驗(yàn)。也因此,馬斯洛批評(píng)杜威哲學(xué),認(rèn)為他過于關(guān)注因果關(guān)系理論,但這種理論“對(duì)于強(qiáng)調(diào)內(nèi)在的完善、審美體驗(yàn)、享樂、鑒賞能力和自我實(shí)現(xiàn)的生活來說毫無用處”[1]3。
顯然,馬斯洛所謂的內(nèi)在的完善、審美體驗(yàn)、享樂、鑒賞能力和自我實(shí)現(xiàn)的生活,實(shí)際上就是一種高層次的休閑生活方式。他認(rèn)為,藝術(shù)、欣賞、享受、驚異、鑒賞、終極體驗(yàn)、風(fēng)格和趣味、游戲、思想意識(shí)、哲學(xué)、神學(xué)、認(rèn)識(shí)等“這些現(xiàn)象都屬于心理學(xué)中相對(duì)容易被忽視的領(lǐng)域”[1]5-6(顯然,這些現(xiàn)象也大都是休閑現(xiàn)象)。故而,馬斯洛提出,當(dāng)時(shí)的心理學(xué)研究首要的任務(wù)就是“公開質(zhì)疑所有行為都具有動(dòng)機(jī)這一公認(rèn)的觀點(diǎn)”[1]12。而這實(shí)際上等于給休閑以地位,促使學(xué)界關(guān)注休閑活動(dòng)的意義和價(jià)值。
在有關(guān)進(jìn)化論、實(shí)用主義的思潮影響下,人們長期以來習(xí)慣于把思維當(dāng)作是解決問題的精神現(xiàn)象,是一個(gè)需要意志努力的過程。德國宗教思想家約瑟夫·皮珀在其名著《閑暇:文化的基礎(chǔ)》(1947年)中卻認(rèn)為:“我們可以這么說,推論思考的過程由無須賣力的直觀伴隨并穿透,以至完成認(rèn)知的活動(dòng),……”[2]15“認(rèn)知的最偉大形式往往是那種靈光乍現(xiàn)般的真知灼見,一種真正的默觀,這毋寧是一種饋贈(zèng),不必經(jīng)過努力,而且亦無任何困難。……認(rèn)知的目的乃在于探尋存在事物之本質(zhì),但不必強(qiáng)調(diào)費(fèi)心思考或‘心智工作’之努力的必要性。”[2]25馬斯洛與皮珀發(fā)出同調(diào)。在馬斯洛看來,思想意識(shí)、哲學(xué)、認(rèn)知等領(lǐng)域的不少現(xiàn)象,也是正統(tǒng)的心理學(xué)所無法解釋的。從動(dòng)機(jī)理論出發(fā),他也認(rèn)為,認(rèn)知可以是無動(dòng)機(jī)的、以休閑方式進(jìn)行的,“不管怎么說,人們往往能夠輕易發(fā)現(xiàn)那些真理和正確的答案,而并非需要艱苦卓絕的努力來追求”[1]10。他指出:人們的認(rèn)知也常常是無動(dòng)機(jī)的,在休閑之中,人們被動(dòng)而不是主動(dòng)地獲得真理。所以思維不一定是解決問題型的,也常常是休閑型的——在休閑中,人們不是主動(dòng)的求知,而是被動(dòng)地獲得。從東方文化體驗(yàn)中的“我不覓詩詩覓我”,到西方科學(xué)家阿基米德、牛頓、凱庫勒、魏格納等人發(fā)現(xiàn)真理的家喻戶曉的故事中,我們很容易看出這一觀點(diǎn)不無道理。馬斯洛還特地指出,隱匿學(xué)習(xí)就是一種無動(dòng)機(jī)的認(rèn)識(shí)方式,“游戲可能是無用和無動(dòng)機(jī)的,可能是存在而非奮斗的現(xiàn)象,是目的而非手段”[1]9。這顯然能啟發(fā)我們?nèi)フJ(rèn)識(shí)休閑、游戲在認(rèn)知、學(xué)習(xí)中的價(jià)值。
在對(duì)動(dòng)機(jī)與行為的討論中,一個(gè)重要而突出的現(xiàn)象就是:馬斯洛提出了“表現(xiàn)性”和“應(yīng)對(duì)性”的區(qū)分。他認(rèn)為,當(dāng)時(shí)的科學(xué)體系過于注重實(shí)用效果、技術(shù)和方法,導(dǎo)致現(xiàn)代世界最缺少一個(gè)自然主義或人本主義的目的或價(jià)值體系,故而心理學(xué)對(duì)當(dāng)時(shí)人類的貢獻(xiàn)甚少。馬斯洛提出,表現(xiàn)性行為是無動(dòng)機(jī)的(亦即休閑的),而應(yīng)對(duì)性行為是有動(dòng)機(jī)、有目的的[1]5。他由此認(rèn)為,這種區(qū)分可以使人發(fā)掘“無用行為”的價(jià)值,從而使得心理學(xué)更好地適應(yīng)時(shí)代,擴(kuò)大其涉及范圍。筆者根據(jù)馬斯洛的相關(guān)思想整理出對(duì)照表,如表1所示。

表1 應(yīng)對(duì)性行為與表現(xiàn)性行為對(duì)照
馬斯洛認(rèn)為,應(yīng)對(duì)性行為不是獨(dú)立的,它與需要、目標(biāo)、目的、職責(zé)等相關(guān)聯(lián);表現(xiàn)性行為不是由基本需要決定的,它只是表現(xiàn)、反映或表達(dá)了機(jī)體的某種狀態(tài)。而這種區(qū)分,恰恰也是勞動(dòng)(工作)與休閑的區(qū)別所在,對(duì)現(xiàn)代休閑學(xué)理論具有啟發(fā)作用。
二、“病人的認(rèn)識(shí)相對(duì)有動(dòng)機(jī)”:動(dòng)機(jī)與健康
在《動(dòng)機(jī)與人格》中,馬斯洛曾提出:只要自我實(shí)現(xiàn)的進(jìn)程遭到破壞,便是心理病態(tài)。而使人回到自我實(shí)現(xiàn)軌道的過程,便是治療。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自我實(shí)現(xiàn)的過程必然是一個(gè)自由的過程,只能在休閑中實(shí)現(xiàn)。因此,一個(gè)人不得休閑,也就必然帶有幾分病態(tài)。
在《科學(xué)心理學(xué)》中,馬斯洛對(duì)此問題有進(jìn)一步發(fā)揮。他反對(duì)行為的過分目的性和功利性,從醫(yī)學(xué)的角度發(fā)出這樣的驚人論斷:“動(dòng)機(jī)與感覺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最好被視為心理病理學(xué)現(xiàn)象,而不是健康的現(xiàn)象。坦率地說,這種聯(lián)系表明機(jī)體相對(duì)有病。……健康人的認(rèn)識(shí)相對(duì)無動(dòng)機(jī),而病人的認(rèn)識(shí)相對(duì)有動(dòng)機(jī)。”[1]4如果我們聯(lián)系后來世界衛(wèi)生組織對(duì)“健康”所下的定義,便能理解馬斯洛的論斷并非聳人聽聞,“健康不僅指沒有疾病,還包括生理、心理、社會(huì)適應(yīng)和道德品質(zhì)的良好狀態(tài)”[3]80。因此,心理的狀態(tài)也必然是健康所考量之物。
從需要理論出發(fā),馬斯洛指出了相對(duì)無動(dòng)機(jī)行為會(huì)在基本需要得到滿足之后立即出現(xiàn)。這從側(cè)面說明了休閑才是人的本性,“在滿足后,機(jī)體立即允許自己放棄壓力、緊張、緊急和必須轉(zhuǎn)而變得閑蕩、懶散、被動(dòng),享受陽光,裝飾,美化,擦洗(而不是使用)壇壇罐罐,消遣,嬉戲,悠閑地注意并不重要的事情,行動(dòng)散漫,沒有目的”[1]3-4。由此,我們也不難繼續(xù)得出推論:不知足的忙碌,事事折射出過強(qiáng)的動(dòng)機(jī)和目的,正是違反人的本性的一種非本真、非健康狀態(tài)。
在馬斯洛看來,動(dòng)機(jī)、目的過強(qiáng)顯示了一種認(rèn)知的狹隘:“一個(gè)狹隘的生活觀將最終創(chuàng)造一個(gè)狹隘的世界。如在木匠眼中,世界是由木頭構(gòu)成的。”[1]5馬斯洛向我們展示出功利者和非功利者的不同心態(tài)與時(shí)間觀:
如果說標(biāo)簽化就是由于該人對(duì)未知事物的恐懼而過早地下固定的結(jié)論,它的動(dòng)機(jī)就是希望減少和回避焦慮,因此,以積極心態(tài)接納未知事物的人,或者,能夠容忍意義不明確的事物,人在感知過程中動(dòng)機(jī)就不如前者那樣明確[1]4。
對(duì)于注意用途、目的,壓低需要這種類型的人來說,沒有完成任何事情,不能服務(wù)于任何目的的時(shí)間都是被浪費(fèi)的時(shí)間。這種說法完全合理,但是我們可以提出一個(gè)同樣合理的說法:或許可以認(rèn)為沒有帶來終極體驗(yàn),即沒有被最大限度地享受的時(shí)間,就是被浪費(fèi)的時(shí)間[1]7。
顯然,前者是狹隘的、帶有病態(tài)色彩的,它通常是俗世之人的價(jià)值觀,而后者才是馬斯洛所倡導(dǎo)的健康的、積極的、自我實(shí)現(xiàn)的人的心態(tài)。自我實(shí)現(xiàn)絕非充滿目的、動(dòng)機(jī)的功利性行為,“自我實(shí)現(xiàn)水平上的自發(fā)性——健康和自然——是無動(dòng)機(jī)的,它的確與動(dòng)機(jī)相矛盾”[1]5。
馬斯洛還認(rèn)為,健康人的思維過程可以較為輕松,“在健康人的健全生活中,思維如同感知一樣,可以是自發(fā)的和被動(dòng)的接受或者生產(chǎn),它們是機(jī)體的存在和性質(zhì)的無動(dòng)機(jī)、不費(fèi)力的表現(xiàn),是讓事情自然發(fā)生而不是人為地使它們發(fā)生,就如同花香或者樹上的蘋果那么自然存在一樣”[1]10。這無疑是在言說休閑在認(rèn)知方面的某種價(jià)值。馬斯洛認(rèn)為:健康的人或自我實(shí)現(xiàn)的人在本質(zhì)上是多才多藝的;他所喪失的聰明才智比常人少得多[1]17。
這里的健康,顯然是指生理、心理、社會(huì)適應(yīng)和道德品質(zhì)的全面良好狀態(tài)。這句話顯然是在斷言休閑在人的自我成就方面所具有的價(jià)值,并隱含了將狹隘的、單向度的人視為某種病態(tài)的意思。
馬斯洛還發(fā)現(xiàn)這樣一種現(xiàn)象:有一類特殊的無目的、無動(dòng)機(jī)行為,“在本質(zhì)上屬于表現(xiàn),然而它對(duì)機(jī)體卻有些帶有目的性的益處,有時(shí)甚至是很明顯的益處。所謂的釋放行為就是一例”[1]19。這實(shí)際說出了休閑活動(dòng)對(duì)于身體健康方面的價(jià)值。馬斯洛又從反面舉例說,一個(gè)精神緊張、裝模作樣、隱藏自己本性的間諜,必然是疲憊不堪的。
從區(qū)分“表現(xiàn)性”和“應(yīng)對(duì)性”的角度,馬斯洛強(qiáng)調(diào)了表現(xiàn)性行為的自由性質(zhì):“對(duì)于自發(fā)的表現(xiàn)很難駕馭、改變、隱藏、控制,或者以任何方式加以影響。實(shí)際上,控制和表現(xiàn)原本就是兩個(gè)對(duì)立的概念。”[1]16而現(xiàn)代休閑學(xué)的基本理論認(rèn)為,休閑的最本質(zhì)屬性就是自由。這與馬斯洛的觀點(diǎn)有某種吻合之處。馬斯洛指出:“表現(xiàn)與應(yīng)對(duì)的區(qū)別還體現(xiàn)為前者不需要費(fèi)力,而后者在原則上需要做出努力”[1]17,而努力便意味著壓力和應(yīng)激。過多的應(yīng)激所帶來的對(duì)健康的巨大負(fù)面影響,早已由坎農(nóng)、塞里等在20世紀(jì)初的相關(guān)研究中闡釋得很清楚了。
相比之下,馬斯洛對(duì)表現(xiàn)性行為的重視便不言而喻了。因?yàn)椤皯?yīng)對(duì)性行為本質(zhì)上是工具性的,始終是達(dá)到一個(gè)明確目的的手段”[1]18。對(duì)照康德的名言:人性公式是“你要如此行動(dòng),即無論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還是其他任何一個(gè)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時(shí)候都同時(shí)當(dāng)作目的,絕不僅僅當(dāng)作手段來使用”[4]437。從此角度而言,一個(gè)人若生活世界里滿是應(yīng)對(duì)性行為,是不合人性的,無疑淪落為了某種工具。如果這是社會(huì)造成的,這便是病態(tài)的社會(huì);如果是自己造成的,這便是病態(tài)的人——要么在自發(fā)的功利性追逐中,要么在社會(huì)的裹挾下喪失了自我、顛倒了本末。
馬斯洛指出,在顛倒手段與目的的情況下,其表現(xiàn)就是:“在我們過分實(shí)用主義的文化中,工具性態(tài)度甚至壓倒終極體驗(yàn)。”[1]18例如,人們把愛情降級(jí)為一般人都要做的事情,把運(yùn)動(dòng)僅僅當(dāng)作有助于消化,將教育僅作為提高工資的手段,把唱歌理解為有利于胸腔發(fā)展,把好天氣看作于事務(wù)有利,把與孩子的感情聯(lián)絡(luò)視為避免孩子得神經(jīng)病的手段,把科學(xué)理解為有助于國家防御,把對(duì)人友善理解為“否則他們會(huì)偷錢”。故而,馬斯洛的價(jià)值取向是很明顯的:他倡導(dǎo)少一些功利性、工具性、應(yīng)對(duì)性行為,多一些無用的、自發(fā)性、表現(xiàn)性行為(尤其是藝術(shù)與審美),認(rèn)為后者才是根本目的,因?yàn)樗軒怼坝芍缘谋M興”“最大的快樂”和“終極體驗(yàn)”。
三、“道家風(fēng)格的自然”:休閑與審美
現(xiàn)代休閑學(xué)的分支——休閑美學(xué)理論認(rèn)為,審美從本質(zhì)上來說是一種無目的、無動(dòng)機(jī)的休閑性行為。而馬斯洛也早已從動(dòng)機(jī)理論提出,對(duì)于高級(jí)的復(fù)雜的人,無實(shí)用性和無目的性的審美體驗(yàn)是一個(gè)重要的問題。他注意到,不少人具有細(xì)膩的審美感受,這無疑也代表了人性所能達(dá)到的高度。對(duì)這樣的人來說,無視審美心理的任何理論都會(huì)被他們所鄙夷。故而,馬斯洛強(qiáng)調(diào)心理學(xué)研究應(yīng)當(dāng)注意審美體驗(yàn),否認(rèn)或者忽視審美體驗(yàn)的心理學(xué)理論,是有嚴(yán)重缺陷的:
審美反應(yīng)的無實(shí)用性和無目標(biāo)性,我們對(duì)它的動(dòng)機(jī)一無所知的現(xiàn)狀(假如在一般意義上說它真具有什么動(dòng)機(jī)的話),這些事實(shí)只應(yīng)該向我們指明我們的正統(tǒng)心理學(xué)的貧乏[1]6。
由于太注重實(shí)用,傳統(tǒng)的心理學(xué)忽略了許多對(duì)它原本意義重大的方面。眾所周知,由于傳統(tǒng)心理學(xué)家專注于實(shí)用效果、技術(shù)和方法,而對(duì)于美、藝術(shù)、娛樂、嬉戲、驚異、敬畏、欣喜、愛、愉快,以及其他“無用的”反應(yīng)和終極體驗(yàn)知之甚少,因而,對(duì)于藝術(shù)家、音樂家、詩人、小說家、人道主義者、鑒賞家、價(jià)值論者、或其他追求樂趣或終極目的的人也絕少有用甚至一點(diǎn)用都沒有[1]12。
馬斯洛認(rèn)識(shí)到審美的非功利性及其價(jià)值,進(jìn)而重視心理學(xué)研究中的審美體驗(yàn),這即使在當(dāng)前的心理學(xué)家中也是不多見的。馬斯洛不但意識(shí)到審美體驗(yàn)的價(jià)值,而且將神秘、敬畏、愉快、驚異、贊賞等審美體驗(yàn)視為“終極體驗(yàn)”。
值得注意的是,馬斯洛不但將美與藝術(shù)視為“無用的”反應(yīng)和終極體驗(yàn),也將娛樂、嬉戲(亦即休閑)視為同類,而且還將休閑與審美進(jìn)行了類比,實(shí)際上說明了二者的相通之處,即休閑也是審美性的。以上無疑為休閑美學(xué)何以可能提供了一定的理論依據(jù):從解釋人的本性和休閑美學(xué)的角度,說出了休閑與審美的關(guān)系以及休閑審美的機(jī)制。可以認(rèn)為,對(duì)馬斯洛來說,休閑和審美常常就是一回事。
馬斯洛進(jìn)一步主張人們更多地把自己的行為當(dāng)作一種忘我的和有意拋棄控制的深切體驗(yàn)來享受。馬斯洛尤其提到“被動(dòng)”的審美感知,提出它在認(rèn)知方面的價(jià)值:“成規(guī)化的感知在最好程度上也有片面性,它不能算是對(duì)于一個(gè)對(duì)象的全部屬性的細(xì)察,就像我們只根據(jù)那些典型,于我們有用的,與我們的利益有關(guān),或是能滿足需要或者是會(huì)威脅需要的屬性來為一個(gè)對(duì)象分類一樣。被動(dòng)地、無偏見地感知一個(gè)現(xiàn)象的多面性是審美感知的一個(gè)特點(diǎn)。”[1]6在這樣的思路下,馬斯洛對(duì)中國道家思想產(chǎn)生了特殊興趣及一定程度的認(rèn)同,故而倡導(dǎo)“道家風(fēng)格的自然、無意、不挑剔以及被動(dòng),努力不做任何努力”[1]14。他比喻說:用道家的立場來看,高境界的舞者能忘記音樂和忘記自我(類似道家的“兩忘”),不帶有任何意識(shí)、愿望,也分不清自動(dòng)抑或被動(dòng)。“舞蹈者必須為此學(xué)會(huì)拋棄禁錮、自我意識(shí)、文化適應(yīng)和尊嚴(yán)。他一旦摒棄一切欲念,對(duì)外表不以為念,那他就會(huì)在不知不覺之中逍遙飄游。”[1]14實(shí)際上,馬斯洛所描繪的“逍遙飄游”狀態(tài),無疑就是一種典型的道家休閑狀態(tài),也通向?qū)徝罓顟B(tài),而且是高層次的審美狀態(tài)。
馬斯洛在《人性發(fā)展能夠達(dá)到的境界》(1971年)中,闡釋對(duì)道家“接受”一詞的理解:“道家式的接受:道家精神和‘接受’都包含了許多意義,這些意義很重要,……大家普遍認(rèn)為,在創(chuàng)造力和原發(fā)期或靈感期,某種程度的接受性、非干擾性或‘無為’是關(guān)鍵特征。”[5]135某種程度上,“接受”即“無為”即“休閑”。此是后話,可以和《科學(xué)心理學(xué)》的休閑審美理論相互對(duì)照。
從區(qū)分“表現(xiàn)性”和“應(yīng)對(duì)性”的角度,馬斯洛又強(qiáng)調(diào)了表現(xiàn)性行為的審美性質(zhì)。他指出,各種言行舉止(諸如步態(tài)、舞蹈、說話的風(fēng)格、笑的樣子)以及繪畫、書法的風(fēng)格等等,這些東西的產(chǎn)生不是源自某種必需的滿足,而只是表面現(xiàn)象的一部分。“這種被動(dòng)的自發(fā)性——或者說由衷的盡興——能夠產(chǎn)生一些生活中最大的快樂。”[1]14馬斯洛列舉說:就像在岸邊任浪花拍打自己的身體;就像任人細(xì)心溫柔照料自己,讓自己承受愛的撫慰;或者像一位母親,任孩子吸奶、嬉戲,在自己身上爬來爬去;“各種形式的表現(xiàn)性行為,例如書法的風(fēng)格,或者與手段或目的全無關(guān)系,或者接近成為目的本身的行為;例如歌唱、閑逛、繪畫、在鋼琴上即興演奏等”[1]18。不難看出,馬斯洛的“表現(xiàn)性行為”在本質(zhì)上就是休閑行為,它的高級(jí)形式就是藝術(shù)表現(xiàn)和審美表現(xiàn)。
在《科學(xué)心理學(xué)》一書的結(jié)論部分,馬斯洛頗為憂慮地指出:在功利主義盛行的社會(huì)中,人已經(jīng)被經(jīng)濟(jì)學(xué)貶低為一個(gè)最優(yōu)化的計(jì)算機(jī)。經(jīng)濟(jì)學(xué)原則把人的行為從全部潛能和多種維度降低到一個(gè)狹小的范圍,這就是異化。馬斯洛堅(jiān)持:不能根據(jù)經(jīng)濟(jì)原則來衡量友誼、愛、創(chuàng)造性行為、審美的和宗教的體驗(yàn)等這些無動(dòng)機(jī)的休閑行為,不能用時(shí)間、勞動(dòng)力、物質(zhì)財(cái)富和金錢的消費(fèi)來評(píng)價(jià)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偉大。因此,“為了平衡經(jīng)濟(jì),我們必須用閑暇來補(bǔ)充勞作,用對(duì)精神和智力的追求來補(bǔ)充物質(zhì)需求的滿足。……商業(yè)精神將需要一種靜思無為、溫文爾雅的生活方式來進(jìn)行調(diào)節(jié)”[1]306-307。
這一論斷,更加明確地提出了休閑文化、休閑審美的重要性,指出了它是對(duì)現(xiàn)代社會(huì)異化現(xiàn)象的矯正策略。
四、余論
除了以上之外,馬斯洛在《科學(xué)心理學(xué)》中還直接或間接地發(fā)表了一些關(guān)于休閑的其他論斷。作為20世紀(jì)60年代誕生的理論,它們或開創(chuàng)了休閑學(xué)思想的某些先河,或成為其呼應(yīng)與共鳴。
(一)休閑與人格(個(gè)性)
人格(個(gè)性)是心理學(xué)的最基本概念,也是人的發(fā)展的最核心問題。正如馬斯洛所言:“個(gè)性的發(fā)展才是真正的發(fā)展。”[1]15我國學(xué)者早在20世紀(jì)30年代就提出這樣的休閑學(xué)基本原理:“一個(gè)人在享受閑暇的時(shí)候,通常是到什么地方去的?他對(duì)于‘閑暇’的觀念是怎樣的?他對(duì)于‘閑暇’是怎樣利用的?在這些問題的答案中,我們很能看出一個(gè)人的個(gè)性和人格是怎樣的。”[6]102而馬斯洛在《科學(xué)心理學(xué)》中也有類似的見解。
馬斯洛認(rèn)為:無動(dòng)機(jī)的選擇表達(dá)、展現(xiàn)了性格結(jié)構(gòu)。他還比喻說,正如植物向外界環(huán)境索取養(yǎng)料,人也向社會(huì)環(huán)境索取愛和地位。而只要獲得必需保障之后,植物也好,人也好,都會(huì)著手以自己獨(dú)特的方式發(fā)展和成長。這種風(fēng)格的外顯,馬斯洛稱之為“純粹的表現(xiàn)性行為”,并說“如果人希望了解性格結(jié)構(gòu),可供研究的最好行為肯定是表現(xiàn)性行為,而不是應(yīng)對(duì)性行為”[1]16。馬斯洛的“表現(xiàn)性行為”,常常就是指休閑行為。故而,“休閑展現(xiàn)人格”的思想,是馬斯洛對(duì)30年代休閑學(xué)理論的異域共鳴。馬斯洛還由此得出推論:在心理學(xué)研究上,表現(xiàn)性測驗(yàn)比應(yīng)對(duì)性測驗(yàn)更富有成效。
馬斯洛還將“休閑展現(xiàn)人格”這一思想延伸到藝術(shù)、審美領(lǐng)域,指出:“藝術(shù)最大的優(yōu)越性在于它是獨(dú)特人格的表現(xiàn)形式;最后,也許應(yīng)該這樣說:任何的科學(xué)事實(shí)或理論都可以由別人提出,但只有塞尚才能畫出塞尚的畫。只有藝術(shù)家才是無法替代的。”[1]26這一“藝術(shù)展現(xiàn)人格”的思想,引申出“藝術(shù)家無法替代”的結(jié)論,是對(duì)人文價(jià)值、藝術(shù)價(jià)值的高度肯定,它糾正了“科學(xué)至高無上”的片面性,誠為高度智慧之論。
(二)休閑與自我實(shí)現(xiàn)
“自我實(shí)現(xiàn)”是馬斯洛人本主義心理學(xué)的核心概念,成為“自我實(shí)現(xiàn)的人”是馬斯洛所認(rèn)為的人性的最高境界。在馬斯洛眼中,一個(gè)人的應(yīng)對(duì)性行為假使得不到報(bào)酬將不會(huì)再繼續(xù),而表現(xiàn)性行為卻會(huì)不斷延續(xù),因?yàn)樗男再|(zhì)決定了它原本不在意得到什么。自我實(shí)現(xiàn)不是追求目的性、功利性的行為,“自我實(shí)現(xiàn),達(dá)到充分發(fā)展,機(jī)體的潛力成為現(xiàn)實(shí)的境界,這一切更類似于成長和成熟而不是通過報(bào)償而形成習(xí)慣或者聯(lián)系的過程,亦即它不是以外界獲得的,而是在內(nèi)部展開在一種微妙的意義上說早已存在的東西”[1]5。故而,處在自我實(shí)現(xiàn)水平的人,其行為和創(chuàng)造“具有高度的自發(fā)性和開放性,無所掩飾,不加修飾,暴露自我,因而也具有很高程度的表現(xiàn)性”[1]14-15。從前文馬斯洛的表現(xiàn)性理論邏輯來看,自我實(shí)現(xiàn)的人無疑應(yīng)當(dāng)是休閑的。馬斯洛還直接指出:自我實(shí)現(xiàn)的人“過著某種意義上的隱居生活(例如,與追求社會(huì)地位相對(duì)),他們并不在一般意義上為改變現(xiàn)狀而做努力”[1]4。這一點(diǎn),用中國古代休閑文化中的隱士群體即可加以印證。總之,馬斯洛的“自我實(shí)現(xiàn)”與休閑有著不解之緣。
馬斯洛認(rèn)為,自我實(shí)現(xiàn)并非像愛和尊重等那樣是人的一種匱乏性需要,而是一種在成長中的自覺性和主動(dòng)性。因此,“最高級(jí)的動(dòng)機(jī)就是達(dá)到非動(dòng)機(jī),……它是‘第二次天真’‘聰明的單純’‘適意的狀態(tài)’”[1]15。而所謂“非動(dòng)機(jī)”“第二次天真”“聰明的單純”“適意的狀態(tài)”,即是休閑狀態(tài),尤其對(duì)成年人而言更是如此。
那么,如何自我實(shí)現(xiàn)?馬斯洛提供的方法途徑就是:通過優(yōu)先解決次級(jí)的動(dòng)機(jī)問題向自我實(shí)現(xiàn)接近。所謂“優(yōu)先解決次級(jí)的動(dòng)機(jī)”,實(shí)際上就是重視本性的需要、休閑的需要。美國哲學(xué)家約翰·凱利在其休閑學(xué)名著《走向自由》(1987年)一書中認(rèn)為,休閑在“成為人”的過程中十分重要,“休閑可能在一生的‘成為’過程中都處于中心地位”[7]79。凱利的著作是建立在人本主義理論之上的,他的“成為人”和馬斯洛的“自我實(shí)現(xiàn)”有很大程度的相通。馬斯洛重視休閑對(duì)自我實(shí)現(xiàn)的作用,這顯然被后起的休閑學(xué)家們所認(rèn)同和繼承。
(三)休閑倫理
人可以(應(yīng)當(dāng))如何休閑以及不應(yīng)當(dāng)如何休閑,屬于休閑學(xué)中的休閑倫理問題。而馬斯洛的“自我控制”理論,亦可認(rèn)為是在討論休閑倫理。馬斯洛指出,對(duì)于自發(fā)性和表現(xiàn)性來說,控制并非總是有害的和不可取的。也可以通過控制來對(duì)自發(fā)性、表現(xiàn)性行為加以優(yōu)化。“自我控制或者抑制有好幾種意義,其中有的非常健康、非常理想,……控制并不一定意味著阻撓或放棄對(duì)基本需要的滿足。”[1]17馬斯洛稱這種控制為協(xié)調(diào)化的控制,“它可以通過各種手段使人們享受到更大而不是更小的滿足”[1]17。他列舉說,通過適當(dāng)?shù)难舆t,如在兩性關(guān)系上;動(dòng)作的優(yōu)雅,如跳舞和游泳時(shí);審美的趣味,如對(duì)待食物、飲料;獨(dú)特的風(fēng)格,如在作詞賦詩中;等等。以上這些,無疑就是在談?wù)摗叭丝梢?應(yīng)當(dāng))如何休閑”。
馬斯洛又辯證地指出,一個(gè)人需要無拘無束,但“同樣也必須有控制自己的能力,有延緩享樂、彬彬有禮、緘默不語的能力,有駕馭自己的沖動(dòng),避免傷害別人的能力。他必須既有能力表現(xiàn)出酒神的狂歡,也有能力表現(xiàn)出日神的莊重;既能耐得住斯多葛式的禁欲,又能沉溺于伊壁鳩魯式的享樂;既能表現(xiàn),又能應(yīng)對(duì);既能克制,又能放任;既能自我暴露,又能自我隱瞞;既能尋歡作樂,又能放棄歡樂;既能考慮現(xiàn)在,又能考慮未來”[1]17。以上這些,既是在談?wù)摗叭丝梢?應(yīng)當(dāng))如何休閑”,又是在談?wù)摗安粦?yīng)當(dāng)如何休閑”。馬斯洛的“自我控制”理論,無疑對(duì)當(dāng)前的休閑文化建設(shè)和休閑倫理規(guī)范具有指導(dǎo)意義。
總之,馬斯洛《科學(xué)心理學(xué)》一書開篇的字里行間處處顯示出“休閑”“健康”“審美”這樣三個(gè)關(guān)鍵詞。這是他對(duì)弗洛伊德的動(dòng)機(jī)理論和杜威實(shí)用主義哲學(xué)的深刻反思的必然結(jié)果。馬斯洛看重人性的自然和內(nèi)心體驗(yàn),反對(duì)把人當(dāng)作“動(dòng)機(jī)的人”,重視“休閑的人”和“審美的人”的價(jià)值,認(rèn)為這才是“健康的人”。并由此主張多研究人類的非動(dòng)機(jī)的行為,認(rèn)為這才是被心理學(xué)所忽視而又真正重要的領(lǐng)域。反觀當(dāng)前我們的“休閑時(shí)代”,社會(huì)功利化日盛,休閑異化比比皆是,馬斯洛昔日的理論仍然顯示出積極的現(xiàn)實(shí)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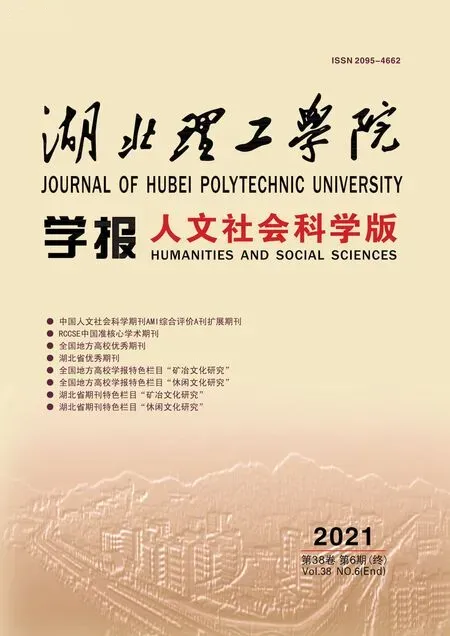 湖北理工學(xué)院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1年6期
湖北理工學(xué)院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1年6期
- 湖北理工學(xué)院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的其它文章
- 《湖北理工學(xué)院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征稿啟事
- 梁燕鶯景觀設(shè)計(jì)作品選登
- 大眾化中后期以來湖北高校本科專業(yè)結(jié)構(gòu)研究*
- 現(xiàn)代漢語中的三種“有…無/沒…”四字格*——以白話文經(jīng)典作家老舍中文小說語言語料庫為依據(jù)
- 政府向社會(huì)力量購買居家養(yǎng)老服務(wù)的探索
——以西安市L區(qū)為例 - 大數(shù)據(jù)時(shí)代大學(xué)思政教學(xué)技術(shù)改革的啟示及反思*——以“學(xué)習(xí)通”平臺(tái)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