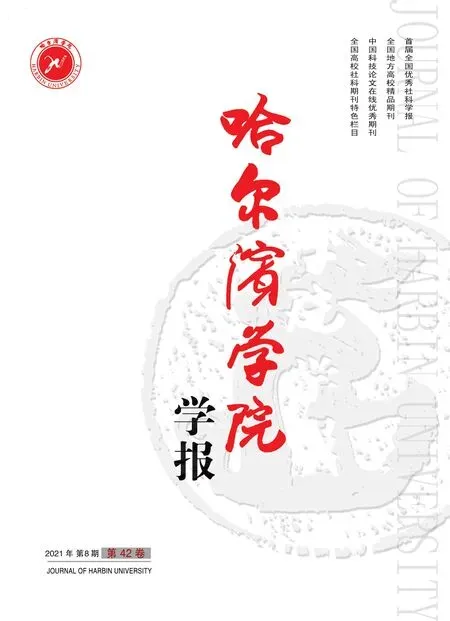寓意解讀:《邊城》三題
黃志軍
(泉州師范學院 應用科技學院,福建 泉州 362000)
沈從文曾說,他創作《邊城》是要“表現一種優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遂“借重”20世紀初葉湘西邊遠的小地方茶峒,幾個“愚夫俗子”——老船夫一家與船總順順一家四五人,被一件普通人事——兒女情事——因緣際會牽連在一起時,“各人應有的一份哀樂”,一份體認和反應,從而“為人類的‘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1](45)沈從文以小見大,以“一”觀“天”,其所推崇和表現的“人生形式”是一種人生與人心的存在狀態,存在于人類社會的整個發展階段,它跟人、人性、人事以及這三者所處的環境——大自然/“天”緊相關聯。正是在“天”的影響與控制下,人在其一生的成長和發展過程中的不同階段,其“人生形式”因受人性與人事的直接影響而呈現出不同形態。而沈從文在構建和表現它們的過程中的手法及寓意,值得通過文本細讀來作一解析。
一、《邊城》的大小虛實
沈從文的寫作用意,在《邊城》中可謂開篇顯志——小說第一自然段,字數不多,意蘊卻頗為豐富。沈從文采用俯視視角,由遠及近,由大到小,由“小”見“大”,由實至虛,虛實交互,廖廖數筆便將故事發生的自然環境及相應人物呈現在讀者面前,同時為全篇定下了田園詩化的民間敘事格調。其以“一”觀“天”的用意彰顯了作品主旨寓意指涉,也為全篇呈現了解構的目標與意義,值得細究。
“由四川過湖南去,靠東有一條官路。這官路將近湘西邊境,到了一個地方名為‘茶峒’的小山城時,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單獨的人家。這人家只一個老人,一個女孩子,一只黃狗。”
在這一段里,沈從文以“一條官路”“一個地方”“一小溪”“一戶人家”“一個老人”“一個女孩子”“一只黃狗”——這一系列的“一”,還有“小山城”“小溪”“小塔”——這一系列的“小”——來呈現其在全篇中“以‘一’觀‘天’”、“以‘小’見‘大’”(廣大而普泛的整個人類社會)而反映普遍的人生狀態的立意用意,即以邊城的這一個小家庭因一件兒女情事而牽連出來的人事悲歡,來書寫和呈現美好的人性、美好的人事及其遭遇的挫折與不幸,展示人因美好存在狀態的漸漸消失而困窘進而漸漸呈現并占據人的現在與未來,在這一敘事過程中沈從文深深的嘆惋則縈繞其間。
上述一系列的“小”與大自然的“大”相映襯,呈現出“人事”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在“天”及“天意”面前的卑微無力。然而“人事”雖小,當其落在人類任何個體(與大自然相較個體顯然卑微弱小)身上。大自然即“天”所施加的力量與影響,卻非任何個體所能輕易承受的,往往需要他們承受長久的痛苦與憂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
不僅于此,四川湖南邊境、官路邊城、溪水白塔等現實風物,這些是實景,是現實與客觀的描述。而老人、女孩兒和黃狗,則是虛擬的存在,誠如小說在后文中所述——“大自然長養”他們、他們在“風日里長養著”,他們依托前述現實風物——四川湖南邊境、官路邊城、溪水白塔等而存在,但他們早晚終將從這個大自然中消失不見,亦如小說中所寫——“老的已作完了自己分上的工作,安安靜靜躺到土坑里去了”“老年人是必需死的”“人死了哭不回來的”,并永不再重返這個由大自然所掌控的存在世界里。而前述客觀存在的現實風物中有個特別的存在物,即白塔,它不是大自然造就的,而是人們建造的,經年之后塔雖然會坍塌,亦如人的病歿,但正如小說后文中所寫——白塔在大雷雨之夜圮坍之后,人們又重建了這座白塔。然而誠如與白塔在同一時間里死去的老船夫的生命卻永不能重還一樣——重建的白塔雖是白塔,卻物是人非,因為此塔非彼塔,甚至人們心里所賦予新塔的意義同舊塔相比都是有所區別的。新塔不過是“有比沒有好”而已,所以塔的重建僅僅是人們聊以寄托一種美好的愿望,舊塔所代表的一切終究是不存在了。沈從文如此建構,這就意味著,小說后文正是將上述由傳統民間風物(白塔)所象征的美好的人、人性和人事,以及由這一切所構建的人的詩意與美好的存在世界解構開來,喻指這美好的一切將不再重還,即使人們主觀意愿重建,也僅如白塔的重建一樣,只能是新的一座對已消失的美好的人生形態的祭奠與紀念,一種徒然的心愿而已,只能令人扼腕長嘆。
二、《邊城》的四季人生
人是大自然的產物,生養在大自然中,受春夏秋冬季節更替的時令變化和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所影響和控制,因而懵懂無知、天真純樸的兒童,其生理和心理都得逐漸發育成長為青年,在荷爾蒙的作用下思慕和愛戀異性,積極尋覓婚配,在身心條件都成熟后結為夫妻并生兒育女,侍奉老人,且等待人生終結的到來。這一過程恰如四季時令變遷的易理——在大自然即“天”的推力作用下,明凈溫婉的春必然升溫進入高溫濕熱、萬物瘋長的夏;但物極必反,夏盛而衰,降溫降水,遂進入溫涼而萬物成熟的秋;大自然進一步降溫,萬物凋敝,進入寒寂的冬天,植物保存種子,動物保守機體,蟄伏靜守以待下一個輪回之春的到來。
正是因為在大自然之力——“天力”的推動下人必須“成長”,必然走向生理和心理的成熟,而生理的成熟是能生兒育女,心理的成熟則是能面對和承擔人生中一應繁瑣與煩苦的人事,承擔“各人應有的一分哀樂”。因而“成長”的過程就是走向人的困境——“長受苦”的存在狀態的過程,是一種出離人在嬌嫩質樸、純真無憂的兒童時期所擁有的美好身心狀態、美好人生階段即“春天”的過程,是一種日漸走向人事煩苦的過程,是從“春天”出發,經過“夏天”的狂熱,“秋天”的凄涼,最終走向“冬天”的沉寂與終結的過程。
而《邊城》的故事情節正是被沈從文精心設置從而“先后經歷”了三個綿長的夏天、一個短暫的秋天,而終結在寒寂的冬天的。春(在《邊城》中以象征的方式存在)夏秋冬這四個時令季節明明白白地與情節及人物命運的發展同步推進,亦步亦趨,沈從文正是在此過程中實現他所要突出表現的“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換言之,在《邊城》中,季節這一時令環境與沈從文所表現的“人生形式”之間存在明確對應的象征關系。沈從文按人的一生自出生至死亡的存在過程的先后形態差異,將之與大自然的四季相對應,在“天人合一”的象征過程中,先后書寫人的四個不同存在階段的“人生形式”,從而“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
(一)人之初
在《邊城》中,按故事時間、環境的先后及人的成長過程,首先書寫的顯然是沈從文最為推賞的“人生形式”——人最美好的性靈的呈現狀態——即人生的早期階段。“人之初”的孩童時期,在作品中正是13歲以前的翠翠所呈現出來的“一只小獸物”的性靈狀態——儼然就是大自然的精靈!其呈現的是一種純凈、樸野、良善、美好的性靈狀態,是與大自然渾然一體即天人合一的存在狀態,在人的一生中唯有在“人之初”階段才能與之相若。有如“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為,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外”。[2](52)作為被沈從文“安置”在荒僻之地“邊城”的女孩翠翠,“在大自然的長養與教育下”,她人生的前十二三年,即她“天真活潑,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的童年,因未解人事,尚未沾染人事的污濁、惹上人事的煩苦,所以“處處儼然如一只小獸物”,這是典型的“人之初性本善”的狀態。倘與她在后文中走向“成熟”的成長過程中的煩苦人生相比較,“人之初”階段的翠翠尚無她后來漸漸長大后伴隨而來的夏天里她的戀愛的苦悶、無助、憂傷和誤解,更無秋天里爺爺死后她的孤寂與痛苦,以及冬天里她的寒寂、憂慮與長受苦。因而現階段仿佛是她人生的春天,所以在沈從文筆下她的性情、精神品格等皆與春天和諧一致。這一段“人之初”的歲月,也就是翠翠人生的春天階段,也是小說所構筑的人物成長的“春季”。
(二)青春期
在大自然力量的推動下時令進入“夏”這個“寬假萬物使生長”的高溫濕熱季節,[3](P78)“天力”促使翠翠走向生理與心理的成熟,以便承擔作為女性應擔的那一分哀樂、那一分人事——在小說中表現為“作茶峒女子做媳婦的一切正經事”。于是——
“時間在成長她,似乎正催促她,使她在另外一件事情上負點兒責。……這女孩子身體既發育得很完全,在本身上因年齡自然而來的一件‘奇事’,到月就來,也使她多了些思索。”
翠翠同大自然上升的溫度與季節的更替同步發展至“夏天”——青春期。翠翠身體成熟,具備了生兒育女的生理條件,然而翠翠心理卻遠未成熟,尚不完全具備做茶峒人家媳婦的基本條件。所以沈從文安排大老天保這個愛慕翠翠的年輕小伙直率地對老船夫說:“翠翠太嬌了,我擔心她只宜于聽點茶峒人的歌聲,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婦的一切正經事。我要個能聽我唱歌的情人,卻更不能缺少個照料家務的媳婦。”
換言之,翠翠必須身心都成熟,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婦的一切正經事”,才能面對成年人所應面對的一應人事,但這一點仍得由“天”來推動翠翠去完成。所以沈從文寫道:“不過一切皆得在一份時間中變化。這一家安靜平凡的生活,也因了一堆接連而來的日子,在人事上把那安靜空氣完全打破了。”
顯然,沈從文認為人的生理成熟靠大自然,而心理的成熟則靠“天”管控之下的“人事”。這里,“時間”與“日子”即指時令,指大自然,指“天”,“天”之力也將實實在在地落實在“人事”上。這段文字也暗示“好景”不常在——大自然所長養出來的人的美好的存在狀態總要變遷,“安靜平凡”的美好生活終將因來臨的“人事”而遭“打破”,是“人事”破壞了安寧、祥和、純凈的人心存在狀態。換言之,“人之初”這一人生最美好的狀態是被“人事”所破壞的,且影響人心的存在狀態。
對此,小說是集中以三個“端午節”所處的季節時令——夏天——來重點和集中演繹主人公翠翠及人們圍繞她而進行的兒女情事的:傾慕、求婚、相思及因之而來的誤會與憤懣等。然而這種基本上只因生理成熟而來的兒女情事,其力量顯然還不足以促使人的心理成熟,還需“天之力”來進一步推動,因而故事不可逆轉地進入了“秋”——“緧迫品物使時成”的季節。[3](78)
(三)緧使成
從夏進入秋,其間的轉折就是夏末秋初的那場大雷雨。為什么是大雷雨?因為大自然推動有生命的萬物的發展,靠的就是水與溫度:春要進入夏,需要升溫加豐沛的雨水;夏要進入秋,需要降溫加雨水。此外,大雷雨還在沈從文筆下承載“天意”這一任務,也就是擔任大自然的“推手”這一角色。“緧迫”一詞,顯見采取的是外在的力量來“迫使”女主人公心理成熟,那么,似乎在“天意”看來——當然實質是在沈從文看來——僅靠一場大雷雨來“打破人事”顯得力度不夠,“天”因此再加之以象征邊城風水(“風水”即是“天”,即大自然的力量)的白塔的圮坍,再加之象征擺渡邊城人們的精神靈魂至其終極追求的“彼岸”的渡船被大洪水沖走,又再加上一個于故事情節極為重要的、親和純樸的老人的死去,四者之力疊加,方才撼動主人公翠翠封閉自守、自幻自戀的心扉開啟一線縫隙。所以,那個大雷雨之夜老船夫死了、白塔圮坍之后,故事陡轉直下,飽染凄涼的氣氛,而亦步亦趨緊跟情節的時令也陡然急轉入秋天。爺爺死后前來陪護孤女翠翠的楊馬兵告知了翠翠她所不知道的一切——
“后來便說到了老船夫死前的一切,翠翠因此明白了祖父活時所不提及的許多事。……凡是翠翠不明白的事,如今可全明白了。翠翠把事情弄明白后,哭了一個夜晚。”
所謂“明白”,就是“懂得”,并且承擔。在“秋”的“緧迫”之下,翠翠似乎自此心理“成熟”了——具備了做茶峒人兒媳的心理條件,已“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婦的一切正經事”,可隨時嫁到船總家去做媳婦,生兒育女。現在,翠翠就只等那個遠在辰州的心上人二老儺送的歸來。
(四)物終滅
很快,情節發展到了最后,時令也同步到了冬天。沈從文僅以一段話來為全文、也為翠翠的愛情和人生畫上一個句號——“到了冬天,那個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個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夢里為歌聲把靈魂輕輕浮起的年青人,還不曾回到茶峒來。”
冬天,大自然的推手已進一步降溫,進入了萬物枯候或終結的時令;而已被允諾做船總順順家兒媳的“成熟”的翠翠,現在則進入了寒冷而長受苦的漸趨寂滅的人生階段——“冬天”。這是萬物的循環,也是人生的必然。但是人在身心上是沒有循環輪回的機會的,誠如《邊城》中所寫“老年人是必需死的”“人死了哭不回來的”。所以在此“冬天”,人除了等待不日將至的死亡,余下的就只有回憶和懷念——回憶和懷念人們在“人之初”的春天階段大自然所賦予人們的那些因本能而來的“小獸物”般的性靈與快樂,以及夏天/青春階段充滿激情和幻想的略帶憂傷的兒女情事,它們是人生中最美好階段的內容,且永遠不能重現了。
因此,沈從文在小說結尾將故事永遠定格在冬天里——碧溪岨山崖下女主人公苦候遠在辰州的心上人(返回茶峒來迎娶她)的場景,這是在寒寂的長受苦的“冬天”里所展開的綿綿無絕期的枯守,等待那個遠在“夏天”的心上人的回來。因為那個在第一個夏天里邂逅并在第三個夏天里愛上翠翠的小伙兒儺送,也是在第三個夏天里因誤會和其他不幸的“人事”的擾攘下負氣出走的,所以,翠翠的愛情實際上是在夏天遭遇并開始,卻也是在夏天里被終結的。在小說結尾,幾乎失去靈性與生機、失去主動與幻想的“成熟的翠翠”魚肉一般被“天力”或“天命”擱置在命運的幾案上,枯候她那幾無懸念的已被天命與“人事”所裁定的人生結局,雖然她才十五歲!因而小說中這個在“冬天”里——人生的困境里——枯守的意象,其所暗指的即是那個有如“人之初”的美好的存在狀態的人生階段已在“天力”的作用下永遠地結束了。
人們難以想像,無論儺送回不回來,無論翠翠最終嫁給了誰,當有一天人們看見二十歲左右頭挽發髻的翠翠背上背著一個嬰兒,左手提一桶衣服,右手挎一竹籃菜蔬,從吊腳樓走下青石階來,到茶峒河邊浣衣洗菜,顯然,這就是大老天保心目中的那個能“照料家務的媳婦”和能做“一切正經事”的茶峒媳婦,這就是一個身心都已成熟的普遍的廣大家庭主婦的形象與命運歸宿,是千百個“翠翠”的形象與命運歸宿。那么,這時,那個作為大自然的精靈、大自然的化身的名叫翠翠的女孩子,那個“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的“小獸物”又在哪里呢?所以,什么叫美好的事物一去不復返?什么叫“那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這或許才是沈從文對美好人性消失不再的謳歌與嘆惋。所以不難理解《邊城》故事為什么終結在冬季。當一個人的身心經歷過人生的夏與秋并完全成熟后,他的人生,剩下的就是置身并面對萬物終滅的冬天了——那就是“長受苦”。
三、《邊城》的天命大魚
其實這就是讓人們發現,《邊城》故事的悲劇,或者說造成小說中幾個愚夫俗子因兒女情事而起的傷心與不幸的,乃是大自然本身——在小說中常稱之為“天”:“這些事從老船夫說來誰也無罪過,只應‘天’去負責”。船總順順也說:“伯伯,一切是天,算了吧。”顯然,無論是老船夫還是順順,都如是看待自家的悲劇,都歸因于“天”,而在他們的語境里,也就是“天命”。
“天”是一種力,一種神秘而無形的力,但它通過轉承在人們身上而呈現為具體的力量。在《邊城》中,它可以作“一物雙面”解:一方面“天”是大自然,另一方面“天”是命運(命運常常是大自然之力與人事之力的合力作用與結果),二者或可合稱為“天命”。“天命”在一定層面和程度上表現為大自然的時令(季節與節氣)、溫度、雨水、雷電、植物等,以及與之緊相關聯的其他物、人、事等。在《邊城》中具體表現為春夏秋冬和端午節等,表現為溫度、雨水、雷電、篁竹、虎耳草等,還表現為圮坍的白塔(因大自然之大雨沖擊、雷聲震撼、重力作用,再加之屬于人為的年久失修,這些皆為“天命”的作用與表現)、老人的死去(人體的生老病死)、少男少女生理與心理的成熟(大自然與人事的合力作用)、人們內心的憂傷、美好人事的消失以及人們因之而起的懷念(人事之力作用的表現與結果,這些皆為命運的作用),等等。
“天”這種力,在《邊城》中還突出表現為沈從文用心構建的“水里大魚”意象,其象征一種命運的力量。沈從文早在小說第四節就頗為用心地設置情節,安排翠翠與儺送這對年輕人邂逅,借儺送之口說出“回頭水里大魚來咬了你”,從而把導致翠翠愛情悲劇的力量——“水里大魚”引了出來,且一語成讖!事實上,翠翠愛情悲劇性的轉折正是天保為翠翠的事賭氣出走而意外淹死。換言之,翠翠的愛情的遭際正是“水里大魚”作祟的結果。老船夫和船總順順雖然都并不在意那句“回頭水里大魚來咬了你”的話,但二者都不約而同地感嘆兒女婚事的不合乃為“天意”。
沈從文的侄子、著名畫家黃永玉為小說《邊城》畫過兩幅插圖,其一即《大魚》,形象地表明他讀懂了《邊城》。因為同樣在湘西邊城風日里長養大并走出來的黃永玉,他對沈從文的親近、了解與理解非一般人所能及。在這幅逆時針構圖的《大魚》畫作中,黃永玉在構圖方面有意將魚最大化,以體現出“大魚”之“大”,此即“天”之“大”,正是命運之不可違逆。此外,圖中大魚的位置恰好介入在一對男女之間(他們分別代表儺送和翠翠),巨大的魚頭張開大口兇惡地咬向女孩,而女孩雖側身走避,卻是低眉垂目回首顧盼,顯見其情愿而卻又無知地面對人事以及她的愛情命運;而男子的頭被黃永玉畫成與畫中“大魚”一樣的魚頭狀。顯然,黃永玉也認為,女孩愛情的悲劇也是由這一“魚頭男子”所造成的,是由她的愛情所對應的異性一方因愛而起的人事所摧折的!換言之,翠翠愛情的悲劇是儺送所代表的男方對翠翠的愛造成的,是因為儺送兄弟二人為爭奪翠翠,兄長負氣出走而意外溺亡,而儺送及父親順順都認為自家親人的死是由老船夫一家造成的,自此以冷臉對待老船夫,導致老船夫絕望地死去。可見,在黃永玉看來,“水里大魚”就是儺送的化身,它承載翠翠的愛情,也吞噬了翠翠的愛情,同時也是翠翠所面臨的命運的象征。所以沈從文安排二人在第一個端午節的傍晚的水邊邂逅時,特意讓儺送對翠翠說“回頭水里大魚來咬了你”,這個“回頭”,就是一種時間的順承。
總而言之,“天”所指代的命運的力量,在《邊城》中是頗為引人注目的。沈從文在小說創作中,有意將《邊城》里的主要人物及他們的命運,與一些特定的動物聯系起來,并寄寓了特別的意蘊。誠如儺送同翠翠的婚事,終因“水里大魚”而牽連延擱下來,懸而未絕。這些,總還是“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