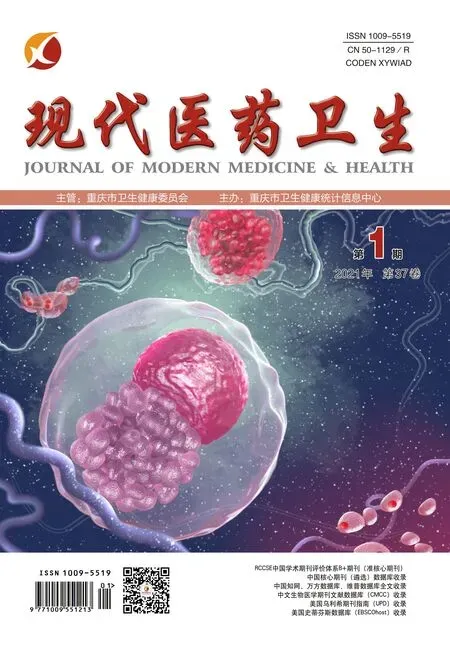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合并肝損傷案例報道及文獻復習
鄭珍川,董文紅
(合肥市第一人民醫院全科醫學科,安徽 合肥 230001)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傳染性強,傳播迅速,已被我國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乙類傳染病,按甲類管理。目前,COVID-19已成為全球共同關注的公共衛生事件。在臨床診療過程中及現有文獻資料中發現,部分COVID-19患者可出現不同程度的肝損傷,多表現為肝生化指標異常,個別病例可表現為嚴重肝損傷[1-4]。本研究以本院救治的1例COVID-19合并肝損傷病例作為切入點,對COVID-19合并肝損傷相關文獻進行了復習、分析和總結。
1 資料與方法
1.1資料
1.1.1臨床資料 患者,女,67歲。因新型冠狀病毒咽拭子核酸檢測陽性1 d于2020年2月16日收入院。其丈夫系COVID-19確診患者,入院前2 d患者被轉運至集中隔離點隔離觀察,1 d前市疾控中心檢測新型冠狀病毒咽拭子核酸陽性,故轉入本院進一步診治。病程中患者無畏寒、發熱、咳嗽、咳痰、胸悶、氣喘、腹痛、腹瀉、咽痛、全身乏力等不適,精神、食欲及睡眠可,二便正常。既往否認糖尿病、高血壓、冠心病等慢性病史,否認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炎、脂肪肝、肝硬化、肝癌等基礎肝臟疾病史。入院前14 d內無武漢市及周邊地區旅居史。入院查體:體溫36.6 ℃,脈搏88次/分,呼吸頻率20次/分,血壓147/91 mm Hg(1 mm Hg=0.133 kPa)。神清,精神可,呼吸平穩,問答切題,查體合作,全身皮膚、黏膜無黃染及出血點,淺表淋巴結未觸及腫大,球結膜無水腫,口唇無發紺,頸軟,氣管居中,胸廓對稱無畸形,雙肺呼吸音粗,未聞及明顯干濕性啰音,心界不大,心率88次/分,律齊,各瓣膜區未聞及雜音,腹部平軟,全腹無壓痛及反跳痛,未捫及包塊,肝、脾肋下未觸及。實驗室檢查血常規:白細胞7.98×109L-1,淋巴細胞1.86×109L-1,淋巴細胞百分比26.1%,超敏C反應蛋白小于0.5 mg/L,血清淀粉樣蛋白30.73 mg/L。生化檢查:清蛋白(ALB)42.2 g/L(正常范圍40.0~55.0 g/L),總膽紅素(TBIL)12.4 μmol/L(正常范圍3.0~22.0 μmol/L),谷丙轉氨酶(ALT)45 U/L(正常范圍9~52 U/L),谷草轉氨酶(AST)43 U/L(正常范圍14~36 U/L),堿性磷酸酶(ALP)84 U/L(正常范圍38~126 U/L),谷氨酰氨基轉移酶(GGT)53 U/L(正常范圍12~43 U/L),降鈣素原小于0.05 ng/mL。腎功能、電解質、血糖、心肌酶未見明顯異常。凝血功能:凝血酶原時間(PT)11.3 s(正常范圍8.0~12.0 s)。免疫組合:乙型肝炎表面抗原、表面抗體、e抗原、e抗體,以及丙型肝炎抗體、人類免疫缺陷病毒抗體、梅毒螺旋體抗體均陰性。肺部CT:右肺下葉斑片狀模糊影,考慮為病毒性肺炎的可能。
1.1.2入院診斷 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診斷標準,患者發病前14 d內有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其丈夫)的接觸史,發病早期查血常規白細胞總數正常,淋巴細胞數正常,肺部CT檢查符合病毒性肺炎影像學特征,且實時熒光聚合酶鏈反應檢測新型冠狀病毒核酸陽性,確診為COVID-19。患者入院時雖無明顯發熱或呼吸道癥狀等表現,但后續住院過程中患者出現發熱、咳嗽、咳痰等呼吸道癥狀,且住院過程中未出現第七版診療方案中符合重型及危重型的情況,故定義為普通型。
1.2方法
1.2.1診治方法 患者入院后給予洛匹那韋利托那韋、阿比多爾口服,α-干擾素霧化吸入抗病毒、抗感染(頭孢曲松鈉、頭孢哌酮鈉舒巴坦鈉、莫西沙星等)、中成藥疏風解毒膠囊、中藥湯劑、血必凈化瘀解毒等綜合治療。治療過程中患者出現肝損傷,表現為肝生化指標異常。2020年3月7日肝生化指標異常達峰值,ALT 389 U/L,AST 234 U/L,ALP 165 U/L,GGT 500 U/L,符合COVID-19相關的急性肝損傷診斷[5]。停用可疑致肝損傷的藥物,同時給予異甘草酸鎂注射液、注射用還原性谷胱甘肽抗炎保肝治療,好轉后改為口服甘草酸二銨腸溶膠囊。
1.2.2文獻檢索 檢索中華醫學期刊網、PubMed數據庫等調查自2019年12月至今國內外有關COVID-19合并肝損傷的文獻報道,收集、整理并匯總成表1。
2 結 果
2.1病情轉歸 患者出院前復查肝生化指標,除GGT仍升高(103 U/L)外,其余指標在正常值范圍內。患者體溫恢復正常3 d以上,呼吸道癥狀明顯好轉,肺部CT檢查急性滲出性病變明顯改善,連續2次咽拭子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陰性,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的出院標準予以出院。患者住院時間大于30 d,肝損傷相關生化指標變化見圖1~4。

1.ALT;2.AST;3.ALP;4.GGT。

圖2 TBIL變化

圖3 ALB變化

圖4 PT變化
2.2文獻檢索基本情況 共納入14篇文獻[1-4,6-15],其中4篇為多中心研究[2,8-9,14],其余均為單中心研究,收集的樣本量為30~1 099例。根據病情嚴重程度分為非危重組(包括輕型和普通型)和危重組(包括重型和危重型)。納入研究的患者以非危重組為主,危重組比例較低,除白澎等[10]納入的研究對象均為58例COVID-19重型和危重型患者外,孫大偉等[11]納入的研究對象中危重組占比例更高[58.8%(30/51)]。所有研究對象中合并肝臟基礎疾病者占少數。文獻基本情況見表1。

表1 文獻基本情況[n/n(%)或n(%)]
2.3肝生化指標 COVID-19合并肝損傷的發生率較高,主要表現為肝生化指標異常,其中以ALT和(或)AST升高多見,鮮有ALP和GGT異常的文獻報道,膽紅素升高也較少見,部分患者可出現ALB下降。同時,大部分研究表明,危重組患者肝損傷發生率較非危重組高,且危重組更多見于合并有基礎疾病者和老年患者。少有嚴重肝損傷的發生,只有CHEN等[1]和汪姝惠等[3]分別報道了1例。
2.4凝血指標(PT、PTA) 大部分患者未出現明顯凝血指標的變化,也有部分文獻報道了出現PT延長或PTA下降,且以危重組病例更多見。
3 討 論
COVID-19作為一種新發的急性呼吸道傳染病,其主要受累靶器官為肺,也可累及肝臟、心臟等器官[16]。本院為COVID-19患者定點收治醫院,在臨床診療過程中發現,部分患者在病程的不同階段甚至整個病程中均可出現不同程度的肝損傷。汪姝惠等[3]回顧性分析了收治于華中科技大學附屬同濟醫院的333例住院患者的肝生化指標,67.4%患者入院時即存在輕度肝損傷,ALT和(或)AST升高,住院期間復查ALT高于入院時。姚娜等[13]發現,疾病過程中出現肝損傷22例(55.0%),且肝酶指標多在病程第2周開始升高。本例患者從入院至出院整個病程均存在不同程度肝功能異常。目前,有關COVID-19合并肝損傷的定義、發病機制、臨床特點、預后等仍存在爭議,本例患者定義COVID-19合并肝損傷參照了近期中國醫師協會消化醫師分會和中華醫學會肝病學分會制訂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合并肝損傷的預防及診療方案》[5]。
肝損傷主要表現在肝生化指標異常(ALT、AST、ALP、GGT、ALB、TBIL)及PT或PTA異常。GUAN等[2]對全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552家醫院收治的1 099例確診COVID-19患者的臨床特征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ALT、AST、TBIL異常比例分別為21.3%、22.2%、10.5%,而ALP、GGT均未見明顯升高,非危重組患者中ALT異常者占19.8%,危重組患者中ALT異常者占28.1%,非危重組、危重組患者中AST異常比例分別為18.2%、39.4%,非危重組、危重組患者中TBIL升高比例分別為9.9%、13.3%。一項對武漢地區COVID-19患者消化系統表現的單中心、描述性研究結果顯示,ALT、AST、TBIL異常比例分別為25.0%、31.9%、2.0%,僅1例患者ALT(385 U/L)、AST(588 U/L)顯著升高,且ALP(235 U/L)、GGT(224 U/L)也顯著升高,危重組患者入院時肝功能異常比例(67.4%)高于非危重組(34.1%)[4]。CHEN等[1]納入了武漢金銀潭醫院99例確診患者,其中出現肝損傷43例,ALT、AST、TBIL、ALB、PT異常比例分別為28.0%、35.0%、18.0%、98.0%、5.0%,也僅有1例患者出現嚴重肝損傷(ALT 7 570 U/L、AST 1 445 U/L)。一項關于江蘇省80例確診COVID-19患者的多中心描述性研究表明,相較于武漢患者,80例患者中發生肝損傷的比例更低[3.8%(3/80)][8]。白澎等[10]對武漢市58例危重組(重型或危重型)患者的臨床特征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重型和危重型更易發生在老年患者和有基礎疾病者中,更易出現肝損傷,ALT、AST、ALB異常分別占55.2%、43.1%、74.1%。孫大偉等[11]采用回顧性隊列對照研究方法分析了51例COVID-19合并肝損傷的相關因素,結果顯示,ALT、AST、BIL、ALB、PT異常分別占47.1%、47.1%、9.8%、51.0%、19.6%,且出現ALP、GGT升高,分別占13.7%、35.3%;危重組患者發生肝損傷比例(63.3%)高于非危重組(47.6%)。總之,COVID-19合并肝臟損害發生率較高,臨床表現多為輕度肝損傷,主要為肝酶中ALT和(或)AST升高,ALP和GGT升高不明顯(僅少數文獻提及有ALP、GGT升高[4,11]),也較少出現膽紅素升高,部分患者可出現ALB下降及PT延長。同時發現,危重組更多見于合并有基礎疾病者和老年患者,且肝損傷表現相較于非危重組更突出。此外,武漢地區重癥病例和死亡病例比例較非武漢地區明顯增高,那么合并肝臟損害的比例是否更高呢?表1中文獻的數據大部分來自武漢地區病例,僅WU等[8]數據來源于江蘇省、XU等[9]數據來源于浙江省、姚娜等[13]來源于陜西省、劉川等[14]數據來源于非武漢地區7家定點醫院。對比數據發現,非武漢地區COVID-19合并肝損傷發生率相對武漢地區低,除陜西省[55.0%(22/40)]外,考慮可能與此部分病例來源于陜西空軍軍醫大學唐都醫院,收治的危重癥患者更多有關。但尚有待于非武漢地區的更多數據進一步支持。
本例女性患者發病期14 d內無武漢及周邊地區旅居史,入院時患者即出現輕度肝功能異常,表現為AST、GGT輕度升高[<2×正常值上限(ULN)],ALT、ALP、TBIL、ALB、PT均在正常范圍內,而在疾病發生、發展和治療過程中患者肝損傷加重,從圖1可見,病程第2、3周肝酶指標具有明顯上升趨勢,2020年3月7日肝生化指標異常值達高峰,ALT、AST、ALP、GGT均異常升高,尤其是GGT(>10×ULN)、ALT(>7×ULN)、AST(>6×ULN)變化顯著。經停用可疑致肝損傷的藥物,同時,給予異甘草酸鎂、還原性谷胱甘肽等藥物抗炎保肝治療后肝酶指標呈下降趨勢,出院前復查肝酶指標基本恢復正常,僅GGT仍升高(103 U/L)。同時,從圖2、3、4可見,ALB在病程第2、3周出現輕度下降,而PT、TBIL在正常范圍內波動。為解釋患者出現上述肝損傷特征,需進一步探討合并肝損傷的可能病因和發病機制。其中一種可能的機制為病毒直接的毒性作用。關貴文等[17]發現,血管緊張素轉化酶2(ACE2)在肝組織中只在膽管上皮細胞表達,而在肝細胞含量微乎其微,認為肝組織中的膽管上皮細胞出現代償性增生,ACE2表達增多,病毒ACE2受體更易與之結合,從而導致肝損傷的發生,可能為病毒直接作用的機制。本例患者入院時即發現AST、GGT(反映膽管損傷的酶)輕度升高,考慮與上述機制相關,但在疾病發生、發展和治療過程中患者肝損傷加重,考慮病毒的直接作用機制非本例患者的主要發病機制。且目前現有的文獻報道中,反映膽管損傷的ALP、GGT在合并肝損傷患者中無明顯升高,可能也說明病毒的直接作用不是主要的發病機制。另一種機制為細胞因子風暴學說,病毒侵入機體,激活機體免疫,導致免疫細胞產生大量炎性細胞因子如白細胞介素-1(IL-1)、IL-6、IL-8、腫瘤壞死因子等,最終導致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以及心臟、肝、腎等多器官衰竭[12,18]。嚴重心功能不全、循環衰竭、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多器官功能障礙等導致的肝臟缺血、缺氧再灌注損傷也是可能的發病機制之一。這2種情況多見于病情進展迅速的危重癥患者或需入住重癥監護病房的患者。本例患者住院期間未出現明顯缺血、缺氧、低血壓、低灌注等表現,期間監測IL-6(受本院實驗室條件限制只能檢測此項細胞因子)無明顯升高,作者考慮細胞因子風暴和缺血、缺氧機制造成本例患者肝損傷的作用很弱。此外,不能忽視治療過程中藥物導致的肝損傷。目前,使用的抗病毒藥物,如洛匹那韋利托那韋、阿比多爾、利巴韋林、α干擾素等[19]和抗感染藥物,如莫西沙星,以及中成藥、中藥湯劑等均可導致肝損傷,原有肝臟基礎疾病患者使用上述藥物發生肝損傷的概率更大。本例患者停用可疑致肝損傷的藥物,同時給予保肝降酶治療后肝損傷減輕,推測藥物性肝損傷是導致本例患者發生肝損傷的主要原因,與汪姝惠等[3]觀點一致。然而,藥物性肝損傷多表現為ALT、ALP異常,本例患者以GGT升高最為顯著,推測可能為綜合因素導致肝損傷的結果。
COVID-19合并肝損傷的治療首先是積極治療原發病。輕度肝損傷者一般不推薦應用抗炎、保肝藥物,應動態監測患者肝生化指標,如ALT、AST、ALB、TBIL、PT變化,進行肝功能分級,及時識別肝衰竭的發生;同時,積極尋找導致肝損傷的原因,關注患者其他臟器功能變化,糾正可能存在的缺血、缺氧損傷,停用或減量使用可疑致肝損傷的藥物,必要時可使用1~2種經證實的抗炎、保肝藥物[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