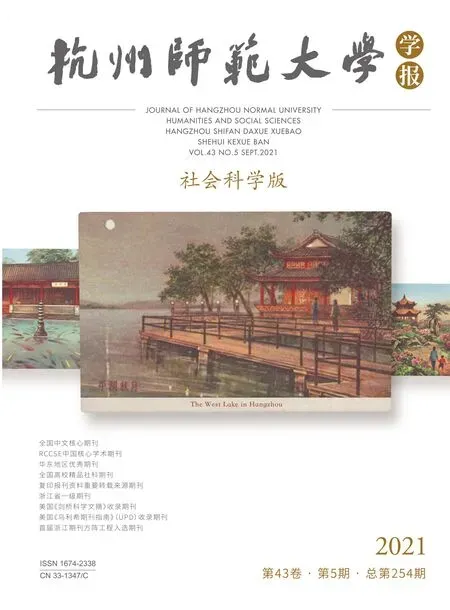百年來中國家庭結構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王躍生
(1.南開大學 歷史學院,天津 300350;2.中國社會科學院 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北京100732)
家庭結構是家庭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它可以反映特定或不同時期民眾的居住方式、家庭關系和家庭功能等狀況。
家庭結構有多個考察視角,總體上可概括為三種:一是家庭類型結構視角,以共同生活的血緣、姻緣和收養關系成員為基礎,以不同代際成員的婚姻狀況及所形成的婚姻單位數量為分類依據。基本類型有:單一婚姻單位家庭—核心家庭(包括標準核心、夫婦核心、擴大核心等),每代直系成員只有一個婚姻單位且共同生活者中至少有兩個婚姻單位—直系家庭(包括二代直系、三代直系、四代及以上直系等),共同生活成員中一代有兩個及以上婚姻單位—復合家庭(包括二代復合、三代復合、四代及以上復合等),單人戶(只有未婚者或喪偶者一人的生活單位)等;二是家庭規模結構視角,按照家庭共同生活成員數量將其分為一人戶、二人戶、三人戶、四人戶、五人戶等;三是家庭代數結構視角,以共同生活成員代數來分,分為一代戶、二代戶、三代戶、四代及以上戶、隔代戶等。
就當代而言,在這三類家庭結構考察方式中,家庭類型結構成為認識當代和歷史時期家庭結構的主要做法。這是因為類型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規模結構和代數結構,而后者則不能揭示前者的狀況。相對來說,類型結構的數據獲取難度也較大。
那么,從民國時期迄至當代,家庭研究者在中國家庭結構考察方面做了哪些主要工作?有何貢獻?不足是什么?本文將分三個階段(民國時期、1949年后至改革開放前、改革開放以來至2010年)進行考察。需要說明的是,本項回顧以類型結構為主,兼及規模結構。為簡化表述,文中所述家庭結構即為家庭類型結構。
我們旨在通過這一回顧對不同社會發展階段、不同制度環境下的民眾居住方式有所認識,借此探討提升家庭結構研究水平的途徑和方法。
一、民國時期的家庭結構研究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隨后民國建立,這可謂中國政治的空前變革。民國中期,城市和非農經濟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新的法律逐漸被制定出來,最突出的是,《民法》在1930年被頒布,女性的財產繼承權明顯增強。但這一時期,多數民眾仍以農村為生存載體,農耕是多數人的就業方式,傳統慣習依然影響甚至制約著民眾的日常行為。這一環境中的家庭結構狀態和變動有何表現?
一般而言,家庭結構的認識和判斷須以數據資料為基礎。而在整體上,這一時期與家庭結構相關的調查數據較少(家庭規模數據有一些,家庭結構數據很少),這成為對當時家庭結構研究的主要障礙,因而難以獲得對本期不同階段家庭結構的總體性認識。
值得指出的是,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特別是1930年前后,學者組織了多個包含家庭信息的調查,有的為跨區域調查,有的針對某一縣份,有的立足一個村莊。如李景漢1929年組織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喬啟明等人1924-1925年組織的安徽等4省11處農村調查和1930-1931年河北等11省22處調查,言心哲1931年組織的江寧縣土山鎮各村調查,吳顧毓1935年組織的山東鄒平縣實驗縣戶口調查,費孝通1936年進行的江村調查等。但除了費孝通的江村調查外,其他調查的匯總數據對家庭類型的劃分并非基于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和復合家庭等分類方法,其中有的只有家庭規模信息,或者僅對家庭共同生活成員親屬關系進行統計,比如將調查地區或樣本中戶主、配偶、子女、父母、孫子女、兒媳、兄弟等親屬各自所占比例加以描述。人們據此難以認識當時的家庭結構狀態。當然,這些調查數據對當時學者把握家庭人口的大小狀態或簡單與復雜程度有一定幫助。
那么,當時的研究者是如何認識和判斷家庭結構的呢?我們發現其中有兩種比較對立的認識:一種認為民國時期親子合爨、已婚兄弟不分家依然是主流,由此形成高比例的復合家庭。言心哲1928年出版的《中國鄉村人口問題之分析》指出:中國素有“大家庭”制度,此種“大家庭”在中國鄉村尤為普遍。所謂“大家庭”,除夫婦子女以外,尚有父母、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姊妹、從兄弟姊妹及其他近親屬同居共食。中國鄉村家庭,父子兄弟同居的固然很多,其他近親屬同居者亦復不少,因此組成鄉村家庭之人口關系非常復雜。[1](P.13)而在1935年一項綜合了30年代前后的多項家庭調查數據的研究中,言心哲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自己所言當時大家庭為普遍形態的認識。他說:中國各地每個家庭平均人口為5.5人,“與其他國家相較,并不為多,因為歐美及日本各國之農村家庭之平均人口,亦在五口上下。若僅依上述之每家庭之平均人口,吾國之農村家庭制度,亦不算大,與普通一般人所想象中國農村家庭大小,正是相反。因為普通民眾大都以為中國農村是大家庭制度”[2](PP.18-20)。可以說,言心哲的前一表述是基于家庭親緣關系所做概括,后面所言則是根據家庭人口規模得出的認識。在我們看來,人口死亡率較高、預期壽命較低的時期,當全國或某一地區平均家庭規模達到5.5人的水平時,復合型家庭將會占一定比例。而在民國研究中,單純從家庭人口規模來說明家庭類型的簡單與復雜的研究并不少見。這可謂是一種模糊的家庭結構認識。
持當時大家庭占主導觀點的學者還有李景漢。李景漢通過1930年前后定縣農村的實地調查,得出這樣的認識:“農村的家庭組織是大家庭制度。歐美的小家庭制度尚沒有影響中國的農村社會。已婚子仍與父母共同生活,結婚的弟兄亦少有分家者。因此家庭內的親屬關系頗為復雜,尤其是人口眾多的家庭。”[3](P.139)
組織過多次農村調查的喬啟明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撰寫了《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學》一書,其中有言:“在我國農村家庭中,父母均與其子女同居,即子婚女嫁以后,大多仍舊同居,結果形成聯合大家庭(Joint family)。在此聯合大家庭中,各人伙合其所得,雖有人遷徙異鄉,但仍視為家人,不與家庭脫離關系。”[4](P.271)基于其所進行的社會調查,喬啟明又有這樣的分析: “近年以來,城市發達,交通便利,農民與社會接觸的機會較多,其生活遂日趨于個人主義化,致當地原有風俗禮教漸失立場。加以年來國內社會經濟狀況衰落,舊式家庭中原有的經濟合伙制度亦告崩潰,于是小家庭制應運而生。但其影響則遍及城市,而農村家庭平均人數仍在五人左右。[4](P.277)喬啟明對農村家庭形態及其變動的表述不夠連貫,給人以“跳躍”之感,其本意還是想表達總體上農村以大家庭為主的狀態并沒有受到外部社會環境變動的深層觸動。不過,也應指出,中國的小家庭制是這一時期才“應運而生”,還是近代之前即已存在?近年來的研究似乎更支持后一種認識。
基于江南農村調查的費孝通(1936年)則看到江村居民小家庭為主導的居住格局,這與李景漢等人所考察的北方農村不同。在江村,按照當地的習慣,孩子長大后就要分家。有限的土地如果一分為二,就意味著兩個兒子都要貧困。[5](P.33)江村1936年的家庭數據顯示:殘缺家庭占27.6%,核心家庭占23.7%,直系家庭占45.4%,復合家庭占3.3%。[6]可見,當地農村沒有已婚子女和只有一個已婚子女的家庭占絕大多數,即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是主體。費孝通進一步推斷說,所謂大家庭,看來主要存在于城鎮之中。[7]當然,其后一種認識尚缺乏經驗數據的支持。
對民國時期城市家庭結構的整體調查相對農村要少得多,不過有一些對城市特定群體的小型調查。值得一提的是,劉臻瑞1938年對成都市192名婦女所做調查顯示,在核心家庭生活者占50%,有老人的折中家庭(與直系家庭接近)占31.42%,大家庭占14.58%,不詳占4.0%。(1)劉臻瑞《成都市婦女社會活動調查》,《社會調查集刊》下編,1939年12月,轉見李文海主編《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婚姻家庭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70頁。這一調查的家庭分類較粗,但從中也可看到當地婦女所生活的家庭結構狀態,其中核心家庭占比最大,其他類型復雜的家庭也占較大比例。
通過對已經出版或刊發的民國時期家庭調查資料進行梳理,不難發現,當時學者所組織的調查雖收集了特定地區的家庭人口規模、家庭關系信息,但與家庭結構有關的類型識別或者較粗略,或者付之闕如。更重要的是,現在所見到的調查數據多屬分類匯總,沒有所調查家庭的戶主與戶內成員關系信息,這為識別家庭類型帶來了困難。一些對家庭進行了初步分類的調查數據,與現代家庭結構分析方法難以對接。另外,限于交通等客觀條件,當時的調查者多選擇城市或調查者供職的學校附近鄉村和城市居民區,即使在外地所選調查點也多是交通相對方便之地。可見,民國時期的家庭結構調查和研究有較大局限性。當然,這一定程度上也與當時中國社會狀況和區域多樣性有關,不能說他們的調查并沒有反映實際,只是所選調查點的隨機性欠缺一些。我們認為,只有獲得更多基于微觀家庭調查和相對完整家庭成員信息的資料,才有可能比較全面地反映民國時期的家庭結構面貌和特征。
需要注意的是,20世紀80年代,當代家庭研究者試圖對經歷不同時期的城鄉民眾進行回溯調查來認識民國特定地區家庭結構的狀態,而追溯的源頭最遠為民國中后期,且選擇地區和樣本有限。其中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組織的上海、北京、天津、南京和成都5個城市所做調查具有較高認識價值,以1937年前結婚者為例,娘家單人戶5.88%,核心家庭55.61%,主干家庭25.67%,聯合家庭8.56%,其他家庭4.28%;婆家單人戶占15.08%,核心家庭占51.35%,主干家庭占17.77%,聯合家庭占8.98%,其他家庭占6.92%。(2)參見五城市家庭研究項目組編《中國城市家庭——五城市家庭調查報告及資料匯編》,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84、508頁。受訪者結婚時雙方家庭比較一致的家庭類型為聯合家庭,核心家庭相對接近;差異最大的是單人戶,其次是直系家庭。此處的單人戶應該指受訪者本人(或配偶)結婚前一個人生活。這一數據表明,男性婚前單獨生活比例明顯高于女性,它與當時社會男性獨自進城或在城市謀生比例高于女性有關。該調查提供了間接認識1949年前民眾家庭結構的數據。
筆者借助1964年“四清”時期《階級成份登記表》檔案復原了1944年冀南地區5個村莊的家庭結構,發現在平原、丘陵和山區存在差異,成份者之間也有不同。總體上當地農村具有大小家庭并存特征。[8](P.199)研究者若能借此資料分析更多省份的村莊家庭結構,則可提升對當時全國農村的家庭結構狀態和特征的認識。
民國時期是政治變革劇烈、鄉村農耕經濟仍占主導、城市工商業初步興起、思想意識多樣性突出、民眾生活傳統主色調中萌生出現代性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家庭結構也顯示出其時代特征。但總體來看,由于數據等第一手資料所限,或調查范圍有限,無論當時研究者還是當代學者并沒有對民國時期家庭結構的總體狀況和階段之別有清晰把握和認識。此外,當時研究者根據自己的調查獲得一些局部性認識,由于選點有限,難以形成對全國或區域家庭結構具有整體性認識的基礎。要改變這種局面,挖掘和收集具有一定規模和區域代表性的數據資料,是必不可少的路徑。總之,民國時期家庭結構研究是一個亟待加強的領域。
二、1949年后至改革開放前的家庭結構研究
若著眼于清末以來百年間中國家庭結構研究的歷史,不難得出這樣的認識,1949年后至改革開放前的家庭結構研究最為薄弱。其中有兩個原因:一是這一時期我國的人口學研究、社會學研究不受重視,可以說基本處于停滯狀態,作為其分支的家庭及其結構研究論著缺乏。翻檢這一時期的文獻,很難獲得微觀家庭調查數據和當時學者對家庭結構的判斷;二是已經公布的1953年和1964年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普查數據中缺少可用于家庭結構分析的微觀家庭信息。改革開放以來,在人口學和社會學這兩個學科重建后,一些學者在研究解放后的家庭結構時試圖開發這兩次重要的人口普查數據,但由于當時數據錄入方式和手段簡單,沒有這方面的信息,因而無從認識這一時期全國整體家庭結構及其變動。
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社會學、人口學專業研究和教育機構的組建,家庭研究首先受到從業者的重視,不同形式、規模的家庭調查陸續展開。其中一些調查的牽頭人(如雷潔瓊、馬俠、潘允康、沈崇麟、楊善華等)在組織人員進行家庭問卷調查時,對受訪者1949年以來不同時期(特別是結婚時點)所生活的家庭類型進行回溯調查,這一定程度上彌補了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家庭結構數據欠缺的不足。其對特定群體和地區家庭結構認識的價值應該肯定。
筆者利用1964年《階級成份登記表》所包含的信息,對冀南農村家庭在高級社初期、1964年時的家庭結構及其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此外,我們在浙江、湖北的調查中也從檔案館中獲得了一些村莊1966年前后的《階級成份登記表》。我們將這些資料信息錄入電腦,建立數據庫,為研究這一時期的家庭結構提供了難得的資料。經過初步分析發現,土改后,農村家庭一直處于分解之中,小型化趨向突出。1964年這些地區的農村即初步實現了核心化(核心家庭和核心家庭所生活的人口占比超過60%)。進而指出,中國農村家庭的核心化與工業化、城市化的推動沒有直接關系,而是自身在制度變遷的作用下實現的。(3)參見王躍生《華北農村家庭結構變動研究——立足于冀南地區的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4期;王躍生《中國農村家庭的核心化分析》,《中國人口科學》,2007年第5期。王天夫等人2013年前后對山西70歲以上老年人進行口述史調查得出與筆者相似的認識:20世紀50年代中期土地集體化之前、50-70年代土地集體化時期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時期農村家庭結構即出現小型化趨向,中國傳統大家庭向小家庭的轉型并不是由西方傳統意義的工業化促成的,作為1949年后國家早期工業化策略的農村土地集體化徹底改變了傳統家庭生產與生活的組織方式,改變了父權制度下的代際關系與結構,進而啟動了家庭結構轉型的歷史進程。[9]
費孝通發現其20世紀30年代所調查的江村,1949年后家庭結構繼續發生變動。其中1950年殘缺家庭占27.4%,核心家庭占32.3%,主干家庭占35.5%,聯合家庭占4.9%;1964年,殘缺家庭占34.4%,核心家庭占44.7%,主干家庭占20.3%,聯合家庭占2.4%[6]。其核心家庭實際占比為78.1%,不僅實現了核心化,而且達到高度核心化水平。
一些回顧性調查對城市1949年后的家庭結構變動有所反映。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1982年在上海、北京、天津、南京和成都5個城市調查數據顯示,核心家庭基本上處于不斷上升狀態:受訪者結婚時娘家1950-1953年核心家庭占48.94%,1954-1957年為52.25%,1966-1976年為67.13%;婆家三個時間段分別為60.53%、49.28%和60.16%。聯合家庭則有波動:娘家分別為6.78%、9.63%和4.30%;婆家分別為4.03%、6.21%和3.50%。(4)參見五城市家庭研究項目組編《中國城市家庭——五城市家庭調查報告及資料匯編》,第484、508頁。
總而言之,這一時期由于資料缺乏,人們只能利用中小型調查或對特定群體的回溯調查來間接認識某一時點民眾的家庭結構,這種探討是有價值的。不過,回溯性調查中的受訪者不同結婚時點娘家和婆家的家庭結構狀態尚難以反映特定階段和地區整體的家庭結構狀態,可視為受訪者在夫婦生命歷程某一事件發生時(如婚姻締結之時)的居住方式。我們必須承認,在對家庭結構整體性把握方面,這一時期家庭結構狀況研究狀況甚為欠缺。
應該說,一個距離現代如此之近、時間跨度較大、地位如此重要時期的家庭結構研究如此薄弱,是一個令人難以接受的事實。不過,已有基于“四清”檔案資料的研究表明,這一時期家庭結構研究的薄弱狀況是有一定條件予以彌補和加強的。
三、改革開放以來的城鄉家庭結構研究狀況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后,中國家庭結構研究被注入了活力,表現為有更多研究者關注這一問題,通過大量田野調查資料和系統的人口普查數據分析當代家庭結構狀態、階段差異和變動趨向。
這一時期對家庭結構研究關注較多的學者,大體可分為兩支:一支是社會學學者(人類學研究者也可歸入其中),如費孝通、雷潔瓊、潘允康、沈崇麟、楊善華、李銀河、徐安琪、唐燦等。他們以城鄉社區、村莊進行的典型調查數據為基礎,分析家庭結構在社會變革時代的最新變動;另一支為人口學學者,他們在家庭結構方面的研究更為深入,且注重開發1982年以來的人口普查等大型數據庫,借此研究全國家庭結構的整體狀態和影響因素,如曾毅、郭志剛、王躍生等。另外,風笑天、宋健等則對第一代獨生子女婚后所組成的家庭形式進行了探討,譚琳等就“空巢”家庭專門分析。因而,這一時期,對家庭結構無論是整體還是特定類型都有相應研究。
歐美一批人口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專門針對中國當代家庭結構變動開展研究。其中以美國學者的成就最為顯著,他們中的代表人物為Susan Greenhalgh[10]、Stevan Harrell[11]等,這些學者關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人口變動,對家庭結構變動及其影響均有涉及。此外 James Lee和王豐還將歷史和現實結合起來,探尋中國人口和家庭結構的演變軌跡。[12](PP.33-65)國外學者對中國家庭結構的研究在方法和視角上給人以啟示,特別是在模型分析上值得借鑒。但外國學者在對中國家庭結構研究中,主要利用已經公布的官方數據,還有的則利用典型調查資料進行描述,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比較少見。
在此我們分幾個專題簡述如下:
(一)家庭結構總體狀況的研究
1982年以來的人口普查數據庫為家庭研究者提供了全面認識中國城鄉家庭結構的條件。
曾毅等較早利用1982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抽樣數據庫分析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家庭結構及其特征,指出至1990年中國家庭以核心家庭為主,同時三代家庭也占重要地位,橫向聯合的大家庭所占比例極小,并將核心家庭與直系家庭并存視為中國的特征,與此相對照的是西方核心家庭占絕對優勢的模式。(5)參見曾毅、李偉、梁志武《中國家庭結構的現狀、區域差異及變動趨勢》,《中國人口科學》,1992年第2期;曾毅、梁志武《中國80年代以來各類核心家庭戶的變動趨勢》,《中國人口科學》,1993年第3期。2000年后,曾毅等又將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抽樣數據集合起來,發現2000年三代家庭戶較前兩次普查上升,而二代核心戶則表現為較1990年降低。他認為,這些變化不能說明中國家庭正向傳統回歸,而是1970年代初以來生育率下降的滯后效應造成。[13]曾毅等的分析基本符合實際,但也有需要改進之處。其結論性認識缺少城鄉視角,而在當代中國,特別是社會出現轉型的時期,城鄉家庭結構變動差異很大,如2000年城市直系家庭與之前相比就是下降的。
筆者基于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三次人口普查抽樣得出當代中國家庭結構變動呈現出三種狀態的認識:一是相對穩定的家庭類型,三代直系家庭是其代表。二是明顯上升的家庭類型:夫婦核心家庭提高幅度顯著,認為實行20余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是這一家庭類型的主要推動力量;隔代直系家庭增長率最高,它既是中國社會轉型階段的重要現象,又是社會發展不夠完善的反映;單人戶也有增長,青年人晚婚和老年人口預期壽命延長、老年喪偶比重提高是主要影響因素。三是以下降為表現形式的家庭類型。缺損核心家庭明顯減少,標準核心家庭有所下降。后者的降低主要是夫婦核心家庭上升所致,或謂核心家庭內部不同類型調整的結果。[14]
郭志剛在人口普查抽樣數據的基礎上,加入2005年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俗稱“小普查”數據),分析中國家庭戶的變動及其特征。他指出:我國的計劃生育推動了人口結構的轉變,是導致平均家庭戶規模迅速縮小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生育水平已經在1990年代降到很低,故此這種純人口因素對家庭戶規模影響不斷減弱,社會經濟發展導致的遷移流動及生活方式變化使主干家庭模式和核心家庭模式此消彼長,家庭分化程度正在提高。現階段純人口因素(獨生子女)對家庭結構的影響實際增強了,而非減弱。[15]
可以說,人口普查抽樣數據和“小普查”數據使研究者增強了對當代中國家庭結構狀態的整體把握。這一時期生育控制政策對家庭結構的影響逐漸顯現并為研究者所關注。但也應看到,這些宏觀分析對象多限于兩次普查之間,時間范圍較小,民眾居住方式的變化尚未充分表現出來。若將改革開放以來至2000年這一時間跨度的家庭結構考察結合起來,將會抽繹出更多理論認識。
(二)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實施對家庭結構的影響
1982年,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的實施是這一時期重要的制度變革舉措。家庭的生產功能在被取消26年之后恢復,它直接影響廣大民眾的家庭經濟活動、謀生方式等,并可能對家庭關系、家庭形態產生影響,因而吸引了研究者的注意。那么,這一制度是否會促使大家庭增長?在研究者中形成兩種認識:
第一種認識為,家庭生產職能的恢復降低了分家頻度,從而有助于直系家庭、復合家庭等相對復雜家庭的生成。這一觀點是通過對聯產承包責任制前后家庭結構的比較得出的。
費孝通從其長期關注的江村得到1985年與家庭結構變動有關的資料,據此認識改革開放初期家庭結構的最新變動。他發現,該村的主干家庭在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后,并未因房屋的增建使小家庭趨向突出,反而有10戶小家庭和2戶殘缺家庭合并成6戶主干家庭。費孝通認為,促使原來分了家的單位重新合并,并加強主干家庭穩定性的因素,除了兩代共同經營其承包的土地效率較高外,贍養方式的變動也在起作用。費孝通同時也指出:承包責任制實行后,主干家庭在數量上的回升并不意味著農民家庭生活方式在走回頭路,重新轉向傳統的家長制度。在他看來,該地也存在著家庭核心化的力量,如農民就業非農化趨向出現,婦女家庭地位提高。[9](P.3)
雷潔瓊也對家庭承包責任制后的農村家庭結構予以關注,她指出,為了發展生產,勞動力是重要因素,有些家庭原要分家的暫不分家;有些家庭已分居的,重新組合,分工合作。[16](P.27)
20世紀80年代中期莊孔韶對福建長樂縣一個農村做過專項調查,該村1975年核心家庭為73.1%,主干和擴大家庭為20.8%,單身家庭為6.1%;1985年三項指標變為64.3%、30.8%和4.9%。他據此認為,這是中國農人實踐其大家庭意識的一個地方例證。[17](PP.300-303)
曾毅以1990年和1982年這兩個年份的人口普查數據為基礎,考察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對農村家庭結構的影響。1990年聯合家庭(即復合家庭)較1982年增加20%。曾毅的解釋是,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的推廣及城鎮個體經營業的發展使得已婚兄弟姐妹分工合作的聯合大家庭更具有存在的基礎。[18]
第二種認識為,農村土地承包制的實行并沒有改變家庭的核心化趨向。
黃宗智1983年和1985年對上海松江縣的考察中對農民家庭的親子關系有了具體認識。據當地農民講,在過去,父母老了一定和兒子們吃在一起,如果老夫妻有幾個兒子,則通常和最小的、一般也是最遲結婚的兒子同灶吃飯。但是現在因為婆媳關系緊張,老人們常常獨自吃飯。由于舊的倫理觀念要求子女照顧老人,故一對老夫妻只有一個兒子的話,他們很可能仍一起吃飯。但是老夫妻有一個以上兒子者通常都分開吃飯。不過獨子家庭有的也分開生活。這在很大程度上與緊張的婆媳關系有關。[19](P.302)
曹錦清等20世紀80年代末對浙北農村的調查發現:只有一子的家庭,一般由核心家庭順利地過渡到直系家庭。在這一地區,80年代中期以后,直系聯合家庭(實際是復合家庭)開始消失,直系家庭比例下降,而核心家庭不斷上升。[20](P.367)
閻云翔對黑龍江省一個農村所做多時段考察顯示,20世紀80年代以來,該村核心家庭持續上升,從1980年的59%,到1991年的72%,再到1998年的81%。與此同時,主干家庭則在慢慢減少,從1980年的32%,減少至1991年的22%,1998年的16%。[21](PP.104-106)
筆者對河北省南部農村的研究表明,土地承包責任制后家庭生產功能的恢復并沒有減慢多子家庭已婚兒子的分家步伐,相反加快了。冀南地區傳統時代大家庭組織對土地耕作具有優勢。而20世紀80年代之后,形勢已大不相同:一是每人的口糧田和責任田合在一起降到1畝或以下的水平,耕作量減少,合作生產的必要性降低了;二是隨著農業科技水平的提高,農田管理所花時間減少,基本上只限于種植和收獲時。為增加收入,成年勞動力更多地尋求農業之外的經商、務工活動。在第一種情況下,人們覺得核心家庭完全可以有效地組織小塊土地的經營,而且靈活方便,沒有必要留在大的家庭類型中。第二種情況下,年輕人在非農經營中的優勢顯示出來,因而更希望盡早分家,以便取得財產的支配權。[7](P.358)
雷潔瓊1986年主持的一項對上海、北京和河南農村的調查結果則比較特殊。1978年與1986年相比,三地既有核心家庭普遍上升的表現,又有直系家庭增加的特征。在對家庭人口增減原因分析的基礎上,該項研究者認為,調查地區農民家庭“分”的趨勢要遠遠超過“合”的趨勢。[22](P.79)
需要指出,對20世紀80年代農村家庭結構分析所得出的不同認識因考察時間不同而有別:那些強調家庭生產職能恢復對分家趨勢有所抑制的研究主要著眼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及之前,而認為責任制對分家趨勢沒有影響的研究則以80年代中后期為主。也許一些地區在土地承包責任制實行初期,分家勢頭有所放緩。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認為家庭分化速度因家庭生產職能恢復而有所降低的學者卻不否認核心型小家庭在這一時期的農村實際居于主導地位。由此可見,對當代家庭結構進行分析,所得出的認識也有“現時”(短期之內)和“歷時”(較長時段)之別,重要的是不應將“現時”觀察所得出的認識擴大化,把家庭結構中某一類型的變動視為一種新的趨向。這提示我們,在家庭結構研究中,要提煉出說明意義較強、較少偏誤的認識,需將兩種研究范式結合起來,既深入研究階段變動,又注意考察較長期的演變趨向。
(三)城市家庭結構的變動
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家庭一直保持著較高水平的核心化狀態,根據人口普查數據,核心家庭占比1982年、1990年和2000年接近,甚至超過70%。至2010年核心家庭降至65.30%,然而它并非直系家庭提高所致,而與單人戶大幅度提高有關。[23]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進行了多次基于城市家庭的調查,其中1993年在1982年五個城市調查的基礎上,增加為七個城市(北京、上海、南京、成都、廣州、蘭州和哈爾濱)。數據匯總結果顯示,核心家庭、主干家庭(直系家庭)和夫妻家庭分別占54.34%、25.28%、12.07%,三者之和占94.69%,調查組織者據此認為,這三種家庭結構類型是所調查的七個城市占主導地位的家庭結構。[24](P.40)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在2008年進行了“中國五城市家庭調查”(廣州、杭州、蘭州、鄭州和哈爾濱),根據該調查數據得出的認識是:核心家庭依然是城市占據主導地位的家庭結構,夫婦家庭的比例在上升,主干家庭的比例在下降,聯合家庭近于消失。[25]這些立足于抽樣調查數據所進行的實證研究結果與基于人口普查數據所得出的結論具有相互印證作用。
(四)對老年人口居住方式的研究
20世紀90年代以后,特別是2000年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后,老年人口居住方式逐漸成為研究熱點。曾毅、王正聯根據2000年普查數據研究發現,65歲以上老人與子女同住的比例分別下降了11.4%和7.2%,表明老年父母與成年子女同住的傳統家庭結構比例在20世紀90年代下降。這一方面可能由于較年輕和健康的老年人傾向于自己單獨居住, 另一方面可能由于更多的子女因為工作而遷移到外地。[13]郭志剛依據2005年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分析老年人口的居住方式。其認識是,老年人口與后代一起居住的比例依然占據多數,尤其在高齡老人中還占70%以上。但是處于“空巢”家庭的老年人口比例已經越來越大,因此他們在家務和醫療方面的特殊服務需要應當加以重視。最新人口數據揭示出與后代共同居住的老年人中,處于隔代戶的比例近年增加十分顯著。[26](P.23)
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數據中沒有老年被“輪養”的類型,若將其作為一個單獨類型,老年與已婚子女所組成的直系家庭比例還會降低。
(五)成年獨生子女及其父母居住方式
2005年以來,隨著第一代獨生子女長大成人,其本人和父母的居住方式受到研究者關注。國內學者中有多項針對城市獨生子女的調查,涉及獨生子女父母在子女成人后的居住方式和獨生子女本人長大后,特別是就業、結婚、生育后的居住方式。
風笑天2008年組織了北京、上海、南京、武漢、成都五城市以獨生子女父母為主的抽樣調查。根據該調查,未婚獨生子女的父母“空巢”比例占7.0%,核心家庭占88.2%;已婚獨生子女父母“空巢”的比例為56.4%,主干比例為35.8%,其他占7.8%。子女結婚成為父母家庭結構變化的最重要的影響因素。[27]該研究的不足是對獨生子女沒有進行年齡劃分。
宋健根據2009年在北京、保定、黃石和西安四城市所做針對獨生子女(20-34歲)就業、婚姻和家庭問卷調查數據(2954個有效樣本)進行研究發現,獨生子女在不同生命階段與父母同居比例差異明顯,不在業不在婚、在業不在婚、在婚未生育、在婚已生育時分別為88.48%、71.82%、24.26%和18.21%;非獨生子女四個歷程中與父母同住比例分別為69.11%、36.39%、12.00%和7.95%,這表明獨生子女與父母同住的可能性高于非獨生子女。其中受訪者夫婦雙方為雙獨、單獨和雙非三種類型與父母同住比例分別為25%、39%和36%。由此得出認識,雙獨夫婦相比較其他類型似乎更傾向于與父母分開居住。整體看,女兒婚后與父母同住的比例只有已婚兒子的30%-60%。[28]按照該調查,城市獨生子女在婚后并沒有形成高比例的與父母同居現象,婚后同居只占約四分之一,生育后同居不足五分之一。
這些調查反映出獨生子女成年,特別是已婚后對父母居住方式的影響具有雙重表現:一方面是一部分獨生子女,特別是兒子婚后與父母同住,提升父母或其本人在直系家庭生活的比例;另一方面是獨生子女婚后單獨生活促使父母“空巢”家庭比例升高,后一種傾向顯得更為突出。
(六)人口流遷對家庭結構的影響研究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勞動年齡人口遷移流動就業成為中國社會一個人口現象,是家庭結構分析中不可缺少的因素。這一時期中國人口的遷移流動多以青壯年勞動者(單身或夫婦)為主,而將未成年子女留在家鄉,由老人照看,在農村導致高比例的隔代家庭出現(6)參見周福林《我國留守家庭研究》,北京:中國農業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24-125頁;王躍生《當代中國家庭結構變動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而郭志剛根據2005年全國人口抽樣調查數據研究發現,2005年的流動人口不像早年那樣多為單身流動,已經顯現出家庭流動特征,其中居住于夫婦戶和二代戶的已經占了很大比例,甚至還有一定比例的三代及以上戶。由此他認為,早期的人口流動促使了家庭戶的分化,然而人口流動的進一步發展,又會出現全家在流入地重新組合,或者舉家同時流動。[15]
實際上,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流動就業對家庭結構的影響要比人口普查顯示的結果更為突出。因為,人口普查時僅把離開家庭半年以上者視為流出人口,那些主要在外地謀生,但間隔一定時間回家者則仍被視為在本家庭戶生活人口。當代社會轉型之下,更多的家庭成員分居兩地,中國家庭在核心化的基礎上出現“空巢”“隔代”甚至單人居住增多現象,可謂在社會變革和轉型中人們所付出的代價。要改變這種狀況,有賴勞動者及其家眷遷移流動相關生活、教育等成本的降低,更需要公共教育制度、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進來推動。
(七)家庭結構變動趨向的理論研究
中國家庭將如何進一步演變?其趨向如何?一些學者對此做了探究。
關于中國當代家庭的發展趨向,黃宗智不同意中國家庭也會沿著西方式的家庭核心化模式發展。他指出:我們所認為是必然的、普適的、來自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現代化”模式,使我們錯誤地把注意力集中于家庭的“核心化”趨勢。其實,在全球的比較視野下,真正應該引起注意的是三代家庭的延續。當然,伴隨集體化和家長權力的衰落,核心戶所占比例確實有所增加,但這并沒有改變贍養父母的基本要求,亦即費孝通之所謂中國家庭組織的基本的“反饋模式”,與西方的“接力模式”十分不同。這些現象也充分反映于當前的法律制度。[29]不過,這一認識缺乏經驗數據的佐證。
筆者認為,當代單個婚姻單位形成的個體家庭將成為主流。分爨各居的親子之間仍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形成網絡家庭。由于人口控制政策的實行,獨生子女家庭、單性別子女家庭逐漸普遍,親代與獨生子或獨生女相互之間保持經濟和情感交往的愿望都很強烈。這成為雙系網絡家庭發展的人口條件。現代法律制度為雙系網絡家庭的產生創造了制度環境。對雙系網絡家庭的認可,已婚女兒與娘家關系的加強,有助于降低生育中的性別偏好。[30]因而在對個體家庭單位研究的同時,有必要增強對親子各自獨立生活家庭之間關系的研究。
可以說,這一時期的家庭結構研究者多致力于定量分析或實證研究,而有深度的理論探討則比較缺乏。當家庭結構的實證研究或定量分析進行到一定程度時,就需要有具有總體把握和系統認識的理論分析成果產生。但要進行理論分析,則需要對更長時段的中國家庭結構及其變動進行考察或有這方面的知識積累。這卻是目前多數研究者所缺乏的。
總之,20世紀80年代以來,特別是90年代后,當代中國家庭結構研究受到研究者的持續關注和探討,主要是在社會變革之下,一系列制度變遷發生,人口結構改變,家庭結構出現新的重要變化等原因促使和推動的。這些研究使家庭結構的實證分析得到了加強,理論研究也有改進。同時,也應看到,多數研究缺少城鄉比較視角,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的城鄉“二元”特征很突出,并在家庭結構上表現出來。此外,對家庭結構變動影響因素的分析也顯得薄弱。
四、結語和討論
民國時期,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前后,家庭研究有一個高潮,家庭相關調查的展開是前提,這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們對本時期家庭結構狀態和特征的認識。但當時的調查數據對家庭類型結構的反映尚有局限性,表現在家庭的分類不細。研究者多以家庭人口規模來推斷當時家庭的簡單與復雜。一些判斷在當時就有相互矛盾之處。
1949年后至改革開放前的家庭結構研究基本處于停滯狀態,可供開發的微觀家庭數據最為缺乏。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研究者雖試圖通過回顧性調查加以彌補,或挖掘檔案資料尋找微觀家庭信息。但樣本或選擇的調查地區有限,難以反映該時期家庭結構的整體面貌。
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家庭結構研究受到社會學、人口學等領域學者的重視。1982年、1990年、2000年人口普查抽樣數據庫中的微觀家庭信息為研究者整體認識家庭結構提供了方便,全國和城鄉的家庭結構狀態和變動脈絡比較清晰地呈現出來。學者們還從制度變遷、人口結構、人口流動等方面分析了家庭結構的影響因素。
不過,也應看到,基于人口普查數據的家庭結構分析也有不足。在中國城鄉,特別是農村,目前高齡老年人往往有多個子女,他們有一定比例由子女“輪養”,人口普查數據對此反映不出來。另外,隨著男女交往觀念、婚姻觀念發生變化,未婚同居增多,城市尤其如此。雖然年輕人在其中占多數,但離婚、喪偶中老年人中同居者也在增加。而人口普查登記時戶主與無親緣關系者往往被視為“其他”成員(沒有同居關系或伴侶選項),若僅有二人生活,該家庭戶也往往會被歸入“其他”類型。還應指出的是,當代少子、獨子夫婦大幅度提高,與多子女夫婦相比,少子、獨子長大婚配后若與父母同地居住但分爨生活,親子兩代人所形成的生活單位之間的界限則較多子女家庭模糊,出現“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格局。若單純以家庭戶為單位分析,則難以揭示親子家庭戶之間的密切關系。這都有待今后加大對與家庭結構有關的專項調查數據的開發,從多個角度揭示當代家庭結構變動的特征。
將三個時期的家庭結構研究結合起來考察,將有助于推動中國家庭結構理論和方法水平的提高。這方面可謂任重道遠,有賴研究者發掘更多的數據資料作為支撐,特別是需要加強對民國時期、1949年后至改革開放前這兩個時期第一手家庭結構資料的搜集。只有這樣,才能對不同階段、城鄉和區域家庭結構狀態和特征有所把握,進而提煉出理論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