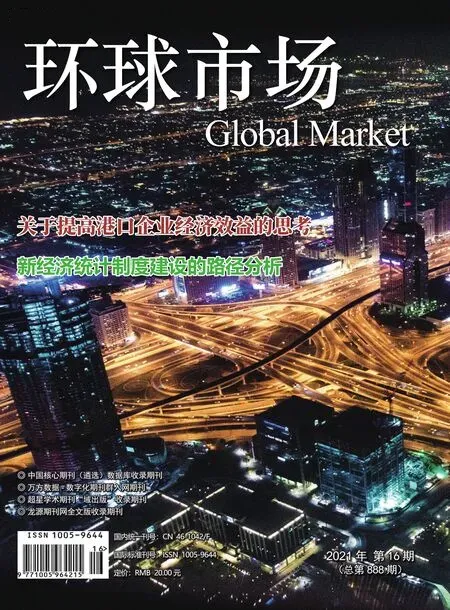非對稱管制定義文獻綜述
羅園 華北電力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非對稱規制并非一種全新的規制手段,首次使用這一概念是指FCC在電信市場上對AT&T實施比競爭對手更為嚴厲的規制。關于非對稱管制的專門研究較少,主要在兩方面展開:一是在政府管制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中,針對需求依據、經濟效益進行研究,以國外研究為主;另一方面,國內學者從電信行業的實際案例入手,對其舉措和影響進行分析并提出建議。
總體來看,關于非對稱管制的定義未有統一的定義,主要在強調新企業進入、在位企業不同競爭權格局和適用對象三方面的觀點存在分歧,本文通過觀點文獻梳理,對非對稱管制的定義作出思考。
一、非對稱管制對新企業的進入扶持
關于非對稱管制的定義,研究中達成了一定的共識:即認為其是微觀規制的經濟性管制內容、存在非對稱競爭的前提條件、措施直接表現為限制優勢市場主體進行而扶持弱勢市場主體。
第一種觀點認為,非對稱管制包含新企業進入扶持研究中,進入分為兩種,一種是新企業或資本進入現有市場或某個業務的規制,一種是已有企業對于現在市場中經營業務的進入規制[1],前者比如國家直接組建中國聯通,進入電信業市場,同時規定基礎電信市場限制民營資本和外資進入,后者對運營商的電信業務范圍中進行限制:中國電信沒有移動業務經營權、中國移動沒有固定業務經營權、只有后進入的中國聯通經營業務較為全面。后者多被認為是第二種觀點,即對市場中已有企業的管制措施,前者國有經營和限制民營和外資進入,都具有非對稱的特征。此外,其他市場主體的進入也會受到市場中已有的非對稱規制的影響,從制度變遷角度看,制度選擇需要比較的是非對稱管制制度造成的生產效率損失和進入速度提高帶來的配置效率的收益[2],有學者以中國鐵路運輸業的規制歷史為例,指出實施非對稱規制并不一定能夠引發廣泛的進入[3];殷繼國認為,在自然壟斷行業由壟斷向競爭轉型的初期,需要實行不對稱規制以扶持新的經營者進入市場。[4]
二、對不同競爭格局下在位企業的非對稱管制
第二種觀點認為,非對稱管制是對市場中處于不同競爭力格局下的現有企業進行的管制,即對不同企業實施不同的規制措施,由于多數學者是以電信業管制案例為研究材料,這一觀點得到多數學者認同。這一觀點認為非對稱管制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對主導運營商和非主導運營商實施不同程度對管制,如學者杜宏偉認為非對稱管制是指在通信市場發展過程中,政府直接介入市場競爭,通過對主導運營商和市場后進入者采取不同的管制規則,借以限制主導運營商對市場的控制力量,創造一個有利于電信市場后進入者的競爭環境的管制規則[5]。另一種是對主導運營商實施管制,對非主導運營商放松管制或不作限制,或者對非主導運營商給予政策上的優惠,而主導運營商不享有。如譚淑貞認為,非對稱管制是管制部門以資費、網間互連為中心,對支配地位的經營者實施的一種管制方式,是在一定時期內,人為地制約處于支配地位的通信經營者對市場的控制力,而放寬對新通信經營者或處于非支配地位的通信經營者的管制,即強調非對稱管制的對象是主導運營商。[6]這兩種形式本質上是一致的,均強調對在位企業管制的非對稱性。
三、非對稱管制的對象范圍
在關于非對稱管制的對象范圍方面,主要認為在電信業、電氣網絡等自然壟斷產業。適用對象是電信行業的觀點認為,顯著經濟規模效應和基礎網絡特點產業特點使得電信領域中強勢競爭者容易擁有規模經濟和網絡覆蓋優勢,利用各種顯隱性技術手段在市場上排擠弱勢競爭者,而同時由于執行反壟斷費時費力,法律程序冗長,電信管制機構普遍利用非對稱管制作為改善電信產業競爭的內在缺陷的管制工具[7];植草益認為,非對稱管制往往是在電氣通信這類垂直型、多邊型聯合企業所在的產業中,新加入企業是僅僅加入特定業務領域的獨立企業;殷繼國將范圍擴大至自然壟斷產業,認為目前我國關于不對稱規制的法律實踐主要局限于電信業,而鐵路、電力、自來水、石油等自然壟斷行業不對稱規制的需求缺乏,當其他自然壟斷行業進行市場化改革之時也需要規制機構采取不對稱規制措施來扶持和保護新的競爭者。[8]
也有學者認為,非對稱管制在部分競爭性行業中也存在,認為非對稱管制是基于競爭主體市場份額、市場影響力的非對稱,而在一定階段、一定時期采取扶持弱勢競爭主體、抑制強勢競爭主體的區別對待的管制政策和措施[9],未對非對稱管制的對象作出行業范圍上的限制,這一定義是針對管制措施作出的,在范圍上較為全面。總體來看,目前研究中非對稱管制范圍主要限制于自然壟斷產業中,主要為經濟性管制,在競爭性產業及社會性管制中的研究幾乎沒有。
四、結語
從文獻來看,非對稱管制最先提出時指的是電信業的規制舉措,在后面的研究中便援引了這一概念,而未對其做內涵和外延以及與相近概念區別的專門分析。是否涉及進入管制,對非對稱管制定義而言十分重要,就非對稱管制運用對象而言,隨著市場化的發展,非對稱管制的適用對象將會不斷增加,判定依據應是所執行的措施,而不應在定義上做具體適用的行業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