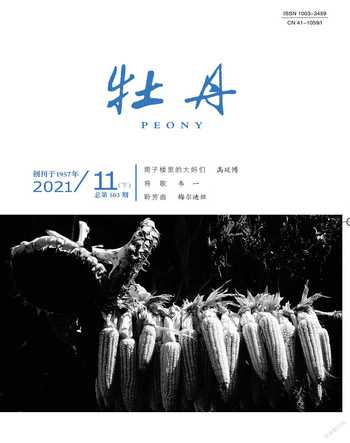淺析朗誦藝術與其他藝術的融合與發展
在融媒體時代,朗誦藝術出現了許多創新的表現形式。朗誦與其他藝術形態本身就有許多交融的地方,近年來,許多朗誦表演藝術家開始探尋新的朗誦表現形式,比如在朗誦中加入戲劇、戲曲、音樂、武術、舞蹈等藝術表現形式,但不免被質疑這些藝術表現形式的加入是否混淆了“朗誦藝術的邊界”。其實這些展現形式只要把握好尺度,都可以作為朗誦的輔助手段。與其他藝術的表現形式只要結合得體,讓其來輔助有聲語言的表達是值得鼓勵和發展的,但不能喧賓奪主。創新是藝術發展的源泉,朗誦藝術也一定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
一、朗誦藝術的定義與發展
關于朗誦的定義,目前學界都沿用了《辭典》中給出的定義,即用清晰、響亮的聲音,結合各種語言手段來完善地表達作品思想感情的一種語言藝術。朗誦的歷史極其悠久,先秦古代著作《尚書·舜典》中就有關于“誦”的記載。但朗誦成為一種藝術表現方式還是要等到近代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白話新詩的出現,這時朗誦才逐漸成熟成為一種藝術形態。許多文藝工作者走上舞臺,朗誦自己的作品或者別人的作品,去發動群眾,喚醒人民。朗誦作為一種傳播手段開始在公共空間出現,伴隨著的是一種文化運動的開展。
隨著時代的發展,朗誦藝術也有著許多新的發展與變化。從傳播方式來看,傳播介質變得多樣化,從各大文藝活動的朗誦到校園朗誦,再到各種小團體的文藝沙龍式的朗誦,從廣播朗誦到電視朗誦,再到融媒體時代“兩微一端”(微博、微信及新聞客戶端)和各種有聲平臺的興起,朗誦藝術的傳播手段豐富多樣。從傳播主體來看,人人都可以成為朗誦藝術的傳播者,朗誦藝術飛入了尋常百姓家。從朗誦的形式來看,由于技術手段的豐富和大量文藝工作者的探索,多種朗誦藝術的形式與形態相繼出現,并為大量朗誦愛好者所喜愛。比如朗誦藝術與表演元素的結合的“演誦”形式,還有朗誦元素與音樂元素的融合,還出現了許多樂團為朗誦藝術家現場伴奏的形式,讓聽眾體驗美文、美聲、美樂的多重邂逅。
二、朗誦藝術的融合發展形式
(一)朗誦+戲劇表演
近年來,一些優秀的朗誦藝術家和表演藝術家不斷探索與嘗試,將許多戲劇表演元素融合到了朗誦當中,創作出了許多優秀的朗誦作品。例如演員出身的濮存昕、吳京安還有配音演員出身的徐濤等,他們的朗誦風格有著明顯的表演元素,有部分學者也將其稱為“表演式朗誦”,以區別于“播音式朗誦”。而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的朗誦藝術家、表演藝術家胡樂民,更是將朗誦藝術和話劇表演藝術相結合之后,開創了“演誦”藝術。這一形式與傳統朗誦的不同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一方面,體現在戲劇化場景的營造上。“演誦”通過大量的舞臺元素來營造身臨其境的感覺,比如舞臺妝容的添加,特定的服裝,外加燈光等多種舞臺元素的綜合運用,使朗誦者更加貼合情景與角色,也給觀眾帶來一種身臨其境之感。比如在胡樂民、徐濤、陳鐸共同演繹的作品《月下徘徊》中,徐濤是古代文人裝束,帶著特定的妝容朗誦蘇東坡的詩歌《明月幾時有》,而胡樂民身著燕尾服,朗誦著普希金的《月亮》,化妝造型上胡樂民也留起了連鬢胡,這也更符合角色的定位。隨后出場的陳鐸也身著燕尾服,在角色造型上也更貼近歌德。他們的精彩演繹讓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詩人對月亮的情感,通過朗誦的舞臺匯集在了同一時空。這樣的創作方式也與傳統只看重聲音塑造的朗誦藝術不同,使朗誦者的人物形象戲劇化,豐富了其表現藝術的形式。
另一方面,體現在戲劇化的展現技法上。“演誦”在舞臺表現上呈現出情景化的演繹和夸張的肢體動作。在胡樂民的朗誦作品《將進酒》中,除了身著一襲白衣,很隨意自然地半躺在舞臺上,還通過道具酒葫蘆和酒葫蘆里面的酒,時而拿起酒杯時而眼神迷離,通過情景的演繹,塑造了李白醉酒的形象。在胡樂民的朗誦作品《滿江紅》中,更是有夸張的肢體動作,通過雙膝跪地和雙手背在身后來呈現出岳飛在回京復命地圖途中被捆綁和掙扎的情景。
在朗誦文本的處理演繹上,“演誦”也有著多種展現方式。
第一是聲音形態上的大開大合,讓朗誦的感染力更強,這在胡樂民和徐濤的朗誦中體現得尤為突出。例如在徐濤的朗誦作品《兵車行》中,在讀到“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云霄”時,徐濤通過高低強弱的節奏變化,將“干云霄”的聲音提高拖長到了極致,不僅體現了聲音的張力,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力,也將凄慘的哭聲直沖九天云霄這種情景完美地演繹了出來。
第二是一些嘆息、啜泣等直接表現情緒的聲音的運用。比如在胡樂民的朗誦作品《繼母的賬本》中,胡樂民以第一人稱的口吻去敘述,在情緒的表達上力求真實,情到深處,聲音也開始顫抖帶有哭腔。繼母在病重后表達自己看不到佳豪時還有自己理解了繼母的良苦用心后,胡樂民將抽泣和哭喊的聲音融入進去,讓聽眾沉浸在這種悲傷的情緒之中,完全是將自己融入進了角色之中。在胡樂民朗誦作品《兵車行》中,在“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這一句的處理上,胡樂民重復了兩遍,最后一遍的結尾加入哭腔,聲音拖長,配合著笙簫的音樂,呈現了將連年征戰帶給百姓的疾苦、在陰天冷雨凄慘哀叫聲不斷的場景,讓人耳目一新。
第三是演唱元素的運用。比如胡樂民朗誦于右任先生的《望鄉詞》時,在前面加入了演唱的元素,由于《望鄉詞》本就有歌曲演唱的作品,在此處先創造性地演唱歌曲,配合胡樂民的精彩演繹,更增添了幾分悲情的色彩。此外,演員郭達用陜西方言朗誦了作品《將進酒》,當讀到“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時,他完全是用說話的方式,生活化、口語化的表達。讀到“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傾耳聽”后,用秦腔的方式來演繹“鐘鼓饌玉不足貴,但愿長醉不復醒。古來圣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縱情的演繹,不僅符合“歌一曲”的情境,更是將李白醉酒后恣意縱情的姿態展現得淋漓盡致。在詩歌的朗誦中加入“演唱”的情況越來越多見,在胡樂民的朗誦作品《定風波》中,最后一句“也無風雨也無晴”胡樂民用瀟灑自然的語氣吟唱出來,使得整個作品更加生動形象,也體現了蘇東坡那種無拘無束、怡然自得的心境。
(二)朗誦藝術+音樂
朗誦加配樂是朗誦藝術常見的表達方式,目前,許多朗誦藝術家都在探索新的表現方式,朗誦藝術家徐濤與琵琶演奏家方錦龍、青年舞蹈家肖富春一起表演了“詩樂舞”《將進酒》,濮存昕、張國立、郭達、關棟天等知名藝術家共同領銜的長安唐詩交響吟誦音樂會,用朗誦+交響樂+合唱+京劇韻白等多種藝術方式就為觀眾呈現了一場朗誦+音樂的視聽盛宴。其中,濮存昕朗誦的《琵琶行》、郭達朗誦的《將進酒》、張國立朗誦的《長恨歌》,都在網絡上獲得了不少好評,取得了非常好的傳播效果。交響樂團和朗誦者的配合最大的好處是靈活,他們的相互配合和碰撞可以使作品展現出不一樣火花。
首先,實現場景轉換的無縫銜接。在《琵琶行》的朗誦中,濮存昕不急于開口,先是一陣蕭瑟的長笛發出的凄涼樂聲,將觀眾迅速地帶入情境之中,隨著一句“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畫面感撲面而來。交響樂團現場指揮,配合朗誦者展現出一幕幕的不同的情景。在“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后,聲音稍做停頓,樂曲聲也漸弱。此時豎琴的聲音響起,伴隨著“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又將當時的場景轉換得恰到好處。
其次,現場的交響樂團的演奏使得音樂在情緒的展現上有著獨到的烘托作用。在全篇的高潮處“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交響樂團的演奏激昂交錯,華麗而又震撼。而到“間關鶯語花底滑”這一段時,整體轉換到深沉低婉,到“此時無聲勝有聲”時僅用豎琴來點綴并陷入沉寂。到“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時,配合著濮存昕高亢的語調,交響樂更是趨向急促。“曲終收撥當心畫,四弦一聲如裂帛”,朗誦與伴奏再次戛然而止。這一段交響樂與朗誦者的聲音配合得恰到好處,體現出的藝術表現力更是極具張力。交響樂團的現場演奏配合著朗誦者,仿佛再現了《琵琶行》中的這一場景,可謂引人入勝。
再次,交響樂團的現場演奏可以對朗誦者的情緒起到補充延續的作用。在郭達朗誦時《將進酒》時,郭達演繹結束之后,現場突然響起的合唱加交響樂團的演奏將整體的情緒推上了高潮,完美呈現了李白的豪放與醉酒之后的縱情。朗誦、交響樂、合唱三種藝術手段在這場詩會中交相輝映,增強了視聽的效果,使得朗誦藝術不再局限于有聲語言,而是在多重融合藝術空間里創造出無限的獨特的意蘊。
三、結語
朗誦作為一種藝術,具有一定的門檻,需要一定的發聲基礎、一定的文學素養、藝術感受力、創造力。也許老一輩的朗誦藝術表現方式已經不適合現在的傳播環境,朗誦藝術的創新是朗誦不斷向前發展的動力。也許有人擔心和憂慮,“朗誦藝術”在與其他藝術融合發展之后是否邊界會變得模糊。如果太熱衷于表演,“朗誦”和“臺詞”、“朗誦”和“小品”有何區別呢?如果帶入太多音樂元素,“朗誦”會不會逐漸演變成“音樂劇”?在筆者看來,朗誦藝術完全不必擔心“越界”。現在需要把握的不是藝術之間的融合,而是一個度,那就是分寸。朗誦藝術其實是完全可以融合、容納更多的藝術形式的,但是最重要的應該是有分寸。不能失去朗誦的本真——用有聲語言傳遞情感,傳遞真善美。在現今的傳播環境之下,朗誦藝術應當鼓勵吸納更多的藝術形式,不能夠故步自封,但是要把握一個度。這個度亟待廣大文藝工作者去反復實踐、推敲。
(武漢傳媒學院)
作者簡介:史泰然(1996-),男,湖北武漢人,碩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為普通話水平測試及語言發聲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