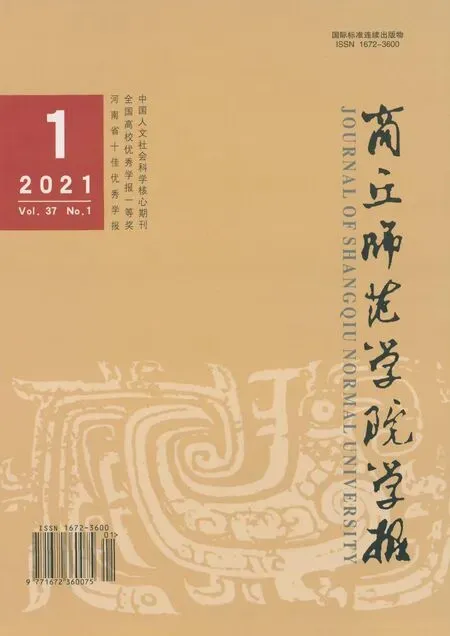中國共產黨勞動教育思想對傳統勞動教育思想的超越
周 海 濤
(中共河南省委黨校 科技文化教研部,河南 鄭州 450018)
一
中國古代官方教育以儒家思想為主要內容,而儒家又以“成圣成賢”作為教育的最高旨歸。從孔子批評樊遲“小人哉”的論述到孟子提出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從“六經”到“十三經”,儒學教育始終圍繞著由道德文章通向成圣成賢而展開,生產勞動一向不被重視,甚至為士大夫階層所不齒。儒學教育的這一導向和機制具有“雙刃劍”的影響:一方面為封建社會輸送了大量讀書明理、道德高尚的士大夫,另一方面也產生了不少“空談心性”“百無一用”的清談書生。
與儒家不同的是,墨家和農家對勞動教育較為重視。墨子理想中的“兼士”除了要具備儒家“君子”般的品行外,還要在生產勞動上有一技之長。墨子教育弟子,“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故圣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為民食”,提倡人們靠勞動為生存打拼。墨子還提出,勞動要遵循科學方法、借助科學手段。和墨家相似,農家學派許行、陳相不僅主張“賢者與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在現實中也堅持“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在歷史上,由于墨家和農家始終未能成為主流意識形態,故其大多數主張未能獲得官方的認可,只能隱于民間。
在中國古代官方教育中,盡管缺乏勞動教育思想的系統性表述,但在經驗和實踐層面,一些有識之士和士大夫,始終把重視勞動、推崇勞動、倡導勞動作為家風的重要內容。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告誡家人 :“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塒圈之所生。爰及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殖之物也。至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1]43顏之推生活于易代之際,飄零的仕宦和亂離的人生經歷,使其對“學而優則仕”產生了幻滅感,故其勸誡子侄要從事勞動,以治生為本。然而,對于大多數士大夫而言,依然把讀書出仕、成圣成賢奉為教育圭臬。尤其是到了北宋,以程頤、朱熹為代表的理學派基本形成了以“成圣”為核心的教育體系。在內容上,核心是以“四書”為代表的儒家精義;在方法上,確立了“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和“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邏輯架構;在態度上,理學家強調立志、主敬、克己、循序漸進、熟讀深思等。科舉架起了讀書與“成圣”之間的橋梁,“學而優則仕”更是成了社會共識和士子們競相追逐的人生目標,從汪洙《神童詩》中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便可見一斑。
但任何時代都不乏冷靜的審視者。兩宋“文治”過于繁盛的背后,則是“武功”的衰微和外交的日漸被動。于是一些學者開始反思儒學教育脫離實踐、脫離生產的種種弊端,如葉夢得在《治生家訓要略》開篇就講到:
人之為人,生而已矣。人不治生,是苦其生也,是拂其生也,何以生為?自古圣賢,以禹治水,稷之播種,皋之明刑,無非以治民之生也。民之生急欲治之,豈己之生而不欲治乎?若曰圣賢不治生,而惟以治民之生,是從井可以救人,而摩頂放踵,利天下亦為之矣,非圣賢之概也。[2]
葉夢得認為,自古以來,圣人首先應該能夠從事生產,而不僅僅是教人生產。不僅如此,他還指出,治生之術和儒家的倫理道德有相通之處 :“蓋嘗論古之人,詩書禮樂與凡義理養心之類,得以為圣為賢,實治生之最善者也。”[2]這種思想,在宋代“重文輕武”的整體氛圍中,既具有一些離經叛道的意味,也閃爍著時代的光芒。
明代是中國儒學發展史的另一座高峰,故宋明理學常常連稱,主要原因在于,兩朝都有著穩定且發達的文官制度。然而,兩朝的歷史命運也驚人的相似:都創造了中國儒學的新高峰,卻都被文明程度相對較低的少數民族政權征服。對于宋元易代,如果說廣大的漢族士大夫還把其歸結于歷史的偶然性以自我安慰,那么對于明清易代,則讓漢族士大夫不得不深思一個問題:以義理思辨著稱的宋明儒學,緣何對于治國安邦顯得空疏無用?終日以道德文章、士人君子自居的士大夫,緣何在國家危難之際不堪重用?清初三大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對此反思甚多。顧炎武就沉痛地指出:

在顧炎武看來,正是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替了“修己治人之實學”,才導致“神州蕩覆,宗社丘墟”的悲劇,這種反思宋明理學空疏之弊的理論自覺,成了清初思想家的主導思想。此外,在明清易代的大潮中,一些底層知識分子或為躲避戰禍,或出于遺民情結,在清入關之后紛紛選擇隱居或閉門授書。在此過程中,或為生計所迫,或出于對明代學術流弊的反思,他們在作品中紛紛表達了對生產勞動的敬畏。如張履祥在《訓子語》中寫道:
人須有恒業。無恒業之人,始于喪其本心,終至喪其身。然擇術不可不慎,除耕讀二事,無一可為者。商賈近利,易壞心術;工技役于人,近賤;醫卜之類,又下工商一等;下此益賤,更無可言者矣。然耕與讀又不可偏廢。讀而廢耕,饑寒交至;耕而廢讀,禮義遂亡。又不可虛有其名而無其實,耕焉而田疇就蕪,讀焉而詩書義塞,故家子弟坐此通病,以至喪亡隨之。古人耕必曰力耕,學必曰力學。[4]1352
張履祥對耕與讀的認識是相對辯證和理性的,他甚至把耕讀和移風俗、正禮義聯系在一起 :“夫能稼穡則可無求于人,可無求于人則能立廉恥。知稼穡之艱則不妄求于人,不妄求于人則能興禮讓。廉恥立,禮讓興,而人心可正,世道可隆矣。”[4]994
顏元特別強調勞動對于修身的重要性,乃至明確提出了“勞動”一詞 :“君子之處世也,甘惡衣粗食,甘艱苦勞動,斯可以無失已矣。”[5]750而他本人即“用力農事,不遑食寢”,“耕田灌園,勞苦淬礪”,弟子李塨亦“以力田不足以養親,兼識醫賣藥”。
顏元認為朱熹等人“舍生盡死,盡在思、讀、講、著四字上做功夫”,結果就是“千百年來率天下入故紙堆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5]250-251他要求學生必須學習農學、錢谷、水利等知識 :“凡為吾徒者,當立志學禮、樂、射、御、書、數及兵、農、錢、谷、水、火、工、虞。”[5]743顏元關于勞動教育的認識和實踐,在當時產生了重要影響。
曾國藩同樣把勞動教育作為家風家訓的重要內容。縱觀中國古代家風的發展史,曾國藩最大的貢獻在于,他能以通達超脫的眼界看待“學而優則仕”的教育觀。盡管他個人的成功靠的也是這樣一條傳統之路,但在他看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子孫讀書不一定非要出仕 :“凡人多望子孫為大官,余不愿為大官,但愿為讀書明理之君子……凡富貴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學作圣賢,全由自己作主,不與天命相干涉。”(《諭紀鴻》)在曾國藩看來,無論選擇以什么為生,勞動都是必備的生存技能,所以,他要求孩子一定要親手種菜喂豬,女子則要端茶、耕種、做衣服鞋帽等。他甚至還親自對孩子們的勞動成果進行驗收,“新婦初來,宜教之入廚作羹,勤于紡織,不因其為富貴子女,不事操作……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雙寄余,各表孝敬之忱”(《諭紀澤》)。這種開闊的教育視野,慎始慎終的言傳身教,時至今日仍十分具有教育意義。
對勞動教育的強調,在古代的社會教育尤其是私學和書院教育層面,也始終以分散、個體、小眾的形式存在。如明代吳與弼認為,勞動能夠提升道德,他自己則“居鄉躬耕食力,弟子從游者甚眾……雨中被蓑笠,負耒耜,與諸生并耕,談乾坤及坎離艮震兌巽于所耕之耒耜可見。歸則解犁,飯糲蔬豆共食。陳白沙自廣來學。晨光才辨,先生手自簸谷,白沙未起,先生大聲曰 :‘秀才,若為懶惰,即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又何從到孟子門下?’”[6]1在吳與弼看來,勤于勞動有助于參悟田間地頭之“道”,體認并臻于圣人境界。元代的鄭玉則把勞動教育作為改造社會的手段,他在《耕讀堂記》中寫道:
夫古之時,一夫受田百畝,無不耕之士,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無不學之人。秦廢井田,開阡陌,焚詩書,坑學士,先王之道滅矣。漢興,雖致隆平之治,卒不能以復淳古之風,而士農分矣。于是從事于學者,則不知稼穡之艱難;從事于農者,則不知禮義之所出。后世有能晝耕夜讀以盡人道之常者,人至以為異,而稱之去古道益遠矣。鮑生從余游,粗知好古人之道,故能耕田以養其親,讀書以修其身。使比屋之人皆如鮑生,皆盡耕田之力,皆有讀書之功,則人情自厚,風俗自淳,雖復三代之治不難矣。[7]卷四
鄭玉對周秦漢以來,耕、讀日分而二,以至于“從事于學者,則不知稼穡之艱難;從事于農者,則不知禮義之所出”現象的判斷基本符合歷史事實,也切中了傳統教育中勞動和教育嚴重脫節的弊端。鄭玉生活于元代中后期,這是一個對漢族知識分子而言人生理想集體幻滅的時代。他希望通過提倡“耕讀”而恢復“三代之治”,這在當時顯然是不可能實現的。
二
在西方教育的發展史上,勞動教育思想也源遠流長。但只有馬克思構建了科學的勞動教育思想。馬克思的勞動教育思想可從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認識論等方面來認知。
從唯物史觀的角度來看,馬克思指出,勞動創造了世界、歷史和人本身。一是勞動創造了世界。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 :“在社會主義的人看來,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8]131馬克思認為,正是因為勞動,人們才能和外部世界建立起聯系。換言之,世界并非抽象實體,而是人類勞動的對象和產物。二是勞動創造了歷史。馬克思指出 :“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人們從幾千年前直到今天單是為了維持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從事的歷史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9]158歷史是人類為了生存生活的奮斗史,也是人類通過勞動改寫世界的歷史。據此可以認為,人類通過勞動創造了歷史。三是勞動創造了人本身。馬克思說 :“勞動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而且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我們在某種意義上不得不說:勞動創造了人本身。”[10]988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馬克思認為,勞動教育與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斗爭和革命學說密切相關。馬克思指出,不平等的私有制造成了資本主義社會教育的不平等。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資本主義社會中專業職業技能的發展是以犧牲無產階級體力、智力和自由而獲得的,這就導致了無產階級及兒童沒有發展智力的條件,惡劣的工作環境剝奪了他們自我發展的機會和條件。所以,無產階級要保障自身權益,就必須接受先進的國民教育。要改變無產階級被剝削的處境,就必須廢除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社會。
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馬克思認為,勞動和教育相結合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唯一途徑 :“它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一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1]530“全面發展的人”中的“發展”包含三個層面:一是才能的全面發展。馬克思指出,分工最重要的影響是使勞動喪失了專業性 :“現代社會內部分工的特點,在于它產生了特長和專業,同時也產生職業的癡呆……自動工廠分工的特點,是勞動在這里已完全喪失專業的性質。”[12]629-630二是自由個性的發展。馬克思指出 :“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將它置于他們的共同的控制之下……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進行這種物質交換。”[13]926可見,只有人們共同控制勞動生產全過程,才能實現自由個性的發展。只有到了社會主義社會,才有望真正實現這一目標。三是個人價值的全部實現。馬克思稱這種狀態為“自由人聯合體”,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此有所展望 :“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范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12]537在馬克思看來,只有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人的全面發展才能實現,通過勞動獲取人的全部價值才能真正實現。
三
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在繼承馬克思勞動教育思想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形成了具有民族性、時代性、實踐性和人民性的中國共產黨勞動教育思想。
從歷史發展來看,中國共產黨勞動教育思想大致經歷了三個歷史性階段。
第一階段,毛澤東開創了中國共產黨勞動教育思想。作為黨的第一代領導核心,毛澤東勞動教育思想最大的特點和貢獻在于,確立了勞動必須和教育緊密結合的社會主義教育方針以及結合中國具體國情探索勞動與教育相結合的基本原則,為當代勞動教育思想奠定了深厚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基礎。在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提出蘇維埃教育總方針必須堅持勞動和教育相結合的方針。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提出民眾教育要服務于抗日戰爭的需要,民眾教育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為了打破敵人的封鎖,毛澤東要求解放區學校開展大生產運動:一方面實現了解放區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另一方面,引導知識分子走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在勞動中實現了經濟目的、政治目的、教育目的三者的有機統一,也是馬克思關于勞動和教育相結合“既是提高社會生產的一種方法”“也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的中國化運用。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勞動教育思想內容更加豐富、體系更加宏大。在繼承馬克思勞動教育思想、揚棄傳統勞動教育思想、結合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國情的基礎上,毛澤東勞動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一是教育和勞動相結合才能擺脫貧困、勤儉立國,二是教育和勞動相結合才能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三是教育和勞動相結合是一個雙向互動的辯證過程,四是勞動和教育相結合才能實現理論和實踐的有機統一。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崇尚勞動、歌頌勞動、反對不勞而獲的勞動教育思想,成為當時的時代主旋律。
第二階段,鄧小平發展了中國共產黨勞動教育思想。作為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充分繼承發揚毛澤東思想,重視勞動與教育相結合的同時又有所突破和超越:一是提出勞動教育不僅是改造人靈魂和思想的手段,而且是實現自我價值、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徑;二是提出勞動教育必須服務于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大局,大大豐富和延展了勞動主體、勞動分工、勞動性質和勞動對象的范圍和內涵。江澤民和胡錦濤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和豐富了中國共產黨勞動教育思想。
第三階段,習近平形成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勞動教育思想。新時代勞動教育思想,是在對傳統勞動教育思想批判揚棄、對馬克思勞動教育思想創新發展、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勞動教育思想總結升華的基礎之上,結合新時代中國的具體實際而形成的新時代勞動教育思想。新時代勞動教育思想主要包括:從勞動教育的目的來看,其最高旨歸是實現“中國夢”。對此,習近平有一段精彩的論述 :“中國夢是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生活在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時代的中國人民,共同享受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受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有夢想,有機會,有奮斗,一切美好的東西都能夠創造出來。”[14]40習近平多次強調“社會主義是干出來的”“要幸福就要奮斗”“實干興邦、空談誤國”等。從勞動教育的主體來看,始終堅持人民首創地位。黨的十八大以來,每年“五一”國際勞動節,習近平都會接見各個領域的勞動者,表彰其勞模精神,強調勞動對個人、對社會、對國家的重大意義,強調要將勞模視作真正的時代楷模和人生榜樣。從勞動教育的原則來看,堅持體力與腦力相結合、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勞動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相結合。習近平明確提出,要建設“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大軍”[15]31。習近平在2018年全國教育大會上強調 :“要在學生中弘揚勞動精神,教育引導學生崇尚勞動、尊重勞動,懂得勞動最光榮、勞動最崇高、勞動最偉大、勞動最美麗的道理,長大后能夠辛勤勞動、誠實勞動、創造性勞動。”[16]從制度保障來看,關于勞動教育的制度建設趨于規范化、常態化、法治化。2020年3月20日出臺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新時代大中小學勞動教育的意見》中明確提出 :“整體優化學校課程設置,將勞動教育納入中小學國家課程方案和職業院校、普通高等學校人才培養方案,形成具有綜合性、實踐性、開放性、針對性的勞動教育課程體系。”
從現實情況來看,當前我國的勞動教育思想和國家發展、學生健康成長還不匹配。從國家發展來看,當前世界范圍內逆全球化和經濟保護主義抬頭,我國要想順利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就必須在制造業等領域徹底解決核心技術“卡脖子”的問題。而要想成為制造強國,就必須有一大批富有創造精神和實干精神的勞動大軍。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一些年輕人受個人主義、消費主義、拜金主義等影響,幻想瞬間暴富、一夜成名。這些現象的存在有許多主客觀的原因,但對青少年勞動教育的缺失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從人的個人成長來看,一個四體不勤、不事勞動的人,即使頂著“學霸”“神童”的光環,也無法成長為一個心理健康、人格健全、有益于社會的人。而當前,我國勞動教育缺失現象一個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便是中小學教育中的唯分數、唯成績論。家長怕占用孩子學習時間,不愿讓其從事家務勞動;教師過分追求升學率,呈現重智育輕體育、重理論輕實踐、重腦力輕體力的傾向。其結果是,不少孩子在完成應試教育走向社會后,缺乏必要的生存和生活技能,更有甚者連洗衣做飯這些最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都不具備。這種現象如果不能引起國家、社會、家庭的高度重視,后果不堪設想。
勞動教育能否搞好,事關個人健康成長、國家前途命運。從操作層面來講,為了更好地發揮勞動教育的重要作用,國家、社會、學校需要形成合力。一是要在全社會范圍內大力營造勞動光榮、勞動偉大的氛圍,大力提倡工匠精神和勞模精神,形成精益求精的敬業風氣。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對此發表了許多重要論述、提出了許多具體要求,全社會正在形成崇尚勞動、謳歌勞模的導向和氛圍。二是要切實提高勞動者的待遇。為什么年輕人在擇業的時候,不愿意選擇當一名普通的勞動者,而幻想去當明星、金融家?因為他們看到,一線的普通勞動者往往是低收入群體。習近平在八一中學慰問教師的時候指出,“讓教師成為讓人羨慕的職業”;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讓農民成為體面的職業”。將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貫徹落實好,對當前整個社會的思想導向、學校的教育導向、個人的價值導向都會起到良好的示范引領作用。三是要逐步改革唯分數論的考試體系和標準,大力提升勞動教育在學校教育中的權重。可喜的是,《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新時代大中小學勞動教育的意見》已經出臺 。《意見》中提出不少具體而明確的要求,如“根據各學段特點,在大中小學設立勞動教育必修課程,系統加強勞動教育。中小學勞動教育課每周不少于1課時,學校要對學生每天課外校外勞動時間作出規定。職業院校以實習實訓課為主要載體開展勞動教育,其中勞動精神、勞模精神、工匠精神專題教育不少于16學時。普通高等學校要明確勞動教育主要依托課程,其中本科階段不少于32學時。除勞動教育必修課程外,其他課程結合學科、專業特點,有機融入勞動教育內容。大中小學每學年設立勞動周,可在學年內或寒暑假自主安排,以集體勞動為主。高等學校也可安排勞動月,集中落實各學年勞動周要求”。對于各級學校而言,除了要把《意見》中的要求落細落實以外,還應該建立一套與之相匹配的課程教學和學校管理的評價體系,以保證學生參與勞動教育實踐的深度和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