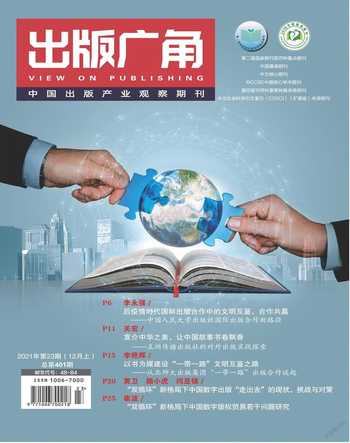“雙循環(huán)”新格局下中國(guó)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若干問題研究
【摘 要】? 在國(guó)際傳播和數(shù)字經(jīng)濟(jì)的雙重驅(qū)動(dòng)下,中國(guó)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發(fā)展迅速。如何在“雙循環(huán)”新格局下,通過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推進(jìn)中國(guó)版權(quán)貿(mào)易高質(zhì)量發(fā)展,實(shí)現(xiàn)中國(guó)由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大國(guó)向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強(qiáng)國(guó)的升級(jí),已經(jīng)成為我國(guó)面臨的一項(xiàng)緊迫課題。
【關(guān)? 鍵? 詞】“雙循環(huán)”;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國(guó)際傳播;數(shù)字經(jīng)濟(jì);高質(zhì)量發(fā)展
【作者單位】崔波,浙江傳媒學(xué)院新聞與傳播學(xué)院。
【基金項(xiàng)目】2021年度國(guó)家社科基金重大項(xiàng)目“‘雙循環(huán)’新格局下中國(guó)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研究”(21&Z
D322)的階段性成果;2018年度國(guó)家社科基金項(xiàng)目“基于文化共識(shí)的中國(guó)版權(quán)輸出供需錯(cuò)位矯正與績(jī)效評(píng)價(jià)研究”(18BXW038)的階段性成果。
【中圖分類號(hào)】F49;F752;G124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23.005
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不僅是一個(gè)國(guó)家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的體現(xiàn),而且是一個(gè)國(guó)家國(guó)際傳播能力和國(guó)際話語權(quán)的重要構(gòu)成維度。研究數(shù)據(jù)顯示,中國(guó)數(shù)字版權(quán)出口能力不斷增強(qiáng),社交媒體國(guó)際化不斷拓展,已發(fā)展成為世界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大國(guó),正在向世界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強(qiáng)國(guó)邁進(jìn)。中國(guó)跨入第二個(gè)一百年之際,遭遇貿(mào)易保護(hù)主義盛行的嚴(yán)酷國(guó)際環(huán)境,加之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加劇全球政治、經(jīng)濟(jì)的不確定性。如何從危機(jī)挑戰(zhàn)中搶抓和創(chuàng)造機(jī)遇,利用新技術(shù)賦能實(shí)現(xiàn)彎道超車,提升中國(guó)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躋身世界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強(qiáng)國(guó),是時(shí)代之問、中國(guó)之問,學(xué)術(shù)界必須通過嚴(yán)謹(jǐn)?shù)目茖W(xué)論證做出正面回應(yīng)。
一、 數(shù)字技術(shù)催生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
與傳統(tǒng)以紙質(zhì)、光盤、磁盤為主要介質(zhì)的版權(quán)貿(mào)易不同,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是由數(shù)字傳輸技術(shù)、區(qū)塊鏈、大數(shù)據(jù)等數(shù)字技術(shù)催生的。目前學(xué)界對(duì)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還未達(dá)成一個(gè)共識(shí)性的定義,并且大多數(shù)從事出版學(xué)研究的學(xué)者將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看作是傳統(tǒng)版權(quán)貿(mào)易的升級(jí)版,認(rèn)為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是一種可限定在以許可或轉(zhuǎn)讓的方式交易數(shù)字化內(nèi)容的貿(mào)易活動(dòng),這種狹隘的對(duì)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的理解嚴(yán)重制約了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研究的拓展。盡管部分學(xué)者已經(jīng)注意到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平臺(tái)在文化“走出去”中的重要價(jià)值,但這些研究尚未將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平臺(tái)上的廣告、讀者打賞、眾籌視作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的新形態(tài)予以重點(diǎn)關(guān)注。此外,還有不少學(xué)者仍然將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圈定在傳統(tǒng)出版產(chǎn)業(yè)的界限之內(nèi)。
盡管目前學(xué)術(shù)研究對(duì)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尚無明確定論,但從可見的一些嘗試性定義來看,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在“版權(quán)貿(mào)易方式的數(shù)字化”和“版權(quán)貿(mào)易對(duì)象的數(shù)字化”兩方面形成學(xué)界共識(shí)。隨著數(shù)字技術(shù)對(duì)版權(quán)貿(mào)易的影響持續(xù)加大,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所觸及的邊界不斷延展,對(duì)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的界定往往根據(jù)現(xiàn)實(shí)需求和具體目的進(jìn)行場(chǎng)景化、包容性的理解和認(rèn)識(shí)。
目前,學(xué)界對(duì)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概念的界定,基本上放在數(shù)字貿(mào)易框架下進(jìn)行,從現(xiàn)有的定義中可以發(fā)現(xiàn),數(shù)字貿(mào)易經(jīng)歷了“狹義階段—擴(kuò)大階段—廣義階段”。比較占主流的定義為世界貿(mào)易組織、經(jīng)濟(jì)合作與發(fā)展組織、國(guó)際貨幣基金組織聯(lián)合下的定義:“數(shù)字貿(mào)易是數(shù)字技術(shù)提供可供性的、由數(shù)字方式或者實(shí)體方式進(jìn)行交付的跨境貨物貿(mào)易和服務(wù)貿(mào)易”。我國(guó)對(duì)數(shù)字貿(mào)易的定義并不統(tǒng)一,但對(duì)數(shù)字貿(mào)易的方式數(shù)字化和對(duì)象數(shù)字化等兩大特征基本上達(dá)成共識(shí)。學(xué)界目前普遍接受的是由美國(guó)國(guó)際貿(mào)易委員會(huì)(USITC)下的定義:“互聯(lián)網(wǎng)以及基于互聯(lián)網(wǎng)的技術(shù)在產(chǎn)品和服務(wù)的訂購(gòu)、生產(chǎn)或交付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國(guó)內(nèi)和國(guó)際貿(mào)易。”此定義包括了互聯(lián)網(wǎng)基礎(chǔ)設(shè)施、通信服務(wù)等諸多行業(yè)。其中,數(shù)字內(nèi)容、搜索和新聞帶有明顯的版權(quán)印記,屬于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的對(duì)象[1]。但是一些國(guó)家和地區(qū)并不認(rèn)同這樣的界定,比如歐洲就將圖文音視頻和計(jì)算機(jī)程序排除在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開放之外[2]。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的概念界定、分類體系與統(tǒng)計(jì)口徑的明確不僅關(guān)系到國(guó)際貿(mào)易規(guī)則體系的話語權(quán),影響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全球價(jià)值鏈的利益分配,更重要的是,以智力密集型、高附加值為主要特征的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已經(jīng)演變?yōu)橹袊?guó)國(guó)際傳播能力提升的核心要素,因此,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的戰(zhàn)略性意義日益凸顯。
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是數(shù)字貿(mào)易中最易引發(fā)屬性爭(zhēng)議的部分,對(duì)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屬性與分類的確定與不同經(jīng)濟(jì)體在國(guó)際貿(mào)易規(guī)則談判中的主張具有密切關(guān)系[3]。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是數(shù)字時(shí)代國(guó)家間競(jìng)爭(zhēng)的主戰(zhàn)場(chǎng),與傳統(tǒng)版權(quán)貿(mào)易相比,其貿(mào)易對(duì)象、貿(mào)易環(huán)境、貿(mào)易范圍都具有全新特征,表現(xiàn)為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渠道和范圍大幅拓寬,線上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tái)成為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的基本經(jīng)濟(jì)單元,中小企業(yè)和個(gè)人在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中的參與程度大幅提升等[4]。在數(shù)字貿(mào)易環(huán)境下,傳統(tǒng)版權(quán)框架下為保護(hù)消費(fèi)者而設(shè)計(jì)的對(duì)作品進(jìn)行再銷售、贈(zèng)予的首次銷售原則,在數(shù)字版權(quán)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難以適用,首次銷售原則某些條款不利于數(shù)字版權(quán)的流通和版權(quán)經(jīng)濟(jì)的繁榮[5]。
數(shù)字版權(quán)內(nèi)容的供給與跨境消費(fèi)是并置發(fā)生的,傳統(tǒng)版權(quán)貿(mào)易中對(duì)版權(quán)的地域性和時(shí)間性的限定不再成為主要的限定因素[2]。如果繼續(xù)延續(xù)傳統(tǒng)版權(quán)貿(mào)易的有形產(chǎn)品和無形產(chǎn)品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對(duì)版權(quán)貿(mào)易類型進(jìn)行分類,顯然就失去了保護(hù)作用。以CD交付的音樂作品構(gòu)成實(shí)物貿(mào)易,而CD播出后以數(shù)字形式傳輸又構(gòu)成服務(wù)貿(mào)易。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結(jié)構(gòu)較傳統(tǒng)版權(quán)貿(mào)易結(jié)構(gòu)更為復(fù)雜,作者、生產(chǎn)者、消費(fèi)者以及其他相關(guān)利益人等版權(quán)市場(chǎng)的新興參與者將原來簡(jiǎn)單均衡的市場(chǎng)引向如今日益復(fù)雜的非均衡化方向發(fā)展[6]。在以美國(guó)為主的各類版權(quán)貿(mào)易談判中,數(shù)字產(chǎn)品指稱的是以圖文音視頻為主要形式的數(shù)字化產(chǎn)品[7]。有學(xué)者進(jìn)而指出了數(shù)字化的兩大表征:傳統(tǒng)版權(quán)貿(mào)易升級(jí)為跨境數(shù)字商務(wù),傳統(tǒng)的版權(quán)貿(mào)易內(nèi)容以數(shù)字化方式進(jìn)行傳輸[1],通過網(wǎng)絡(luò)進(jìn)行傳輸和交付的文化內(nèi)容產(chǎn)品被稱為“數(shù)字內(nèi)容產(chǎn)品”或“數(shù)字產(chǎn)品”,數(shù)字貿(mào)易是數(shù)字內(nèi)容產(chǎn)品和信息服務(wù)的跨國(guó)交易[8]。
綜合上述數(shù)字貿(mào)易概念、分類與特征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第一,現(xiàn)有研究從不同視角概述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的內(nèi)涵或外延、特征、發(fā)展趨勢(shì)及其影響,但大多處于初步定性描述階段,對(duì)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的規(guī)范性研究處于萌發(fā)期。第二,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作為數(shù)字時(shí)代一種新型的貿(mào)易模式,是傳統(tǒng)版權(quán)貿(mào)易在數(shù)字經(jīng)濟(jì)時(shí)代的拓展、延伸和迭代,既包括傳統(tǒng)內(nèi)容產(chǎn)品和服務(wù)貿(mào)易的數(shù)字化(貿(mào)易方式的數(shù)字化),也包括數(shù)字內(nèi)容產(chǎn)品和服務(wù)的貿(mào)易(貿(mào)易對(duì)象的數(shù)字化)。第三,數(shù)字技術(shù)推動(dòng)傳統(tǒng)內(nèi)容產(chǎn)業(yè)發(fā)展,使得版權(quán)貿(mào)易呈現(xiàn)數(shù)字化、網(wǎng)絡(luò)化、智能化。因此,針對(duì)現(xiàn)有文獻(xiàn)中存在的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內(nèi)涵與外延尚未明確,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新特征與新模式相關(guān)學(xué)理性研究較少等問題,亟待建立系統(tǒng)性的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基礎(chǔ)理論。
通過與傳統(tǒng)版權(quán)貿(mào)易相比較,我們可以操作化地將“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定義為“以數(shù)據(jù)化交易方式對(duì)具有版權(quán)屬性的數(shù)字化內(nèi)容進(jìn)行交易的活動(dòng)”。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可以分為數(shù)字內(nèi)容、社交媒體、搜索引擎、數(shù)字產(chǎn)品與服務(wù)等四類;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方式由數(shù)字平臺(tái)、數(shù)字交付和數(shù)字訂閱構(gòu)成;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內(nèi)容由數(shù)字產(chǎn)品、數(shù)字服務(wù)、數(shù)字信息構(gòu)成;數(shù)字貿(mào)易主體包括企業(yè)、政府和消費(fèi)者。
二、 作為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坐標(biāo)系的“雙循環(huán)”新格局
在“十四五”之前,中國(guó)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主要是依托國(guó)際經(jīng)濟(jì)大循環(huán)的出口導(dǎo)向型趕超模式。隨著貿(mào)易保護(hù)主義的興起,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全球經(jīng)濟(jì)失速、政策失靈、治理失范,這對(duì)中國(guó)既是挑戰(zhàn)也是彎道超車的機(jī)遇。站在兩個(gè)一百年的交匯點(diǎn),“雙循環(huán)”是適應(yīng)我國(guó)經(jīng)濟(jì)發(fā)展變化的主動(dòng)選擇,有助于厘清對(duì)中國(guó)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雙循環(huán)”新格局的模糊認(rèn)識(shí),提升對(duì)“雙循環(huán)”新格局與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理解。
1.“雙循環(huán)”對(duì)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的影響
“雙循環(huán)”是適應(yīng)我國(guó)經(jīng)濟(jì)發(fā)展變化的主動(dòng)選擇,是應(yīng)對(duì)國(guó)際環(huán)境變化的戰(zhàn)略舉措,也是發(fā)揮我國(guó)超大規(guī)模經(jīng)濟(jì)優(yōu)勢(shì)的內(nèi)在要求[9]。新冠肺炎疫情暴發(fā)與擴(kuò)散以來,全球發(fā)展深層次矛盾日益突出,作為深度融入世界市場(chǎng)和國(guó)際供應(yīng)鏈體系的外向型經(jīng)濟(jì)體,我國(guó)經(jīng)濟(jì)發(fā)展逐步轉(zhuǎn)向以國(guó)內(nèi)大循環(huán)為主體、國(guó)內(nèi)國(guó)際雙循環(huán)相互促進(jìn)的新發(fā)展格局。從全球價(jià)值鏈下國(guó)際分工形態(tài)演變、國(guó)內(nèi)要素稟賦變遷以及外部競(jìng)爭(zhēng)與合作關(guān)系調(diào)整等基礎(chǔ)條件出發(fā),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中內(nèi)循環(huán)與外循環(huán)的地位及其相互關(guān)系發(fā)生顯著變化。過去國(guó)內(nèi)循環(huán)和國(guó)際循環(huán)雙輪驅(qū)動(dòng),特別是外循環(huán)發(fā)揮重要作用的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模式需要革新,轉(zhuǎn)向內(nèi)循環(huán)為主、雙循環(huán)暢通的高質(zhì)量發(fā)展模式,這既是現(xiàn)實(shí)表現(xiàn),也是必然選擇[10]。國(guó)際循環(huán)在一定程度上易受國(guó)際形勢(shì)波動(dòng)影響,而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因同時(shí)具有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新引擎與國(guó)際傳播新動(dòng)能的雙重屬性而具有特殊的戰(zhàn)略價(jià)值,因此需要發(fā)揮國(guó)內(nèi)循環(huán)的積極作用,依賴統(tǒng)一龐大的國(guó)內(nèi)需求市場(chǎng),發(fā)揮我國(guó)的比較優(yōu)勢(shì),協(xié)同推進(jìn)國(guó)內(nèi)大市場(chǎng)和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競(jìng)爭(zhēng)力建設(shè)[11]。曲如曉等人的研究表明,貿(mào)易開放對(duì)文化存在正向效應(yīng),總體而言開放會(huì)促進(jìn)一國(guó)文化的進(jìn)步,但這個(gè)影響效應(yīng)會(huì)隨著國(guó)內(nèi)經(jīng)濟(jì)水平、國(guó)民收入分配等現(xiàn)實(shí)情形而動(dòng)態(tài)變化,這從側(cè)面印證了“雙循環(huán)”發(fā)展格局之于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競(jìng)爭(zhēng)力提升的正當(dāng)性。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是連接國(guó)內(nèi)外雙循環(huán)的重要紐帶,在“雙循環(huán)”新格局下,國(guó)內(nèi)貿(mào)易與對(duì)外貿(mào)易一體化程度進(jìn)一步提升[4]。
2.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對(duì)“雙循環(huán)”的作用
在實(shí)現(xiàn)“雙循環(huán)”新發(fā)展格局的過程中,數(shù)字經(jīng)濟(jì)是重要的支撐力量[12],這是中國(guó)發(fā)展和提升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的前提條件。數(shù)字經(jīng)濟(jì)和數(shù)字貿(mào)易使得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而處于“中斷”狀態(tài)的全球貿(mào)易產(chǎn)業(yè)鏈和供應(yīng)鏈逆勢(shì)發(fā)展[13]。數(shù)字貿(mào)易的興起與發(fā)展不僅會(huì)對(duì)傳統(tǒng)國(guó)際貿(mào)易規(guī)則帶來重大挑戰(zhàn),而且會(huì)重構(gòu)全球價(jià)值鏈,改變?nèi)騼r(jià)值鏈的運(yùn)行模式,顛覆全球價(jià)值鏈的全球分布體系和利益分配格局,進(jìn)而影響一個(gè)國(guó)家或區(qū)域在全球價(jià)值鏈中的位置[14]。2018年以來,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的雁陣轉(zhuǎn)移模式宣告終結(jié),迎來以中國(guó)為樞紐的環(huán)流發(fā)展模式,即以中國(guó)為樞紐的發(fā)達(dá)經(jīng)濟(jì)體價(jià)值環(huán)流和發(fā)展中經(jīng)濟(jì)體價(jià)值環(huán)流共振的“共軛環(huán)流”[15]。中國(guó)應(yīng)致力互利共贏發(fā)展理念,構(gòu)建以中國(guó)國(guó)家價(jià)值鏈(NVC)為樞紐的“一帶一路”三環(huán)流貿(mào)易體系[16],促進(jìn)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動(dòng)力向以提升產(chǎn)業(yè)鏈發(fā)展水平、提高核心技術(shù)供給水平方向轉(zhuǎn)換。在“十三五”期間中國(guó)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所獲得的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優(yōu)勢(shì)基礎(chǔ)上,將新業(yè)態(tài)新模式發(fā)展和企業(yè)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作為文化“走出去”的重點(diǎn)[17],針對(duì)不同的國(guó)家和地區(qū),中國(guó)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的發(fā)力點(diǎn)應(yīng)不同。對(duì)于上環(huán)流的發(fā)達(dá)國(guó)家國(guó)家,重在體現(xiàn)智慧、知識(shí)和創(chuàng)意;對(duì)于處在下環(huán)流的發(fā)展中國(guó)家,重在體現(xiàn)文化引導(dǎo)效益[18]。未來數(shù)字產(chǎn)業(yè)巨大發(fā)展?jié)摿⒊蔀槲覈?guó)與“一帶一路”沿線國(guó)家文化貿(mào)易的重點(diǎn)內(nèi)容[19]。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對(duì)全球價(jià)值鏈的作用顯著,數(shù)字產(chǎn)品嵌入全球價(jià)值鏈,使全球價(jià)值創(chuàng)造越來越知識(shí)密集化,微型跨國(guó)公司成為全球價(jià)值鏈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新動(dòng)力,少數(shù)科技公司和數(shù)字平臺(tái)可能主導(dǎo)全球價(jià)值鏈,進(jìn)一步延伸全球價(jià)值鏈分工的深度和廣度[20]。如以TIK TOK為代表的數(shù)字平臺(tái)在全球交易市場(chǎng)上具備將流量入口轉(zhuǎn)化為金融優(yōu)勢(shì)的能力,更加堅(jiān)強(qiáng)有力地推動(dòng)數(shù)字主權(quán)貨幣的跨境流動(dòng)[21]。
雖然有學(xué)者初步研究“雙循環(huán)”新格局下數(shù)字貿(mào)易發(fā)展的論題,但是尚未探討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與“雙循環(huán)”新格局的相互關(guān)系,尚未深入分析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對(duì)全球價(jià)值鏈重構(gòu)的影響。分析中國(guó)在全球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格局中的定位,并深入剖析“雙循環(huán)”新格局下中國(guó)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的發(fā)展路徑,具有深遠(yuǎn)意義。
三、中國(guó)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
數(shù)字經(jīng)濟(jì)為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的提升帶來了機(jī)遇和挑戰(zhàn),深刻影響著脫胎于傳統(tǒng)實(shí)體貿(mào)易時(shí)代的多邊貿(mào)易協(xié)定,既有的貿(mào)易治理架構(gòu)難以適應(yīng)數(shù)字貿(mào)易的新情境,尤其是數(shù)據(jù)流通壁壘、數(shù)據(jù)風(fēng)險(xiǎn)約束等方面的制度缺席亟待得到正視與關(guān)注。數(shù)字貿(mào)易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提升路徑,不僅關(guān)涉各國(guó)自身利益,而且也是各主權(quán)國(guó)家就網(wǎng)絡(luò)空間主張主權(quán)的重要實(shí)踐領(lǐng)域之一[22],中國(guó)應(yīng)當(dāng)從全球治理體系的參與者、建設(shè)者努力轉(zhuǎn)變成為國(guó)際體系的引領(lǐng)者[23]。與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時(shí)代相比,數(shù)字經(jīng)濟(jì)時(shí)代的全球經(jīng)濟(jì)治理在治理議題、治理主體、治理目的和治理邏輯等方面并無本質(zhì)改變,但在影響因素、國(guó)際格局、側(cè)重領(lǐng)域和治理路徑等方面與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時(shí)代有所不同[24]。數(shù)據(jù)規(guī)制與貿(mào)易規(guī)制是數(shù)字貿(mào)易治理的兩條主要路徑,其中數(shù)據(jù)規(guī)制針對(duì)跨境數(shù)據(jù)流動(dòng),貿(mào)易規(guī)制關(guān)涉貿(mào)易自由化,具有主權(quán)性和互惠性[25]。目前,國(guó)際貿(mào)易規(guī)則體系主要有美式規(guī)則和歐式規(guī)則。美式規(guī)則側(cè)重于貿(mào)易的自由化和數(shù)據(jù)存儲(chǔ)設(shè)備非強(qiáng)制本地化,歐式規(guī)則則將重點(diǎn)放在數(shù)據(jù)自由流動(dòng)、版權(quán)保護(hù)和隱私保護(hù)上[3]。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大國(guó)最近幾年將全球性規(guī)則制定的重心轉(zhuǎn)移到區(qū)域貿(mào)易規(guī)則的談判上,推出了《跨太平洋伙伴關(guān)系協(xié)定》(TPP)、《歐加全面經(jīng)濟(jì)與貿(mào)易協(xié)定》(CETA)、《美國(guó)—墨西哥—加拿大協(xié)定》(USMCA)等協(xié)定。這些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規(guī)則有如下特點(diǎn):針對(duì)數(shù)字內(nèi)容的規(guī)則兼容了貨物和服務(wù)在內(nèi)的開放規(guī)則;試圖打破數(shù)據(jù)流通壁壘;聯(lián)合抵制數(shù)字貿(mào)易風(fēng)險(xiǎn)。中國(guó)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國(guó)內(nèi)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法律法規(guī)不統(tǒng)一且滯后,在進(jìn)行多邊談判中話語權(quán)較弱。
具體到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提升路徑,現(xiàn)有的研究側(cè)重于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規(guī)則制定、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風(fēng)險(xiǎn)監(jiān)管等方面,如周念利和陳寰琦、孫益武等研究具體的國(guó)際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規(guī)則及其對(duì)中國(guó)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的影響;李墨絲進(jìn)一步分析《全面與進(jìn)步跨太平洋伙伴關(guān)系協(xié)定》(CPTPP)數(shù)字貿(mào)易規(guī)則形成機(jī)理,揭示數(shù)字貿(mào)易規(guī)則的整體走向,建議中國(guó)加強(qiáng)數(shù)字貿(mào)易監(jiān)管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推動(dòng)國(guó)內(nèi)改革開放與全球改革同步進(jìn)行[26]。藍(lán)慶新等的研究發(fā)現(xiàn),數(shù)字文化產(chǎn)業(yè)開放度對(duì)數(shù)字文化產(chǎn)品出口的影響顯著,并認(rèn)為數(shù)字文化產(chǎn)業(yè)應(yīng)繼續(xù)加大開放度[27]。在確保經(jīng)濟(jì)安全的同時(shí),中國(guó)應(yīng)當(dāng)放寬對(duì)跨境數(shù)據(jù)流動(dòng)的限制,積極促進(jìn)數(shù)字文化產(chǎn)品“走出去”,參與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同時(shí),著眼于國(guó)家安全、數(shù)據(jù)隱私保護(hù)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平衡,積極推動(dòng)現(xiàn)有跨境數(shù)據(jù)流動(dòng)等立法的完善,通過加入現(xiàn)有區(qū)域性隱私框架等積極措施提升“中國(guó)模式”的國(guó)際影響力[28]。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風(fēng)險(xiǎn)不容忽視,如果一個(gè)國(guó)家缺乏數(shù)字安全,面臨的潛在損失將更為嚴(yán)重[29]。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風(fēng)險(xiǎn)監(jiān)管主要涉及數(shù)據(jù)風(fēng)險(xiǎn)、網(wǎng)絡(luò)安全風(fēng)險(xiǎn)、隱私安全等。針對(duì)數(shù)字貿(mào)易本土化措施、數(shù)據(jù)隱私保護(hù)措施、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措施等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中的突出問題,我國(guó)相應(yīng)的支持性要素供給不足、數(shù)字貿(mào)易規(guī)制發(fā)展相對(duì)滯后[30]。因此,當(dāng)中國(guó)日益走向世界舞臺(tái)中心,需要及時(shí)提出代表國(guó)家意志的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框架,捍衛(wèi)中國(guó)在國(guó)際規(guī)則制定中的話語權(quán)。
盡管現(xiàn)有文獻(xiàn)對(duì)數(shù)字貿(mào)易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提升給予重點(diǎn)關(guān)注,全球主要經(jīng)濟(jì)體都主張對(duì)貿(mào)易規(guī)則進(jìn)行系統(tǒng)研判,但已有研究對(duì)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相關(guān)的治理規(guī)則與體系建構(gòu)仍然相對(duì)有限,并且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的特殊屬性使得其治理規(guī)則體系往往是整個(gè)數(shù)字貿(mào)易治理體系中的例外,需要規(guī)則體系的專項(xiàng)性設(shè)計(jì),這也是學(xué)界研究亟待著重深入補(bǔ)充的焦點(diǎn)。
四、中國(guó)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高質(zhì)量發(fā)展之路
1.中國(guó)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理念和目標(biāo)
中國(guó)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高質(zhì)量發(fā)展理念和目標(biāo),必須從“雙循環(huán)”新格局出發(fā),緊跟數(shù)字經(jīng)濟(jì)浪潮,樹立“有序、包容、開放、高效”的八字理念,確立“市場(chǎng)配置力—產(chǎn)業(yè)支撐力—企業(yè)創(chuàng)新力—國(guó)際傳播力”四力合一的目標(biāo),為“雙循環(huán)”新格局下中國(guó)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提升方略提供思想先導(dǎo)。
(1)樹立“有序、包容、開放、高效”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提升理念
“有序”針對(duì)的是中國(guó)版權(quán)貿(mào)易的發(fā)展順序,優(yōu)先支持全球版權(quán)貿(mào)易發(fā)展方向的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作為中國(guó)版權(quán)貿(mào)易提質(zhì)增效的重要突破口,不能偏廢傳統(tǒng)版權(quán)貿(mào)易長(zhǎng)期積累的版權(quán)貿(mào)易市場(chǎng),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市場(chǎng)和傳統(tǒng)版權(quán)貿(mào)易市場(chǎng)協(xié)同發(fā)力。“包容”針對(duì)的是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的主體,無論是國(guó)有企業(yè),還是民營(yíng)企業(yè)和個(gè)人,只要符合國(guó)家安全要求都應(yīng)當(dāng)?shù)玫街С帧!伴_放”針對(duì)的是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環(huán)境,中國(guó)要從政策性開放向制度性開放轉(zhuǎn)變,平等看待版權(quán)輸出和版權(quán)輸入,平等看待國(guó)有企業(yè)和民營(yíng)企業(yè),平等看待吸收外資和國(guó)外投資,向“共創(chuàng)、共享、共贏”雙向交互創(chuàng)新模式轉(zhuǎn)變。“高效”針對(duì)的是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的效果,要通過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賦能消費(fèi)者、創(chuàng)意者、生產(chǎn)者,賦能社交行為和文化傳播。
(2)樹立“市場(chǎng)配置力—產(chǎn)業(yè)支撐力—企業(yè)創(chuàng)新力—國(guó)際傳播力”四力合一目標(biāo)
所謂“市場(chǎng)配置力”,就是充分發(fā)揮市場(chǎng)在數(shù)字版權(quán)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找到市場(chǎng)與政府相互補(bǔ)位、協(xié)調(diào)配合的結(jié)合點(diǎn)。所謂“產(chǎn)業(yè)支撐力”,是推動(dòng)版權(quán)相關(guān)企業(yè)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優(yōu)化產(chǎn)業(yè)鏈、供應(yīng)鏈和價(jià)值鏈。所謂“企業(yè)創(chuàng)新力”,是以數(shù)字驅(qū)動(dòng)版權(quán)相關(guān)企業(yè)的高質(zhì)量發(fā)展,激勵(lì)企業(yè)對(duì)核心數(shù)字技術(shù)研發(fā)創(chuàng)新。所謂“國(guó)際傳播力”,一是通過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活動(dòng),傳播中國(guó)促進(jìn)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國(guó)際多邊治理、反對(duì)單邊治理的主張;二是掌握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的中國(guó)話語權(quán),通過主導(dǎo)區(qū)域性和全球性數(shù)字貿(mào)易談判,提升中國(guó)在區(qū)域性和全球性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規(guī)則制定中的話語權(quán)和引導(dǎo)權(quán)。市場(chǎng)配置力、產(chǎn)業(yè)支撐力、企業(yè)創(chuàng)新力指向的是中國(guó)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中的核心競(jìng)爭(zhēng)力、基礎(chǔ)競(jìng)爭(zhēng)力兩大維度;國(guó)際傳播力指向的是中國(guó)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中的環(huán)境競(jìng)爭(zhēng)力維度。
2.“四位一體”的高質(zhì)量發(fā)展方略
依據(jù)中國(guó)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高質(zhì)量發(fā)展理念、目標(biāo),圍繞中國(guó)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提升的突破點(diǎn)、著力點(diǎn)、堵點(diǎn),本研究提出中國(guó)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提升的“四位一體”發(fā)展方略,即“數(shù)字技術(shù)—數(shù)字應(yīng)用—數(shù)字安全—數(shù)字監(jiān)管”。
數(shù)字技術(shù)是提升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的支撐,也是中國(guó)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提升的突破點(diǎn)。國(guó)家要鼓勵(lì)民營(yíng)企業(yè)和新型研發(fā)機(jī)構(gòu)發(fā)揮技術(shù)創(chuàng)新作用,利用中國(guó)的制度優(yōu)勢(shì)集中攻關(guān)“卡脖子”關(guān)鍵技術(shù)問題,推動(dòng)數(shù)字技術(shù)向產(chǎn)業(yè)化轉(zhuǎn)化,促進(jìn)傳統(tǒng)出版企業(yè)的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
數(shù)字應(yīng)用是中國(guó)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的具體體現(xiàn),也是中國(guó)提升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的著力點(diǎn)。應(yīng)當(dāng)發(fā)揮既有數(shù)字應(yīng)用優(yōu)勢(shì),拓展數(shù)字消費(fèi)應(yīng)用場(chǎng)景,豐富產(chǎn)業(yè)交互應(yīng)用場(chǎng)景,推動(dòng)智慧城市和數(shù)字鄉(xiāng)村建設(shè),設(shè)計(jì)出具體的路線圖和舉措。
數(shù)字安全是提升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的安全保障。然而,數(shù)字安全意識(shí)淡漠、數(shù)據(jù)泄露頻發(fā),已成為制約我國(guó)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提升的一大堵點(diǎn)。我國(guó)應(yīng)加大軟件著作權(quán)、數(shù)字技術(shù)專利、數(shù)字版權(quán)、數(shù)字商標(biāo)權(quán)、商業(yè)秘密、個(gè)人隱私保護(hù)、服務(wù)審查、數(shù)字化交易等保護(hù)力度的關(guān)鍵條款研制。
數(shù)字監(jiān)管是提升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的體制保障,在發(fā)展方略中處于基礎(chǔ)性地位。目前,數(shù)字監(jiān)管水平較低已成為制約我國(guó)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卡點(diǎn)。我國(guó)應(yīng)充分認(rèn)識(shí)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與傳統(tǒng)版權(quán)貿(mào)易的差異,完善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統(tǒng)計(jì)體系,通過跨部門數(shù)據(jù)打通和合作,建立便利企業(yè)的合理合規(guī)管理體制。
3.以問題意識(shí)為導(dǎo)向的國(guó)際方略
以問題為導(dǎo)向,確立中國(guó)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提升的國(guó)際方略。目前制約我國(guó)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提升的三大現(xiàn)實(shí)問題是:如何突破美歐日主導(dǎo)的數(shù)字流通格局;如何加入國(guó)際數(shù)字貿(mào)易談判并參與數(shù)字貿(mào)易規(guī)則的制定;如何通過創(chuàng)新驅(qū)動(dòng)突破數(shù)字貿(mào)易壁壘。首先,我國(guó)應(yīng)找到突破美、歐、日主導(dǎo)的數(shù)字流通格局對(duì)策,重點(diǎn)從雙邊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多邊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和地區(qū)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的研究中找到與美國(guó)、日本和歐盟利益的沖突點(diǎn),從而提供有效對(duì)策。其次,我國(guó)應(yīng)參與國(guó)際數(shù)字貿(mào)易規(guī)則的具體對(duì)策。探求WTO主導(dǎo)的多邊體系作用減弱、高標(biāo)準(zhǔn)貿(mào)易協(xié)定頻出的背景和原因,研究國(guó)際經(jīng)貿(mào)體系和貿(mào)易投資規(guī)則的調(diào)整及其影響,分析我國(guó)自身優(yōu)勢(shì)、特點(diǎn)和需求,積極參與具有互惠性、長(zhǎng)效性和共識(shí)性特征的高標(biāo)準(zhǔn)規(guī)則體系的建構(gòu)。最后,我國(guó)應(yīng)突破發(fā)達(dá)國(guó)家設(shè)置的數(shù)字貿(mào)易壁壘對(duì)策與舉措,運(yùn)用倡導(dǎo)聯(lián)盟框架,分析由發(fā)達(dá)國(guó)家主導(dǎo)的數(shù)字貿(mào)易規(guī)則形成過程,對(duì)“美國(guó)規(guī)則”“歐盟規(guī)則”進(jìn)行結(jié)構(gòu)性把握,找到我國(guó)突破發(fā)達(dá)國(guó)家制造的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壁壘的方案,研制出破局策略。
|參考文獻(xiàn)|
[1] 方英,吳雪純. 我國(guó)文化貿(mào)易數(shù)字化發(fā)展的正效應(yīng)及推進(jìn)方略[J]. 現(xiàn)代傳播(中國(guó)傳媒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20 (11):1-7.
[2] 王燕. 數(shù)字經(jīng)濟(jì)對(duì)全球貿(mào)易治理的挑戰(zhàn)及制度回應(yīng)[J]. 國(guó)際經(jīng)貿(mào)探索,2021 (1):99-112.
[3] 張正榮,楊金東,顧國(guó)達(dá). 數(shù)字貿(mào)易的概念維度、國(guó)際規(guī)則與商業(yè)模式[J]. 經(jīng)濟(jì)學(xué)家,2021(4):61-69.
[4] 趙新泉,張相偉,林志剛. “雙循環(huán)”新發(fā)展格局下我國(guó)數(shù)字貿(mào)易發(fā)展機(jī)遇、挑戰(zhàn)及應(yīng)對(duì)措施[J]. 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2021(4):22-28.
[5] 崔波,趙忠楠. 數(shù)字環(huán)境下作品首次銷售原則的改良適用研究[J]. 陜西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1 (1):125-133.
[6]吳佩,韓順法. 產(chǎn)業(yè)鏈視角下數(shù)字版權(quán)貿(mào)易結(jié)構(gòu)的演變趨勢(shì)分析[J]. 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與科技,2016 (23):294-296.
[7] 周姬文希. 數(shù)字貿(mào)易對(duì)全球價(jià)值鏈的影響和重構(gòu):基于知名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數(shù)字產(chǎn)品的案例分析[J]. 現(xiàn)代商業(yè),2020(28):3-5.
[8] 何向蓮. 上海數(shù)字內(nèi)容產(chǎn)業(yè)貿(mào)易競(jìng)爭(zhēng)力分析與思考[J]. 編輯學(xué)刊,2018(4):12-16.
[9] 劉鶴. 加快構(gòu)建“雙循環(huán)”新發(fā)展格局的決策部署[J]. 西部財(cái)會(huì),2020(12):2.
[10] 江小涓,孟麗君. 內(nèi)循環(huán)為主、外循環(huán)賦能與更高水平雙循環(huán):國(guó)際經(jīng)驗(yàn)與中國(guó)實(shí)踐[J]. 管理世界,2021 (1):1-19.
[11] 林桂軍,郭龍飛,展金泳. “雙循環(huán)”對(duì)我國(guó)對(duì)外貿(mào)易發(fā)展的影響與對(duì)策[J]. 國(guó)際貿(mào)易,2021(4):22-31.
[12] 趙姍. 充分發(fā)揮數(shù)字經(jīng)濟(jì)引擎作用 助力“雙循環(huán)”新發(fā)展格局[N]. 中國(guó)經(jīng)濟(jì)時(shí)報(bào),2020-11-17.
[13] 鄧宇. 數(shù)字貿(mào)易:“雙循環(huán)”發(fā)展新格局下的經(jīng)濟(jì)風(fēng)向標(biāo)[J]. 現(xiàn)代商業(yè)銀行,2020(19):46-49.
[14] 徐金海,夏杰長(zhǎng). 全球價(jià)值鏈視角的數(shù)字貿(mào)易發(fā)展:戰(zhàn)略定位與中國(guó)路徑[J]. 改革,2020(5):58-67.
[15] 洪俊杰,商輝. 中國(guó)開放型經(jīng)濟(jì)的“共軛環(huán)流論”:理論與證據(jù)[J]. 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2019(1):42-64+205.
[16] 徐卓,楊正東,李富強(qiáng). “一帶一路”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創(chuàng)新驅(qū)動(dòng)研究[J]. 宏觀經(jīng)濟(jì)研究,2019(12):112-118+147.
[17] 王曉紅,朱福林,夏友仁. “十三五”時(shí)期中國(guó)數(shù)字服務(wù)貿(mào)易發(fā)展及“十四五”展望[J]. 首都經(jīng)濟(jì)貿(mào)易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20 (6):28-42.
[18] 楊正東,鄭承軍. “一帶一路”文化貿(mào)易“雙環(huán)流”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體系[J]. 文化產(chǎn)業(yè)研究,2020(2):196-209.
[19] 尤立杰,張凌志. “一帶一路”框架內(nèi)中國(guó)文化貿(mào)易發(fā)展策略研究[J]. 東北亞經(jīng)濟(jì)研究,2020 (6):18-27.
[20] 方英. 數(shù)字貿(mào)易成為全球價(jià)值鏈調(diào)整的重要?jiǎng)恿J]. 人民論壇,2021(1):53-55.
[21] 楊東,陳哲立. 法定數(shù)字貨幣的定位與性質(zhì)研究[J]. 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20 (3):108-121.
[22]Burri-Nenova Mira. Trade versus Culture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An Old Conflict in Need of a New Definit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09 (1) : 17-62.
[23]史志欽.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中國(guó)身份的變遷[J]. 人民論壇·學(xué)術(shù)前沿,2019(7):13-20.
[24]馬述忠,郭繼文. 數(shù)字經(jīng)濟(jì)時(shí)代的全球經(jīng)濟(jì)治理:影響解構(gòu)、特征刻畫與取向選擇[J]. 改革,2020(11):69-83.
[25]彭岳. 數(shù)字貿(mào)易治理及其規(guī)制路徑[J]. 比較法研究,2021(4):158-173.
[26] 李墨絲. CPTPP+數(shù)字貿(mào)易規(guī)則、影響及對(duì)策[J]. 國(guó)際經(jīng)貿(mào)探索,2020 (12):20-32.
[27] 藍(lán)慶新,竇凱. 中國(guó)數(shù)字文化產(chǎn)業(yè)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影響因素研究[J]. 廣東社會(huì)科學(xué),2019(4):12-22+254.
[28] 黃志雄,韋欣妤. 美歐跨境數(shù)據(jù)流動(dòng)規(guī)則博弈及中國(guó)因應(yīng):以《隱私盾協(xié)議》無效判決為視角[J]. 同濟(jì)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1(2):31-43.
[29] Normaz Wana Ismail. Digital trade facilitation and bilateral trade in selected Asian countries[J]. Studie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20 ahead-of-print(ahead-of-print) : 257-271.
[30]李忠民,周維穎,田仲他. 數(shù)字貿(mào)易:發(fā)展態(tài)勢(shì)、影響及對(duì)策[J]. 國(guó)際經(jīng)濟(jì)評(píng)論,2014(6):131-1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