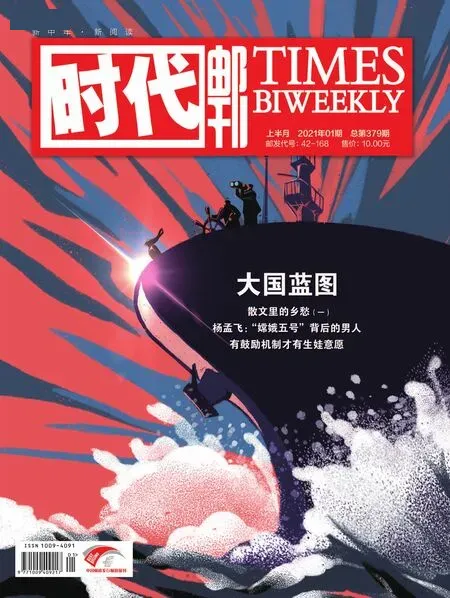教培市場“爆雷”背后

創立21年的一對一輔導機構優勝教育,倒在了2020年秋天。“沒想到,一場疫情讓我曾經引以為傲的事業瞬間崩塌。”2020年11月5日,優勝教育創始人陳昊發布致歉信,為他“個人的失敗”向學員、家長、同事、加盟商和教育行業道歉。
一家老牌機構“爆雷”的背后,是更多年輕機構的倒下。2020年以來,多家教培機構宣布資金鏈斷裂并停止運營。當中既有各地線下機構,也有線上機構,分屬不同的細分賽道,規模不一。
盡管陳昊稱“疫情使事業崩塌”,但疫情只是導火索,幾乎所有“爆雷”機構,此前就已“有病在身”。現象背后,是整個行業在商業模式、市場競爭等方面存在的既有問題。
加盟:“玩的就是現金流”
李玲2015年起加盟優勝教育,校區分布在北京和長沙。幾年前她就覺得,這家公司“遲早會出問題”。這一判斷,源于合作過程中優勝教育的種種表現:內部管理混亂,合同暗藏玄機,作出了承諾而事后卻各種推諉扯皮。“他的目的不是想把企業運營好,這個結果是必然的。”
一直未融資的優勝,采取的是加盟模式。陳昊透露,優勝全國1200多個校區,多數為加盟校區。他的講述中,加盟商經營不善、“甩鍋”總部,是導致優勝資金鏈斷裂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
但在加盟商口中,加盟校區的角色更像是優勝的提款機。加盟商繳納從數十萬元到數百萬元不等的加盟費,以自己作為法人注冊公司,但不被允許參與校區運營。總部派來自己的校長,校長之上有城市總監、區域經理,還有運營、教務、營銷和市場線的分管經理。
危機浮現之前,“省心”卻正是優勝的某種吸引人之處。當初吸引朱瀟瀟加盟的,正是“只要投入就可以做老板”。“你什么都不懂,沒關系,手把手幫你搞定一切,他們來負責經營管理。”
優勝與加盟商約定每月按51∶49分賬,分的賬,是刨去當月開支的預付款。預付款本是教培行業的一大特色。由于教學行為的長期性和連貫性,學員的學費都是一次性繳納。事實上,早在2018年8月,國務院就已出臺《關于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其中規定不得一次性收取時間跨度超過3個月的費用,但現實中,培訓機構為了業績,通過優惠手段吸引家長預交一年甚至幾年的費用仍很常見。
預付款的本質是企業負債,但卻很容易被當成企業資金。此前從未涉足教培領域的李玲起初“不懂”,后來才意識到“優勝式分賬”的問題:家長交學費動輒一兩萬元,這相當于提前把幾年內的收入當利潤分掉了。她就此向總部反映,一直與她對接的優勝中層說:“優勝玩的就是現金流。”
“玩現金流”的一個表現是,優勝方面似乎并不在意校區的盈虧,無論校長還是其上的管理層,都更在意業績,也就是預付款。打折促銷常有,當打折力度大到課程價格不足以覆蓋成本時,就出現了一個局面:招的學生越多,虧得越多。
虧損的錢理論上雙方都要負擔,但實際上,加盟商都經歷過優勝方面的各種推諉。朱瀟瀟稱,現金流為正時,優勝會每月準時劃款;現金流為負時,向總部要求打款卻遲遲得不到回應。
李玲與朱瀟瀟同在的維權群里,100多名加盟商經歷大同小異:加盟之后,多數時間都只見錢出不見錢進,留給自己的,是動輒數百萬元的虧損。
人性:“這么多錢擺在賬上”
將預付款“挪用”到企業發展擴張,這一運作方式再常見不過,風險卻也藏身其中。企業的正常運轉依賴“拆東墻補西墻”,新的學員繳費填補此前的窟窿,如此循環往復。一旦出現招生人數減少、新增現金流降低,或是家長退費擠兌,資金鏈斷裂就必然發生。
北京市安理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孫瑞濤曾接手多起互聯網金融“爆雷”案件,在他看來,不同領域的“爆雷”不盡相同,但有一些共同的邏輯。“如果沒有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模式,碰上經濟不景氣,再加上個人消費不太理性,‘爆雷’是必然。”
多位業內人士都提到了一個詞——“人性”。
“很多CEO是老師出身,不是財務出身,一看這么多錢擺在賬上,就飄了。”某留學機構合伙人常安分析說。“我覺得還是貪念,想賺快錢,不想去賺利潤。”另一位行業創業者葉峰說,據他觀察,“爆雷”的、跑路的,基本都屬于老板“心思變野了”。
資本的介入進一步放大了人性的弱點。梳理近年來多起教培機構“爆雷”案例后發現,“爆雷”大都與瘋狂擴張直接相關,而這背后是創始人的野心與資本的欲望。2017年“爆雷”的星空琴行,5年時間在高端商場開店近60家。但在“爆雷”前的2016年,創始團隊和投資人做著上市夢,企業卻虧損近兩億元。
作為同行,葉峰反感一些機構引入學費貸的做法,比如之前“爆雷”的韋博英語。學費貸的運作模式很簡單,金融機構幫學員一次性付清學費,學員再分期還款給金融機構。這種看似完美的方法,實際上將預付款模式本就存在的“爆雷”風險進一步放大,資本杠桿所產生的風險被轉嫁給了消費者。
競爭:“好人”更是默默“死”去
3年前成為教育行業創業者的科幻作家郝景芳,也經歷了幾個月資金困難時期。她自救的方式是,砍掉核心產品之外的業務,以保證盈虧平衡。在她看來,很多公司不停融資,是因為公司實在無法盈利,只能靠融資輸血。進入資本系統的教育公司,像被綁上一列高速運行的列車,再也停不下來。
沈軍是一家源自國外的思維教育機構的加盟商,在他看來,“為投資人負責”的上市公司和大機構起了不好的示范效應,它們為了“報表好看”,不惜成本投廣告、低價促銷甚至開免費課,讓整個行業的獲客成本居高不下。
市場環境改變的節點出現在2013年,此后“燒錢大戰”愈演愈烈。據《21世紀商業評論》統計,新東方、好未來、網易有道和跟誰學四家K12教育頭部機構在2020年暑期招生旺季共花掉65億元銷售費用,同比增長超30億元。更直觀的是公交站牌、電梯間和綜藝節目中的教培品牌廣告,都是燒錢營銷的去處。沈軍介紹,整個行業2020年的獲客成本幾乎比5年前翻了一番,“很多無序競爭,進入門檻太低,導致可能在一個區域里,局部競爭非常慘烈。”
線下機構與線上機構面對的市場環境并不相同。線上教育具有明顯的頭部效應,贏者通吃;線下機構則有“護城河”保護,它們具有更強的本地化屬性。但資本邏輯主導的市場下,“護城河”抵擋不了綿延的戰火,教培行業被推著進入“互聯網+”。
優勝教育管培生是周翔的第一份工作。他的感受是公司“重營銷,不重教育品質”。備課全靠自己找資料,開會則“基本在談業績”。有重點大學學歷的人因為轉化率不夠好被“優化”的現象時有發生。“985、211大學畢業的學生,連一個小學生都教不好?不可能吧?但他被‘優化’,因為‘服務’沒做好。”“服務”不過是營銷的另一種表達。營銷的對象自然是家長,目標是將他們“轉化”或“留存”。
專科生包裝成重點大學畢業生,畢業一兩年的老師包裝成有豐富教學經驗的名師,流量廣告要“三秒鐘打動家長”,制造焦慮、刺激并激發目標用戶的消費欲。有網友總結:中國的教培行業滿足的市場需求是家長的焦慮。
常安曾參與過教培行業創業公司的篩選投資。他認為,簡單地批判機構重營銷輕教學,并未看到問題的核心。“教培行業永遠存在一個矛盾,就這么多錢,到底是拿去搞擴張,還是提高服務水平?搞服務、不搞營銷的公司,我個人猜測倒閉數量遠大于搞擴張、不搞服務的,只是這些機構‘死’的時候都默默無聞,‘好人’就這樣‘死’去了。”
市場:離真正的教育很遠
在一位從業10余年的受訪者看來,商業競爭不是機構“忽悠”的理由。“做生意核心在于什么?首先不能去賣假貨對吧?”在孫瑞濤看來,只要現有發展模式和市場環境不改變,“爆雷”的故事還會繼續。
教培行業分析師周瑩認為:“從近兩年的發展情況來看,整個教培行業已經走過了爆發式增長階段,進入洗牌階段,缺乏良好商業模式以及健康資金鏈的機構會被逐漸淘汰。”也就是說,“爆雷”是教培行業洗牌的一部分。
但頭部機構就可以一路凱歌嗎?多名業內人士認為,風頭正勁的在線教育機構,“爆雷”風險同樣存在,它們都有成為下一個優勝的可能。資本一時的追捧,無法解決商業模式的固有問題。
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提到,“我還不認為在線教育是一個跑通的商業模式。”疫情期間,“全中國的產業里拿到最多融資的是教育領域,其中大部分融資流向在線教育”,但“在線教育現在的特點是,每收入一塊錢,要花掉兩塊錢”。俞敏洪談到未來的幾個目標,第一條是“把新東方打造成對得起‘教育’這兩個字的企業”。作為教培行業“教父”,俞敏洪坦誠地道出了現實:盡管名字中帶著“教育”二字,但它離真正的教育還很遠。市面上絕大多數教培機構都是應試教育的延伸,目標仍然圍繞著分數和升學,這也是焦慮的家長關注的焦點。
郝景芳創立的是一家兒童通識教育機構,她創業的初衷是“補充(學校)教育體系中特別匱乏的部分,即(孩子們)對科學、人文、藝術的認知和理解,真正讓孩子打開視野”。在她看來,校外教育與學校教育形成互補“才是教育正常的狀態”。“出了學校,如果還跟學校里學的東西一樣,模式也都一樣,那不就把時間、把生命都浪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