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電視文化類綜藝節目如何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張金堯 張 崢
【內容提要】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于當代中國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如何做到對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仍舊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電視文化類綜藝節目既與日常生活同頻共振,又伴隨電子技術進步不斷創新制作方式,從而成為文化之體走向致用的重要中介。本文通過對電視文化類綜藝節目“體、相、用”的分析,進一步闡明此類節目的文化之體、中介之相、目的之用,從而在三者互相成就、制約的基礎上,探討中華傳統文化如何通過電視文化類綜藝節目獲得符合時代特征的具體意義。
在2014年10月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數千年積淀而來的文化精魂在當代如何完成契合時代精神的書寫一直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影視藝術復合的連接屬性使其在文化傳播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事實上,當下以中華傳統文化為內核衍生出來的電視節目已有許多。從《國家寶藏》《中國詩詞大會》《詩書中華》到《故事里的中國》,此類文化節目之相已蔚為大觀。但本應內蘊其中的文化之體是否恰切得建,體相旨歸之致用又能否生出效果,這已然是關涉藝術創作、藝術傳播、藝術欣賞的重要問題。于電視文化類綜藝節目而言,如何真正做到“建體致用不舍相”——提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電視節目中的傳播效果而非空有文化之相,值得進一步的探索。
一、文化類電視節目“體相用”之辨
廣義的文化類節目在中國電視領域并非新鮮事物,畢竟我們對“電視散文”這一節目的記憶還不曾散去。但是近幾年,文化類節目又以一種新的姿態和形式重新回到主流視線空間內,收獲著眾多觀眾的好評。借助一種更容易被當下接受的形式把中華傳統文化展現出來,這當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對于中華傳統文化這樣一個生命意味濃厚的整體而言,僅僅展現是遠遠不夠的。在面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時,當下的文化類節目似乎一直都存在兩種取向,一種是甘心做那“得意忘言”之“言”,借助節目的種種傳播形式把作為核心內容的文化傳達出去,傳達的過程就是節目的形式與外在逐漸消隱的過程;另一種則是把文化視為節目的眾多元素之一,參與到節目創作和編排的排列組合之中,借此讓節目凸顯出來。很難說這兩種節目創作的取向孰是孰非,畢竟二者創作的出發點本就不一致。但是,面對如何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樣一個問題,是時候重新審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于文化類節目究竟意味著什么了。
清末時候,馮桂芬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這算得上是中國傳統體用思想的延續。在這里,“體”是根本、原本,“用”是應用,二者涇渭分明,但又相互聯系。具體到電視文化類綜藝節目中,什么才能成為立身根本的“體”?是節目,還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相伴而生的中華美學精神?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中華文化繁榮興盛”。在具體的論述中,他談到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中華民族提供了豐厚滋養”“為世界文明貢獻了華彩篇章”;談到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使中華民族保持了堅定的民族自信和強大的修復能力”。可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本身所擁有的巨大能量和綿延的生命力值得我們去珍視和傳承。這才是文化類電視節目應當秉承的“體”。我們無需給文化類電視節目下一個精準的定義,因為觀眾和從業者似乎都有著難得的默契,將熒屏上一系列的節目視為一類。這恰是文化之體帶來的一種規約和共識。美國傳播學者詹姆斯·W·凱瑞認為,傳播并非指信息在空間的擴散,而是指在時間上對一個社會的維系;它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它強調的是觀眾被內容所營造的認同感所吸引,節目成為一場情感與信仰的盛宴[1]。由此出發,傳播并非一定要在信息層面有實質的收獲,而是有可能借助整個傳播過程所營造的情景和氛圍使受眾獲得一種文化性的群體認同。換言之,無論是寄于書信的《見字如面》,還是聚焦于文物的《國家寶藏》,甚至是探索文創之路的《上新了·故宮》,都是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本之體的觀照下才形成了所謂的文化類節目。觀眾除了在節目中獲取存在于表層的信息以外,更多的是以此為路徑進入一種共有文化的場域,獲取認同。無論是繼承還是發展,認同永遠是無法舍去的第一步,也只有從認同開始,才有可能覺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本身的靈韻。
覓得根本之“體”,“相”與“用”自然清晰明了。就電視文化類綜藝節目而言,各種層出不窮的形式和重新組合的元素構成了節目呈現出來的樣態,或者不如說這是文化之體經中介之后的一種外在顯現。而這正是文化類節目的蕓蕓之相。《經典詠流傳》將詩詞譜新曲,完成了歷史與當下、古典與潮流,甚至中國與西方的對話;《中國詩詞大會》則是將古時雅集的競爭因素予以凸顯,你來我往的“飛花令”營造的是足夠緊張的氛圍;相較之下,《國家寶藏》更加綜合,舞臺劇、文物點評在故事化的呈現中都更加便于接受。但,這些都是“相”。所有的節目,究其根本都是在構建一種情境,讓人跟隨情境的內在變動而逐漸進入其中,國寶是如此,書信也是如此,核心問題在于,情境構建只是第一步。如同每年上映的數量巨大的電影一般,每一部電影都各不相同,可能夠留下印記、被人們真正記住的總是少之又少。亂花漸欲迷人眼,卻總有人囿于這些文化之相中。

《見字如面》海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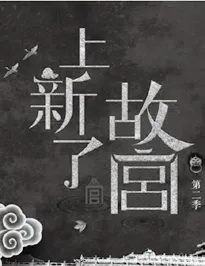
《上新了·故宮》海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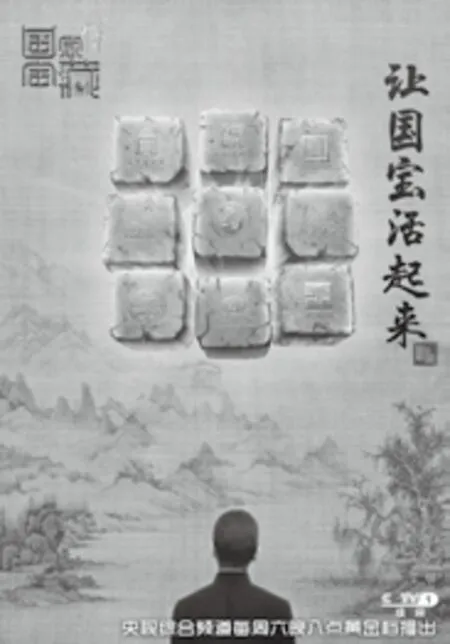
《國家寶藏》海報
如果我們認可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讓其在當代中國完成生意盎然的繼承與發展,那么這就是電視文化類綜藝節目最為根本的“用”。無論是藝術欣賞還是信息傳播,受眾總是十分重要的環節。缺少了受眾,藝術作品就沒有真正得以完成;信息傳播也沒有形成完整的通路。文化也不例外,無論體、相多么深入與繁復,總要落到地上才能生長。于是,“體、相、用”在文化內在動力的驅動之下,形成了一種互相制約的平衡。在文化類節目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需經過節目的形式與設計完成顯現,進而與受眾產生關聯、發揮作用。反過來,受眾對于節目的認知決定了文化本身的展現程度,從而影響著文化與節目的傳播。但三者間的平衡顯然不是一成不變的,平衡的存在有賴于周圍的社會、經濟、文化環境。當這些發生了變化,平衡會不斷被打破,然后在三者共同的作用下重新形成平衡。這也是為什么文化類節目在近幾年重新“翻紅”的重要原因。可見,想要通過文化類節目的傳播,將中華傳統文化更好地繼承和發揚,從“體、相、用”三者著力是可取之道。
二、建體與致用
如前所言,文化類電視節目之體應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文化之前加上的諸多修飾,顯然完成了一種對于文化的提煉,而這種提煉的過程正是建體。數千年不曾間斷的中華文明史,使眾多文化得以存續。只是,這文化無法也不能被全盤繼承,因為中華文化某些部分是應被舍棄的,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的揚棄。建體的核心在于建怎樣的體。傳統文化的命名顯然是相對于現代文化而言的,但這二者都不是單純的時間概念。并不是說存在某一時間節點,在此之前的統稱為傳統,在此之后的定義為現代,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存在著性質上的差別。人類社會在工業革命之后逐漸向工業社會過渡,在新的社會形態下人類活動產生了現代文化。而現代文化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衡量某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重要標準。世界各國現代化的具體實踐進程是不同的,其所呈現的特殊性與差異性無不深植于本國的傳統文化之中[2]。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更像是一橋相連的大河兩岸,二者始終連接、并不割裂,只是更多地在對岸互相觀審。回歸傳統文化透視現代文化,通過現代文化反觀傳統文化,進而在現代社會中重新找到傳統文化的位置,使之發揮重要的作用,才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最好的相處模式。可見,文化的發展永遠是“接著講”的。我們是無法確定一個穩定的時間點,并以此為界限開始對之前的文化“照著講”的。文化與時間的流淌始終同向而行,只要一個民族文化的傳承不曾斷絕,那么我們所謂的傳統與現代也只不過是人為添加了一種限制,讓文化本身呈現出更加規律的狀態。因此,不論是通過提煉,還是借助現代文化的觀審,最終都是要錨定一個具有相對穩定內核和動態發展外延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使之在當代語境中完成再書寫,而這就是建體。從這一點看,文化類節目并非只是被動承載著文化,而是參與到了建體的整個過程中。因為如果缺少了顯現的載體,建構的“體”永遠只能是空洞的存在,而無法與實際生活產生聯系。借用英伽登的說法,文化本身也充滿著未定點,需要繼承文化的人予以填補和連接才能真正得以完成。文化的特殊之處在于總要通過中介或者載體才能進入到人們的視野之中。文化類電視節目恰好滿足了這種中介和載體的需要。加之電視媒體與生活同頻共振的傳播特性,此類節目受到關注就順理成章了。
建體的目的就是為了致用。對于文化類節目而言,致用的最終歸宿應該是讓中華傳統文化落地生根發芽,產生持續和長久的影響。而當這種追求與諸如收視率、點擊率等因素產生沖突時,孰輕孰重就顯而易見。同社會效益相比,經濟效益是第二位的,當兩個效益、兩種價值發生矛盾時,經濟效益要服從社會效益,市場價值要服從社會價值[3]。無法否認,在市場的大潮中,電視節目實現經濟價值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經濟價值永遠不應該成為決定節目創作的根本性因素。否則,無論出發點多么的正確,在發展的過程中難免會被經濟大潮帶動偏離方向。尤其是當節目的創作開始偏向單純為了獲取關注與點擊的時候,節目的根本和樣態就不再遵從文化和藝術的規律,而是開始從屬于經濟。當一些節目把“競爭性”“利益最大化”等語匯反復提及時,就已經有滑向唯利益泥沼的風險。體現在節目中,就是為了迎合市場的關注,將各種所謂流行元素堆砌起來,在環節設定和嘉賓人設上著墨甚多,儼然將一檔節目變成了一場鬧劇。
縱觀我國電視節目的現狀,優秀的節目時常有之,但惡劣的重復卻也揮之不去。當對文化之體的關注降至谷底,創新的根本動力就不復存在,剩下的除了為創新而變化的表面,就只有一場空虛的展演。事實上,所謂某一階段的潮流類型節目,更像是吃膩了大餐之后的鄉間野味,慢而美只是特定時間中的美好假象,當更多的相似甚至重復不斷沖擊著觀眾的視覺神經,慢而美就變成膩且煩了。所以,我國的許多電視節目常常在三五季之后悄無聲息地退出電視舞臺。這似乎是我國電視節目一個無法逃離的詛咒。就文化類節目而言,其原因就在于,一些節目只是空有文化之殼,而無文化之本。它們不是在文化的指導下完成節目的創作,而是在節目創作中把文化視為其眾多元素之一而加以組合、轉換、變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文化類節目立身之本就是“體相用”中最為根本的“體”。缺了這環,“相”“用”兩廢是必然的結果。更為重要的是,對于中華傳統文化的簡單借用而非融合借鑒,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化本身的完整性和統一性?這是更為重要的問題。梁漱溟說:“一家民族的文化原是有趨往的活東西,不是擺在那里的死東西。”[4]對待這種“活東西”,我們顯然不能將之視為磚瓦石墻,粗暴地添加減損,而是應以一種身在其中的體認來保留文化的生命性。當文化成了元素,有機整體的生命意味就再難被察覺;而此時,在文化類節目中呈現的究竟又是什么呢?
三、著相與舍相
“相”在中國佛教的“體相用”論中舉足輕重,因為“相”是從“體”生“用”的一個中介。但緊接著佛家又講,“相”也只是中介,遠非目的;而且作為實踐層面上的“體相用”,其中的“相”都是虛幻的,都是不能執著的,因為一著相便違背了佛教的不執著精神[5]。換言之,“相”最終可以舍去。但是,佛教的“體、相、用”論的出發點是萬法皆空的前提。就文化類電視節目而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節目立身之“體”,而節目實際存在中經編排、設計呈現出來的種種節目樣態與形式就是節目之“相”了。在“體、相、用”三者的關系中,相是指假相,只是這里的假并不是虛假之意,而是取假借意。丁福保解釋“假”,“假者,借之義,諸法各無實體,借他而有,故名假”[6]。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本身必須經過中介才能得以與當代發生關聯,進而產生影響。因此,文化在節目中的呈現,頗有種借道而行的意味。只是這道路通暢而行,有賴諸“相”的努力。所幸,以《見字如面》《國家寶藏》《中國詩詞大會》《故事里的中國》等為代表的電視文化類綜藝節目已經開始了探索。
以往很多節目聚焦于中華傳統文化時,總是選擇從十分宏大的視角概觀五千年不曾中斷的文化長河,多仰觀而少俯察。這當然也曾發揮過巨大的作用。但是這種概觀和仰視總是少了血脈相連的親近之意,平白堆起了崖岸,觀眾獲得的只是抽象的文化概念,而缺少真正的連接。而在當下,日常敘事凸顯。日常敘事之為日常,就在于其關注平常狀態下的個體的生存,換言之,這是一種個性化敘事。這種個性化敘事可能缺少恢弘的氣勢,但它將視線聚焦于個體之上,嘗試展現出小人物的離合悲歡,宏大歷史背景所掩蓋的個體層面的內容被日常敘事重新發掘。體現在節目創作中,日常敘事表現為更加注重故事化的表達、更加努力營造儀式感的空間。
故事化是電視節目內容呈現過程中常用的方法。在文化類節目中,追求故事化是為了獲取文化意義,而非單純通過故事來獲取娛樂。這種文化意義無論如何得以實現,觀眾的認同是前提。“讓國寶活起來”是《國家寶藏》的一句宣傳語。所謂“活起來”就是讓隱于玻璃窗之后的文物沖出歷史的迷霧,以一種開放的姿態迎接當代人們的注目。節目中歷史劇演出的形式,也是讓文物重回當時的情景,從而讓文物摘下古老的面具,揭示出本真的狀態,以今觀古的同時也拉近了古與今的距離。文物之所以為文物,不僅在于其物質性地記載了工藝,更在于其精神性地傳承了文化。故事讓文物有了溫度,由此激發觀眾的興趣,才有可能進一步產生影響。古詩詞同樣不例外,除卻部分耳熟能詳的詩詞外,很大一部分詩詞既少被接觸,又很難接觸,畢竟古詩詞的語匯、語法和用典與當今的表述習慣已經相差甚多。但是,在《經典詠流傳》中,詩詞以一種新的形式進行了轉換。和詩以歌,不僅僅是讓古詩詞借流行音樂傳唱開來,更是讓似乎遠離人們日常生活的詩意語言與當下的情景重新建立了關聯。節目環節的設定,結合了音樂點評與詩詞背景的介紹。流行音樂的編配理念與古詩詞的內在韻味在拉平的歷史空間中產生新的碰撞,看似不搭調的組合方式,在故事化的展示之下,有了一種異樣的協調。古詩詞不再是“背誦全文”的晦澀對象,而變得充滿新奇感與親近感。正是故事化的呈現,給了古詩詞以貼近生活的溫度。
廣義的儀式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各種情境中。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通過儀式闡述了社會與個體的關系:“社會不僅成就個體,還依賴并內在于個體。一方面,社會超越于個體意識,但另一方面,它只有在構成它的個體意識中、并通過個體意識才能存在。”[7]換言之,除卻法律方面的規約,社會的維持還有賴于每一個個體意識中的共有約定。當個體在實際生活中觸及到這種共有約定時,儀式感就產生了。當《見字如面》中不同時間、不同內容的書信被展開時,觀眾心中由中華文化孕育的家書、情書與友人書的集體記憶就被喚醒了。信件本是私密的,這一判斷的隱含意義就是對信件內容真實性的確證。因此,將這種私密的真實在“圍爐夜話”式的小劇場進行展現時,情景的參與程度得以最大程度的建立。加上節目對于書信主題的整體把握,生死、愛恨、成長、相思、不舍等一系列人類共通情感帶來了強烈的力量。正是在這種力量的影響下,各不相同的書信才能將不同的觀眾凝聚在一起,進而參與到文化的當代書寫之中。“展信佳”,本就是一個儀式感具足的開場。當觀眾隨著信件的展開而參與其中時,原本私密的信件就被轉變為公共空間對集體記憶的緬懷與反思,從而形成了一種儀式化的狂歡。這種集體記憶更像是種子。初始時只是潛藏在人們意識之中,當經過不斷的復現和時間作用下的沉淀、凝結后,種子開始生根發芽,文化的繼承自然就完成了。
故事與儀式都是在努力塑造一個凸顯“體”的“相”;有了“相”作為中介,才能將中華傳統文化以一種真實可感的方式延續下去,而非僅僅留存于概念化的表面。由此來看,“相”當然不應舍去,但也大可不必將所有的重心都置于“相”上,因為一旦過于著力于某方面,節目就不可避免地開始走向刻板與僵化,那個逃不過三五季的“詛咒”就會出現。一些節目視熱點為核心,把流行元素不假思索地移植到節目中,看似樣態豐富,實則缺少內在的統一性,最終呈現出來的只能是一個個相互疏離的切片。這恰是因為過于重視“相”。面對紛繁復雜的相時,心中仍需有一線清明,知曉哪里才是根本,畢竟形式總是要為內容服務。著相也好,舍相也罷,凡相都只是過程,最終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加以凸顯,才是目的。
結語
對電視文化類綜藝節目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問題的探討很難單純局限在藝術或傳播的領域。因為究其根本,提及文化的藝術創作和信息傳播都只是表象而已。本質上,應探討的是如何完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當代社會生活中的再書寫,亦或是更為直接地稱為轉譯。馮友蘭曾提出“抽象繼承法”,并指出:“在中國哲學史中有些哲學命題,如果作全面了解,應該注意到這些命題底兩方面的意義:一是抽象的意義,一是具體的意義。”[8]何為具體、何為抽象,馮友蘭舉例說:“《論語》中所說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從這句話的‘具體意義’看,孔子叫人學的是詩、書、禮、樂等傳統的東西。從這方面來理解,這句話對于現在就沒有多大用處,不需要繼承它,因為我們現在所學的不是這些東西。但是,如果從這句話的‘抽象意義’看,這句話就是說:無論學什么東西,學了之后,都要及時地、經常地溫習和實習,這就是很快樂的事。這樣的理解,這句話到現在還是正確的,對我們現在還是有用的。”[9]哲學命題是如此,傳統文化也是如此。具體意義當然需要被關注,只是這種在具體情境之下的意義在當代也許會水土不服,這也是不可忽略的事實。抽象繼承并不是將有機整體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抽離成為概念化的、限定性的表述,放在樓臺之上枯等人們憑吊瞻仰;而是將原本情境中合理、有益的傳統文化之精神內核總結出來,根據當前時代的發展重新賦予其符合時代特征的具體意義。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影視藝術領域的傳承大抵都是如此——“建體”通過中介的“相”達到“致用”。近幾年的文化類電視節目是明確文化之體后,在尋“相”之路上的更新的探索,也是對文化之體進行當代書寫的更新的嘗試。而這些節目所依托的電視媒體毫無疑問是大眾文化傳播的重要陣地,“在整個國家的文化建設和美學建構中發揮著別的文藝形式難以企及和替代的作用”[10],能夠結合新的技術手段,在多平臺進行內容傳播,如此多方合力的推動下,電視文化類綜藝節目所產生的影響已經超越了節目形式本身的局限,開始向著營造一種更為廣泛的社會氛圍轉變。建體致用不舍相,電視文化類綜藝節目在連接“體”與“用”之間所發揮的巨大作用,使其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方面能夠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引領大眾走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世界。
【注 釋】
[1]陳力丹.傳播是信息的傳遞,還是一種儀式?——關于傳播“傳遞觀”與“儀式觀”的討論[J].國際新聞界,2008(8):46-51.
[2]徐小躍.中國傳統文化與儒道佛[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1.
[3]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5-10-15(2).
[4]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M].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25.
[5]陳堅.不是“體用”,而是“體相用”——中國佛教中的“體用”論再思[J].佛學研究,2006:329-344.
[6]丁福保.佛學大辭典[M].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11:1599.
[7]〔法〕涂爾干.職業倫理與公民道德[M].渠東,付德根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11.
[8][9]馮友蘭.三松堂自序[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1:259,259-260.
[10]仲呈祥.自厚天美[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3:3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