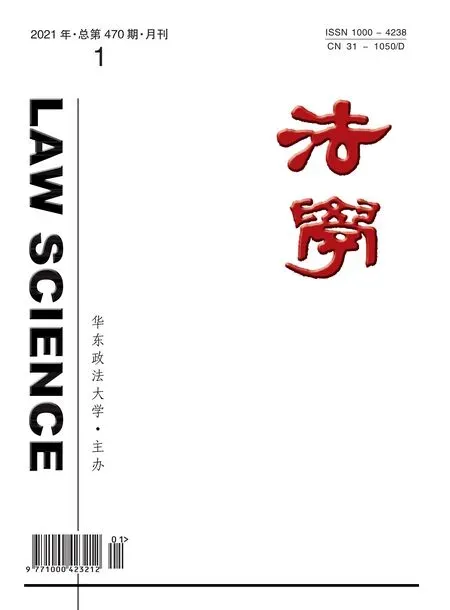股權利益分離視角下夫妻股權共有與繼承問題省思
●周 游
* 作者單位: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中央財經大學企業合規與風險防控法律研究中心。本文是中國法學會2018 年度部級一般課題“公司法之功能嬗變及結構性革新研究”[CLS(2018)C44]的研究成果。
一、問題切入與研究進路
所謂“夫妻共有股權”的問題涉及公司法、婚姻家庭法等領域,一直以來都受到法律界的廣泛關注,夫妻共有股權如何行使以及如何分割等議題尤其受到重視。〔1〕例如參見王涌、曠涵瀟:《夫妻共有股權行使的困境及其應對——兼論商法與婚姻法的關系》,載《法學評論》2020 年第1 期。從表面上看,這似乎不應成為一個難點。盡管其涉及多個領域,然而只要以公司內外部關系為區隔,在處理公司外部關系時優先考慮夫妻雙方的利益配置,在涉及公司內部關系時則需顧及公司人合性,此類問題就可能得到妥善解決。
只是實踐中人與人之間的法律關系總比理論設想中的更加紛繁多樣、錯綜復雜。一旦在夫妻共有股權情形中還涉及諸如繼承等其他法律關系時,糾紛處理就可能有更多值得關注的問題。例如,張某與其他四人為北京某甲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公司)股東,張某持股比例為40%,為其與配偶高某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取得。2019 年8 月21 日,張某去世,張某的合法繼承人只有高某及女兒張小某,甲公司章程沒有關于股東資格繼承的排除或限制性規定。2019 年9 月16 日,高某明確表示自愿放棄張某所持股權的繼承權。繼而,高某、張小某請求法院確認兩人為甲公司股東,各享有該公司20%的股權;而甲公司認為高某既已放棄繼承,就不應取得公司股東資格。后一審與二審法院皆判決認為,高某自愿放棄對張某所享有的甲公司股權的繼承權,但并未表示放棄其基于夫妻共同財產所享有的甲公司20%股權的所有權。故認定高某與張小某系甲公司的股東,各享有公司20%的股權(以下簡稱“張某案”)。〔2〕參見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20)京02 民終1505 號民事判決書;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2019)京0101 民初20178號民事判決書。該案基本案情似乎并不復雜,但映射出司法實踐對夫妻共有股權情形下股東資格繼承問題的通常做法,其中隱含若干可能被忽視的細節,并由此引申出一些值得分析探討的重要議題。
第一,如何理解夫妻共有關系情形下繼承與共有之關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四)》(以下簡稱《公司法解釋(四)》)第16 條規定,在有限公司自然人股東因繼承發生變化時,其他股東原則上不得主張行使優先購買權。這似乎成為司法實踐中不言而喻的規則。然而在涉及夫妻共有關系的場合,例如在“張某案”中,張某持有40%股權所對應的財產份額并非全為其遺產,其中一半理應屬于其配偶高某所有,那么與之相對應的20%股權比例,高某何以自動取得?在此情形下,其他股東能否主張行使優先購買權?再者,倘若配偶是唯一合法繼承人,那么繼承股東資格的配偶是否就必然自動享有被繼承人的全部股權?這些問題皆不無疑惑。
第二,對于股權(及其利益)與股東資格這兩個概念是否有必要加以區分,這實則是前一議題之延伸,之所以會在繼承場合忽視了夫妻共有關系的問題,主因在于未能將股東資格與股權加以區分。實踐中法院通常認為這兩者是合一的,例如有判決指出:“股東資格可以被繼承,該股東資格既包括股東的財產權,也包括基于財產產生的身份權。”〔3〕“耿馬縣孟洲金粒開發有限責任公司、趙潤華股東資格確認糾紛案”,云南省臨滄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云09 民終455 號民事判決書。捆綁式的股權利益結構有礙于對股權本質的理解,由此也可能誤讀了《公司法》第75 條關于自然人股東之股東資格原則上可以繼承之規定的內涵。
第三,在夫妻共有關系中,所謂股權共有及繼承,“共有”“繼承”具體何指,這是立法與司法都需要直面的問題。就共有而言,其究竟是股權共有,還是股權的財產利益或其他利益的共有?就繼承而言,其究竟是股權繼承,還是股東資格繼承?這不僅關乎公司法與婚姻家庭繼承法之沖突與協調,還涉及公司法理念及其影響下的相關股權規則的革新問題。〔4〕最高人民法院曾在裁判中指出:“對于以夫妻共同財產認繳有限責任公司出資但登記在夫或妻一方名下的股權,是否屬于夫妻共同財產,存在一定爭議。”參見“李順祥、羅菊芳執行異議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6275 號民事裁定書。
二、從夫妻共有到繼承:相關股權規則適用之惑
涉及共有及繼承的股權規則主要散見于我國公司法與婚姻家庭繼承法的相關規定。《民法典》對夫妻共同財產及其分割、繼承問題,在整體接受既往規定的同時亦略作修改。這些規定能否很好地回應實踐,規則之間又有何關聯或者沖突,仍需深入分析。
(一)公司法之應對
我國公司法涉及股權之共有和繼承的規定較為粗糙,許多方面都存在制度空白。
一方面,對于股權能否共有或如何共有的問題,《公司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只字未提。因為立法的缺失,法律界對于如何處理相關問題就有了不同看法。有學者認為,既然《公司法》未對此設特別規定,則意味著應適用關于股權轉讓的一般規定。〔5〕參見范健、王建文:《公司法》(第5 版),法律出版社2018 年版,第301 頁。除此之外,理論界和實務界亦有按照隱名出資規則處理夫妻共有股權之觀點。不過需要斟酌的問題在于,股權共有與隱名出資在特定情形下可能存在若干相似之處,但隱名出資的表現形式紛繁多樣,常見的是名義股東并不出資而只有實際出資人履行出資義務,故難以將其看作共有關系。〔6〕有學者根據共有形式是否在公司股東登記簿作備注記載將其分為顯名共有和隱名共有。這可能是借鑒了隱名出資的相關理論研究,但在股權共有不引發股權變動的情形下,這一分類對公司治理的意義并不大;一旦引發股權變動,則可通過隱名出資、股權轉讓等其他策略解決,而無需細化股權共有的規則。參見梁開銀:《論公司股權之共有權》,載《法律科學》2010 年第2 期。況且,隱名出資場合是否必須適用股權轉讓之優先購買權規則不無爭議。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以下簡稱《公司法解釋(三)》)第24 條第3 款的規定,只有經過公司其他股東半數以上同意后,實際出資人方能請求公司確認其股東資格。此處并未強調其他股東“不同意即應購買、同意即享有優先購買權”之規則;況且,“半數以上”的規定反映出最高人民法院在隱名出資問題上有意表明其與股權轉讓存在區別。由此觀之,公司法未對股權共有問題予以回應,不能被認為是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相反,這可能會引發諸多難題,而這些難題能否根據婚姻法、物權法等規定妥善解決不無疑問。
另一方面,在面對繼承問題時,《公司法》第75 條規定的是自然人股東之合法繼承人通常可以繼承股東資格。為了維護公司人合性,該條之但書強調公司章程可就此作出特殊規定。當然,中國人往往在行事伊始即希望圖個好意頭,因而公司章程對與死亡有關的問題作出特殊安排極為罕見。〔7〕例如在個案中,公司并未在章程中作出特殊的制度安排,但當繼承開始時,公司希望作出股東會決議阻止繼承人成為股東,但法院認為公司決議不能違反《公司法》第75 條的規定,故判決繼承人可以繼承股東資格。參見“北京市宣武炊事食品機械有限公司與徐佳等股東資格確認糾紛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5)二中民(商)終字第04210 號民事判決書。在章程中作出繼承人不能取得股東資格之規定的公司也大多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例如因為企業改制而存在職工持股現象,當職工辭職、退休、死亡時股權由公司回購或在股東間進行內部轉讓。〔8〕例如參見“王某某、申某玲與青島萬興商貿有限公司股東資格確認糾紛案”,山東省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青民二商終字第875 號民事判決書。從文義上看,《公司法》第75 條明確了公司法與繼承法各自的調整范圍:前者對于股權所具有的財產利益如何繼承在所不問;而后者對作為股權人身利益之重要體現的股東資格應如何繼承的問題則不加干涉。既然如此,為何還有規則之間的沖突問題呢?如前所述,司法實踐多持股東資格與股權合二為一之立場,從而引致不必要之疑難。
繼而,《公司法解釋(四)》第16 條進一步指出,在繼承場合其他股東原則上不得主張行使優先購買權。繼承場合不適用優先購買權規則是我國司法實踐長期秉持的立場,《公司法解釋(四)》第16 條只是對這一立場的確認。〔9〕在《公司法解釋(四)》出臺之前,不少判決已經明確了相關規則。例如“韓靜波與南興控股有限公司、吳振宇、梁濟文、徐昌標股東資格確認糾紛案”,上海市閘北區人民法院(2015)閘民二(商)初字第574 號民事判決書。問題在于此時不得主張優先購買權的理由,這其中可能涉及公司人合性與親屬身份關系之間的沖突與磨合問題。有學者認為,“當二者發生沖突時,對特定親屬關系的優先照顧是法律倫理性和人文主義的表現和必然選擇”。〔10〕趙旭東主編:《公司法學》(第4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第259-260 頁。德國《有限責任公司法》的相關規定表面上與此立場相仿,然省察其背后邏輯,似與倫理無關。德國法上的爭議焦點在于如何調和公司法的人合性與繼承法要處理的財產分配問題之間的沖突。德國學界主流觀點認為,“不能基于德國《有限責任公司法》來排除或變更繼承法關于遺產繼承順序的規定,通過章程也不存在這種可能性”。〔11〕[德]托馬斯·萊塞爾、呂迪格·法伊爾:《德國資合公司法》(第6 版),高旭軍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632 頁。由此,對于繼承人已經成為公司股東之既定事實,公司可采取的策略要么是按照該法第60 條第2 款解散公司,要么是按照該法第34 條在此前已規定可在股東死亡時收回股權。〔12〕參見《德國商事公司法》,胡曉靜、楊代雄譯,法律出版社2014 年版,第39 頁、第56 頁。在這兩種舉措中,前者可謂玉石俱焚,后者則徒增繁瑣,可見德國法采取的是一種更關注繼承法規則之傾向。相比之下,我國公司法的立場試圖與繼承法之間實現衡平,盡管司法實踐所呈現的問題與德國法的情形在本質上存在共通之處,下文將對此作詳細剖析。
(二)婚姻家庭繼承法之應對
相比公司法之應對,我國婚姻家庭繼承法對共有和繼承問題之規定較為詳細,司法實踐中亦多有運用相關規則解決股權糾紛的案例。
一方面,針對夫妻共有關系,《民法典》第1062 條在原《婚姻法》第17 條的基礎上完善了夫妻共同財產規則。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民法典》在“生產、經營的收益”之基礎上增加了“投資的收益”之內容,這與股權存在密切聯系。繼而,夫妻對共同財產有“平等的處理權”之規定也引發了夫妻共有關系下股權享有與行使的諸多爭議問題。實踐中主要有以下兩種情形。一是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之股權投資如何處理的問題。通常而言,此種情形若是涉及股東權利行使或股權轉讓時并不過問配偶之意思;然而,倘若其他股東或受讓人明知配偶之存在,而涉事股東又罔顧配偶意愿而自行其是,此時行為之效力如何存在爭議。有法院判決認為,涉案股份應屬夫妻共同財產,應由雙方平等協商處置。〔13〕參見“李某某、李堅忠與郎某某確認合同無效糾紛案”,浙江省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浙金商終字第1678 號民事判決書。二是當夫妻共同出資設立公司時,夫妻一方名下之股權是否為共同財產。司法實踐中通常認為此時任何一方名下的股權都屬于共同財產,繼而認為此種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對夫妻共同財產做重要處理的決定,夫妻雙方應當平等協商,取得一致意見。〔14〕例如參見“彭麗靜與梁喜平、王保山、河北金海岸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股權轉讓侵權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二終字第219 號民事判決書,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9 年第5 期。以上兩種情形之共性在于強調對股權的共同協商處置。然而,所謂享有平等處理權之對象值得斟酌。應注意的是,無論是《民法典》還是原《婚姻法》,二者規定的都是財產而非權利之共有,當然也未明確規定股權之共有。有學者認為,我國婚姻法“關注的焦點從來都不是財產的具體形式,而是財產的取得原因”,即“只在于當事人取得該財產的對價是什么”。〔15〕參見龍俊:《夫妻共同財產的潛在共有》,載《法學研究》2017 年第4 期。故而夫妻共有關系情形下之股權,其所謂共有的客體的確迷霧重重。
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一)》(以下簡稱《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解釋(一)》)第73 條的確在很大程度上緩和了公司人合性與親屬身份關系之間的沖突。根據該條規定,公司人合性理應得到尊重,故而在審理離婚案件時,若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財產中以一方名義在有限責任公司的出資額,其配偶想成為公司股東是需要經過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的,此時其他股東對擬轉讓的部分亦享有優先購買權。這其實借鑒了《公司法》第71 條有關股權對外轉讓的規定。如此一來,盡管該條置于婚姻法體系中而不是由公司法予以回應略顯突兀,但至少有其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然而,司法實踐中仍存有不少疑惑之處。該條明確適用的情形是離婚案件,那么對夫妻共有關系下之繼承問題能否直接適用存有爭議。更有甚者,一旦采取前述隱名出資的思路理解夫妻共有股權問題,《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解釋(一)》第73 條就可能被架空。近年來也的確出現了類似案件。〔16〕有法院判決認為,夫妻雙方在離婚時由一方向另一方轉讓股權的行為,“實際上是對其夫妻存續期間共有財產的分割,是股東由隱名向顯名的轉化方式”。該案特殊之處在于兩點,即當事人申請確認轉讓合同無效,以及在分割股權時約定的是無償轉讓。司法裁判確認合同無效通常秉持非常謹慎的態度,同時涉及贈與之情形如何適用優先購買權的規定存有爭議,這些都可能是致使法院排除適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解釋(一)》第73 條的考量因素。參見“李福珍與李軍、陳紅確認合同無效糾紛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7)京01 民終5852 號民事判決書。
另一方面,針對夫妻共有財產繼承問題,《民法典》第1153 條整體接受了原《繼承法》第26 條的規定,只對部分表述作了調整。可以說,相關規定之立場是非常明確的,即遺產分割應先分出共同所有財產的一半為配偶所有,其余的才是被繼承人的遺產。那么,對于涉及夫妻共有關系情形下之股權如何繼承的問題,原本也不應存在疑惑,因為被繼承人的遺產僅僅是股權項下一半的財產份額,另外一半應歸其配偶所有,對這部分的處理不適用繼承法規則。據此,重新省察包括前述“張某案”在內的類似案件,表面上看的確也是這樣處理的,即先行分出一半股權歸配偶所有,另一半股權由合法繼承人繼承。只不過先行分出的一半股權何以由配偶當然取得,或者說配偶何以當然享有股權項下的全部利益?問題的關鍵在于股權分割情形下“共同所有的財產的一半”應當如何理解。不僅是“張某案”,法院通常采取的做法都是將股權的一半直接分出為配偶所有。〔17〕類似案件可參見“郭宗閔、李恕珍與青島昌隆文具有限公司股東資格確認糾紛案”,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魯民終2270 號民事判決書。另參見謝秋榮:《公司法實務精要》,中國法制出版社2020 年版,第798 頁。由此,夫妻共有的客體分明就是股權,而非法律規定的投資收益。如此矛盾之處有待更深入的理論釋疑。
此外,結合《公司法》第75 條,倘若公司章程規定自然人股東死亡后其合法繼承人不得繼承股東資格,那么此時既有共有關系又有繼承關系之配偶,根據繼承法規則所分出的為其所有的一半,又當如何處置?對此,實踐中多采取直接返還其對應財產份額的方式。然而,這分出一半之基礎理應是共有而非繼承,配偶何以不能主張適用股權對外轉讓的規則不無爭議。顯然,將股東資格與股權相捆綁的做法,使得共有問題在繼承場合被自然而然地忽略了,而在繼承方面也存在需要澄清的問題。
三、問題癥結:股權與股東資格之捆綁式處理
當今社會發展之速度與范式,基于科技化、信息化、數字化等因素,已然遠遠超出人類的原初設想。現代公司正是在此大背景下濫觴及發展,股權也因此愈加受到關注,進而成為一種社會時尚與潮流。〔18〕See Arianna Pretto-Sakmann, Boundaries of Personal Property: Shares and Sub-Shares, Hart Publishing, 2005, p. 3.這不但沖擊傳統的思維模式,而且動搖了固有的法律架構。夫妻股權共有與繼承之難題盡管表面上看是不同法律規定之間尚有需要闡釋之余地,然其根本仍在于如何理解股權性質。
在過去,對股權性質的認知深受財產法之理念與制度的影響。這部分源于對美國公司法上所有權(ownership)、所有者(owner)之誤解,〔19〕參見周游:《股權性質之爭:誤區釋疑與價值重述》,載《經貿法律評論》2019 年第2 期。也與我國學界早期關于股權(主要是國有股權)是物權還是債權之爭論有關。〔20〕例如參見郭鋒:《股份制企業所有權問題的探討》,載《中國法學》1988 年第3 期;王利明:《論股份制企業所有權的二重結構——與郭鋒同志商榷》,載《中國法學》1989 年第1 期。這兩個方面經由兩權分離理論之中國化,〔21〕美國傳統理論認為,兩權分離因其可能增加代理成本,故而是一個公司法上亟待解決的問題;而在中國,實現兩權分離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一項目的。參見周游:《公司法上的兩權分離之反思》,載《中國法學》2017 年第4 期。形成極具中國特色的股權理念。我國《公司法》第4 條規定,公司股東依法享有資產收益、參與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權利。在實踐中,股東無法參與或不愿參與公司治理,股東在公司中的角色定位主要就是向公司出資以及取得投資收益。如此一來,股東所享有的股權幾乎與資產收益權等同,從而掩蓋了股權中因股東資格而享有之非財產利益,將原本紛繁多樣的股權利益捆綁在一起。由此,即便承認股權是一種獨立的權利,也可能仍主要停留在財產權范疇予以探討。例如有學者認為,除了某些股東權可否與股份分離讓與之討論有意義外,此種分類實益不大,故認為股東權就是財產權。〔22〕參見曾宛如:《多數股東權行使之界限——以多數股東于股東會行使表決權為觀察》,載《月旦民商法雜志》總第31 期(2011年3 月)。實際上,當糾問股權究竟是(或者屬于)何種權利時,我們在潛意識里早已將股權看成一種必須被歸類的子權利,這依然未能跳出物權與債權之大部類分法,從而使股權性質之爭陷入迷思,并始終在財產權框架下進行。所謂對股權內部結構的誤解,歸根到底就是將股權內部各種利益視為不可分離的整體,并將股權利益的享有與讓渡進行了“捆綁式”處理。在這種捆綁式的股權利益結構下,財產利益成為最核心的部分,包括名聲、榮譽、意愿等在內的人身利益將僅被視為實現財產利益的工具,亦即極易得出財產未受損則權利未被侵害之謬論。推而廣之,在探索股東資格確認、股權變動等具體問題時,也可能誤用財產權保護的原理及規則,從而忽視了公司獨立意志、股東之間的合意等公司法上的重要元素。〔23〕鄧峰指出,只要出資就能成為公司股東的所謂“實質標準”,本質上與將公司稱為股東財產的衍生物是一致的。參見鄧峰:《普通公司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年版,第347-348 頁。如此捆綁式的股權利益結構無異于淡化公司法之存在必要性,從而強化財產法、合同法及侵權法對公司糾紛解決的影響。
在這種捆綁式的股權利益結構下,原本法律關系非常清晰的夫妻共有與繼承問題就變得撲朔迷離。而從當事人的訴求來看,他們在夫妻共有關系情形下主張行使優先購買權,也大多針對“作為整體”的股權而言,而非只就配偶因分割取得的那一部分主張權利。〔24〕例如“譚某、韓某乙等與韓某甲、程某繼承糾紛案”,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柳市民一終字第208 號民事判決書。如此一來,法院也的確不必深究其中理應區分的不同法律關系了。一旦將本可拆分的訴訟請求合為一體,那么法院將其視為一個純粹的繼承問題而非同時涉及共有問題便不足為奇。第一,由于當事人請求的是對股權整體行使優先購買權,那么按照《公司法》第75 條、《公司法解釋(四)》第16 條的規定,涉及繼承的那一部分不適用優先購買權規則,由此推及股權整體也采取相同處理方式。第二,即便法院注意到《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解釋(一)》第73 條的存在,但由于該條明確規定適用于離婚案件審理,而在夫妻共有股權分割場合適用股權對外轉讓的規定本身就存在爭議,因而在繼承與共有問題并存之場合,又存在《公司法》第75 條、《公司法解釋(四)》第16 條之前提下,法院類推適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解釋(一)》第73 條的確需要更充分的解釋。第三,再加之公司法的當前規則僅對繼承予以回應,那么不采取共有的解決思路亦是順理成章,畢竟公司法領域對此類問題目前仍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甚至從形式上看,這是在一個同時涉及公司法與婚姻家庭繼承法之糾紛中優先適用公司法規則之“商事”裁判立場。
一旦聚焦于公司利益保護的問題,這顯然是需要反思和改進的裁判策略。倘若股東之配偶在繼承場合自動取得分出的一半所對應的股權,這就不僅僅是妨礙其他股東行使優先購買權的問題,還可能影響公司的持續運營和發展。有限責任公司之兩權分離程度相對較低,股東通常直接參與公司決策,處理公司事務可能并非其配偶之所長;而被繼承股東持股比例越高,對公司的不確定的負面效應也可能越大。〔25〕一個需要注意的細節是,不少家族企業往往是多個家族成員共同參與公司運營,包括夫妻共同運營的情形。而在這種情形下,夫妻雙方通常同為公司的股東,若是一方死亡所引起的也是股權內部轉讓問題,與本文討論的情形有別。倘若公司出現運營危機或內訌,公司員工、債權人等利益相關者也可能受到影響。那么,在維護有限公司人合性的同時是否就無法很好地保護被繼承股東之配偶的合法權益呢?當然不是。對此,首先需要明晰對配偶而言,法律應當保護的是何種法益。無論是基于共有關系還是繼承關系,股東之配偶在通常情況下往往更看重股權可能帶來的收益,主要包括股權價格收益及現金或其他形式的持續性收益。前者主要是通過股權變動的方式,除了其他股東購買股權以外,還可能存在公司回購股權等情形。后者主要是采取信托的方式,但這種方式囿于我國信托實踐之不足,在過往并不常見;〔26〕但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第1133 條第4 款規定,自然人可以依法設立遺囑信托。這將可能促進包括股權信托在內之相關實踐的發展。類似的做法,通常是采取由其他股東代持(即隱名出資)的策略,而配偶及其他合法繼承人作為實際出資人(也是受益人)取得持續性收益。不難發現無論是以上何種方式,其落腳點皆為股權之財產利益,而并不主要指向股東資格本身。然而,只要依然堅持股權(及其利益)與股東資格不可分離之立場,司法實踐就難免要在維護被繼承股東之配偶財產利益的同時也對股東資格確認問題劃一處理。要實現公司利益與配偶個人利益之平衡,宜秉持股權利益分離視角,重新厘清夫妻共有與繼承之不同法律關系,并分別依據相應的法律規定予以調整。
四、股權利益分離視角下的夫妻共有與繼承
(一)股權利益分離與股權變動之邏輯關聯
公司法學界很早就注意到股權內部結構的復雜性。19 世紀末,就有德國研究者將股權劃分為共益權與自益權兩大類,這一分類對日本等國之公司法理論構造帶來深刻影響。〔27〕神田秀樹『會社法』(弘文堂,2015 年)68-69 頁;新津和典「19 世紀ドイツにおける社員権論の生成と展開:社員権の歴史性と現代的意義」法と政治59 巻1 號(2008 年)185 頁參照。另有美國學者在對股權進行分類時采用權利(right)與權力(power)的劃分,這在表面上看有點匪夷所思,畢竟權利與權力是涇渭分明的,不可能也不應當同時納入股權。倘若將其置換成我們熟知的語境,那么權利主要就是指稱財產權,而權力則意指參與公司的管理與控制,主要就是人身權,其落腳點最終還是權利。〔28〕See James D. Cox and Thomas Lee Hazen, Cox & Hazen on Corporations: Including Unincorporated Forms of Doing Business, Vol. 2, Aspen Publishers, 2003, p. 718-719.繼而,20 世紀80 年代催生出所謂的股東行動主義,這實質上是以機構投資者為代表的要求奪回股東在公司中的權利并且積極參與公司決策的運動。〔29〕See Edward B. Rock, The Logic and( Uncertain) Significance of 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Activism, 79 Georgetown Law Journal 445(1991).此處所言之股東在公司中的權利,主要指的是非財產性的權利。然而,以上各維度的見解盡管指出股權內部結構的復雜性,但本質上仍是將不同的權能、利益混雜在股權當中且視為同時并存的一個整體。反對股權之權益分離是域內外傳統公司法理論與實踐的主流看法。例如在日本,學界通常認為表決權不得單獨從股權中分離出來;〔30〕吉本健一「議決権信託に関する若干の法的問題點」阪大法學総95 號(1975 年)69 頁參照。而在我國臺灣地區,盡管通說是將股東權分成具有身份權色彩之表決權以及參與會議、經營公司等共益權,而將盈余分配及剩余財產分配請求權等歸類為具有財產權色彩之自益權,但如我國臺灣地區學者劉連煜認為,表決權與股東權均不可與股東分離,僅股東才可享有表決權,也不能將表決權出售他人,故股東權可謂是一種“人格權”。〔31〕參見劉連煜:《現代公司法》(第11 版),臺灣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版,第378 頁。按照這一觀點,雖然是強調股權之人身利益,但仍屬于一種捆綁式的策略。此外,英國法的做法值得注意,其明確區分了公司成員(member)與股東(shareholder)兩種身份。未經登記的股東只取得了一定的財產權利,沒有表決權等人身權利;而一旦經過登記就變成成員,享有類似于中國公司法關于股東的完整權利。〔32〕參見葛偉軍譯注:《英國2006 年公司法》(第3 版),法律出版社2017 年版,第84 頁。不過,這實際上是對不同主體的分類,不同類別的主體相應地享有不同的權利,還談不上是對股權內部結構的解構。既往看法之所以反對股權利益分離,主要是考慮到分離可能誘使機會主義行為產生,例如以往經常討論的表決權買賣可能帶來的代理成本問題,〔33〕有學者指出,政治領域禁止表決權買賣的理由在公司表決權買賣問題上并非完全站得住腳,“一次性表決權買賣”的代理成本可通過一些前置程序緩解,不應禁止。參見夏戴樂:《上市公司表決權買賣之法律經濟學分析——以代理成本問題為中心》,載張育軍、徐明主編:《證券法苑》(第6 卷),法律出版社2012 年版,第426 頁。還有新近備受關注的股權質押所涉及的表決權空心化隱憂。〔34〕根據學者的研究,股權設質盡管資金融入方仍保有表決權,但股票質押式回購本質上是一種復合技術性與法律性的場內資金融通金融工具,只要固守其擔保資金借貸的法律屬性,并考慮作為場內金融交易的功能設置,完善各類救濟措施,就能更好地厘清權責,促進業務健康發展。參見洪艷蓉:《股票質押式回購的法律性質與爭議解決》,載《法學》2019 年第11 期。然而,投資者對股權利益所作出的特殊安排層出不窮,其中不乏值得肯定的商業模式,倘若僅僅因為其中可能存在的問題而一概否定商人實踐,實屬因噎廢食之舉,并不可取。
省察我國商法學界之過往研究,亦不乏對股權內部結構的有益反思。有學者較早提出,股權不是基于股東身份而產生,而是與股東同時產生,是同一出資法律關系的兩個要素。〔35〕參見江平、孔祥俊:《論股權》,載《中國法學》1994 年第1 期。類似觀點可參見雷興虎、馮果:《論股東的股權與公司的法人財產權》,載《法學評論》1997 年第2 期。這一觀點無疑含有原初的分離思想。還有學者也認為,股東資格與股東權利并非總是合一的。〔36〕參見葉林:《公司股東出資義務研究》,載《河南社會科學》2008 年第4 期。另有學者將股權分為人身權與財產權兩大部分,并將其稱為“股權二分論”,繼而嘗試將這一理論運用到解決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轉讓的司法實踐問題上。〔37〕參見蔡元慶:《股權二分論下的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轉讓》,載《北方法學》2014 年第1 期。當下,公司法學者已經充分注意到股東“異質化”之趨勢。〔38〕在域外相關論著中,經典研究當屬克拉克對不同階段股東分化的梳理和論證,而域內學者近十年來亦多有建樹。例如參見馮果:《股東異質化視角下的雙層股權結構》,載《政法論壇》2016 年第4 期;汪青松、趙萬一:《股份公司內部權力配置的結構性變革——以股東“同質化”假定到“異質化”現實的演進為視角》,載《現代法學》2011 年第3 期。See Robert C. Clark, The Four Stages of Capitalism: Reflections on Investment Management Treatises, 94 Harvard Law Review 561( 1981).與此同時,因應股東之不同需求,股權項下之投票權、收益權等能否分離行使的問題也漸次引起重視。〔39〕例如參見李安安:《股份投票權與收益權的分離及其法律規制》,載《比較法研究》2016 年第4 期。此外,新近諸多研究也關注到金融交易領域的股權利益分離問題。〔40〕例如參見張艷:《認股期權新應用的法律規制——以市場化科創貸款的風險抵補為視角》,載《金融法苑》2019 年總第100輯。See Xu Ke, Research on the Separation of Shareholder Interests in Derivatives Area and Its Regulation in China, 7 China Legal Science 110 (2019).
因此,無論是共有股權之分割還是股權繼承,乃至股權轉讓、股權贈與、隱名出資情形下之顯名、股權出質情形下之質權實現等股權變動問題,秉持股權利益分離的視角,興許能發現皆無一例外地涉及有限責任公司股權利益之二元分解。一方面,股東與公司以外的當事人可根據意定條件或法定事由實現股權財產利益的讓渡;另一方面,公司意思形成將成為股權人身利益變動的必經程序。繼而,盡管當事人亦可能主動作出股權利益分離的安排,但股權變動將更多地呈現出法理分離,即可能因為立法或司法上的利益配置及利益衡量而呈現分離。〔41〕參見周游:《股權的利益結構及其分離實現機理》,載《北方法學》2018 年第3 期。在這種法理分離的背景下,股權變動的制度設計側重保護股權財產利益的實現不因公司人合性而受到影響。
在捆綁式股權利益結構下,公司與相對人之間往往存在利益沖突關系,制度設置需要在公司及相對人之間作出利益衡量,因而股東的利益需求在其中并未受到充分重視。在這樣的結構下,制度將法律正義過分寄望于司法過程,這使得法院在法律運行整個過程中負擔過重,對法官的能力與素質也是極大考驗,從而可能引起司法過度干預、司法裁判不一等諸多問題。問題之癥結在于制度未能適時對當事人之利益進行理性配置,也未對當事人所作之利益配置予以必要的容忍乃至認可。總之,捆綁式股權利益結構在本質上仍是對公司內外部法律關系存在較大的偏差理解(參見表1)。

表1 捆綁式股權利益結構的保護策略
相比之下,股權利益分離視角下的保護策略更注重利益配置,以盡可能防止利益發生沖突,繼而減少過分運用利益衡量可能帶來的不確定性。利益優化配置往往在主體意思自治或者法律所設置的衡平機制中進行,這不僅要明確利益的內容,厘定利益結構的基本框架與界限,還要識別處于不同法律關系中利益的實現方式,并通過法律原則及法價值判斷明確其合法性要件。由此,制度設置在保護公司人合性的同時并不會影響相對人利益的實現,反之亦然。同時,股東的利益也因為經過二元分解而實現最優化(參見表2)。

表2 股權利益分離視角下的保護策略
(二)涉及共有之公司法規則構建
如前所述,我國公司法沒有對股權共有作出規定,對于夫妻關系情形下的股權享有與行使問題更是只字未提。這的確涉及婚姻法、物權法之調整范圍,但民事法律規則難以回應股權共有狀態究竟會對公司治理產生何種影響。對此,公司法有必要予以回應。
首先是股權共有之客體有待厘清。按照《民法典》第308 條、第1062 條的規定,夫妻之財產共有為共同共有。那么,這是否意味著股東之配偶可不分份額地共同享有股權,甚至連股東資格也可共享?日本法律界較早將股權共有視為一種準共有形態,以區別于對所有權的單純共有。〔42〕山田泰彥「株式の共同相続と相続株主の株主権」早稲田法學69 巻4 號(1994 年)179 頁參照。然而,在沒有特殊規定之情形下,準共有通常適用共有的一般規定,這依然沒有跳出財產共有之理論框架。故而股權共有人所“共有”的客體問題顯得極為關鍵。按照股權利益分離的邏輯,股權共有的客體只能是股權的財產利益,無論是因離婚還是因死亡而解除共有關系所引致之分割,亦僅限于此。因而股權人身利益之享有仍需經過公司意思形成程序,這表明股東資格并不是共有的客體。
繼而,公司法相關規則構建之重點是明確股權共有與公司治理之間的關系。股權之財產利益可由夫妻共同共有,這也屬于《民法典》第1062 條規定的“投資的收益”之范圍。然而,共有人無法同時享有股權的人身利益,故而在只有夫妻一方登記為股東的情形下不可能兩人都取得股東資格。因此,在通常情況下,只有具備股東身份的丈夫或妻子方能向公司主張權利。那么,配偶之意愿是否就完全不需考慮呢?也不盡然,但前提是公司法需要構建相對完善的股權共有制度。省察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的相關實踐,共有人應當約定一人為權利行使者,并將這一約定通知公司,否則公司有權拒絕共有人行使股東權利。〔43〕例如我國臺灣地區“公司法”在股份有限公司一章中規定,股份為數人共有者,其共有人應推定一人行使股東之權利;在日本,除非公司認可,股權共有人必須約定一人為該股權之行使權利人,并將其姓名或名稱通知公司,否則不得行使股東權利。參見我國臺灣地區“公司法”第160 條、日本『會社法』第106 條。至于如何確定權利行使者,則由共有人協商一致,在不能達成一致意見時采取表決方式確定。〔44〕例如在日本,有判決認為共有人應就指定權利行使者達成事前協議,或經共有人所持股權的過半數通過。「総會決議存否確認請求控訴、同附帯控訴事件」,日本大阪高裁平成20 年(ネ)1758、1961 號;宮鳥司「共同相続株式の権利行使者の指定と事前協議の要否」法學研究:法律·政治·社會84 巻10 號(2011 年)89-99 頁參照。在此基礎上,諸如表決權分割行使或不統一行使等相關規則也可加以明確。〔45〕例如持有公司10%表決權的某一股東,可將其中5%投贊成票,將另外5%投反對票。這種策略選擇亦為股權利益分離之一種體現,對于股權共有問題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通常認為只要在股權信托、股權共有等特殊場合才能允許表決權分割行使和不統一行使。參見前注〔31〕,劉連煜書,第380 頁;我國臺灣地區“公司法”第181 條; 江頭憲治郎『株式會社法』(有斐閣,2015 年)339 頁;日本『會社法』第313 條參照。據此,我國公司法未來修訂時可以考慮在股東名冊規則中細化共有之內容,包括夫妻關系在內的共有關系可以作為備注事項記載于股東名冊中。〔46〕例如因繼承形成的共有關系。在實踐中,因為繼承人眾多而使得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人數超過《公司法》規定之限制的案例并不少見。有判決認為,即便股東人數違反法律規定,也屬行政法調整范疇,當然不能作為原告要求確認協議無效的法定理由。這表明當事人完全可以通過合同實現股權共有。參見“孫某某與賈某某股權轉讓糾紛案”,甘肅省張掖市甘州區人民法院(2010)甘民初字第801 號民事判決書。與之相關的股東權利行使規則也可予以明確。
(三)涉及繼承之公司法規則改進
如前所述,我國《公司法》第75 條的本意是只對股東資格的繼承作出規定,至于股權所對應的財產份額應如何處置則由民法調整。然而,由于該規定過于簡略,加之股權利益結構之捆綁處理,從而導致前述法律適用存在疑惑與困難,公司法有必要作出相應修改。
一方面,股東資格繼承之說法是否準確值得討論。繼承人原則上可直接繼承股東資格之規定仍是對股權人身利益的核心問題欠缺充分考量。實際上,繼承人并無當然取得股東資格之現實可能,即便是按照《公司法》第75 條的規定,繼承人充其量獲得請求公司確認其股東資格并變更股東名冊及公司章程、工商登記的權利,只有完成相關程序,才能真正取得股東資格。故而,股權人身利益并不存在繼承的問題,其仍需經過公司意思形成程序方能實現變動。在日本,非公開的股份有限公司可在章程中規定,經股東大會決議,請求因繼承而獲得轉讓受限股份的繼承人向公司出售其股份,而當公司依此合意方式不能實現回購股份時,公司還可依章程規定強制取得該股份,從而維護公司的人合性。〔47〕此外,在持份公司場合,繼承人如何繼承股東出資份額的規則完全交由公司章程進行安排,在日本法上并無當然獲得股東資格之一般規定。日本『會社法』第162、174-177、608 條參照。我國臺灣地區“公司法”在有限公司一章中并沒有規定與繼承相關的內容,學界一般認為應類推適用股權轉讓之規定。〔48〕參見廖大穎:《公司法原論》,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版,第510 頁。這也主要是為了解決股權的人身利益問題。與股權相關的繼承問題必然涉及股權變動,為維護公司人合性,繼承人能否取得股東資格應當經過公司及其他股東的認可。
另一方面,在因繼承引起夫妻共有財產的分割而導致股權變動之情形下,對共有與繼承兩種法律關系理應加以區分。首先,被繼承股東之配偶原則上取得股東資格是因為繼承而非共有,故其只能當然取得該部分所對應的股權比例。其次,法律應明確配偶所獲得“分出的一半”指的是股權之財產利益,這一利益的取得原因是自然人股東死亡導致夫妻共有關系終止而進行的分割,而非基于繼承關系之取得,故其所對應的股權之處理應當適用股權對外轉讓的規則。由此,公司章程即便規定股東資格不得繼承,那么該規定對“分出的一半”所對應的股權而言并不適用。最后,公司法未來修訂時可以辯證地吸收《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解釋(一)》第73 條的規定,以避免在婚姻法中回應公司人合性不甚協調的制度安排。一旦明晰在自然人股東死亡后其配偶可能處于共有與繼承兩種法律關系,法律也可分別回應。
此外,依循股權利益分離之邏輯,股權之贈與(包括遺贈)情形下如何兼顧公司人合性以及其他股東能否行使優先購買權之難題也有望得以解決。〔49〕參見前注〔16〕提及的案件。股東能夠贈與或遺贈的客體僅僅是股權之財產利益,這也與《民法典》第657 條、第1133 條有關贈與及遺贈的客體是“個人財產”之規定相符。至于受贈人或受遺贈人能否取得股東資格,仍需經過公司意思形成程序。不過,此時其他股東行使優先購買權應如何確定“同等條件”的確值得探討,畢竟在此情形下并無預先確定的股權價格。有鑒于此,司法實踐宜首先尊重當事人之協商議價,亦可根據當事人之意愿采取第三方評估方式確定價格。一旦其他股東不同意以依法確定的價格購買股權,那么受贈人或受遺贈人將獲得股權,并成為公司股東;而若有股東同意購買,則其支付的股權價金將歸屬于受贈人或受遺贈人,這既不妨礙贈與或遺贈目的的實現,也可維護公司人合性。
五、結語:重思有限公司人合性
在面對一個兼涉公司法、婚姻法及繼承法的糾紛時,若以《公司法》第75 條以及《公司法解釋(四)》第16 條的規定為依據,徑行認為一旦涉及繼承問題則不適用優先購買權之規定,表面上似乎是將其視為一個公司法問題看待,實則是以捆綁式的處理策略將理應區分的不同法律關系混為一談。有學者認為,夫妻內部關系首先應考慮親屬法的特殊性,而不按照物權法等財產法的規則確定夫妻間財產的歸屬。〔50〕同前注〔15〕,龍俊文。其較好地解決了親屬法與財產法的關系。至于親屬法與公司法乃至整個商事法之間應當如何協調,夫妻股權共有與繼承的問題可能僅僅是其中的一個面向。中國傳統文化蘊含“人命關天”“死者為大”的淳樸觀念,意在彰顯對逝者的尊重與懷念。〔51〕參見楊仁壽:《法學方法論》(第2 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 年版,第7 頁。然而,法律人在面對這樣的淳樸觀念時,可能仍需立足于明晰當事人法律關系之基礎,真正達致定分止爭的效果。在面對夫妻股權與繼承及由此產生的股東資格確認糾紛時,究竟是人身問題抑或財產問題理應首先得到回應。
公司人合性是處理夫妻股權共有與繼承問題時無法回避的核心命題,也是構建有限公司規則體系時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52〕盡管本文聚焦于有限公司場合,但并不否認股份公司亦存在需要兼顧人合性之可能,在此不贅。相關研究可參見周游:《公司法語境下決議與協議之界分》,載《政法論壇》2019 年第5 期。然而,何為人合性,以及在中國語境下強調公司人合性又有何特殊意義,尤需進一步闡釋。德國公司法明確區分人合公司與資合公司兩種類型,其區分標準是公司以股東個人信用抑或以資本信用為其基礎。〔53〕參見甘培忠、周淳、周游:《企業與公司法學》(第10 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 年版,第119 頁。按照德國法的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盡管呈現一定程度的人合性特質,但歸根到底屬于資合公司。〔54〕同前注〔11〕,托馬斯·萊塞爾、呂迪格·法伊爾書,第4 頁。只是為了突出有限責任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的區別,有限責任公司的組織性文件被稱為“公司合同”(Gesellschaftsvertrag),這和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的規定類似,以彰顯有限責任公司的人合性色彩;而股份有限公司的組織性文件被稱為“Satzung”,即公司章程。〔55〕在德國的有限責任公司場合,盡管法律使用“公司合同”之稱謂,但基于團體法上的考慮也可將其稱為章程。當然,從公司合同的全部內容來看,它不必然具有章程的特性。參見[德]格茨·懷克、[德]克里斯蒂娜·溫德比西勒:《德國公司法》(第21 版),殷盛譯,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第297 頁、第401 頁。所謂“公司合同”在一定程度上與英國法的立場類似。根據英國《2006 年公司法》第33 條的規定,公司章程對公司及其成員具有相同的約束力,如同公司和每個成員之間存在遵守那些條款的契約。〔56〕有學者進一步總結指出,根據普通法判例,公司章程實際上創設了四個方面的法律關系:第一,公司章程在股東和股東之間創設了一個合同;第二,公司章程在股東和公司之間創設了一個合同;第三,公司章程沒有在股東或公司與第三人之間創設合同;第四,依據公司章程而創設的合同。同前注〔32〕,葛偉軍譯注書,第29-30 頁。美國學者吉爾森更極端地指出,調整非公開公司的法律可能根本不屬于公司法范疇,將其視為合同法之特別適用更妥當。〔57〕See Ronald J. Gilson, Separation and the Function of Corporation Law, 2 Berkeley Business Law Journal 141, 152 (2005).應當指出,中國的有限公司形式盡管借鑒了德國的做法,但自其濫觴之時就內含豐富的中國元素。其一,從其表征看,我國的有限公司并不純然是資合公司,其所蘊含的人合性特征較為突出,尤其是在實行注冊資本認繳制之后,資本信用的色彩更是被進一步淡化。〔58〕相比之下,德國有限責任公司仍堅守最低注冊資本額規則。根據德國《有限責任公司法》第5 條的規定,公司注冊資本必須至少達到2.5 萬歐元。當然,其第5a 條亦規定了一種例外,在此不贅。其二,我國自1946 年引入有限公司形式的初衷并非因應中小投資者之創業需求,而是試圖以此強化經濟統制,發展國營事業和走計劃經濟的道路;至于1993 年《公司法》設置的有限責任公司形式實際上也主要是為國企改革服務的產物。〔59〕參見方流芳:《試解薛福成和柯比的中國公司之迷——解讀1946 年和1993 年公司法的國企情結》,載梁治平主編:《法治在中國:制度、話語與實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年版,第285-286 頁。相比之下,中國的有限責任公司更顯著地呈現出公司之非契約性色彩,在迎合國家需求的同時更需強化公司規則之程式要求。
由此,不難發現日本學者前田庸的觀點對于省察中國的有限公司本質之啟發意義:“公司人合性實則不是指股東之間的合意,而是強調公司對股東個性(即誰是股東)的重視。”〔60〕前田庸『會社法入門』(有斐閣,2009 年)14 頁參照。可以說,比起德國的有限責任公司(GmbH)和美國的有限責任公司(LLC),我國的有限責任公司具有顯著的本土特色。與域外慣常做法不同,我國法將有限責任公司作為“普通公司”,盡管該立法模式有其弊病,但究其淵源則不難發現其背后之本土邏輯。故而在處理諸如夫妻股權共有與繼承問題時,面對這樣一種具有鮮明特色的公司形式,理應更加注重對其人合性之維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