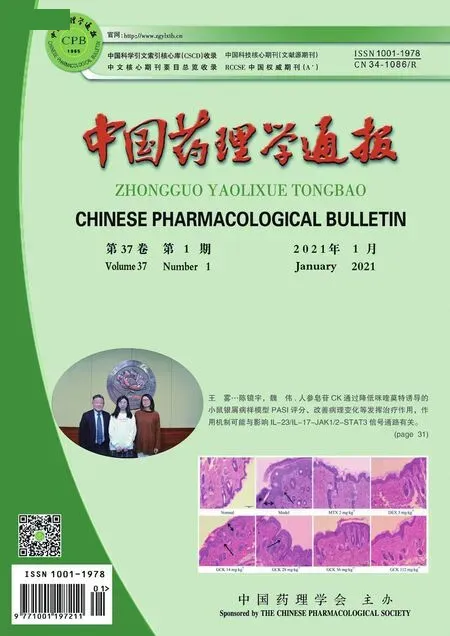黑色素聚集激素與抑郁癥關(guān)系的研究進(jìn)展
努爾乎瑪爾·庫爾班,崔素穎,張永鶴
(北京大學(xué)基礎(chǔ)醫(yī)學(xué)院藥理學(xué)系,北京 100191)
抑郁癥是以顯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快感缺失為主要臨床特征的一類心境障礙,嚴(yán)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zhì)量[1]。世界衛(wèi)生組織最新調(diào)研報(bào)告顯示,在全球范圍內(nèi),超過3億人患有抑郁癥,相當(dāng)于世界人口的4.4%[2]。抑郁癥是世界各地的首要致殘?jiān)颍莾H次于心血管疾病造成全球疾病負(fù)擔(dān)的重大因素之一。抑郁癥的神經(jīng)生物學(xué)和藥理學(xué)研究始于20世紀(jì)50年代,關(guān)于其發(fā)病機(jī)制有多種假說,如單胺耗竭、突觸可塑性、神經(jīng)發(fā)生、神經(jīng)炎癥、能量代謝和谷氨酸假說等[2]。但由于抑郁癥臨床表現(xiàn)、病因、病程的復(fù)雜性,無法用現(xiàn)有的假說機(jī)制詮釋該病。近年來,隨著神經(jīng)生物學(xué)和藥理學(xué)研究技術(shù)的進(jìn)步,對(duì)抑郁癥發(fā)病機(jī)制有了新認(rèn)識(shí),其中有關(guān)黑色素聚集激素(melanin concentrating hormone,MCH)與抑郁癥的相關(guān)性研究及以MCH系統(tǒng)為靶點(diǎn)的新型抗抑郁藥的研發(fā)備受關(guān)注。
1 黑色素聚集激素概述
MCH是由19個(gè)氨基酸構(gòu)成的高度保守的環(huán)形神經(jīng)肽,其氨基酸序列為Asp-Phe-Asp-Met-Leu-Arg-Cys-Met-Leu-Gly-Arg-Val-Tyr-Arg-Pro-Cys-Trp-Gln-Val。MCH最初在硬骨魚類中發(fā)現(xiàn),是一種與皮膚色素沉著有關(guān)的垂體分泌肽。MCH參與復(fù)雜的下丘腦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信號(hào)傳導(dǎo),整合內(nèi)源性和外源性信息,調(diào)節(jié)多種神經(jīng)生理功能,如情緒、攝食行為、睡眠-覺醒周期、學(xué)習(xí)記憶和能量平衡[3]。研究人員通過放射免疫學(xué)、免疫組織化學(xué)等研究方法,證實(shí)大鼠的MCH能神經(jīng)元主要分布于外側(cè)下丘腦及未定帶,并投射至整個(gè)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包括前額葉皮層、海馬、藍(lán)斑核、中縫背核和腹外側(cè)視前區(qū)等[4-5],見Tab 1。

Tab 1 Projections of MCH-containing neurons of rats
MCH通過作用于兩種G蛋白偶聯(lián)受體MCH-R1和MCH-R2發(fā)揮其生物學(xué)作用。1999年幾個(gè)實(shí)驗(yàn)室同時(shí)鑒定了一種稱為SLC-1(GPR24)的孤兒G蛋白偶聯(lián)受體,后被命名為MCH-R1[6]。MCH-R1在所有哺乳動(dòng)物中都有表達(dá),在嚙齒動(dòng)物和人類之間的同源性超過90%。MCH-R1廣泛分布于整個(gè)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大量表達(dá)于下丘腦腹內(nèi)側(cè)核、海馬、杏仁核、伏隔核殼部、中縫背核和藍(lán)斑核等腦區(qū),提示MCH-R1可能參與攝食、情緒、認(rèn)知、睡眠-覺醒行為的調(diào)節(jié)[7]。此外,MCH-R1在腸道、淋巴細(xì)胞和脂肪細(xì)胞等外周組織中也有表達(dá),但在人和大鼠外周組織中檢測(cè)到的MCH-R1 mRNA水平遠(yuǎn)低于大腦[6],提示MCH/MCH-R1系統(tǒng)廣泛參與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以及外周的生理功能,但是在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可能發(fā)揮更為主要的作用。
另一個(gè)受體MCH-R2最初是利用電子數(shù)據(jù)挖掘技術(shù),在人類基因中發(fā)現(xiàn)并鑒定的。MCH-R2與Gq蛋白偶聯(lián),激活Gq蛋白下游的信號(hào)傳導(dǎo)通路,興奮神經(jīng)元[8]。已在人、狗、雪貂等動(dòng)物中檢測(cè)到MCH-R2蛋白,但在嚙齒類動(dòng)物中尚未發(fā)現(xiàn)其功能性表達(dá)。人類MCH-R1與MCH-R2僅有38%的序列同源性。由于缺乏MCH-R2受體相關(guān)的動(dòng)物模型,MCH-R2的功能尚不清楚,有待于后續(xù)研究[9]。
2 黑色素聚集激素與抑郁癥
盡管早期關(guān)于MCH能神經(jīng)元投射以及MCH-R1受體分布的研究,提示MCH可能參與情緒調(diào)控,但是MCH是否直接參與抑郁癥相關(guān)的情感障礙一直缺乏證據(jù)[3]。而近幾年的神經(jīng)生物學(xué)、藥理學(xué)臨床前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直接證據(jù)。這些研究表明,在大、小鼠拮抗MCH-R1或敲除Mchr1基因可能誘導(dǎo)動(dòng)物產(chǎn)生抗抑郁樣效應(yīng)[10],并且其作用機(jī)制可能有別于經(jīng)典抗抑郁藥。盡管許多研究已證實(shí)MCH/MCH-R1系統(tǒng)參與抑郁樣行為調(diào)控,但目前對(duì)于這一調(diào)控所涉及的神經(jīng)環(huán)路仍知之甚少。近年來,MCH參與抑郁癥的作用機(jī)制研究主要聚焦在兩個(gè)方面。(1)MCH通過抑制中縫背核、藍(lán)斑核等腦區(qū)的單胺能神經(jīng)遞質(zhì)功能直接參與抑郁樣行為調(diào)節(jié);(2)通過調(diào)控睡眠-覺醒間接參與抑郁樣行為調(diào)節(jié)(Fig 1)。
2.1 MCH/MCHR1系統(tǒng)直接參與抑郁樣行為調(diào)節(jié)機(jī)制由于藍(lán)斑核的去甲腎上腺素能神經(jīng)元、中縫背核的5-羥色胺能神經(jīng)元和伏隔核的多巴胺能神經(jīng)元在抑郁癥的神經(jīng)生物學(xué)機(jī)制中均發(fā)揮重要的作用,因此,多數(shù)研究集中在了這些核團(tuán)中的MCH/MCH-R1系統(tǒng)參與抑郁癥的形成及其作為抗抑郁作用靶點(diǎn)或靶系統(tǒng)的機(jī)制方面。
2.1.1藍(lán)斑核的MCH能系統(tǒng)與抑郁癥 藍(lán)斑核位于腦橋前背部,是合成去甲腎上腺素的主要核團(tuán),在應(yīng)激反應(yīng)、抑郁樣行為調(diào)節(jié)及快速眼動(dòng)睡眠(rapid eye movement sleep,REMS)的調(diào)控中起重要作用。藍(lán)斑核的去甲腎上腺素能神經(jīng)元也與抑郁癥的調(diào)控關(guān)系密切。去甲腎上腺素再攝取抑制劑是治療抑郁癥的一線藥物之一,可顯著增強(qiáng)大腦去甲腎上腺素信號(hào)傳導(dǎo)。研究表明[11],在大鼠藍(lán)斑核微量注射MCH使前額葉皮層去甲腎上腺素水平顯著降低,并且誘導(dǎo)大鼠出現(xiàn)抑郁樣行為,如在強(qiáng)迫游泳實(shí)驗(yàn)中不動(dòng)時(shí)間顯著增加,攀爬或游泳時(shí)間減少,在糖水偏好實(shí)驗(yàn)中對(duì)糖水的偏愛降低;而在藍(lán)斑核內(nèi)預(yù)先注射MCH-R1拮抗劑SNAP-94847可顯著逆轉(zhuǎn)MCH誘導(dǎo)的大鼠抑郁樣行為[3]。
2.1.2中縫背核的MCH能系統(tǒng)與抑郁癥 中縫背核位于中腦導(dǎo)水管腹側(cè),存在大量的5-羥色胺能神經(jīng)元,并廣泛投射至整個(gè)大腦,參與多種生理功能調(diào)節(jié),如情緒、焦慮、獎(jiǎng)賞與睡眠-覺醒等[12]。臨床一線抗抑郁藥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RI)主要是基于增強(qiáng)中樞的5-羥色胺能神經(jīng)元傳導(dǎo)而實(shí)現(xiàn)抗抑郁作用。中縫背核的5-羥色胺能神經(jīng)元接受MCH能抑制性神經(jīng)纖維投射。研究表明在大鼠中縫背核微量注射MCH,在強(qiáng)迫游泳實(shí)驗(yàn)中出現(xiàn)抑郁樣行為,如不動(dòng)時(shí)間增加,攀爬或游泳行為減少等。SSRI類藥物氟西汀和MCH-R1拮抗劑可有效逆轉(zhuǎn)此抑郁樣行為[13-14]。在大鼠中縫背核中微量注射MCH下調(diào)中縫背核5-羥色胺水平,這種抑制效應(yīng)被認(rèn)為是誘導(dǎo)大鼠出現(xiàn)抑郁樣行為的原因[15]。
2.1.3伏隔核的MCH能系統(tǒng)與抑郁癥 伏隔核位于基底核與邊緣系統(tǒng)交界處。有大量實(shí)驗(yàn)證實(shí)伏隔核參與動(dòng)機(jī)、快樂、成癮和獎(jiǎng)賞的調(diào)控[16]。快感缺失、動(dòng)機(jī)減退和焦慮是人類抑郁狀態(tài)的主要表現(xiàn)。MCH-R1在伏隔核中也密集表達(dá)。有研究表明,側(cè)腦室注射MCH降低伏隔核中多巴胺代謝產(chǎn)物3,4-二羥基苯乙酸(3,4-dihydroxyphenylacetic acid,DOPAC)水平。與野生型小鼠相比,Mchr1基因敲除小鼠中腦邊緣多巴胺受體表達(dá)上調(diào),伏隔核殼部多巴胺D1和D2受體的表達(dá)增加[17]。以上結(jié)果提示,MCH對(duì)伏隔核多巴胺系統(tǒng)可能有負(fù)性調(diào)節(jié)作用。值得關(guān)注的是,在大鼠伏隔核定位注射MCH顯著減少大鼠強(qiáng)迫游泳實(shí)驗(yàn)中的不動(dòng)時(shí)間,誘導(dǎo)抑郁樣行為。而用MCH-R1拮抗劑可有效地逆轉(zhuǎn)該抑郁樣行為[18]。這些發(fā)現(xiàn)提示,伏隔核中的MCH系統(tǒng)與抑郁癥的發(fā)展密切相關(guān)。

Fig 1 Role of MCH/MCHR1 system in pathophysiology of depression
2.1.4MCH-R1拮抗劑與抑郁癥 大量藥理學(xué)研究表明,在嚙齒類動(dòng)物中急性或慢性予以MCH-R1拮抗劑可直接引起抗抑郁樣和抗焦慮樣作用。選擇性MCH-R1拮抗劑SNAP-7941具有抗抑郁樣作用,顯著降低強(qiáng)迫游泳中的不動(dòng)時(shí)間,其功效與氟西汀相似。隨后,另有幾種MCH-R1拮抗劑ATC0065、ATC0175和GW803430均在大鼠強(qiáng)迫游泳實(shí)驗(yàn)中表現(xiàn)出抗抑郁樣效應(yīng)[6]。另一種選擇性MCH-R1拮抗劑SNAP-94847則被報(bào)道能顯著逆轉(zhuǎn)慢性應(yīng)激造成的糖水偏好實(shí)驗(yàn)中的快感缺乏現(xiàn)象。這些研究結(jié)果提示,MCH-R1拮抗劑在急性及慢性抑郁模型中均有效。除了藥理學(xué)研究,遺傳學(xué)研究也進(jìn)一步說明了MCH能系統(tǒng)與抑郁樣行為的聯(lián)系。研究表明,在慢性應(yīng)激抑郁癥模型中,海馬的MCH-R1表達(dá)水平顯著升高,且這一變化可被SSRI類藥物氟西汀逆轉(zhuǎn)[10]。Mchr1基因敲除小鼠與正常小鼠相比,強(qiáng)迫游泳的不動(dòng)時(shí)間顯著減少,攀爬行為顯著增多,表現(xiàn)出抗抑郁樣行為特征[6]。最近一項(xiàng)研究表明,MCH合成前體(prepro-melanin concentrating hormone,ppMCH)高表達(dá)以及MCH-R1的低表達(dá)可作為抑郁癥嚴(yán)重程度的生物標(biāo)記物,再次強(qiáng)調(diào)了MCH能系統(tǒng)在抑郁癥病生理學(xué)機(jī)制中的重要性[19]。
2.2 MCH/MCH-R1系統(tǒng)間接參與抑郁樣行為調(diào)節(jié)機(jī)制在21世紀(jì)初,MCH引起了睡眠領(lǐng)域的關(guān)注,被認(rèn)為是一種新型“內(nèi)源性促眠因子”。研究發(fā)現(xiàn)[9],在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腦室注射MCH,延長非快速眼動(dòng)睡眠(non-rapid eye movement sleep,NREMS)時(shí)間和REMS時(shí)間,并且對(duì)REMS的影響尤其顯著。在大鼠側(cè)腦室注射MCH,REMS時(shí)間增加一倍,同時(shí)REMS潛伏期縮短。神經(jīng)組化研究表明,MCH能神經(jīng)元的c-Fos蛋白表達(dá)在REMS期間增加[20],睡眠剝奪使大鼠MCH能神經(jīng)元c-Fos表達(dá)減少。大鼠REMS剝奪會(huì)導(dǎo)致REMS反彈,并伴隨MCH神經(jīng)元過度激活[21]。電生理研究顯示MCH能神經(jīng)元在覺醒期間放電頻率最低,在NREMS期間放電頻率略有增加而在REMS期間活性達(dá)到最高,提示該神經(jīng)元在REMS期間最為活躍[9]。近年來,得益于光遺傳學(xué)實(shí)驗(yàn)技術(shù)的發(fā)展,研究人員可選擇性操控MCH能神經(jīng)元的活性,借此MCH能系統(tǒng)與睡眠關(guān)系的相關(guān)研究取得了重要進(jìn)展。采用光遺傳實(shí)驗(yàn)技術(shù),激活大鼠MCH神經(jīng)元可顯著縮短睡眠潛伏期、減少覺醒,并且增加夜間REMS及NREMS,而在白天僅增加了REMS[22]。但在后來的研究中發(fā)現(xiàn)了一些不同的結(jié)果,激活MCH神經(jīng)元增加了REMS,但并沒有增加NREMS,反而NREMS略有減少[23]。在NREM睡眠期間,激活MCH神經(jīng)元使進(jìn)入REMS的頻率增加一倍,而在REMS期間激活MCH神經(jīng)元延長REMS的持續(xù)時(shí)間。NREMS的減少可能歸因于REMS轉(zhuǎn)換的頻率增加,從而導(dǎo)致NREM時(shí)間縮短[23]。化學(xué)遺傳學(xué)研究表明慢波睡眠(slow wave sleep,SWS)的超正節(jié)律與MCH神經(jīng)元的活性有顯著的關(guān)系,MCH能神經(jīng)元被抑制時(shí),SWS平均持續(xù)時(shí)間顯著延長。相反,激活MCH能神經(jīng)元時(shí)SWS時(shí)間明顯縮短,進(jìn)一步說明MCH神經(jīng)元不僅參與REMS的發(fā)生和調(diào)節(jié),同時(shí)也可能參與SWS的終止,從而增加SWS向REMS的過渡,增加REMS[24]。
MCH能神經(jīng)元向藍(lán)斑核、中縫背核、中腦導(dǎo)水管周圍灰質(zhì)腹外側(cè)區(qū)和腦橋外側(cè)被蓋區(qū)發(fā)送密集投射,并且在這些投射部位有大量Mchr1基因表達(dá)。這些區(qū)域與REMS的調(diào)節(jié)有關(guān)[25]。所有這些投射部位神經(jīng)元具有共同特征,即在清醒時(shí)活躍,進(jìn)入REMS后,會(huì)變得沉默,稱為REM-OFF神經(jīng)元。一般認(rèn)為,REM-Off神經(jīng)元在清醒時(shí)抑制REM-On神經(jīng)元的活動(dòng),但在REMS發(fā)生時(shí)停止放電。這些REM-On神經(jīng)元投射到REM-Off神經(jīng)元,形成一種REM-on/off回路[26]。考慮到MCH能神經(jīng)元投射至許多與睡眠-覺醒調(diào)節(jié)相關(guān)的腦區(qū),一系列研究采用在以上腦區(qū)定位注射MCH的方法探究MCH參與REMS調(diào)節(jié)的可能神經(jīng)環(huán)路。5-羥色胺能的中縫背核和去甲腎上腺素能的藍(lán)斑核在REMS的產(chǎn)生和抑郁癥的病理生理學(xué)機(jī)制均起重要作用。在中縫背核和藍(lán)斑核定位注射MCH可誘發(fā)REMS[13, 27],而注射MCH-R1拮抗劑或MCH抗體進(jìn)行免疫中和均可產(chǎn)生相反的作用[3, 14],表明MCH神經(jīng)元參與了REMS的發(fā)生和調(diào)節(jié)。
睡眠障礙,尤其是REMS行為異常,被認(rèn)為是抑郁癥的核心特征,并與其發(fā)病和持續(xù)性有關(guān)。大量研究表明,睡眠障礙癥狀并非繼發(fā)于抑郁癥,相反,它往往先于抑郁發(fā)作,而在抑郁發(fā)作后及緩解期也持續(xù)存在。NREMS障礙與REMS失調(diào)均與抑郁癥嚴(yán)重程度呈正相關(guān)[28]。抗抑郁藥對(duì)抑郁癥患者的睡眠結(jié)構(gòu)產(chǎn)生長久影響,總體上有改善抑郁癥患者睡眠障礙的趨勢(shì),大多數(shù)抗抑郁藥對(duì)REMS均有抑制作用。睡眠完全剝奪或選擇性REMS剝奪可以快速改善抑郁癥狀[29],再次強(qiáng)調(diào)REMS與抑郁癥的密切相關(guān)性。MCH對(duì)睡眠-覺醒的影響,如REMS潛伏期縮短、REMS增加、總SWS減少等均與抑郁癥患者睡眠特征相對(duì)應(yīng)[30]。目前主流的觀點(diǎn)認(rèn)為抑郁癥往往伴隨著MCH能神經(jīng)元的過度激活,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抑郁癥患者REMS過多現(xiàn)象。與之對(duì)應(yīng)的,拮抗MCH能系統(tǒng)則減少REMS,同時(shí)逆轉(zhuǎn)抑郁樣行為[29]。綜上所述,大量的研究已證實(shí),MCH在REMS的啟動(dòng)、維持中起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REMS的異常伴發(fā)于抑郁癥。因此,MCH能系統(tǒng)可能通過調(diào)控REMS間接參與抑郁癥的發(fā)生和發(fā)展,MCH能系統(tǒng)有望成為治療和預(yù)防抑郁癥伴發(fā)睡眠障礙的干預(yù)靶點(diǎn)。
上述神經(jīng)生物學(xué)和藥理學(xué)研究為抑郁癥的MCH能假說提供了有利的實(shí)驗(yàn)室依據(jù),初步探明MCH-R1拮抗劑在抑郁癥治療中的潛在用途,提示MCH-R1可能是治療抑郁癥的新靶點(diǎn)(Tab 2)。今后仍需要采用多種動(dòng)物模型及分子生物學(xué)研究方法,進(jìn)一步深入闡釋MCH能系統(tǒng)與抑郁樣行為之間的內(nèi)在關(guān)系。
3 小結(jié)與展望
總之,大量臨床前研究表明,MCH/MCH-R1系統(tǒng)可能與抑郁癥的病因?qū)W機(jī)制有關(guān),但相關(guān)的神經(jīng)解剖學(xué)通路和分子生物學(xué)研究相對(duì)缺乏,有待進(jìn)一步研究闡明。盡管如此,迄今為止的研究數(shù)據(jù)為MCH/MCH-R1系統(tǒng)是否可作為臨床治療抑郁癥的新靶點(diǎn)或靶系統(tǒng),提供了可借鑒的、具有潛在臨床應(yīng)用價(jià)值的參考依據(jù)。但關(guān)于MCH/MCH-R1系統(tǒng)參與抑郁形成機(jī)制及其臨床抗抑郁療效尚未得到充分證實(shí)。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將進(jìn)一步研究MCH/MCH-R1系統(tǒng)參與抑郁形成及其在抗抑郁治療中的作用機(jī)制的同時(shí),還需要把尋找更有效、更安全的MCH/MCH-R1系統(tǒng)抑制劑或MCH-R1拮抗劑作為臨床前研究重點(diǎn)。考慮到MCH/MCH-R1系統(tǒng)與抑郁癥之間相關(guān)機(jī)制的獨(dú)特性,MCH能系統(tǒng)的抑制劑或MCH-R1拮抗劑將有望成為克服現(xiàn)有抗抑郁藥不足的新型抗抑郁劑,并為抑郁癥的治療提供一種新的治療途徑和治療策略。

Tab 2 MCH/MCH-R1 system and its main effects on different brain reg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