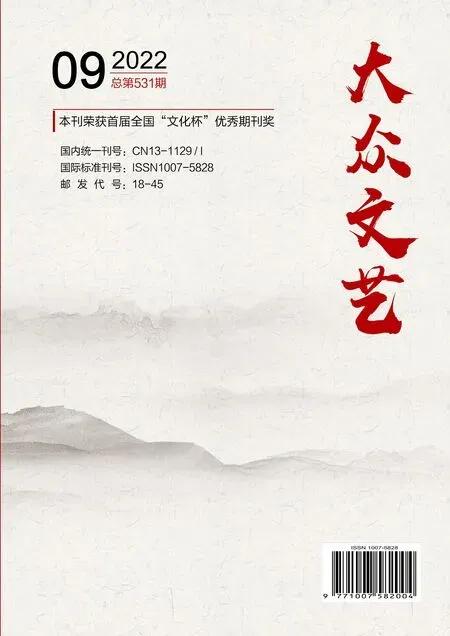翰墨飄香 音韻傳情
——論音樂與書法的內(nèi)在關(guān)系
周巧旻 (四川電視臺 610000)
一、追本溯源:音樂和書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眾所周知書法屬于視覺藝術(shù),音樂屬于聽覺藝術(shù),但兩者又同為中國文化精神的本體象征,有著美學共性。追溯歷史,中國早期藝術(shù)史的基本審美特征之一就是中國書法和音樂的融合。書法傳承著深厚的傳統(tǒng)文化內(nèi)涵和精神,禮樂文化也曾是中華文化的核心,他們在文化中相互交錯影響。歷代上的名人雅士對二者的關(guān)系都有過自己的理解和闡釋:唐代書家張懷瓘就曾說過:書法是“無聲之音”;明代的項穆把書法比為“如彼音樂,干戚羽旎”;西方的藝術(shù)家也曾提到“一切藝術(shù)到精微境界都要求逼近音樂”。當代鄭誦先先生從通感的角度把書法稱之為“看得見的音樂”。音樂與書法在發(fā)展中相互啟迪,素有草圣聞水潮之聲,而得草法之韻一說,書圣張旭在鼓吹之調(diào)之中頓悟狂草筆法的典故。
二、從構(gòu)成和表現(xiàn)形式來談音樂和書法的同質(zhì)性
書法的表現(xiàn)形式是借助于毛筆書寫不同的點和線作為具體表現(xiàn)的。書法家在創(chuàng)作時,用筆的疾馳、輕緩、厚重或枯潤與不同樂器的音色相對應性。音樂里有哆、來、咪、發(fā)、梭、拉、西、哆八個音符,其中每一個音符都帶有高低、輕重、緩急、長短等變化;書法中有著永字八法,每一個元素都帶有速度,猶樂之宮商五音也。音樂通過樂音的不同組合,諸如書法通過點線、行筆、和章法的構(gòu)建,組成節(jié)奏、旋律、和聲等,來抒發(fā)作者的藝術(shù)情感,渲染營造自己的意境。書法點畫形式豐富多變,豎如懸針垂露,點若高山墜石,橫似千里陣云……,正如不同的樂器演奏所發(fā)出的音色是各具特色,千變?nèi)f化的。書法的生命力在于線條,不同線條如同抽象出的音樂旋律,筆法又好比樂器演奏的指法、弓法與吹法等。如果說點給人的審美享受如同打擊樂或彈撥樂的話,那么線的美就好比絲竹管弦。著名書法家沃興華在《書法技法通論》里說到“線條越細越尖越快,音質(zhì)就越高,書法的情感就越亢奮激昂;線條越粗越鈍越慢,音質(zhì)就越底,書法的情感就越深沉渾厚”。書法中線條的粗細之美可對應于音調(diào)高低不同樂器所帶來的不同感受,書法中粗的線如若單簧管和大提琴的音色,比較細的線好比短笛、長笛和小提琴。除了點和線之外,不得不提到就是章法。書法中的筆墨節(jié)奏和韻律大多就是通過章法體現(xiàn)。書法運用章法的謀篇布局、相避相形、相呼相應等,使作品跌宕起伏,如同音符在組合曲調(diào)時,通過重音、輕音、滑音、節(jié)拍,使之抑揚頓挫又和諧統(tǒng)一;一幅好的書法、一首動聽的樂曲必是章法嚴謹?shù)摹?/p>
三、書法和音樂在節(jié)奏和韻律上具有相通性
書法家的書寫速度隨著人的狀態(tài)和心境是不停發(fā)生變化的,而這種速度的變化遵守著與音樂的節(jié)奏相通的規(guī)律。英國人羅杰·弗萊說:“線的節(jié)奏是最引人注目的,應該占據(jù)中國藝術(shù)的首要地位”。節(jié)奏是貫穿音樂的靈魂,美國音樂家柏西·該丘斯說:“有了節(jié)奏,音樂才能產(chǎn)生豐富的生命力”。書法書寫速度上有緩急,節(jié)奏上有起伏,力度上有強弱,情感上有張弛,就如同音樂的韻律一樣富于變化。書法點畫的呼應關(guān)系主要通過筆勢的映帶來維系,一波三折的的用筆,酣暢淋漓的用墨,在快速連貫且有規(guī)律的書寫過程中就產(chǎn)生了波折起伏、逶迤相屬的節(jié)奏,如同音樂的一般。而音樂是通過音符的休止,各樂段之間的間歇和停頓來體現(xiàn)節(jié)奏。
四、音樂創(chuàng)作與書法藝術(shù)兩者兼具時間性和空間性的特性
從時空關(guān)系來說,音樂和書法都具有時間性和空間性的特性,但有所側(cè)重。書法是可視的藝術(shù)、它用毛筆在紙張等載體上的造型、布白、構(gòu)建章法,都體現(xiàn)了其空間特征。與此同時,創(chuàng)作書法的全程是也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起訖使轉(zhuǎn)、俯仰向背的節(jié)奏得以實現(xiàn)都以時間性為表現(xiàn),使書法藝術(shù)又兼具時間性特征。書法家沃興華認為書法“有了運動的感覺,就開始有了時間因素”。因此,我們說書法藝術(shù)是空間性與時間性兼?zhèn)涞乃囆g(shù)。音樂的時間性也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不斷運動展開的節(jié)奏和旋律中體現(xiàn)的,由于書法和音樂的運動節(jié)奏和韻律在精神內(nèi)核上是貫通的,那么通過運動表現(xiàn)和記錄的時間性也是貫通的。而音樂的空間感更加抽象,它由心理的空間維度來體現(xiàn)。音樂的所有要素音高、音程、力度、速度、音色、節(jié)奏均被記錄于二維平面并表現(xiàn)出來,演奏者讀取這些元素并加以表現(xiàn),因此對于聽眾與奏者來說接收到的藝術(shù)維度是不同的——聽眾接收到一維的音樂,奏者接收到二維的樂譜,但他們接收的又是同樣的音樂藝術(shù),兩者必統(tǒng)一于一個場景,即具備空間感的場景。音樂帶來的空間感是由聽覺引起的人思維上的共鳴與聯(lián)想產(chǎn)生的心理空間。
五、音樂與書法都是追求格調(diào)、氣韻的藝術(shù)
人們常說的書法格調(diào)是指在作品中表現(xiàn)出來的思想情操和美學品格,是藝術(shù)家文學修養(yǎng)、藝術(shù)造詣、審美情趣的總匯體現(xiàn)。藝術(shù)作品的格調(diào)有雅俗之分,從創(chuàng)作角度來看,格調(diào)是藝術(shù)家思想境界和藝術(shù)境界的最高體現(xiàn);從賞鑒的角度來看,它是藝術(shù)批評的重要標準之一。書法格調(diào)的形成,用三句話概括即:書法是“研”出來的;書法是“悟”出來的;書法是“養(yǎng)”出來的。同樣,音樂的高雅格調(diào)來自于音樂人的真情實感,來自于蘊藏在這真情實感中美好的意愿,以及生活中的日積月累和有感而發(fā)的藝術(shù)表達。
氣韻是中國藝術(shù)審美里最重要的標準,“氣韻生動”是《畫品》中書畫六法論之首,可見“氣韻”在書法藝術(shù)中占據(jù)重要位置。宗白華在《中國美學史中重要問題的初步探索》一文中談到:“氣韻,就是宇宙中鼓動萬物的‘氣’的節(jié)奏、和諧。繪畫書法有氣韻,就能給欣賞者一種音樂感”。書法的氣韻是書法的靈魂之所在,是書法家與書法作品與之間互相的感知交流,“氣”是一種流動的狀態(tài),一種生命的張力;“韻”從字面上來說是神韻也是韻味;書法所求的傳神之處即是心手和暢、氣韻生動,不僅是線條的諧和統(tǒng)一,更要求形神合一。書法之氣,有陰陽之氣,分為剛與柔;又有“內(nèi)氣”、“外氣”之分。“內(nèi)氣”指一字有氣勢韻味,從點畫調(diào)停和諧中來;“外氣”指字與字、行與行、整幅作品聯(lián)絡照應而言。書法的“氣”,在更多程度上表現(xiàn)為高級追求的,如“文人氣”、“金石氣”,次之的,則有“柔美之氣”、“陽剛之氣”,最不可取的則是“匠氣”、“俗氣”。再觀音樂,它由一根看不見、摸不著的“線”—“氣息”貫穿始終,它的巧妙應用,賦予作品生命。對于表奏者來說,一部音樂作品是否能打動人最重要的在于表奏者對音樂作品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內(nèi)在的藝術(shù)素養(yǎng),而不僅僅由純熟的表演技巧來決定。總言之,就是表奏者能否準確演繹出作品的“韻”來,讓“氣”和“韻”在音樂藝術(shù)中完美結(jié)合。
六、書法與音樂都能傳情達意并能引起觀者共鳴
黑格爾說過:音樂是心情的藝術(shù),直接針對心情;“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旎,謂之樂。”《禮記。樂記》上說的音樂,與書法也是一致的;書乃心畫也,流美者人也,欲書先欲舒懷抱,沉秘神采,從而“書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書。”這種邏輯推理如出一轍。可見書法家與音樂家對生活中所喚起的情感,都是通過各自特有藝術(shù)語言來抒發(fā)的。書法和音樂一樣,是通過線條、節(jié)奏來表現(xiàn)情感的。舒展的節(jié)奏常常表現(xiàn)平和、遼闊、優(yōu)美的情緒和意境,緊湊急促的節(jié)奏常常帶來緊張、活潑、興奮歡樂等不平靜的情緒。楷書也就是正書,相對體制嚴謹,跟交響樂的正式演奏有異曲同工之處;行書類似于行云流水的輕音樂,自由自在;隸書古拙質(zhì)樸如同一曲典雅的民樂合奏;狂草自然如搖滾樂般奔放激揚;篆書如同圓和、清寒、古雅的古箏、鼓與笛的完美合奏。
它們通過不同的介質(zhì),無一不展示著人類內(nèi)在的微妙情感色彩及心理狀態(tài),并喚起欣賞者的感情意象,如若親聞其聲,親見其形,從而獲得一種藝術(shù)美的享受。王羲之在惠風和暢的暮春寫就《蘭亭》,讀之如清風拂面令人神往;而顏真卿的《祭侄文稿》則表達了痛悼侄兒悲憤交加之感,引人傷懷。我們觀張旭、懷素作草,皆以醉酒進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狀態(tài),如親臨一場搖滾演唱會;文征明的小楷“歸去來辭”的情感又在貝多芬恬靜的“田園交響曲”中容易找到;凝聽琵琶獨奏“十面埋伏”如同夢里神游黃庭堅騰挪跌宕的草書;六一居士流暢婉轉(zhuǎn)的楷書《醉翁亭記》中所蘊含的雅士風流,似乎又能在小提琴世界名曲《G弦上的詠嘆調(diào)》中得到共鳴;而昌碩的金石之氣又讓我們夢回青銅時代,傾聽編鐘和著戰(zhàn)鼓奏出的黃鐘大呂之聲。當音樂與書法兩者相遇,充滿了生命的活力和律動感。
七、結(jié)語
書之有動靜、柔剛,猶樂之有曲折跌宕;書的結(jié)構(gòu)間架,猶樂之章節(jié)構(gòu)成也;書之有篆、隸、真、草,猶樂歌之風雅頌也;書家之有鐘、王、歐、褚、顏、柳、蘇、黃,猶樂章之有蕭韶、咸池、云門、八音也;翰墨飄香,音韻傳情,書法和音樂在藝術(shù)鏈上如同一對各自舞蹈著的姊妹,完美融合情感、心靈、天地萬物,一起律動發(fā)展,激發(fā)著人們的藝術(shù)生活熱情。在歷史的進程中,他們兩者之間互相融合又相互滲透,音樂中有書法,書法中有音樂,相互啟發(fā),擴大了各自的外延,豐富了內(nèi)容和形式,技可進乎道,藝可通乎神,在不斷探索借鑒的道路上,二者用節(jié)奏譜寫了新的華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