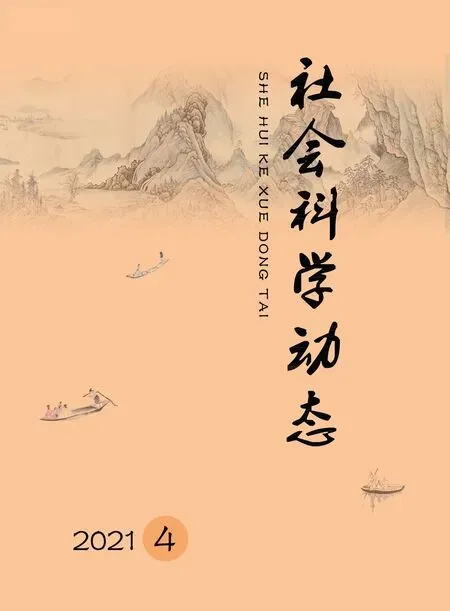“文化辯護”中國化的路徑探索
李亞龍
一、文化辯護的概述
上個世紀60 年代,美國爆發了許多社會運動。隨著多元文化運動的興起,各種文化激蕩沖突,“文化辯護”也在20 世紀中后期進入美國刑事司法領域。當然,“文化因素”在刑事案件中具有影響的判決,最早可以追溯到19 世紀后期。但是,現代意義上的“文化辯護”,最早出現在1985 年的People V. Kimura①案中,此案中檢察官使用了一個叫做“文化辯護”的新理論。次年,美國學者以“文化辯護”為主題,在《哈佛大學法學評論》上發文,“文化辯護”第一次在學界得到了系統性的闡述。②自此,司法實務界與理論學界,圍繞著文化辯護制度的設計、理論的建構,展開了持續性的討論。
(一) 文化辯護的概念
“文化辯護”是美國刑法中辯護理由的一種,“辯護理由”(Defenses) 的理論地位和功能大體相當于大陸法系中的“阻卻違法事由”或是我國刑法中的“排除犯罪事由”。但是,就范圍上來說比其他辯護理由廣泛得多。凡是被告人針對有罪指控而提出的證明自己無罪或者不應當被追究刑事責任的事實和理由,都屬于辯護理由。③英美刑法中的辯護理由,如正當化事由:正當防衛、緊急避險、警察圈套等;可寬恕事由:未成年、精神病、醉態、認識錯誤、受脅迫、受挑釁等,都被國人所熟識。但是,就“文化辯護”而言,或囿于其非正式辯護理由的地位,在我國刑法學界“出鏡甚少。”
美國刑法理論認為,一個人如果因遵循于自己的文化習慣,且對其行為的適當性具有真誠信念而違背法律,則不應該負全部的法律責任或不負法律責任,否則法律將是不公正的。④簡言之,在某些情況下,一個人的罪責可能會因他的文化背景而減少或免除。如此,所謂的“文化辯護” (Cultural Defense),即指在刑事法庭上以被告人的文化背景作為減免罪責因素的做法和理念。
(二) 文化辯護的現狀
就目前來說,“文化辯護”在美國還不是一個得到正式確認的積極辯護理由(Affirmative De-fense),且“關于文化辯護的判例法也還沒有很好地確立”⑤,以致于法官在采納文化辯護時顯得猶豫不決。但無礙于“文化辯護”非正式辯護理由地位,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美國州法院、聯邦法院都有了采納文化辯護的成功案例,而且,法院允許被告人在刑事訴訟的各階段提出文化證據,已經成為一種潮流。⑥甚至,早在1991 年聯邦法院的一項裁決中,就極大肯定了“文化辯護”的作用,并認為如果辯護律師沒有提出“文化辯護”,就可能構成無效的咨詢協助。⑦
總而言之,在現行制度下,即使沒有正式建立文化辯護制度,法院在評估罪責方面也越來越愿意接受文化證據,文化證據對刑事審判的結果也仍然產生重大影響。
(三) 文化辯護的發展
目前,文化辯護在實踐中的適用模式為“文化+(Culture-plus)”模式,即文化證據與其他正式辯護理由一并提出的辯護模式。⑧但是,把文化辯護作為獨立、正式的辯護理由的“獨立說”影響日隆,大有取代之勢。
堅持“文化+”模式的觀點認為,“文化+”的處理模式,也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考慮到了被告人特有的文化因素,使其結果符合了個體正義原則,沒必要再單列其作為獨立、正式的辯護理由。而且,假如把文化辯護作為一種正式辯護,會把庭審的焦點從個人罪責轉移到個人文化認同上⑨,因為此時,刑事訴訟的關鍵問題,將是移民被告的行為是否充分符合其原國籍國的文化規范,而不是被告是否確實具備了定罪所必需的犯罪條件。如此,過于耗費司法資源暫且不論,但把刑事司法制度推向不穩定、個體化司法體系,極有可能導致社會陷入無政府狀態。持“獨立說”的觀點則這樣反駁:其一,文化辯護的非正式辯護地位,只是在表面上推進了刑事司法制度對于文化多元化和個別化正義的追求,并無實際有效地阻止主流社會利用刑事司法系統壓制文化多樣性⑩;其二,雖然“文化+”模式,在結果上很可能確保所期望的公平結果,但從過程上看,此種模式是把亞文化證據與精神病、智識能力弱等等同看待,不能給予亞文化群體應有的尊重。正如Anh T. Lam 言,“雖然這種辯護有助于減輕被告的刑期,但精神病的判決在未來可能會對少數族裔被告造成恥辱和傷害。?而且,此種模式產生了一個詭異且并非毫無疑問的命題:亞文化會讓人發瘋?;其三,“文化+”模式存在太多的不確定性因素,因為非獨立模式使其缺乏正式的指導方針,文化證據適用于刑事法庭留給了法官過多的自由裁量權,以致于在最壞的情況下,審判的過程以及最后的判決都可能取決于法官或陪審團的個人偏見?;其四,基于聯邦政府作為亞文化群體監護人的保護義務,以及根據聯邦民族自決政策,應該為在法庭受審的亞文化群體成員設立正式的文化辯護。?最后,文化辯護作為正式、獨立的辯護理由,將減輕下級法院在審判時考量文化因素的擔憂,即擔心在量刑時考慮這些文化證據會被視為濫用自由裁量權而推翻判決。
二、文化辯護中國化的有益性分析
文化辯護,作為刑事法律對于“文化沖突”案件的一種應對策略,或存有弊病,但就適用效果而言,文化辯護更有助益。所以,文化辯護在司法中的運用,可以作為一種方略推及開來。
(一) 文化辯護的詰難及其澄清
文化辯護的反對者,大多是立于“國家主義”的考量,多從形式平等、社會治理、民族同化、刑法功能維護等角度闡述立場。而文化辯護的倡導者,更加側重“個人主義”的基本立場,多從實質平等、尊重維護多元文化、保護公民個人基本權利的角度對其詰難給予澄清。
1. 平等原則的背離及其澄清
平等原則是美國憲法的基本原則,在這個原則的指引下,任何人都共守同一個法律,任何人都不得逾越法律之上。而文化辯護的適用,使得亞文化群體的被告基于其文化背景受到了“優惠待遇”,違反了憲法的平等原則。此外,批評人士還斷言,這種不平等會削弱整個司法體系的權威,因為“在同一個國家政治體系中,為不同群體適用不同的法律準則太令人困惑”,如此,“個人和團體可以自行決定遵守哪些法律,法律將不再有任何確定性或可預測性”。?
但是,談及平等原則,主流文化群體的被告則是坐享決策者的“奢侈待遇”,因為其決定什么樣的行為違背法律,是根據主流文化的習慣制定的。主流文化群體可以繼續遵守熟悉的法律和文化規范,在自己的行為與社會要求之間取得平衡。?任何法律制度都是特定主流文化的產物,反應了多數人的規范、價值觀和做法,其并不能很好地兼顧亞文化群體的文化、習慣,也沒有考慮到他們能否理解、適應這一標準。如果不加區別的適用同樣標準的法律,本質而言,無非是傲慢的偏見在作怪。
亞文化群體,由于沒有足夠的政治權力在主流文化的立法層面發言,使得這些被告將在主流文化圈的法庭上經歷一番艱苦的戰斗,才有些許可能得到公平對待。為了對抗這種不公平現象,才設計了諸如文化辯護的制度,允許文化證據進入法庭以確保法官能夠真正設身處地的理解亞文化群體的被告人的行為。申言之,真正有違平等原則的情形,反而是以主流文化圈的標準,規范亞文化群體的被告人的行為。
2. 威懾功能的式微及其澄清
對文化辯護的另一個擔憂是,其破壞了刑罰的一個總目標——威懾。因為“法律必須制裁越軌行為,以維護社會秩序”,只有如此,刑罰才可以實現阻止“被告本人犯罪”或“阻止社會上其他人犯罪”的功能。?而文化辯護致力于在刑事司法體系中實現個別正義、維護文化多元化,那么由此帶來一定程度的社會混亂則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文化辯護的存在,可能會不恰當地向亞文化群體暗示,法律并不真正適用于他們,從而會對有犯罪傾向的亞文化群體產生一種鼓勵,促使他們違抗法律。正如Julia Sams 指出,只有對犯罪的亞文化群體實施刑罰,亞文化群體才會有強烈的動機去尊重這個國家的法律。通過亞文化背景為他們開脫,只會向他們傳遞一個訊號,即他們不必遵守刑法。?因此,文化辯護的適用,會對刑罰威懾、遏制犯罪的功用產生反面效果。
其實,將文化辯護適用于司法實踐中,并無破壞刑事處罰的威懾目的。首先,威懾并不一定等于酷刑,甚至懲罰的嚴重程度對威懾無關緊要。而且,威懾并不是刑事處罰的唯一目的。基于亞文化背景給予亞文化群體寬宥處罰,也會向亞文化群體發出警告,表明這種行為是不允許的。其次,刑法對因其文化的“適當行為”而處于刑罰,于亞文化群體幾乎沒有威懾作用,并且他們會認為此時的刑法是非正義的,由此帶來的社會危害性更為劇烈。再次,懲罰犯罪的另一個理由是報應,報應的前提是犯罪者應受到公共道德的懲罰——“以牙還牙”。?不考慮被告的文化,不能滿足被告的倫理可責性。最后,從刑罰的預防功能來說,只有個體內在的相信,法律代表的價值是在文化、道德上正確,才能被更有效遵守。只是存粹的意識到行為與法律不一致,并不足以令行為人放棄對原文化價值觀的信仰。
3. 落后文化的庇護及其澄清
實證研究表明,提出文化辯護的許多刑事案件,實際上是涉及婦女兒童有關父權文化準則的案件(強迫婚姻、榮譽犯罪、生殖器切割)。?在這些情況下,允許文化辯護只會加強父權規范,并通過承認壓迫行為是文化內“適當”做法,從而使其具有某種合法性。那么,文化辯護實質公正、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的目標將會落空,也固化主流文化群體與亞文化群體之間的差距,以致于少數民族會被以某種看似公平方式“囚禁”在他們的文化里。如此觀點,與1990 年的AAA(美國人類學學會) 會議上,一些人類學家的看法如出一轍。在會議上,那些人類學家聲稱,“文化辯護”是利用人類學專業知識來合法虐待婦女。?法學家萊曼也認為,允許文化辯護打開了各種信仰的大門,從而使得宗教、政治、恐怖主義可以作為合法的借口。?例如,People v. Chen 案件(來自中國的Chen 被控一級殺人罪,因為他在得知妻子通奸后用錘子將其打死。Chen 聲稱因為其特定的文化背景,使其在面對此類事件時,責任能力下降。在庭審中,專家證人作出證言稱:中國文化認為通奸是丈夫軟弱的標志,是極大的恥辱。并且在中國文化中,男性對通奸做出威脅和傷害妻子的反應并不罕見。所以,法庭考慮到Chen,剛移民到美國又缺乏社區交流,他的文化背景會使他特別容易在這種情況下崩潰。因此,Chen 只被判犯有二級殺人罪。?此判決之后,據統計紐約亞裔社區的家庭暴力事件有所增加。?因為,此判決向整個亞裔社區釋放了一個訊號,那就是遭受虐待的亞洲移民婦女可以被“合法”的家庭暴力。
對于“文化辯護”成為落后文化庇護所的另一種擔憂,被描述為“飛去來器效應(Boomerang Effect)”。飛去來器效應認為,“亞文化群體的特別規范”也會影響主流文化,因為在“遵循先例”的判例法制度的影響下,這些判例為如此文化開創先河,必將有效地“重塑”主流法律?,以致于“強化了錯誤的、不合時宜的”規范。
對于文化辯護會成為落后文化的庇護所而言,不可否認文化辯護并不是完滿的制度,但是,承認文化辯護必將利大于弊,不能因為其有缺點而被拋棄。首先,在可預見的將來,文化多元的社會長期存在。誠如美國學者亨廷頓所言,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設性的道路是棄絕普世主義,接受多樣性和尋求共同性。?而且,刑事司法制度應該努力探尋實現法治、文化多元化和個別化正義的道路。不幸的是,法律和秩序往往與文化多元化和個別化正義相沖突。而“文化辯護”,正是刑事司法制度尋求平衡這些相互競爭的利益之間的一種手段。
4. 固化分裂的鴻溝及其澄清
文化辯護沒有加速融合的裨益,反而固化分裂的鴻溝。亞文化群體應該盡快被同化,個性化的司法導致無政府主義和犯罪率的增加。對于亞文化群體最重要的是“入鄉隨俗”,即“每個人都應該遵守相同的、單一的標準。?而且,文化本身并不是如磐石一般固定不動的存在,文化的外延邊界和內核精神是隨著時間的流變而變化?,我們很難在時間、空間和人群方面確定文化的邊界。由于文化標準的不確定性,那么“文化辯護”的適用也隨之具有了肆意性。
但是,把同化擺到重要位置的觀點,忽視了許多現實。首先,同化政策已經被證明是不可持續的。倘若國家過度強調文化的同質性,對亞文化群體強行實施同化,結果往往會把他們推向“另一面”,并不斷異化。在極端的情形下,它還容易催生離心力極強的民族分離主義,使國家陷入分裂的危機。其次,亞文化群體對他們的傳統保持著強烈的行為定型。希冀通過與主流文化的互動交流,讓亞文化群體的人遵守主流社會的行為標準是不現實的。因為,一個人從本質上是由他的文化塑造的,并不會自動地吸收另一個世界的世界觀和規范。?最后,基于人權范疇中“自我決定權”的要求,一個民主國家應該承認、欣賞和促進亞文化群體的獨特習慣、習俗,包括根據這些習慣、習俗作出合理的司法裁判標準。?
(二) 文化辯護中國化的功用
文化辯護的提倡,并不意味著“國家主義”立場的偏廢,也不意味著會將“個人主義”推向極致。其實,兩個主義完全具有并存的可能性,也可相互配合共同助力于我國的司法實踐。文化辯護中國化,還具有如下功能性的意義:
1. 利于保障人權
人權發展進路,通常區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系爭取個人自由、避免國家干預的消極人權概念,屬于公民政治權的第一代人權;第二階段則是需要國家積極作為,給付以求平等的積極人權概念,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屬于個人權利,這是第二代人權。第三階段以族群、集體連帶關系作為基礎,擴充人權之概念,包含了發展權、和平權、資源權、環境權、人類共同的遺產權以及民族權、民族自決權等“集體性人權”的概念,這是第三代人權。國際上構建集體性人權之重要意義,在于保障少數或弱勢之族群或團體。?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人權的內涵層次愈加豐富,人們對于人權保障的需求也愈發強烈。刑事司法制度,作為國家執行公共政策的重要工具,也應該不斷填補、豐富其內涵,進而滿足人民群眾對于保障人權不斷攀升的要求。而文化辯護中國化,正可與之契合,即可以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權通過體現不同于主流社會價值觀的實踐,以表達他們的文化身份,尋求歸屬感。
2. 利于探求事實
沒有亞文化教育背景的審判人員,難以理解被告的文化和法律規范之間的聯系。如此情況下的定罪,被告有罪的原因可能不是源于案件本身的是非,而是通過強化亞文化群體的負面刻板印象抑或是基于將被告融入主流文化的需要得出。?因此,文化辯護中國化,就可以通過文化證據的示明,讓審判人員了解被告的特有文化,用積極的了解來取代消極的成見,從而更利于發掘案件的真相。而且,通過對美國刑事司法實踐了解,不難發現文化證據對于探明被告的理性意識、精神狀態、意圖、事實的錯誤等具有積極作用。一言以蔽之,文化辯護中國化,有利于法庭辯明是非曲直。
3. 利于整合社會
在具有多元文化融合的國家,很可能在評價同一個行為時存在差別看法,一個行為可以在這一社會群體看來是無序和犯罪的,卻在另一個社會群體中被認為是英雄美德的縮影。所以,當兩個或多個文化價值觀相對的群體,被納入一個更大范圍的單一政治領域時,可能會產生沖突。在美國印第安部落中,他們認為比起監禁被告人而言,讓被告人贈予被害人牲畜、照顧被害人的家庭等處罰手段,更可以安撫被害人及其家庭。?這些文化傳統體現著截然不同的世界觀,而且各文化群體仍然保持著截然不同的社會現實,以主流文化的標準和規范去評價亞文化群體的行為,必然不利于社會矛盾的整合。再者,雖然不同文化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但各種文化間的內核又有著符合全人類文明要求的道德標準之相似性。法律調整社會的功能畢竟是有限的,在法律無法觸及的領域,這些文化正可以發揮著“規范”的功用,從而指引該群體的行為,同樣達到維護社會的效果。總的來說,文化辯護中國化,可以很好的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亦能在法律失效的領域起到規范的功用,有利于社會矛盾的整合。
4. 利于實現正義
司法活動歸根結底是一種追求個體正義的活動,誠如學者言,個體正義的實現端賴于尊重個體間的客觀差異,并對這些差異給予充分認同。?根據文化心理學的相關理論,文化對于一個人行為和心理的塑造影響最為深遠,產生的規制力量也最為強烈。?如此,在文化因素作用下的被告人,存在即使違反法律也無倫理可責的可能性。誠如德國學者威爾·澤爾所言,某一行為即便有其法益侵害性,但只要符合社會傳統文化傳承的倫理習慣,就應當阻卻其違法性。?總而言之,文化辯護中國化是司法追求個體正義的要求,同時,其亦可為實現司法上的正確認定提供方法論上的指引。
三、文化辯護中國化的路徑選擇
美國刑法中的文化辯護,為我國處理“文化沖突”案件,提供了有益的經驗指引。但任何制度并不一定是完滿的,我國司法制度在借鑒文化辯護的經驗時,也應考慮到如此制度弊病的規避。
(一) 文化辯護中國化的移植條件
文化辯護中國化,具有諸如:人權保障、發現案件事實、利于社會整合等益處,能夠為處于轉型期的中國司法提供有益經驗借鑒。但是,在具體制度設計之前,應該明確文化辯護是否具有進行移植的本土條件。
1. 政策條件
“一帶一路”是我國倡導的全球化的新模式,“一帶一路”的背景下,中國將是一個更加包容、開放的中國。“一帶一路”政策之于法律領域的影響,在于謀求法律的愈發開放性,也即兼容并包含域外法中的合理因素。?為順應“一帶一路”政策的需要,在立法層面,應該吸收域外法的有利因素融入我國法律體系;在司法方面,秉承開放、包容態度,尊重各國特殊文化習慣,為各國特殊文化習慣進入司法領域打開通道。
我國是由五十六個民族組成的多民族國家,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獨特的文化習慣。為了進一步促進民族團結、國家的繁榮穩定,我國專門為少數民族提出了多項政策,例如:1984 年第5 號文件提出的“兩少一寬”刑事政策等。這些政策都從國家層面表達了我國充分尊重和維護我國各個少數民族所特有的文化習慣的治國理念。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我國刑事司法政策要求,在量刑中要做到“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達成,與充分尊重與維護亞文化群體的文化習慣密不可分。
總體而言,我國所持有的更加開放、包容的外交態度,以及充分尊重、維護各民族文化習慣的治國理念,都要求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立法上吸收融合多種文化的可取之處,司法上尊重不同文化的區別之處。由此,文化辯護中國化,已經具有切實充分的政策條件。
2. 法律條件
我國簽署的聯合國《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7 條要求,在存在人種、宗教、語言的少數人的國家中,國家層面應該保障少數人群體享有自己文化、宗教、語言的權利。在我國《憲法》中,亦規定了各民族都有保持自己風俗習慣的自由。在實體法方面,我國《刑法》第90 條規定了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據當地民族文化等特點,對刑法規定的基本原則作出變通或者補充的規定。以上等等法律文件,都從立法層面保障了將不同文化引入我國法律體系中的路徑。
此外,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如最高人民法院2010 年發布的《關于進一步發揮訴訟調解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積極作用的若干意見》、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09 年發布的《關于在審判工作中運用善良民俗習慣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指導意見》等意見,都表達了審判機關對于在司法實踐中考量文化習慣的積極傾向。通過以上法律文件的規范目的探尋,不難得出,文化辯護中國化已經具備豐富的法律條件作為保障。
3. 現實條件
我國與美國都是具有豐富多彩的多元文化國家,同時也都面臨著“文化沖突”案件時常發生的現實情況。首先,我國司法中“文化沖突”案件將持續性增長。在“一帶一路”積極倡導下,我國已經與多達100 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合作文件。日后,國際交流將更加頻繁,各國的文化沖突成為了一個不可回避的議題。此外,我國還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少數民族就有55 個。據最新的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少數民族人口約為1.1379 億人,占比8.49%。我國少數民族中,不少具有自己獨特的習慣文化,這些文化習慣都與我國現行刑法相左。所以,據于我國國際國內文化愈發多元的背景,在不久的將來很有可能會產生大量的“文化沖突”的案例,從而導致法律適用的緊張。
其次,司法中存在“文化沖突”案件應對不足的情況。這主要體現在,我國審判中考量文化因素,不僅在刑事實體法定位上不明,在程序法上也沒有可行的舉證方式和認定標準?,以致于多數法官都“極為嚴格”的依法辦事,對于被告提出其行為背后有特殊文化動因的證據一般不予支持。哪怕在特殊情況下,采信了文化證據,對其論證也并不充分,僅依靠是否具有少數民族或外國人的身份的判斷。再就是,適用文化證據的案件范圍狹小。“我國法院的采信文化證據僅局限于重婚、虐待等自訴案件中,而對于公訴案件,法官不敢以此阻卻行為人違法。”?
最后,民眾希望自己的文化在司法中受到尊重。通過對少數民族地區某基層法院辦理案件的實證研究顯示,盡管少數民族地區法官,對文化抗辯所代表的鄉村民意持謹慎的態度,但就將其融入到判決中的案件來說,受訪民眾評價為“非常好”的比例高達87%。?這顯現了民眾期望自己的文化習俗,能夠在司法中受到重視。
綜上所述,文化沖突案件持可見性的增長,我國司法體系卻對此應對不足,美國刑法中文化辯護的采用,可為我國提供可行性的模式參考。而且,民眾迫切希望在司法中自己獨特的文化習慣能被尊重。如此,文化辯護中國化在我國具有了堅實的現實基礎。
(二) 文化辯護中國化的司法路徑
如上文述及,文化辯護具有中國化的移植條件。針對我國司法中,在應對文化沖突案件中制度缺位、案件適用范圍狹小和文化證據缺乏統一標準等弊病,可以從如下方面進行文化辯護中國化的路徑改造。
1. 文化辯護中國化的適用階段
文化因素對于被告人思想的塑造、行為的規制能力極強。因此,在評價被告人的行為時,應該進行全方位的評價,也即不論是在論罪或是科刑上,文化證據都不應輕易被忽略、排除。在美國刑法中,被告提出的文化辯護,是可以作用于刑事訴訟中任意階段的處理方式。比如:在People v. Kimura 案中,一位日本母親在得知丈夫對自己不忠后,把她的兩個孩子推入太平洋溺亡后自殺,但自殺未得逞。檢察官沒有指控她犯有謀殺罪,而是允許她就較輕的故意殺人罪進行辯訴交易。檢察官減輕對Kimura 的指控,是考慮到她的日本本土信仰,即在日本文化中,丈夫不忠對女性的刺激是極為強烈的,以致于通過自殺以及傷害子女的方式擺脫恥辱的方式是可以被接受的。?在上訴時,法官不當地排除了文化證據,法官沒有恰如其分地給陪審團示明相關的文化證據,辯護律師沒有提出文化辯護等都可以作為上訴時的理由。甚至在執行時,也需要考慮到被執行人的特有文化。?不難看出,“文化辯護”在美國刑法中的作用是全方位的。
所以,為了保護亞文化被告權利的全面性,文化辯護中國化,應該確保在刑事訴訟進行的各個階段,都應該綜合考量文化因素對被告人的影響。如此,文化辯護中國化的適用階段,應該覆蓋了訴前的偵查起訴階段、訴中的定罪量刑階段以及訴后的執行階段。具體而言,訴前可以根據文化因素對被告的影響,作出起訴與否的決定。訴中綜合文化因素對被告人的影響來判斷,影響越大正當化可能性就越高。例如,有些少數民族地區,因妻子不能生育再娶是具有社會相當性的行為,并不具有實質的違法性。所以,當亞文化被告具有這一特有文化背景時,不宜評價其行為的“不法”。若受此文化影響但并不能得出完全正當化的結論時,則應繼續進入下一階段“責任”層面的評價。對于責任層面而言,文化因素對被告影響,可以表現為事實認識錯誤、違法性認識錯誤等,當文化因素使亞文化被告在對于事實認定抑或是違法性的認識不具有正確評價的可能性時,可以阻卻故意或責任而出罪。若只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達不到阻卻罪責的程度時,仍有從輕、減輕處罰的余地。在量刑時也應該考量相關文化因素的影響,適度從輕、減輕的處罰。比如:“買命錢”的習俗,經過賠償之后,危害的社會秩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被告人的再犯可能性也得到了降低,而且亞文化被害人也并不希望被告人再得到嚴厲的處罰。如此,訴訟的目的已經達到了一定程度,在量刑上法院應考慮給予一定程度的減輕。
2. 文化辯護中國化的作用方式
文化辯護在美國得以減免罪責,主要是因為相應的文化證據,證明了亞文化群體的被告人存在事實錯誤、法律錯誤以及其精神狀態和罪過形式與法律規定不適切。文化證據證明事實錯誤是指,被告人所處的文化背景,使其誤解了自己所處的現實處境,從而否定所需的犯罪意圖。比如:People v.Moua 案?,赫蒙族部落的Moua 被控強奸后,辯稱其行為并非強奸而是行了赫蒙族部落的儀式——“搶婚”。因為根據赫蒙族的傳統,搶婚是一種儀式,一個男人追捕一個女人,并與她發生性關系,而后迎娶她。作為儀式的一部分,女人應該表現出反抗,以顯示她的美德。這種文化儀式的存在作為證據表明,盡管Moua 遇到阻力,但他不知道這個女人不是自愿的,因為阻力也是搶婚儀式的一部分。所以,法院最后并沒有認定其構成強奸罪,而是定了罪責程度更低的非法拘禁罪。文化證據證明法律錯誤指,被告所處的文化環境,致使其沒有意識到違反法律。與事實錯誤的辯護不同,法律錯誤的辯護運用文化證據表明,盡管被告對事實的全部知識有了解,但被告無法了解其行動的規范含義。因為,在其背景下不存在如此法律或對此種法律有特別的理解,甚至某些行為還是在其文化上是作為美德被提倡的。雖然對法律的錯誤,在美國通常不會被認為是一個合理的借口去違反法律。但是,還是存在某些情況下的變通,可以因其法律錯誤免除或者減輕處罰。文化證據證明精神狀態是指,文化因素可以通過確定被告的精神情況、處境和認知能力,表明一個人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以此減少指控或減輕懲罰。因為,文化上的特殊環境可能會迫使個人做出被視為“精神疾病”的行為模式。?文化證據證明罪過形式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結果的認知能力、回避能力等存在差別,結合文化證據可以對被告人的罪過形式,為疏忽、輕率、明知抑或是故意進行精準識別。
文化辯護中國化的作用方式,可以借鑒美國文化辯護的作用方式,通過文化證據證明,亞文化群體的被告人是否存在:事實認識錯誤、違法性認識錯誤、具體的罪過形式以及等同“精神病人”的精神狀態。
3. 文化辯護中國化的證據規則
首先,文化辯護中國化的證據內容。為了確保亞文化被告確實受到了其文化的影響,亞文化被告應該提供證據證明: (1) 確定他屬于亞文化群體中的一員,(2) “此文化信仰確實存在亞文化群體的社會生活中”,(3) 被告實際上相信并受到了文化傳統的驅使。?此外,我們還需要明確,行為人是否有機會認識法。行為人的“機會”可以根據行為人融入“主流文化”的程度判斷,具體需要綜合被告人的年齡、與“主流文化”交流的情況、從事職業的性質和時間、語言的能力、平時是否遵守其本文化傳統的習慣等因素作出綜合判斷。如無機會認識法,則可以承認其的確不具有回避文化影響的可能性。若有機會認識法,則需要考慮行為人是否去認識法。若不去認識,或是僅在一個過分狹窄的范圍內去認識法,在這種情況下,被告人對于文化因素造成的影響是可以避免的,不能適用“文化辯護”。只有當被告人做出了足夠努力來認識法而不得時,方才可以適用“文化辯護”。
其次,文化辯護中國化的證據獲得。為了證明這種特有文化確實存在,亞文化群體的被告可以提供專家證人或部落領袖對案件的文化影響進行說明。但是,為防止專家證人成為“雙方律師的雇傭槍手”,或亞文化群體的領導人“屈服于壓力,歪曲他們的文化,以挽救一個親戚或朋友。”?司法系統可以編制關于不同文化和習俗的著名專家名單,在專家的名錄建成之后,由控辯雙方共同選擇專家證人。此外,作為專家證人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民族學家等外部專家,本身并不是相關亞文化群體的成員,其掌握的文化細節很有可能并不準確。所以,在文化證據獲得的過程中,不能賦予外部專家的絕對地位。應該給予一些內部人士空間,內部人士還應包括那些通常在文化問題上不被視為權威的人,包括年輕婦女,以及該群體較進步和激進的成員的意見?,以此來平衡所有可能造成偏見的證據證明權力的結構組成。
再次,文化辯護中國化的證據區分。誠如Anne·Phillips 所言,認為文化會以相同的方式影響所有成員的想法是荒謬的。?因為文化塑造人們以特定方式行事,其實也只是提供了一個制式的框架,在這個框架內,人們可以對這些選擇進行評估并對如何選擇具有預期。根據文化對行為影響的強烈程度,我們可以把文化規范分為:允許的、鼓勵的、需要的和必須的四種。在文化辯護中國化中,不應查明只要具有文化的影響,就一律給予“優待”。法院應該根據評估被告可能被其文化“強迫”的程度區別評價,比如:對那些在被告的文化中被視為必須的行為,對于減免責任的評價采取更包容的態度。若被告的行為在其文化中也僅是鼓勵的行為,對其行為的評價則應采取更加嚴格的態度等。
最后,文化辯護中國化的證據標準。公平來講,被告與審理法官的相似之處越多,法官就越有可能認為被告的信念和行為是合理的。而亞文化群體,很可能并不與法官處于同一文化生活圈,以致于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常用的“理性人標準”可能并不“理性”。所以,審理亞文化群體的被告時,采用的標準應該是“合理的亞文化群體的一般人”而不是“合理的一般人”。之所以不采取完全的“(被告人) 行為人標準”,因為純粹的主觀標準實際上會“瓦解”所有標準和內核,所以保持一定程度的客觀性(群體的一般性) 是至關重要的。?據于此,文化證據的采納標準是“合理的亞文化群體的一般人”。
(三) 文化辯護中國化的弊病規避
正如上文所言,文化辯護制度并不可能是盡善盡美。但是,基于此制度的功效而言,文化辯護制度的建立是利大于弊的。為了讓文化辯護中國化進路為坦途,有必要警惕如下風險:
1. 文化辯護的濫用
如同美國文化辯護存在濫用的風險一樣,中國化的過程也應警惕其被濫用的風險。在美國濫用文化辯護,是為了行使誤導陪審團、拖延訴訟程序等訴訟意圖。所以,在文化辯護中國化過程中,為了規避類似風險,應該建立相應的文化證據排除規則,比如:被告存在受特定的文化影響的客觀情況,但是此種文化哪怕存在形成了偏見的,也不至于影響案件的結果時,就應該排除文化辯護的適用。再如,若調查某一文化證據需要投入過多的司法成本,大于獲得其證據在司法審判中應有的價值時,也應該被排除適用。
2. 被害人權利的壓縮
刑法要求公平、平等地對待所有人,似乎為刑事法庭允許文化辯護提供了強有力的理由,但是,有一個群體——被害人卻被忽視。正如一個女權主義者所言,在實踐中“文化辯護”的適用往往會使施害人成為特權人,而受害的婦女和兒童的生活權利、自由和身體的完整性卻被壓縮對待,例如:Razack 案 (1994)、Rimonte 案 (1991)、Sam 案(1986) 等。”?所以,在文化辯護中國化過程中,公平強調的不僅是對于被告,而且應該兼顧考慮到受害者。
為了防止壓縮被害人權利這一弊端,文化辯護中國化時,可以針對犯罪中有無具體被害人,分別適用“文化辯護”。可以把犯罪分為兩類:一類是不一定有明確被害人的犯罪,如吸毒、自愿重婚等案件;另一類是有明確被害人的犯罪,如強迫婚姻等有關父權文化案件。在第一類案件中,“文化辯護”主要被視為一種平衡文化偏見的手段,可以正常適用。但在第二類案件中,允許“文化辯護”,實際或等于文化壓迫,會讓文化群體中最脆弱的群體得不到保護。所以,此類案件中要減少“文化辯護”對審判的影響。此外,還可以采取在第二類案件中,設立更加嚴格的文化證據標準等措施以平衡對于受害者的保護。
注釋:
①People versus Kimura, Santa Monica Superior Court,1985, Case Number: A-091133.
②John Alan Cohan, Honor Killings and the Cultural Defense, California Wester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2010, 40(3), pp.177-252.
③ 劉士心:《美國刑法中的犯罪論原理》,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129 頁。
④? Annamari Vitikainen, The Limits of Liberal Multiculturalism: Towards an Individuated Approach to Cultural Diversity, St Martin’s Press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2015, p.153, p.170.
⑤? Alison Dundes Renteln, Raising Cultural Defenses, in Cultural Issues in Criminal Defense, Huntington Juris Publishing, 2010, p.772, p.766.
⑥⑧Naomi Mendelsohn, At The Crossroads: The Case for and Against a Cultural Defense to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Rutgers Law Review, 2004, 56 (4), pp.1011-1038.
⑦Kwan Mak versus James Blogett, Washington Supreme Court, 1991, Case Number: C88-1421WD.
⑨Daina Chin, The Cultural Defense: Beyond Exclusion, Assimilation, and Guilty Liberalism, California Law Review, 1994, 82(8), pp.1053-1060.
⑩? Augustine T. Lam, Culture as a Defense: Preventing Judicial Bias Against Asi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Asian American Pacific Islands Law Journal, 1993, 1(1), pp.49-68.
?Reddy Sita, Temporarily Insane: Pathologising Cultural Difference in American Criminal,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2002, 24(5), pp.667-687.
? Katheleen R. Guzman, Give or Take an Acre: Property Norms and the Indian Land Consolidation Act, Iowa Law Review, 2000, 85(2), pp.595-662.
????? Alison Dundes Renteln, The Cultural Defen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92-193, p.25,pp.92-97, p.137, p.206.
???? Megan H. De, Defending the“Indefensible”:Replacing Ethnocentrism with a Defense of Native American Culture Defense,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2011, 6(2), pp.621-660.
? Julia P. Sams, The Availability of a“Cultural Defense”as an Excuse for Criminal Behavior, Georgi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Law Journal, 1986, 16(2), pp.335-354.
?John Kaplan, Criminal Law Cases and Materials,Wolters Kluwer, 2008, p.21.
? Carole E. Goldberg, Individual Rights and Tribal Revitalization, 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 2003, 35(3), pp.889-938.
?? Winkelman, Michael, Cultural Factors in Criminal Defense Proceedings, Human Organization, 1996, 55(2),pp.154-159.
?John C. Lyman, Cultural Defense: Viable Doctrine of Wishful Thinking, Criminal Justice Journal, 1986, 9(1),pp.87-118.
?Left Volpp, Misidentifying Culture: Asian Women and the “Cultural Defense”, Harverd Women’s Law Journal, 1994, 17(3), pp.64-77.
? Alexis Jetter, Fear is Legacy of Wife Killing in Chinatown: Battered Asians Shocked by Husband’s Probation, New York Newsday, 1989, 26(11), p.4.
? [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構》, 周琪等譯, 新華出版社2002 年版, 第369 頁。
??Andrew Kanter, The Yenaldlooshi in Court and the Killing of a Witch: The Case for an Indian Cultural Defense, Southern California Interdisciplinarity Law Journal,1995, 4(2), pp.411-451.
?John Tom Morgan, Laurel Parker, The Dangers of The Cultural Defense, Judicature, 2009, 92(5), pp.206-208.
? 李建良:《淺說原住民的憲法權利若干初探性的想法》,《臺灣本土法學》2003 年第6 期。
? Robert J. McWhirter, Jon M. Sands, Does the Punishment Fit the Crime? A Defense Perspective on Sentencing in Aggravated Felon Re-Entry Cases, Federal Sentencing Reporter, 1996, 8(5), pp.275-278.
? 陳家林:《外國刑法通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 年版,第388 頁。
? 陳山、李昊:《多元文化社會中文化沖突型違法性認識錯誤及其處理》,《四川師范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14 年第 6 期。
? [德]岡特·施特拉騰韋特,洛塔克·庫倫:《刑法總論Ⅰ——犯罪論》,楊萌譯,法律出版社2006 年版,第98-99 頁。
? 嚴存生:《“全球化”時代與“一帶一路”的法治建設》,《上海政法學院學報》2019 第2 期。
??? 劉東利、陸銀清:《論文化抗辯在刑事司法適用之實證分析——以少數民族地區某基層法院辦理的案件為視角》,《深化司法改革與行政審判實踐研究(上下冊) ——全國法院第28 屆學術討論會獲獎論文集》,2017年,第797、801、799 頁。
?Sharon Marie Tomao, The Cultural Defense: Traditional or FOormal?, Georgetown Immigration Law Journal,1996, 10(2), pp.241-256.
?People of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versus Kong Pheng Moua, Fresno County Superior Court, 1985, Case Number:315972-0.
?Anne Phillips, Multiculturalism without Cul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47.
? Cynthia Lee, Murder and the Reasonable Man: Passion and Fear in the Criminal Courtroom,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09.
? Melissa Demian, Fictions of Intention in the“Cultural Defens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2008, 110(12),pp.432-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