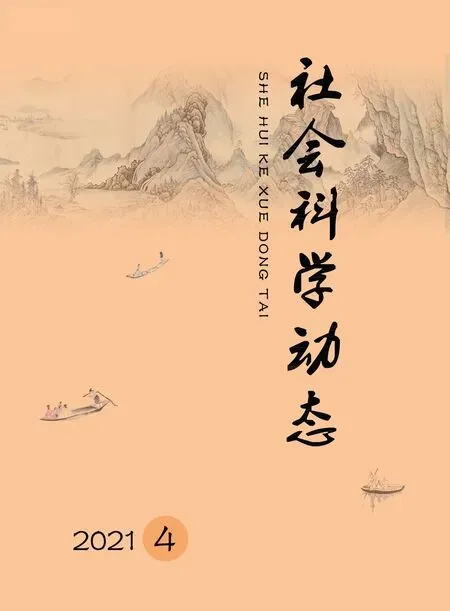黃世瑜先生訪談錄
李世濤
編者按:黃世瑜,1934 年生于上海,1956 年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本科畢業(yè),留校任教。1963年至1964 年在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進修班進修。長期擔任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主任,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曾兼任全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理事,《文藝理論研究》雜志編委等。主要學術研究領域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文學理論等,撰有學術專著《馬列文論與文藝現(xiàn)實》、專題散文集《雙槳同舟》 (合著) 等,主編《文學理論新編》;任副主編并參與撰寫的有《文學概論》 《馬克思主義文藝論著選讀》 《文藝美學辭典》等;作為主要作者,參加了葉以群主編的全國高校文科統(tǒng)編教材《文學的基本原理》的編寫、修訂再版的全程,1986 年該書獲國家教委頒發(fā)的全國優(yōu)秀教材一等獎。
李世濤(以下簡稱“李”):黃老師好!首先感謝您接受我的采訪!我最近就中國當代文藝理論在做一個口述史的課題,計劃邀請當代文論研究的一些親歷者談談自己經(jīng)歷或知道的事情,為學術研究保留一點資料。您是我國當代文論研究、教學的老一輩學者,不但參與了不少的文藝界活動,有著豐富的經(jīng)歷,而且還非常活躍地出現(xiàn)在高校科研、教學一線。希望您能夠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涉足文論界
李:我首先想了解的,您是如何走上文藝理論的科研和教學道路的?
黃世瑜(以下簡“黃”):我是1952 年考進華東師大中文系的。當初在中學的時候,我就喜歡文學,我的語文老師是個作家,她介紹我看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她出的作文題目也很有趣,如《大小姐與小大姐》 《秋蟬》等。
我因為喜歡文學,在考大學時就選擇了文學這個專業(yè)。專業(yè)是定了考中文,我為什么考華東師大呢?因為當時的師范院校是不收學費的,我也希望經(jīng)濟上能夠獨立,這樣就可以直接解決我的經(jīng)濟問題了。所以我就報考了華東師大中文系。來了以后,我接受了系統(tǒng)的中文知識、理論訓練。
那么,當時我為什么喜歡文學、會學理論呢?第一個是我在中學不偏科,我高一的時候有一門社會基礎知識課,我對意識形態(tài)、經(jīng)濟基礎、上層建筑等概念學得很認真,對理論思考是蠻喜歡的。加上我們大學一年級時,許杰先生是華東作協(xié)主席(或是副主席,具體我忘了),他沒有系統(tǒng)地給我們上過文學概論課,但因為是作協(xié)的領導,他就把當時《文藝月報》編輯部的一幫人,像王西彥、唐弢等人都請來給我們上課。我記得唐弢講“文學遺產(chǎn)的繼承”,王西彥講“距離與美”,魏金枝講“主題與題材”。那時候,雖然我們才剛上一年級,但聽了也很感興趣,受益也是很大的。
上課的時候,學校提倡學生課外搞科研活動,所以系里就組織了一個跨年級的科研小組。小組人不多,包括四個年級的同學,每個年級就兩三個人,成立了一個科研小組。系里把我抽選進來了,等于這方面有了一些專門的接觸。我們自己也搞了一個科學討論的小組,小組的指導老師是徐中玉,他定期開一個書單給我,讓我拿去給大家看。他自己是搞理論的,開的都是理論方面的書,所以,我無形當中對理論的書接觸得多了點。就這樣慢慢地接觸多了,思考得也多一點。
畢業(yè)以后,學校就把我留下來了,跟著徐中玉先生輔導學生。當時的教學很嚴格,教授給學生上大班課,我們年輕教師就輔導、搞課堂討論這些,等于成為文學理論教師了。這樣,我從助教、講師慢慢升上去,就走了文藝理論研究這條路了。
李:當時徐先生還沒被打成“右派”吧?
黃:沒有,他是1957 年被打成“右派”的。那個時候他還很年輕,大概40 歲左右,我那個時候才20 多歲,比他小近20 歲。
李:后來許杰先生是參加文學藝術界討論被打成“右派”?
黃:我也說不清楚。許杰先生被打成“右派”之前,學校是準備派他到蘇聯(lián)講學的。最初,許杰要我做他的研究生,考試都考了。結(jié)果,他去蘇聯(lián)的計劃取消了,取消之后,系里和徐中玉先生就把我留下,留校成了系里的助教。許杰先生在當“右派”之前,拿今天的話來說,還是“蠻紅”的。
李:您是說許杰先生要去蘇聯(lián)?他不是“右派”嗎?
黃:是的,許先生曾經(jīng)要去蘇聯(lián)。后來,這個計劃取消了,這種事情要聽上面的意見,學校自己做不了主,是國家派的。那時候是1957 年,我也搞不清楚具體情況,只是聽說他給《文匯報》寫了一篇東西,說“黨要怎么整風”之類的話。我就看到墻上貼了很多關于他的大字報,氣氛緊張,就覺得這個不好了。許先生向報紙投稿文章,是報社那頭把他弄出來,后來抄成大字報貼在中文系辦公室回廊的墻上。我高度近視看不清楚,記得校黨委書記也來看了,還和個別教師發(fā)生了爭執(zhí)。
徐中玉先生在系里沒有“鳴放”,就是臨時接替系總支書記主持過一次“鳴放”會議;主要是應各種報刊之約寫了幾篇文章,說了一些要糾正的問題。后來作協(xié)把這些文章歸納起來開批判會。他當“右派”比許杰遲。
以后就是“大躍進”了,我們“大躍進”都下去了,1958 年我們就到嘉定落戶了。到嘉定那個地方去,叫“教育改革”,其實就是參加勞動。上課不像現(xiàn)在這樣排課,好比你這個禮拜上語言的課,下個禮拜上文學的課,單科獨進。那個時候就來了王西彥,還有一個中學教師。我那時還年輕,才畢業(yè)不能上課,畢業(yè)以后要先做輔導工作,然后才能上課。到1960 年時,我和王西彥就一起上文學概論的課了。文學理論教研室也單獨抽出來成立了,我就當了教研室的副主任。文學理論教師本來跟寫作教師一起,人很少,各有教師教這兩門課。我教文學概論課又教寫作課。以后招生多了,從1956年以后招生很多。像我們上學時一個班只有40 多人,到1956 年新生入學時,有6 個班,每班40 多人,那個時候教師資源就緊張了。
所以,一個是自己喜歡,還有一個確實是工作需要,還有老師的提拔、提攜。1952 年的時候,根本沒有文學概論課,只是請人家來搞講座。
李:你們當時用的教材是您和徐中玉先生一起編的?
黃:不是。他是1954 年來的。徐先生這個人既勤奮又負責。他來了之后,說上課沒有教材不行,就自己寫了一本《文學概論》的講義,在內(nèi)部使用。因為我是助教,我就拿他這部書來輔導學生。那個時候還有函授課,上課是書面的,我做的工作一方面是教本系的學生,另一方面就是函授,要出一個函授的刊物,讓學生學習。如學習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寫“什么是工農(nóng)兵方向”“普及與提高的辯證關系”等短文讓同學們學習,或者直接針對同學提的問題答疑。我還寫了一本《文學概論》的教學指導書,是本小冊子。后來1956 年入學的同學編寫了一本《毛澤東文藝思想》,1957 年入學的同學編寫了一本《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后一本較前一本理論性強一點,材料也要豐富一些。我受同學們邀請,解答一些問題。學生還沒學習就編教材,水平自然不可能高。所以,1960 年上海作家協(xié)會就從復旦、師大、師院這三所學校抽了幾個教師和學生來編教材,學校里的教授成了“右派”,我們幾個年青教師就帶著一些學生和編寫的鉛印講義、教材到作協(xié)去,由葉以群、孔羅蓀指導,“修改、提高”去了,就這樣開始三校合作集體編寫教材了。
李:這個教材是當時中央規(guī)劃的那個嗎?
黃:不是。這個是1960 年三校集體編寫的,是群眾性的,由作協(xié)派出專家,專家輔導青年作者。
全國統(tǒng)一性的編寫教材是1961 年,是周揚開會定的,周揚當時是中央文科教材辦公室主任,他上任以后抓這個工作。周揚定主編,上海定的是葉以群,北京也搞一本。之后,主編再去挑編寫人員,我們原來三個學校的教師,葉以群是保留的,但是學生就不參加了,而且畢業(yè)班的學生也畢業(yè)走了。
李:當時盛行學生批判老師,我讀書知道戴厚英曾經(jīng)批判過她的老師錢谷融。當時你們作為學生有沒有批判過老師?
黃:師大那時提出所謂“要扶植新生力量”,有所謂“老教師不如青年教師,青年教師不如大學生”的說法。有些人既要批判前輩,又要接受和提防后輩的批判,弄得人人自危。
錢谷融的《論“文學是人學”》是1957 年5 月發(fā)表的。據(jù)說當時要開科學討論會,許杰先生要錢先生寫文章參加討論。當時許杰先生是系主任,錢先生平時喜歡看看自己喜歡的書,動筆相對不是很多。許杰先生是好心,勸他寫文章。錢先生聽后就思考了,把平時對文學作品怎么寫人、寫人與反映現(xiàn)實的關系、對人道主義的看法等問題的思考都寫出來了,并且在科學討論會上作了報告,就引起到會教師、來賓、學生的關注。據(jù)說會上大多數(shù)人不同意這篇文章的觀點。開始沒有什么,錢先生說他拿到一筆稿費,請老朋友們吃了一頓飯。后來有文章說編輯部發(fā)稿前后有種種考慮,這個一般人就不知道了。反正,以后就開始書面批判了。
錢先生沒有教過我們,我們年級的現(xiàn)代文學課是許杰先生教的。但是那時教師少,教現(xiàn)代文學的和教文藝理論的合在一個教研室。有一段時間錢先生是教研室主任,逢到開會或系辦公室有具體事情,錢先生要我記錄、辦理,我承擔著教研室秘書的工作。因此,到錢先生家去得多些,每次去,他總給我泡茶,在他家喝茶也多些。作協(xié)批判錢先生時,系領導指定要我在會上發(fā)言,我的發(fā)言雖然不是慷慨激昂、聲嘶力竭,但也傷害了錢先生,我應該致歉。
1960 年上海作家協(xié)會組織批判19 世紀資產(chǎn)階級文學,批判巴爾扎克、托爾斯泰,以為打倒巴爾扎克、托爾斯泰,打掉資產(chǎn)階級文學高峰,就可以為無產(chǎn)階級開路。于是在復旦、師大和師院找了三個靶子,復旦批判蔣孔陽,他寫了《文學的基本知識》,師大批判錢谷融,他寫了《論“文學是人學”》,師院批判任鈞,他是1930 年代寫詩的。這個會議前后開了49 天,各校都推舉了參加批判的同學,戴厚英就是那時冒出來的,人稱“小鋼炮”。
李:戴厚英當時是復旦大學的學生吧?
黃:她是我們?nèi)A東師大的學生。
李:她年齡比你們小?
黃:對,那時我們比她冷靜,她更容易沖動,所以人家叫她“小鋼炮”。戴厚英發(fā)言很起勁兒,在一個大的浪潮里面,盡管她也可能會有自己的思想,但是,因為那個時候太年輕,她可能不會去多想、多懷疑。領導講某某人比如錢先生是不好的,她就都往不好的地方想,就放炮,就是這樣,不轉(zhuǎn)彎的。有些事也講不清楚。錢先生是參加學術活動,他也不是很復雜的人。
李:錢先生人很隨和,也放得開。
黃:是的,“文革”結(jié)束后,戴厚英職稱提升,錢先生還為她寫評語,作推薦。
參編全國文論教材
李:1961 年你們開始合作編寫教材,教材是全國性的統(tǒng)編教材,參加的人多嗎?
黃:沒有好多人,主要是原來上海的。
李:最初主要是上海的,后來呢?
黃:也主要是上海的。
李:后來不是還有南京的葉子銘、蘇州的應啟后等學者嗎?
黃:后來又來了兩位,一位是葉子銘,一位是應啟后。上海是個海納百川的地方,南京、廈門的到了上海,就是上海的。應啟后的上海話比復旦的王永生、師院的劉叔成講得還流暢。葉子銘是南大的教師,他業(yè)務出色,那時候?qū)懥艘槐緯小墩撁┒芩氖甑奈膶W道路》,可以說是第一本系統(tǒng)研究茅盾的書,當時很有影響,在年輕教師里面確實是突出的,這本書是葉以群給他寫的序。葉以群很賞識他,因為周揚給了編寫教材這個任務,所以就把葉子銘調(diào)來了。還調(diào)來了一位應啟后,是蘇州大學的,年齡比我們要大一點,他教學有經(jīng)驗。
李:當時為什么把應啟后調(diào)來?葉以群和他應該比較熟吧?
黃:應啟后跟葉以群并不是很熟。原來俞銘璜在江蘇時自己曾經(jīng)編過教材,詳細的就不清楚了,我估計如果編教材的話,應啟后在里面也是會起作用的,因為他一直在上文學理論課。上海后來還增加了曾文淵,他是從廈門大學來的。
李:然后調(diào)到復旦大學的?
黃:沒有。曾文淵不是調(diào),他是分配,廈門大學畢業(yè)以后,就分配到了上海文學研究所,在《上海文學》雜志當編輯,在同一個地點辦公的。因為編教材跟群眾運動不一樣,人也不能很多。
李:你們編寫這個教材之前,當時上面給大家有什么指示嗎?因為同時規(guī)劃要編兩本教材,北方的、南方的,你們這邊肯定也要有側(cè)重,不可能編寫成兩個完全一樣的教材。
黃:不可能一樣的。周揚在挑選人的時候應該就考慮到了。你想,這兩個人站在你面前,同行肯定能想到這兩個人是不一樣的。蔡儀因為他的觀點、著作、文章,領導、同行都是心里有數(shù)的,上海的葉以群又是什么樣的,領導、同行也不可能一無所知。
李:當時,上海的葉以群不是文藝理論家吧?為什么讓他領導呢?
黃:葉以群曾做過很多黨的工作,也寫過理論著作,翻譯過文藝理論著作,后來他在上海理論界工作,也會就有關理論問題發(fā)表意見。除了葉以群,還有孔羅蓀一些其他人。
李:葉以群工作的單位是哪里?
黃:大概屬于作協(xié)。他是上海作協(xié)黨組成員,還分管雜志。雜志里面也有理論部,具體情況就不太清楚了。當時定的就是這兩個人(指葉以群和蔡儀),這個是周揚定的。當時選主編很明確,下面的編寫人員,就由主編來選定。
李:作為主編,葉以群應該起了很大的作用。
黃:那時葉以群起了很大的作用,因為當時是主編負責制,而且從輩分、年齡、學問、資歷來講也是這樣的。葉以群當時40 多歲,我們都是20 多歲,也是不同輩的。
當時,葉以群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我們那個時候年紀輕,看問題也比較簡單,思想上就強調(diào)階級斗爭。他強調(diào)文學和生活的關系,然后再談階級性,也強調(diào)文學的語言之類的。我們寫了稿子,他看了我們寫的稿子,就取里面一些有用的來用。
李:就是1960 年你們編寫的教材?
黃:對。那時全國大部分高校都自己編教材,山東大學編過,華中師大的王先霈他們可能也編過。
李:你們當時編寫的教材后來給學生使用過嗎?
黃:我們使用的是統(tǒng)編教材,我們學生自己編的沒怎么用。
李:1960 年編寫的教材沒有用?
黃:學生編的不能強制規(guī)定給教師用。好的意見可以吸取,教師還是自己寫講義。因此,到后來,葉以群組織編寫教材,確實是很慎重的。他還談到,要去各地訪問專家,聽取他們的意見,有些專家還寫了書面意見。
李:你們當時到了哪些地方?
黃:編寫組第一次主要是到江南這邊,南京、揚州各地。第二次去看周揚,他就在北京,那時是“文革”以后了,主要就跑北京。
李:你們這個教材出版得很早吧?
黃:對。因為我們組的成員跟蔡儀組的成員也不一樣,我們都很年輕。我們完成這個稿子以后,開頭就在華東師大出版社鉛印,一冊幾章地試用,因為我們幾個都是學校的文學理論老師,像我這樣,一邊用這個教材,一旦發(fā)現(xiàn)有什么不當?shù)牡胤骄透摹D莻€時候,我覺得我們很認真,也很仔細。我們后來還繼續(xù)使用,我還在廣播電視大學上課時使用過。當時剛好是國家困難時期,大學招生人數(shù)緊縮,市委是將教書作為政治任務的。要穩(wěn)住這個社會,要讓年輕人能進大學讀書,所以要搞廣播電視大學,電大使用面就比較廣了。我去電大上課,然后還到學生家里去輔導學生。
李:你們這個教材出版的時候也是兩本吧?第一版是哪一年出版的?
黃:有上下兩本,上冊是1963 年出版的,下冊是1964 年出版的。因為有的章節(jié)要改,或者葉以群要審看,所以下冊出版就晚了一些。
李:這個教材你們一直用到了1966 年?然后就“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吧?
黃:“文化大革命”當中沒有用。但是,它使用的時間是最長的,從上冊1963 年開始,一直用到1964 年、1965 年、1966 年,雖然后來停課了,整個課程的系統(tǒng)性沒有了,但是各地各校零零星星地還在用。
李:這部教材的印數(shù)應該很可觀吧!
黃:我后來在各地區(qū)了解到,這本書的影響極大。后來雖然停課了,但是,學生畢業(yè)后也工作了,那他拿什么教材來教學生?沒有書,他還是用這部書。當然這部書也有缺點、問題,當時不可能沒有錯,以后周揚被打成“黑線頭目”,下面就是黑線人物了。再后來,葉以群跳樓自殺了。
李:就主要因為這個書批他?
黃:當然,我們也不清楚其他那些批判他的東西。但這部書加重了他的罪名。
李:當時,你們的工作程序如何?是不是大家先討論,完成了提綱,然后再根據(jù)定下的提綱,分配任務,確定每人分幾章來寫作?
黃:對。但我們是反復修改的,就是我改你的,你改我的。當時不像現(xiàn)在,現(xiàn)在我們幾個人合作寫一本書,你寫一章我寫一章,就完了,你是你的我是我的,也沒有什么問題,因為外國也是這樣的,個人的寫作風格不一樣也不要緊。以前,我們是不一樣的,首先就是統(tǒng)編的名義在那里,所以我寫的跟你寫的,都需要統(tǒng)一。而且我改你的,你改我的,要求彼此互換修改。還有,葉以群要求細致到這樣的程度:哪些材料放到那一章,哪些材料放到你這章,都需要平衡。因為大家都引這句話,或者大家都引這個作者或這個觀點,重復多了,就成了傾向,這個書等于整體上就不平衡了。這些葉以群都仔細得很,否則的話,就不會這樣打磨了。
李:你們這個書進展得很快?是從哪一年開始的?
黃:從1961 年開始的。
李:1963 年上冊出來了,1964 年第二本也出來了。
黃:1964 年是下冊。速度快是因為有前面的基礎。
李:前面有個1960 年的。
黃: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大家都是上這門課的老師,負擔到自己頭上的也就一兩章,然后你改我的,我改你的。
李:之后,自己又在上課中間繼續(xù)使用這個教材?
黃:對,自己又在那里用。如果你沒有教材的話,你自己還得備課、寫講義,講廣播電視大學的課,稿子也需要寫出來。
李:“文革”以后,這部教材又修改了一次吧?
黃:1983 年又修訂出版了第三版。“文革”以后,很快再版,因為要招生了,招生以后沒有教材。當時教育部就在武漢開了一個會,決定要確定教材,文學理論教材當時定的就是《文學的基本原理》。這樣,就得趕快修改,因為學生馬上就要進校了。學生們是1978 年進來的,進來就要用這個書,就把我們這些人重新招回去。但是問題也很大,因為葉以群已經(jīng)去世了,周揚也不管這個事了。上海方面就找了孔羅蓀、劉金當顧問,又把我們這些人組織回去重新修改。時間那么短,怎么改呢?要大改也不可能了,最后就決定基本上保留葉以群在的時候的原貌,改寫個別章節(jié)。
李:后來又增加作者了嗎?
黃:基本沒有,就增加了一個徐俊西,他是復旦大學的。修改就是由復旦跟南大來組織。
李:你們那個書第一次編的時候,主編就是葉以群吧?好像有的版本上寫著主編葉以群,副主編葉子銘。那是后來的事情吧?
黃:葉子銘沒有當過副主編,他是統(tǒng)稿。
李:就是“文革”以后這個版本的統(tǒng)稿是嗎?
黃:對。因為“文革”以后,葉以群不在了,以前統(tǒng)稿是主編統(tǒng)稿。但后來也沒有寫副主編,因為也考慮到個中情況。
李:后來是以南京大學為主?
黃:是以復旦大學和南大為主,上海學校最多,復旦老大哥,葉子銘和應啟后是江蘇過來的。葉子銘的學術地位高些,他統(tǒng)稿也自然。
李:后來修改過程中去見周揚了?
黃:對,1961 年我們第一次寫的時候,周揚就接見過我們,1978 年修改的時候又去拜見過周揚。
李:你們第一次見面是去北京,還是在上海?
黃:就是在上海。當時周揚住在東湖飯店,有一天下午通知我們,他要見見主編,見見編寫組的人。主編是葉以群,還有華東宣傳部的領導俞銘璜也去了。要見編寫組的人員,就把我們也找去了。他講了很多注意事項,以及很多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文論,要我們注意中國的傳統(tǒng)文學理論,講了古今的關系,也講了政策。他說,教科書不要講政策,政策由領導講,我們要講基本理論,有些問題不要自己去找麻煩,如“國際無產(chǎn)階級文學的經(jīng)驗”之類,教科書擔任不了的就不要去講。他還談到自己在河北講過建立中國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批評,當然說法也可以換,可以講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jié)合,搞得更準確些;要總結(jié)中國經(jīng)驗,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不是從司馬相如、劉勰發(fā)展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要以毛澤東思想總結(jié)中國文學革命的經(jīng)驗,總結(jié)文學遺產(chǎn);如果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經(jīng)驗、“五四”以來的還不豐富,不能總結(jié),那就不能有中國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只能跟別人走;我們要站起來,站起來的意義很多,根本問題是要總結(jié),總結(jié)自己的經(jīng)驗、自己遺產(chǎn)。等等。
后來,葉以群就把編寫組工作地點搬到上海圖書館的三樓,便于查找各方面的書籍。
到了1978 年決定修訂時,我們又到北京去了。10 月16 日當天上午,周揚早早地在中國社科院等我們了。我們一進屋,他從沙發(fā)上起身,和我們一一握手,連聲說:“海派,好啊,海派。”他說修訂時間這么短,你們怎么辦?葉以群又不在了,你們是大改還是想怎么樣?另外,還是要葉以群做主編嗎?我們要保留葉以群主編,就改具體的觀點、材料和文字,各個章節(jié)可以有一些變化,但基本上以1964 年為界,尊重葉以群負責的那個版本。他建議我們補充一些當時葉以群也能想到的意見。
在北京,我們到北大、北師大、人大召開座談會,請教前輩、專家、同行。北大是劉烜、閔開德接待我們,提出寶貴意見;北師大馬新國、梁仲華、劉慶福、鐘子翱等人都談了看法;人大紀懷民、鄭國銓、肖風、蔡仲翔、余飄、周文柏、丁子霖等發(fā)言與我們交流。楊晦和黃藥眠先生是我們分別前往他們的寓所請教的。
我們到文研所、外文所,聽取了蔡儀、王善忠、李傳龍、張寶坤、張國民的意見。蔡儀先生給了我們很多鼓勵,認為書中的材料豐富,寫得活潑好懂,重版不做大改是好的。外文所馮至先生強調(diào)要用列寧兩種文化學說分析傳統(tǒng),對人道主義也要一分為二;葉水夫著重分析了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柳鳴九著重分析了現(xiàn)代派文學及當代西方理論和文藝現(xiàn)狀。我們是到錢鐘書先生寓所請教的。他認為有“真繼承”和“假繼承”,他問:究竟有多少人繼承了“詩三百篇”?中國起作用的還是《文選》、“選學”,不在《文賦》 《詩品》。告別時,錢先生送到門口,我們下樓梯走到拐角處,一抬頭,看到他還站在家門口目送著,傳統(tǒng)的禮儀滲透進前輩的日常舉動之中。
在北京,我們還對許多領導同志和專家進行了個別訪問,如林默涵、陳荒煤、馮牧、毛星、唐弢、何洛、潔珉、孔羅蓀等。南下回滬時,特地又到南京拜訪了陳白塵先生,還拜訪了南大、南師大、江蘇師院、揚州師院等單位的同行,聽了包忠文、馬瑩伯、王長俊、賴先德、王永健、陳遼等同志的意見和建議。
李:你們的教材在20 世紀90 年代還在用,發(fā)行量應該很大吧。
黃:發(fā)行量應該是大得不得了。就我手邊的幾本來看,1983 年6 月第三版就一下印了37 萬冊,三個月后的9 月加印了40 萬冊,到1992 年7 月的修訂版第17 次印刷,印數(shù)達到了193 萬5 千冊。后來,教育部開過兩次教學討論會,我都參加了。
李:是1986 年召開的吧?
黃:海南島有一次。
李:那是最早的一次嗎?
黃:不是最早的一次。第一次是1985 年,在北戴河開的,還是蔣孔陽去的那次。那時候,長時間開會還不是很多,是借吳玉章在北戴河的住處開的會,人比較少,大概就是十來個人。當時許多學校已經(jīng)在編文學概論教材了,會上說要討論討論我們的文學理論到底應該怎么做,有些什么問題。這也就成了1986 年海南島開會的議題。
李:北戴河會議是國家教委組織的嗎?
黃:是國家教委倡議和支持的,具體工作是人民大學在做,要不然我們怎么能住到吳玉章的住處呢?因為會議是教育部倡議的,他又是人大校長。后來,會議對《文學的基本原理》 《文學概論》這兩本教材作出評價,評價還是比較高的,認為它們起到了很好的歷史作用,代表了那個時候的研究水平。
李:主要是你們這個教材還是蔡儀主編的教材?
黃:一起籠統(tǒng)地指統(tǒng)編教材。蔡儀的可能后面沒有改,傳說可能有“右派”分子的提法,有一些人對此比較惱火和反感。不過我也沒仔細去查,我想,也可能是初稿中的,后面沒有修改。
李:1986 年海南那次會議您參加了?
黃:我去了,會上還發(fā)言了,因為我主編了一本《文學理論新編》。
李:您這本書我大學時候讀過,現(xiàn)在還有印象。
黃:我們的書是我任主編,教研室的幾位青年教師執(zhí)筆寫就的。當時寫教材,有的是主編負責的,有的是個人寫的,有的是同一個學校三、四個文學理論老師合寫的。當時對《文學的基本原理》等統(tǒng)編教材的評價挺高的,滿足了歷史的需要(因為那時沒有什么別的書),體現(xiàn)了當時的最高水平。當然這部書也很難說完全是這些編寫人的成績,實際上領導起了作用,專家也提了很多寶貴的意見。
李:你們這個書當年曾經(jīng)送給錢鐘書審閱?
黃:沒有送給他,就是有些問題去請教過他,他回答問題是坦率的。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所、北大、北師大、人民大學、民族學院等高校,都去過。到大家編了一些教材的時候,海南會上也把各自怎么編寫的情況講了講。當時,建立新的文論體系的呼聲很高。
李:海南會議好像還出過一本論文集?
黃:我沒有多少印象了,其實,每次開會討論,都是有會議簡報的。
李:海南會議的中心議題是什么?
黃: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教材上。大家都在編,有的是集體的,有的是個人的,有的影響大,有的影響小。會議對統(tǒng)編教材做了一個分析和評價,然后就涉及到下面怎么做?這其中一些意見很好的,也挺深的,如是否要先建立一個新的文論體系等。現(xiàn)在跟以前不一樣了,大概不會再來搞一個統(tǒng)編教材。現(xiàn)在,一本書都可以前后各部分由合作撰寫者各自寫,不求統(tǒng)一,反而是中小學要用統(tǒng)編教材了。
李:您后來還研究文學基礎理論嗎?
黃:我主編了那本《文學理論新編》,主要吸取了“文化大革命”后文論界的一些研究成果,如注意主體性研究、文藝特點研究,有些特殊現(xiàn)象如“靈感的探討”等。
李:就是說,在您的這本教材之前,你們學校一直用的是《文學的基本原理》?后來,就被您主編的教材替換了?
黃:對。我的那個是1986 年出版的。但《文學的基本原理》在1983 年又出了第三版,其中前言是我寫的,比較簡單,就交代一下編寫經(jīng)過,那本教材當時又用了幾年。我的這本教材書是1986年出的,然后就開始用我們自己的了。再后來,又有了新的教材。
李:現(xiàn)在您主編的那本教材還用嗎?
黃:現(xiàn)在這個教材有沒有用,我也搞不清了,因為我退休多年了。
李:如果繼續(xù)使用,重新印的話,應該給您支付版稅的。
黃:那個時候是不講版稅的,現(xiàn)在估計沒有再重印了。使用情況就比較多樣了,有的教師喜歡、習慣某部教材,會把它作為主要參考書或者課堂講授的講義。
人大進修
李:據(jù)我所知,您60 年代編寫《文學的基本原理》之后,還到中國人民大學進修過。您是被公派去的?
黃:人大我是考去的。當時學員分兩部分人,一部分是各地作協(xié)、雜志領導和宣傳部門的一些干部,還有一部分是高校的骨干教師。
李:除您以外,上海還有別人去嗎?
黃:有的。好像復旦沒有人去,上師大也沒有人去,音樂學院、戲劇學院有人去。我們學校比較重視。我丈夫那時在松江參加“四清”試點工作,領導跟我講,有個去人大進修的機會,你愿不愿意去考下試試?我想,去當然好了。只是沒辦法和家里人商量,就說,有可能的話就去考。當時是市委一個處長監(jiān)考,前后考了兩天,我有一些題目也忘記了,就記得要當場寫一篇文章,關于《青春之歌》 或者是《紅旗譜》 的文章。具體題目也忘記了,因為密密麻麻地有好多題目。之后,通知了我,歡迎我去,那我就去了。我很珍惜這次機會,算是我畢業(yè)后第一次能集中力量大量閱讀,向周圍眾多專家、同行學習。學習內(nèi)容主要分幾部分:一是馬列的著作,馬奇給我們講《1844 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一是文學理論專題,何其芳給我們講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及當時延安文藝界的情況。記得當時我認真翻閱了1942 年一整年《解放日報》副刊上的文章和發(fā)表的文藝創(chuàng)作,以加深了解《講話》的背景。班上由我將同志們學習毛澤東《講話》和聽了何其芳講課后提出的問題整理成書面材料,又和另一位同志到何其芳先生家里,親手交給他。他表示要再次到學校向大家答疑。告別時,他親自送到門口,并且在院中那棵大樹下停留著,再次詢問大家的生活、學習情況,關切之情,令人感動,忽然像他所寫的《生活是多么廣闊》 《我為少男少女們歌唱》兩首詩歌的韻味在胸中升騰……我們還聽王金陵講“蘇修文藝介紹與批判”,聽著名專家與作家開的講座,觀看西方繪畫流派演變中的代表作、各國有影響有代表性的電影。當時,距鐵獅子胡同不遠有個蟾宮電影院,專門放映各國各時段的代表作品,我們經(jīng)常去補看那些應該看而沒有看的電影,而且享受“學生”待遇,影院里的人都知道鐵獅子胡同里有一批三四十歲的“大學生”是憑學生證買學生票的。
80 年代,我從北戴河開會回來時,跟蔣孔陽先生都住在人大招待所里。那次,馬奇請蔣孔陽吃飯,他跟蔣培坤都在人民大學哲學系,就叫上蔣培坤陪同。蔣培坤是華師大畢業(yè)的,我們等于是前后校友。蔣先生叫我陪同,我們在一起吃飯,談話比較隨便。我講到60 年代在人大文學進修班聽馬奇講《1844 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的情景。
李:馬先生人很好,也很認真,我曾做過他的訪談,他是2003 年非典時期去世的。
黃:馬奇先生講課很認真。我們進修班原定兩年,后來根據(jù)形勢提前一年結(jié)業(yè)。在這一年里我認真讀了幾本馬列的書,閱讀了這些著作中涉及的文學作品,研究了幾個理論問題,聽了許多講座、報告,他們講的內(nèi)容精彩,講課時的神態(tài)、激情和風采讓我難以忘懷。這一年讓我開了眼界,提高了理論修養(yǎng),給我以后的教學、科研帶來了不一樣的風景。我回來后,就給學生上馬列文論的課。實際上,一回來氣氛就變了,我到安徽參加“四清”運動。之后,“文化大革命”就來了。但是我學的東西沒丟,雖然停課了,但生活在繼續(xù),學習也要繼續(xù)。
動蕩歲月
李:“文化大革命”期間,華東師大還招收學生嗎?
黃:招過兩屆一年制的培訓班。1970 年冬正式招收工農(nóng)兵學員,不是考試選拔的,是由各地所在工廠、公社和部隊挑選后保送的。這批學員文化水平不一,有的高中畢業(yè),有的小學程度。學員入學要擔負“上、管、改”任務,也即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因此要批判資產(chǎn)階級教育路線。開學的第一課是拉練,從上海拉練到安徽廣德,當時的口號是“練就鐵腳板,打擊帝修反”。全體師生以營、連、排編制。我們白天上課,晚上學習《毛選》,有時也安排教師講毛主席詩詞,或批判資產(chǎn)階級。各系好像都找一個靶子來批,我們系是批錢谷融;政教系在我們前面,聽說好像是在批馮契。拉練結(jié)束,我們也上課,但批判資產(chǎn)階級始終堅持。學《紅樓夢》 批判“《紅樓夢》 是愛情小說”的觀點;學魯迅,學習魯迅的戰(zhàn)斗精神,要痛打“落水狗”;學樣板戲,就講樣板戲。
李:那時,老先生都靠邊站了吧?當時上課的老師應該是你們這撥人吧?
黃:一般是我們這撥人。“文革”初期,大多有年紀大的老師擋在前面。后來去和學生一起下鄉(xiāng)搞教改實踐、勞動、拉練、觸及靈魂搞批判,就是我們這撥人了。當然有些身體還可以的老先生也一樣參加拉練、到干校勞動。錢谷融先生就參加拉練,到洪涇教改小分隊搞教改、大文科。我和他還一起在“五七”干校挑大糞,挑是挑不動的,主要負責掏。
李:你們當時在什么地方勞動、改造?
黃:“五七”干校我去過兩次。一次在大豐農(nóng)場,邊上就是勞改農(nóng)場,去了一年。一次在奉賢“五七”干校,1976 年7 月去的,直到1977 年2 月回學校。我和工農(nóng)兵學員一起到上港三區(qū)參加卸貨勞動,到襪廠定型車間勞動,到天馬山調(diào)查血吸蟲病的治理,和學員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其他還有“三夏”“三秋”的勞動等等。
后來好些了,干校搞了一間圖書室,可以在這里看看報,報紙有好幾種。我常常在晚上穿上長筒套鞋防蚊子,坐在圖書室里面翻看報紙。信件和報紙是干校派人到南橋去拿的。一天,我從干校廣播里聽到恩格斯的《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聽到那熟悉的論斷:“馬克思發(fā)現(xiàn)了人類歷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那歷來為繁茂蕪雜的意識形態(tài)所掩蓋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zhì)的生活資料的生產(chǎn),因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jīng)濟發(fā)展的階段,便構(gòu)成為基礎,人們的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我內(nèi)心涌動著,隱隱地感到不會再那樣聲嘶力竭地批判“唯生產(chǎn)力論”了,社會可能會有變化,沿著正確的軌跡變化。以后學校恢復教研室的時候,系里宣布我為文學理論教研室主任,重新走上講臺,規(guī)劃課程,要寫文章。當時我寫了一篇討論形象思維的文章,發(fā)表在《華東師大學報》的復刊號上。
李:這是哪一年?
黃:1978 年了。
李:“文革”后,您正式給學生上課是哪一年?您的課基本上沒停?
黃:我是1978 年77 級同學入學正式給他們上課講文學概論的。之前,我的課斷斷續(xù)續(xù)沒有停過,有時候到教改小分隊,有時和工農(nóng)兵學員在勞動中,我到洪涇大隊政教系辦的教改分隊,辦大文科。原定計劃抽我去講毛澤東文藝思想,后來小分隊實行“三三制”,一部分人搞革命,一部分人上課,我和歷史系的教師分配到隊里勞動。需要就叫你到駐地上課,否則就在隊里搞“三同” (同吃、同住、同勞動)。我趁這個機會學習了棉花種植的全過程,老鄉(xiāng)還試著讓我跟著他弄秧田。
步入正軌
李:“文化大革命”之后,各行各業(yè)逐漸恢復正常。您的教學、研究也常態(tài)化了吧?
黃:粉碎“四人幫”以后,學校恢復正常的教學秩序,有正式排課表,嚴格按排課表上課。1978年我就正式上課了,先上文學概論課,后來上馬列文論課。
李:您不是1986 年還出版了那本《文學理論新編》嗎?怎么就不上文學概論課了呢?
黃:有的時候還是上的,如自學考試班的課。因為所有留下來的新教師,必須給他們鍛煉機會,先上文學概論課。
李:“文革”以后,你們教研室留下來的新教師有哪些?
黃:人員變動是一方面,還有新留下來的77級畢業(yè)生如夏中義、宋耀良,后來有方克強,還有73 級陳勤建。夏中義、宋耀良、方克強都是《文學理論新編》的執(zhí)筆人,通過寫書進一步深入學習和思考了理論問題,要給他們講課的平臺。
李:張德林老師是新來的老師嗎?
黃:他是因為“右派”問題,被調(diào)到一個中專學校,那里就不一定上專業(yè)的文論課了。
李:他是粉碎“四人幫”后就回來的嗎?
黃:對,粉碎“四人幫”以后就調(diào)回來了。他主要跟徐先生負責雜志,給學生上作品賞析課和寫作實踐課,講課和寫作,他更擅長、喜歡寫作吧!
李:他不在文藝理論教研室嗎?
黃:不在,他的志趣比較多的在鑒賞上面,還跨了現(xiàn)代文學,這從他寫的東西也都看得出來。
李:您與樓昔勇老師在一起吧?
黃:樓昔勇是研究美學的。因為當時北京辦了一個美學班,他去了。回來以后,他也喜歡,既然這樣,就主要教美學。教師到了一定程度,大家的特長都能夠明顯一點,整個教研室就可以豐富一點,對學生也有好處。樓昔勇后來跟夏之放、劉叔成他們編了一本美學原理的書。
后來,我跟北師大劉慶福一樣,教馬列文論課了。我們和全國部分高校合作,主編了《馬克思主義文藝論著選讀》。劉慶福老師人很實在,身體好像有病,他做過系主任。
馬列文論方面,根據(jù)我自己的學習情況,結(jié)合文藝現(xiàn)狀寫了一些東西。后來,上海市委宣傳部可以資助出書,系里叫我申報一個項目,我就把之前寫的有關文章集結(jié)起來形成了一本書《馬列文論與文藝現(xiàn)實》。我還跟其他同行搞了一些東西,也是一個交代。我們學校的文藝理論跟其他學校一樣要開設各種課程,除了這個特點以外,比較特殊的一點就是辦雜志。
李:你們學校有幾本雜志?
黃:一個《文藝理論研究》,一個《古代文學理論研究》,一個《詞學》,還有一個是《中文自學指導》,是關于中學語文教學的。這個是我們學校與國內(nèi)其他高校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徐中玉先生出了很大的力。
李:您編過雜志嗎?
黃:我參加過。
李:您參加過哪個雜志?
黃:我參加過《文藝理論研究》雜志的工作,我只是兼職做些編輯工作,閱讀一些分配給我審看的有關稿件,參與有關方面的問題討論。
我們教研室在1978 年主持召開了一個關于典型問題的文學理論討論會,全國各地來參加這個討論會的有幾十位,人們熱情得不得了。有些是“文革”前我們就認識的,有些是后來認識的新朋友。會上,有人提出要華東師大牽頭搞些學術活動,要我們定期這么搞。我覺得自己沒有這個力量,那個時候有要徐中玉先生出來擔任工作的呼聲,我就跟徐先生商量,請徐先生出來負責,籌備成立學會。關于這個學會,最初師大方面就是這樣醞釀的。
李:您當時是文藝理論教研室主任?
黃:對。擔子在身上好做事,徐中玉先生負責系里工作后,根據(jù)方方面面的情況,多方面協(xié)調(diào)、醞釀,后來1979 年5 月在西安會議上成立了中國文藝理論學會,陳荒煤是學會首任會長。
李:當時,你們既要上課,還要辦雜志?
黃:對。學會成立以后,我們系和學會就合辦《文藝理論研究》雜志。辦雜志是很辛苦的,因為沒有專門編制的人員,有關的稿子我們是分頭看。如果你專門搞這個方面的研究,這個問題你更熟悉,就叫你看。看了以后就寫意見,能用的就推薦,如果是明確不能用的就表態(tài),然后處理。我這個編委是創(chuàng)刊前后當?shù)模傻靡埠莒`活,張德林負責具體工作,我只是兼職看看稿。還有一個事情,就是辦班。
李:你們學校好像辦過一個古代文學理論的教師進修班?
黃:古代文論班和我們辦的班不是一個班,一個是1980 年,一個是1982 年。
李:還有不同的班嗎?我只知道有一個古代文學理論的進修班。
黃:古代文論班的影響比較大,是教育部委托辦的。我們的班是我們系自己辦的。
李:這個班的名字叫什么?
黃:我們的叫全國文學理論教師進修班。這個班是徐中玉先生和錢谷融先生領銜,我是班主任,還有一個教師陳貽恩是副班主任,辦班有很多具體的事務要做。我們發(fā)了通知以后,歡迎大家來報名,看報名的情況,基本上都能夠滿足要求。
李:當時你們辦了幾期?學生大約多少人?
黃:就辦了一期。學員來自于全國各個高校。我們這個班的學員不像古代文論班,古代文論班里,有的學員都是副教授或者老講師了,有自己的計劃和研究方向。我們這里很多學員是寫作課的教師轉(zhuǎn)到文學理論課的。我們辦班請了很多人,花了比較多的精力,等于一個個去找老師,一個個到家里親自去請。請的時候,跟專家本人聊天,他們感興趣的或者正在研究的題目,如果符合我們的需要,就定下來。
李:當時你們請了哪些先生來授課?
黃:我們請了馮契,講“真善美”,他正好要發(fā)表這方面的文章,我們請王道乾講“法國的文學流派和現(xiàn)代派”,請吳調(diào)公講“文藝真實問題”,請蔣孔陽、伍蠡甫講“形式美”,請草嬰講托爾斯泰,請王西彥講“現(xiàn)實主義”,請孔羅蓀講“文學動態(tài)”,等等。他們都很支持。系里則是徐中玉、錢谷融和我負責講課。
李:王道乾翻譯了不少東西。他是上海的學者嗎?
黃:他在《上海文學》理論組,我曾經(jīng)到他家去請他給我們班學員上課。他有一個觀點很有意思,我問他對現(xiàn)代派怎么看?他認為,拿現(xiàn)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這條線索來講,現(xiàn)代派實際上屬于消極浪漫主義。他對自己的這個看法是很當回事的,跟我講了好幾遍,還說,你跟學員再談談看,問他們有什么看法。他早年編過《馬克思恩格斯論文藝》一書,我說,你那么年輕就編過書!他說,那個時候是年輕。看得出來,他對自己的成績還是很高興的。他很有才華,要是集中力量搞法國文學,肯定能做得很好。
李:他一直在國內(nèi)?
黃:他是法國留學歸來的。有文章寫到他從法國回來以后,曾經(jīng)覺得文學沒有用。他的一位在法國的朋友寫過,說自己從法國到中國來,與王道乾再見面的時候,王的話不多了。“文革”中和他見面,我問他還好嗎?他說自己被打倒過,點名打倒他,他就倒了。很簡單,說話時還帶著一絲笑。我們聽的人無言以對。
李:中國古代文論那個進修班給高校培養(yǎng)了很多老師,滿足了時代的需求,極大地促進了古代文論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黃:中國古代文論的那個班,是教育部委托辦的,主要由郭紹虞先生來領銜,有許多教學方面的事要多方面協(xié)調(diào)、配合。
李:郭紹虞先生、許杰先生都在那個班上過課?
黃:許杰是搞現(xiàn)代文學的。
李:徐中玉先生給他們上過課。
黃:對。徐中玉是班主任,陳謙豫是副班主任。這個班影響很大。還有一個是《古代文學理論研究叢刊》,等于會刊,相當于我們這里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的《文藝理論研究》,不過,我們的刊物是大開本的,而《古代文學理論研究叢刊》就像一般的書本一樣,蠻有影響的。這個刊物原先是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來拿到華師大出版社來,編輯部就在我們這邊。
李:陳謙豫先生跟您是不是在同一個教研室?
黃:沒有。他是古代文學教研室主任,我們?nèi)A東師大這里,古代文論是屬于古典文學教研室的,強調(diào)的是古典文學,不像北大張少康他們在文藝理論室,各個學校情況不大一樣。我們的古代文論是放在古典文學教研室,那些老師都是教古代文學的。像陳謙豫是讀過私塾的,所以他詩詞都做過,留下來當助教時是跟著一位老師萬云駿,還請萬先生看過自己寫的詩詞集。萬先生是吳梅的學生,就是那個研究詞曲的大家。陳謙豫教歷代文學作品選,教文學史課程,還參加了影響很大的《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的編撰,并在“文革”后協(xié)助主編朱東潤先生修訂完成了全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六卷本的新版。
李:陳先生參與過《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的工作,出了不少力。他自己編過類似的書嗎?
黃:他自己主編過一本《歷代名篇選讀》,分為上下兩冊,5 次再版重印。1988 年修訂交稿,90年代的修訂版是合為一冊出版的。然后就是朱老的這部統(tǒng)編教材。
李:我們讀大學時,使用的就是那套教材。
黃:后來,還出過兩本的簡裝本。朱東潤先生對謙豫很好,他經(jīng)常到朱先生家商量篇目選定和交換意見。
李:那陳先生后來為什么搞古代文論了呢?
黃:復旦比較早就有批評史的課程,南大也有。陳謙豫很早寫過文論的文章,“文革”前就有討論李卓吾小說評點的論文。有一次錦江飯店有四天會議,就是討論批評史教學研究的會議。系里領導說,人家都有批評史課,我們應該開這個課,于是叫陳謙豫準備給學生上這個課。同時,也是在1958 年的時候,他跟學生也編教材,就是后來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負責《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專題資料叢刊》 的季壽榮那個年級的同學。“文化大革命”爆發(fā),批評史的課也都停止了,謙豫的《中國小說理論批評史》專著也被擱置下來,直到80 年代才問世。
李:您剛才提到錦江飯店的會議,當時還專門開這么高規(guī)格的會議?
黃:1961 年12 月1 日到4 日,上海市高教局在錦江飯店召開中國文學批評史座談會,討論了復旦大學、南京大學編寫的兩套文學批評史教材,就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和提高教材編寫水平等議題展開了討論。夏征農(nóng)、俞銘璜、曹未風、郭紹虞、朱東潤、劉大杰、伍蠡甫、郝昺衡、錢仲聯(lián)、王氣中、蔣祖怡、陸侃如、趙景深、管雄、胡云翼、馬茂元、吳調(diào)公、王運熙、陳謙豫、葉子銘等出席了會議。曹未風(時任上海市高教局負責人)、朱東潤、王氣中、蔣祖怡、錢仲聯(lián)、劉大杰先后主持了會議。與會的領導、學者對相關問題坦率地發(fā)表了個人的看法,不少看法很有道理,至今還仍有參考價值。俞銘璜(時任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 在會議的第二天上午作了專題性的長篇發(fā)言,在第四天下午又作了大會總結(jié)發(fā)言。2009年,謙豫寫了《錦江飯店的四天———中國文學批評史教材座談會紀要》這篇文章,發(fā)表在《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28 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講述了這次會議的詳情,留下了一份難得的記錄,很有意思,也很有價值。
李:后來,怎么考慮到要編古代文論的專題資料?
黃:等到“文革”結(jié)束以后,再招研究生時,就把研究生和其他一些人的力量組織起來,搞了那個古代文論的資料,就是《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專題資料叢刊》,徐中玉先生是主編,陳謙豫是副主編。這個資料開頭是分專題成編,一本一本出版的,各編沒有完全出完;后來重版,集成四大部16 開的精裝本。這件事也幾經(jīng)磨難:一個是人員問題,歷時很久,人員變動大,要補充、調(diào)配;還有就是在整個過程中,要不斷補充文獻、更換材料;再有就是經(jīng)濟大潮來時,出版社不賺錢,這個書不是一下子能夠產(chǎn)生轟動的東西,是細水長流慢慢推出、發(fā)生作用的,所以出版就是一個很大的難題。我們系里的郭豫適教授(曾任華東師大副校長) 講,一個集體項目,總要有人頂住,哪怕一個人堅持住,咬住不放,最后才可能有成果。
李:主要還是陳先生在繼續(xù)做?
黃:他繼續(xù)做這事,花了不少精力。徐先生看著慢慢變老,后來不大能與人交流了。最后四部書出來,那天正好太陽好,他們叫了一個小車,把書送到徐先生家。天好,我想去看看徐先生,就一起去了。徐先生微笑迎接,但要他題字簽名的時候,茫然了,要謙豫指點他簽名的地方才動筆。
謙豫協(xié)助徐先生編《古代文學理論研究》,還做了中國古代文論學會多年的秘書長,為每次年會的召開,多方協(xié)調(diào),結(jié)交了許多同行朋友,做了不少為大家服務的工作。陳謙豫是2018 年走的,錢先生是2017 年走的,徐先生是2019 年走的。
我的老師們
李:施蟄存先生去世得早?
黃:施先生年歲比他們大,他是1905 年出生,2003 年去世的。
李:你們讀大學的時候,施先生給你們上過課吧?
黃:他教過我們的,我們都聽過他講課。施先生給我們上文學史,唐宋以下的部分。徐震堮先生沒有給我們年級上課,但是他代課,那個時候是教研室主任,哪個老師來不了,他就來代課。程俊英是給我們上《詩經(jīng)》課,羅玉君先生是上外國文學課,王西彥常被請來做講座。
李:毛時安他們也都參加編輯資料了嗎?
黃:參加了。
李:他文章里說自己參加了。主要力量應該是咱們學校的老師吧?
黃:主要是研究生和本校教師,還有進修班的老師。
李:就是校外來進修的學員嗎?
黃:是古代文論進修班的王汝梅他們一批人。《資料叢刊》前面有陳謙豫寫的工作人員名單。
李:這個時間跨度還是挺長的?
黃:這個書持續(xù)30 多年了。所以,有的時候搞一樣東西回過頭看都多少年了。
李:就像您編寫的文學理論教材,實際上,您從華東師范大學教學時就開始了。
黃:有的時候,尤其一個人的培養(yǎng)也是很難講的。有的可能是學校里一些好的措施,還有科研小組里的一些人,都會起到很大的作用。對于老師來說也是,當時可能很普通,你們學生有一個組織,有興趣,那就由我來管管吧。但對學生來講,他看了書,有問題就來問了,就找上你了,可能慢慢就走上了這條路。
李:你們編《文學的基本原理》時,孔羅蓀就是你們的顧問了。他在文學界的影響好像挺大的?
黃:孔羅蓀是上海作協(xié)的黨組成員。“文革”以前作協(xié)的會員很少,理論組就是他管的,也編雜志。他人脈關系比較豐富,像我們到北京去要找哪些人,他打個電話約一下,我們就方便了。
李:解放前他是不是在你們這里工作的?
黃:孔羅蓀在東北待過,他好像有這個經(jīng)歷。“文革”期間五校合并時有段時間,他在我們中文系現(xiàn)代文學支部。那時我們也不問他是因為什么原因受審查,審查他什么。他在受審查的狀態(tài)下轉(zhuǎn)到我們這里感到放松一些。后來他的問題解決了,一起開會時還說到他對在師大這段日子印象很好的。后來我從雜志上還看到他寫的一些回憶文章,講到葉以群當時做地下工作,幫助自己同志順利完成任務,至今十分感激。他們?nèi)嗣}很豐富。
李:施先生被打成“右派”以后,就沒怎么上課了吧?
黃:“摘帽”以后還上的。徐中玉“摘帽”后,我們請他給青年教師講《文心雕龍》,就在他家會客室里,大約每周一次,定期的。
李:后來施先生還一直給學生上課嗎?
黃:有段時間在資料室工作。“文革”中恢復教研室的時候,工宣隊等系里領導認為他和魯迅有過爭論,將他分在現(xiàn)代文學教研室。一次,遇到施先生,他對我說:你告訴謙豫,讓他在古典文學教研室替我放張桌子。我明白了,他還是想在古典文學教研室,上古典文學的課。他帶了好幾個古代文學研究生,好像是恢復招生之后系里第一個帶研究生的。
李:他后來寫了好多文章,晚年一直在寫。
黃:他一直在家寫,一次我到他家去,他拿出一份登了他文章的報紙給我,很高興地說:“給你看看。”他后來出了一本《唐詩百話》,很有影響。
辦班的時候,我們本系的教師,徐中玉先生講了“幾個文藝理論問題”,錢谷融先生講了“文學的具體性”,我講“馬克思恩格斯論典型”。我也想請施先生講課。但他有點脾氣,他是性情中人。
有一次,石西民來上海了,打電話到系里問:施先生在不在?想見見他。然后,系里的人就到處找他。正好我在資料室看書,見他從外面進來,我說,施先生,石西民來了,他想見您。他看看我,有點不高興,說:“誰來都叫我去,我怎么工作?我不認識他。”然后,轉(zhuǎn)身又去找資料了。
有這樣的前例,我怕要是請他來給學生上課,他不肯,一口回絕,就麻煩了。我就請徐先生給他寫了個條子,說明學生的識荊之意,拿了這個給他。他說,好。他就是有點脾氣,人蠻好的。有一次,他托一位老師告訴我,施先生問你好。我說,我知道了,就趕緊到他那里去了。見了面,也沒什么事情,就是聊聊天。
他上課很風趣的。我一年級剛進校,那時他翻譯了一本書。有次下課,他跟我一起走,要分開的時候,他把這本書翻出來給我,說這本書是我翻譯的,你找一找看有沒有錯處?快點給我。那個時候,我還不懂得怎么出書,我想,怎么會不通呢?每一次你跟他講話,他都有一些話很生動、很風趣,你會老記著。
李:他學問很好。
黃:對,他實在厲害,能創(chuàng)作,會翻譯,寫文章,還研究碑帖。施先生是我們的老師,是個大家,非常風趣,是一位可以開開玩笑的老師。
李:您當時讀大學的時候,許杰先生是系主任吧?他后來還搞創(chuàng)作嗎?
黃:后來創(chuàng)作也難搞了。實際上,他大量的精力都放在行政上。有一次中央電視臺來,大概是許先生有文章被他們收到書里去了,但沒有給他書。請他去。中央電視臺請我是去講課,主要是講《文學概論》。
李:有教學活動,應該是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吧?
黃:對,大概是中央電視大學。當時,在我們前后,還請了余秋雨、劉叔成。我跟許先生排在一個上午,他也蠻隨便的。我跟他一起,就讓他先講。他講完了,不回去。我說,您可以先回去休息。當時許先生已80 多了。他說,我坐在這里要聽你講些什么,我現(xiàn)在不知道外面都講些什么東西。后來他一直把我的課聽完,等我代他向臺里的同志要書,答應寄來,才一起回師大。
李:王元化先生是華師的兼職教授。20 世紀80 年代,他在哪里工作?
黃:他曾經(jīng)在上海宣傳部工作過。
李:是1978 年嗎?
黃:1978 年他還沒在宣傳部。
李:他那個時候是不是在上海文學研究所?
黃:當時他的胡風問題好像還沒有徹底平反。
李:這個應該晚些。
黃:1980 年在廬山召開學會第一次會議的時候,記得他是參加的。
李:王元化先生從宣傳部長位上退下來以后,一直在華東師大嗎?
黃:他在華東師大做兼職教授。
李:他的單位還在上海宣傳部?
黃:我們這里算兼職,他當時是市委干部。
李:王智量先生跟您的年齡差不多吧?他翻譯了不少東西。
黃:比我大六七歲吧。他也是因為“右派”問題吃了苦,他是在北京出了問題,到西北去的。“四人幫”粉碎后,才從西北回到上海。他是上海人,在我們這里外國文學教研室。
我親歷的學術活動
李:粉碎“四人幫”以后,上海文論界還挺活躍,學術活動也多。
黃:總的來說,我們的活動不少。我參加的,一個是市里面作家協(xié)會這一頭,有的是活動,有的是討論一些文學問題。一個是美學學會討論一些美學問題。又如像新書出來要討論這一類的,我就參加過蔣孔陽《美學新論》一書的專門討論會。還有一些外國作家來訪之類的,像聶華苓跟她先生安格爾一起到作協(xié)的活動,我記得當時黃宗英還朗誦了安格爾的詩。“四人幫”剛粉碎時, 《上海文學》的李子云等搞了一個關于文學工具論的座談會,我去參加了,大家當時討論得很熱烈。
李:當時,署名《上海文學》評論員的文章是誰寫的?
黃:那個不清楚。我記得那個時候有的會議是李子云主持,她現(xiàn)在已經(jīng)走了。還有,周介人也去世了。參加討論的人不少,很多人都講,要多給文學自由,政治要寬松。有人講,政治跟我們沒有什么關系。我想,這個話是不對的。我就沖口而出,說政治跟我們沒有關系的話,大家坐在這里要求寬松干什么?正是因為覺得緊了,所以才要求寬松。這個是基本的理論問題。王元化當時就說,我們發(fā)表意見要像研究生答辯那樣,要經(jīng)得起辯論和檢驗,你講了以后大家可以問你。
李:你們教研室在廬山開的那次會議,影響還是挺大的。
黃:廬山會議是系里出面組織、徐中玉出面籌備的,到會的人特別多,那個會上談的就是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看到過一篇文章,好像丁玲在這個問題上有保留意見。
李:她是不是也去參加會議了?
黃:是的。可能因為她才從那個環(huán)境里轉(zhuǎn)過來。她說,我們黨叫我當作家,后來,不叫我當作家,我就不當了。實際上,各人的情況也不一樣。
李:北京的顧驤、王若水、丁玲他們都參加了,說明那個會的影響還是挺大的,參會者不僅有高校的老師,也有社會上的人。
黃:因為粉碎“四人幫”以后,各種會議都還沒有恢復,聽說有這么一個會,大家都要求參加,聚在一起討論問題。要是會議多了,可能就分散了。我就是籌備會議的時候參加得多些。因為是從我們這里發(fā)起的。1978 年我們教研室搞了一個文藝理論討論會,許多學校的老師、同行都來了。在這個會上許多同志倡議成立學會,要正式成立學會,我覺得范圍會很大,我的經(jīng)驗和能力也都達不到了。徐先生已經(jīng)出來工作,他有這個能力,也相當。
李:當時討論“文學是否是階級斗爭的工具”,您當時參加那個討論了嗎?
黃:參加了。沒有寫正面辯論的文章,但結(jié)合教學寫了幾篇政治家與文學家、政治與文藝關系的理論文章,像列寧與高爾基的關系,都是從文論的角度來寫的。
李:現(xiàn)在那幾個學會,像中國古代文論學會也是掛靠在華東師大中文系的嗎?
黃:對。
李:有中國文藝理論學會、中國古代文論學會,還有大學語文研究會。
黃:古代文論學會的活動最經(jīng)常,大學語文學會,因為大學里有這門課。
李:當時,您與蔣孔陽先生應該有不少接觸吧?
黃:我們跟蔣先生碰頭的機會還是有的。
我們上海有一個“三校”文學理論教師交流會,就是復旦、師大和師院,三校理論室的教師定期開展的。在“文革”前,就有這個傳統(tǒng),原來還比較勤一點。“文革”后,三校教師第一次聚會時,吳中杰就喊,說你要恢復這個會,叫我恢復這個會。后來,我們就恢復了。“三校”聯(lián)合,定期交流一下,有些什么理論動態(tài)動向,有什么問題需要討論,大家的看法是什么,大家都講講,這個還是蠻好的,就等于有一個定期交流的機會。
“文革”后第一次會是在上海師大開的,那個時候華東師大還沒有獨立出來。因為“文革”當中,我們跟上海師院并校了,校名稱為上海師范大學。當時,我們還沒完全分開的時候,就開了一次會議,蔣孔陽也去了。以后,蔣先生多次請我參加他的研究生答辯會,在作協(xié)、美學學會一起開會,見面機會不少的。
李:“文革”期間,蔣孔陽好像沒被打倒吧?
黃:“文革”期間我們沒有來往,學校之間也沒有學術活動和交流。
李:但當時也批判他。
黃:具體情況不清楚。要批判,總得找對象吧,蔣孔陽當時在復旦年歲大一點,資格也老一點,又寫了書。蔣先生也不容易,他那個時候搞翻譯,“四人幫”粉碎以后,他就出版了外國文藝理論的譯著,像李斯托威爾的《近代美學史評述》。
李:聽王先霈老師說,您的講師評得很早,在人大進修之前就評上講師了。
黃:我是1964 年大學畢業(yè)8 年后評上的。
李:當時人民大學進修生中講師極少,所以,您就是高級知識分子了。
黃:南京師大的盛思明也是講師。有的人當了20 年助教,像錢谷融就當了幾十年的講師。
李:錢先生是“文革”以后直接就當?shù)慕淌诎桑?/p>
黃:那個是因為他耽擱的時間太長了,現(xiàn)在水平到了,就不要副教授、教授一級一級提升了,可以直接升教授。領導聽了這個意見,但還是鄭重地請錢先生上一次全校公開課,廣泛征求意見,結(jié)果是可以直接提升教授。
李:您和其他學者也有不少接觸吧?
黃:錢中文的那本《文學發(fā)展論》出來時,到上海找我們幾個人開過討論會,后來在雜志上發(fā)表了。他身體不太好。還有就是童慶炳牽頭、大家合作的“文學概論”自學考試教材那本書,找杜書瀛審的稿。他看了書稿之后出版的,他身體很好,給人很結(jié)實的感覺。外文所吳元邁的年齡比我小點,他參加會議在上海停留,有一個晚上我請他給學員們講了一次課。我們有幾次在馬列文論年會上見到,交換意見,討論問題。
李:您談了這么多有價值的材料,幫助我澄清了不少疑問。再次感謝您的支持,并祝您身體健康、長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