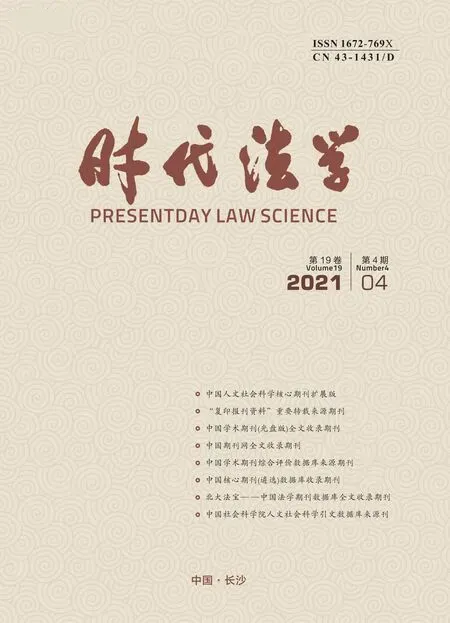反制國內法域外適用的工具:阻斷法的經驗及啟示?
黃文旭,鄒璞韜
(湖南師范大學法學院,湖南長沙 410081)
近年來,美國頻繁對中國境內主體采取各類國內法域外適用措施,引起了黨和國家的高度關注。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要加快推進我國法域外適用的法律體系建設〔1〕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EB/OL].(2019-02-25)[2020-10-10].載新華網,http:/ /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2/25/c_1124161654.htm.。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再次強調,要加快我國法域外適用的法律體系建設〔2〕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EB/OL].(2019-11-05)[2020-10-10].載新華網, http:/ /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11/05/c_1125195786.htm.。實際上,黨中央要求加快我國法域外適用體系建設的目的是與美國法域外適用措施形成制衡,以間接反制美國法域外適用〔3〕廖詩評.國內法域外適用及其應對——以美國法域外適用措施為例[J].環球法律評論,2019,(3):176.。 一些國家則制定了“阻斷法”,明確本國個人和實體不得遵守具有域外效力的外國法,以直接反制美國法域外適用。 在中美經貿摩擦不斷升級的情況下,學界也呼吁我國應盡快制定阻斷法,以反制美國日趨擴張的長臂管轄〔4〕肖永平.“長臂管轄”的法理分析與對策研究[J].中國法學,2019,(6):62;佟欣秋.基于國家主權的反壟斷法域外管轄權的實現機制[J].大連海事大學學報,2010,(4):39-40.。 2020 年6 月20 日,調整后的全國人大常委會2020 年度立法工作計劃正式對外公布。 計劃提出,要“強化對加快我國法域外適用的法律體系建設,阻斷、反制‘長臂管轄’法律制度的研究工作”〔5〕羅沙.全國人大常委會調整2020 年度立法工作計劃個人信息保護法等多部法律草案將提請審議[EB/OL]. (2020-06-12)[2020-06-20].人民網,https:/ /baijiahao.baidu.com/s? id =1670022420426053498&wfr =spider&for =pc.。 阻斷法正式進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工作計劃。 2021 年1月9 日,商務部頒布《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以下簡稱“《阻斷辦法》”),是我國阻斷立法工作的初步實踐〔6〕商務部令2021 年第1 號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EB/OL].(2021-01-03)[2021-01-12].商務部網站, ht?tp:/ /www.mofcom.gov.cn/article/b/c/202101/20210103029710.shtml.。 《阻斷辦法》全文共十五條,多為宏觀層面的制度規定,有待未來相關法律法規以及具體細則對其予以進一步細化落實。 此外,《阻斷辦法》僅適用于外國法律與措施的域外適用不當禁止或者限制中國主體與第三國(地區)主體進行正常的經貿及相關活動的情形,不能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在經貿領域以外的域外適用。 有鑒于此,本文將深入考察其他國家阻斷法的內容與實踐,并就我國如何總結其他國家阻斷法的經驗以繼續發展完善我國阻斷立法,更好應對美國日益擴張的單邊經濟制裁提出建議。
一、阻斷法的歷史演進
(一)阻斷法的興起:對美國訴訟程序的阻斷
一些國家于20 世紀下半葉開啟了阻斷法的立法工作,通過禁止本國特定主體配合外國法院的證據調查程序,從而阻礙外國于其境外獲取涉及本國特殊行業或事項的相關信息,禁止相關主體為了訴訟目的向特定國家進行證據信息披露〔7〕Erica M. Davila, International E?Discovery: Navigating the Maze,8 Pittsburgh Journal of Technology Law & Policy 34,44(2007).。 法國于1968 年通過的第68-678 號法律是其中最早的一部趨于成熟的阻斷立法,其對于向外國當局提供特定海上運輸信息的行為予以了明確禁止,以此希望阻斷美國對法國海運企業的域外反壟斷調查活動。 法國在1980 年擴大了該法的調整范圍,明確禁止本國主體配合外國法院的訴訟取證程序進而提供相關信息〔8〕李鳳寧.國內法域外適用的反制急先鋒——法國阻斷法研究及啟示[J].國際經濟法學刊,2020,(3):97.。
隨著美國單邊經濟制裁范圍的不斷擴大,20 世紀70 年代開始,著手制定阻斷法的國家逐漸增加。隨著各國阻斷立法實踐的深入,與法國第68-678 號法律同樣以阻斷外國法院程序事項為內容的阻斷法逐漸發展,在信息披露的方式層面進一步細化演變出了大致兩種類型〔9〕M. J. Hoda,The Aerospatiale Dilemma: Why U.S. CourtsIgnore Blocking Statutes and What Foreign States Can Do About It,106 Cali?fornia Law Review 231,238(2018).:一是政府審批型。 此類阻斷法賦予了本國政府主動審批的自由裁量權,以決定他國哪些調查取證行為可以在本國進行。 英國的《貿易利益保護法案》是此類阻斷法的典型代表,其要求政府官員對外國法院的調查請求進行審批,對可能危害英國主權或國家安全的調查取證行為予以禁止,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也采用了類似的阻斷法立法模式;二是當事人申請型。 這類阻斷法以證據內容為立法標準,只要他國法院需要調查的涉案證據涉及特殊行業的生產等國家秘密或重要情報,該類阻斷法便自動禁止此類證據調查行為,除非本國特定主體向政府有關部門申請并得到允許。 然而,上述阻斷法的執行與適用并未完全落實到位。 事實上,這亦是多數阻斷法均面臨的問題,即本國當局對于阻斷法的執行意愿不強烈,制定阻斷法的初衷更多是基于政治目的的考慮〔10〕Bates C. Toms Ⅲ,The French Response to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United States Antitrust Laws,15 International Lawyer 585,590(1981).。 后文將對該現象的成因進行分析。
上述阻斷外國法院程序事項的阻斷法在上世紀60 到70 年代為世界各國廣泛制定,并在“西屋公司”一案中最早得以規模化實踐〔11〕Deborah Senzand Hilary Charlesworth, Building Blocks: Australia's Response to Foreign Extraterritorial Legislation,2 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69(2001).。 美國西屋能源公司在上世紀70 年代末向美國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確認包括南非、澳大利亞、法國等國的鈾礦企業實施了違反《謝爾曼法》的達成壟斷協議的行為。美國法院據此要求各國的被告企業提供涉及本國能源信息的材料作為本案證據于法庭上審查。 上述被告企業均以本國阻斷法為由抗辯美國法院的程序命令并為法院所接受〔12〕In re 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 Uranium Contracts Litigation,563 F. 2d 992 (10th Cir. 1977).。
“西屋公司”一案在使各國制定的阻斷美國法院程序事項的阻斷法得以實踐的同時,也推動了各國進一步發展更為完備的阻斷法體系。 同時,隨著20 世紀90 年代美國通過的一系列針對特定國家的單邊經濟制裁法律的通過,阻斷法的調整對象也不再局限于外國法院調查取證行為。 阻斷法逐漸從原先的取證禁止,逐漸演變出從實體效果上直接禁止外國某些具有域外效力的特定法律在本國適用或執行。該類以阻斷美國實體法律效力為內容的阻斷法成為了國際社會阻斷法發展的新潮流。
(二)阻斷法的新潮流:對美國特定法律的實體阻斷
20 世紀90 年代,美國繼續加強了單邊經濟制裁的力度,相繼通過了《達瑪托法案》《赫爾姆斯-伯頓法案》等禁止相關國際貿易主體與古巴等國的經貿往來。 隨著美國單邊經濟制裁范圍擴大至頂峰以及各國阻斷立法的深入實踐,阻斷法于上世紀90 年代后期逐漸發展出了禁止在本國管轄范圍內適用外國具有域外效果之法律并消除其影響的功能〔13〕Menno T. Kamminga,Extraterritoriality, in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Rüdiger Wolfrum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這一類國際社會新興的阻斷法與前文所述的阻斷美國法院訴訟程序的阻斷法相比,最顯著的特征在于能直接阻斷外國特定法律的域外效力,即直接宣告外國特定法律在本國境內無效。 該類阻斷法興起較晚,其中體系較為完善并為學界討論最多的是歐盟的《免受第三國立法及由此產生行動之域外適用影響的保護法》〔14〕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271/96 of protecting against the effects of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legislation adopted by a third?country, and actions based thereon or resulting therefrom,39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1996).(以下簡稱“《歐盟阻斷法》”),以及日本的《保護公司免受美國1916 反傾銷法影響的特別措施法》〔15〕《損害賠償追償法》的主要內容見:Yokomizo Dai,Japanese Blocking Statute against the U.S. Anti?Dumping Act of 1916,36 Japanese Annu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6,2006.(以下簡稱“《日本阻斷法》”)。 前者于1996 年制定,主要是為了阻斷美國當時頒布的制裁古巴、伊朗以及利比亞等國家的一系列法律對歐盟企業產生的管轄效果,并于2018 年8 月7 日修訂;后者則是日本在2004 年為了阻斷美國依據1916 年《反傾銷法》對日本公司實施的訴訟活動而制定。 上述兩部阻斷法的主要內容包括下述三項:
1.適用主體
對于適用主體,《歐盟阻斷法》與《日本阻斷法》采用的立法模式不盡相同。 《歐盟阻斷法》采取的是列舉式立法,其第11 條規定的適用主體如下:(1)歐盟居民或歐盟成員國公民;(2)歐盟境內注冊成立的法人;(3)歐洲議會第4055/86 號法案第1 條第2 款規定的自然人或法人(包括居住于歐盟境外的成員國公民、受歐盟成員國公民控制的在歐盟以外注冊成立,其船舶依成員國法律登記在該成員國的船運公司〔16〕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55/86 of applying the principle of freedom to provide services to maritime transport between Member States and between Member States and third countries,29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1986).);(4)其他擁有歐盟居民身份的自然人,除非該自然人身處其國籍國;(5)其他處于歐盟境內(包括領水、領空,以及為歐盟管轄或控制的船舶、飛行器)的自然人。 《日本阻斷法》則采用了概括式的立法模式,僅以“受日本管轄之主體等”(Japanese juridical person)一筆帶過。
可以看到,無論是歐盟的列舉式立法模式還是日本的概括式立法模式均包含了擁有歐盟成員國國籍或日本國籍的自然人與法人,即采取了屬人主義的立法原則。 然而,《歐盟阻斷法》第11 條除了第1款和第2 款采取了屬人主義的立法模式外,第3、4、5 款均采用了“身處歐盟境內”的屬地主義原則。 而《日本阻斷法》僅以‘Japanese juridical person’一詞概括適用主體,而對該詞的理解卻存在著“嚴格屬人說”和“目的說”兩種理論差異。 在此試舉一例區分二者區別:一家外國公司將商品從日本出口至美國,美國以《反傾銷法》對其施以制裁,該制裁措施將損害日本國內民商事主體的合法權益,但該外國公司違反《日本阻斷法》規定的法定義務遵守了相應制裁。 就該情況而言,持“嚴格屬人說”的學者認為,《日本阻斷法》的主體應依照嚴格的屬人主義原則進行文本解釋,認為該法適用之主體只包括依照日本法律登記成立的法人和其他組織,以及擁有日本國籍的自然人,故不得以《日本阻斷法》對上述引例中的外國公司進行追責〔17〕Yokomizo Dai,Japanese Blocking Statute against the U. S. Anti?Dumping Act of 1916, 36 Japanese Annu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6,2006.;支持“目的說”的學者則認為《日本阻斷法》一開始的立法目的在于阻斷美國無視WTO 相關貿易規定而制定的《反傾銷法》,倘若對上述引例中的外國公司無法適用,《日本阻斷法》的目的將難以得到實現〔18〕Mitsuo Matsushita and Aya Ilino, Blocking Statute against the U.S. 1916 AD Act—Antagonism between WTO rules and Civil Law(2),Boeki to Kanzei, cited from Yokomizo Dai,Japanese Blocking Statute against the U.S. Anti?Dumping Act of 1916,36 Japanese Annu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6,39(2006).。
本文認為,在解釋《日本阻斷法》中的‘Japanese juridical person’一詞時應采用嚴格的屬人主義理論。 其原因在于:首先,在與之相近的《歐盟阻斷法》所采用的適用主體之規定中,雖然實現了屬地主義和屬人主義兩項國際法基本原則的結合,但其主體范圍仍然未脫離與歐盟成員的聯系。 即便是在歐盟外注冊成立的船運公司,其主要控制人仍需擁有歐盟成員身份;其次,對于上述引例中的外國公司,由于相關商品原先位于日本,若其因遵循美國的《反傾銷法》而對日本的民商事主體造成損害,相關主體仍可以該外國公司為被告在日本境內法院提起侵權訴訟,對自己的權益進行保護,可援引日本的相應沖突規范對法律適用問題進行處理;最后,需要認識到,阻斷法的目的在于阻斷美國肆無忌憚的域外管轄之行使,而非對美國域外管轄的對等反制。 正如有學者所言之“安全閥”條款(即本文所言之阻斷法)本身是一種歸屬于“防御型制度”的應對〔19〕韓永紅.美國法域外適用的司法實踐及中國應對[J].環球法律評論,2020,(4):174.。 從其本質來看,阻斷法仍是國家的防御性手段而非報復措施。倘若依據阻斷法文本,不能在其語義極限內將適用范圍擴大到外國企業,則不宜任意擴大‘Japanese ju?ridical person’一詞的內涵,切不可將防御性的阻斷法升級為主動出擊的報復和制裁手段。 如此為之,既不利于一國經貿活動的正常進行,同時也可能進一步加劇國際單邊主義的演進。
2.民事救濟
《歐盟阻斷法》與《日本阻斷法》均為阻斷立法型的阻斷法,即直接于立法中規定禁止外國某些具有域外效力的特定法律在本國的適用、承認或執行。 然而,兩者在針對相關主體違反阻斷法后的民事救濟方式上對于索賠對象的范圍規定不同。 《日本阻斷法》僅于第3 條規定:“任何因外國法院基于美國《反傾銷法》而受益之人(Beneficiary)并因此對日本主體造成損害,其必須返還因此獲得的所有利益。”可見,《日本阻斷法》對于美國《反傾銷法》的阻斷僅限于通過介入私主體之間的侵權糾紛達成對遵循《反傾銷法》之私主體的懲罰,這也正如一些學者對這部阻斷法的評價:“《日本阻斷法》應被視為一部特殊的沖突法律規則,這部法規制定的目的在于通過聯合私人力量以此實現日本的貿易政策。”〔20〕Yokomizo Dai,Japanese Blocking Statute against the U. S. Anti?Dumping Act of 1916, 36 Japanese Annu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6,2006, p. 45.《歐盟阻斷法》雖同樣允許私主體就因對外國法律的遵守而導致的侵權糾紛提出索賠請求,但其對索賠對象范圍的規定從法案文本上看并未明確限制于私主體。 《歐盟阻斷法》第6 條規定,相關主體可就因遵守附件中的外國法律給其造成損害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實體提出索賠請求。 與《日本阻斷法》第3 條規定的“受益人(Beneficiary)”不同,《歐盟阻斷法》中索賠對象除了自然人和法人以外,“其他主體”的設置頗為耐人尋味。 歐盟于2018 年修訂阻斷法的同時,公布了一份關于阻斷法適用的《指導文件》〔21〕Guidance Note Questions and Answers: adoption of update of the Blocking Statute, 68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4(2018).。 該文件列舉了《歐盟阻斷法》適用的23 個問題并予以回答。 其中,第13 項問題是“美國行政當局是否可以作為被起訴對象”。 對此,這份指導文件的回應較為模糊:一方面,該份指導文件對第13 項問題做出了“需按照個案情況決定”的回答;另一方面,其又在第15 項問題回答中表示,“國家行使國家權力時的作為或不作為不受《歐盟阻斷法》追責”。
本文認為,該指導文件對第13 項問題與第15 項問題的回答本身并不矛盾,其規定之內容只是屬于不同范疇的法律問題。 指導文件第13 項問答解決的是“私主體有權就外國相關法律的適用向誰進行索賠”,第15 項問答則回答了“違反阻斷法的責任主體是否包含國家”;前者指向的是私主體之間的糾紛問題,后者指向的則是歐盟成員國的公權力對于違反阻斷法之主體的追責問題。 故指導文件第13 項與第15 項本身不存在矛盾。 然而,真正的問題在于:即便兩項問答內部不矛盾,但《歐盟阻斷法》第11條規定的適用主體中并不包括外國政府。 倘若認為《歐盟阻斷法》第6 條中的“其他主體”包括外國政府,如何理解第6 條與第11 條之間的關系則成為需要歐盟進一步做出相關解釋的新問題。
3.豁免申請
阻斷法往往為本國主體提供了一定例外免責申請權,即倘若本國私主體遵循相關程序提出申請,則可能無需承擔阻斷法規定之義務。 《日本阻斷法》由于不涉及公權力追責故而無此規定,《歐盟阻斷法》則在其第5 條中規定,若相關主體不遵循外國特定法律將會嚴重損害該主體或歐盟利益,相關主體可向歐委會提出申請,由此被允許全部或部分履行外國特定法律之義務。 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利益損害只有在足夠嚴重的情況下才會被歐委會允許。 這種豁免申請權的保留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相關主體與阻斷法之整體法秩序之間的利益。
綜上,阻斷法從一開始的阻斷程序型,逐漸發展成為對美國特定法律效力的直接阻斷。 由于阻斷美國法院程序事項的阻斷法并未被廢除或失效,故應將阻斷法定義為禁止外國特定法律以及依據這些特定法律做出的行為(包含實體行為與程序行為)在一國境內產生效力的法律統稱。 當今世界,許多國家都著手制定本國阻斷法或對已有阻斷法進行修訂。 通過比較研究可以發現,《歐盟阻斷法》在經歷了1996 年制定后的一系列修訂,其規定更為靈活廣泛,理論上應更加適應對美國單邊制裁的阻斷工作,值得我國借鑒學習。 然而,包括《歐盟阻斷法》在內的各國阻斷法并沒有一勞永逸地阻斷美國相關制裁。經驗研究表明,由于公權力追責制度的設計缺陷,各國阻斷法在執行上都不可避免使本國私主體陷入兩難之困境,很難對相關制裁之執行加以落實,這使得本國私主體難以在美國法庭上建立阻斷法與外國主權強制原則、國際禮讓原則等合理抗辯理由的聯系。
二、阻斷法的發展經驗:執行與司法層面的困境
20 世紀以來,各國陸續開啟了阻斷法的立法工作,積累了大量阻斷立法的經驗。 這些經驗既包含了值得我國借鑒學習的制度設計思路,也包含了因設計的缺陷所導致的諸多困境。 由于公權力追責制度的設計缺陷,阻斷法的執行勢必會使當事人與各國各自面臨一種“兩難境地”。 由此,通過對美國司法實踐的研究可以發現,這種執行上的困難直接導致了阻斷法在美國法院的司法實踐中難以適用,進而無法有效限制美國的單邊制裁。
(一) 阻斷法的執行經驗:執行層面的“兩難境地”
《歐盟阻斷法》第9 條規定:“由成員國對違反本法相關條款的主體決定實施何種制裁,但這種制裁必須是有效、成比例且勸誡性的。”從該條文可以看出,《歐盟阻斷法》將對于違反阻斷法之相關主體的行政處罰權交由各成員國自行規定,即由成員國對相關主體進行公權力追責,只不過這種追責必須達到“有效的”(effective),“成比例的”(proportional)且“勸誡性的”(dissuasive)這三項標準。
對此,歐盟成員國根據《歐盟阻斷法》制定了自己的制裁標準,既有行政處罰,又有刑事追責。 然而,縱使各國制定了相應的公權力制裁措施,這些制裁措施在事實上都難以得到執行。 因為一旦執行,就會使得本國諸多私主體處于一種“兩難境地”,即倘若遵循阻斷法,將受到美國相關當局制裁;倘若違反阻斷法遵循特定外國法律,則將面臨本國政府的追責。 德國法庭審理的“伊朗國民銀行案”〔22〕Bank Melli Iran v. Telekom Deutschland GmbH, Hanseatic Higher Regional Court, C?124/20,02 March 2020.便體現了此種“兩難境地”。 該案中,原告伊朗國民銀行與德國電訊公司簽訂了一份通訊設施交易合同。2018 年,美國重啟了針對伊朗的單邊經濟制裁。 原告由于被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制定的《特別指定國民與禁止往來人員名單》(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and Blocked Persons List)列為制裁對象,被告因此終止了合同義務履行。 在此情況下,被告若遵守《歐盟阻斷法》繼續履行與伊朗國民銀行的合同義務,其將遭受美國制裁,在美國市場遭受重大經濟損失;另一方面,被告終止了合同履行,則違反《歐盟阻斷法》,將承擔對原告的違約責任以及歐盟執行機關的制裁。 這種當事人面臨的“兩難境地”同樣也適用于各國公權力機關,即在本國私主體于美國境內從事相關經營活動,屈于美國當局施加的巨額經濟制裁而不得違抗美國特定法律帶來的強制義務時,各國難以克服社會輿論壓力再對相關私主體實施本國阻斷法要求之制裁。 如此一來,各國阻斷法的公權力懲戒難以落到實處,進而使得阻斷法淪為了“宣誓性立法”,阻斷法所明確的權利義務也難以在執行層面得到深入貫徹和落實。
(二) 阻斷法的司法經驗:外國主權強制原則與國際禮讓原則下的適用困境
1.外國主權強制原則下的適用困境
外國主權強制原則起源于美國判例法,其含義本身難以得到精準統一的界定。 在“泛美煉油公司訴德士古馬拉開波公司”一案中,美國法院第一次明確了外國主權強制原則在同類案件中的地位:“當一國強制企業必須遵守相關貿易實踐,則商業行為成為了有效的主權行為,謝爾曼法并未賦予美國法院對外國主權行為的管轄權。”〔23〕Interamerican Refining Corp. v. Texaco Maracaibo, Inc.,307 F. Supp. 1291(D. Del. 1970).進一步言之,“當事人陷入同時履行兩個相沖突的、分屬于兩個主權國家的法律義務之困境中時,若當事人被強制遵從其本國法律,則其可以提出外國主權強制之抗辯”〔24〕In Re Vitamin C Antitrust Litigation,810 F. Supp. 2d 522 (E. D. N. Y 2011).。同時,在“美國訴第一國家城市銀行案”中,法院明確外國對企業施加的制裁同樣可視為外國強制行為〔25〕United States v. First National City Bank,396 F. 2d 897(1968).。
從法理層面看,當事人若想建立阻斷法與外國主權強制原則之間的聯系,必須證明其本國阻斷法這一國家主權行為強迫其履行義務,進而使其陷于本國與美國兩項相沖突的強制法律義務,即當事人倘若對兩國相沖突的法律選擇其一遵守,其必定會違反另一國法律之義務,從而受到一國制裁,至此外國主權強制之抗辯才能得以滿足。 然而,在美國法院的司法實踐中,當事人建立這兩者聯系的嘗試往往不能成功。 其原因在于有的阻斷法并未規定制裁措施,有的即便規定了制裁措施,但由于將使本國私主體陷于兩難困境,在現實中也難以得到執行。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法院往往認定相關阻斷法并不具有制裁的強制性〔26〕龔柏華,朱瀟瀟.以“國家行為”抗辯美國反托拉斯法域外適用的法律分析[J].國際商務研究,2011,(6):63-64.,故而當事人主張的外國主權強制原則之抗辯不能成立。
2.國際禮讓原則下的適用困境
國際禮讓原則最早由著名的國際私法學家胡伯(Ulrich Huber)提出,其認為如果每一國家的法律已在其本國領域內實施,根據禮讓,行使主權權力者也應讓它們在內國境內保持其效力,只要這樣做不損害內國及其臣民的權利或利益〔27〕李雙元,歐福永.國際私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46.。 經過柯里(Brainerdc Currie)政府利益分析說的發展,美國法院在涉及兩國政府利益沖突時,審視國際禮讓原則的主要依據在于兩國政府之間的“利益平衡”(balancing in?terests)。 美國的《第三次對外關系法重述》要求美國法院裁判時所平衡的國家利益分別為:(1)美國的國家利益;以及(2)相關阻斷法之制定國的利益。
關于“國家利益”的定義,有學者認為,其本身應同時包含個人利益、集體利益、全民利益這三個方面〔28〕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10-11.。 在“法國航天制造公司案”中,法院將“美國國家利益”具象化為“美國公民因侵權受到的利益損害(如產品責任)”。 可見,所謂的“美國國家利益”不僅涵蓋了美國國家安全等重大國家利益,其自身同樣包含了美國公民的個人權益,在民事侵權訴訟中這樣的裁判觀點較為普遍;而主權的完整性毫無疑問是阻斷法之制定國意圖維護的國家利益之首。 然而,將阻斷法制定國之利益僅理解為以上內容,在民事訴訟中似乎構成了“內國個人利益”與“外國司法主權”的個人和國家之二元對立。
筆者認為,對于阻斷法之制定國的利益可從形式和實質兩方面對其加以理解。 從形式上看,由于法院所作命令的直接后果,是使當事人直接違背本國阻斷法,從而履行法院的相關裁定,其涉及的看似是當事國的主權利益;從實質上看,各國制定或遵守的阻斷法所保護的法益,并非僅有主權,而是包括了本國國民之利益以及其他國家重大利益。 正如“法國航天制造公司案”〔29〕Société Nationale Industrielle Aérospatiale v. U.S.,482 U.S. 522 (1987).同樣將此利益解釋為“法國保護其國民之合法權益被外國的取證程序侵害”一樣,阻斷法的制定看似是國家的政治措施,事實上對于國內私主體的合法權益仍起到了保護作用。 因此,進行利益衡量的雙方——相關阻斷法制定國的利益與美國國家利益本身并無利益主體之差異,均涵蓋了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兩項標準,美國下級法院仍難以得到一個明確的具體標準去進行利益衡量。
基于此,美國的各級法院通過一系列司法實踐的發展,逐漸將“阻斷法在當事國的執行情況”作為審查“利益平衡”要素時的主要參考標準。 在“摩托羅拉信貸公司訴烏贊等人”一案〔30〕Motorola Credit Corp. v. Uzan,73 F. Supp. 3d 397(2014).中,法院論述道:“倘若相關國家確實重視其政策利益,在其公民違反阻斷法進而遵循阻斷法所禁止之事項時,其應當對自己的公民提起相應訴訟。”遺憾的是,各國即便于阻斷法中規定了公權力追責制裁的措施,但其實施情況并不理想。 美國法院在審視了相關阻斷法的執行情況之歷史后,往往并未發現相關國家對阻斷法進行了執行與落實。 這就導致在進行利益衡量時,美國當局之命令所維護的美國當事人合法權益以及美國國家利益,顯然重于相關國家雖完成了制定,但對執行不加以落實的阻斷法所維護的不為當事國重視的利益。 在這種阻斷法執行歷史幾乎為空白的情況下,當事人基于利益平衡所提出的國際禮讓原則之抗辯顯然無法成立,美國法院甚至將阻斷法視為特定國家為本國主體提供的法庭之上的談判籌碼而不具有特定國家的重要主權利益〔31〕Adidas Ltd. v. S. S. Seatrain Bennington, No. 80 Civ. 1922, Slip op. (S. D. N. Y. May 29,1984).。 加之外國主權強制原則同樣不適用,美國法院便認定阻斷法并未剝奪其要求當事人服從其管轄并提交證據的權力。
可見,在司法層面,無論是外國主權強制原則還是國際禮讓原則,相關主體都難以將之與阻斷法規定的義務在美國法庭上聯系起來,進而提出合理抗辯。 其原因均在于各國阻斷法在執行層面的追責制裁難以得到落實。 正如前文所述,阻斷法之所以難以得到各國執行,是因為阻斷法在將各國私主體陷入美國法律和本國法律沖突之困境下時,同樣也將各國政府或法院陷入了兩難境地:各國希望達到阻斷美國特定法律效力的效果,前提條件是對阻斷法進行強有力的貫徹和執行,即在達成阻斷效果前,先對本國私主體進行強有力的制裁。 如此邏輯顯然既難以說服各國政府,也極易引發國內的輿論熱議。 在這樣的情況下,阻斷法似乎淪為了一種“宣誓性立法”,僅能用以表明國家政治立場的無用工具。
三、阻斷法對中國的啟示
誠然,由于阻斷法把國家政府以及相關當事人均置于一種兩難困境中,其在現實中難以得到執行落實,因此在目前美國的司法實踐中難以得到有效適用。 然而,這些困境經驗在一定程度上也為我國未來設計出一套富有成效的阻斷制度提供了啟示與幫助。
(一) 立法層面的啟示:明確阻斷事項,兼顧企業利益
1.明確阻斷事項,制定具有中國特色的阻斷法
縱觀當前世界各國阻斷法之發展趨勢,不難看出阻斷法由最早的阻斷程序型逐漸向阻斷實體型演變。 阻斷實體型的阻斷法從特定法律之效力、依據特定法律做出的判決或裁決的承認與執行,以及違反阻斷法之救濟方式等方面出發,全方位地對美國特定的單邊制裁法規進行了域外效果阻斷。 我國應當吸取這一類阻斷法的優勢特點,同時應當重新整理程序方面的阻斷措施,實現阻斷效果在程序與實體問題上的有機統一。
就阻斷實體的方面而言,首先,阻斷的美國特定法律應主要為其對特定國家實施的單邊制裁法律,以及外國行政當局根據這些單邊制裁法律實施并意圖在我國境內得以落實的,嚴重影響我國國家利益與私人利益的一切執行措施。 這類單邊制裁法律主要集中于美國對伊朗、古巴等國的經濟制裁。 以歐盟為例,《歐盟阻斷法》的附件中所列明的美國特定法律包括著名的《赫爾姆斯-伯頓法》《達瑪托法》,其均為美國對古巴、伊朗與利比亞等國實施的單邊制裁。 這些單邊制裁禁止歐盟主體與上述國家進行相關貿易往來,嚴重影響歐盟利益。 事實上,在中美貿易糾紛的案例中同樣出現了這些制裁法律的身影。 以著名的中興事件為例,美國對中興施加制裁的最初原因是中興違反了美國對伊朗的出口禁令〔32〕張薇.外電:FBI 調查中興指其向伊朗售禁運品[EB/OL].(2012-07-15)[2021-01-12]. 人民網,http:/ /news. cnr. cn/gjxw/list/201207/t20120715_510224103.html.。 因此,美國一系列單邊制裁法律不僅為各國明確阻斷,更是我國現實中的阻斷立法急需面對并解決的問題。 美國當局依據這些單邊制裁法律實施的域外執行行為,也極有可能影響到我國對外經貿主體的合法權益,故未來我國的阻斷法應當對美國立法層面的單邊制裁法律,以及行政層面的可能影響我國國家利益或私人利益的行政執行行為做出回應。 對此涉及到兩方面問題:(1)何種單邊制裁法律應當被納入阻斷范圍? 筆者認為應當從相關國際法規則、我國國家利益以及我國私主體利益三個角度進行認定。 就國際法規則而言,涉及違反我國締結的國際條約或協定的強制性規定的外國法律應當在我國境內被予以無效評價;就我國國家利益而言,涉及國家主權、安全以及相關發展利益的信息或秘密不得為外國法院根據相關單邊制裁法律命令實施的司法取證程序所披露;就我國私主體利益而言,對于依據特定單邊制裁法律實施的可能影響我國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從事對外經貿活動,或者影響我國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進行海外正常投資生產的措施,同樣應當被納入阻斷范圍。 總之,應當從國際法規則、我國國家利益與我國私主體利益出發,對于美國特定單邊制裁法律在我國境內予以全方位的無效評價;(2)何種公權力主體有權審查特定單邊制裁法律是否應納入阻斷范圍? 對此,應當由國務院商務主管部門進行預先審查,就違反我國締結的國際條約或協定,或影響我國國家利益或私人合法權益的單邊制裁法律的情況,頒布相應行政禁令并報國務院備案。 由國務院商務主管部門審查并決定納入阻斷范圍的外國單邊制裁法律在我國境內一律無效,不能被遵守、承認或執行。
其次,阻斷法在直接規定特定法律于我國境內不發生效力的同時,應當明確我國相關主體因遵守特定法律而履行義務的行為應承擔的法律責任。 這種責任不僅包括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賠償責任,同樣應當包括相應的行政責任。 對于民事賠償責任,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我國私主體可以于人民法院提起相應民事訴訟;對于行政責任,其關鍵在于對行政處罰的落實與執行。 我國阻斷法對于相應刑事責任的設立應當持謹慎保守的態度。 因為阻斷法的實施必定伴隨著一段“陣痛期”,在相關主體還不能完全適應這種強制法律義務的背景下,阻斷法體系建立之初便將“兩難義務(即美國特定法律義務和我國阻斷法義務)中的一方”上升至刑事責任高度,既不符合刑法謙抑性的特性,亦將對我國經貿主體的活動積極性產生負面影響。
就阻斷的程序方面而言,我國可借鑒法國的相關立法經驗。 法國1968 年第68-678 號法第1 條規定,“在相關披露行為可能影響法國國家主權,安全或基礎經濟利益時,禁止其國民,居民,公司的雇員、機構和官員在任何地方向外國當局披露任何具有經濟性、商業性、工業性、金融性或技術特性的文件或信息”〔33〕Marc J. Gottridge and Thomas Rouhette, France Puts Some Muscle Behind Its Blocking Statute, 82 New York Law Journal (Outside Counsel),2008.。 該條款是阻斷程序型阻斷法的典型代表,禁止有關主體對外披露涉及國家重大利益的相關信息。 同時,該法案的第1 條之規定上述的文件或信息禁止被作為外國行政或司法程序中的證據,此項規定不涉及法國主權利益的判斷,只要有關文件與信息涉及外國行政或司法程序的證據部分,原則上應禁止披露。
事實上,我國也有類似的禁止遵循美國法院程序命令的條款,且該條款同樣在美國國內的司法程序中被美國法院加以審視。 在著名的“Gucci 案”中,作為被告的中國銀行援引我國《商業銀行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中禁止商業銀行披露客戶信息的規定,以此抗辯美國法院要求中國銀行履行的證據開示義務,但同樣被法院以執行情況為由判定抗辯不成立〔34〕Gucci Am., Inc. v. Li,No. 10 Civ. 4974(RJS),2011 WL 6156936 (S.D.N.Y. Aug. 23,2011),vacated on other grounds,768 F.3d 122 (2d Cir. 2014).。 這樣的判決無疑是對我國《商業銀行法》以及其他相關法律中有關銀行保密制度的巨大沖擊。 對此,設立相應的權能機關對程序方面的阻斷立法予以落實是極為必要的。 阻斷程序型的阻斷條款主要是為了防止涉及國家重大利益的信息被當事人披露。 因此,應當由政府權能部門對被要求披露之信息進行審查,做出相關禁止披露的決定并加以執行落實。 如此一來,程序方面的阻斷立法才能實現保護國家秘密、法律秩序等重大利益的立法目的。
2. 兼顧企業利益,幫助企業走出兩難困境
正如前文所述,阻斷法的制定必然將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本國私主體陷入美國與本國兩項強制法律義務的兩難困境。 倘若阻斷法制定完成后不能合理權衡好我國各私主體的合法權益,必將打擊其從事經貿活動的積極性。 就目前我國立法來看,對于美國法律域外適用的反制報復在一定程度上已有落實與體現,但對于我國私主體在此過程中利益保護的關注程度仍然不夠〔35〕廖詩評.中國法域外適用法律體系:現狀、問題與完善[J].中國法學,2019,(6):37.。 我國阻斷立法的制定應當就此方面顧及企業利益,為企業提供相應的補償以及豁免程序。
對于中國的阻斷立法,豁免程序的設立與適用應當注意幾方面要點:(1)豁免申請的審查權力應由國務院主管部門統一行使;(2)由企業自行提出豁免申請;(3)保留國務院主管部門針對涉及國家安全等重大利益事項,依職權啟動主動審查程序的權力;(4)優化行政程序,盡量縮短審查程序期限。 由于美國法院對于當事人的禁令期限往往結合個案情況而定,因而對豁免申請的審查不宜于立法中規定過長期限,否則將無法適應美國單邊制裁多發的現實復雜情形;(5)因執行阻斷法可能會給企業生產造成損失的,應當給予企業必要的政策優惠與支持。 阻斷法的落實與執行勢必給海外投資生產企業造成利益損失。 對此,筆者認為,對于因遵守阻斷法進而海外投資生產或貿易活動受損的企業,國務院相關部門可以給予其一定政策上的優惠或補償,例如稅收的減免、高科技產業補貼等。 總而言之,阻斷法的制定既要嚴厲阻斷美國特定法律,同時也要體現對企業利益的兼顧,堅定企業應對美國單邊制裁的恒心與信心。 只有這樣,阻斷法規范所確立的法律秩序才能得到長久維護。
(二) 執行層面的啟示:構建成熟的阻斷體系,實現有效的阻斷效果
事實上,在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的大背景下,中國的一些阻斷程序型法律條款便遭到了本國主體在美國法院的程序命令下的違背。 2020 年9 月28 日,孟晚舟案再次開庭,美方于庭上遞交的一份文檔證據便是由中國匯豐銀行提供。 而這樣的證據提供行為違背了我國《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第4 條、《民事訴訟法》第272 條第3 款、《涉及恐怖活動資產凍結管理辦法》第15 條以及《商業銀行法》第29 條、第30條中規定的主體對有關信息的保密義務。 匯豐銀行未經允許不應向美方當局提供相應文檔證據〔36〕黃風.匯豐銀行向美國提供關鍵材料,但不要忘了還有中國法律[EB/OL]. (2020-09-29)[2021-01-12]. 觀察者網,https:/ /www.guancha.cn/huangfeng/2020_09_29_566715_2.shtml.。誠然,阻斷法的制定與適用必然會使我國政府以及企業面臨一段時間的“陣痛期”。 但應當認識到,只有堅定適用法律的決心,將一切制裁或救濟措施納入法治的軌道,我國才能在實現阻斷效果的同時進一步促進經貿活動的長遠發展。 為此,我國應當構建成熟的阻斷體系,以期配合阻斷法在執行層面取得更為有效的阻斷效果。
所謂阻斷體系,指的是各國以阻斷法為核心,能夠實現阻斷效果的一系列法律、政治以及經濟等方面的措施的總稱。 阻斷法的制定只是阻斷體系中的一部分,成熟的阻斷體系更應包含全方位的執行措施。 以歐盟為例,其對于阻斷體系的構建手段大可劃分為法律與政治兩個層面:
在法律層面,首先,加強對《歐盟阻斷法》的國際執行協作。 歐盟于1996 年通過《歐盟阻斷法》后,同年頒布了《聯合行動》〔37〕Joint Action,39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7(1996).作為《歐盟阻斷法》的執行補充。 《歐盟阻斷法》第9 條賦予了歐盟成員國對違反相關條款的主體決定實施何種制裁的權力(必須達到有效,成比例且勸誡性這三個標準),但這樣的規定將使得各國當局的自由操作空間過大,極有可能使得《歐盟阻斷法》的實施力度無法在歐盟境內實現統一,不僅影響阻斷效果,亦違反了歐盟的“一致性原則”(即歐盟各成員國整體對外行動的一致性〔38〕張華.歐盟對外關系法中的一致性原則:以《里斯本條約》為新視角[J].歐洲研究,2010,(3):19.)。 為此,《聯合行動》在第1 條重申了各成員國應當保證《歐盟阻斷法》的執行落實之義務的同時,于第2 條賦予了歐盟理事會依靠統一行動執行《歐盟阻斷法》的權力,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各成員國在《阻斷法案》的執行層面的差異性。 其次,加強后續對《歐盟阻斷法》執行規則的修訂和解釋。 2018年,為了進一步遏制美國不斷擴張的單邊制裁和域外管轄,歐盟對《歐盟阻斷法》進行了附錄更新,將美國自1996 年后的更多制裁法案納入了阻斷范圍。 同時,為了更好地適用《歐盟阻斷法》,其出臺了《執行條例》〔39〕Commission Implementing Regulation No. 2018/1101,61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7(2018).以及《指導文件》。 前者對《歐盟阻斷法》中的豁免程序做出了更為詳細的程序性規定,后者則以23 項問題回答的方式對《歐盟阻斷法》的法律適用進行了詳細的官方解釋。 兩項執行層面的補充規定有效填補了1996 年《歐盟阻斷法》自身的缺漏空白,為后續歐盟執行阻斷法提供了清晰指導。
在政治層面,積極在國際外交中運用斡旋、談判與施壓等政治手段。 1996 年《歐盟阻斷法》制定的背景是美國對古巴的單邊制裁損害了歐共體主體的正當利益。 在《歐盟阻斷法》通過后,歐共體積極開展美國與古巴關系緩和的外交工作,并于1997 年的聯合國大會上呼吁美國結束對古巴制裁〔40〕See A/C.3/52/SR.27.。 最終,憑借著法律上的阻斷法制度體系為核心,配合政治外交上的多元化手段,最終使得美國與歐共體達成了和解與豁免協議。 同樣以“意大利STET 公司”案為例,歐盟就曾宣布將對遵循了美國特定法律的STET公司依據《歐盟阻斷法》進行調查,最終使得美國與歐盟在此問題上達成了政治妥協方案〔41〕Harry L. Clark,Dealing with U.S. Extraterritorial Sanctions and Foreign Countermeasures,20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61,77(1999).。 而在“奧地利勞動經濟銀行”案中,奧地利外交大臣Ursula Plassnik 便曾公開聲明,意圖依據《歐盟阻斷法》對奧地利勞動經濟銀行的相關配合美國制裁的行為提起司法訴訟。 這使得美國政府出于政治上的顧慮最終給予了奧地利勞動經濟銀行相應豁免〔42〕Beatrix Immenkamp,Updating the Blocking Regulation: the EU's Answer to US Extraterritorial Sanctions, European Union (Sept.29,2020), https:/ /www.europarl.europa.eu/thinktank/en/document.html? reference =EPRS_BRI(2018)623535.。
如前所述,由于阻斷法將當事人與涉案國均各自陷入了一種兩難境地,故其執行無法得到徹底落實,進而使得當事人在美國法庭上無法將阻斷法變為有效的合理抗辯理由。 事實上,多數阻斷法制定之初的目的便是為了迫使美國重新回到政治談判桌上。 因而阻斷法的有效執行不應僅靠阻斷立法文本,更應如歐盟的實踐一樣,一方面完善法律對于執行方面的規則解釋、理解與補充,另一方面需要積極在政治層面爭取談判斡旋的空間,進而構建更為立體豐富的阻斷體系,對美國的單邊經濟制裁實現更為有效的阻斷效果。
(三) 中國最新的阻斷立法需要進一步細化完善
2021 年1 月9 日,商務部頒布了《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以下簡稱“《阻斷辦法》”),這是我國阻斷立法的第一次實踐。 縱觀《阻斷辦法》全文,商務部對于適用主體、法律責任以及阻斷對象均有了相應初步規定。 然而,《阻斷辦法》一共只有十五條,作為我國阻斷立法的初步實踐,其在很多問題上的規范仍然較為模糊,需要落實具體細則。 這些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主體問題。 《阻斷辦法》第2 條規定:“本辦法適用于外國法律與措施的域外適用違反國際法和國際法關系基本準則,不當禁止或者限制中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與第三國(地區)及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進行正常的經貿及相關活動的情形。”可見,《阻斷辦法》的適用主體限于“中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 筆者認為,如前文所述,作為一種針對外國域外管轄不當擴張的防御性手段,阻斷法本身是一種防御性措施,而非主動出擊的對等反制。 阻斷法如果將適用主體擴張至外國實體,則正當性和法律基礎將受到懷疑。 因此,《阻斷辦法》第2 條對于“中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規定是合理的。 然而,該條規定對于港澳私主體是否適用不能從《阻斷辦法》條文中得出結論,需要落實具體細則。
第二,《阻斷辦法》的法律適用問題。 縱觀《阻斷辦法》全文,筆者認為將其置于我國整個法律規范體系中進行審查時,會有諸多疑問。 《阻斷辦法》第7 條規定:“工作機制評估,確認有關外國法律與措施存在不當域外適用情形的,可以決定由國務院商務主管部門發布不得承認、不得執行、不得遵守有關外國法律與措施的禁令。”針對該條需要進一步明確的問題包括:由商務部制定的針對特定外國法律與措施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禁令,其性質究竟為部門規章還是行政規范性文件? 這種禁令能否適用于《阻斷辦法》第9 條第2 款所言的民事訴訟程序? 《阻斷辦法》第7 條對于商務部做出禁令的授權是否涉嫌部門規章自我授權? 對此,筆者認為有必要通過國務院的行政法規對商務部在此問題上的職權做出清晰界定。
第三,“必要支持”的細化問題。 《阻斷辦法》第11 條規定:“中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根據禁令,未遵守有關外國法律與措施并因此受到重大損失的,政府有關部門可以根據具體情況給予必要支持。”該條文可以理解為政府對于因遵守阻斷法而利益受損的國內私主體的補償,對于這種支持或者補償的措施問題在未來應進一步細化:究竟是稅收優惠還是資金補貼? 這種支持是否會違反WTO 關于專向性補貼的禁止性規定?
總之,《阻斷辦法》作為我國阻斷立法的初步實踐,其對于阻斷事項以及私主體豁免等方面的規定值得肯定。 但在未來,這部只有十五條的概括性《阻斷辦法》的操作與落實需要更多細則確定。 必要時,需要國務院通過行政法規來對相關部門的職權問題做出清晰界定。
四、結論
首先,阻斷法是指禁止外國特定法律以及依據這些特定法律做出的行為(包含實體行為與程序行為)在一國境內產生效力的法律統稱。 隨著美國單邊制裁的擴大,阻斷法從上世紀的對于美國司法程序的阻斷逐漸擴展至對美國特定法律之效力的阻斷。 因此,縱觀目前世界各國立法,阻斷法可被劃分為阻斷程序型與阻斷實體型,后者為當今世界各國之立法潮流。 對阻斷實體型阻斷法中的典型代表:對《歐盟阻斷法》和《日本阻斷法》加以比較研究,可以發現,二者在適用主體、救濟方式與豁免申請等方面規定不盡相同。 其中,《歐盟阻斷法》的規定更為全面,應為我國阻斷立法的主要借鑒對象。
其次,各國阻斷法的發展經驗表明,其自身在執行和司法層面均面臨一定困境。 就執行層面而言,阻斷法的執行在一定程度上將國家政府與本國當事人均陷入了一種兩難境地。 對于本國當事人而言,一方面面臨美國特定法律的制裁,另一方面倘若遵守美國特定法律則將面臨本國當局制裁;對于國家政府而言,一方面為了落實阻斷法勢必對阻斷法加以執行,另一方面執行阻斷法對本國主體加以制裁,則將使得本國主體陷入前述兩難境地,從而使政府當局承受國內輿論等各方面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阻斷法將很難得以真正的落實與執行,于是其在司法層面就面臨與外國主權強制原則和國際禮讓原則的聯系減弱之窘境,使得當事人無法在美國法庭上提出合理有效的抗辯。
阻斷法積累的經驗教訓一定程度上也給我國未來的阻斷立法與執行帶來了一定啟示。 為了改變阻斷法前述之現狀困境,我國應當在立法層面做到阻斷實體與程序的有機統一、兼顧我國企業合法權益,優化阻斷法中的豁免申請程序。 對于因遵守阻斷法生產經營受損的企業,政府可給予其必要支持和補償,加強法律適用決心。 同時,在執行層面,我國應當積極尋求政治層面的談判斡旋手段,配合阻斷法執行規則的補充和強化,構建具有我國特色的阻斷體系。 最后,對于商務部最新頒布的《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應當根據實踐進一步細化完善,推動我國更為成熟的阻斷立法,對美國不斷擴張的單邊經濟制裁做出更好的中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