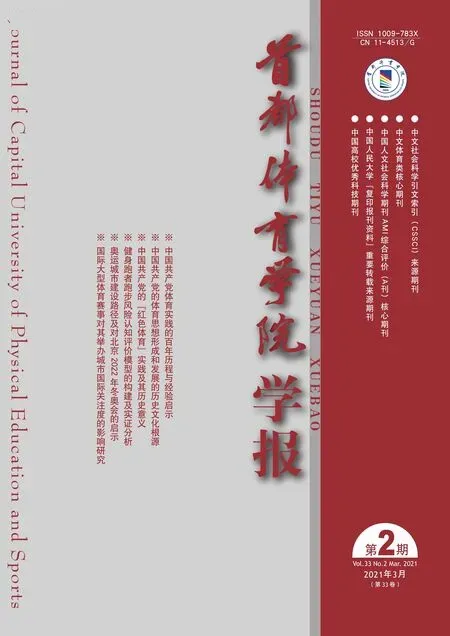中國共產黨的“紅色體育”實踐及其歷史意義
畢金澤,郭 振,劉 波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之際,2021 年2 月20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京召開了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全黨同志要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以昂揚姿態奮力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以優異成績迎接建黨一百周年。”[1]從歷史經驗中汲取創新和前進的動力是中國共產黨歷來的優良傳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由中國共產黨帶領開展的“紅色體育”是中國體育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當代中國體育事業發展的重要源頭。新中國成立之初,許多體育方針、政策和制度的制定都與“紅色體育”實踐息息相關,許多體育工作者也都經歷過革命戰爭時期“紅色體育”實踐的歷練。通過對“紅色體育”的時代背景、實踐經驗與歷史意義的深入分析,對當代中國體育事業發展和豐富中國體育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1 關于“紅色體育”歷史分期的討論
“紅色體育”一詞由毛澤東于1934 年在全國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最先提出[2]。新中國成立后,“紅色體育”逐漸成為學術界研究中國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體育實踐的代名詞,也有學者稱其為“赤色體育”“新民主主義體育”或“革命根據地體育”。而長期以來,學術界將“紅色體育”視為一個具有時代特征的名詞,主要是為了區別同一歷史時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和偽滿洲國統治區的體育活動。從已有研究來看,對“紅色體育”的界定主要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紅色體育”主要是指20 世紀30 至40 年代由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瑞金中央蘇區、陜甘寧邊區等革命根據地開展的體育活動[3]。廣義上,從“五四運動”開始至新中國成立的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由中國共產黨帶領、組織開展的體育活動,都稱為“紅色體育”[4]。無論“紅色體育”的概念外延如何界定,從其內涵而言,“紅色體育”是指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勞苦大眾以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所開展的體育實踐。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早期代表性人物較早地意識到體育運動對強健軍民體魄的重要作用,進而開展了各種富有特色的體育活動。從中央蘇區、陜甘寧邊區,到各個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在不同的艱苦戰爭環境中,“紅色體育”在不斷地發展和延續,并在指導思想上形成了較為完善的理論體系。通過對“紅色體育”發展歷程的分析,結合中國近代不同時期的歷史背景,本文將“紅色體育”演進歷程作出以下劃分:中國共產黨早期代表性人物的體育主張與“紅色體育”的興起(1919—1927 年)、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色體育”的形成(1927—1937 年)、抗日戰爭時期“紅色體育”的發展壯大(1937—1945 年),以及解放戰爭時期“紅色體育”的成熟(1945—1949 年)。不同時期“紅色體育”的廣泛開展既增強了軍民體魄,又活躍了革命隊伍,增進了軍民團結,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具有積極意義。
2 “紅色體育”實踐及其歷史背景
在中國共產黨早期代表性人物的影響下,“紅色體育”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及解放戰爭時期均有著不同程度地發展。“紅色體育”實踐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廣大軍民共同參與下不斷發展的。其中既包括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又融匯了中國近代以來由西方傳入的現代體育運動項目,更有著廣大軍民因地制宜而創造的體育活動方式;其組織形式和參與方式帶有典型的實用性和軍事化。這一在戰爭時期形成的體育實踐形態,提高了中國共產黨軍隊的戰斗力,豐富了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軍民的文化生活,對戰爭的勝利具有積極意義。
2.1 中國共產黨早期代表性人物的體育主張與“紅色體育”的興起(1919—1927 年)
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受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西方體育思想開始傳入中國,“強國強種”“救國救民”等思想成為中國近代一些有識之士的強烈共鳴。中國共產黨的早期代表性人物以體育為號召,宣揚民主與科學,反對封建思想束縛,以召喚民眾覺醒[5]。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惲代英、楊賢江、鄧中夏等一些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代表性人物在革命斗爭之余,均從不同視角批判了封建社會“重文輕武”的思想和清末“兵式體操”對學校學生身體發展的束縛,啟發民眾從新角度重新認識體育的作用與意義。
陳獨秀在《青年雜志》創刊不久發表的《今日之教育方針》《敬告青年》等文中,首先體現了對青年體質羸弱的擔憂:“余每見吾國曾受教育之青年,手無縛雞之力,心無一夫之雄,白面纖腰,嫵媚若處子,畏寒怯熱,柔弱若病夫,以如此之心身薄弱之國民何以任重而致遠乎”[6],并提出了“德之立教,體育殊重”的觀點[7],同時,他還批評“教育大部分重在后腦的記憶,小部分重在前腦的思索,訓練全身的教育,從來不大講究”[8]。他主張“全身皆有訓練,不單獨注重腦部。既能有體操發展全身的力量,又有圖畫和各種游戲,練習耳目手腳的活動能力”[8]的完整教育。此外,陳獨秀還提出體育的功能在于塑造人的情感與道德,例如,在《新教育是什么樣》一文中指出:“游戲、體操不專是發育體力的,兼且是發育各種器官、肢體之感覺神經,及運動神經反應的本能和道德情感。”[9]這種將體育的功能與塑造道德、情感聯系到一起的主張,無疑是一種進步思想。
1917 年,毛澤東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體育之研究》[10]。文中通過提出國人體質孱弱的現象,強調了體育的重要性。毛澤東還就體育的目的、作用,體育與智育、德育的關系,以及體育鍛煉方法等方面作了詳盡的闡述。他認為,體育是使身體全面發展的“養生之道”,具有“強筋骨、增知識、調感情、強意志”“使人身心并完”[10]的積極作用。他還提出了“體育一道,配德育與智育,而德智皆寄于體。無體是無德智也”“體育于吾人實占第一之位置。體強壯而后學問道德之進修勇而收效遠”[10]等觀點,強調了體育的教育意義。毛澤東從個人視角強調體育可以“養生”;從國家角度認為體育可以“衛國”,主張通過發展體育,走“救國救民”的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正值中西方文化碰撞最為激烈的時期,體育界也出現了“全盤西化”和“體育國粹化”相對極端的思想,毛澤東《體育之研究》一文的發表,則以辯證的視角對中西方體育思想與體育實踐進行了科學的揚棄,成了批判舊文化和啟發民眾新思想的有力武器[11]。
面對當時學校體育“多形式,無實質”的狀況,惲代英于1917 年發表了《學校體育之研究》一文,從近代科學觀角度對學校體育的目的、功能、本質進行了論述。他還針對當時流行的“軍國民體育”“選手體育”“放羊式體育”等學校體育思想進行了嚴厲批判,指出了其中的弊病,提出了改革學校體育的建議及措施。他嚴厲地指出,“軍國民體育”推行的結果就是學生“究其對于強健身體之關系,毫不知曉”[12]。他還批判“選手體育”使許多青年人“騖于虛榮,枉正道以求不可必得之名譽”[12]。為此,他呼吁“吾國學校之體育,斷不可不研究改良”,建議“改片斷的體育為有系統的體育,改偏枯的體育為圓滿的體育,改驟進的體育為漸進的體育,改枯燥的體育為有興趣的體育。”[12]主張學校開設《生理衛生學》課程、定期進行身體檢查、增加體育鍛煉時間等措施。
在之后幾年的時間里,惲代英又以《嬰兒之體操》《兒童游戲時間之教育》《運動訓練之正誤》《與黃勝白先生論中學體育》《學生課外之事業》等[4]進一步闡述了學校體育的目的及作用,深化了對體育教育的認識。
總之,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中華民族正處于民族求獨立、社會求變革的時代背景下。陳獨秀、毛澤東、惲代英等人通過對體育的全新詮釋,強調體育的作用,并將其用于思想啟蒙和民族救亡中,強調體育是改善國民體質、重塑民族性格的有效手段之一。雖然萌芽時期的“紅色體育”思想尚未形成體系,其相關體育實踐也幾乎未得到全面開展,但卻是中國近現代體育史上首次突破階級局限,將“強身”“衛國”的體育思想傳播到無產階級的實踐。對國人認識體育、形成新的體育觀等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也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色體育”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礎。
2.2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色體育”的形成(1927—1937 年)
1927 年,由于國民黨叛變,大革命失敗。同年9月,中國工農紅軍在井岡山開辟了第一個革命根據地。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戰爭空閑休整時,經常因地制宜地開展爬山、劈刀、爬云梯、軍體拳、越障礙、射擊打靶、過獨木橋等與軍事訓練相關的體育活動。工農紅軍內部還設立了“三操兩講堂”(每天出3 次操,上2 次理論課)的管理制度,利用出操機會進行爬山奪紅旗比賽。1927 年冬,駐守井岡山茅坪村附近的紅軍戰士,還在步云山舉行爬山活動[13]。1929 年古田會議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指出,在開展軍事體育活動的同時,還應以大隊為單位,開展踢足球、練武術等運動競賽。在中央蘇區鼓勵下,連隊俱樂部組織開展了各種球類運動、游泳等體育比賽,大大豐富了中國共產黨軍隊的文化生活。
1931 年,中國工農紅軍又轉戰了閩西、贛南等地區,創立了以江西瑞金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即中央蘇區),并于1931 年11 月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革命根據地建立之初,面對人數、武器裝備占絕對優勢的國民黨反動軍隊,中國工農紅軍的將領認為,紅軍體力的優勢會成為敵我雙方優劣勢轉化的重要因素,只有憑借體力方面的優勢,才能揚長避短取得戰爭勝利[14]。
在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黨中央為了將教育普及于兒童,成立了一批“列寧小學”(人民學校)。據統計,1934 年江西、福建、廣東三省2 232 個鄉中,共有“列寧小學”3 052 所,學生 89 710 人[15]。為了培養革命干部,黨中央還創立了蘇維埃大學、紅軍大學、農業學校、衛生學校、戲劇學校等,這些學校都根據各自的教學特點,將體育課列入教學計劃中。通過開設體育課或進行體育鍛煉,既培養了后備革命力量,也帶動了革命根據地學校體育的發展。例如,“列寧小學”在體育課中開展體操、跳躍、投石等運動項目外,還制定了早操(練步伐和跑步)和晚操(操練木槍和隊列)的體育鍛煉制度,提高了該校學生的軍事作戰技能。再如,“蘇維埃大學”為適應革命戰爭需要,對學員生活實行軍事化管理,開展的體育活動也大多與軍事訓練有關[16]191。
隨著國內戰爭形勢的變化和革命根據地的擴大,中共中央為進一步增強軍民體質,發出開展群眾性體育活動的號召,同時還根據實際情況在借鑒國外經驗基礎上,成立了群眾性文化娛樂組織——俱樂部和列寧室。到1933 年,僅在中央蘇區的2 932 個鄉中,就有俱樂部1 917 個,經常參加文體活動的中央蘇區機關干部有近10 萬人[17]。在俱樂部和列寧室的組織下,各類體育活動也在群眾中廣泛開展了起來。對于群眾體育的開展情況,《青年實話》的相關報道中寫道:蘇區內的體育運動一天天地開展著。各地工農群眾參與跳高、跳遠、賽跑、游泳、蕩秋千、打籃球、踢足球、打乒乓球及運動會,體育健兒一天天地多了起來。各地到處在舉行體育比賽,發展“紅色體育”[16]130。
隨著蘇區運動競賽的普遍開展,同時在國民黨不斷圍剿的情況下,1933 年中共中央成立了“五卅運動會籌備會”,決定舉辦大規模、全局性的綜合運動會。《紅色中華》還以《“五卅”舉行赤色運動會》為題進行了報道[18]。在反圍剿的硝煙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五卅運動會”于5 月30 日在江西瑞金葉坪村運動場如期舉行,競賽內容包括田徑、球類運動等共18 個運動項目。來自紅一方面軍的一、三、五軍團,中央蘇區機關,江西省和福建省各市、縣共19 個代表隊的180 名運動員參加了比賽[16]232。為慶祝運動會召開,毛澤東以中央政府名義題寫了“鍛煉工農階級鐵的筋骨,戰勝一切敵人”的題詞,成為中央蘇區體育工作的總方針。在這一總方針指導下,中共中央于運動會結束后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赤色體育委員會”,推選出項英、王盛榮、張愛萍、鄧發、施碧晨為赤色體育委員會委員,這一體育組織的成立為中央蘇區體育運動的全面開展提供了組織保障。
隨著革命根據地群眾體育的廣泛開展,各類體育活動紛紛舉辦。據統計,僅1933 年中央蘇區就開展了96 場球類比賽、123 場田徑比賽、15 場體操比賽、42場軍事體育比賽和5 場游戲比賽[19]。在赤色體育委員會的統一組織下,福建、江西的一些地區相繼開展了一系列體育競賽活動,并成立了省級和縣級的赤色體育分會。在革命根據地體育組織的推動下,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先后舉辦了大、中型運動會20 余次,發布了20 余項和體育有關的指示[20]。體現出了這一時期“紅色體育”的組織機構、參與范圍、開展形式等已初步確立,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的體育事業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1934 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主力紅軍被迫實行戰略性轉移,在艱苦的長征途中,廣大紅軍指戰員仍會在“五一”“五卅”“八一”等紀念日或戰爭空閑積極開展體育活動。例如,紅四方面軍南下川西北后期,因戰事相對減少,就經常組織以加強戰術訓練為目的的體育活動[21]。1936 年,為鼓勵全軍指戰員提高身體素質,紅四方面軍舉行了為期3 天的“五一全軍運動會”。比賽項目除了球類運動、賽跑外,還有跳高、跳遠、擲手榴彈、競走、障礙賽跑等運動項目[22]。
總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為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圍剿,中共中央號召開展以“養成工農階級強健體格”為目的的體育活動。通過開展這類體育活動,既豐富了軍民文化生活,又增強了軍民的體質和工農紅軍的戰斗力,有力粉碎了國民黨的大舉進攻與四次“圍剿”。由中共中央成立的各級體育組織,對于擴大“紅色體育”規模,組織形式多樣的“紅色體育”活動,起到了組織保障作用。歷經不斷地實踐探索,“紅色體育”在開展范圍、內容與組織形式等方面逐步完善,為革命根據地“紅色體育”后續開展提供了經驗。
2.3 抗日戰爭時期“紅色體育”的發展壯大(1937—1945 年)
1936 年,紅軍各方面軍在會寧和靜寧將臺堡會師,在陜甘寧邊區建立了中國革命的中心根據地。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國共合作后,紅軍部隊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并開辟了晉察冀、晉綏、晉冀魯豫等14 個較大的抗日革命根據地。這些抗日革命根據地在傳承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蘇區優良傳統的同時,繼續大力提倡體育運動。為了進一步推動“紅色體育”開展,1938 年,毛澤東發出了“廣泛發展民眾教育,組織各種補習學校、識字運動、戲劇運動、歌詠運動、體育運動”[23]的號召,激發了軍民參與體育鍛煉的熱情,抗日革命根據地內開展體育運動蔚然成風。
抗日戰爭爆發后,為了提高軍隊戰斗力,爭取抗日戰爭勝利,八路軍和新四軍十分重視開展各類體育活動。當時開展的體育運動項目既有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又有現代競技體育項目,同時還有結合當時戰爭形勢自創的體育運動項目,包括:武術、摔跤、蕩秋千、拔河、舉石鎖、賽跑、跳高、跳遠、單杠、球類運動、隊列隊形操、馬術、刺槍、軍事障礙賽、擲手榴彈、射擊等[24]。在朱德總司令發出開展邊區體育運動號召后,邊區保安司令部設立“體育干部訓練班”,專門負責開展軍事體育活動。當時,各部隊以“創造大批的神槍手與優秀軍事技術體育英雄”為目標,將實彈射擊、擲手榴彈、武裝翻越障礙、武裝爬山作為勤練項目,既增強了中國共產黨軍隊指戰員的體質,也提高了中國共產黨軍隊指戰員的作戰技巧。1938 年,陳毅率新四軍支隊東進蘇南敵后,面對日本侵略軍、偽軍和國民黨反動軍隊的包圍,為了適應在江南水網地區作戰,號召人人學游泳,組織軍隊進行游泳訓練,還先后4 次率軍隊武裝泅渡運河[25]。東北抗日革命根據地內的饒河游擊隊為適應在高山雪地作戰,組成了滑雪隊,進行滑雪技術訓練[26]。
為了推動學校體育發展,邊區政府教育廳相繼頒布了一系列學校體育法規,對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開設的體育課提出了具體要求。例如,各類學校都設置體育課程,在教授一些運動項目規則、訓練方法和體育常識的基礎上,加入了防空急救、軍事游戲、夜間緊急集合、軍事演習、步槍刺殺和投擲手榴彈等內容。各個學校還在空閑時間開展了許多體育競賽活動,例如,延安保育小學除了舉行“三大球”比賽和田徑比賽,還參加了由體育會組織的小學生運動會和兒童運動會[27],當時的中國抗日軍政大學也曾多次舉行過球類運動比賽與校運動會[28]。
1940 年,在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倡議下,成立了“延安體育會”,積極組織和推動各機關、軍隊、學校及工廠開展群眾體育,除了參與常規體育活動,還帶領軍民開展武裝障礙賽跑、實彈射擊、擲手榴彈、賽馬等軍事體育項目。“延安體育會”還發起每天“十分鐘運動”,鼓勵群眾養成體育鍛煉的習慣。1942 年,為糾正軍民體育活動中一些不正確的觀念,在朱德等人帶領下,聯合“延安體育會”、延安大學體育系等于“延安軍人俱樂部”成立了“延安新體育學會”,負責抗日革命根據地體育活動的調查研究與編譯體育教材等工作。
在“延安體育會”和“延安新體育學會”的帶動下,抗日革命根據地的體育活動逐漸得到發展,先后舉辦了多次運動會。其中規模較大的有“五一運動大會”“三八運動大會”“九·一八運動大會”“朱德杯排球賽”“九一運動大會”“八一抗戰動員運動大會”和“九一擴大運動會”[16]122。在上述運動會舉辦過程中,毛澤東的“鍛煉身體,好打日本”,朱德的“運動要經常”,賀龍的“體育運動軍事化”等題詞成為推動抗日革命根據地體育工作開展的指導思想。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期間,在國民黨統治區曾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代表機關——八路軍辦事處。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經常開展多種文體活動。例如,在周恩來的倡議下,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自己動手修建運動場地,制作運動器材,開展排球、乒乓球、籃球、八段錦等體育運動項目。1942 年,受延安“九一運動大會”影響,重慶八路軍辦事處也舉行了一次運動會,競賽項目包括球類運動、跳高、跳遠、舉重、單杠、石鎖、爬山和競走等[29]。
總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抗日戰爭時期的“紅色體育”在吸取中央蘇區體育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指導思想更加成熟,體育活動內容、組織形式更加全面,組織機構更加健全,開展范圍更加廣泛。“紅色體育”的蓬勃開展造就了一大批身強體壯的革命力量,為提高中國共產黨軍隊的戰斗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4 解放戰爭時期“紅色體育”的成熟(1945—1949 年)
抗日戰爭勝利后,國共兩黨經過重慶談判簽署了《雙十協定》。然而,《雙十協定》公布不久,就被國民黨公開撕毀。1946 年,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國民黨反動派悍然發動內戰,中國共產黨帶領軍民進行了堅決的抵抗。在整個解放戰爭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軍隊、廣大群眾及一些學校,根據當時戰時需要開展了以軍事訓練為主的體育活動。
解放戰爭初期,根據毛澤東“應利用作戰間隙著重練兵”“練兵項目仍以提高射擊、刺殺、投彈等技術為主,以提高戰術為輔”[16]74的指示,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練兵熱潮。為此,各野戰軍、地方軍、民兵在作戰間隙和休整時,既開展以投彈、刺殺、射擊為主的戰場必備技能訓練,也組織了與奪槍、摔跤等戰爭相關的體育活動[30]。在大練兵的號召下,各地廣泛開展軍事體育活動。在此基礎上,有的軍隊還組織開展了以軍事訓練為主的表演活動,例如,陜北邊區保衛團就曾進行了劈刀、投彈、刺殺、木馬及杠架等表演展示活動。通過這類軍事體育活動的開展和普及,在增強中國共產黨軍隊指戰員體質的同時,也提高了戰士的殺敵本領。
解放戰爭全面爆發后,解放區各級學校在學校體育課中也加入了有關軍事體育的教學內容,有的學校直接將體育課改為軍事課,學習和掌握偵察、站崗、放哨、埋地雷、擲炸彈等軍事技能。例如:《陜甘寧邊區政府令——陜甘寧邊區戰時教育方案》“教學內容與組織形式”中就規定:“根據時局發展和學校的具體情況,把課程及授課時間酌予變動,如增加時事、軍事及社會活動時間,并減少一些不急需的課程”[31]314,同時還建議“體育課應加入簡單的軍事訓練,學習偵查、站崗、放哨、埋地雷、擲炸彈等技能”[31]315。此外,廣大民眾自發開展的體育活動也都接近軍事體育,并針對當時的物質條件創造了多樣的練習方式,例如:利用手腕綁沙袋練投擲、小腿綁沙袋練跑跳、拉硬弓練臂力,以及建造了“沙袋木馬”“練武樁”等獨具特色的訓練器械。以上這些體育活動的開展,使得廣大民眾也掌握了一定的軍事戰斗技能。
總之,解放戰爭時期,“紅色體育”的內容和組織形式雖然較為單一,但隨著軍事體育活動的開展,廣大軍民通過掌握不同形式的軍事戰斗技巧,增強了部隊戰斗力。尤其是大練兵的開展,進一步提高了各野戰軍、地方軍和民兵的作戰技巧,并鼓舞了中國共產黨軍隊指戰員的戰斗精神。同時,大練兵過程中提出的練兵思想與練兵方式也為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隊建設與發展提供了實踐經驗。
3 “紅色體育”的時代特征與歷史意義
歷經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的“紅色體育”,在中國共產黨影響、組織和帶領下,開展以奪取戰爭勝利為目的的體育實踐,使各時期體育運動的開展不僅配合了軍事戰爭,豐富和活躍了廣大軍民的文化生活,而且為建設新中國體育事業積累了寶貴的實踐經驗。
3.1 “紅色體育”的時代特征
1)為奪取革命戰爭勝利的軍事化體育。“紅色體育”誕生于革命與戰爭時期,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以工人和農民為參與主體的全新體育活動,其指導思想、組織方式與內容均服從于當時戰爭的需要,體現出了較強的軍事化特征。這一特征不僅體現在中國共產黨軍隊的體育實踐中,更融合在學校體育和群眾體育中。從運動項目開展的情況來看,既有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和從西方傳入的現代競技體育項目,更有自創的適宜軍事戰爭需要的武裝爬山、障礙賽跑、實彈射擊和投擲手榴彈等軍事體育項目,這些運動項目的開展與普及與戰時環境及軍事戰爭密切相關。由于具有較強的軍事性,廣大軍民在開展“紅色體育”強健體魄的同時,革命熱情更為高漲,軍隊戰斗力大為提高,為革命戰爭的勝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在中國共產黨的體育思想與體育實踐影響下,革命根據地的“紅色體育”形成了與國統區“錦標體育”“選手體育”截然相反的指導思想。國統區的體育只是少數人的特權,但在中國共產黨開辟的革命根據地內,“紅色體育”的參與者不僅有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將領,還有革命根據地的廣大群眾,具備廣泛的群眾基礎。延安時期,毛澤東為《解放日報》體育專刊題詞:“發展體育運動,提高人民體質”[32]。在這種“體育為民”的思想引領下,參與體育運動的主體人群越來越廣泛。例如,1942 年在延安舉辦的“九一運動會”上,就有小商販組織籃球隊參賽[16]45”。“紅色體育”成為了中國近代以來最具廣泛群眾基礎的體育實踐。在“紅色體育”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還相繼成立了俱樂部、列寧室、赤色體育會、延安體育會等體育組織,為革命根據地群眾體育的開展提供了組織層面的保障。
3)從實際出發的創新實踐。革命戰爭時期,受自然環境、物質條件等客觀因素影響,“紅色體育”還體現出了較強的創新實踐特征。在革命根據地廣大軍民參與體育運動的過程中,根據當地的實際物質條件,適當調整了運動競賽的組織形式和比賽內容,促進了“紅色體育”的普及。例如:延安時期,因資金短缺,革命根據地的軍民“節省每一個銅板為著戰爭和革命事業”[33]。用雙手將線編織成籃球網和排球網,將木材制作成籃球架、排球架、足球門、單雙杠和木馬,將石頭磨成象棋、跳棋或打成石鎖、石盤、石擔。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革命根據地的廣大軍民通過制作這些簡陋而實用的體育器材,促進了體育活動的開展,也體現了“紅色體育”因地制宜的創新實踐特征。
3.2 “紅色體育”的歷史意義
雖然“紅色體育”在中國近代體育史進程中所占時間較短,但其歷史意義不容忽視。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嚴峻的戰爭局勢要求中國共產黨軍隊指戰員必須具備鋼鐵般的意志和強壯的身體。中國共產黨在改善軍隊生活條件的同時,也注重開展體育運動,并通過賽跑、跳高、跳遠、爬山、射擊等提高了軍民鍛煉身體的基本技能,提高了中國共產黨軍隊指戰員的投彈、射擊、劈刀、騎馬等基本軍事技能。通過開展“紅色體育”,增強了革命根據地廣大軍民的體質,提高了戰士的實戰技術與技能,從而有助于提高軍隊戰斗力。“紅色體育”的開展融洽了軍民關系,增進了軍民團結,豐富和活躍了革命根據地軍民的文化生活,提高了人民群眾體育鍛煉的自覺性,推動了革命根據地群眾體育的廣泛開展。在抗日革命根據地,廣大軍民都會在戰爭間隙,組織各式各樣的體育活動,例如:集體跑步、集體操、球類運動比賽、扭秧歌等。“紅色體育”活動的開展與普及,在豐富革命根據地軍民文化生活的同時,也改變了革命根據地軍民的精神面貌。
“紅色體育”作為中國近代的特殊體育形態,在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革命根據地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土地革命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詮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體育的指導理念與工作方針。在革命戰爭中形成的“紅色體育”,為建設新中國體育事業積累了實踐經驗,在中國體育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4 結束語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歷經不同時期的“紅色體育”,既鍛煉了革命根據地廣大軍民的身體和意志,更對戰爭的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紅色體育”在不同時期形成的指導思想、組織方式,為建設新中國的體育事業積累了歷史經驗。雖然受戰爭、物質條件等方面的制約,“紅色體育”的開展存在著一定的空間局限性,但從當時的戰爭形勢來看,“紅色體育”是中國群眾體育的一種初步實踐。作為一種從無到有的體育新形態,“紅色體育”為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建設初期體育事業的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儲備了體育人才,成為新中國體育事業發展初期的重要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