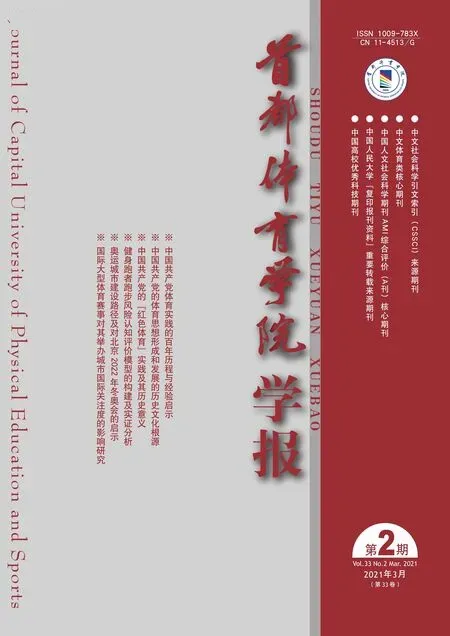動作發展視角下3~6 歲幼兒功能性練習方案的設計與實證研究
周喆嘯 ,顧耀東,李建設 ,趙煥彬 ,趙曉光
動作是人類早期生長發育的核心,是保障個體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技能。3~6 歲是人類動作發展的關鍵期[1],此階段主要為粗大動作學習,粗大動作的熟練掌握是幼兒能完成日常生活、學習和游戲的前提[2],是未來習得復雜運動技能的關鍵[3]。有研究證明,動作發展與幼兒感知覺、認知能力、身心健康及社會適應等方面緊密關聯。在身心健康方面,幼兒階段粗大動作掌握得優劣與肥胖[4]、心肺功能[5]、自信[6]存在明顯正相關,并可預測其未來的身體素質水平[7]、心理健康程度[8]。感知覺方面,幼兒在以動作為媒介與客觀世界發生交互作用的過程中,通過整合視、聽、觸等多種感覺通道信息,使感知覺更加精確[9]、修正搜尋目標[10]、擴展對物體的認知[11]、增強對身體與空間的認識[12]。在認知方面,幼兒通過積累爬行、行走等大肌肉動作經驗,對新環境逐漸適應,能促進其認知發展[13]。隨著年齡增長,大肌肉動作發展水平與行為表現、認知功能相一致[14];若幼兒大肌肉動作發展水平較低,則視覺工作記憶與認知能力也較差[15]。在社會適應方面,動作改變幼兒與社會環境的互動模式[16],不斷促進其對社會規則的掌握,改善與同伴的關系[17];無論在教室或游戲中,動作表現較差的兒童很難被同齡人所接受[18]。因此,動作發展在幼兒健康成長過程中有重要作用。
幼兒時期的動作學習,是在機體發育基礎上,在外界環境刺激下依次經歷習得、掌握、鞏固直至熟練運用各種基本動作技能的一個過程[19]。包含科學性、多元化動作元素的環境可使幼兒正確掌握多種動作技能,而較為單一或缺乏動作元素的環境只能使幼兒掌握某幾種動作技能,例如“狼孩”善于爬行卻無法展現行走、奔跑技能,所以適當的動作練習干預、良好的動作環境建立是極其重要的。基于此種原因,國內外學者做了大量的干預研究,下文針對干預方式、干預實施進行簡要介紹。1)干預方式大致由結構化、非結構化或混合式3 種組成。結構化干預是指針對位移、穩定及物控動作技能進行專門性強化,有“Jump Start模式”[20]“MAZE 模式”[21]等;非結構化干預則采用游戲、音樂等非專門化活動方式干預,有“傳統希臘舞蹈”[22]“音樂-運動模式”[23];而混合式干預就是將結構化干預與非結構化干預進行融合,有“Active Play 模式”[24]“激勵動作氛圍模式”[25]。從效果來看,結構化干預對粗大動作的影響最顯著,非結構化干預對單項動作指標提高較顯著,但在效果保持方面最差,而混合式干預雖然在效果方面沒有結構化干預顯著,但在組織形式、內容選擇方面更符合幼兒身心特點。2)干預實施方面,主要由“教師主導”[26]與“以幼兒為中心”[27]2 種模式構成。“以幼兒為中心”干預效果最好,隨著認知、動作、感知覺發展,幼兒可以依據任務自主組合、設計動作,主動完成干預的全部內容,效果要優于被動的教師指導[28],但此種模式要求幼兒必須掌握一定量的動作技能后才可使用,否則極有可能將干預練習演變成自由活動。需要強調的是,多數研究會采用“教師主導”[26,29],因為教師與幼兒共處時間最長、指導身體活動的機會最多,由教師實施最為適宜。而在實踐中,部分教師往往在活動組織、方案設計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這一點在國內尤為凸顯。國內多數幼兒體育教師沒有經過體育知識培訓,缺乏動作技能教學經驗,體育專業畢業的幼兒教師只占幼兒園教師的2%[30]。綜上所述,已有的較為成熟的干預方式為本文干預方案的制定提供了依據,但作為運動干預的主要實施者,我國幼兒體育教師急需一種切實可行、快速有效的體育活動方式,為科學地體育組織活動、精準地促進動作發展提供參考,從而滿足幼兒的成長需要。
功能性練習最早由希臘學者Herodikos 使用,以模仿動物的動作來改善人體的運動功能[31]79。其認為,人體的任何動作是建立在有效的功能結構基礎上,并通過肌肉骨骼的杠桿原理作為驅動,在神經系統、本體感覺及思維動員下實現,因此,功能性練習的本質就是整合神經肌肉控制能力與本體感覺有序自動化模式下,進行動作學習與控制[32]115-116。其原理與方法已應用到多個領域。在康復領域,功能性練習可提高術后患者關節穩定性、神經肌肉控制[33],改善腦癱兒童步行速度和行走距離[34],改善帕金森患者功能性動作表現、姿勢控制、骨密度及降低跌倒風險[35-36]。在大眾健身領域,功能性練習可促進青少年體質健康,預防由于動作技能不正確和力量發展不均衡所導致的損傷[37],均衡發揮機體神經、骨骼、肌肉系統的功能[38],改善老年人步態、日常身體活動能力[39]及生活質量[40]。已有研究顯示,功能性練習在促進兒童動作發展方面具有積極作用[41],但能否對各年齡段幼兒的位移動作、物控動作都產生影響,以及教師能否在各年齡段幼兒身體活動方案設計與組織方面形成系統、完整的認識等問題,仍有待深入研究。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依據3~6歲幼兒身心發育特點,設計一套適合幼兒練習的功能性練習方案,對動作學習層次劃分、練習內容及組織形式的選擇等問題進行詳細闡釋,并通過運動干預,探討功能性練習對3~6 歲幼兒粗大動作的影響,從而為幼兒制定身體活動方案、探索更科學的體育活動形式提供新思路。
1 研究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與實施周期
1.1.1 研究對象
隨機抽取249 名幼兒為測試對象,分為3~4 歲(小班)、4~5 歲(中班)和 5~6 歲(大班)3 個年齡段,并將各年齡段幼兒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實驗組有5~6歲的 48 人,對照組有 5~6 歲的 47 人;實驗組有 4~5歲的 39 人,對照組有 4~5 歲的 40 人;實驗組有 3~4歲的 37 人、對照組有 3~4 歲的 38 人(見表 1)。實驗對象的排除條件:1)沒有完成干預前、后粗大動作測試或沒有完整參加功能性練習課程;2)參加運動項目培訓班,例如:跆拳道、拉丁舞、足球等;3)身體發育異常或先天具有某種疾病。

表1 各年齡段幼兒實驗組與對照組基本信息(xˉ ±s)
1.1.2 實施周期
實施周期為24 周,每周一、三、五進行,小、中、大班幼兒每次練習時間依次為 20~30 min、30~40 min 和40~50 min(上課的中間安排 3~5 min 休息時間)。對照組各年齡段幼兒進行常規體育活動,實驗組具體實施內容見下文的“3~6 歲幼兒功能性練習方案”。利用《幼兒體育活動強度評價量表》[42],觀察幼兒在練習過程中的面部表情、呼吸和出汗程度,使實驗組和對照組練習強度基本保持一致。
1.2 研究方法
1.2.1 系統分析法
從系統的角度對“3~6 歲幼兒功能性練習方案”進行全面分析和設計。分析方案的總目標、內容、規模及原則。由方案的總目標,自上而下進行分解為若干內容和子內容。在自上而下分解、自下而上認識的過程中,嚴格遵循方法論中對內容設計的基本原則和要求,從而使練習方案更加科學、系統、有層次和實用。
1.2.2 粗大動作發展測試
采用美國學者Ulrich 編制的《TGMD-2 量表》對各年齡段實驗組和對照組幼兒進行干預前、后的粗大動作測試。《TGMD-2 量表》總計12 個測試動作,每個動作評分標準為3~5 個,若達到一個標準得1 分,未達到得0 分,每個動作有2 次完成機會,2 次得分相加為該動作的最后得分。12 個測試動作滿分為96 分,位移與物控動作各48 分。《TGMD-2 量表》既是標準參照也是常模參照測試[43],以動作完成過程為目標導向,其優點為量化動作結果、標準易于理解、操作可行,已在中國、巴西、澳大利亞、比利時、韓國等多個國家開展過跨文化研究[44-45],在評估 3~10 歲兒童粗大動作方面具有較高的信度和效度[46]。由于該測試在評估動作發展遲緩[47]、制定個性化干預方案[48]及衡量練習內容有效性[49]方面具有較高的價值,因此被廣泛應用在臨床、教育與學術研究中[3]。本研究干預前、后由同一批人員(共6 人,均進行過《TGMD-2 量表》評估要求的指導;Kendall 和諧系數W 值為0.946,評分者一致性信度較高)進行粗大動作測試,干預后的測試將對照組和實驗組的幼兒排序進行重組,從而保持測試評價的客觀性。
1.2.3 統計學方法
使用“SPSS 22.0”軟件對各年齡段幼兒粗大動作測試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所有數據均采用(平均值±標準差)表示。采用獨立樣本t 檢驗、配對樣本t 檢驗方法,對干預前組間,干預前、后組內各測試指標進行差異比較;使用協方差分析法對各年齡段幼兒實驗組與對照組粗大動作得分干預前、后變化差值進行對比(干預前幼兒身高與體質量作為協變量),顯著性標準為 p<0.05 或 p<0.01。由于已有研究證明 3~6 歲幼兒粗大動作水平沒有顯著的性別差異[50],故本文不再對幼兒動作變化的性別差異進行分析。
2 3~6 歲幼兒功能性練習方案的設計
2.1 方案內容設計思路
本研究依據人類動作發展理論[51]、動作學習與控制理論[32]79-116中有關幼兒動作的內涵與分類,結合功能性練習的主旨與特點[31]79,以及參考國外“CHAMP”[28]“MAZE”[21]或“Active Play”[24]等較為成熟的幼兒動作干預課程,設計本研究的3~6 歲幼兒功能性練習內容。由功能性動作模塊與功能性身體素質模塊構成。
功能性動作模塊(如圖1)依據3~6 歲幼兒認知特點、體力活動經驗及動作學習習得程度,分為基礎動作、動作模式及動作技能3 個練習層面。第1 層為基礎動作,指幼兒機體單個關節結構所對應的練習動作,主要為屈曲與伸展、內收與外展等動作,例如:坐姿膝關節屈伸動作練習、站姿肩關節內外旋動作練習。Payne 認為,幼兒動作學習的初始,應首先確立“出發點”,為后續復雜動作學習、教師制定身體活動方案建立基礎[51];而基礎動作簡單可行,是開展幼兒功能性練習活動的第1 步、是后續一系列動作學習的基礎,符合幼兒動作學習初級階段的要求。第2 層為動作模式,指多個關節功能共同在一維或多維平面內進行的動作,由推撐、提拉、旋轉、翻滾、彎身、爬行、下蹲及擺動8 類動作模式組成,8 類動作模式依據一維運動平面至三維運動平面的學習過程,又分為一維動作模式與多維動作模式。前者強調8 類動作模式彼此獨自在一維運動平面內的表現,例如:雙臂矢狀面推撐動作、軀干矢狀面彎身動作等;后者強調8 類動作模式彼此獨自在多維運動空間內的表現,例如:失穩狀態下雙手提拉動作等。以往幼兒園體育活動主要對滑步、拍球等對幼兒而言較為復雜的動作技能進行大量練習,并未在這些復雜技能學習前安排中等難度動作的練習或其他過渡環節, 這樣易導致下一階段動作技能學習周期長、掌握程度不穩定等情況[52],因此,本層內容強化幼兒大腦支配機體不同部位在多維運動空間內的整體運用能力,使身心逐漸適應復雜的三維運動空間特性,為下一步動作技能學習作準備。第3 層為動作技能,指為完成同一目標、多種動作模式排列組合,在三維運動空間內的綜合表達,是運動項目技能構成的重要元素,由移動類(跳、跑、跨等)與操作類(傳、投、揮等)組成。李靜等認為,幼兒只有熟練掌握一定數量的動作技能,未來才能順利進行田徑、足球等運動項目技能的學習[45]。此外,《3~6 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中明確要求幼兒階段須掌握走、跑、跳等動作技能,故此層練習內容對接指南動作學習要求、銜接學齡期運動項目技能學習,進一步深入發展粗大動作技能。以上3 層彼此之間的關系,由簡至難、層層遞進,當前一環節練習動作掌握熟練后再開始下一環節的內容,猶如數學學習中基礎數字、四則運算至運算應用的邏輯層次,具體動作內容見表2。

圖1 功能性動作模塊3 層內容及相互關系
功能性身體素質模塊主要依據3~6 歲幼兒神經系統、運動系統、循環系統等發育特點,設計適宜幼兒練習的身體素質內容,以平衡穩定、靈敏速度及脊柱強化3 個方面組成。平衡穩定是幼兒完成一切動作時控制身體的能力,也是速度、靈敏素質等發展的基礎[32]115-116。將聽覺元素與視覺元素結合進行難度設置,小、中、大班練習依次分為靜止狀態視覺通道關閉類練習、移動狀態視覺通道開放類練習及移動狀態視覺通道關閉類練習。幼兒階段大腦最早發育、神經系統快速增長,大約6~7 歲時幼兒大腦發育水平已經達到成人水平的80%~90%[53],為進行反應速度、靈敏性和協調性練習奠定了基礎,將動作完成快慢元素與動作幅度大小元素結合進行難度設置,小、中、大班練習依次分為慢速大幅度類練習、快速小幅度類練習及快速大幅度類練習。脊柱強化為遵循兒童“由近及遠”的發展原則,強調在不同力學環境下能夠維持較好的脊柱姿勢。脊柱側彎、高低肩等是兒童常見異常體態疾病,“早干預、治未病”是當前治療脊柱側彎的主要思路,因而在功能性身體素質模塊中加入此方面內容;將支撐點數量元素與支撐平面穩定性元素結合進行難度設置,小、中、大班練習依次分為多點穩定平面支撐類練習、少點穩定平面支撐類練習及少點不穩定平面支撐類練習,具體練習內容見表2。

表2 幼兒功能性練習方案實施階段劃分及具體內容設置
2.2 階段劃分、練習內容及組織形式
2.2.1 階段劃分
動作發展學者Goodway 發現,某種動作練習的累積時間只有在90~120 min 情況下才能在大腦皮層形成深刻的痕跡效應[19],這樣幼兒對已掌握的動作才不會遺忘。因此,為保證各個動作能夠得到充分練習,將實施周期劃分為5 個階段(見表2)。
2.2.2 練習內容
練習內容為上文的功能性動作模塊和功能性身體素質模塊,考慮到小、中、大班幼兒在身心發育特點、動作練習實際完成情況方面存在差異,故將上文2個模塊內容與各年齡段幼兒身心特點結合進行有側重的練習。具體安排如下:1)董奇研究發現,小班幼兒在情感、交往等認知方面要差于中、大班兒童,且小班幼兒剛剛開始集體生活,對新生事物具有抵觸心理[54]。此外,還存在身體發育不完善及練習負荷承受能力弱等情況。因此綜合考慮,小班幼兒主要進行練習難度較低的基礎動作練習,故1~5 階段主要為基礎動作練習,僅在4~5 階段安排少量的、較為復雜的一維動作模式練習。2)中班幼兒已經具備一定的身體活動經驗,能夠清晰理解動作要領,并可以較為準確地進行展示。但是,過高的動作自我知覺與較低的動作水平所導致的動作自我知覺偏差,是此年齡段幼兒常見的一種現象,倘若此現象持續時間較長會阻礙動作發展[55]。因此,本層內容主要縮小動作知覺偏差時間、強化在一維平面內熟練展示動作以及具備在復雜三維空間環境下完成動作整合的能力,為到大班階段動作技能的進一步學習做好鋪墊,故本年齡段幼兒主要為動作模式練習,1~3 階段為一維動作模式練習、4~5 階段為三維動作模式練習,僅在第5 階段進行少量的動作技能學習。3)大班幼兒無論在身體發育、認知發展都較小、中班具有顯著優勢,可以接受身體活動量較大、動作難度較復雜的練習,因此,1~5 階段著重進行要求高、難度大的動作技能練習。4)前文提到平衡、靈敏等是幼兒身體素質發展的重要方面,但考慮到幼兒階段身體活動以動作發展為主、身體素質發展為輔[45],故僅在2~4 階段開展少量的“功能性身體素質模塊”內容練習(見表2)。此外,為鞏固已學習的動作模塊與素質模塊內容及克服方案實施末期的枯燥感,在第5 階段安排循環練習(兩模塊融合的“闖關”游戲),從而保證練習的效果。
2.2.3 練習組織安排
由于幼兒在進行戶外身體活動時,更喜歡自主活動或集體游戲[29],在實施本方案時要采用情景建立、游戲包裝等趣味性、娛樂化的形式進行,營造幼兒主動練習的氛圍,使幼兒在練習過程中保持濃厚的興趣和積極性。例如,將某次課的主題設置為“游玩動物園”,組織幼兒進行模仿老虎、大象爬行的游戲,使其學習爬的動作;引導幼兒模仿動物園單腿站立的鴕鳥、雙腿交換舞動的公雞等發展平衡能力。
3 結果
3.1 干預前對照組與實驗組幼兒粗大動作測試結果的比較
由表3 可知,干預前對照組各年齡段幼兒粗大動作得分較實驗組,除中班踢球動作、大班立定跳遠動作得分有顯著差異,其他測試動作均未見顯著差異(p>0.05),說明實驗前各年齡段幼兒分組基本符合實驗要求。

表3 對照組與實驗組小、中、大班幼兒粗大動作測試得分干預前的比較 單位:分
3.2 干預前、后對照組幼兒粗大動作測試結果的比較
由表4 可知,對照組各年齡段幼兒粗大動作能力較實驗前均出現顯著變化。小班幼兒粗大動作總分、位移動作得分和物控動作得分較干預前,差異呈顯著性(p<0.01)。各具體動作分析,除側滑步得分較干預前未見顯著差異(p>0.05),其他動作較干預前得分均出現顯著變化,但前滑步和踢球動作雖有顯著變化,但得分相較干預前出現明顯下降。中班幼兒粗大動作總分、位移動作總分、物控動作總分相較干預前,除位移動作總分其他2 項較干預前變化呈顯著性(p<0.01)。中班各練習動作中,單腳跳、前跨跳、側滑步、原地拍球和踢球動作得分較干預前并未出現顯著變化(p>0.05),其他動作得分較干預前出現顯著變化,但前滑步和雙手接球動作得分較干預前出現明顯下降。大班幼兒粗大動作總分、位移動作總分、物控動作總分較干預前,呈顯著性差異(p<0.05)。大班各測試動作中的前滑步、側滑步、雙手接球、擊固定球、上手投球和地滾球的得分相較干預前未見顯著變化(p>0.05),其他動作得分較干預前出現明顯提高,但踢球動作得分較干預前明顯下降。

表4 對照組小、中、大班幼兒粗大動作測試得分干預前、后的比較 單位:分
3.3 干預前、后實驗組幼兒粗大動作測試結果的比較
由表5 可知,實驗組各年齡段幼兒在完成功能性練習后,粗大動作總分、位移動作總分和物控動作總分相較干預前變化非常顯著(p<0.01)。小班幼兒粗大動作總分、位移動作總分和物控動作總分相較干預前,變化非常顯著(p<0.01)。小班的各動作中,除前滑步、側滑步和踢球動作相較干預前未出現顯著變化,其他9 個測試動作得分相較干預前均出現明顯提高(p<0.01)。中班幼兒粗大動作總分、位移動作總分和物控動作總分相較干預前,變化非常顯著(p<0.01)。各測試動作中,除前滑步和側滑步動作得分相較干預前未見顯著變化,其他10 個測試動作得分相較干預前均出現顯著變化(p<0.05 或p<0.01)。大班幼兒粗大動作總分、位移動作總分和物控動作總分相較干預前,變化呈非常顯著性(p<0.01)。大班的各測試動作中,除側滑步和踢球動作得分相較干預前未有顯著變化,其他10 個測試動作得分均呈現非常顯著性變化(p<0.01)。

表5 實驗組小、中、大班幼兒粗大動作測試得分干預前、后的比較 單位:分
3.4 干預前、后實驗組與對照組幼兒粗大動作測試得分的差值比較
身高和體質量因素對幼兒動作練習干預過程中動作學習、練習效果及干預后效果有一定的影響,因此,將各年齡段幼兒干預前身高、體質量作為協變量,通過協方差分析對比實驗組與對照組各年齡段幼兒干預前、后粗大動作變化的差異。由表6 可以看出,干預前、后各年齡段實驗組幼兒粗大動作得分、位移動作得分和物控動作得分差值均高于對照組,差異非常顯著(p<0.01),并且大、中、小班幼兒多數測試動作變化的差值顯著或非常顯著高于對照組(p<0.05或 p<0.01)。

表6 小、中、大班幼兒實驗組與對照組粗大動作得分干預前、后差值的比較 單位:分
4 討論
4.1 常規體育活動與功能性練習對幼兒粗大動作能力的影響
幼兒期的動作發展主要為粗大動作的發展,一定水平的粗大動作能力是幼兒進行玩耍、游戲的必備基礎[52],是整個生命周期習得生活必要動作、運動項目技能的先決條件[56],7 歲時就應該具備較為熟練的動作技能[57];良好的動作發展不僅影響幼兒與教師的教學互動,而且對幼兒體質量保持、情感抒發及社交融入等方面[58]具有重要影響。本研究發現常規體育活動可以對幼兒粗大動作產生影響,例如:健身操發展四肢協調、團隊游戲發展下肢移動、各種體育運動器材提高上肢攀爬動作能力等,所以對照組各年齡段幼兒多數動作得分較實驗前出現明顯提高。但在本研究的常規體育活動中實際包含的動作技能數量較少,各年齡段幼兒動作設計簡單、難易程度劃分模糊,并且沒有依據各年段幼兒動作學習特點對練習動作進行分類、細化,導致各年齡段幼兒動作技能發展不均衡、某些動作實驗前、后沒有變化,例如:表4 小班幼兒側滑步、中班原地拍球及大班幼兒擊固定球等動作得分較干預前未見顯著變化(p>0.05)。Vassiliki 認為不帶有動作學習目的的身體活動,無法保證幼兒能掌握較復雜的動作技能,而這些動作技能與成年后的變化性動作高度相關[59]。常規體育活動雖然能夠做到以多種練習形式激發幼兒動作學習的興趣,但卻忽視了對已學習動作的鞏固,這樣容易對已掌握的動作出現遺忘。表4 小班幼兒前滑步、大班踢球動作得分相較實驗前出現明顯下降,就是典型例子。Goodway 研究發現,某項動作技能累積練習時間只有在90~120 min 情況下才能在大腦皮層形成深刻的痕跡效應[19],若沒有對已學習的動作進行復習,勢必會使幼兒已掌握的動作退變至分化或泛化階段。此外,中班雙手接球動作得分也顯著低于實驗前,此動作在所有物控動作中難度較高,接球之前要先對球的空間位置、速度和高度作出預判,對幼兒綜合表現動作能力要求高,需要進行有針對性的練習。Donath 認為,若要成功地表現接球動作,需要對兒童“感知-動作整合”能力進行有針對性的練習[60],因此,常規體育活動可以對幼兒粗大動作發展產生影響,但在全面促進各年齡段動作能力提高、鞏固已掌握的動作等方面還有待改善。
通過表5 和表6 可知,對實驗組幼兒進行24 周的功能性練習后,各年齡段幼兒粗大動作總分、位移動作總分及物控動作總分相較干預前均出現非常顯著性的提高,其中多數動作在干預后相較對照組呈顯著性變化(p<0.05)。說明依據幼兒身心規律、動作特點所設計的功能性練習在發展幼兒粗大動作方面具有積極作用,且效果要好于常規體育活動。但本研究也發現,干預后實驗組各年齡段幼兒都出現側滑步變化不明顯情況。由中樞模式發生器信號輸出分段控制機制(CPGs)[61]可知,此動作主要由脊神經段控制肌肉實現,而幼兒脊柱仍處于生長發育階段,所有動作表現均由大腦皮層主導,難以完成需要脊神經段參與調控的復雜動作,因此,側滑步動作的變化幅度較小,但也證明在幼兒功能性練習中安排脊柱強化模塊的必要性。Gallahue 等認為,幼兒大約在6.5 歲之后才能較為流暢地表現側滑步動作[62]。結合前文分析結果可知,相較常規體育活動,基于動作發展的功能性練習對幼兒粗大動作發展的影響更為全面和顯著。
4.2 幼兒功能性練習方案對粗大動作發展的意義
本研究與外國學者的同類型研究均屬于早期兒童動作結構性干預,并且研究結果一致表明專門性干預能對幼兒動作發展產生積極作用[59,63-64]。從動態系統論可知,基本動作技能雖然簡單,但卻不會隨著幼兒年齡增長、機體發育而自動獲得[65],其是機體生長、環境刺激及特定干預共同作用的結果,而特定結構性干預占主導作用[66]。較國外使用的干預方法,幼兒功能性練習方案的特色、不同之處有以下幾個方面。
1) 明確了3~6 歲幼兒動作學習的不同階段。Seefeldt 在動作熟練度發展序列模型中提出,兒童是在“反射- 反應”階段后開始進入基本動作技能學習階段[51],但沒有闡釋兒童由反射階段開始后通過何種練習方式過渡到基本動作技能學習階段。功能性動作模塊將動作學習過程劃分為基礎動作、動作模式及動作技能3 個層次。這樣的層次劃分,猶如人類動作研究學者Payne 將動作學習比作數學中的基礎數字、四則運算及運算應用這樣一個由簡單至復雜的漸進過程[51]。幼兒按照這樣的順序進行動作學習,才能掌握《3~6 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中所要求的各類動作技能。
2)3 個動作學習層次的劃分,也為教師在制定幼兒體育活動方案時提供了依據;適時預判幼兒動作習得過程中所處階段,發現制約幼兒動作學習的癥結,采取針對性解決措施。Wick 認為,倘若教師無法將動作教學系統化、層次化,他們施教的對象就很難正確理解和表現動作,更無法獲得成功的運動體驗與持續的練習動力[67]。功能性身體素質模塊則能使幼兒在動作學習過程中促進身體素質發展。Bardin 認為人體各方面發展都具有窗口期,即使在兒童早期也存在某項素質的“開關”[68]。功能性身體素質模塊,以動作為載體,結合幼兒大腦發育早、神經系統增長快等特點,以功能性平衡穩定動作為起點、功能性靈敏速度動作為重點及預防脊柱側彎的功能性核心脊柱板塊為特色,針對幼兒階段特定身體素質的發展實施科學刺激。Huotari 等[69]認為,幼兒教師倘若無法把動作學習與機體發展兩者融合,對健康有積極益處的身體素質將無法得到強化。
3)安排循環練習板塊,將兩大模塊的內容融合,以游戲比賽的形式,使幼兒自主完成各個循環站點的動作練習內容。一方面,鞏固已學習的“動作模塊”與“素質模塊”內容,加深鞏固學習的痕跡、避免遺忘或生疏。Wadsworth 認為在“自主練習”中可以復習和鞏固已掌握的動作技能,同時多樣的情景設置可提高兒童之間的情感融入與拼搏精神[70]。另一方面,轉變練習方式,由“教師主導”轉變為“幼兒主動學習”,進一步提升幼兒動作水平。幼兒依據各個站點動作練習任務,將已具備的動作能力與練習環境、器材、完成路徑等結合,自主組合或設計動作。Powell 認為,“幼兒為中心”相較“教師主導”更加注重動作學習的過程,提高幼兒主動選擇練習動作或組合設計動作的能力,但前提是幼兒必須掌握一定數量的動作,否則“自主學習”可能演變成缺乏動作學習目的的“自由玩耍”[71]。因此,本研究設計的幼兒功能性練習,在練習動作層級分類、不同年齡段練習動作的選擇性及趣味性、組織形式等方面,可作為教師實施戶外身體活動、設計體育游戲的參考,為幼兒粗大動作能力的發展提供依據。
5 結論
1)幼兒功能性練習方案由功能性動作模塊與功能性身體素質模塊構成,前者將幼兒期動作學習系統地劃分為基礎動作、動作模式和動作技能3 個由低到高的層次,便于教師針對大、中、小班幼兒的特點逐級、有針對性地安排動作練習方案;后者可在動作學習過程中,針對幼兒特定身體素質實施科學刺激,在動作練習的同時兼顧身體素質的發展。循環練習板塊設置,突出“以幼兒為中心”的練習方式,可提高動作質量、增強動作練習痕跡效應,進一步鞏固動作學習效果。
2)常規體育活動與功能性練習均能有效地促進幼兒粗大動作的發展,但前者由于無法對幼兒動作學習產生較好的痕跡效應,使個別動作出現變化不明顯、掌握不穩定等問題。而進行功能性練習的幼兒,其粗大動作變化效果相較干預前得分和相較對照組干預前、后變化差值均呈顯著性,且多數動作變化具有全面性、一致性的特點,因此,在促進幼兒動作發展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