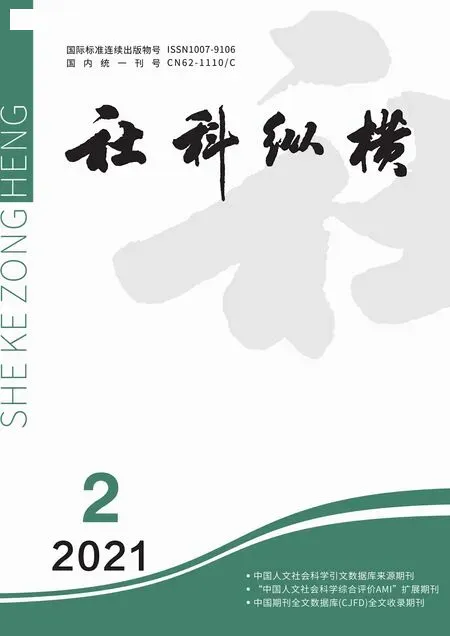論《速求共眠》的電影征用與敘事探索
(湖南科技學院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湖南 永州 425199;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北京 海淀 100875)
在閻連科看來,當代文學,面臨一種深刻的表意危機,就是文學的內容表達與形式革新跟不上現實生活變化的腳步;就他自己而言,對此已經產生一種“沉在水里憋氣一樣”[1](P267)的感覺,甚至感到一種絕望。生活矗立在作家的面前,就缺合適與有力的表達,“今天的現實富得像是一個礦,而小說的內容卻窮得只有幾粒鵝卵石”,“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么覺得文學的無力和無趣”[1](P266)。文學如何在當代社會氛圍與媒介環境下發展,一直是閻連科積極思考并努力探索的問題。其最新的長篇小說《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可以說就是以電影的名義來“解決如何寫的問題”[2]的一次嘗試,是尋找更合適的方式來反映和思考當代生活的一次敘述變革實踐。“速求共眠”這個關鍵詞,既是對當代社會生活的癥候式歸納,又是以電影為方法的敘事“換氣”實踐,更是一種閻連科式的批判性哲思。
一、電影的“閃念”[1](P1)
小說一開始就,談到了這次小說創作的緣起。這次“創作遠行的始發站”[1](P11),是一個叫“閻連科”的不得意作家,腦子突然浮現一個制作一部電影來擺脫作為作家的困窘的靈感。小說開頭用了很長的篇幅來夸張地寫他這個閃念,這是在他50 歲生日苦苦思考藝術與名利關系問題并終于明白“藝術的鄉愁是名利”的那個深夜產生的,并夸張地說,這是失眠送來的“神賜的靈感之大禮”[1](P2)。他本來是在從黑夜里摸索治療失眠的藥,但摸到了手機,聯想到攝像機,聯想到把自己紀實小說《速求共眠》中的李撞故事“自編、自導、自演一部電影”[1](P3),進而暴得名利,從而“讓自己從貧窮而又自詡清高的文學隊伍中,一躍跨界為電影藝術的大師”[1](P3),就好像一條土狗成功“混進貴婦人的懷抱”[1](P1)。這個過程,充滿隱喻。失眠,隱喻著當代作家與文學陷入困頓、精神焦慮甚至生病,電影似乎成為治療患病作家或者當代文學的藥。雖然這個藥也許有毒,但他仍然為想到能以“銅臭花開,暗香撲鼻”[1](P3)的電影事業來拯救自己這個直到今天“還在文壇為微名小利而蠅營狗茍、偷偷竊竊,活得像牢籠中要光無光、要滅不滅的豆油燈”[1](P2)一樣千辛萬苦的作家而激動不已。小說由此出發,意義頓時變得深刻、博大。
在這個激勵自己的靈感基礎上,“閻連科”通過與電影、美術等別的藝術對比,進一步指出文學如今已經面臨困境,已經失去應付現實的平衡能力,“若寫出了人的靈魂,就一定要放棄對讀者的苛求,要獲取讀者和錢包的喜悅,那就一定要在小說中把靈魂當作大鍋燉菜中的豬肝和豬心”[1](P5)。而電影卻能夠更好地照顧到現實利益的訴求,“電影這門所謂的藝術是最能把金錢、名聲和精神、靈魂混為一談而糾纏不清的一個魔藝桶。在我看到的現實中,世界上唯有電影才可以把靈魂的斤兩以正比的方式,擺上巨型天秤的兩端。而別的藝術,則完全失去或正在失去這種正比的依據。”[1](P5)雖然不乏調侃的意味,但出于現實的藝術利益考量,“閻連科”決心利用過去所寫紀實小說《速求共眠》里的人物與故事為基礎,打了雞血似的將這樣一種奇思妙想,努力去付諸實踐,真的努力去做電影了;目的也很明確,就是想借此“在世界電影場上鬧騰一下子,得名贏利”[1](P5)!
不管電影到底是不是這樣一種能夠讓患病的作家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很明顯的事情是,電影作為一種有別于文學的藝術樣式,從《速求共眠》的寫作緣起到整個寫作過程中,已經被征調到小說里面,當做一個激發藝術動力的機制存在:一方面電影被看作是優于文學的能夠更好實現精神與物質兌換的當代靈魂交易場所,正如“閻連科”所說,世界上的藝術不過是“名利上的西裝或者中山裝”[1](P2),而電影“是今天唯一可以把靈魂以斤兩變賣的典當行”[1](P5);另一方面電影被看作是通向藝術天堂的當代巴別塔,成為敘述創新的一個夢想通道,20 世紀文學“要成為世界文學的一個新高峰”[1](P265),要更多地關注“作家那通向靈魂的路——什么敘述結構呀,腔調節奏呀,前流后派呀,創造主義呀”[1](P265)。電影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呼出,仿佛當代的末世英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故事和文學”[1](P2),但“我們正處在現實的巨大漩渦內,可幾乎每一個作家都只能站在岸上眼巴巴的望,還生怕渾水濕了自己的腳”[1](P266),這樣是不行的,我們必須行動,必須下水。當代小說的形式創新,需要面對時代持續不斷地切實進行,努力實踐,從而探索新的敘述模式與新的藝術道路。電影就是這樣的思考之下,被“閻連科”從世界眾多藝術對象中選中,成為文學乞靈的對象。
二、方法的征用
在《速求共眠》里,電影已經被作為解決當代作家生存困境的一種方法,閻連科由此展開一場對小說敘述模式進行革新的探索。那么,電影具體是如何重構作家“通向靈魂的路”的?在《速求共眠》中,不僅全文圍繞著編導電影的目標展開影像思維賽跑,而且在具體行文之中掄起電影敘事的刀槍,吸收運用電影的結構與手法,如鏡頭式多角度展現、片斷式大跨度組合、戲劇化跌宕轉換等,結合多聲部的口頭語言、“閻連科”的攝像機式運動、開放形態的場面調度與嵌套的結構布局,使得整個小說有一種影像化的立體感。
首先,構建電影化故事核與劇情鏈。小說的開頭就拋出一個亟待電影化的故事,也就是李撞的故事,全文圍繞李撞過去與苗娟的強奸故事、現在與李靜的愛情故事,然后通過對李撞、李靜本人以及對洪老師、羅麥子、李社、蔣方舟等旁人的采訪調查,多方求證,采用戲中戲的模式,在小說中衍生勾連地設置紀實小說、采訪記錄、審判案卷、電影劇本形成基本的故事文本鏈,在似是而非的探討過程中,不斷擴展延伸,交叉嵌套,形成一個駁雜豐富的敘述,建構起一個環環相扣的有機文本整體。
其中關鍵之處,是設置能夠分身的作家閻連科:既作為小說的現實作者閻連科,又作為文本里面的敘述者“閻連科”。作為外在作者的閻連科,以小說家立場來構建整個小說,設計布局;而作為文本內敘述者的“閻連科”,則在自己的電影功名心驅動下不斷行動,成為推進故事向前發展的敘述發動機,既像是《速求共眠》各場戲真正的導演,又像是運動中不斷變化的電影鏡頭。在小說中,敘述者“閻連科”展現出一種元小說式的打破框架特點,在各種文本之間走進走出。他以拍電影的名義,串聯各種散落的材料,將所有的人、事激活,掌控著故事的推進,貫穿全文。文本里的“閻連科”,可以命名為“電影中毒者”,他像一個如癡似狂的戲精,上串下跳,或調查、或討論、或闡述、或表演、或編寫,通過他帶有戲劇化的行為,有機地構建起全文的內外鏈接,使得小說的內容越來越充實,將小說的內涵不斷推向深化。
其次,進行畫面化處理與蒙太奇式剪接。情景的畫面化和情節的戲劇化,成為小說《速求共眠》的重要表現形式。《速求共眠》全文按照先后次序主要由靈感閃念、紀實小說、菊餐廳場景、采訪調查、審訊卷宗、電影劇本與顧長衛工作室討論等情景畫面構成,呈現明顯的片斷拼接特點。這種結構方法其實就是借鑒了電影敘事技巧,也就是蒙太奇手法。小說將那些看起來雜亂無章的人事、場面,通過拼接、對比、交叉切入等方式,剪輯成極具張力的現世奇談。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整個《速求共眠》可以說是作者一次精心設計與剪輯的一部電影。作為窺視現實的孔道,“電影畫面可以為某些內容制造隱喻效果提供方便”[3](P29),表達象征的意思。文中那些閻連科式宣稱的“非虛構”人事片斷,幾乎都被鏡頭化與象征化,看起來頗像一個個冷靜客觀的長鏡頭、悲傷的閃回鏡頭、深挖內心的特寫鏡頭或者充滿迷幻色彩的逆光鏡頭等等。整個小說就像在一個一個鏡頭之間進行蒙太奇處理,從而將不同形式的文本或者敘述片段結構成一個整體。小說中的場景片段看似孤立、散落,呈現出一種形式上的紛亂、混雜,實際上又互相勾連、抵牾與轉進,通過快速切換不同的生活情景,呼應當代中國的現實,反映現代人的功利心態和多元情思。如此,既使得文學敘述與迅速多變的當代生活節拍更契合,又進而能犁進社會與個體的思想深層。也許,這正是閻連科探索突破既有敘述的努力之所在。
最后,語言上的對話化。整個《速求共眠》簡直就是一場關于如何炮制一部讓人信以為真的電影的對話,隨處可見獨白、對白等類電影語言的運用,具有明顯的口語化特點。“電影和戲劇中的語言是說出來的”[3](P245),可以看到,整個《速求共眠》是以說話為主,通過口述或者現代媒介進行對話,或現場討論,或彼此詰問,或追憶解釋,或激情宣講,或電話,或微信,或短信,或電郵……將所有人物進行戲劇性對話設置,并且大量使用新媒介,對話的形式與內容更具當代特點。小說里三種版本《速求共眠》:紀實版的《速求共眠》、訪談版《速求共眠》、電影劇本版的《速求共眠》,幾乎都是以交談、對話來構建文本,如閻連科、楊薇薇、顧長衛、蔣方舟、郭芳芳等關于電影業務的咨詢、商量、討論,李撞、洪文鑫、羅麥子、李靜等圍繞有關事件的告知、猜測、議論、對峙,警察趙強國、李靜、李撞等進行的問詢、審訊等。這些對話多向而交錯,以人帶事,依托場景、細節與背景,一起構建起全文的故事內容。通過日常對話、應急對話、交際對話、采訪對話、心靈對話、審訊對話等多種形式,讓事情互相證實或者證偽,推動敘事發展,輔以旁白、潛臺詞、畫外音,讓人物的善良、虛偽、懦弱、勇敢、沖動、理性等內在特點得以展現。內容的不斷切換與場景的城鄉跳躍,又能讓對話情景不雷同重復,并且能多角度廣闊地反映當代社會生活。《速求共眠》語言上的對話化設置,吸收了電影臺詞藝術的營養,很好地推動了情節、塑造了人物、深化了主題,使得整個小說內容飽滿、形式新穎,甚至使得小說因為“有著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由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真正的復調”[4](P29)。這種形式上的探索,是很能體現閻連科文學敘事的先鋒考慮。
三、表意的冒險
對于當代中國文學的發展,閻連科有種深刻的危機感,表現出一種對自己寫作現狀的閻連科式憂慮,甚至絕望。閻連科不僅在小說里曾借李靜的老師的嘴對當代文學作品進行揶揄,“當代文學都是垃圾”,“讀當代文學,純粹就是浪費時間”[1](P114),而且自己也一再感嘆說“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感到寫作無意義”[1](P263)。這是作為當代著名作家閻連科的個人感受,雖然可能有些夸張,但也多少能反映當代文學的時代癥候。置身文化多元、媒介多樣、讀者分化的當下社會,作家個體甚至文學整體都有著一種表意的焦慮。
當代文學的前進之路在何方?閻連科秉持一個寫作者的立場,滿懷表意焦慮地堅持不懈進行探索,在他的每一部新作中,都極盡所能地嘗試文學與時俱進的新可能。就像小說《速求共眠》所寫的那樣,在消費時代的經濟規則主導之下,作家與文學已經身處邊緣,對文學及其發展、探索也無多少人關注,作家常常是顧影自憐,甚至顯得無用、滑稽。對于身兼時代優勢與毛病、可看作當代社會縮影的電影,雖然小說里的作家“閻連科”內心不服,時時反諷,但擋不住現實潮流的裹挾,一次又一次不斷俯下身去尋求以顧長衛為代表的電影行業的各種人物,鼓動如簧之舌以謀求理解與支持,企圖以自己紀實小說中的人物李撞為基礎自己來做一部電影。在他看來,這已經成為拯救彷徨無路的作家的暗夜靈光,成為藝術事業與文學人生中激動人心的目標,成為名利增殖與身份轉變的康莊大道,顯得夸張又現實、荒誕又瘋狂。
閻連科認為,面對不斷變化的當代生活文學應該用新的形式與方式來反映,這是當代作家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與應該擔當的重要責任。但是,事實上這很不容易,閻連科常常被這種責任感壓得喘不過氣來。為此,早些年,閻連科就提出一個“神實主義”[5]寫作的概念,試圖通過運用“在日常生活與社會現實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話、傳說、夢境、幻想、魔變、移植等”手法與渠道來“創造真實”[5],反映當代人的生活。當然,“神實主義”引起了爭議,但是這無疑是閻連科的一種積極探索,他始終堅持選擇用持續不斷的文學創新來回應現實。小說《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就是閻連科在這種情況之下,直面文本內外的危機做出的又一次悲壯努力,表現出一種重構當代敘述的宏愿。為此,他化身為敘述者“閻連科”,在小說里以電影之名,綜合運用紀實性小說、微信、采訪記錄、審訊案卷與電影劇本等多種樣式的現代文本,尤其是通過對電影、微信、電郵為代表的現代媒介、文本虛虛實實的大膽征用,使得整個敘事呈現出一種技藝的狂歡。“閻連科”甚至自己在小說里戲謔地稱之為“混虛構于紀實之中、混紀實于藝術之中、混藝術于現實的場景與生活之中”的革命性的“混藝敘事法”[1](P234)。
吊詭的是,雖然閻連科很賣力,在小說形式上別出心裁以及大膽實驗,但是很長時間以來并沒有讓他的創作在小說內外兩個世界變得更加容易被接受。在文本里,以文字為業的作家“閻連科”在消費與聲像主導的當下社會正陷入窘境,“閻連科”自己在《速求共眠》里發現,書店里“原來擺著我的書的書架上,全都改擺了別的當代作家的書”,店員告訴他,“閻連科的小說從來沒人看,兩個月才賣出去一兩本,我們前幾天把他所有的小說都下架退回了出版社”;而小說之外的現實情況是,在《速求共眠》出版之前五年中,閻連科已經寫過三部小說,都得不到出版[6]。小說《速求共眠》的出版也屢屢遭挫,“閻連科曾將此書的文稿向雜志社投稿,原本以為會非常輕松,未料出版過程卻出乎意料的艱難:在被《花城》拒絕了之后,《速求共眠》經歷很多周轉,直到 2017 年才部分刊載于《收獲》。后來閻連科又找了十家出版社希望推出單行本,結果收到的回復均是一紙退稿函。直到(2018 年)歲末年初,意識比較先鋒的出版機構理想國才愿意接手本書在內地的出版發行。”[7]這樣的現實遭遇,讓作家閻連科在挑戰藝術創新的壓力之外,還有種源于當代文學艱難的生存環境的壓力,藝術創造和現實存續的雙重艱難,讓他覺得“到了一個寫作的焦慮期和掙扎期”,“每次提筆都感到有手卡在脖子上,讓我呼吸不上來”,“如一個人沉在水里憋氣一樣”,“如若換不了氣,那就只有憋死在水下邊”,無法預測未來,只能降低要求,“不求痛快和暢游,只求能讓人換口氣”[1](P267)甚至讓他覺得自己在寫作上可能已經是“逐漸走向謝幕”[1](P263)。
現實的危機與表意的焦慮,通過小說里的“閻連科”竭力跨界電影以助他擺脫困局的時而激動不已、時而火燒火燎的言行,表現得淋漓盡致。文本內作家“閻連科”甚至不惜孤注一擲,“我要用自己所謂的名聲,再次以李撞這個人物為原型,自編、自導、自演一部電影。集編劇、導演、主演于一身,讓自己從貧窮而又自詡清高的文學隊伍中,一躍跨界為電影藝術的大師,讓那些苦苦在電影圈里為名聲、票房、片酬和國內、國際的獎項而每日奮斗的導演和演員,完全折服于這部電影。”[1](P3)文本內的“閻連科”為了改變作為作家的困境,近乎瘋狂地想成為一個名利雙收的電影藝術家,看起來似乎不干文學了。不過,他的奢望、妄想和堅持,他的妥協、說服與激辯,其實都只是現實中的作者閻連科采用的一種文學表達策略。面對名利引誘、受眾期待與媒介編碼,文學與作家都面臨沖擊,閻連科清醒地看到這一點,一方面讓敘述者佯裝被電影迷了心竅,在現代消費與媒介增殖的誘惑之下,日益逸出文學范疇,從紀實小說《速求共眠》(一),到微信新聞《蟲凰相愛緣何來,蓮花盛開污泥香》,再到電影劇本《速求共眠》(二),文本生產與文學敘述全力遵循影視化的原則與大眾化期待,“踏上奮不顧身的名利之途”[1](P1);另一方面在小說里,對電影圈冷嘲熱諷,認為那是一個“飄飛在垃圾場上的花園”[1](P3),內心深深地鄙視;小說最終讓電影制作的預期沒有實現,這正是對電影的最終否決,是文學對庸俗化路線的蔑視,是敘述對文學歧途的修正。而在小說之外,作為看到問題的作家,閻連科高明地讓小說反過來對媒介、影視、新聞等進行兼容與收編,通過《速求共眠》的敘事實驗展示文學在消費文化夾擊下的突圍努力,展示并保持著作家的主體性,展示并保持著文學的主體性,為了文學,他不惜做一個當代寫作探索道路上的賭徒,“要么重新開始,要么就此落幕”[1](P268)。
四、“非虛構”的思考
在小說封面上,閻連科就以副標題的方式首先居中亮出“我與生活中的一段非虛構”[1]封面這幾個字,在小說里又重申要“讓藝術回歸全真實、回歸實生活,回歸生活本身最真實的一切”[1](P63),似乎里里外外都在宣告小說寫的都是真實的。閻連科就這樣,以一個編電影的故事,努力營造出一個所謂“非虛構”的敘述烏托邦,讓人重返“真實”的迷宮,讓人不得不對文學及其真實與虛構的關系再度思考。什么是真實,界限在哪里?很多時候,這在閻連科的文學世界里變得難以確認。當然,他自己也正一直在努力這樣干。文學、作者與世界本身及其關系,在他,似乎都變得恍惚。也許,這種恍惚感,就是他要說的真。他所說的真,也許,就是他所提倡的“神實主義”里的那種真,就是努力在對生活進行閻連科式描寫的同時,讓其處處充滿象征或隱喻。
首先,生活敘述真假難辨。《速求共眠》以“非虛構”的名義,似乎費盡力氣想弄清楚的,是鄉村青年李撞強奸同村少女苗娟、農民工與李撞與北京大學研究生李靜戀愛的兩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然后以此來做一個似乎要紀實的電影。整個小說以籌拍電影為抓手,圍繞這兩件事情展開追溯與構想,通過走訪當事人、查看案卷與反復研討,讓李撞、李靜、“閻連科”等在時空的不斷切換中彼此交互,通過事件的不斷勾連、衍生,把鄉村與都市串聯起來,反映當代中國人的個體生活,將局部真實與整體象征多層疊加,在當代中國人的欲望、道德、倫理、文化、人性等深礦中,不斷掘進。
敘述者“閻連科”首先拿出一篇紀實小說《速求共眠》,如實記錄青年農民李撞農村強奸事件,然后又拿出河南中年農民工李撞和青年北京大學研究生李靜的離奇都市愛情微信新聞,并且掛出“非虛構”的三字招牌予以標示。那么,《速求共眠》里的生活敘述到底真實不真實?在隨后的調查中,似乎全部變成說不清楚的事情。因為一旦換個人、換個時間、換個角度來看,都不再那么真實,幾乎所有的人、事都走了樣,甚至彼此不斷顛覆。有人說,這是一種《羅生門》式的敘述[8]。初一看,的確有點像,但細細一想并不是簡單類似,閻連科顯然有著更大的野心。比如,從敘事技巧看,小說打破文本框架,讓“閻連科”在文本內外穿行,這是《羅生門》所不具備的元小說特點。從內容看,小說《速求共眠》比《羅生門》更多一些現實的批判性,更多、更廣地指向當代中國生活的本身。從思考來說,小說《速求共眠》也可能比《羅生門》更深刻,不僅像“神實主義”所提倡的那樣,努力“在創作中摒棄固有真實生活的表面邏輯關系”,去探求一種“看不見的真實、被真實掩蓋的真實”[5],而且通過小說內人物與事件的反復追問,將生活的真實性、敘事的可能性推向深刻的猶疑,而且質疑世界與意義的確定性,從而顯現出某種深刻的哲學性,甚至有些玄思的意味。閻連科通過敘事結構技巧的實驗,在兼收并蓄和刻意求新的敘事中,表達出一種對人與世界本身的深思,作家、小說與世界似乎都有了一種虛與空的恍惚,以致于讓人懷疑存在的確定與必要。這既展示出中國當代人在生活、情感與思想等方面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又展現出當代文學仍然擁有反映當下生活復雜性的巨大能力。
其次,真實可能就是一種丑陋。在閻連科筆下,揭開真實的面紗之后,很多時候看到的不一定是美的。比如促成苗娟與李撞合法、恩愛婚姻的真實原因可能是惡名遠揚的強奸,李靜與李撞傳奇式愛情起因是其導師妻子毫無道理的猜疑引發的工作迫害。《速求共眠》里的各種事情打開之后,露出的常常是美好面紗之下的各種丑陋底色。比如,美好的電影藝術設想,不過就是名利的驅動。作為“教授”“理想主義者”“社會良知的代言人”“作家”的敘述者“閻連科”真實的一面,可能是“瘋子、商人、巫師和謊言制造者,是藝術的仇敵和名利的設計師,是這個社會的毒瘤和靈魂假藥的制造商”,以及“野心家、最誠實的奸詐者”[1](P9),以致于他在采訪中被李撞指責:“你寫的文章沒有一篇是說咱村人、鎮人的好,全在賣咱村人的孬。你是靠賣咱村人的孬處換了名聲的。靠賣中國的孬處才有名望的”[1](P80)。敘述者“閻連科”一方面癡心艷羨地想做看起來很美的電影,另一方面不斷揭電影及其行業的短,對其嘲諷鄙視。也許這正反映閻連科一貫的真實觀念,“審美就像裸體外的紗羅,在馬虎的眼里美成一首詩,而當你定睛細看之后,就只有丑陋而已。”[1](P263)而當敘述者把丑陋的真實置換成審美的紗羅的時候,反過來又揭示出另一種丑陋,就是作家為了自己的虛名實利常常進行不道德的瞎編,“渴求某一天名利雙收”,以致于在“高尚和虛偽的夾道上”,“健步如飛”[1](P1)。小說《速求共眠》就是這樣,用電影快鏡頭式的切換,不斷用一個真相將另一個真相置于尷尬的境地。
最后,真實或者就是一種荒誕。強奸、畸戀、猜忌、失業、詩句、絕境、性交易、報復殺人、賣骨灰、賣王八、偷竊、審訊、派出所、高考、大學、鄉下、工地、北京、電影、人民幣……《速求共眠》以這樣一些有賣點的“非虛構”,展開極有張力的敘述與夸張吸睛的故事,件件看起來都似乎離奇又荒誕。比如小說里那個來自河南的50 多歲農民工李撞,有著強奸苗娟前科的李撞,竟然在北京被與他相差30 歲的北京大學女研究生李靜愛上了,“中國最有名的大學里最漂亮、最有前程的南方大學生”,愛上了“一個最土、最沒有文化又最窮最丑的北方男中年”[1](P62),這完全不合常情。號稱“視藝術為親情的顧長衛”[1](P14)實質上不過就是一個名利的發動機,其三層樓的工作室里充斥著“取材于人民幣的局部異變的巨幅現代攝影作品”,這些裝飾品的尺寸、數量與傳達出來的意味無不夸張得讓人驚訝與恍惚[1](P244)。敘述者“閻連科”為拍電影所經歷或見聞的故事與人物,幾乎無不如此奇詭和荒誕。對這樣的敘述,閻連科解釋道:“如果說這個小說是有意義的,那么最大的意義不是閻連科在里面還能不能寫作,也不是到底有沒有李撞這個人物,他和北大的姑娘李靜到底有沒有愛情,這都不重要,這就是一個荒誕的故事,是今天中國的一個巨大的真實。”[7]在閻連科看來,“生活其實遠比文學更夸張、荒謬”,“我要解決如何寫的問題”,閻連科通過夸張而又荒誕的寫作,“讓真實把虛構給擊碎了,同時又是讓虛構把真實給擊碎了”[2],通過模擬非虛構,試圖勾勒出這個時代的詭譎,努力揭示鄉村與都市人難以盡述的生存樣貌與精神形態。閻連科正是通過這種電影獨白式的荒誕敘述,“讓自己朝著真實走過去”[1](P10),啟發大家對當代中國人的生活及其面臨的問題展開深刻思考。
總之,在《速求共眠》中,閻連科借電影的名義展開小說寫作,記錄當代個體的人生、感情,反映資本、網絡、媒介等豐富的時代與社會內容,以電影為方法進行敘事實驗與社會反思。閻連科讓小說里的“閻連科”故意困惑地說,“我不知道那么快捷流淌的寫作,是有賴于我那大量的采訪和生活之積累,還是有賴于名利膨脹成的創作激情或者名利發動機”[1](P146)。看起來,電影似乎在小說里成為敘述者“閻連科”點燃文學創作激情的發動機,實際上當代環境與個體生活才是作者閻連科敘事生長的養料,因為當代中國的現實生活才是當代文學持續自我更新的一個社會性輸液管道,最終是“生活創造了文學故事”[2]。電影在小說里可以說已經成為了具有極強精神操控性的現代實利社會的隱喻,企圖拍出口碑爆棚的電影則是小說呈現的迎合庸俗社會規則的一種象征行為。閻連科在《速求共眠》中充分表現出文學理想和生活柵欄之間的緊張,在表意的焦慮中努力開拓,推動著中國當代小說敘事的技術改進和觀念革新,探索文學未來發展的可能和道路。不過,也應該看到,閻連科在鏡像現實生活、尋求文學突破的“憋氣”與“換氣”過程中,表現出某種沉溺敘事技術實驗的亢奮,也有種將生活簡單化,甚至表現出虛無主義的跡象,這很難說是危險還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