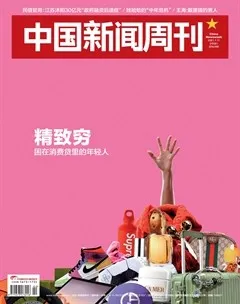妥善處理中美關系中的意識形態因素
樊吉社

特朗普執政后調整了美國對華戰略的框架,用戰略競爭取代對華接觸與中美合作。美國宣稱作出這種調整是因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治理模式沒有朝著美國期待的方向發展。從2017年到2019年,經貿爭端及其解決之道是雙邊關系的核心問題,意識形態因素并不突出。
2020年5月以來,這種情況開始出現顯著變化。特朗普政府發布《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方針》報告,其外交安全團隊發表系列演講,采取系列政策,激烈攻擊并定向瞄準中國共產黨、中國政治制度和中國國家領導人,試圖將中美戰略競爭塑造為制度之爭、意識形態之爭。
那么,我們應如何看待中美關系中的意識形態因素?
中國的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自信越來越強,這是無須質疑、不用回避的客觀現實,理解中國政治和政策中的意識形態內容需要回歸歷史背景。鴉片戰爭讓中國先后喪失了器物和精神兩個層面的信心,此后的180年是中國通過各種嘗試與探索尋回器物和精神自信的歷程,包括向日本、歐洲、蘇聯和美國學習。這些探索讓中國找到了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找回了器物層面的自信。
對中國而言,過去二十年國際形勢的發展也是一個西方話語和制度去魅的過程。一些國家以種種借口干涉他國內政、對其他國家發起侵略戰爭、在國際事務中采取雙重標準、國內政治和社會治理失能和失靈,其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治理模式并不值得中國學習效仿。
中國融入國際體系后,一方面經濟保持高速發展,另一方面社會保持穩定,中國無須“拷貝”他國模式同樣可以實現繁榮富強。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治理模式是在長期探索中形成的,并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是適合中國人民的制度。中國現在要尋回精神層面的信心,擺脫歷史的沉重枷鎖,相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不僅行得通,而且可以走得好。這也是為什么中國強調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夢和四個自信。
中國擁有意識形態自信,愿意與世界各國、各政黨進行對話,但這既不表示中國會進行意識形態輸出,更不意味著中國將與其他國家進行意識形態競爭。2017年12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中指出:“我們不‘輸入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不會要求別國‘復制中國的做法。”對于近期美國部分政客試圖將中美關系意識形態化的言論,中國外交高層在公開場合的表態中均強調,中美雖然制度不同,但應相互尊重;“中美雙方不應尋求改造對方,而應共同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存之道。”
近期特朗普政府高官有關意識形態和制度之爭的言論充滿了偏見和焦慮。中美兩國在具體議題上存在一些分歧甚至摩擦,這是正常的,可以通過對話或談判解決。如果將中美所有的分歧都視為意識形態之爭,中美將面臨零和博弈,分歧將無從解決,這不僅不利于中美任何一方的國家利益,也不符合兩國關系的基本現實。
中美兩國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治理模式不同,美國應該基于這樣一個基本事實處理雙邊關系。外部力量以前沒有能夠改變中國,以后也不可能,中國更不可能在此種外部壓力下妥協。能否妥善處理雙邊關系中的意識形態因素,不僅影響中美兩國各自的政治、經濟和外交政策,而且將塑造雙邊關系的發展方向。
對中美兩國而言,和平共存而非意識形態之爭,才是唯一的正確選項。

2019年11月22日,由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重慶圖書館共同舉辦的《繼往開來:紀念美中建交40周年》圖片展在重慶圖書館開幕。展覽共展出照片37幅,拍攝內容在時間跨度上記錄了從1979年以來,中美兩國在各領域交流合作的重要時刻。圖/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