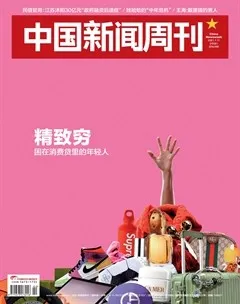宿務:麥哲倫的滑鐵盧
馬劍

定光寶殿遠處是宿務的海港。
客輪剛剛抵近宿務港口,坐在一旁的愛莎便開始在她的胸前劃起了十字架,嘴里還不停地念叨,感謝上帝讓這趟旅程風平浪靜。在菲律賓出行,人們習慣說跳島,菲律賓大大小小分布著七千座多座島嶼,島民間往來的交通工具基本都是靠船,在這里坐船猶如日常乘坐地鐵一般,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但如果趕上了大風大浪,就遠沒有地鐵那樣安全了。
愛莎的家住在距宿務30公里遠的保和島,她平日都在宿務工作,只有到周末才能回去。船艙外一座乳白色的教堂屹立在岸邊,教堂上方的十字架,似乎是在向遠道而來的客人昭示,你已經進入了它的地盤。
宿務位于整個菲律賓的中部,同時也是米沙鄢群島的中心島嶼,作為菲律賓第二大城市及最重要的港口,每天往來、穿行的客輪不計其數,大大小小的客輪,早已把港口擠得滿滿當當。
相較于無序的港口,市內的交通同樣混亂不堪。路上飛馳而過的摩托車,絕少會禮讓行人;造型各異的吉普尼,這種“二戰”時期美軍遺留下的改裝加長吉普車,是當地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沒有固定的站牌,路人隨時可以招手上下車;路邊的建筑同樣混亂感十足,略顯老舊的高樓中間夾雜著殖民時期留下的西洋小樓,加之炎熱、潮濕的天氣,讓初到此地的人多少感到有些躁動不安。
而這種感覺,不知道500年前第一次踏上這片土地的麥哲倫是不是也會有同樣的感觸。1521年,麥哲倫率領船隊途經宿務,當地的酋長帶領部下歡迎了他,并很快被麥哲倫說服,并接受了施洗,成為首批菲律賓基督教徒。然而,不久之后,麥哲倫在試圖征服鄰近的麥克坦島時,被島上的酋長拉普拉普殺害。沒想到,這位對人類地理大發現有著重要影響的人物,就這樣草率了結了自己,他的尸體至今下落不明。

存放麥哲倫十字架的六角形亭子。

宿務街頭的雕塑,反映當年來到這里的西方傳教士。
當地人在經歷過短暫的勝利后,宿務島于1565年最終還是被來自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占領。在歷經西班牙、美國、日本的先后占領,直到1946年菲律賓才獲得了完全獨立。雖然擺脫了殖民者的束縛,但在信仰上卻不可避免地烙下了殖民者的印記,如今的菲律賓約85%的國民信奉天主教。在宿務,教堂隨處可見,但凡規模大一些的學校或是醫學院都會自帶教堂,學生們不但要學習圣經課程,還要按時做彌撒,而在教堂中,最常見的圣物是一張被復制的圣嬰像。
圣嬰像的真身保存在圣嬰教堂,教堂位于宿務的下城區,這座始建于1565年的教堂外表看上去多少有些殘舊,但并不妨礙這里是宿務,甚至是整個菲律賓的精神家園。
當地人在教堂中祈禱過后會不約而同地向一間小屋聚集,只為一睹小屋中的圣嬰像。這是一個木雕像,造型是幼兒時期的耶穌, 安置在有玻璃保護的神龕中。人們走到圣嬰像前畫十字禱告,有的人還要盡力用雙手觸碰圣嬰前的玻璃罩,親吻圣嬰周圍的擺設,離去時還難舍地深情回望。
據說,圣嬰像是當年麥哲倫贈給土著首領老婆的,多年后,存放圣嬰像的房子被一場大火毀盡,這個木雕卻沒有被大火燒壞。當地人相信一定是因為神的力量,這尊圣嬰像此后就一直供奉在這座教堂里。每年1月第三個星期日,宿務都會舉行盛大的圣嬰節,屆時整個宿務的大街小巷都會看到圣嬰像的身影。
教堂旁邊還有一個并不起眼的六角形亭子,這里存放著麥哲倫當年到達宿務后在海灘上豎起的十字架。逐漸被當地人神化的麥哲倫,讓他們相信服用十字架上削下來的木屑可包治百病,為了保護十字架不被吃掉,外面不得不用木頭建造了一個空心十字架將原來的十字架包住。不過這并不妨礙信眾對十字架的期待,不少人會跪在十字架前,為家人的健康祈禱。
但當人們走出教堂,剛剛還虔誠滿滿的當地人,立刻變得歡快起來。教堂外的廣場上,各式各樣的小吃攤以及販賣供孩子們玩耍的氣球,將凡間的世界裝點得異常熱鬧。
宿務市區除了隨處可見的教堂外,同樣作為舶來品的中國道家寺廟,也零星分布其間,其中最為有名的道觀是定光寶殿。這座道觀位于宿務北郊的山坡上,建于1948年。雖然年代很久,但看上去卻很新,所有的雕塑、裝飾都像剛剛刷過一番。正殿門口坐著一位上了年紀的老先生,明顯是華人的模樣。見我用普通話向他問好,他同樣報以標準的普通話,老人在這里做義工,他告訴我,道觀的裝修都是當地華人的捐贈。

圣佩特羅堡內的博物館,介紹宿務的建立過程。
來道觀參觀的不僅是華人,也有不少當地土著的年輕人,他們也會學著華人的樣子,上香、叩拜、祈福。我略有冒失地問了其中的一個年輕人,“你們不是信仰上帝嗎?怎么也會來這里?”“這里的風景好,我的姥爺是華人,小時候也會和家人一起來求簽占卜。”在宿務,華人的數量只占百分之十幾,可卻掌握這里一半以上的財富,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何在天主教的地盤上,道教也可以占據一方寶地。
宿務的商業貿易、旅館餐飲、金融等大多被華人所把持著,最明顯的是街邊規模較大的連鎖快餐店基本都是華人經營的中餐館。不過這些中餐的味道大多被改良過,并不合我的胃口。通過當地人的指點,才知道這里的正宗美食多半集中在大商場里。宿務的大商場像所有發達城市一樣,裝飾豪華、大氣。但走進去卻聽到不少擦肩而過的年輕人說的是韓語,商場內的商家宣傳標語、價目表不少也是英韓對照。哪里冒出來這么多的韓國人?一問才知道他們是來這里學習英語的。
菲律賓現在的官方語言是英語,加之低廉的人力成本,讓這里的英語語言培訓價格遠低于西方國家,逐漸開始吸引了大量韓國留學生。不過,與我同住一家旅館的日本人工藤并不這么認為,他覺得,這與近幾年韓國對菲律賓貿易和投資迅速增長有關,從而帶動了更多韓國人來到了這里,“我們已經退步了”。工藤多少有些憂慮,菲律賓作為日本傳統的市場,大街上跑的汽車大多是日系的,但很明顯,在這座城市中,韓國車也越來越多,路邊韓式燒烤店開始受到歡迎,商場內的液晶大屏上循環播放的也都是韓國女團的勁歌熱舞,韓國的痕跡已經越來越重。
相對于工藤的悲觀,路上結識的中國游客阿凱則樂觀得多。身為浙江人的他,有著敏捷的商業嗅覺,他來宿務的主要目的是想聯系當地的芒果供應商,尋找適合的商機。對于他來說,菲律賓是一塊尚未完全開發的處女地。
傍晚,我與阿凱結伴來到港口旁邊的圣佩特羅堡,難掩風化裂縫的墻壁能夠讓人感受到它的久遠,城堡是當年西班牙殖民者抵達宿務后建造的,如今已經改造為開放式的花園。我倆剛好趕上一場正在城墻上舉行的婚禮,一對新人穿著西式的婚紗禮服,雙雙跪在親朋好友的面前接受著眾人的祝福。這種既西式又菲式甚至還夾雜些華人風俗的婚禮,在開闊的草坪上,伴隨著悅耳的音樂,似乎毫無違和感。天性樂觀的菲律賓人,似乎樂于接受一切新鮮的事物。
麥哲倫恐怕永遠也想不到,自己的到來與意外離世,竟能深深地影響到一個國家的信仰與文化。如今看來,真的很難說,他對歷史的作用到底是環球航海更大,還是改變了一個有著億萬人口的國家信仰更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