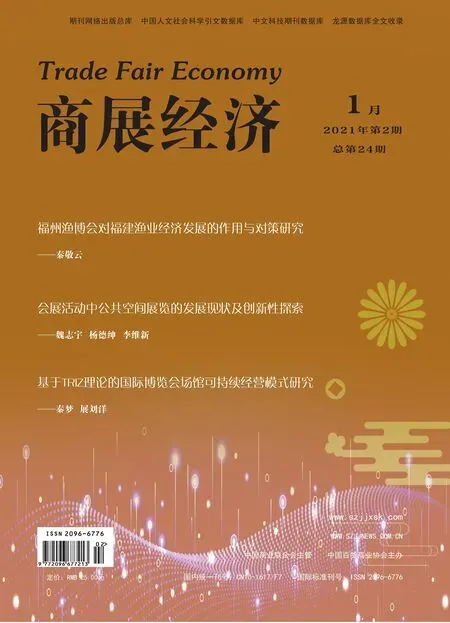資本市場信息披露與內幕交易文獻綜述
上海杉達學院 黃伊婧
關健詞:信息披露;內幕交易;資本配置;投資者決策;文獻綜述
1 信息披露文獻綜述
1.1 信息披露動因
在外文文獻方面,Jiang(2013)以選擇性披露和內幕信息作為落腳點,探討了中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動因及其阻力[1]。Darmadi等(2013)通過橫截面回歸模型發現,家族制企業的自愿信息披露的意愿程度較低,這主要是出于保護家族利益、防止私人信息暴露的目的,而且公司治理機制在促進家族制企業信息透明度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較小[2]。
在國內研究方面,我國學者借鑒國外已有研究成果,結合中國信息披露的現狀與問題,主要從公司的聲譽、公司的社會價值、企業控制權的競爭、證券補償、交易費用的減少、管理層才能信號傳遞、法律訴訟成本、公司治理結構、公司核心能力等方面來探討我國上市公司進行信息披露的動因(張學勇和廖理,2010;羅瑋和朱春艷,2010)[3][4]。
1.2 信息披露影響因素
Broberg等(2010)的實證分析,主要是通過對2002—2005年的斯德哥爾摩證券交易431份年報數據進行的,結果顯示管理層持股比例的提高會降低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程度[5]。Amiri等(2011)通過對法國2004—2007年證券市場的研究發現,上市公司年報內容的翔實程度與市場流動性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因此建議法國監管當局通過加強信息環境建設來減少信息不對稱及流動性不足的風險[6]。李慧云等(2013)研究發現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高的公司,國有控股占比相對高一些[7],其主要以2011年上市的396家深市和滬市制造業上市公司為樣本。牛建波等人(2013)率先比較研究了不同類型投資者(交易型機構投資者和穩定型機構投資者)的不同作用機制,并通過實證分析,發現自愿性信息披露受機構投資者的影響,且是顯著負向影響,但穩定型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能顯著提升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8],其還進一步探索了自愿性信息披露受機構投資者與其所處股權環境的交互作用的影響。
1.3 信息披露經濟后果
目前的研究成果普遍認為良好的信息披露機制對降低信息不對稱并提高投資者保護是有利的,如降低信息不對稱(尤其是降低公司外部和內部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減少投資者對項目的風險(尤其是估計風險),并使公司的資本成本降低(汪煒,蔣高峰,2004)[9],使不知情者與知情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也降低,減少流動性風險和逆向選擇(Asciogluetal,2012)[10]。而低質量的信息披露對改善市場信息不對稱是不利的,會增加內幕交易,造成對不知情投資者的市場剝奪(辛清泉等,2014)[11],甚至加重市場信息不對稱。
1.4 信息披露監管模式
Chowdhjy等(1991)通過模型,分析了內幕交易被監管罰沒的概率,認為最有效的監管政策對內幕交易既不是不限制也不是完全限制,而是允許一定的內幕交易[13]。Chen等(2011)通過分析34個國家和地區1980—2004年中美國次級債公開發行的數據,發現內幕交易行為減少的49—61個百分點有賴于內幕交易的法律法規,說明法律監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顯著的效果[14]。Kadir等(2012)認為馬來西亞法律中有關內幕交易的調查和處罰力度不夠。為達到政府監管的目的[15],提倡通過法律來對內幕交易進行嚴格的規定。
2 內幕交易文獻綜述
2.1 內幕交易產生根源
國內外的研究文獻均表明,超額收益是內幕交易產生的主要根源,如Heitzman等(2011)收集了美國1995—2006年間的545個并購樣本,其實證研究發現非公開談判信息會反映在股價中,股價變動促使了內幕交易的發生[16]。對于中國而言,蔡寧(2012)認為,中國的股權分置改革,使得在解禁股份減持中的內幕交易,成為全流通環境下大股東利益輸送的新途徑[17]。凌玲等(2014)的實證研究發現,脆弱的公司治理會滋生內幕交易的動機從而借此獲利[18]。邵新建等(2014)通過對ST類公司的研究,發現證監會針對內幕交易的行政執法越嚴格,借殼上市的過程中越容易存在內幕交易行為。上市公司在敏感信息披露前的停牌越及時,對抑制內幕信息的提前泄露[19]越有利。
2.2 內幕交易影響因素
Cziraki(2014)以荷蘭證券市場上的內幕交易為研究對象,將荷蘭公司治理法規的變化作為一個自然實驗,實證結果表明法規的變化將顯著影響內幕交易利潤[20]。
姜華東(2010)在一個實施內幕交易監管的框架下,對內部人的利益分配進行了研究,發現內部人的利益不僅與內幕交易監管力度和執行能力有關,還與市場流動性、交易者類型、信息準確度和市場波動性等因素密切相關[21]。劉曉峰(2013)從公司管理層和外部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出發,同時考慮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股票價格、內幕交易監管行為等因素的模型,并將此模型建立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此模型表明:若上市公司CEO是內部交易者,除非將某種形式的額外補償給予CEO,否則對于此類型的內幕交易是不會有效率的,不論怎樣加強監管,市場將不存在均衡。對此模型的模擬計算表明:CEO補償計劃與內幕交易監管行動的結合,有助于提升市場的效率[22]。
2.3 內幕交易經濟后果
通過已有的文獻研究發現,內幕交易對上市公司、資本市場均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如Inci(2012)發現上市公司高管人員的任職期限會對其進行內幕交易產生顯著影響,并進而影響到上市公司的業績,因此良好的薪酬體系可以起到約束高管人員的內幕交易行為的作用[23]。Hsu(2014)發現操作股票價格的內幕交易會加劇逆向選擇問題,并對市場的流動性及市場效率產生負面影響[24]。Agrawal(2015)的研究發現,內幕交易與盈余管理緊密相關,內幕交易會對公司信息披露質量起到負面影響,甚至有礙于資本市場的運行效率[25]。
2.4 內幕交易監管
Bach(2010)研究了116個國家在1977—2006年所發生的內幕交易案例,結果發現跨國合作有助于監管政策的趨同,并可提升對內幕交易的監管程度[26]。
劉曉峰(2012)認為內幕交易者一般是公司高管,而且其一般直接掌握公司信息和運營,因此要研究內幕交易監管,需要關注公司治理的微觀結構。他將公司高管薪酬、股票價格和監管行為等因素納入一般均衡模型中,通過模型分析認為,若公司CEO是內幕交易者,模型不存在均衡解,即內幕交易監管是無效的,除非將薪酬之外的其他額外補償給予公司CEO。劉曉峰指出將公司CEO的補償計劃與監管行為相結合,才能使內幕交易監管達到期望的成效,進一步達到最優監管[27]。
游家興等(2013) 計算PIN指數(知情交易概率),其具體方式是借助證監會下發給上市公司的調查問卷,以此來構建投資者保護指數,并通過實證分析發現內幕交易監管效率受投資者保護在公司內的執行情況的影響較大,改善監管效率很大程度上依靠執行情況的提升,兩者呈現較強的正相關性[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