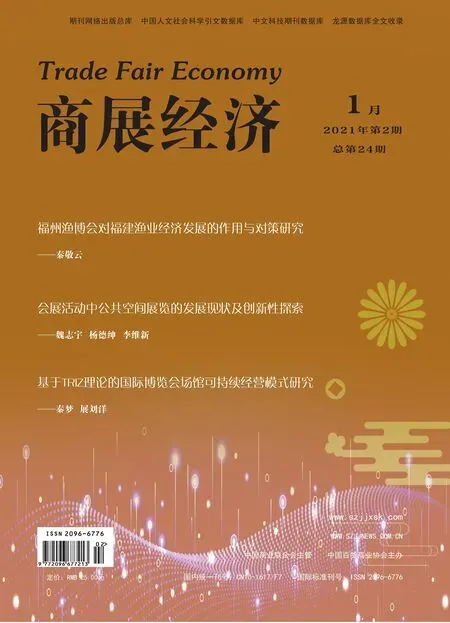探究文博創意標本的建構方式①
——以古熊貓高仿真標本技術為例
四川美術學院影視動畫學院 白世宇
在文創產業興起的大背景下,文博資源創意開發已成為文博產品發揮經濟價值的重要形式,在文博行業中動物標本資源被慣用于科普展示、科研及生物教學等用途,對動物標本資源的創意價值沒有引起業界的足夠重視,動物標本常規的制作主要使用動物真體本身,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復制性的固有屬性,極大地限制了標本文創資源的開發。
在動物標本制作領域,仍然以“標本剝制術”這種傳統方式為主,這一方式對遺存的動物身體毛皮材料進行制作,因珍稀動物的身體資源有限,影響了文博創意產品批量化開發和大面積銷售,“標本剝制術”存在諸多的缺陷,不適用于已經絕滅的或沒有身體依存的動物標本的制作,現有的動物標本僅重視了科普的科學性,但是忽略了審美的觀賞性,標本動態簡單以走、站、跑等動作為主,神情呆滯、形態缺乏表現力,影響著民眾對標本的觀賞體驗。因此,動物標本制作技術亟待優化。
針對以上問題,本文通過對古熊貓高仿真標本技術方式及應用領域的分析,探究文博動物創意標本建構方式,助力文博創意標本開發和文博產業的發展。
1 高仿真標本技術及其擴展應用
古熊貓是中國絕滅動物類別中的典型代表物種之一,是現代大熊貓進化過程中的物種,現存的古熊貓資源主要是化石資源,存放于我國的自然博物館,古熊貓資源的創新開發對加深國寶熊貓的深度認知具有重要意義。四川美術學院影視動畫學院周宗凱教授專注于藝術與古生物跨界融合,采用3D數字技術手段開發了“中國古熊貓進化演繹復原工程”[1],該復原項目2019年1月29日于重慶自然博物館“熊貓時代——揭秘大熊貓的前世今生”大型特別展覽中展出,深化了觀眾對現代大熊貓的前身古熊貓的全面認知,為古熊貓科普文化知識的傳播作出了一定貢獻。本文在導師周宗凱的科研影響下,以古熊貓作為動物代表,探究高仿真創意標本的開發方式,探索古動物資源在文博產業中新的建構方式和路徑,并對動物寫實形態的創意開發做出實驗性嘗試。
1.1 古熊貓高仿真標本技術及特點
古熊貓高仿真標本制作遴選古熊貓家族成員中始熊貓和小種大熊貓為試驗對象,對古熊貓的形態特征、骨骼、解剖形態和生理習性等進行分析、歸納、提煉、總結,采用3D掃描技術、數字藝術、3D打印技術和手工制作四個環節實施其制作過程,使用3D掃描設備采集古熊貓化石數據生成立體模型,將模型數據置入Maya軟件中作為結構和數據準確參考,再借用Maya的建模功能對無法掃描的熊貓外形進行多邊形建模,使用Maya虛擬骨骼綁定功能實現熊貓各種動態的樣式;制作完成的古熊貓虛擬形態借用3D打印設備制作出實體標本的底膜,底膜基礎上使用高仿真材料制作熊貓毛皮、爪牙、眼球及花紋等外表高逼真形態,所以古熊貓高仿真標本技術工藝具有科學性、嚴謹性的特點。
古熊貓使用數字藝術的原理主要是在古生物學的理論基礎上,借用藝用解剖學和藝術造型規律,該理論可以解決科研人員提煉脊椎動物骨骼共性形態規律,數字藝術依據動物骨骼和肌肉的結構原理,結合古熊貓化石尺寸和立體造型,分析古熊貓脊椎、四肢骨骼、頭骨解剖的結構形態;在骨架建構的基礎上,結合熊貓的解剖結構圖,厘清肌肉形態,肌肉與骨骼的連接方式,以及由骨骼和肌肉引起的熊貓身體表皮的起伏形態;以3D掃描采集準確化石形態的立體數據,結合Maya軟件的建模功能,采用與文獻資料和現生大熊貓的體形和骨骼尺寸的數據、形態和骨骼圖片進行比較實驗,對殘缺的化石形態進行修復或者仿真標本的制作,對于無法采集的形態資源,則借助動物藝用解剖的造型規律進行推衍,尤其適合解決由于古動物化石等科研資料欠缺而無法做出合理推理的問題,以及解決古動物外形復原的開發問題。
古熊貓數字模型動態的塑造原理主要借助動畫學科的運動規律理論,該理論涉及脊椎動物的共性運動方式、曲線規律、重量感和節奏規律、形態變形原理,動作的跟隨與滯后現象,骨骼與肌肉的聯動關系等,將這些規律應用于古熊貓的肢體動作調整過程中,再結合現代熊貓的影像視頻參考,可還原古熊貓走路、跑步、攀爬、摔跤、進食等各種生動的動態。
1.2 高仿真標本技術的擴展應用
古熊貓作為四足動物的代表動物之一,在頭頸、胸腔、軀干及四肢方面與其他四足動物結構組合方式相似,所以高仿真標本制作技術可普遍應用于四足動物的標本制作。在高仿真動物標本制作中的3D數字技術結合藝用解剖學可建構準確的動物外形,利用動畫功能調整各種生動的動態,可在軟件環境中增設藝術創意,創意主題設置的自由度較大,可圍繞動物生命進化、動物生活習性、動物生存現狀等多種主題展開,可極大地豐富文博標本展示的主題內容,開發成為高仿真創意標本。高仿真創意標本促使標本由科普展示、科研使用功能擴展到大眾文創的消費領域。
高仿真標本技術不僅用于動物外形的高逼真復原,也可以用于動物的內臟、骨骼等解剖結構的塑造,并服務于生物學教學。隨著3D打印材料的不斷更新,動物不同質地的仿真材料發明促進標本的仿真度的提升,其質感和效果接近動物真實的材質。
動物高仿真標本與動物真體標本兩者相似之處在于均具有逼真準確的造型特點,但高仿真標本并非使用動物真體,所以不具有動物學的鑒定和考證價值,兩者主要用途不同。高仿真標本相當于動物標本形態的替代品,其外觀形態具有科學性和嚴謹性的特點,所以可用于外觀的展覽和教育普及。
1.3 高仿真標本技術與“標本剝制術”的比較
高仿真標本技術可擴展應用到傳統的標本制作工藝中。動物傳統標本制作工藝主要采用“標本剝制術”,“標本剝制術”需對動物進行真體剝皮、皮張處理、假體制作并填充、熏蒸等環節的處理,對動物身體皮毛切開剝皮,皮張處理環節需要掏空內臟、肌肉后進行防腐處理,假體制作使用填充物使標本飽滿,熏蒸則為標本防潮、防干裂、防蟲等起到保護作用,讓標本經久耐用,高仿真標本制作技術可用于“標本剝制術”的假體制作環節中,省去了填充物的制作,使用3D打印的動物模型底膜替代假體的基本造型,供后面的套用皮毛使用。“標本剝制術”只能應用于有動物真皮現存情況下動物標本的制作,而高仿真標本技術解決沒有生命遺存的古動物或瀕危動物的標本制作問題,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對動物資源的消耗,間接保護了動物資源。
高仿真創意標本資源彌補了動物真體標本的缺陷,兼具文創特性。動物真體標本常以站、蹲、走等動態類型為主,動態形式單一,動物皮毛內填充物質地較軟,常導致形態太過圓潤和身體填充不飽滿等問題,所以表現動物標本準確的形態特征方面有一定的損失。高仿真創意標本采用3D打印技術,而使用硬質材料或柔韌性的材料,保證身體形態準確而飽滿,高仿真標本采用數字藝術方式開發的寫實文創標本產品,寫實標本外形保證了與真實動物高度相似性。
2 文博創意標本資源建構的新方式
2.1 文博展館需求高仿真標本展品
當前自然博物館動物標本資源的展示內容,主要以化石標本和動物真體標本展示為主,化石標本雖然具有極高的科考研究價值,但動物的體態和樣態不夠直觀,影響觀賞體驗度和科普宣傳效果。動物高仿真標本解決絕滅動物和瀕危動物的標本制作,成為有效的解決方案,可有效填補絕滅動物和瀕危動物的文博展品資源。高仿真標本使用高仿真材料,并非動物真體本身,在物理和化學成分上不具有科考價值,但在外形特征上,因經過科學嚴謹的形態復原過程,可呈現動物準確外貌和特點,具備文博展品的文化價值和科普價值。
2.2 文博創意標本資源建構的技術路徑
(1)高仿真標本一體化工藝手段的應用。現代模型技術與材料廣泛用于考古、仿古研究與展覽[2],高仿真標本一體化工藝手段,以3D掃描、數字藝術、3D打印和人工仿制四個環節順次進行,分別解決數字模型的精準采集、高逼真形態的塑造、虛擬形態的實體模型轉化、高逼真材質等四個問題,將四個開發環節一體化運用,成為文博創意標本資源的建構方式。數字藝術可進行創意主題的設計,如動物進食、追跑、打鬧,甚至群體遷徙等,成為博物館開發系列化、體系化的文博標本展品和創意標本文創產品的有效技術路徑。
(2)文博創意標本的批量化開發與生產。數字藝術創建的虛擬資源具有可復制、易傳播、便捷使用的特點。3D打印技術手段對虛擬資源采用實體產品一體化工藝,推動批量化開發和生產得以實施,并可保證標本模型形體的一致性,依據動物身體各部位的質地特征選擇不同硬度、柔韌性、質感及色澤的最佳材料,完成動物身體模型的批量開發,為人工仿制表層質地做好鋪墊工作。
(3)動物高仿真材料的應用。主要用來處理動物頭部、腳部、四肢等身體表層的部位,動物高仿真材料替換動物真體材料,選用動物身體、眼睛、爪牙、皮毛高逼真現成材料,在3D打印模型外形的基礎上,按照動物真實的生長規律和毛發圖案規律,兼顧動物的動態和體態特征,采用人工手工精細處理的方式,塑造標本表層高逼真、高相似度的外表面形態。
2.3 文博創意標本資源建構的價值和意義
為動物真體標本尋求新的替代品。“文創產品作為博物館藏品的替代物,一定程度上發揮著展品的功能”[3],“文創產品所呈現出來的原創原真性、獨特原真性”[4],動物真體標本滿足文博展陳的功能和日常消費,則必須尋求替代品,同時延續標本的特質,并突破動物真體標本不可復制、唯一性的資源特殊性,高仿真標本以寫實和逼真的形態繼承了標本真實的外形特征,借用高仿真材料替換動物真體,擴展標本的用途,可以作為有效的解決途徑。
采用高仿真標本技術探索文博標本資源的創新路徑。文博資源不僅要走出博物館,而且要市場化,文博自然資源和文物資源唯一性和不可復制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資源商品化和市場化。高仿真標本技術為博物館自然資源中動物資源的開發,提供了新的技術路徑。
高仿真標本豐富了文博展品資源。增加了絕滅動物和瀕危動物高仿真標本等展品資源,高仿真標本批量化資源的供應,有利于改變各地館藏文博資源不易共享使用的現狀,高仿真創意標本資源則是文博文創展陳的組成部分,可提高展品存儲量,豐富展品的內容和種類。
本文著重探討了文博創意標本的建構方式,聚焦于動物高仿真創意標本的建構方式,探究文博資源開發和文博文創產品走入市場的技術方式。數字藝術與3D打印技術結合使用,具有極強的科研、創意開發、產品生產的自由度,在考古文物創意資源開發方面應用潛力巨大。因為考古文創開發與動物創意標本開發中開發對象的屬性和技術工藝不完全相同,所以沒有在此方面進行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