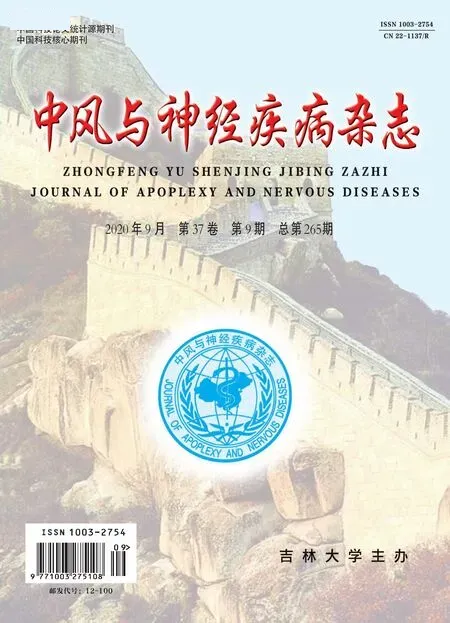非手術(shù)中青年腦出血患者預(yù)后影響因素研究進(jìn)展
張 欣, 呂曉民, 魯瑩雪, 李萌萌綜述, 呂 洋審校
腦出血是指非創(chuàng)傷性原發(fā)性的腦實質(zhì)內(nèi)出血,占卒中總?cè)藬?shù)的20%,其具有發(fā)病率高、病死率高、致殘率高及復(fù)發(fā)率高等特點,嚴(yán)重危害人類的生命健康[1]。最新數(shù)據(jù)表明,人群中腦出血的發(fā)病率為12~15/10萬人年,3 m內(nèi)的死亡率為20%~30%[2,3],超過70%的患者早期出現(xiàn)血腫擴(kuò)大或累及腦室,青年腦出血占10%~15%[4,5],同時,中青年腦出血患者的預(yù)后直接影響到患者的生活質(zhì)量及社會經(jīng)濟(jì)負(fù)擔(dān)[6],2003年我國統(tǒng)計腦出血的直接醫(yī)療費用為137.2億/y[7],研究表明,血壓、血糖、早期意識及出血的部位、出血量等因素可導(dǎo)致病情惡化或預(yù)后不良。因此,早期認(rèn)識并及時干預(yù)中青年腦出血患者的預(yù)后影響因素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綜上,本文將對中青年腦出血患者預(yù)后影響因素,包括臨床、實驗室及影像學(xué)指標(biāo)進(jìn)行綜述。
1 臨床表現(xiàn)
相對于老年患者,中青年的病因及臨床表現(xiàn)有所不同,相對于老年患者,中青年腦出血患者的危險因素通常是由結(jié)構(gòu)損傷或高血壓引起的,而關(guān)于中青年患者的臨床表現(xiàn)仍有部分爭議。LoesCA調(diào)查了1980年至2010年間,當(dāng)?shù)蒯t(yī)院98例18~50歲的ICH患者[8]。常見癥狀為劇烈頭痛(70例,71.4%),惡心(32例,32.7%),意識障礙(64例,65.3%),病死率20.4%(n=20)。Koivunen回顧性分析2000至2010年間336例青年腦出血患者,并與老年患者進(jìn)行比較[9]。他們發(fā)現(xiàn)最常見的癥狀包括:運動性偏癱[n=189(56.3%)],頭痛[n=164(48.8%)]和惡心[n=120(35.7%)],3 m死亡率為17%。Bernardo回顧性地選擇了161例65歲以下的ICH患者,記錄了2002年至2018年間的住院死亡率以及成人出院后的死亡率和復(fù)發(fā)性中風(fēng)[10],結(jié)果顯示14.9%的患者死于醫(yī)院,5 y生存率為92.0%,10 y生存率為78.1%,15 y生存率為62.0%。最近,Sanne對15527例患者進(jìn)行了回顧性分析[11],發(fā)現(xiàn)1776例患者在中風(fēng)后30 d內(nèi)死亡,1764例患者(23.2%)在9.3 y的隨訪中死亡,17.0%在15 y內(nèi)死亡。
2 臨床指標(biāo)與預(yù)后
2.1 意識障礙 意識水平是血腫擴(kuò)大的預(yù)測指標(biāo),當(dāng)血腫擴(kuò)大侵及大腦上行網(wǎng)狀激活系統(tǒng)及大腦皮質(zhì)時,患者出現(xiàn)意識障礙。美國國立衛(wèi)生研究院卒中量表評分(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和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lasgow coma scale,GCS)是反應(yīng)患者的嚴(yán)重程度的重要參考依據(jù)[12]。NIHSS是一個綜合的卒中量表,共15項,由Thmos等于1989年設(shè)計[13]。用于急性腦卒中的治療研究。該量表主要用于評價腦卒中患者的神經(jīng)功能損害程度[9]。近期Broderick等[14]總結(jié)了從2011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的86例腦出血患者的臨床數(shù)據(jù),患者年齡為18~45歲的中青年,采用卡方檢驗評估腦出血評分與預(yù)后的關(guān)系,結(jié)果顯示患者NIHSS評分與患者預(yù)后呈負(fù)相關(guān)性。2018年中國的周紅霞教授[15]團(tuán)隊回顧性分析2005年6月至2015年6月天津環(huán)湖醫(yī)院收治的196例中青年腦出血患者入院后30 d內(nèi)的臨床資料,單因素回歸分析發(fā)現(xiàn)GCS、NIHSS的分?jǐn)?shù)與腦出血患者早期死亡呈負(fù)相關(guān)。2019年趙小景研究團(tuán)隊[16]對189例入院24 h的急性中青年腦出血患者分別進(jìn)行NIHSS評分,通過 ROC曲線下面積來評估預(yù)后,結(jié)果發(fā)現(xiàn) ROC曲線下面積為0.845,分度值分別為17,預(yù)測準(zhǔn)確率為79.9%,提示NIHSS評分對急性腦出血患者的短期預(yù)后有較好的預(yù)測價值。綜上,現(xiàn)有的研究結(jié)果顯示,腦血管患者入院NIHSS評分及CGS評分的高低是反映患者預(yù)后不良的重要因素,但目前的臨床研究數(shù)量較少,對預(yù)后的具體影響程度仍需進(jìn)一步研究。
2.2 血壓 原發(fā)性腦出血急性期血壓管理存在保守和積極兩種方案,目前多數(shù)學(xué)者認(rèn)為人院時高血壓與腦出血患者的不良預(yù)后呈正相關(guān),因為早期血壓控制尤其是收縮壓的控制可預(yù)防血腫的進(jìn)一步擴(kuò)大[17,18]。2017年Aigner等[19]收集了2007年至2010年26個臨床卒中中心的2125例年齡在18~55歲之間的腦出血患者,計算8個危險因素包括高血壓對原發(fā)性腦出血的預(yù)后影響,結(jié)果發(fā)現(xiàn)高血壓是腦卒中的主要危險因素,占27.1%。2018年Mustanoja等[20]評估334例50歲以下首次非創(chuàng)傷性急性腦出血患者血壓與死亡率之間的關(guān)系。結(jié)果發(fā)現(xiàn)SBP≥160 mmHg患者的死亡率顯著高于對照組。2019年Bernardo等[10]回顧性分析從1997年至2018年65歲以下的腦出血患者的臨床資料,結(jié)果發(fā)現(xiàn)血壓升高是腦出血后長期死亡率的獨立預(yù)測因素。雖然現(xiàn)有研究均表明降壓可以改善中青年腦出血的預(yù)后,但是相關(guān)的臨床研究數(shù)量較少,在不限制年齡的部分研究認(rèn)為二者無絕對關(guān)系,并且認(rèn)為早期降壓并不能改善患者的病死率,因此,早期血壓與血腫擴(kuò)大及預(yù)后間的關(guān)系仍需要進(jìn)一步探索。
2.3 血糖 目前研究腦出血患者血糖升高使血腫擴(kuò)大,導(dǎo)致死亡率升高,但同時50%以上的患者伴有高血糖[20]。2015年Koga等[21]認(rèn)為短暫性血糖升高是因腦出血導(dǎo)致的應(yīng)激反應(yīng),高血糖可引起酸中毒、炎性細(xì)胞因子釋放和自由基形成,增加血腦屏障的通透性和完整性,可導(dǎo)致活動性出血加重。2015年Koivunen等[22]人回顧分析了2000年1月至2010年3月16至49歲腦出血患者的臨床資料,結(jié)果發(fā)現(xiàn)高血糖是腦出血患者3 m死亡率的相關(guān)因素。2019年Bernardo等[10]回顧性分析從1997年至2018年65歲以下的腦出血患者的臨床資料中同樣發(fā)現(xiàn),血糖升高是腦出血后長期死亡率的獨立預(yù)測因素。2018年中國的周紅霞教授[15]團(tuán)隊回顧性分析2005年6月至2015年6月天津環(huán)湖醫(yī)院收治的196例中青年腦出血患者入院后30 d內(nèi)的臨床資料,采用Cox風(fēng)險回歸模型進(jìn)行單變量和多變量分析發(fā)現(xiàn)血糖對中青年腦出血預(yù)后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但是,部分不限制年齡的研究表明,臨床過度控制血糖也可能增加危重患者的死亡率[23]。因此,關(guān)于血糖水平對于中青年腦出血患者的預(yù)后仍需進(jìn)一步研究。
3 影像學(xué)指標(biāo)與預(yù)后
3.1 基線腦出血量 腦出血量與病后死亡率呈顯著相關(guān),有研究表明,超過30 ml的血腫擴(kuò)大的可能性明顯高于出血量較少(10 ml)出血的可能性[24]。同時,研究表明,較大基線出血量造成外周血管二次機(jī)械剪切,即血腫牽拉周圍組織,致周圍微小血管破裂進(jìn)一步誘發(fā)活動性出血[25]。2014年趙衛(wèi)麗[26]回顧性分析了90例中青年高血壓性腦出血患者的臨床資料、影像學(xué)表現(xiàn)及預(yù)后,結(jié)果發(fā)現(xiàn)不同出血量導(dǎo)致死亡率的差異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出血量≤30 ml病死率9.6%,出血量≥80 ml病死率80%,出血量較大的病死風(fēng)險明顯高于出血量較小的患者。中線移位程度與患者病死率有顯著差異,中線無移位的患者病死率為2.63%,中線位移>10 mm者病死率高達(dá)85.7%。綜上,較大出血量可導(dǎo)致腦出血患者較差的預(yù)后。
3.2 血腫形態(tài)和密度 根據(jù)血腫形狀和密度可以預(yù)測血腫是否擴(kuò)大。Fujii等[27]認(rèn)為血腫形狀不規(guī)則由多個病灶所致,易導(dǎo)致活動性出血。Barras等[28]將血腫形態(tài)分為5型,并認(rèn)為血腫形態(tài)越不規(guī)則,其血腫擴(kuò)大風(fēng)險越高。早期Fujii[27]回顧性分析627例腦出血患者發(fā)病后24 h內(nèi)入院的臨床資料。入院時進(jìn)行第1次CT檢查,入院后24 h內(nèi)進(jìn)行第2次CT檢查。采用單因素及多因素分許評估多個臨床指標(biāo),結(jié)果發(fā)現(xiàn)血腫形狀不規(guī)則可增加血腫增大的可能性。一些特定的影像學(xué)征象可有效預(yù)測血腫的增大可能性,CT顯示血腫密度不均勻表示有新鮮出血,2007年Wada等[29]提出CTA斑點征,是血腫擴(kuò)大和預(yù)后不良的影像學(xué)特征,為CT對比劑外滲所致,提示病灶部位有活動性出血或破裂血管再出血,其預(yù)測血腫擴(kuò)大的敏感度為51%~98%,特異度為50%~89%。后續(xù)黑洞征被提出,黑洞征表現(xiàn)為在平掃CT血腫內(nèi)相對高密度區(qū)域包裹相對低密度區(qū)域所致,研究[30,31]表明黑洞征與血腫擴(kuò)大相關(guān),其預(yù)測血腫擴(kuò)大的敏感度為43.8%,特異度為84.54%,陽性預(yù)測值和陰性預(yù)測值分別為48.28%和82.00%。雖然血腫的形狀和密度可預(yù)測血腫的預(yù)后,但是大部分研究并無年齡限制,因此,對于中青年的血腫形態(tài)對于預(yù)后的影響仍需進(jìn)一步研究。
3.3 出血部位 腦內(nèi)的不同結(jié)構(gòu)具有不同功能,因此,出血部位可影響腦出血的預(yù)后。腦室內(nèi)出血(intraventricular haemorrhage,IVH)時,預(yù)后較差的風(fēng)險較高,研究表明IVH患者的白細(xì)胞計數(shù)、凝血酶復(fù)合物、纖溶蛋白酶原復(fù)合物和D-二聚體水平較高,表明其處于纖溶系統(tǒng)應(yīng)激狀態(tài),可導(dǎo)致血腦屏障破壞及血管完整性而導(dǎo)致再出血[32]。2018年中國的周紅霞教授[15]團(tuán)隊同樣分析了出血部位與中青年患者預(yù)后的關(guān)系,研究結(jié)果表明,在腦出血早期出現(xiàn)幕下出血和腦室擴(kuò)大可導(dǎo)致中青年腦出血患者死亡風(fēng)險增加。部分無年齡限制的臨床研究中顯示腦室出血與預(yù)后不良相關(guān),但是少量出血并無影響[33,34],因此,關(guān)于出血部位對預(yù)后的影響程度尚無定論,并且中青年患者的臨床研究較少,因此,仍需進(jìn)一步的臨床研究。
4 實驗室指標(biāo)與預(yù)后
4.1 凝血功能異常 凝血功能可直接影響血腫是否擴(kuò)大,研究表明纖維蛋白原、D-二聚體、血小板水平是血腫擴(kuò)大的預(yù)測因子,其中纖維蛋白原、D-二聚體與血腫擴(kuò)大呈正相關(guān),血小板與血腫擴(kuò)大呈負(fù)相關(guān)[35]。一項收集251例患者臨床資料的回顧性研究[36]表明,抗血小板治療是血腫擴(kuò)大的獨立危險因素,因此,凝血功能影響患者的預(yù)后,糾正凝血障礙是臨床干預(yù)的方向。
4.2 炎癥因子 炎癥反應(yīng)參與腦出血后腦損傷的病理生理過程,炎癥標(biāo)志物如白細(xì)胞計數(shù)、白細(xì)胞介素-6、C-反應(yīng)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等與血腫擴(kuò)大相關(guān)。研究發(fā)現(xiàn)[37]通過患者CTA影像學(xué)成像統(tǒng)計后發(fā)現(xiàn),CRP>10 mg/L導(dǎo)致腦出血患者血腫擴(kuò)大的風(fēng)險更高。此外,炎癥反應(yīng)會破壞凝血功能和血管壁完整性,從而增加活動性出血的風(fēng)險[38]。
4.3 免疫因子 免疫因子在腦出血發(fā)生發(fā)展過程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生理條件下,巨噬細(xì)胞移動抑制因子( Macrophage mobility inhibitor,MIF)在神經(jīng)細(xì)胞、腦脊液和血中表達(dá)穩(wěn)定,腦出血時,MIF表達(dá)失調(diào),血中含量發(fā)生明顯變化[39]。高遷移率蛋白-1(high mobility group box-1,HMGB-1) 是一種炎性介質(zhì),在患者組織損傷及修復(fù)過程中具有放大炎癥反應(yīng)的作用,不僅對多種疾病的發(fā)生抑制,且對外界刺激的敏感性低,穩(wěn)定性強(qiáng)。近年來,在腦血管疾病中,組織基質(zhì)金屬蛋白酶抑制劑-1(tissue inhibitor of metalloproteinase,TIMP-1)受到越來越多的學(xué)者關(guān)注[40]。
5 其他因素
5.1 種族 不同人群地遺傳異質(zhì)性較大,可能直接影響腦出血患者地預(yù)后。2020年5月Miyares等[41]將登記的418例年齡<50歲腦出血患者進(jìn)行研究,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確定與不良結(jié)局相關(guān)的因素,并按種族/民族進(jìn)行分析,以確定這些組之間的差異。418例患者中,其中48例(12%)為白人,173例(41%)為黑人,197例(47%)為西班牙裔。對于幕上腦出血患者,黑人患者(OR,0.42)和西班牙患者(OR,0.34;P=0.01)在調(diào)整后或其他與預(yù)后不良相關(guān)的因素后,其預(yù)后優(yōu)于白人參與者。
5.2 遺傳因素 有特定基因突變的青年腦出血患者,復(fù)發(fā)率高于普通人群,并且遺傳因素對年輕患者的影響更大。如COL4A1 基因突變患者在運動時極易發(fā)生腦出血,患者常表現(xiàn)為反復(fù)腦出血。因為COL4A1編碼蛋白質(zhì)是許多組織基底膜的主要成分。Meuwissen等[42]在2005年至2013年間,對183例青年腦出血患者的COL4A1和COL4A2進(jìn)行了診斷性DNA分析。共檢測到21個COL4A1和3個COL4A2突變,新突變率高達(dá)40%。此外,APOE、KRIT1、CCM2、PDCD10、APP40、KRIT1、CCM2和PDCD10等基因突變均有可能影響青年出血患者的預(yù)后[43]。
5.3 性別 相對于男性,女性有更好的生活習(xí)慣及較少的危險因素,同時,中青年女性雌激素可通過與血管壁雌激素受體結(jié)合,發(fā)揮其特有的生物效應(yīng),從而抑制血管平滑肌細(xì)胞的增殖和移行,從而對血管起保護(hù)作用[44]。目前的研究尚未發(fā)現(xiàn)性別對預(yù)后的影響,但相關(guān)臨床研究少,仍需進(jìn)一步研究。
綜上所述,腦出血是一種神經(jīng)內(nèi)科常見病,而年輕人群患病率正在上升,年輕的腦出血患者的預(yù)后直接影響家庭及社會。血壓、血糖、意識、出血量、出血部位、血腫形狀及密度、炎癥因子、凝血功能、種族、性別及遺傳因素均有可能影響中青年患者的預(yù)后,但相關(guān)研究仍較少,對于預(yù)后影響因素的了解及控制十分重要,希望今后能有針對年輕人預(yù)后更多的臨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