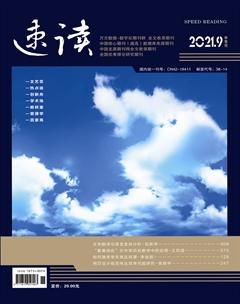小學體育高效教學的應用策略分析
王梅
◆摘? 要:在小學體育教學過程當中,應用高效教學的策略大致可以合理分組、教師參與、反饋評價等環節展開,從而促進學生互動合作、師生感情交流以及教學的完善與改進。教師要時刻注意好把握學生的心態,觀察好學生的一舉一動,從而使得自身的教學更加貼合學生的需求。由于種種原因,小學體育可能會被學生誤解為“自由活動課”,對課堂體系和教師的要求采取漠視的態度,因此。教師要想方設法地引起學生對于體育課堂的重視,這樣才能夠既教給學生基本的知識,又讓學生學到體育技能,從而讓學生養成鍛煉身體的好習慣,培養學生的體育意識。
◆關鍵詞:小學體育;高效教學;應用策略
一、進行合理分組 促進學生互動合作
分組教學是一種高效的學習方式,教師通過分析學生的性格、成績、興趣、能力等方面的因素給學生設置合理的分組,并且指定其中的一人當作小組長,讓小組長帶領成員在教師的指導下進行學習交流。學習小組在課堂討論環節有著重要的意義,能夠促進學生查缺補漏,讓優等生帶動學困生進行學習,增進學習氛圍。同樣的,分組教學的策略也能使用在體育教學中,教師可以通過構建興趣小組、任務小組等方式來促進學生的學習。否則,體育課堂很容易出現混亂的狀況,學生不聽教師的指導,只顧自娛自樂。在學習體育理論知識時,小組合作的方式能夠幫助學生分析一些簡單的問題,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提高,在學習體育動作要領或參與體育活動時,小組內的同學也可以互幫互助,促進彼此對體育動作要領的掌握。體育課堂也同樣需要強調紀律的重要性,合作學習的方式可以從一定程度上避免學生個人學習容易出現的注意力不集中、開小差等問題。在實際教學過程中,教師可以提前收集好學生的課堂建議,總結出學生的需求,然后對學生進行興趣分組、任務分組。例如,教師可以讓體育委員以匿名的形式收集全班同學的意見,以此來了解學生不同的愛好,然后為學生定制教學計劃,再根據學生的意見進行分組。在小組學習過程中,教師要首先強調好紀律,制定好小組長,強化學生的規范意識。
二、設計體育游戲 提高學生興趣
符合學生特點的教學設計才是最有效的,更能促進教學目標的達成,小學階段的體育教學不僅僅要求教師將體育知識講解給學生,最重要的是提高學生參與體育活動的熱情,培養學生良好的體育活動習慣,從而達到提高學生身體素質的目的。考慮到小學生對趣味性內容比較感興趣的性格特征以及學生經常參與游戲的實際情況,教師可以使體育活動與游戲相融合,使體育活動具備游戲化的特征,更加符合小學生的興趣特點。
三、通過教師參與其中 增進師生感情交流
在小學體育教學中,教師絕對是必不可少的一環,不僅僅起著引導學生的作用,還扮演著“家長”“朋友”等角色,在學生的身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小學生往往比較喜歡結伴,他們渴望得到他人的認可,也喜歡與他人分享心得。教師作為學生在學校中的“家長”,也作為學生日常生活中的“朋友”,扮演著一種亦師亦友的角色,這些復雜的角色叢需要教師本身有過硬的本領和素質才能掌控得住。因此,一方面,教師要利用一切機會加強學習,參與教研培訓,增強自身教學素質,另一方面,教師需要親身參與到學生的活動當中,以此拉近師生距離,當學生放下對教師的戒備心理后,不僅會與教師坦誠交流,學習效果也會更好。體育教學涉及眾多的體育活動,與其他文化科目相比,更有助于教師與學生進行互動,教師可以經常與學生合作完成具體的課堂活動。
四、組織體育競賽 調動學生參與的積極性
學生參與體育活動的積極性會影響學生的具體表現,進而對學生參與體育活動的效果產生影響。高效的體育教學要求學生能夠在參與體育活動的過程中,對有關活動技巧和方法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同時能夠通過參與活動提高自身的身體素質。為了調動學生的參與積極性,教師可以組織學生進行體育競賽,將學生完成簡單、反復練習的過程轉化為競賽的方式。體育競賽主要是引導學生按照不同的分組,根據競賽的要求和規則,完成具體的體育活動,與平時的練習相比,競賽具有競爭性的特點,更能激發學生的熱情和積極性。由于大部分比賽都是合作的方式,對學生合作意識的提升也有一定的幫助,也符合小學生喜歡與其他同學結伴游戲的特點。
五、收集反饋評價 促進教學的完善及改進
眾所周知,在教師完成教學任務以后,還需要不斷地進行教學反思,以此促進教學改進與完善。雖然在日常的教學中,學校會安排一些講評課、活動課,收集到了一定教職人員的反饋與評價,但是來自學生的評價仍然不可忽視。因為教師面對的主體是學生,只有充分地了解了學生的需求,才能股更好地改善教學計劃,促進教學實施。如果教師忽視了學生的評價,學生內心的需求得不到響應,長此以往就會對教師產生不滿,并且不配合教師的教學工作。因此,教師有必要隨時注意傾聽學生的心聲,及時得到學生的反饋,使自身的教學安排更加貼合實際,從而促進教學相長。
六、結束語
綜上所述,體育教學主要以多種多樣的活動形式為主,從而增添課堂的趣味,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值得注意的是,小學生天性活潑好動,體育課堂能讓他們擺脫一定的束縛,自由自在地學習和娛樂,在全新的學習環境當中,學生也能夠更加積極主動地配合老師的工作。體育課堂大多以戶外課堂為主,教給學生基礎的體育知識和技能,這種上課形式本身就對學生帶有一定的吸引力,因此,教師要把握好機會,在小學體育教學中開展高效教學,達成寓教于樂的效果。
參考文獻
[1]謝燕.構建小學體育高效課堂的策略探析[J].新智慧,2021(03):85-86.
[2]姜華靜.高效課堂構建視域下的小學體育教學策略[J].啟迪與智慧(中),2020(11):61.
[3]陳繼偉.如何構建一個高效小學體育課堂[J].小學生(下旬刊),2020(0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