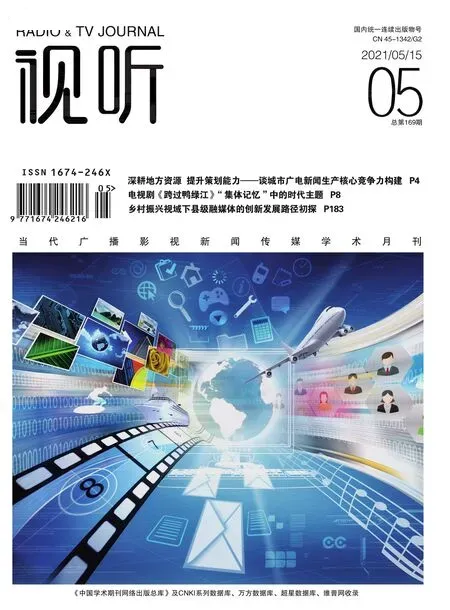無濾鏡美顏的突圍:短視頻視覺消費語境下的狂歡與凝視——基于對“丁真的世界”走紅的探討
□ 易云梅
2021年2月9日,丁真在其微博社交平臺上發布新歌《1376心想事成》,迅速登上微博熱搜榜。在2020年11月,來自四川省甘孜州理塘縣的藏族男孩丁真無意間被攝影師胡波拍攝下來,關于他的一條不到10秒的抖音短視頻吸引了巨大關注。這個沒上過幾天學,漢語說得結結巴巴,不會寫字的康巴漢子,因為純真的笑容被廣大網友奉上“甜野男孩”的昵稱,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迅速走紅,關于他的話題屢屢登上微博熱搜。他的走紅甚至吸引了日本媒體的關注與報道,日本朝日電視臺以“因為太帥成為地方觀光大使,在社交網絡上人氣爆棚的19歲少年”為主題,報道了丁真意外走紅的過程。
一、身體消費:田園牧歌下的“甜野男孩”
作為“理塘縣旅游大使”,丁真在微博上引發了四川日報、西藏日報等官微之間的“爭斗”(battle),以及包括山東、陜西、青海、云南、湖北、遼寧、江蘇等多地官微和媒體的“邀請丁真來我家鄉”的搶人大戰。外交部新聞司司長華春瑩甚至還在推特上介紹了他:“一張燦爛、陽光、天真的微笑照片在網上走紅后,丁真最近成為了社交媒體上的明星。”
(一)稀缺審美渴求:原生態的清澈少年
在消費主義大潮中,人體借助大眾傳媒的崛起成為當代重要的審美對象并形成身體景觀。丁真絕美的臉部輪廓和健朗的身材滿足了網民對超越磨皮的美顏的渴求。
2020年11月11日,在一個不足10秒卻火爆了全網的短視頻中,一個身穿民族服飾的大男孩在鏡頭面前露出羞澀的笑容,在視頻的彈幕和評論區里爆發了對丁真原生態顏值的贊嘆。評論區的驚訝和贊美,反映出人們對于無濾鏡呈現出的這種稀缺性的審美渴求以及完全不同于精修磨皮的身體美學主張。不斷迭代的“會拍照”的手機對于前后置攝像頭、超高清人像像素等的不斷升級,市面上各種經過算法精心調制角度的“美顏相機”App的普及,技術不斷打破對現實的再現,侵入了日常的審美領域,改變著人們的生活行為和交流方式。原生態清澈少年丁真的突圍,無疑是對規范化的濾鏡審美體系的突破,滿足了用戶對真實呈現的渴求。
法國哲學家保羅·維利里奧在《視覺機器》中提出了圖像演進的三層邏輯,即圖像的形式邏輯時代、辯證邏輯時代和反邏輯時代(保羅·維利里奧,2014)。而丁真之所以受到廣泛的關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的身體并非由技術和機器所制造和雕飾。他是真實的、可觸摸的存在,而非維利里奧所言的“刻寫的、再現的存在”。因此,丁真的短視頻迅速地被截圖、保存、實現了爆炸性的網絡傳播。
(二)市場化的身體:異質特性迎合消費邏輯
在消費主義時代,身體成為消費的對象,成為“心理所擁有的、操縱的、消費的那些物品中最美麗的一個”(讓·鮑德里亞,2001)。短視頻中的丁真有著黝黑的臉龐和獨特的民族服飾,一方面向人們展示了康藏高原的淳樸民風,另一方面也給觀看者提供了不同于城市規律的別樣景觀。丁真厚重的黑頭發,長期接受日照的具有紋理的臉龐,有些干裂但又始終保持微笑的嘴唇,都與城市廣告里的男主角白皙的臉龐、整潔的衣冠有著本質區別。
丁真身上異質的特性也在迎合市場消費的邏輯。平臺通過推薦機制將丁真這樣的異質性身體作為模板,讓其他人知道這種身體也可以成為頂流,進而引發人們對這種獨特性和異質性身體的模仿和再造。丁真的微博有著148萬的粉絲,他的稀缺性和不同于其他網紅的異質性實現了流量上的突圍。
二、凝視與反凝視:顏值何以為正義
在虎撲的論壇上,曾發起過一個話題為“你覺得丁真有你帥嗎?”的投票,最后有63%的投票網友覺得自己比丁真帥,不少網友們還借此曬起了自拍。網友們對丁真的討論并沒有停止,部分網友對丁真現象的恨與嘲諷也在網絡世界中不斷迭代。只要在百度的搜索框內輸入“我覺得他的眼神很純真,有一種野性的美感”,就會出現無數與丁真相關的“惡作劇”截圖。除了截圖、語言的戲謔外,還有不少侮辱性的評論。
(一)前所未有的“女性凝視”
“男性氣質從不存在于一種單純的狀態之中,而是多層情感共存并相互矛盾的,男性氣質中必然包含了女性氣質”(R.W.康奈爾,2003)。丁真在被媒體和大部分女性正面贊揚和肯定的同時,也成了新一代男性的公敵。這背后包容著一種容貌的審判:在某些男性眼中,丁真單純靠“臉”出圈,火得沒有道理。從網絡投票到通過文字、圖片對丁真進行戲謔和負面侮辱,都在顯示著丁真終于引起了部分男性的容貌焦慮了。
當男性群體還沉迷在“白幼瘦”的統一標準時,突然發現女性對男性的審美不再停留在他們的想象中:她們不再需要所謂的英雄,不再仰仗強壯的臂彎,甚至不再期待家境富有。丁真打破了男性群體對女性“夢中情人”的認知。
一些網友甚至翻出當地的比美大賽,試圖“證明”他不符合康巴漢子的審美標準。他們認為正宗的康巴男人,外形彪悍、灑脫豪放,隨身攜帶著三件寶。而丁真于傳統的康巴男人而言,則顯得瘦弱青澀。網友們全然無視生活在高原的藏民特征,搬出陳舊的膚色歧視。在固化的男性視角中,沒人相信黑色是美的(black is beautiful),所以他們覺得丁真火得莫名其妙。顯而易見,“白”這一審美已經挾持了全世界,光是女性“膚白貌美”還不夠,男性也被期待白到發光。
丁真的出現讓部分男性感覺到了前所未有的“女性凝視”,這讓習慣處在自上而下的主視角的他們感到極度不適。
(二)由來已久的“男性凝視”
“我們所擁有的并加以思考的身體是我們歷史、文化記憶、政治經濟總的媒介”(約翰·奧尼爾,1999)。當下的男性對女性的凝視又是一種怎樣的視角呢?回想起“網紅臉”這個詞最初走紅,便是網絡上都長著大同小異的歐式大眼、高鼻梁的錐子臉。這種趨同的審美標準,也促成了美的“修正史”,從線上P圖到線下整容,模板式的美似乎可以被輕易塑造。而終歸到底的受益人,就是讓審美走向狹隘之道的凝視者。
“我們尊敬另一位主體,并不是因為他有什么杰出品性,而是因為他存在著某種基礎性匱乏”,這個基礎性的匱乏便界定了他的存在(斯拉沃熱·齊澤克,2004:11)。值得慶幸的是,女性并沒有被時代的審美形態捆綁。在越來越多猛男熱衷于油頭粉面的時候,她們看到了丁真這種不一樣的美。她們為丁真造了一個新詞“甜野男孩”,說他“野性與純真并存”。這一種對純真的向往,可能與現代標準的審美無關,與網紅也無關。
三、個體編碼:鏡頭后的真實景觀
居伊·德波認為“景觀是宗教幻覺的物質重構,景觀技術并沒有驅散宗教的烏云”(居伊·德波,2017)。圍繞丁真的話題不僅僅只有對他所處環境的拍攝,還有對丁真本人生活資料的挖掘與披露。
(一)真實的景觀:日常生活的呈現
歐文·戈夫曼認為面具代表自我概念,“我們不斷努力地表現角色,這種面具就是更加真實的自我,即我們想要成為的自我”(歐文·戈夫曼,2016)。丁真褪下了常穿在鏡頭前的民族服飾,在自拍鏡頭面前比了一個中指,有的人則認為丁真也曾是“非主流男孩”。另外一個爭議是關于丁真抽煙的視頻廣泛流傳,視頻中丁真熟練地口吐煙圈引來了眾多網友的圍觀,認為丁真這樣的形象與之前淳樸的賽馬王子人設有些不符。
當丁真不再是視頻中那樣的美好、清澈和樸實后,鏡頭祛魅后的個體是否還值得推崇?無論是在視頻中豎立中指還是后來抽煙的行為,都可以算作是鏡頭后的真實的景觀。
(二)景觀的堆聚:忽略現實生活真相
對丁真身體的過度關注,以小見大地反映了數字化技術對人類精神世界的遮蔽。在視頻化的傳播過程中,我們尤能看到,網絡對貧困地區的絕美男孩健朗的身體和美顏的喜愛,和對丁真個人想法、精神世界及他所在地區發展的漠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人們熱衷于探討丁真雖布滿日曬痕跡和紋理的臉部器官、在鏡頭面前依舊“能打”且近乎“完美”的黝黑的身體皮膚,不斷地消費著絕美少年這一符號,而不在乎丁真這個人有著怎樣的精神世界,他貧困的家鄉該怎樣發展。盡管有微弱的聲音建議“丁真好好念書和好好學漢語”,但在微博和直播平臺上,這樣微弱的聲音幾乎是零分貝的存在,被“丁真真帥”“丁真做我老公吧”“丁真絕美”這樣的話語所淹沒。
四、結語
丁真的意外走紅,引來了互聯網時代線上線下的一場視覺狂歡。丁真的“美”滿足了人們對于田園牧歌生活的想象,滿足了人們的稀缺審美,借助消費主義浪潮,成為了當代重要的審美對象并形成身體景觀。當“甜野男孩”開始突圍濾鏡美顏時,女性在這場狂歡中占據了主動權,男性容貌開始被討論和“凝視”。在這場對丁真身體的過度關注中,也以小見大地反映了數字化技術對人類精神世界的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