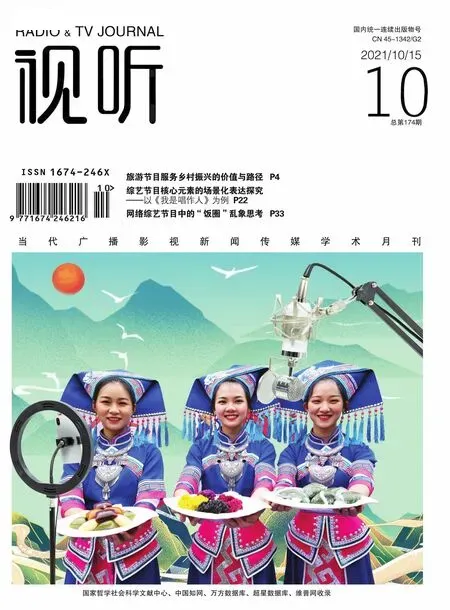方言、景觀與現(xiàn)實(shí)關(guān)懷:近年來貴州電影創(chuàng)作評述
陳玉婷
從2015年開始,一批貴州籍導(dǎo)演拍攝的以貴州為表現(xiàn)對象的作品相繼問世,在口碑及市場上取得不俗的成績。畢贛的《路邊野餐》(2015)獲洛迦諾國際電影節(jié)當(dāng)代電影人單元最佳新導(dǎo)演銀豹獎(jiǎng)、第52屆金馬獎(jiǎng)最佳新導(dǎo)演獎(jiǎng),《地球最后的夜晚》(2018)入圍第71屆戛納電影節(jié)一種關(guān)注單元并在第55屆金馬獎(jiǎng)斬獲三項(xiàng)大獎(jiǎng),同時(shí)以2.8億的票房創(chuàng)造藝術(shù)電影票房奇跡。陸慶屹的《四個(gè)春天》(2017)榮獲第12屆FIRST青年影展最佳紀(jì)錄長片同時(shí)也贏得優(yōu)異的票房成績。饒曉志的《無名之輩》(2018)以3000萬成本斬獲近8億票房,創(chuàng)造了中小成本電影的票房奇跡。一時(shí)間,畢贛、陸慶屹、饒曉志等導(dǎo)演形成一股貴州電影新勢力,成為一種電影現(xiàn)象,讓觀眾認(rèn)識到貴州電影的獨(dú)特魅力,成功取得學(xué)界和業(yè)界的關(guān)注。
關(guān)于“貴州電影”的界定,學(xué)者支菲娜認(rèn)為,“學(xué)術(shù)意義上的‘貴州電影’包括三個(gè)維度:第一個(gè)維度是貴州的電影銀幕形象建構(gòu),即電影銀幕是如何展現(xiàn)貴州的;第二個(gè)維度是貴州的電影美學(xué)生長脈絡(luò),狹義上是指貴州影人是如何書寫貴州的,廣義的則包括貴州籍貫或具備較長貴州生活經(jīng)歷的影人的電影創(chuàng)作;第三個(gè)維度則是貴州的電影產(chǎn)業(yè)發(fā)展。”本文主要從第二個(gè)維度出發(fā),集中討論以畢贛、陸慶屹、饒曉志等為代表的貴州新力量導(dǎo)演關(guān)于貴州的創(chuàng)作情況,結(jié)合他們的作品進(jìn)行梳理和評述。
一、方言與紀(jì)實(shí)美學(xué)
在電影創(chuàng)作中,方言的意義在于將人物形象、地域文化、生活習(xí)慣和歷史過往進(jìn)行最真實(shí)的呈現(xiàn)。在全球化潮流的影響下保留拗口、小眾的方言,原本是對全球化潮流的背離,但方言傳達(dá)的特殊的地域文化、歷史傳統(tǒng)和生存狀況,消解了全球化進(jìn)程中的人們被同化的焦慮,從而找到自我認(rèn)同與歸屬感。方言一開始出現(xiàn)在張藝謀、賈樟柯等導(dǎo)演的紀(jì)實(shí)作品中,近幾年,方言電影逐漸成為潮流,除了《南方車站的聚會(huì)》(武漢話)、《風(fēng)中有朵雨做的云》(廣東話)等藝術(shù)性較強(qiáng)的作品外,一些類型化的商業(yè)作品如《火鍋英雄》(重慶話)、《羅曼蒂克消亡史》(上海話)、《我的姐姐》(四川話)、《了不起的老爸》(重慶話)等都使用了方言。貴州新力量導(dǎo)演敏銳地捕捉到了這股潮流,《路邊野餐》《四個(gè)春天》《地球最后的夜晚》《無名之輩》都使用了方言,貴州本土方言獨(dú)特的音調(diào)使得這批作品區(qū)別于同時(shí)代其他導(dǎo)演的作品。
一般來說,為了讓觀眾更容易進(jìn)入影片情節(jié),創(chuàng)作者往往會(huì)優(yōu)先選擇普通話作為電影人聲方案。之前的貴州題材電影都是以普通話為主的,如貴州籍導(dǎo)演丑丑的《阿娜依》(2006)、《云上太陽》(2012)、《侗族大歌》(2017),寧敬武導(dǎo)演的《鳥巢》(2008)、《滾拉拉的槍》(2008)等。普通話的使用,使影片情節(jié)容易被大眾理解,同時(shí)也加大了電影的傳播效率。但普通話的使用會(huì)使影片在真實(shí)性上大打折扣,弱化了影片的藝術(shù)價(jià)值,畢竟貴州本土居民并不是以普通話作為交流語言的。
貴州新力量導(dǎo)演的這批作品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方言,方言使這批電影更具本土特色,使其獨(dú)立于同時(shí)代其他導(dǎo)演的作品。畢贛的《路邊野餐》里標(biāo)準(zhǔn)的凱里話加強(qiáng)了影片的地域特色,主演陳永忠用方言吟頌的詩句成了影片獨(dú)特的標(biāo)簽。在饒曉志的《無名之輩》中,貴州方言在一群非貴州籍演員口中脫口而出,就連電影片尾曲《瞎子》也使用了貴州方言。“貴州的方言比起四川重慶方言更加潑辣,更加‘野’。貴州方言這種‘野’到極致的魅力在當(dāng)下越來越‘同質(zhì)化’的電影空間景觀中,無疑鶴立雞群,別有‘陌生化’的感覺。”在影視作品浩如煙海、觀影條件門檻極低的當(dāng)下,觀眾對影視作品的反應(yīng)是遲鈍的,方言帶來的“陌生化”增強(qiáng)了電影的獨(dú)特性,使得觀眾在“同質(zhì)化”的影視作品中對貴州電影有了更為深刻的印象。
以畢贛、陸慶屹、饒曉志等為代表的貴州新力量導(dǎo)演的創(chuàng)作整體呈現(xiàn)出紀(jì)實(shí)美學(xué)傾向。紀(jì)實(shí)美學(xué)最大的特點(diǎn)在于根據(jù)現(xiàn)實(shí)的模樣進(jìn)行創(chuàng)作,這批導(dǎo)演的作品將紀(jì)實(shí)美學(xué)置于貴州三四線城市空間及獨(dú)特的自然地貌中,對貴州地域、景觀、習(xí)俗、文化等進(jìn)行真實(shí)呈現(xiàn)。巴贊紀(jì)實(shí)美學(xué)理論推崇意大利新現(xiàn)實(shí)主義,除了方言的使用,意大利新現(xiàn)實(shí)主義最主要的特征在于非職業(yè)演員的使用。畢贛的《路邊野餐》大膽起用自己的姑父陳永忠作為主角,其他配角如謝理循、羅飛揚(yáng)等都是非職業(yè)演員,非職業(yè)演員最大的特點(diǎn)在于真實(shí)性極強(qiáng),沒有專業(yè)演員刻意的戲劇化表演。
巴贊的紀(jì)實(shí)美學(xué)還推崇長鏡頭和景深鏡頭,長鏡頭的主要特點(diǎn)在于遵循時(shí)空的統(tǒng)一性,對物質(zhì)現(xiàn)實(shí)做最真實(shí)的復(fù)原。畢贛喜歡使用長鏡頭,在《路邊野餐》和《地球最后的夜晚》中有充分的展現(xiàn),如《路邊野餐》中超過半小時(shí)的長鏡頭,將一個(gè)沿河小鎮(zhèn)獨(dú)特的地理空間交代得淋漓盡致,讓人拍案叫絕;《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的3D長鏡頭長達(dá)一小時(shí),更是以高超的技法把貴州獨(dú)特的山地、洞穴、小鎮(zhèn)等景觀囊括其中,時(shí)間和空間實(shí)現(xiàn)了高度統(tǒng)一。
二、自然景觀與空間建構(gòu)
電影中的景觀指的是客觀的景色與景象,在電影空間敘事中,城市與鄉(xiāng)村空間往往占據(jù)著重要位置并被賦予獨(dú)特的景觀呈現(xiàn)。俗話說,貴州“地?zé)o三里平,天無三日晴”,主要指貴州地處云貴高原,以山地為主,喀斯特地貌特征明顯,多陰雨潮濕天氣。這種獨(dú)特的地理特征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創(chuàng)作者的審美心理、文化性格和環(huán)境感知的形成。作為從小成長于貴州這片土地上的新力量導(dǎo)演,舍棄了繁華都市場景,將視角對準(zhǔn)具有貴州特色的小城、鄉(xiāng)村、山野,這是由創(chuàng)作者個(gè)體生命體驗(yàn)和生活沉淀決定的。在畢贛、陸慶屹、饒曉志等貴州新力量導(dǎo)演的影像中,凱里、都勻、獨(dú)山等貴州小城成為描摹對象,塑造了具有貴州特色的鮮活影像志。
“‘電影貴州’的意義在于——在一個(gè)同質(zhì)化、平面化的全球化時(shí)代重建差異性空間。依照列斐伏爾的思想,就是通過差異化主體對物質(zhì)形態(tài)的空間的干預(yù),即導(dǎo)演主體的影像再造和空間生產(chǎn),超越空間的物質(zhì)性,進(jìn)入以藝術(shù)對抗科學(xué)、以精神對抗物質(zhì)、以主體對抗客體的象征化的第二空間,即精神空間。只有不同空間的斗爭才能制造空間的獨(dú)特性和差異性,避免同質(zhì)化。”近幾年,國產(chǎn)電影產(chǎn)業(yè)發(fā)展迅速,票房紀(jì)錄不斷被打破,同時(shí),新的問題也隨之而來,即國產(chǎn)電影尤其是類型電影在空間選擇上呈現(xiàn)出高度“同質(zhì)化”的現(xiàn)象。這一問題在城市題材作品中比較突出,這些作品無不都是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四通八達(dá)的交通、光鮮亮麗的室內(nèi)空間。雖然非城市空間如西北、西藏等地區(qū)的自然景觀也許能充分體現(xiàn)出空間的主體性,但已不再新鮮,早有一批西部電影或藏地電影表現(xiàn)了這些景觀。貴州新力量導(dǎo)演的這批作品,為國產(chǎn)電影原本單一的空間表現(xiàn)注入了新鮮的異質(zhì)元素。
空間建構(gòu)是指在空間上進(jìn)行的關(guān)于所呈現(xiàn)的實(shí)物的建構(gòu)和營造。在貴州電影中,地域景觀成為認(rèn)識貴州地域、城市空間的一個(gè)重要標(biāo)識,使得觀眾通過空間即可進(jìn)行識別。空間是識別地域文化的重要標(biāo)識,如霍建起的《那山那人那狗》對湘西的自然景觀和空間進(jìn)行充分的展示,郵差的職業(yè)身份與鄉(xiāng)村自然景觀結(jié)合,十分貼切。《瘋狂的石頭》里面山城的地域景觀讓人對重慶城市有了一定的了解。《尋槍》將有數(shù)百年歷史的貴州青巖古鎮(zhèn)風(fēng)貌和警察“尋槍”的故事合理“嫁接”,呈現(xiàn)原本安靜的小鎮(zhèn)因?yàn)榫靵G槍而產(chǎn)生的一場風(fēng)波。《阿娜依》《云上太陽》中呈現(xiàn)了黔東南苗寨的鄉(xiāng)土氣息,《四個(gè)春天》中展現(xiàn)了獨(dú)山和獨(dú)山話的魅力及房屋空間、社區(qū)街道、鄉(xiāng)村圖景,饒曉志的《無名之輩》則全力聚焦在貴州都勻這個(gè)小城市中掙扎的個(gè)體。《路邊野餐》和《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的凱里都市空間,影像風(fēng)格偏重于破爛的街道、殘?jiān)珨啾凇⑧l(xiāng)鎮(zhèn)街道、城鄉(xiāng)接合部、路邊荒野、陳舊過時(shí)的發(fā)廊等頹廢的景觀標(biāo)識,與現(xiàn)代的繁華的都市景觀形成強(qiáng)烈的反差。貴州電影影像風(fēng)格呈現(xiàn)出來的異于當(dāng)下大都市繁華的景觀,通過對鄉(xiāng)鎮(zhèn)、都市空間的考察和抒寫,找到了適合貴州新力量導(dǎo)演創(chuàng)作的空間景觀,適合低成本、中小成本電影的創(chuàng)作。
三、平民意識與現(xiàn)實(shí)關(guān)懷
貴州長期以來交通閉塞,城市化水平不高,文化產(chǎn)業(yè)相對不發(fā)達(dá),電影人才相對較少,大眾對貴州電影的認(rèn)知還停留在少數(shù)民族題材等傳統(tǒng)主題上。以往的貴州電影主要集中表現(xiàn)少數(shù)民族的生活習(xí)俗,展現(xiàn)貴州黔東南民族鄉(xiāng)村氣息和民族風(fēng)情,如丑丑的《阿娜依》(2006)、《云上太陽》(2012)、《侗族大歌》(2017),寧敬武導(dǎo)演的《鳥巢》(2008)、《滾拉拉的槍》(2008),韓萬峰的《我們的嗓嘎》(2010)、吳娜的《行歌坐月》(2011)等。這批具有“宣傳”意味的作品出發(fā)點(diǎn)是積極的,其目的在于將貴州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置于全球化潮流中,試圖向外界展示貴州文化獨(dú)特的魅力。但這種帶有“民族想象”的作品是缺乏平民意識的,它往往迎合了外界對貴州“獵奇”的心態(tài),也容易給外界造成一種刻板印象,給人一種貴州只有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錯(cuò)覺。
隨著貴州新力量導(dǎo)演的崛起,貴州電影的敘事視角悄然發(fā)生轉(zhuǎn)向。畢贛、陸慶屹、饒曉志等導(dǎo)演在選材上有著不約而同的一致性,他們都把敘事焦點(diǎn)對準(zhǔn)了城鎮(zhèn)中下層民眾和農(nóng)村普通百姓的生活,著力于描摹貴州現(xiàn)實(shí)以及本土平民最真實(shí)的生活面貌。影像中流露出社會(huì)的現(xiàn)實(shí)狀況,散發(fā)著日常生活氣息,通過對普通人生活的描述、對普通人的關(guān)注,反映普通人的真實(shí)狀況,拉近與觀眾的距離,很大程度上贏得大眾的共鳴。貴州新力量導(dǎo)演的平民視角,一定程度上歸結(jié)為創(chuàng)作團(tuán)隊(duì)對貴州文化景觀和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深刻認(rèn)識。由于地域文化限制,貴州電影在內(nèi)容、題材、影像風(fēng)格上往往是以欠發(fā)達(dá)的城鎮(zhèn)空間為主,通過對普通群像的關(guān)注,表現(xiàn)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普通個(gè)體,對個(gè)體的內(nèi)心予以現(xiàn)實(shí)關(guān)懷。“影片敘事展現(xiàn)出對意識形態(tài)層面的疏遠(yuǎn),把重點(diǎn)放置在困窘生存本質(zhì)和個(gè)體人生體悟的展示上,不失為新力量藝術(shù)導(dǎo)演在后現(xiàn)代文化語境下的意識解放和敘事升級。”《路邊野餐》把鏡頭對準(zhǔn)了凱里小診所里的醫(yī)生陳升,講述了陳升尋找侄子衛(wèi)衛(wèi)的旅程;《四個(gè)春天》記錄了獨(dú)山縣城一對老年夫妻的生活及家庭的變遷;《地球最后的夜晚》與《無名之輩》雖然借用了類型電影的外殼,但主要人物還是生活中的平民大眾,創(chuàng)作者在湯唯、陳建斌等明星身上做了“去光環(huán)化”的處理,使得這些演員如同普通人一般呈現(xiàn)在熒幕上。
“貴州電影人對于社會(huì)有著類似第六代導(dǎo)演的恐慌和疏離,社會(huì)的發(fā)展以及文化的沖突迫使他們用影像來反思變革給生活帶來的改變,關(guān)注經(jīng)濟(jì)飛速發(fā)展的背景下,人民真正的生活狀況。”貴州新力量導(dǎo)演作品不同程度地呈現(xiàn)了不同人群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遭遇與困境,給予了人物最大限度的關(guān)懷,讓觀眾感受到生活之不易,體現(xiàn)了現(xiàn)實(shí)主義題材的內(nèi)在文化訴求。如《無名之輩》中的保安馬先勇(陳建斌飾),是一個(gè)沒文化、生活困窘的單身父親,冒著生命危險(xiǎn)幫警察尋槍也只是為了能當(dāng)上協(xié)警有個(gè)足夠安穩(wěn)的生活,“槍”代表了馬先勇亟須找回的尊嚴(yán)。笨賊胡廣生(章宇飾)和李海根(潘斌龍飾)的“盜竊”行為體現(xiàn)了務(wù)工群體對成功的渴望,他們最后被抓時(shí)看著天空絢麗的煙花傻笑,喻示了底層群體的成功如煙花一樣幻滅。《四個(gè)春天》中的陸運(yùn)坤、李桂賢的日常生活看似平常,但死亡卻悄然降臨到女兒身上,兩位老人白發(fā)人送黑發(fā)人,這樣的痛苦可以說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但兩位老人雖然內(nèi)心悲痛卻沒有因此一蹶不振,他們依舊樂觀豁達(dá)地生活著。《路邊野餐》中的醫(yī)生陳升踏上了尋找衛(wèi)衛(wèi)的靈魂之旅,《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羅纮武回到貴州漫無目的地追尋殺害好友的兇手,畢贛的鏡頭關(guān)注了這片土地上的中年男人靈魂深處的落寞和困頓。
四、結(jié)語
方言的使用及對紀(jì)實(shí)美學(xué)的追求、自然景觀的呈現(xiàn)及獨(dú)特的空間建構(gòu)、平民視角及對現(xiàn)實(shí)飽含深情的關(guān)懷,使得貴州電影充滿了神秘又獨(dú)特的氣質(zhì)。隨著貴州新力量導(dǎo)演在低成本、中小成本電影創(chuàng)作上不斷取得成績,表現(xiàn)貴州地域文化特色、文化習(xí)俗及生活現(xiàn)狀的貴州電影將會(huì)不斷出現(xiàn)在大銀幕上。在獨(dú)特的自然環(huán)境和漸漸發(fā)展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以及相對落后的文化產(chǎn)業(yè)困境中創(chuàng)作出獨(dú)特的貴州故事,避免同質(zhì)化作品的出現(xiàn),或許是貴州電影人才和產(chǎn)業(yè)今后將面對的現(xiàn)實(shí)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