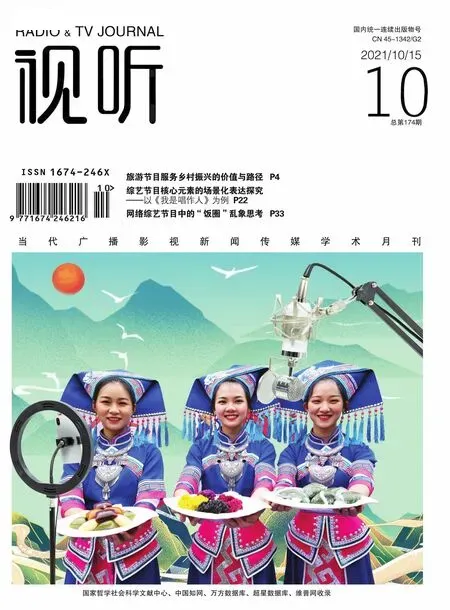從文化自信到文化消費(fèi):《只有河南》戲劇幻城中的生態(tài)觀
陸曉蕓
文化自信是一個(gè)民族對(duì)自身文化的底氣①。文化消費(fèi)建立在文化自信的基礎(chǔ)之上,指“用文化產(chǎn)品或服務(wù)來(lái)滿足人們精神需求的一種消費(fèi)”②。但同時(shí)“文化消費(fèi)也是以物質(zhì)消費(fèi)為依托和前提的”③。隨著社會(huì)生產(chǎn)力的不斷發(fā)展,群眾對(duì)于文化的需求進(jìn)一步提升,不再滿足于淺層次的娛樂(lè)。他們開(kāi)始追求一種精神上的慰藉,尋覓高品質(zhì)、有深度的文化娛樂(lè)產(chǎn)品。《只有河南》戲劇幻城作為一部貫穿河南古今歷史的“現(xiàn)象級(jí)”戲劇作品,所展現(xiàn)的河南文化的厚重與博大正是一個(gè)民族文化自信的體現(xiàn)。但在《只有河南》走紅的背后,只談“文化自信”是遠(yuǎn)遠(yuǎn)不夠的,還離不開(kāi)它深入創(chuàng)作、全方位投入市場(chǎng)等環(huán)節(jié)中的“生態(tài)”理念。
一、創(chuàng)作內(nèi)容中顯露的文化自信
一部作品內(nèi)容的好壞取決于它的深度與廣度。從生態(tài)角度來(lái)看,深,在于內(nèi)涵的深刻,體現(xiàn)出的是一種多元的層次感;廣,在于內(nèi)容的普世性,表現(xiàn)出的是一種平等的關(guān)懷。好的作品往往用平靜的語(yǔ)調(diào)講述“震撼人心”的故事,讓受眾能從炫目的舞臺(tái)上感受到創(chuàng)作者深埋的情感。
層次感主要體現(xiàn)在創(chuàng)作者對(duì)內(nèi)容的挖掘上。首先是《只有河南》的投資人胡葆森先生,作為土生土長(zhǎng)的河南人,他有屬于自己的河南情懷。這種情懷對(duì)“生于此,長(zhǎng)于此”的河南本地創(chuàng)作者來(lái)說(shuō),是一種對(duì)河南文化的依戀與敬畏。也正是在這樣一個(gè)文化環(huán)境的浸潤(rùn)下,才得以讓更多的河南創(chuàng)作者在作品中流露出濃烈的家國(guó)意識(shí)以及對(duì)“中原文化”走出去的自信。其次是導(dǎo)演王潮歌,她是個(gè)地道的北京人,但她卻用戲劇展現(xiàn)了一個(gè)“比河南更河南”的中原文化。作為一名文化愛(ài)好者,她對(duì)于文化有一種來(lái)自骨子里的崇敬,《只有河南》是她繼“印象”“又見(jiàn)”系列文化產(chǎn)品之后的又一扛鼎之作。相較于本地創(chuàng)作者的文化自覺(jué),外地導(dǎo)演則更加注重表現(xiàn)自己對(duì)河南文化的新解讀。他們以受眾的身份,懷揣著對(duì)河南文化的敬意,在吸收和理解河南文化的基礎(chǔ)上,對(duì)河南文化進(jìn)行二次創(chuàng)作,為河南文化的“出圈”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在當(dāng)?shù)貏?chuàng)作者文化自覺(jué)和外來(lái)創(chuàng)作者新解讀的共同作用下,《只有河南》打破了歷史的時(shí)間維度,通過(guò)獨(dú)立的空間構(gòu)造出不同時(shí)期的河南,賦予中原文化“一人千面”的特性,使得作品呈現(xiàn)出一種多元的層次感,以至于受眾在每一次的沉浸式體驗(yàn)中都對(duì)河南有一種新的認(rèn)識(shí)。
普世性主要體現(xiàn)在創(chuàng)作者對(duì)創(chuàng)作對(duì)象的一種平等關(guān)懷。從生態(tài)角度看,《只有河南》是一個(gè)超大體量的戲劇劇場(chǎng)聚落群,它拋離了一個(gè)劇場(chǎng)的概念:21個(gè)劇場(chǎng),21個(gè)故事,21個(gè)主體,各自獨(dú)立卻又相互關(guān)聯(lián)。在以小見(jiàn)大的手法下,涵蓋了中原文化的精髓。在這21個(gè)劇目中,既有河南唐宋時(shí)的繁榮,也有1942年的苦難,還有河南精神的傳承。一方水土養(yǎng)育一方人,《只有河南》打破了歷史的空間維度,以人物群像的方式展現(xiàn)了中原文化的廣博與兼容并包,讓受眾更為客觀地認(rèn)識(shí)河南。
《只有河南》將文化自信與創(chuàng)作內(nèi)容相結(jié)合,以一種“毫無(wú)保留”的方式將中原文化全盤(pán)托出,并將其與“戲劇幻城”的建筑特色和戲劇內(nèi)核相融合,打破了歷史與現(xiàn)實(shí)的時(shí)空界限,以獨(dú)立的空間為媒介,連接過(guò)去與現(xiàn)在。給受眾提供了一個(gè)用平等的眼光來(lái)看待中原文化的平臺(tái),在潛移默化中“顛覆”受眾對(duì)河南的刻板印象。
二、市場(chǎng)生態(tài)機(jī)制下崛起的文化消費(fèi)
政策為市場(chǎng)提供大環(huán)境,市場(chǎng)憑政策得以更好地發(fā)展。從黨的十九大提出的“文化自信”到現(xiàn)在“十四五”規(guī)劃提出的“構(gòu)建生態(tài)文明體系,促進(jìn)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全面綠色轉(zhuǎn)型”,體現(xiàn)的是文化消費(fèi)理念的轉(zhuǎn)變,一種從自信到可持續(xù)的嬗變。藝術(shù)與市場(chǎng)是兩個(gè)獨(dú)立又相互聯(lián)系的實(shí)體,它們各自發(fā)展、相互滲透,共同作用于文藝作品。從生態(tài)角度看,《只有河南》是一個(gè)較為完整的業(yè)態(tài)產(chǎn)業(yè)鏈。從前期的籌備創(chuàng)作,到中期的包裝銷(xiāo)售,再到后期的宣發(fā)以及相關(guān)衍生品的推廣都呈現(xiàn)出平穩(wěn)上升的趨勢(shì)。在這些表象之下,值得一提的是其創(chuàng)作者、受眾及大環(huán)境中的市場(chǎng)生態(tài)機(jī)制。
從文藝創(chuàng)作者角度來(lái)看,市場(chǎng)對(duì)其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gè)方面。首先是創(chuàng)作者對(duì)自己的高要求。《只有河南》作為一種建立在商業(yè)基礎(chǔ)上的文化現(xiàn)象,很容易被人誤解為是借科技的噱頭消費(fèi)文化。但創(chuàng)作者卻將《只有河南》中厚重的文化與先進(jìn)的科技進(jìn)行融合,重現(xiàn)河南歷史,不再是淺層次的復(fù)現(xiàn),而是上升到了一種精神再造的境界。其次是“創(chuàng)作理念”的表達(dá)。一部作品能否受到受眾的認(rèn)可,關(guān)鍵在于創(chuàng)作者的“理念”是否能得到受眾的認(rèn)同和共鳴。《只有河南》通過(guò)群像式的戲劇演出,涵蓋了河南百態(tài),以此吸引愈來(lái)愈多的外來(lái)受眾。再次是為“賣(mài)點(diǎn)”做好了伏筆。在《只有河南》中,導(dǎo)演王潮歌利用小麥作為意象,為后面“戲劇幻城”的開(kāi)園埋下引子,“六月六,麥?zhǔn)斐情_(kāi)”幾乎一度成為“戲劇幻城”開(kāi)業(yè)的口頭禪。隨著創(chuàng)作者們對(duì)文化認(rèn)識(shí)的不斷深入,文化自信的種子也漸漸扎根于文藝創(chuàng)作者們的心中,成為他們創(chuàng)作的潛意識(shí)。
從受眾角度來(lái)看,受眾與市場(chǎng)是相互彌補(bǔ)的。首先,隨著群眾物質(zhì)生活和文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受眾對(duì)于有深度的作品的需求也在不斷提高,具體表現(xiàn)為受眾開(kāi)始關(guān)注文化,并投身其中感受文化。其次,科技水平的提高讓之前很多難以實(shí)現(xiàn)的設(shè)想成為可能。《只有河南》對(duì)受眾的吸引之處就在于它利用科技對(duì)文化進(jìn)行全新的包裝:以黃河文化為創(chuàng)作根基,通過(guò)一種可觸摸、可感知、可沉浸的全新藝術(shù)形式,去感受河南文化的厚重與彌遠(yuǎn)。再次,國(guó)家政策給受眾提供了一個(gè)文化大環(huán)境。無(wú)論是“十九大”還是“十四五”規(guī)劃都能明顯感受到國(guó)家對(duì)文化的重視,以及國(guó)家為年輕人營(yíng)造文化氛圍的努力。在內(nèi)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只有河南》成了一種里程碑式的存在,讓越來(lái)越多的受眾前往,瞻其真容。在文化消費(fèi)飛速增長(zhǎng)的背后,離不開(kāi)受眾物質(zhì)水平和精神境界的提高,以及文化大環(huán)境對(duì)他們的熏陶。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只有河南》的出現(xiàn)為國(guó)人文化自信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條件。
從宣傳推廣角度來(lái)看,《只有河南》打破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推廣方式。首先,就宣傳主題而言,常規(guī)的推廣主題大多展現(xiàn)產(chǎn)品理念,但《只有河南》的推廣以“情懷”為主、文化為輔。情懷是一種情感,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垂髫小兒,人人都有。因此,相較于宣傳文化產(chǎn)品的“高概念”,選擇“情懷”輔之以河南文化則更容易引起觀眾共鳴。其次,在宣傳媒介方面,常規(guī)的推廣方式大多以宣傳片、平面廣告為主,但《只有河南》很好地利用了全媒體時(shí)代的特性,選用訪談和短視頻這種傳統(tǒng)媒體與新興媒體結(jié)合的模式進(jìn)行。通過(guò)視頻中的一些劇透和一些名人游玩過(guò)后的觀后感來(lái)吸引受眾,將此處打造為一個(gè)“網(wǎng)紅打卡地”。再次,在整體市場(chǎng)運(yùn)營(yíng)方面,衍生品是市場(chǎng)運(yùn)營(yíng)的最后環(huán)節(jié)。它既是一種從主體中演變出來(lái)的新產(chǎn)物,也是市場(chǎng)生態(tài)圈銜接的關(guān)鍵所在。《只有河南》的衍生品很好地做到了文化與商業(yè)的融合,實(shí)現(xiàn)了市場(chǎng)運(yùn)營(yíng)的有機(jī)循環(huán),推動(dòng)了新一輪的文化消費(fèi)。
在政策導(dǎo)向和文化價(jià)值的共同驅(qū)使下,《只有河南》憑借其在市場(chǎng)中敏銳的“生態(tài)意識(shí)”打造了一個(gè)可持續(xù)的生態(tài)市場(chǎng)體系。在這一體系中,各個(gè)環(huán)節(jié)相互配合,相輔相成,將原本割裂的流程彌合,構(gòu)成了一個(gè)完整、全面的生態(tài)體系。
三、文化“重塑”之鑒
《只有河南》戲劇幻城憑借其“規(guī)模最大、演出時(shí)長(zhǎng)最長(zhǎng)的新劇種”的稱號(hào),一度成為河南最火的文旅景點(diǎn),堪稱文化“包裝”的典范。用戲劇論述河南古今,用全息影像再現(xiàn)河南歷史,高高的黃土墻內(nèi)夯起的是一座充滿地方記憶和文化意蘊(yùn)的古城。此種簇新的藝術(shù)形式給文藝創(chuàng)作的兼容并“包”帶來(lái)了新的借鑒意義,主要體現(xiàn)在創(chuàng)作內(nèi)容的“包容”和作品的“包裝”方面。
其一,用多元的視角“包容”創(chuàng)作內(nèi)容。好的文藝作品往往具有普適性,任何一個(gè)人都能在作品中找到他們那個(gè)時(shí)代的情感共鳴點(diǎn)。讓藝術(shù)走近人,藝術(shù)才有靈魂。因此,創(chuàng)作者應(yīng)該聯(lián)系實(shí)際生活,結(jié)合地域文化的人文性、社會(huì)性以及獨(dú)特性進(jìn)行挖掘和創(chuàng)造。無(wú)論是“陽(yáng)春白雪”還是“下里巴人”,它們都是藝術(shù)的表現(xiàn)形式。創(chuàng)作者要做的則是二者之間的權(quán)衡,利用科技拆解并簡(jiǎn)化精英文化,用高雅藝術(shù)的表現(xiàn)形式升華大眾文化的內(nèi)涵,以多元的視角賦予作品層次感,以達(dá)到“千人千味”的效果。
其二,用人文色彩“包裝”文化“短板”。在當(dāng)今這個(gè)“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時(shí)代,再好的文化也離不開(kāi)精美的“包裝”。中原文化深沉厚重,卻因其擺脫不掉的“鄉(xiāng)土氣”而難以跨越“走出去”的鴻溝。但《只有河南》反其道而行之,直面短板,以“鄉(xiāng)土文化”為特色,另辟蹊徑,以河南的“泥土”為主創(chuàng)元素,將傍土而生的小麥作為一種意象元素。因此,“包裝”時(shí)應(yīng)注意元素的選擇和搭配,不能太過(guò)露骨、直接地選擇文化中淺層的肉眼可見(jiàn)的元素,要盡量選擇與地方文化相關(guān),且能與人產(chǎn)生聯(lián)系的、有深度的事物作為“包裝”對(duì)象,輔之以相應(yīng)的人文色彩,以實(shí)現(xiàn)文化形象的重塑。
四、結(jié)語(yǔ)
文化自信是一種對(duì)文化價(jià)值的充分肯定,是一種對(duì)文化生命力的堅(jiān)定信念④。《只有河南》戲劇幻城作為一部構(gòu)筑獨(dú)具河南特色的、有良好發(fā)展勢(shì)態(tài)的“現(xiàn)象級(jí)”作品,讓地方文化完成了一次從文化自信到文化消費(fèi)的過(guò)渡。該作品用發(fā)展的觀點(diǎn)來(lái)看待“文藝創(chuàng)作”這一問(wèn)題,以河南文化為核心,以現(xiàn)代化劇場(chǎng)為紐帶,建構(gòu)了一個(gè)全新的、綠色的、可持續(xù)的文化產(chǎn)業(yè)生態(tài)體系。
注釋?zhuān)?/p>
①李松,王建民,張躍,朱凌飛,馬居里,許雪蓮.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節(jié)日在國(guó)家文化建設(shè)中的地位和意義[J].藝術(shù)百家,2012(05):27-38+62.
②楊曉光.關(guān)于文化消費(fèi)的理論探討[J].山東社會(huì)科學(xué),2006(03):156-159.
③顧向鋒.思想政治教學(xué)中文化消費(fèi)決策素養(yǎng)的培養(yǎng)研究[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xué),2011.
④劉正全.正確理解文化自信的內(nèi)涵及時(shí)代意義[J].魅力中國(guó),2018(43):250-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