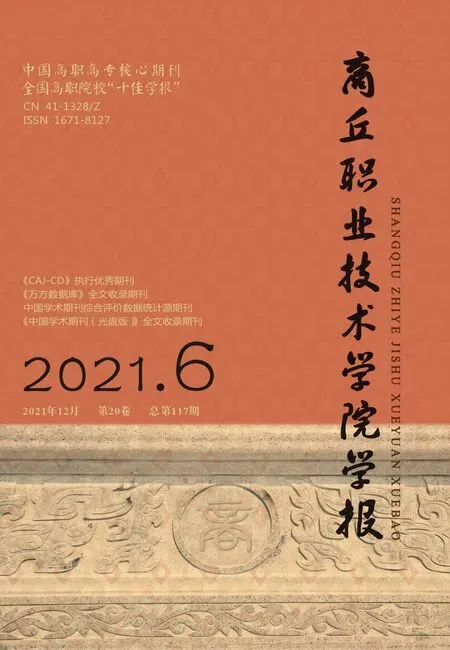性別與身份認同的張力結構
——中西語境中的“姐妹情誼”研究
趙思奇,聶平均
(河南大學 文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姐妹情誼”是伴隨著女性意識覺醒、女性在男性話語的鏡像下的一種話語回歸建構。相對于男性的邏輯性、秩序性和等級性的話語,女性話語建構者認為,女性有普遍的屬于女性的隱秘體驗、特殊的言說方式和書寫方式,而這則可以作為建構“姐妹情誼”的基石[1]376。這種設想的“締結女性共同體”,為女性主義的身份認同和女性解放的基礎帶來了希望,但是這種脆弱的聯盟有著太多的不確定性和短暫性,其最終是否會導向烏托邦式的“幻象”是值得深思的[2]。作為一種設想,“姐妹情誼”是一種女性聯合體,是要跨越種族、身份、膚色和階層的,但是如何才能真正地“跨越身份界限”[3],這里其實是存在著一個性別與身份認同之間的張力結構的。從性別的角度來看,“女性的從屬是‘結構性的’”,尤其是早期的女性主義者的研究就會把注意力放在女性受到的“共同壓制”上面,而忽略了由于身份認同(種族、膚色、階級等)帶來的“差異”上[4],從而也會使理論指向烏托邦。但是,如果在尊重身份認同的情況下,彼此體諒對方的“差異性和獨立性”,也未嘗不可相互促進,結成穩固的女性同盟勢力,來共同對抗來自父權和男權話語的壓制,開創屬于女性的話語空間并最終走向女性解放之路[5]。所以,對性別和身份認同之間的張力結構的揭示和研究,可以很好消解“姐妹情誼”理論自身固有的烏托邦指向,為建立新型的“姐妹情誼”提供重要的參考意見。
一、“平等”與“差異”的張力:西方女性詩學中的“姐妹情誼”
女性主義詩學是與女性主義糾纏在一起的,而女性主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就是“平等與差異”問題,當強調“性別平等”就會導致“差異”被抹殺,而過分強調“差異”就會造成“多元立場”“內部分化”[6],這是女性主義理論中最重要的背離或者悖論。女性主義理論就是強調“差異性”的,這種男女的差異僅僅是一個方面,還有女性內部的種族、階級和人生閱歷的差異。如果抹平“差異”追求“平等”,那么“平等”是建立在什么基礎上的呢?比如男女平等、女性平等等。這些問題啟迪了女性詩學試圖嘗試構建“女性傳統”“女性氣質”和“姐妹情誼”理論來解決女性內部的一致性問題。從前面的分析得知,“姐妹情誼”這個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帶有抹平女性內部“差異性”的傾向,“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和階級歧視”是阻礙女性團體團結的主要障礙[7]74。所以,“姐妹情誼”在有些研究者看來就指向了烏托邦,也只有在共在的“集體情感”中才有可能克服這種烏托邦性質[8]。也有學者通過對胡克斯的研究表明,“姐妹情誼”構建盡管困難重重,但是在承認“差異”的基礎上才有走向理想未來的可行性[9]。
早期的女性主義者伍爾夫在《一間自己的房間》中分析瑪格麗特·卡文迪什和溫切西爾夫人的時候,用“兩人都沉溺于詩,又都因此而形容憔悴”“打開公爵夫人的詩集,你會看到同樣的躁動”[10]來描述女性作家有著相通的體驗和煩惱。此外,伍爾夫進一步分析了女性作家在創作時會面臨的困境,比如說相同的經濟困擾、阻力和障礙,以及來自男性話語的詰難。這種女性的共通性到了肖瓦爾特時,女性就從開始講述“她們”的故事,變成了《她們自己的文學》,這條在伍爾夫手中還不是很清晰的路線圖已經清晰可見了。“女性傳統”作為文學史中的“亞特蘭蒂斯”被重新發現,也就是說在整個文學史當中,由于女性文學當中“某些循環出現的類型、主題、問題和形象”構成了文學史當中的“亞文化”[11]。女性的亞文化在肖瓦爾特看來是由女性共同的生理經驗和共同的社會經驗所形成的需要掩蓋的“秘傳知識”,所以,女性作家從一開始就具有“隱秘”的團結和“共謀”,而這種由于建立在共同女性經驗基礎上的女性團體之間的身份認同就是“姐妹情誼”[12]。比如簡·奧斯汀和夏洛蒂·勃朗特對筆下人物伊麗莎白和簡·愛的刻畫,都不約而同地從她們不顧世俗的偏見,敢于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愛情的角度展開,簡·奧斯汀和夏洛蒂·勃朗特之間的這種跨時間的亞文化身份認同,可以作為肖瓦爾特理論的注腳。
這種共同的女性經驗在愛麗斯·沃克看來其合法性就非常值得懷疑,因為黑人在女性傳統理論中是缺席者,黑人僅存在于白人理論的注腳里,這讓她萌發了追尋屬于黑人的女性傳統、風俗的理論追求[13]47-52。愛麗斯·沃克認為,黑人女性的傳統是祖母傳給母親再傳給女兒的,是一種在種族壓迫、階級壓迫和男性壓迫下的艱難處境。在赫斯頓的《他們的眼睛望著上帝》和愛麗斯·沃克的《紫色》中,就穿透著這種傳承性,前者用“驢子”來形容黑人女性在白人男性和黑人男性的雙重壓迫下的處境,而黑人女性的解放則寄托在一種純粹的烏托邦世界中,相反,后者中的夏格則敢于掙脫男性世界的束縛,并鼓勵自己的姐妹塞莉跳出藩籬。前者塑造了珍妮和菲比,后者刻畫了夏格和塞莉“姐妹情誼”關系,而這種在種族關系上的身份認同就比白人女性的那種抽象的建構更加牢固。
在胡克斯看來,如果女性主義不將種族問題和階級問題納入其中,其實質就是一個抹殺黑人女性,一個純粹的白人女性用于自娛自樂的“非人化的過程”。胡克斯舉例說,白人女性在發言的時候不僅不考慮黑人女性的利益和訴求,在講話的時候也不會考慮其他女性的感受。在胡克斯看來,這種能夠處理女性理論內部“差異”的能力是決定女性是否能夠團結起來對男權社會進行抗爭取得最終勝利的關鍵所在[7]65-69。來自階級底層和受壓迫的種族的女性,當她們在白人女性家中做女仆和奴隸的時候,跟她們提“姐妹情誼”這種完全忽略受壓迫階層利益和訴求的口號,只能是一種沒有任何可能實現的泡影。
梳理英美較有代表性的批評家的“姐妹情誼”理論,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英美哲學當中的經驗主義影響深遠,理論當中充斥著感性和經驗性的感受和描寫。相比較而言,法國女性主義則比較偏重于“以激進的態度,將語言作為性別與權力斗爭的一個場域,試圖以與女性身體相結合的女性寫作來拆解父權文化象征秩序”[14],更側重從文本、語言學、語義學以及心理分析等方面的理論建構工作[15]126。波夫娃的女性理論是建立在對黑格爾主奴辯證法的批判上,她認為,“若每個人都能夠坦率地承認他者,將自己和他者相互看成既是客體又是主體,那么超越這種沖突便會成為可能”[16]。 女性的形成在她看來是與男性世界和男性話語的“他者”凝視密切相關,而語言和神話結構則是環繞在女性頭上的另外一層束縛。在波夫娃的筆下,女性是具有相同的形成過程,“她”是被社會所規訓、所凝視、所教化,是一個比較抽象的存在。但是,她寫出了女性的形成、處境和生存之境,在她的筆下,女性的“差異”還不是很明顯,她還企圖構建男女平等的理想愿景,但是沒有人繼承她的衣缽[15]128。
盡管如此,得益于波夫娃對于主奴辯證法的批判和解構主義者對能指和所指的解構,西蘇就首先選擇從解構語言結構開始,她認為,寫作是女性最有力的武器,唯有寫作才能讓女人跨越前俄狄浦斯階段,感受到未被男權污染的純凈的世界。但是,如果使用男性的語言結構進行創作就會再次掉入男權中心主義的窠臼中,唯有借助于“身體寫作”才能給予女性“洞察力和力量”[17]。而西蘇所指的女性“是指那些不可避免地要與傳統的男人做斗爭的婦女,還包括了必須使婦女覺悟起來,爭取她們的歷史地位這樣一個全球性的婦女主題”[13]397,西蘇和波夫娃雖然沒有承認“姐妹情誼”,但是她們的理論相對比較側重于女性的“共性”。西蘇并不否認“差異”,但是借助于“身體寫作”挖掘女性身體的潛意識可以讓女人之間產生一種共鳴。到了法國理論家克里斯蒂娃那里,主體被消解掉了,文本之間存在著一種“文本間性”,處在主體位置上的“是文本間的對話”[18],換句話說,主體是一種“流動性的過程主體”,是對父權象征秩序致命的解構。解構之后的主體的流動性讓整個文本世界呈現出一種隨意流動和無目的、無秩序的狀態,但是,如果沒有主體,誰又為文本提供了流動的場域和“語境”呢,這在克里斯蒂娃這里是一個永恒難解的謎。也就是說,到了克里斯蒂娃,“女性”這個概念也是不存在的,“女性氣質”和“姐妹情誼”都是遭到嚴重質疑的概念。
二、“女兒國”原型視域下的中國女性詩學中烏托邦式表征
與之相應的是,中國女性詩學是以中國傳統的“女兒國”原型為文化基底,以西方女性主義文論為鏡像,通過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鏡像的交互,才逐漸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女性主義詩學。“女兒國”作為中國詩學中女性生成和存在的空間,是文學作品中主要表征“姐妹情誼”原型結構,在中國女性詩學中分別有三種烏托邦:第一種是以《紅樓夢》為代表的原生態的中國古典式“姐妹情誼”的烏托邦;第二種是以《方舟》《兄弟們》為代表的初步啟蒙(有性別認同但是沒有自覺身份認同)的烏托邦;第三種是以《一個人的戰爭》《無處告別》《另一只耳朵的敲擊聲》為代表的“同性之愛”的烏托邦。其中,第一種為未經西方女性主義理論鏡像浸染過的、獨具中國特色的古典形態,后兩者則是以中國文化為基底,又積極汲取了西方女性主義思想有益成分,在中國女性詩學中的表征形式。
(一)原生態中國古典式烏托邦
從神話學的角度講,“女兒國”可以追溯到《山海經·大荒西經》中對“女子國”的描述,其后在《淮南子》《三國志》和《后漢書》中皆有類似的記載。《西游記》中的“女兒國”則來源于《大唐西域記》和《馬可·波羅行記》中對印度附近的“女子國”的記載[19]。《西游記》對“女兒國”的描寫就比較成熟了。小說當中的“女兒國”,是為了襯托唐僧取經的堅定所設計的妖魔化的女性王國,這個王國里面雖然已經有女性當家做主的影子,只是完全借用了男權社會的權力而設計的,里面并沒有“姐妹情誼”。《鏡花緣》中的“女兒國”則是對現實的倒置——男性主內而女性主外,男性穿裙子、梳妝打扮、裹足,女性在封建社會所受到的一切壓迫都讓男性去承擔,頗具有啟蒙意義。到了《紅樓夢》中的“女兒國”(就是賈寶玉所居住的“大觀園”),里面的一系列女性人物才具有中國意義上的“姐妹情誼”雛形:一種相互扶持、相互體諒和相互尊重的姐妹表征。
原生態的中國“姐妹情誼”,首先是高度審美化的,因為這群姐妹是沒有生產和生存的現實需要的,她們過的是吟詩結社的生活,人物形象是婀娜多姿的,性格是多姿多彩的,氣質是藻雪精神的,氣氛是圓融和諧的;其次是高度理想化的,因為這群姐妹都是完美的,都是可人的,都是讓人憐惜的,都是不占塵埃的。基于此,她們的結局注定是悲劇的,她們之間的“姐妹情誼”最終導向了烏托邦。究其深層次原因,一方面是她們的女性意識尚未覺醒,并未意識到自己的悲劇命運根源是封建父系社會和男權制度;另一方面是由于她們的自我身份認同。比如,香菱是個被買來的丫頭,雖說被薛寶釵當作妹妹看待,但畢竟身份不同;林黛玉雖說是主子的身份,由于雙親皆不在身邊,始終有一種寄人籬下的感覺,再加上與賈寶玉之間曖昧的關系,與薛寶釵等人始終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姐妹關系等。在傳統意義上的“女兒國”空間中,在塑造原生態的“姐妹情誼”中,曹雪芹不自覺地把性別與身份認同二者的張力結構表現了出來:一方面作為女性,她們與男性和男權社會劃清界限,在烏托邦幻象的“大觀園”中自由自在的生活;另一方面她們又不得不屈從于封建男權社會。曹雪芹囿于時代和歷史的限制,顯然無法超脫出來,所以,他精心營造的“大觀園”最終走向了衰敗和沒落,這既是他的悲哀,又是時代的悲哀,更是女性的悲哀。
(二)以《方舟》《弟兄們》為代表的初步啟蒙的烏托邦
張潔在《方舟》中描寫的三個女性同窗好友:荊華、梁倩、柳泉,各自有其不幸,但都不愿意接受沒有愛情的婚姻,就共同擠在“方舟”上,組成三個人的“女兒國”。這個“女兒國”對于女性共同面臨的困境,比如婚姻問題、孩子問題、工作問題以及與男人交往過程中受到的騷擾、侵略以及欲望的或者蔑視型凝視都有比較認真的細節描寫。雖說她們想象著如果各自問題解決后,大家要好好“出去玩一玩”,可是什么時候是個頭兒呢?她們是絕望和無奈的[20]。王安憶的《兄弟們》中“老大”“老二”和“老三”三個姐妹基本上被作家切斷了與社會聯系,作者把她們放在一個校園內,可以算是一種烏托邦設計了。 三個姐妹在校園中產生了純潔的友誼,只是這種“姐妹情誼”無法經受現實的考驗和沖擊。王安憶比張潔犀利的地方在于,王安憶讓三個姐妹離開了烏托邦空間。“老三”一畢業就不能抗拒自己丈夫的壓力而跟隨丈夫回到小縣城;“老大”回去后也很快生了孩子,這也算是背叛了她們之間的約定和諾言;“老二”雖堅守的時間最長,但因扛不住那種外在的無形的壓力最終決定要孩子,也算是沒有堅守住承諾。
這種形態的“姐妹情誼”,主要關注的是凝視問題,主要集中于異性的欲望的凝視、外在權利的凝視以及身份認同的自我凝視。它不僅僅是一個“看與被看”的問題,而是一種欲望的投射、權利的壓力和自我的異化的一個問題。女性在男性為主導的場域中,欲望的凝視是她們首先會遇到的問題。一方面,欲望的凝視會給女性造成困擾,另一方面,有些女性為了贏取權利和地位通過塑造自己的氣質和外貌等[1]357來迎合這種欲望的凝視。比如《方舟》中魏經理對柳泉的凝視就是這種欲望的凝視,實際上還混雜著權利的凝視。柳泉可以對抗甚至無視魏經理欲望的凝視,但是卻不能忽略他帶有權利的凝視,尤其是涉及具體的工作。前兩種凝視會形成一種外在的鏡像對女性的自我身份認同產生強大的不自覺的自我凝視,而女性一旦不自覺地屈從了外在的對于角色的定位要求,很快就又會從覺醒狀態劃入未覺醒狀態。這是在多重凝視下的女性“姐妹情誼”會導致烏托邦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這在王安憶的《弟兄們》中有非常明顯地體現。
(三)林白、陳染“同性之愛”的烏托邦
在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中,南丹的存在“總是使我返回我的原來面目,這是她對我的意義”[21]。由于南丹的追求,才讓她有了做女人的感覺,在南丹闖入她的生活之前,沒有男生對她有興趣,她同樣對男生沒有興趣。在這里,南丹的性別實質上被倒錯了,南丹雖然性別為女性,但是,其扮演的卻是一個闖入主人公生活的“男生”,一是作者把南丹與男生類比,二是作者讓南丹做了只有男生才會做的事情——主動追求主人公多米。在多米眼里,南丹用只有男性才擁有的欲望,凝視著她,她最終融化在了南丹的柔情之中。
與《弟兄們》類似的是,戴二也有兩個小姐妹,也曾經相約不嫁男人,甚至到了一周不見就會思念的地步。當小姐妹繆一和麥三相繼與自己的男友結婚和同居之后,她們三人的“姐妹情誼”也就煙消云散了。尤其是當繆一懷孕之后,戴二明顯感覺到由于身份認同的原因她們之間的隔膜越來越嚴重了,甚至到了打通電話兩人無話可說的地步[22]。在另外一部小說中,陳染描寫了戴二在不堪重負的母愛下與伊墮人之間的“同性之愛”,伊墮人擁有戴二另一面的氣質,也可以算作是戴二的自我分離、自我分裂,她與伊墮人之間的“同性之愛”甚至可以看作是戴二的自我復位,是一種自我追尋和自我雙性同體的一種復歸。伊墮人曾經對戴二說:“沒有男人肯于要你,因為你的內心與我一樣,同他們一樣強大有力,他們恐懼我們,避之唯恐不及。”[23]79母親對戴二的愛,在戴二看來是一種窒息的令人發瘋的愛,是一種監視式的牢籠的愛,是一種窺視和懷疑式的愛。但是,在戴二的母親看來,她對戴二的愛,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女兒不受傷害、不受欺凌,尤其是不讓女兒墮入不正常的男女關系、不正常的女性之間的關系之中去[23]83,其實這何嘗不是一種“同性之愛”的另外一種版本呢。
林白建構的“姐妹情誼”,其中一個女性會自然而然地將自我的性別認定為“男性”,當性別認同倒錯之后,她會用一種男性鏡像式的自我凝視要求自我身份認同。她們最大的問題是來自他者的凝視,她們該如何面對強烈的集體身份認同,如何面對外在的和內在的焦慮和不安。當性別倒錯了之后,她們該怎樣對自我的身份進行定位和認同,這是一個棘手問題。陳染的“姐妹情誼”更像是一種自我的心靈投射,與其說是為了“同性之愛”,不如說為了一種自我的心靈安慰和心靈慰藉。與林白不同的是,陳染有意模糊性別的界限,她不認為“同性之愛”是一種性別倒錯,而是試圖通過女性的私人化描寫來展現女性獨特的體驗和經驗,而且她從一開始就知道這種“同性之愛”的“姐妹情誼”是一種不可靠的、隨時都會由于身份認同瓦解的不穩定結構。陳染的“女兒國”的烏托邦是由于在“母親”過于沉重之愛的壓迫下,在母親和自我的雙重凝視下,對于異性的警惕和自我情感的投射下所導致的。由于母親的警惕和窺視,無論是“同性之愛”抑或者異性之愛都被破壞,而也正是由于母親的監視和刺探,戴二與母親之間這種母女之間的愛也被破壞,最終全部導向了烏托邦。
三、結語
在西方和中國的早期建構中,理論和踐行的先行者都只注意到了女性話語的性別意識,卻不大注重對身份認同的研究,這就導致了“姐妹情誼”具有非常明顯的烏托邦性質。在西方,“姐妹情誼”是由于階級、膚色和民族問題所造成的性別與身份認同之間的緊張關系;在中國,“姐妹情誼”則是由于受到“女兒國”原型的影響,往往會把人物設定在一個狹小的空間內,對性別與身份認同之間的張力認識不夠。即便是被增添了身體書寫、雌雄同體以及母女關系問題的探索,由于“姐妹情誼”對身份認同所造成的社會復雜性認知程度不夠,所以,從簡單的人物性別、人物獨特的心理感受以及人物獨特的生理體驗出發是不夠的,因為這樣很容易會導致理論的烏托邦性質。那么,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呢?我們認為,利用中國古老的“和而不同”的智慧,也許會可以比較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這將是我們下大功夫努力研究的問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