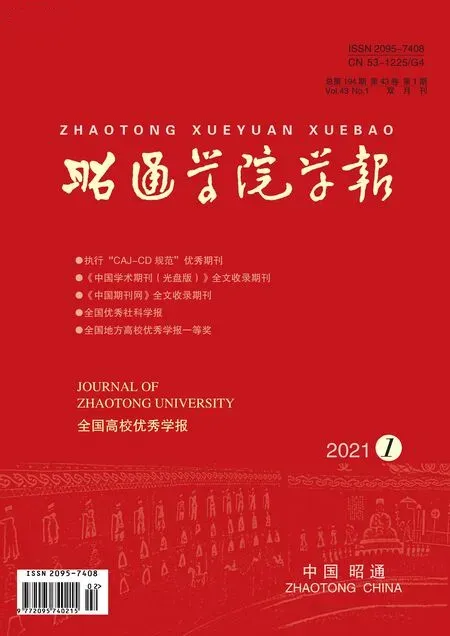從“二元對立”到“多元和諧”
——對《恩惠》的生態女性主義解讀
張 晶
(閩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福建 漳州 363000)
一、引言
生態女性主義是婦女解放運動和環境保護運動相結合的產物,它出現在20 世紀70年代,并在90年代蓬勃發展。被認為是第三次女權運動的重要流派,也是生態哲學的重要流派。弗朗索瓦·德·艾奧博尼于1974年首次提出“生態女性主義”一詞,標志著生態女性主義研究的開端。隨著全球環境污染的加重,越來越多的學者和機構關注生態女性主義。生態女性主義是從女性性別的角度來看待生態問題,指出人對自然的統治與父權壓迫女性同出一轍,都是在根植于以父權制為邏輯的認識之上,對世界進行簡單粗暴、一分為二的統治,從而對此進行批判。生態女性主義者關注女性和自然,認為“西方文化在貶低自然和貶低女人之間存在著某種歷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性的關系”。[1]它倡導建構多元生態文化,旨在建立一個人與人、男人與女人、人與自然三個系統之間和諧與可持續發展的社會。
托妮·莫里森是當代美國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獲得了美國圖書獎,普利策小說獎,諾貝爾文學獎等諸多獎項,被譽為美國黑人文學領域的代言人之一。她的小說以意味深長的主題、生動的對話和不同類型的人物而聞名。作為黑人女性作家,莫里森深切關注黑人女性的生存和自我身份的建構,她的作品真實地刻畫了黑人女性遭受來自社會以及黑人男性的歧視的痛苦,展現了她們為追求自我認同、平等和幸福而奮斗的過程。
莫里森的第九部長篇小說《恩惠》一出版就備受關注,獲得評論家們的贊譽,并被《紐約時報書評》編輯遴選為“2008年度十佳圖書”之一。小說篇幅不長,僅僅167 頁。在小說中,佛羅倫斯的母親為了改變女兒的命運,自小將她賣給“心里沒有野獸”的小農場主雅各布,這個16 歲的黑人女孩卻最終沒有擺脫命運的摧殘,她渴望得到母愛和愛情,最終都失敗了。莫里森通過對小說中的人和自然事物的描寫,揭示了人類將自然邊緣化、男權中心主義將女性邊緣化的社會現實,傳達了建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男人和女人平等相處的新型社會的愿望,彰顯了生態女性主義思想。
二、父權制社會中的二元對立
(一)人類對自然的主宰
在西方傳統思維中,人與自然的二元對立就是自我和他者的對立。尼爾·史密斯說:“自然是上帝賜予的禮物……是人類的設計,既是荒野,也是耕作的田園。”[2]這一對自然的定義表現了在西方傳統中根深蒂固的人類中心主義,認為人能統治自然,自然為我所用。在十七世紀的殖民時期,殖民統治者的物質欲望極度膨脹,瘋狂地追求財富、掠奪自然資源。西方殖民者將自己與自然割裂開來,把自然視為他者、被統治者和剝削的對象。在《恩惠》中,莫里森通過對美洲殖民地的描寫說明了早期的歐洲移民者肆意地破壞大自然、剝削原住民。殖民者無休止地圈地,砍伐整棵整棵的大樹,把森林變成無法生長任何植物的沙丘,并且隨意占有女人,企圖毀掉一切土著居民。“他們從大地的靈魂中掙脫出來……像所有嬰兒一樣不足。”[3]59“生態女性主義理論家普魯姆伍德認為,殖民主義思想意識形態表現出人類中心主義的形式,通過強加的殖民者土地模式和理想風景意識來對非人類自然進行殖民化。”[4]當時殖民者主要從事皮毛、煙草、木材、朗姆酒等生意,掠奪和占有自然資源。他們認為自然資源永遠不會枯竭,“就像木柴,很快燒成灰又很快會得到補充”,[3]32“土壤永不會衰竭”。[3]33他們有一個強大的對自然的占有欲,莉娜告訴弗洛倫斯一個關于旅人和鷹的故事:當旅人站在峰巔,欣賞著大自然的美景,他開懷大笑說:“這是我的。”[3]68故事中的旅人認為自己無所不能,世上的一切都取決于自己的精神,心中充滿了征服的快感。這是一種典型的人類中心主義。
農場主雅各布·伐爾克早年是個孤兒。他心酸的經歷使他不同于其他白人奴隸主。起初,他心懷仁慈,富有同情心,厭惡作把奴隸當做商品進行買賣,他認為“血肉之軀不是他的商品”。[3]22然而,在目睹了他去收債的奴隸主恢弘、華麗的大房子以后,他無法抑制對財富的欲望,他開始夢想要在不遠的將來,在自己的土地上蓋起一棟這么大的住宅。在回家的路上,雅各布的想法發生了重大變化。小說對自然環境的描寫暗示了雅各布物質欲望的膨脹和掠奪自然資源的計劃,“當他返回小旅館時……沒有霧——無論是金色或灰色的 ——阻礙他。”“遠處閃耀的銀光根本并非遙不可及……等著他去品嘗。”[3]37回到農場后,雅各布變得“遲緩且不易討好”。[3]39他逐漸開始投資種植園,并通過剝削和控制奴隸以滿足他的擴張欲望。貪婪的種子他在心中瘋狂地成長,他開始破壞自然,建立自己的夢想豪宅,“一棟既不適合農場主,甚至不適合商人,而是與一名鄉紳相匹配的宅子。”[3]97他未經樹木的同意,砍伐了五十棵,最后招來了厄運。雅各布建造的未完工的豪宅正是人類破壞自然、剝削自然的罪證。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人類和自然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當人類因貪婪無視自然界和人類存在的規律,無視對自然環境的破壞,人類離災難就不遠了。
(二)男性對女性的壓迫
“根據墨菲的理論,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從最開始就把自然和文化、人類對自然的主宰和對女性的壓迫緊密相連”。[4]在西方傳統的價值論中,人與自然、男性與女性是相互對立的,女性和自然同樣受到父權制社會的壓迫。女性是莫里森關注的焦點,她在作品中忠實地展現了她們無法言說的慘痛經歷和心理創傷。農場女主人麗貝卡來自中下層,盡管她是個白人女人,在父權文化中仍然遭受著很多歧視,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當她父親得知雅各布正在尋找一個身強力壯的妻子,便抓住機會賣掉了自己的女兒。“她可以指望的只能是做傭仆、娼妓和妻子。”[3]85她選擇了最后一個,對她來說似乎是最安全的。所以她橫渡大海來到了她從未踏足過的新大陸,把自己的未來交給了雅各布。兩人名義上是夫妻關系而實質上他們處于從屬關系。當雅各布洗澡時她用肥皂和短刷清洗他的身體,然后用布擦干,而麗貝卡卻沒有得到同樣的對待。當雅各布建造一所根本不需要的大房子時,她高興得就像她在收獲季節一樣,因為這可以讓她丈夫在農場呆得更久。雅各布因病去世后,她覺得自己失去了一切,無心照顧農場。顯然在父權制社會中,女性完全依附于男性,始終無法擺脫男性的奴役。
在小說中,佛羅倫斯是最后一個來到農場的女奴,她是小說中最悲劇的人物。雅各布到奴隸主家里討債時,奴隸主想利用他的女奴作為補償。令雅各布驚訝的是,女奴懇求讓她和兒子留下,而帶走佛羅倫斯——她八歲的女兒。因為被母親拋棄,佛洛倫斯從此失去了身份和歸屬感,給她的內心造成了巨大的創傷。在雅各布的農場,她的生活比以前好一點。她得到了莉娜的關心和愛護,但這一切都沒有使她擺脫精神的奴役,她總是想取悅別人,渴望獲得別人的認可。遇見鐵匠后,她成了愛的奴隸。她在墻上寫道:“在你知道這個世界上有我存在之前,我就已經被你殺死了……最終當我們的目光相遇時,我沒有死。我第一次活著。”[3]41深深的愛慕使她歷盡艱難險阻找到了鐵匠,但鐵匠誤以為她故意傷害一個小男孩,揍了她一頓,把她無情地趕走,不給她任何解釋的機會。在父權制社會,男性統治、壓迫和奴役女性,女性沒有話語權。男性的壓迫和奴役根植于女性的內心,使女性認為自己是男性的奴隸。
小說中描述的其他女性角色也同樣受到父權制社會的歧視和壓迫。土著女奴莉娜原本生活在一個和平的印第安部落。歐洲殖民者的入侵摧毀了他們的家園,使她成了孤兒。在白人奴役和文化的影響下,她被迫改變了生活方式。一天晚上,主人喝醉了爬上她的床,此后經常毒打她,最后把她賣給了新主人雅各布。到了農場,莉娜教會雅各布如何曬魚干,如何為家畜繁殖做準備、如何保護莊稼,幫助他打理農場。但是她卻沒有得到任何回報,“只要天氣不是太惡劣,她就住在雞舍里”。[3]54佛羅倫斯的母親在小說的最后敘述了自己身為黑人和女性所遭受的摧殘和壓迫,還有她不得不拋棄女兒的苦衷:母親從非洲被販賣到美洲,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迫害。“我不知道誰是你的爸爸。四下太黑,我看不清他們任何人……在這種地方做女人,就是做一個永遠長不上的裸露傷口。”[3]180佛羅倫斯正在發育的胸脯引起了主人的注意,母親對此憂心忡忡。她在前來討債的雅各布身上看到了希望,認為他“心中沒有野獸”,懇請他把女兒帶走,希望女兒不再重蹈自己的覆轍。
三、多元和諧關系的建構
(一)女性的自我建構
“艾琳·戴夢得和歐藍斯坦曾經指出,生態女性主義不能停滯于摧毀西方文明中的人類中心主義和男權中心主義,還應該注重構建新故事,新故事是尊重確保生命延續的生物文化多樣性的”。[4]莫里森在《恩惠》中也體現了鮮明的生態女性主義特點,不僅呈現了“互為聯系的壓迫”,[5]解構了人與自然、男性與女性的二元對立關系,而且勾畫了一個新型的多元和諧的世界。小說中的主要女性角色從大自然中汲取靈感,通過不同的方式自我建構。
莉娜通過回歸自然和找回記憶中的印第安文化實現自我建構。在印第安文化中,地球是萬物之母,人類的棲息地,也是他們精神的源泉力量。在他們眼中,人和自然融為一體,他們的生命旅程源于自然,并以回歸到自然結束生命的旅程。大火燒毀了莉娜的家園,使她不得不抹掉記憶、遠離自然。到了農場,她在村子里沒有一點舒適感和安逸感。最后,帶著極大的孤獨、氣惱和傷痛,莉娜決定依靠自己的記憶和才智,把母親教給她的東西和印第安的習俗拼湊起來,使自己變得強大。回歸印第安文化使莉娜找到一種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的方式。同時,莉娜全身心地投入到大自然的懷抱中,成為自然界又一活躍的事物,她和動物唧唧喳喳地交談,與植物聊天,在陽光和細雨中嬉戲。融入大自然使她找到了生活的樂趣。“在太太到來時,她的自我創造已臻于完美。”[3]55顯然,莉娜已成功地完成了自我建構。
雅各布死后,女主人麗貝卡也染上了重病,佛羅倫斯為了拯救她的生命,孤身一人踏上路途遙遠、艱辛重重的尋找鐵匠之旅,這象征著佛羅倫斯開始自我認同的建構。在佛羅倫斯尋找鐵匠的路途中,大量的自然景象的描寫,象征著大自然給予她的指引,并暗示了她對鐵匠的愛的悲慘結局。“我夢到櫻桃樹朝我走來……我不知道它們想要什么。看一看?摸一摸?一棵樹彎下腰來”。[3]113這里的櫻桃樹是母親的象征,母親想說點什么向女兒表達她的愛,但是佛羅倫斯不能理解。在鐵匠的房子里,她夢見自己在一片湛藍的湖邊,當她靠近水面時,她看不到自己的臉,連個影子也沒有。“藏到哪兒去了?為什么藏呢?”[3]152她仍然不能理解大自然給她的暗示。直到鐵匠因為誤會讓她離開,佛羅倫斯終于明白她的臉不在藍色的湖里暗示了在鐵匠眼里她沒有自我,只是一個粗野的奴隸。歷經磨難后,佛羅倫斯開始自我反思,逐漸意識到沒有精神獨立連愛情都得不到,精神自由對女性極其重要。由此可以發現她的主體意識被喚醒,開始自我認同的建構。回到農場后,佛羅倫斯不再溫順,而是變得野性。她在墻上刻下了告白:“我還是佛羅倫斯。從頭到腳。不被原諒。不肯原諒……奴隸。自由。我延續著。”[3]177通過最后的告白佛羅倫斯向鐵匠所代表的父權制男性發出了反抗的怒吼,自我認同之旅得到了升華。小說的最后一章,母親敘述了自己“賣女為奴”的苦心、無奈和深深的母愛,佛羅倫斯在告白結束時把對母親稱呼從最初的憫哈妹改成了媽媽,并對媽媽說:“你現在可以開心了,因為我的腳底板和堅柏樹一樣堅硬了。”[3]177至此母親和女兒在心中達成了和解,弗洛倫斯找到了遺失多年的母愛,最終實現了自我建構。
如果說弗洛倫斯通過尋找失去的母愛找回自我,“悲哀”則是通過成為母親完成了自我建構。“悲哀”是一位船長的混血女兒,經歷了一次沉船事故成了孤兒。后來被好心的雅各布帶回農場,喚作Sorrow, 意為悲哀。因為心里障礙,她性格孤僻,只和她自己幻想出來的“雙胞”交流。“雙胞”是她的”安全保障,是她的快樂所在,是她的向導”。[3]133“雙胞”成了她有機的組成部分,是她的靈魂,表現了”悲哀”深切渴望追尋自我。“悲哀”具有強烈的母性本能,在兩名白人承包工人的幫助下,憑借勇敢和冷靜,她最終在水中生下了第二個孩子。水象征著自然,表明自然在女性尋求自我認同中起著重要作用。同時“悲哀”的生產過程就像萬物在自然界的生長的過程一樣,水中的嬰兒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說明了大自然在人類延續過程中的重要性。“悲哀”成為母親后,她從一個沒有自我的個體蛻變成一個完整獨立的個體。“她自信她這次獨自完成了一件事,一件重要的事……她當即就知道了該給她起什么名字。該給自己起什么名字。”[3]148她把自己重新命名為“完整”“雙胞”也悄無聲息地消失了,“悲哀”最終實現了自我獨立,成為莫里森描寫的女性角色中自我建構最成功的。由此可見,融入自然與女性的自我建構緊密相連。
(二)建構和諧的兩性關系
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男性和女性是相互依存的,“女人承擔和男人一樣重要的任務,并不存在從屬關系,而男人并不感到威脅,因為他需要她”。[6]只有男女平等協作,互補互助,才能構建多元和諧的世界。在小說中,莫里森不僅描寫了被壓迫婦女的悲慘遭遇,也試圖找到一個解決方案。在她看來,男性和女性只有互相尊重和依賴,才能建構一個和諧的世界。雅各布意外地繼承了一個120 英畝的小農場,但是“土地似乎拒絕遵從他的意志”[3]54,他遇到了各種困難,是莉娜教他如何種植和看管家畜。女主人麗貝卡來到農場后,他絲毫不必操心農場的營生,因為“麗貝卡和她的兩個助手像日出一樣可靠,像柱樁一樣牢固”。[3]22雅各布堅信女人天生比男人可靠。起初,農場呈現出一種相互依存和共生的關系,男性和女性的才能得到充分發揮,“成為仁愛,非中央集權的社區”。[7]雅各布的農場猶如“伊甸園”,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觀念、不同身份和利益的人在那里過著平靜的生活。他們互相幫助,親如一家。在承包工人威拉德和斯卡利眼里,在農場里有父母(雅各布和麗貝卡),姐妹(莉娜,弗洛倫斯,和“悲哀”)和兒子(他們倆)。在小說中,莫里森把雅各布的農場描繪成“伊甸園”,表達她對一個新型和諧社會的渴望,在這個社會里,不同種族、不同性別和不同階層的人可以克服種族和性別歧視,彼此和諧相處。
四、結語
生態女性主義的“終極關懷是建立一個新的秩序,一個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和諧的精神家園和物質家園”。[8]《恩惠》通過解構父權制統治下人與自然、男性與女性的二元對立,建構了一個多元的新型和諧世界,表達了莫里森希望解放女性和自然,實現男女平等,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愿望。同時,也為我們緩解生態危機,建立一個平等、和諧、多元的社會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