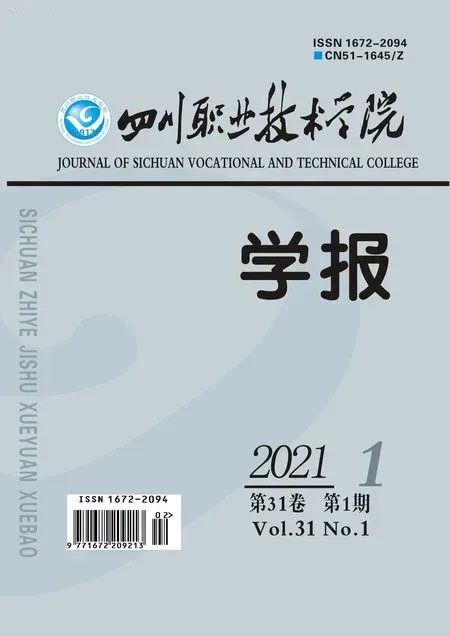漢晉時期的狀研究
蘇曉敏
(南京師范大學 歷史系,南京 210097)
中正官的任務在于品第人物,而其所需材料則為狀、品、家世三項。狀是早期品第人物重要參考資料。漢末至西晉狀的演變與九品中正制密不可分,故先敘述相關研究。唐長孺先生在《九品中正制度試釋》論述詳盡,提出西晉時家世成為品第高下的主要依據[1]90。宮崎市定先生在《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提出,該制度為貴族服務是九品官人法創立之初就有的。魏末創立的州中正使得九品中正制越來越貴族化,并指出西晉時該制度已成為維護貴族社會上流階層利益的制度[2]8-101。黃惠賢先生也認為西晉時期,構成狀的德和才,日漸不被中正們所重視[3]。祝總斌先生認為曹魏、西晉處于門閥制度的過渡性時期[4]。閻步克先生也提出西晉中正官的評價標準逐漸向士族門閥傾斜了[5]。兩位先生多側重曹魏、西晉中正制度的過渡性演變。而胡寶國先生則略有不同,提出盡管士族的力量在發展,但皇權仍能有限地利用中正制度維護統治[6]。
關于狀的專門性研究,唐長孺先生則提出中正之狀的淵源出自漢末名士的名目或題目[1]89。張旭華先生在其《九品中正制研究》進一步提出,九品中正制建立以后,中正品評人物也多采用這種方法,而這種高度概括的品題發展到后來就成為中正所作之狀[7]70。此外,日本學者的研究亦頗有建樹。矢野主稅先生對士族高門潁川荀氏、瑯琊王氏、陳郡袁氏、太原王氏、平原華氏以及潁川庾氏等家族子弟的一系列狀進行仔細爬梳[8]37-42。宮崎市定先生則提出狀是對品的說明,狀必須調查并且記錄性行、才德。這種文學性的描述難以據其判斷為官品級[2]99。永田拓治先生在《“狀”和〈先賢傳〉〈耆舊傳〉的編纂》中對漢魏嬗變之際出現兩傳進行細致研究,認為鄉里社會人物評定之風盛行,提出人物評定的狀即是其寫作的參考來源,并在文末對二十四賢狀進行詳細考證[9]。
學界對狀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然而對于漢末至西晉狀的專題研究尚有進一步討論空間。故本文不揣谫陋,擬在前輩們研究基礎上,再探中正之狀的來由嬗變。如有不當之處,謹請方家指正。
一、早期的狀
《文心雕龍》對狀的相關特征進行最早總結,概括為“狀者,貌也。體貌本原,取其事實。”[10]劉勰總結了狀文體的一般特征。而任昉的《文章緣起》中則有記載“狀者,貌也。類也。貌本類實,備史官之采,或乞銘志于作者之辭也。”[11]可見狀主要作用在于客觀記載狀主生平以及品評其人事跡。
《漢書·高帝紀》則有最早的關于“行狀”的史料,暫可從中一窺特征,現摘錄如下: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蘇林曰:“行狀年紀也。”[12]71-72
該段史料記載是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國之初立,局勢不穩,諸侯謀反頻現,劉邦下求賢詔擴大統治基礎。該詔令提出賢能之人經當地郡守親自送至相國府,需進行登記年齡等一系列的操作。其文中記載需登記“行、義、年”,蘇林注將“行、義”解釋為行狀,把“年”理解為年齡。而《漢書補注》中則又作新解:“署行,若云本身并無違礙過犯;署儀,若云身中、面白、有無須;署年,若干歲也。”[13]110-111今人陳直先生基于居延木簡名籍簡,統計其反復出現的“行、義、年”,又作解,即行為品行,義為儀表、年為年齡。[14]陳直先生和王先謙先生觀點大抵相同。從上可窺見,狀其原意應多為其內在品行,外在儀表,整體年齡等,此其一。求賢詔中稱將送至相國府,進行登記,類似一種人才評價檔案,存放至相國府。可見漢代以降,狀即有固定的存放所在地,此其二。
二、漢末鄉里月旦與狀源流
九品中正制是“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的結合與制度化[15]141。談及以名取人,則可追溯至漢代。從漢末名士“品題”到中正之狀,二者一脈相承,有著難以割絕的歷史淵源[7]70。漢代的人物好談論,且重視名聲,有很深厚的社會基礎。如《后漢書·蘇章傳》載其人:“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乃相謂曰:‘見蘇恒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16]1106該段史料有下述值得注意點,如蘇章習慣品評他人。士人們都擔心他品評之結果,實則也可見蘇章的評價有很大影響力,此其一。“有高名”,這一評價屢見于《后漢書》中,如《后漢書·循吏列傳》載:“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16]2481《后漢書·逸民列傳》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16]2763。不難從中窺探出漢末人們對于喜好品題,重視聲名的形勢,故該評價屢見之,此其二。
《漢書·揚雄傳》又載:“仲尼之后,訖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12]3582我們從中不難窺見,德行和才能兩項在漢末的評價中屢見不鮮。師古注:“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質。”[12]3582即按照德行、才能至于名將排列尊卑,這與后世中正狀評價的兩項標準相似。
《廿二史札記》對于東漢重視名節的現象亦有詳細記載:“蓋當時薦舉征辟,必采名譽,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為茍難,遂成風俗。”[17]88趙翼分別從讓官位、替他人報仇等種種現象中證明了漢末人們對于名節的重視。
汝南月旦評對中正制形成有著深遠的影響。張旭華先生也曾在其著作中記載二者之間密不可分的聯系。現擇錄史料如下:
初,邵與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論鄉邑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16]2235。
此段史料記載了漢末月旦評的實際情況,即許邵等人因好“品評”人物而有高名。更值得注意的其中說到,“每月輒更名品題”。即漢末的汝南月旦評每月都會更換相應的品題,引領討論。這個品題的具體內容,我們不妨從后文中一覽究竟。
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目。邵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協邵,邵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16]2234
許邵對于曹操的評價,這是從才能、事跡等方面來繼續曹操其人的相關能力的。此外《資治通鑒》載:“操乃劫之,邵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按注解:“言其才絕世也。天下治則盡其能為世用,天下亂則逞其智為時雄。”[18]按《資治通鑒》中則是從才學和能力兩個品題里來評價曹操,且字語簡短中,后世狀的源流可見。許邵看不起曹操并不想給予評價。只有到曹操劫持許邵的情況下,許邵才給出了相應的評價。短短數語言,便使曹操因此評價而成名,可見漢末的鄉里月旦的巨大影響。《通典》亦載:“大小中正為內官者,聽月三會議上東門外,設幔陳席。”[19]892該條史料亦陳述了州郡中正每月皆有一次會議,以便了解鄉里輿論,亦可從該史料看出了月旦評和中正制之間的源流關系。
三、魏晉時期的狀
(一)曹魏時期
《三國志·常林傳》載:“時論以林節操清峻。”[20]660常林有孝悌之行,而后擔任太守、刺史,從政期間亦頗有政績。常林對同鄉司馬懿行拜禮則不倨不傲,認為這是司馬懿遵循長幼禮節所至,并不因其官位所重而有所顧忌。當時人們評價常林清正高尚,實則也是一種相對客觀的評價。按其注解引《魏略》:“嘉敘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20]661吉茂和常林同為《清介傳》所載,史稱吉茂出自世代都很有名的家族,此時九品中正制剛創制不久,中正官重在選拔有才能的人,故吉茂雖身在高門第,卻被評定能力一般亦不足為奇。縱覽其生平,為官多是清廉之職,但曾經因族人犯罪而連坐。從吉茂因評語而怒,易見不好的狀的評語對于仕途有極大的阻礙作用,不難窺見在曹魏時期,家世對狀的評價并不完全起決定作用,此其一。早期中正制的狀評語,對其后的仕途有著很大參考作用,此其二。
《三國志·程郭董劉蔣劉傳》載:
楚鄉人王濟,豪俊公子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關求楚品狀,濟曰:“此人非請卿所能名。”自狀之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20]462
孫資以及其子孫宏是曹魏重臣,而其孫則是西晉官員,其狀也可體現魏晉之際的一些特征。孫楚是西晉官員,其狀評價其才能也是很簡單的八字,且多貼合其人物形象。此外,孫楚獲良好的狀評語,位至護軍、太守等要害官職,良好的狀評語對于仕途的助力可見一斑。矢野主稅先生對當時士族子弟之狀進行爬梳,發現他們的狀中往往會有“清純”“清靖”“清和”“清凈”“清譽”“清虛”“清簡”“清粹”“清素”等詞語,而其狀評價高低直接關系到“狀主”的仕途[8]37-42。我們從這些簡短的狀的評語中,不難窺見其多和漢代名目品題一脈相承,字數極為簡短。作為選官依據實則帶有一定模糊性。有些評語多側重于評價其文采方面,如“并有文藻”。將文采高低作為品第官位的幾項依據之一,似不能夠直接體現其和選官任職能力的具體相關性。
曹魏時期,狀的評價還是選官的重要參考之一。一般狀的評語都較為簡短。同時,好的狀的評語,對仕途也是一種極其重要的推力。故史載:“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勉,猶有鄉論余風。”[21]1058衛瓘在批駁九品中正制其品評人物幾大弊端,痛批有失公允之時,同樣贊揚過其在曹魏建制之初,亦曾經陟罰臧否,根據漢末鄉里清議之風品評,選拔了一批有用之士,這亦是對曹魏九品中正制的恰當肯定。
(二)西晉時期
西晉時,山濤于吏部任職,曾為朝廷需要推舉過不少人才。山濤所甄人才,其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啟事》。《山公啟事》反映了山濤品鑒人物的標準,亦是西晉時人物品評的風尚表現,現擇錄如下:
此三人皆眾論所稱,諒尤質正少華,可以敦教。
吏部郎主選舉,宜能得整風俗理人倫者。
舊選尚書郎極清望,號稱大臣之副,州取尤者以應[22]。
《山公啟事》是山濤向皇帝推舉人才的匯編,所涉及的范圍有吏部郎主、尚書郎、侍中、太常、河南尹等官職。其選官多擇錄人物性格、才能,故亦反映了西晉時期標準。縱覽《山公啟事》,不難發現其和狀的特征有共通之處。如推舉崔諒、陳準、史曜為尚書郎時,多考慮了眾人時評。也因此點,選拔能整頓風俗的人當選吏部郎主,足見時下評論對選官的參照性;其外,評價尚書郎二詞引用“清望”二字,亦和狀的評語異曲同工,多為對人物才能性格的簡短評述。山濤推舉人物,多為對人物才能性格作簡短品題,供皇帝參考,此點和狀之簡短評語異曲同工。
九品中正制推行以后,其在選官體系中地位日漸不可替代,與此同時批駁之聲時亦有之。狀作為中正評價的三項材料,推行中有流于形式之弊。曹魏后期重臣傅嘏曾曰:“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為敘。”[20]623傅嘏此條是對于劉劭的“《都官考課》”的駁難,但也體現出了狀的記敘人物的缺點——實際運用中名實難當,此外亦不難窺見了狀在當時中正選官中的廣泛參考作用。
關于狀在后世選官時的參考作用,《通典》注引西晉劉毅上表則曰:“若吏部選用,猶下中正,問人事所在、父祖位狀。[19]892即在吏部選官時,?需了解被選官者的相關情況,則需要自身的狀,父輩的狀以及祖輩的狀,故狀在當時選官的參考作用中可見一斑。隨著九品中正制的盛行,弊端亦隨之凸顯,劉毅亦陳述了九品中正制有不少弊害,納之如下:
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于臺府,納毀于流言。
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為好丑。
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系縶選舉,使不得精于才宜。[21]1276
劉毅認為在曹魏時創立九品中正制只是權宜之計,而隨后九品中正制亦有八大弊病。未能選拔到特別合適的人才,其狀更有流于形式之嫌。定品第只為朋黨修飾名譽,違背了最初的求取有識之士的動機。在品和狀的關系上,則又顯得過于機械。根據品級來取人,則才能不一定達到。而根據狀來取人,又可能會被原初的品級所限制。故根據狀定品實際操作中往往會流于形式。即使是品狀相仿,也會被九品中正制度的形式束縛,使其不能發揮應有的才能。退一步講,即便是所評價的人能力突出,也不能超過本品所能給予的最高官職。更何況在中正官手里操作又有極大任意性,可根據其親疏遠近來選人。劉毅大抵也是窺見了九品中正的弊端,故曾奏請恢復古代的鄉舉里選,在位者也并沒有采納。西晉時期,評定高下的依據已經只參照家世,那么狀的作用便已經形同虛設。
曹魏時,狀的評語可作為仕途晉升的重要依據,而至魏晉之際狀已經逐漸變得徒具形式。一方面,側面證實了九品中正制在當時選官制度中地位舉足輕重。其曾為魏晉時期的統治集團選拔了大量人才。另一方面,也不難窺見,狀作為一種評價體系至后期已徒具形式。這也是九品中正制從最初的為評定人才擴大統治基礎,走向后期的僵化成為門閥把持選舉的一個影射。
四、結語
狀是早期中正品第的重要材料。其多記敘一個人的品行,儀表,年齡三項。漢代的臧否之風多興盛,其月旦品題和狀源流一脈相承。狀的評語一般字少簡潔,故其對于選官的參考則有一定的模糊性。但如能獲得好的狀的評語,對于仕途是一種極大的助力。但即使狀的評語再高,也不能超出本品相應該有的官位。西晉以降,多以家世品第高下,狀的作用便已經微乎其微了。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從狀之演變多可管窺九品中正制在各個時期的不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