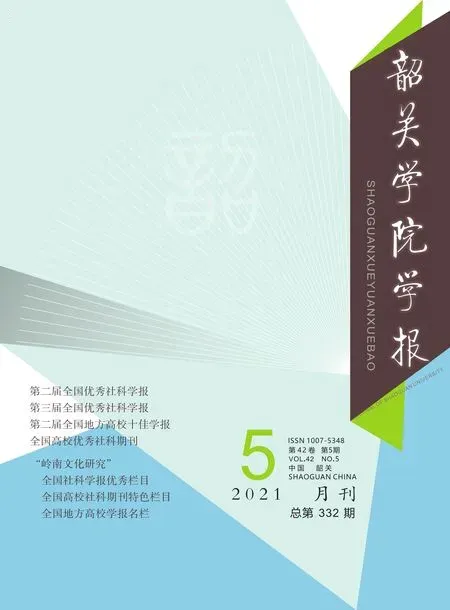詞源分析在英語專業精讀課篇章理解中的作用
——以《現代大學英語精讀》為例
詹曉慧
(嘉應學院 外國語學院,廣東 梅州 514000)
英語精讀課也稱綜合英語課,是英語專業的核心課程。新版《高等學校英語專業教學大綱》對基礎和高級階段的綜合課課程提出了具體要求:基礎階段的綜合英語課程主要通過語言基礎訓練與篇章講解分析,使學生逐步提高語篇閱讀理解能力;高級階段的綜合英語課程則主要通過閱讀和分析內容廣泛的材料,培養學生對名篇的分析和欣賞能力、邏輯思維與獨立思考的能力,鞏固和提高學生的英語語言技能[1]。
《現代大學英語精讀》是目前廣泛使用的一套英語精讀課教材①本文所引課文例句均選自楊立民、徐克容主編的《現代大學英語精讀3、4》(以下分別簡稱《精讀3》《精讀4》)。。主編楊立民教授在教材前言指出,精讀課中心任務是提升閱讀能力[2]。提升閱讀能力的基礎又在于準確理解詞義。英語詞語并非枯燥無味的字母組合,詞語意義在語言發展過程中也非一成不變的思維產物。學生在閱讀課文時若能對關鍵詞語追本溯源,透過詞源了解詞語意義演變的歷史過程及其文化背景,就可以更為準確地理解詞義,從而沿著詞源的路徑走向文章思想的叢林。
一、詞源信息對外語學習的作用
“etymology(詞源)”源自希臘語詞“étumos(真實的)”,以“etymon(詞的本義或最初形式)”的形式進入英語詞匯,最后以“etymology”的拼寫形式穩定下來。從廣義而言,詞源研究的是詞的來源與歷史,包括詞性與詞義的變化,以及對由其他語言引入的借詞所作的研究等[3]。詞源的豐富內涵對外語學習者的詞匯學習可起到補充和強化作用。首先,在文化方面,詞源信息從詞的溯源向學習者展示該詞的文化內涵,使學習者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譬如,《精讀3》第四課Diogenes and Alexander中作者這樣描述亞歷山大帝:“and toward women,he was nobly restrained and chivalrous”。學生通過“chivalrous”一詞的詞源可以了解到西方歷史上的騎士制度(chivalry)及其對英國紳士文化形成的影響,加深對課文人物形象塑造的理解。在詞法層面,英語詞匯的長期演變決定了英語構詞法的多樣性,查閱詞源信息可以對詞匯的構成方式有較為直接的了解,有助于詞匯的有效記憶和猜詞能力的培養。《精讀4》第四課Lions and Tigers and Bears出現的新詞“indefatigable”,該詞雖生僻卻可通過詞源推斷其詞義,其詞源信息顯示該詞由三部分構成:in-‘not’+de-‘away,completely’+fatigare‘wear out’,組 合起來即“孜孜不倦的;堅持不懈的”之意。在詞義方面,有些詞語的詞源展示了詞義擴大、縮小、升格和降格的變化,了解詞語在某個特定歷史時期的意義對于理解詞語所在的語境有很大幫助。如《精讀4》第二課Spring Sowing中“shrewd”一 詞,“shrewd”是“shrew(‘evil person or thing’)”的 變 體,本 指“evil in nature or character”,后來其貶義色彩逐漸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如今廣為人知的褒義涵義“having or showing sharp powers of judgment(精明的,機敏的)”,因此莎士比 亞 喜劇“The Taming of the Shrew(馴悍 記)”中“shrew”指的是“悍婦”,而課文句子“Mary,with her shrewd woman’s mind...”中“shrewd”的意思則是“敏銳的;靈敏的”。在語用方面,詞源信息可以明確詞匯使用的規范性,引導學習者通過詞語的語體色彩體會文章的文體色彩,從而提高學習者用詞的準確度。如《精讀3》第十一課Why Historians Disagree,作者 說 道:“‘truth’is but an elusive yet intriguing goal in a never-ending quest.” quest屬于書面用語,意為“探索”,了解其語體色彩不僅可用于辨析近義詞而且有助于把握文章整體語言風格。由此可見,詞源信息既可提高學習者的文化認知,也能幫助學習者挖掘詞語之間在結構上的聯系,了解詞義的擴大與縮小、揚升與貶降、弱化與轉移等,增加對詞語語體色彩的了解,提升語言運用的得體性[4]。
詞源信息不僅可以運用于詞匯習得,同時也能對學習者閱讀能力的提升起到積極作用。在篇章閱讀中,詞源信息所展示的詞義演變過程可以成為學習者準確把握詞匯語義內涵的有效途徑。學習者通過詞源信息與語境的結合,可以在準確把握關鍵詞涵義的基礎上將詞匯學習逐步提升到句子、段落乃至整個篇章閱讀層面,從而提高理解和賞析英文作品的閱讀能力。筆者以“詞源”“閱讀”為關鍵詞在中國知網數據庫中進行檢索時則發現在閱讀中利用詞源信息促進篇章理解的文獻較少。因此,本文擬從詞源信息與教材篇章內容相結合的視角出發,以《現代大學英語精讀》第三、四冊為例,從詞源的文化信息、詞法信息、詞義信息和語用信息四個層面探析詞源信息在英語專業精讀課篇章理解中的作用。
二、詞源信息在篇章理解中的運用
(一)詞源文化信息與篇章理解
《精讀3》第三課是凱瑟琳·曼斯菲爾德(Katherine Mansfield)的短篇小說《蒔蘿泡菜》A Dill Pickle。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出生于維多利亞時期新西蘭的一個中上階層家庭。在她的作品中女主人公們大多帶有其自身的影子:家境優渥、教養良好,《蒔蘿泡菜》的女主人公Vera亦不例外。故事延續作者一貫的散淡文風,情節簡單,語言詩意,字里行間卻透露出Vera內心的孤獨與幻滅。故事講述一對舊日戀人的別后重逢。昔日時光借由Vera豐富的內心獨白逐漸浮現,其中有這么一段文字:A great many people takingteain aChinese pagoda,and he behaving like a maniac about the wasps—waving them away,flapping at them with his straw hat,serious and infuriated out of all proportion to the occasion. How she had suffered. 本段描述他們在倫敦皇家植物園邱園(Kew Gardens)共度的第一個午后,作者雖未對景物加以濃墨重彩的描寫,但寥寥幾筆已將一個色彩明亮的午后邱園如印象派油畫般展現于讀者眼前:陽光和煦,花開如荼,茶會上圍桌而坐的飲茶者們衣著講究舉止優雅。邱園的婆娑塔影(a Chinese pagoda),裊裊茶香(tea),無一不散發出歷史沉淀的東方氣息。
“pagoda(佛塔)”源自印度梵語,本指吠陀時期為藏納圣人骨骸所修建的墓冢([f. Port.pagode,prob. ult. F. Pers.Butkadaidol temple]),后來作為佛教文化的重要象征傳入中國。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遣派使團訪華,使團專職畫家約翰·尼霍夫精心描摹了當時南京大報恩寺琉璃塔舉世無雙的風姿,寺塔圖像隨后在歐洲廣為流傳,報恩寺塔也因此成為17世紀至19世紀歐洲人心目中的中國標志性建筑[5]。1757年,英國著名建筑師威廉·錢伯斯受命對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Kew Gardens)進行改造。對中國傳統園林建筑藝術頗有見地的錢伯斯將其心得付諸于造園實踐中,并參照約翰·尼霍夫繪制的寺塔圖像在園中建造了中式寶塔(Great Pagoda)[6]。若說“pagoda”一詞展現出了歐洲曾盛行一時的中式園林建筑風尚,“tea”的詞源信息則濃縮了厚重深遠的世界茶葉貿易史([17thc.tay,tey,prob. F. Du.teef. Chin.(Amoy dial.)te,= Mandarin dial.Cha])。在歐洲諸國中,葡萄牙人最先開始了西方與中國之間的貿易。17世紀葡萄牙公主凱瑟琳嫁給英國國王查爾斯二世并將飲茶之風帶入英國宮廷,茶葉隨之成為當時貴族階層追求異國情調的昂貴舶來品。英國維多利亞時期,“下午茶(afternoon tea)”開始興起于宮廷和貴族之間,隨后在中上階層蔚然成風,并逐漸普及至平民階層。
在文中,“Chinese pagoda(中國塔)”和“afternoon tea(下午茶)”勾勒出了茶香繚繞的午后邱園。作者用詞雖簡,讀來卻唇齒留香,仿佛置身于氣派高雅的邱園之中享受氤氳茶香。文中關于午后邱園的片斷描述看似云淡風輕,事實上當時情形卻頗具玩味:那個午后讓 “He” 念念不忘(a haunting memory)的是Vera告訴他各種奇花異卉名稱時宛若天籟的聲音( beautiful voice ),而當Vera回想起那個午后,腦海中浮現的卻是一個荒唐場景(…that particular afternoon was an absurd scene)。時間地點一樣,兩人的感受卻大相徑庭,故事從一開始便為兩人后來的感情走向埋下伏筆。源于維多利亞時期的“下午茶”不僅是貴婦小姐們單調生活的調劑,更是她們彰顯高雅品位的重要社交場合。精美茶具、別致茶點、華美服飾和優雅禮儀是富裕階層“下午茶”的必需品。文中提及的皇家植物園邱園花木繁茂,更是為這樣的一場下午茶平添了幾分悠然雅趣。然而在眾人氣定神閑淺笑低語享受下午茶之時,“He”竟氣急敗壞地像瘋子般用草帽趕起黃蜂來(…he behaving like a maniac about the wasps—waving them away,flapping at them with his straw hat,serious and infuriated out of all proportion to the occasion)。這 可 逗樂了眾人,大家竊笑不已。如此天真莽撞的舉動必然是為追求格調的上流階層所嗤笑,本該是午后暖陽中的優雅時光,卻因他的冒失而讓Vera陷入窘境。兩人分手六年后再見,憶及當時心情,Vera 僅是一句“How she had suffered”。句子簡短,語調平靜,而她當時的尷尬和難堪已盡述筆下。盡管這是Vera和“He”戀情剛開始時的小插曲,但階層不同所帶來的審美差距和認知差異由此可見一斑。故事結尾處, “He” 喚來侍者結賬,并要求點的那份奶油不能計入賬單,因為奶油沒被動過(“But the cream has not been touched,”he said. “Please do not charge me for it.”)。倘若說“He”此前言談中的種種炫耀未必是性格使然,而只是為了填補當初戀愛時自信不足的心理缺失(“…And I shall suffer so terribly,Vera,because you never,never will love me”)。
(二)詞源語用信息與篇章理解
《精讀4》第一課節選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威廉·戈爾丁(William Golding)的論說文Thinking as a Hobby。課文標題令人耳目一新,思考(Thinking)的嚴肅性與業余愛好(hobby)的樂趣性戲劇般地糅合為一體。作者在文中講述思考帶給他的樂趣,并別出心裁地將思考分成三個級別,文章亦莊亦諧的語言風格使讀者們意外地發現“thinking”并不是讓人望而生畏的哲理性話題,然而文章筆鋒犀利,用詞之深邃令不少讀者深感晦澀。讀者如能細心研究文中關鍵詞語,就能更好地提升對文章主旨理解的層次。例如,文中第31段的一句:I wasirreverentat the best of times. “irreverent”的 詞 根 是“revere”,結 合 其 詞 源 信 息([f. Frévéreror Lre(vere-rito fear)])可知,其本義帶有“fear”之意,加之其前綴“ir-”用于強調,因此“revere”所體現的“尊敬”程度遠高于“respect”,近似于“敬畏”。作為動詞“revere”的形容詞否定形式,“irreverent”延續其動詞形式的涵義,可根據不同情景語境譯為“不恭的”、“不敬的”等。《朗文當代高級英語辭典》和《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認為“irreverent”常含褒義。“Irreverent”一詞如同珠線般串連起文章的前后段落,深化了文章主旨:它可以是作者在文法學校讀書時對校規的不屑(I was a frequent visitor to the headmaster’s study,because of the latest thing I had done or left undone);可以是對學校老師霍頓先生言行相詭的調侃(Mr. Houghton thought with his neck.);可以是對社會繁文縟節的鄙夷(Political and religious systems,social customs,loyalties and traditions,they all came tumbling down like so many rotten apples off a tree)。作者所有看似離經叛道的行為實際上來源于內心對真理的渴求,追求理想的堅定信念和強大勇氣使得作者即使是在遭到打壓排擠時(They have immense solidarity),或是在因為“深思高舉”而獨自 品 嘗“自 令放 為”的 苦 澀 時(It was Ruth all over again.),依舊不屑君子明哲保身的中庸,無懼曲高和寡的孤獨,心中始存“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義無反顧 (I dropped my hobby and turned professional)。
(三)詞源詞法信息與篇章理解
《精讀4》第二課是愛爾蘭作家Liam O’Flaherty的短篇小說《春種》Spring Sowing。小說故事發生在愛爾蘭阿倫群島上的一處村落,那里遠離英國本土,年輕的一代仍舊沿襲祖輩們傳承下來的農耕生活模式。作者描繪了新婚夫婦Mary和Martin在春種第一天的生活場景,精心勾畫出Mary當日于田間家中來回奔波時的內心波瀾,將女兒家特有的感性和細膩描摹得活靈活現:時而是對春天到來新生活開 始 的 滿 心歡喜(…For the joy of spring had now taken complete hold of them),時而是瞥見丈夫眼神凌厲埋頭耕種時突如其來的恐懼(…the sudden terror that had seized her ...),時而是田間午后休憩時涌上心頭的歡欣(…a strange joy swept over her),時而是在心中一閃而過的對農婦生活枷鎖的抗拒(…a momentary flash of rebellion…),時而是一天勞作之后看著勞動成果時 油 然 而 起 的 愉 悅(…delicious feeling of comfort that overcame her…)。Mary喜憂交織的復雜情緒讓有些讀者頗感不解,事實上作者在故事開始時對此早有鋪 墊,文 中 第5段:Still,as they walked silently in their rawhide shoes through thelittle hamlet,there was not a soul about…and they both looked back at the little cluster of cabins that was the centre of their world,with throbbing hearts. 其 個 中 緣 由 從 段 落 中 的“little hamlet” 兩詞可見端倪。“little”一詞自無需贅述。hamlet從構詞上看,是由詞根“ham-”和后綴“-let”組合而成:“-let”是常見后綴,用以描述物體之小,如booklet (小 冊 子),piglet(小 豬)等,至 于“ham-”, 參 照 其 詞 源 信 息:[ME,f. AFhamelet(t)e,OFhameletdim. Ofhameldim. Ofhamf. MLGhamm]可 知“ham”源自日耳曼語,意為 “ place where one lives,house,village (某人居住的地方、房屋或村莊)”,后經由古法語進入中世紀英語,其起初所指亦不斷縮小并最終弱化為“a very small village (非常小的村莊)” 之義。作者在故事中將Mary和Martin所生活的村子Inverara描述為“little hamlet”更是凸顯出這片地域之狹小。村民們對世界的全部認知都來自這座極小的村莊,年輕一輩重復著父輩們的生活軌跡:朝耕暮耘、春種秋收。Mary雖已成家但還年輕 (… his wife looked hardly more than a girl ),可以預見種種的稼穡之苦。但Mary每一次的不安甚至恐懼都會被不經意間涌上心頭的欣喜與慰藉所撫平,那是因為在這座偏居一隅的海島小村里,父輩們默默耕耘、各安天命的生活讓他們夫婦間相濡以沫。這片土地給予村民們以歸屬感和安定感。
(四)詞源語義信息與篇章理解
《精讀4》第六課《電話》The Telephone是Anwar F. Accawi的作品,他在文章里生動流暢地敘述了童年往事。所謂“文以情生”,作者用真摯的情感喚起他與讀者之間跨越時空和文化的心理共鳴。作者小時候生活在黎巴嫩南部小山村Magdaluna,那里土地貧瘠、自然災害頻發,村里大人們普遍認為安裝電話既可連接繁華外界又能與文明進步接軌,于是電話公司的卡車如期而至。作者在文中以小孩的視角描述了村里安裝電話前后村民們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反差。此前與外界隔絕的Magdaluna偏僻落后卻其樂無窮,即使是嚴峻的干旱年也成為作者多年后飽含深情的回憶。那時漫長的排隊取水時光讓孩子們學會感受涓滴細流的彌足珍貴(There were days when we had to wait from sunup until later afternoon just to fill a small clay jar with precious,cool water),有時年輕的母親們會因牽掛家中小孩而在等得心急火燎時相互間起了爭執甚至是大打出手,可就在婦女們打架而揚起了漫天塵埃時,調皮的小男孩們卻為偶爾能夠看到精彩瞬間而竊喜不已(God,how I used to look forward to those fights. I remember the rush,the excitement,the sun dancing on the dust clouds as a dress ripped and a young white breast was revealed,then quickly hidden)。村里的女人們忙于操持家務,男人們卻終日無所事事閑聚在寡婦Im Kaleem家(Im Kaleem’s house was bustling at just about any time of day),作者更是熱衷于替他們跑腿買煙酒捎口信賺些 跑 腿 小 費(On a good day,I ran nine or ten of those errands,which assured a steady supply of marbels that I usually lost to other boys)。村民們彼此間親密的相處模式讓人感覺到Magdaluna這個貧窮的村莊既溫暖又安心。但在村里安裝了電話之后,Im Kaleem家原先的熱鬧漸漸消失了,留給作者的是“笑漸不聞聲漸消”的無限沮喪和落寞(In the evenings,the laughter and noise of the men trailed off and finally stop)。人們不再安于現狀,各奔前程(…men and women started leaving the village the way a hailstorm begins:first one,then two,then bunches)。電話帶給了村民們通往繁華之地的生活機遇,同時也帶走了Magdaluna的生氣和活力。文章近末尾處有這樣一句描述:Magdaluna became askeletonof its former self,desolate and forsaken,like the tombs,a place to get away from. 句中skeleton的詞義是讀者讀懂句子意義乃至理解作者情感的關鍵。在詞典里skeleton的漢語釋義通常為“骨骼;骨架”,其正確性毋庸置疑,但讀者若能追本溯源,其詞源信息可以幫助他們更為深刻地領會skeleton一詞所凝聚著的作者對故土百感交集的游子情。依據其詞源信息[mod. L f. Gk,neu.(as n.)Ofskeletosdried-up(skello-dry up)]可 知“skeleton(骨骼;骨架)”源自希臘語,其最初詞義為“to dry up (干涸;枯竭)”。作者在句中將Magdaluna村莊隱喻化:村莊仿佛身體,村民如同體內流動的血液,當血液逐漸流失,身體日益萎縮,最終就只剩一副空殼。曾經的喧囂熱鬧不復存在,人們只想逃離這個彌漫著墳墓般荒涼的地方。那個曾散發著人間溫暖煙火氣的Magdaluna,最終只能成為作者心中揮之不去的鄉愁。“skeleton”的詞源所蘊含的語義信息將作者生于斯、長于斯、卻又流離于斯的惆悵與無奈展現得 淋 漓 盡 致(Like the others who left Magdaluna before me,I am still looking for that better life.)。
三、結束語
精讀課本中收選的課文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和人文價值,文中一詞一句都值得我們細細品味。只有走向課文的細微處,對課文內在復雜性進行深入剖析,學生的鑒賞能力、語言能力和思辯能力才可能得到充分的施展和運用[7]。唯有正確理解詞語,才能讀懂句子段落,領會文章深意,欣賞原文語言的精妙,感悟作者雕詞琢句的苦心經營,從而真正學會語言文字的運用,最終達到“透”的要求。
英語詞語并非隨意排列的字母組合。每一則詞源折射出的都是一段詞語的生命歷程。有些詞語是以古典語單詞為根基的開枝散葉,有些詞語則可能在語言發展過程中產生形式或意義上的變化。“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若能在學習過程中恰到好處地引入詞源信息,就能讓詞語原本隱晦的喻意明朗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