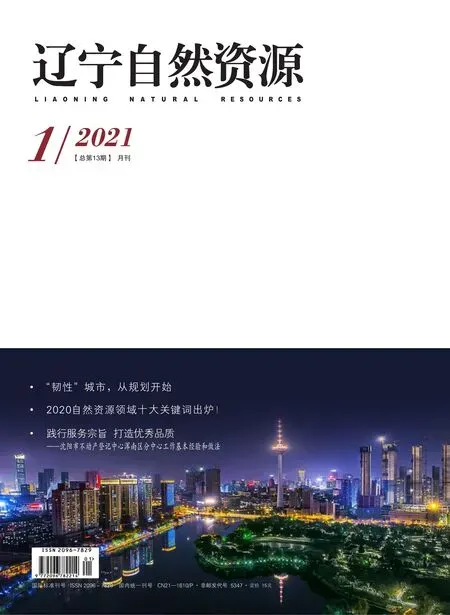嫦娥五號采回的“土特產”,可以用來研究些什么?

一轉眼,上個月24日才發射的嫦娥五號任務已經速去速回,滿分完成了前往月球-月面采樣-月面起飛-月軌對接-返回地球的全套復雜操作。
2020年12月1日夜里,嫦娥五號著陸器上升器組合體順利著陸在月球正面風暴洋東北部的呂姆克山一帶,并隨后在這里展開了采樣工作。
12月17日凌晨,“四件套”里接過最后一棒的返回器,帶著珍貴的月球“土特產”成功降落在內蒙古四子王旗,人類時隔44年再次迎來月球樣品。
嫦娥五號設計了兩種“挖土”方式:
一是鉆取:通過鉆具鉆入月表下2米深,采集0.5公斤月球地下樣品;
二是表取:通過機械臂鏟取1.5公斤月球表面樣品。
最終,兩種方式的采樣工作都非常順利,原計劃在48個小時內完成的月面采樣僅19個小時就完成了。
這些珍貴的月球“土特產”,除了一部分會用于科普和展示之外,重頭戲還是會用于科學研究。這些月球“土特產”,可以用來研究些啥呢?
改進月球定年體系
月球形成于約45億年前,但具體在第幾億年里發生了什么事,卻不是那么容易搞清楚的。
對于相對年齡,我們有一些直觀而樸素的認知。形成年代越早的區域,累積被撞出的撞擊坑就越多,也就是說,一片撞擊坑密度更高的區域,往往比撞擊坑密度低的區域古老。
但絕對年齡就難多了,因為這需要把不同區域撞擊坑統計的密度與一些已知年齡的區域建立聯系,用后者來為前者定標。阿波羅和月球號樣品就擔當了這樣的橋梁作用,對這些樣品進行放射性定年,就可以知道采樣區表面的絕對年齡,再和這些區域的撞擊坑密度一比對,一套覆蓋月球45億年的定年體系就完成了。
以這套撞擊坑定年體系為工具,我們可以進一步確定月球上那些沒有樣品和絕對定年的區域年齡。然而,這套定年體系始終是令人疑慮的。用來定標的阿波羅和月球號樣品大多來自月球正面中低緯度的月海區域,形成年齡集中在42~32億年前,而在這個范圍之外的月球地質事件所對應的時間,全部是以此為錨點外推來的。尤其是30~10億年前這段漫長的歷史,幾乎可以說是空白。
按照目前的撞擊坑定年體系估算,嫦娥五號的采樣區表面非常年輕,年齡在 1 0億年出頭。如果對嫦娥五號樣品的放射性定年結果表明,這里確實就是這個年紀,那就有力地證明了之前的定年體系是可靠的;如果差別很大,則表明之前的定年體系需要作出大幅修正。

無論是哪種,都會讓我們對月球45億年的歷史有更準確的認識。
月球晚期火山活動和熱歷史
如今的月球,寒冷枯寂,除了時不時被小行星彗星撞一撞之外,幾乎沒有什么“像樣”的地質活動。月球太小了,內部的熱量太容易散失了。
但曾經的月球,也是“熱鬧”過的。三四十億年前的月球上,活躍的火山活動噴出了大量的玄武巖,這些巖漿填充了月面低洼的區域,塑造了如今月面上廣闊的暗黑色月海。
月球上的火山活動到底持續了多久,這取決于月球內部“炙熱”了多久。阿波羅和月球號的樣品只體現了40-30億年前這段時期的火山活動,但通過撞擊坑統計估算,月球上的火山活動持續的時期遠比這悠長:從40億年前到近期都有。
嫦娥五號的采樣區,就是一片極其年輕的玄武巖區域。這里的樣品,有望告訴我們月球近期(地質上的“近期”,十幾億年前的那種“近期”)的火山活動是怎樣的,月球內部“熱”了多久,這顆小球內部在這段無可避免的“失溫之路”上可能經歷了些什么。
放射性元素之謎
對月球稍有觀察的盆友們一定能發現,月球上的月海分布得很不均勻,基本上都在正面。這是因為月球的正面地下的巖漿比較多嗎?
這些月海區域原本大多是大型撞擊留下的低洼盆地,然后被玄武巖趁低而入,大塊大塊地填滿。所以是因為月球正面的撞擊盆地更多更大,有更多低地容納月海玄武巖嗎?
這些月海聚集的區域也大多對應著月殼比較薄的地方,是因為月球正面的月殼更薄,火山熔巖更容易噴發涌出嗎?
GRAIL重力數據估算的月殼厚度,月海盆地所在的區域大多對應于月殼較薄的區域。
然而,還有一個要素是不容忽視的:這些月海聚集的區域,也和月球上一種特殊的巖石單元分布高度吻合,那就是——克里普巖。克里普巖(KREEP)是一類富鉀(K)、稀土元素(Rare-Earth Elements)和磷(P)的巖石的統稱,這類巖石常伴隨著鈾、釷等的放射性元素的富集。
許多研究推測,這些能不能都串連起來?會不會是因為月球某些地方有放射性元素富集,所以那些地方特別熱,導致地下產生的巖漿更多,月殼也更薄——這些都有利于月海的形成。更熱的地方,形成的撞擊盆地也會變得更大,這會讓原本被撞的時候沒什么區別的月球正面最終形成了更多巨大的盆地?
風暴洋就是月球上克里普巖和放射性元素最集中的地方,這塊區域還有個專門的名字——“風暴洋克里普地體”(Procellarum KREEP Terrane,簡稱PKT)。著陸在風暴洋東北部的嫦娥五號,就有可能采集到富克里普巖的樣品。
這些富放射性元素的巖石是怎么形成的?為什么剛好在月球正面富集?它們是風暴洋中晚期火山活動的熱量來源嗎?……對克里普巖樣品的直接研究,有望讓我們距離諸多月球之謎的答案更近一步。
“窺探”月球內部
月海玄武巖,“前世”是誕生于月球深處的巖漿。盡管經歷了再冷卻結晶固化的“重塑”,加之月幔物質在上涌的過程中本身也會不斷發生演化,所以最終形成的月海玄武巖并不能等同于月幔成分——但這依然是我們了解月球內部化學成分的鑰匙。
遙感光譜探測告訴我們,不同時期噴發的玄武巖成分是有差異的,一個常用的指標是鐵和鈦的含量,但月海玄武巖中鐵鈦含量的高低和噴發的早晚似乎也沒有必然的相關性。那么不同鐵鈦含量的玄武巖意味著什么嗎?是來自月球不同深度的地方?或者是月球內部的巖漿也在經歷演化,不同時期噴發的巖漿反應了月球內部不同時期的化學演化產物?或許嫦娥五號的樣品可以給出新的線索。
太陽系撞擊歷史和生命演化
更年輕的月球樣品,不僅可以幫助我們改進月球的“編年史”,還能幫助我們修正整個太陽系的“編年史”。這是因為更古老/年輕的表面就意味著更多/少的小天體撞擊,而更多/少的小天體撞擊則是太陽系動蕩歷史的體現。
月球被撞得多的時期,地球火星也不可能好到哪里去,被撞不分你我,星球們都是命運共同體。
太陽系經歷了怎樣的撞擊歷史?我們知道太陽系早期的撞擊非常頻繁,火星那么大的天體撞上地球也未必罕見,不過幸運的是,隨著撞擊體慢慢變少,太陽系也慢慢趨于寧靜。或許正是更溫和的撞擊環境,給了地球生命生息繁衍的機會。
但這些撞擊體的大小和頻率是如何隨時間減少的,我們一直缺少近30億年內的可靠證據。十幾二十億年前的地球生命會經歷些什么?是一個和如今差不多溫和的撞擊環境,還是一個頻繁被撞的hard模式?嫦娥五號更年輕的樣品,有望幫助我們填補這段撞擊歷史,了解近30億年里的撞擊事件如何影響地球生命,甚至如何影響太陽系中其他星球上可能誕生的生命。
除了這些,樣品可以做的科學研究還有許許多多。例如,表取和鉆取的樣品對比,可以告訴我們表層和次表層物質有什么區別,空間風化對月球表面物質有什么影響,可以為遙感光譜探測定標;樣品磁場的測量,可以告訴我們月球古磁場的強度和樣品被磁化的時間,進而約束月核的演化和產生月球磁場的內部“發電機”……
當然,這些宏大的“月球謎題”,是不可能僅僅通過某一次探測或者對某一次樣品的研究就輕易獲得答案的。探索未知的道路注定充滿曲折,我們唯有通過一次又一次的探索,來越來越接近答案。
怕什么真理無窮,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
而實地采樣最珍貴之處,在于樣品背后孕育的無限可能——那些我們現在還沒有想到,但隨著對樣品的深入研究而不斷發現新的研究方向和思路的可能性;那些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理論知識的更新,一次又一次重新探索和認識這些樣品的可能性;那些和過去將來的探測成果結合,擦出意想不到的新火花的可能性。
五十多年前的阿波羅樣品,直到今天還在為行星科學家們帶來新的發現和驚喜,相信下一個五十年,更多關于月球的謎霧,會由嫦娥五號和六號的樣品照亮。
除了“土特產”,還有它們
除了“挖土”本身,嫦娥五號著陸器還攜帶了降落相機、全景相機、月壤結構探測儀、月球礦物光譜分析儀等多種科學儀器。
雖然這些儀器最重要的使命還是輔助嫦五找到更安全、更有價值的挖土地點,不被堅硬的障礙物磕傷,但這些探測成果傳回地球之后,也可以用于分析著陸區一帶的月表形貌、礦物成分和淺層地下結構。
由12個天線組成的豪華探月雷達陣列(月壤結構探測儀),可以探測著陸區地下2米多深的地層結構?
簡而言之呢,就是這些儀器的探測成果,也會有科學產出。(科普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