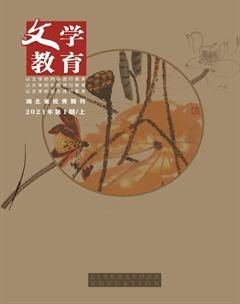蕭紅《手》中的隱喻意象和悲劇意味
紀(jì)東妹
內(nèi)容摘要:本文試圖探討蕭紅的短篇小說《手》中王亞明和父親的形象、王亞明的“黑手”和父親的“白毛巾”的隱喻和象征,以及看似光明的結(jié)局隱含的悲劇意味。
關(guān)鍵詞:蕭紅 《手》 王亞明
《手》是蕭紅唯一的一篇描寫中學(xué)生活的小說,以蕭紅就讀的中學(xué)“東特女一中”為背景[1],在對鄉(xiāng)下染坊家庭出身的王亞明進(jìn)城讀書的艱難處境的描寫中,充滿了對下層人民苦難生活的同情,而王亞明和父親的互動中則充滿了溫暖的親情。《手》中反復(fù)書寫了王亞明和父親黑色的手,以及王亞明的父親攜帶的白色毛巾。“黑手”和“白毛巾”兩個意象形成了共同的隱喻。結(jié)局中王亞明和父親走向朝陽的方向,然而故事中卻埋下了許多通往悲劇未來的暗示。
一.王亞明與“黑手”
《手》開篇展示了富有沖擊力的特寫鏡頭:“在我們的同學(xué)中,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手:藍(lán)的,黑的,又好像紫的;從指甲一直變色到手腕以上。”[2]這樣的手立刻使人產(chǎn)生無盡的疑惑和好奇:手的主人是怎么了?是生病了嗎?那是不自然的顏色,是非人類的顏色,是疾病和死亡的顏色——令人想起張愛玲的《金鎖記》中芝壽在恐懼中看到自己的腳的顏色:“月光里,她的腳沒有一點(diǎn)血色——青,綠,紫,冷去的尸身的顏色。”[3]這樣的顏色觸目驚心,使人產(chǎn)生不祥的聯(lián)想。但“黑手”的主人王亞明在初登場時的身體卻是“蠻野和強(qiáng)壯”的,帶有鄉(xiāng)下人健康而強(qiáng)韌的生命力。她的“黑手”是勤苦勞動的印記,是家庭苦難的標(biāo)記,到了學(xué)校里,又成了她在學(xué)校生活中處于“異類”地位的徽記。她的手和她的言行多次引來同學(xué)們的嘲笑,但是“不管同學(xué)們怎樣笑她,她一點(diǎn)也不感到慌亂”,即使其他人嘲諷她,“她自己卻安然的坐下去”。她有堅強(qiáng)的精神,仿佛若無其事般面對同學(xué)們的惡意,廢寢忘食,用功讀書,“她的眼睛完全爬滿著紅絲條;貪婪,把持,和那青色的手一樣在爭取她不能滿足的愿望。”她的手和露出疲態(tài)的眼睛共同構(gòu)成了對愿望的追求的象征。
故事初期的王亞明看似遲鈍,在同學(xué)們的嘲笑中表現(xiàn)安然,毫不慌亂,但她并不是真的對這一切都無所謂,也不是遲鈍到無法感受別人的惡意。在她父親來看望她之后,她向“我”問接見室要不要錢的事時說:“你小點(diǎn)聲說,叫她們聽見,她們又談笑話了。”可見,王亞明的內(nèi)心也是敏感的,只要有機(jī)會,她也想盡量避免別人的嘲笑。可是很多時候她避免不了,她無法改變,她的染布技術(shù)不僅給她帶來“黑手”的印記,還進(jìn)一步使她無法融入學(xué)校的集體。有一次,王亞明用鐵鍋染了襪子,結(jié)果導(dǎo)致別人用鍋煮的雞蛋變成了黑色。面對同學(xué)的憤怒,王亞明提出去清洗鐵鍋,但并不能解決問題。她沒有道歉,以為洗干凈鍋就可以彌補(bǔ)(可能是因為沒有錢買新鍋,但更可能是出于窮苦生活影響下的慣性思維,完全沒有想到還可以買新的),甚至自言自語地辯解:“喲!染了兩雙新襪,鐵鍋就不要了!新襪子怎么會臭呢?”從小生活在鄉(xiāng)村的王亞明,不了解處理錯誤應(yīng)有的交際方式。隨便使用他人或公用鐵鍋的行為——“我不知道這鍋還有人用,我用它煮了兩雙襪子”也表現(xiàn)出了物權(quán)意識的缺失。這些不僅體現(xiàn)了王亞明缺少基礎(chǔ)教育的背景,更顯現(xiàn)出了傳統(tǒng)農(nóng)村與城市文明之間的隔膜。
但是,同學(xué)的嘲笑、排擠,校長和學(xué)校工作人員的冷漠,并不使王亞明因此厭惡學(xué)習(xí)、憎恨學(xué)校。故事中的“我們”都嘲笑王亞明,從她來的那一天開始;但是當(dāng)王亞明要走了的時候,她卻“向我們每個人笑著”,即使“并沒有人和她去告別,也沒有人和她說一聲再見。”對王亞明來說,在學(xué)校里努力獲取知識想必是幸福的。即使她很難掌握那些對別人來說很容易的知識,即使大家對她的態(tài)度不好,但是她卻愿意對學(xué)校這個給她知識的環(huán)境、對和她朝夕相處過的同學(xué)表露善意。盡管王亞明所處的環(huán)境是冷漠的,但是她的內(nèi)心卻是溫暖的。
老師和同學(xué)對王亞明的手的過分挑剔、嘲笑,的確顯現(xiàn)出學(xué)校內(nèi)的人情冷漠,但王亞明自身的缺點(diǎn)也是受到排斥的原因。蕭紅在塑造王亞明的形象時,把她勤奮、努力、善良的優(yōu)點(diǎn)和笨拙、不懂人情世故的缺點(diǎn)結(jié)合起來,從而塑造了豐富立體的形象。蕭紅通過敘述者“我”對她的觀察,不僅多次描寫她各種各樣的努力表現(xiàn),還采用直接的心理感受表達(dá)出“她的眼淚比我的同情高貴得多”,這些都顯現(xiàn)出了對王亞明的欣賞,而王亞明難以改變的缺點(diǎn)則使讀者看到了鄉(xiāng)村底層人民融入城市生活的艱難。
二.王亞明的父親與“白毛巾”
王亞明的父親的手“也是青色的手,比王亞明的手更大更黑。”他的言行也同樣成為學(xué)生們嘲弄的對象。他第一次來過之后“在課堂上,一個星期之內(nèi)人們都是學(xué)著王亞明的父親。”但另一方面,文中又多次強(qiáng)調(diào)了他的“白毛巾”,和變了顏色的手形成鮮明的對比。如暑假后父親送王亞明過來的時候,“她父親腰帶上掛著的白毛巾一抖一抖的走上了臺階”;知道校長已經(jīng)不讓王亞明考試之后,“她的父親站在樓梯口,把臉向著墻壁,腰間掛著的白手巾動也不動。”以白毛巾的動態(tài)指代父親的動態(tài),“白毛巾”的意象似乎是父親的某種精神內(nèi)涵的外化。
從事染布工作的人隨身的衣物很容易沾上染料的顏色,王亞明的個人衛(wèi)生也有很大的問題,但父親每次來到學(xué)校總是隨身帶著潔白的毛巾,是不是為了靠外在形象給自己和女兒爭取尊嚴(yán)呢?故事中通過很多細(xì)節(jié)表現(xiàn)出父親對王亞明的愛護(hù)。王亞明有兩個弟弟,但父親并沒有因為“重男輕女”剝奪她受教育的權(quán)利。如果他重男輕女,顯然要為家里的男孩節(jié)省資金,絕不會支持女孩上學(xué)。在那個時代,作為一個連自己的姓氏都“記了半頓飯的工夫還沒記住”,而且家里有很多孩子的底層勞動者,能讓女兒去學(xué)習(xí),鼓勵她努力,是非常珍貴的。他對王亞明說:“好好干吧!干下三年來,不成圣人吧,也總算明白明白人情大道理。”因此,父親的“白毛巾”與言行的細(xì)節(jié)結(jié)合起來,隱喻的是一個染布為生的勞動者對心愛的女兒的期望。他希望王亞明把知識從學(xué)校帶回來,傳給弟弟妹妹們,表現(xiàn)出了農(nóng)耕文明下的底層勞動者對現(xiàn)代文明的向往。
故事中對王亞明的父親著墨不多,但精煉的描寫卻展現(xiàn)出了濃濃的親情,顯示出了蕭紅的深厚筆力。在王亞明因為學(xué)習(xí)太差,不能參加考試,無法繼續(xù)讀書的時候,父親沒有表現(xiàn)出憤怒,沒有責(zé)怪她,只是“站在樓梯口,把臉向著墻壁,腰間掛著的白手巾動也不動。”沒有一句臺詞,僅僅通過面向墻壁的動作和不動的白毛巾,傳達(dá)他內(nèi)心復(fù)雜的感受——寄予希望的女兒沒能學(xué)出成果,該是多么失望。但是他不僅沒有生氣,給她背來了氈靴,怕她凍掉雙腳,而且還讓王亞明戴著僅有的一副手套,自己在寒冷的天氣里赤著手幫她拿行李:“王亞明的氈靴在樓梯上撲撲的拍著,父親走在前面,變了顏色的手抓著行李的角落。”這個畫面使人聯(lián)想到朱自清《背影》中描繪的父親背影,那種質(zhì)樸的溫情,在無言之中最是動人。
王亞明溫和敦厚的性格的形成,與這樣的親人不無關(guān)系。盡管同學(xué)嘲笑她,校長對她百般挑剔,學(xué)校的工作人員也排擠她,但她并不放棄,甚至能以笑容面對嘲諷自己的同學(xué)們,不僅是因為在學(xué)校里得到了知識,也是因為在她的背后有溫暖的家庭,有愛她的家人在支持著她,給她心靈的力量。蕭紅自身的經(jīng)歷在生母早逝、關(guān)愛弟弟妹妹等方面與王亞明有所相似,但另一方面又有強(qiáng)烈的反差:蕭紅家境雖然比底層好一些,但她卻經(jīng)常和嚴(yán)厲的父親張廷舉發(fā)生沖突。因此,蕭紅的作品中常見嚴(yán)酷的父親形象的描寫以及對父權(quán)制的反抗。[1]但在《手》中卻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溫情書寫:“父親這一形象對于蕭紅而言,在其他文本中往往是粗暴甚至是可怕的,而文本中王亞明的父親卻是淳樸與慈愛的代表,這也恰恰不自覺的流露出蕭紅對于溫情父愛的憧憬。”[4]
三.家庭衰落的書寫和隱含的悲劇
《手》從王亞明個人身心遭受的摧殘寫到她的家庭的衰敗,體現(xiàn)出蕭紅作品中常見的“整體潰敗”的主題。王亞明的姐姐已出嫁,有很多弟弟妹妹,母親早逝,生活艱苦,勉強(qiáng)供得起王亞明上學(xué)。而故事中的細(xì)節(jié)顯示出,這個家庭還在繼續(xù)走向衰落。
王亞明的父親最初來學(xué)校看她時,發(fā)現(xiàn)她長胖了,還跟她說了家里的很多好事,如女兒走訪親戚、家里的豬長得更更胖了、王亞明的姐姐回家?guī)兔﹄绮说龋@些都是喜慶的事情,值得和她分享。但這之后,王亞明在春天萬象更新的時候卻“漸漸變成了干縮……那開始陷下的胸部使我立刻從她想到了生肺病的人。”她的身體顯然出了問題。但在暑假回來后,她在學(xué)校洗得有些褪色的手卻變得更黑了,甚至黑得像鐵一樣,可見王亞明暑期在家?guī)兔M(jìn)行染布工作。盡管身患疾病,還是不能休息。盡管如此,這時父親還能叫來馬車,送她來學(xué)校。而在故事的結(jié)局,卻連馬車也沒有了:“她問她的父親:‘叫來的馬車就在門外嗎?‘馬車,什么馬車?走著上站吧……我背著行李……”滴水成冰的冬天,父親的胡子上掛著冰溜,可見他是從車站走來學(xué)校的。天氣寒冷,路上有雪,難以前進(jìn),他為什么不坐馬車來?他那么疼愛王亞明,難道不想讓她坐上馬車,趕快回去嗎?這恐怕是因為她的父親已經(jīng)沒有錢了,雇不起馬車了。
在故事的最后寫到,王亞明和父親“向著迷漫著朝陽的方向走去。”看似引向了光明,但卻埋藏著深深的憂慮。王亞明得了肺病,咳嗽很厲害,家里每況愈下。王亞明向“我”借閱《屠場》后,從故事人物的死亡聯(lián)想到自己母親的死,不僅揭示了家庭的悲苦過去,可能也暗含著對自己身體狀況的憂慮。她不能繼續(xù)讀書,回去還要幫家里勞動。她的家庭衰落到這種地步,能負(fù)擔(dān)起看病的費(fèi)用嗎?王亞明的未來真的是光明的嗎?最終王亞明只是從“我”的視野里消失了,走向朝陽的方向并不等于她的問題解決了。看似光明的場景和文本中的悲劇線索形成一種張力,真正的結(jié)局其實(shí)落在“我一直看到那遠(yuǎn)處的雪地刺痛了我的眼睛”上。這種痛或許暗含著出身于衰敗家族的蕭紅對王亞明的生命之痛的深切共鳴,對她的未來的深沉擔(dān)憂。王亞明對知識的追求化為泡影,溫暖的家庭可能在貧病交加中走向更加苦難的將來。由此可見,《手》的文本在種種細(xì)節(jié)中,傳達(dá)出說不盡的悲劇意味。
參考文獻(xiàn)
[1]季紅真《蕭紅全傳:呼蘭河的女兒》,現(xiàn)代出版社,2016年版。
[2]蕭紅:《手》,《蕭紅全集》,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版。
[3]張愛玲:《金鎖記》,《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作品選(1917~2000)第一卷》,朱棟霖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51頁。
[4]劉偉平:《蕭紅〈手〉創(chuàng)作中的分裂》,《文學(xué)教育(上)》,2016年7月,第73頁。
(作者單位:沈陽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