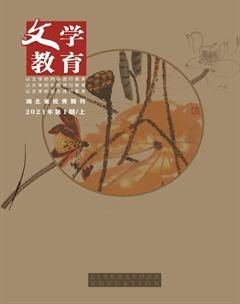劉恒影視創(chuàng)作的思想與風格
陸金燕
內(nèi)容摘要:身處一個多種藝術(shù)形式相互交往、對話與融合的時代,劉恒這位兩棲作家向我們展現(xiàn)了文學與影視聯(lián)姻的成功范例。通過對劉恒影視創(chuàng)作思想與風格的解讀,能使我們更好地了解劉恒,也能為影視文學的研究打開了一個新的視角。
關(guān)鍵詞:劉恒 影視創(chuàng)作 思想與風格
劉恒是一位關(guān)注底層民眾的作家,他的創(chuàng)作以直面底層民眾的生存困境體現(xiàn)啟蒙精神而名噪文壇。經(jīng)歷了70年代詩意溫情的青春暢想、80年代苦難的生存寫實、90年代戲謔的人性省察,從著名的小說家到優(yōu)秀的影視劇作家,劉恒多變的風格帶給我們?nèi)碌捏w驗,那些文字、韻律、思考一再帶著我們穿越生命的現(xiàn)實狀態(tài)。從1988年開始,劉恒的創(chuàng)作重點逐步轉(zhuǎn)向影視劇本領(lǐng)域。《本命年》、《菊豆》、《秋菊打官司》、《云水謠》、《集結(jié)號》、《金陵十三釵》等一部部成績斐然的影片都深深地留下了劉恒創(chuàng)作的印記。這一系列的成功奠定了劉恒作為一名優(yōu)秀的電影劇作家在中國影壇上的重要地位。那么,通過解讀劉恒影視創(chuàng)作的思想與風格,無論是對我們了解劉恒這位作家還是對影視文學的研究都顯得很有意義。
劉恒影視創(chuàng)作的思想與風格可以歸結(jié)為這幾點:人性之善、主旋律基調(diào)和個體生命價值、寫實精神、人物形象與語言特點。
一.人性之善
綜觀劉恒的影視劇作,可以說,表現(xiàn)人性善惡,揭示人生意蘊乃是其最重要的主題內(nèi)涵。① 電影《張思德》直接鮮明地凸顯了人性之善的主題。純樸、善良、“為人民服務(wù)”的品德都內(nèi)化在了張思德的生命里。他對領(lǐng)袖、對老革命、對部下、對朋友、對烈士遺孤都普照著善的光輝。一個厚道而簡單的靈魂化為銀幕上的美,讓觀眾得到一種寓于平淡善的滋潤。在張思德的追悼會上,毛主席發(fā)表了《為人民服務(wù)》的講話:“你們中間大多數(shù)人可能不了解他,走在延安的大街上,你們也不會認識他,認識了不會記住他,但他就像這清涼山上的一棵草,平凡、普通,正是像他這樣平凡普通的戰(zhàn)士,支撐了我們?nèi)康氖聵I(yè)……”。講話詮釋了張思德的為人,從他身上表現(xiàn)出來中國人骨子里的那種樸實、謙和、善良,是一種從人的內(nèi)心涌動的自我犧牲、自我奉獻的精神。這種精神不論在什么時代都是值得弘揚的。今天的人們?nèi)绾卧诘赖氯∠蚝蛢r值取向上做選擇和探求,張思德,這個在精神、在道德方面堪為楷模的人物給了我們最好的回答。
《金陵十三釵》的視角很獨特,從十三個金陵風塵女子傳奇性的角度切入,表達一個救贖的主題,反映了崇高的人道主義。劉恒說,《金陵十三釵》是“用人類之善向人類之惡宣戰(zhàn)”;張藝謀認為:“電影最基本的是人性、善良、救贖和愛。如果拍一個歷史題材的電影立即變成民族狹隘的仇恨,這樣拍電影是不對的。我認為這個是戰(zhàn)爭背景下或者災難背景下人性的光輝,這是我們最緊要的。”②
在生與死面前,人性從開始就散發(fā)出不一樣的味道。影片開頭的戰(zhàn)爭場面中,機槍手在阻擊敵人的時候?qū)χ罱坦僬f,我們馬上就可以出城了。可學生們突然出現(xiàn),為了掩護學生們安全返回教堂,這群本可以沖出城去的士兵們卻犧牲在了敵人的炮火之下;當日本兵瘋狂侵入教會,女學生逃往地窖時被日本兵發(fā)現(xiàn),她們放棄了逃往地窖,而是轉(zhuǎn)向跑到了樓上,掩護了那些地窖下面的同胞;殉葬師開始只想著那些香艷的妓女,可是當日本兵進入教會時,他義正言辭的交涉。豆蔻是個心地善良的女子,當李教官抱著浦生來到地窖,是她在細心的照顧。為了能讓浦生在臨死前聽一段秦淮曲,顧不得危險就跑回妓院拿琴弦,卻慘死在日本兵刀下;香蘭跑回妓院,尋找自己喜歡的一副耳墜兒,破碎的鏡子已經(jīng)照不全她的模樣;面臨女學生要跳樓之際,妓女們哄他們下來,回來之后,她們也在問自己,剛才是在哄他們的吧,難道要真的替學生們前往日本兵營嗎?人性不斷地被放大!小蚊子上車后,突然哭了,說自己不是女學生,此時人性尤為真實。生命對每個人只有一次,生的渴望是如此強烈!
故事中的十三個風塵女子被放置于一種特殊的文化和道德的背景之下,進行心靈的剖析和人性的拷問,帶給人們的自然是一種剝絲抽繭般的閱讀疼痛。這些妓女們,打一出場,就成為全片的焦點人物。從最初“商女不知亡故恨,隔江猶唱后庭花”到甘愿替學生們前往日本兵營,這個獨特的視角使寓于影片之中的人性內(nèi)涵更深刻、更光輝,也更給人以最別樣的震撼。原著作者嚴歌苓在談到劇本改編時說:“這些妓女們平日里被看成是非常下賤的身體和靈魂,她們卻能在危難之時,為了別人獻出自己,這種行為是一種巨大的悲憫。這些女人,帶來一種震撼和感動。”③
二.主旋律基調(diào)和個體生命價值
“主旋律電影”一詞誕生于國家電影局1987年3月召開的全國故事片創(chuàng)作會議上,會議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堅持多樣化”的口號。通過主旋律電影宣揚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可以弘揚國家意識、民族意識,激發(fā)大眾對國家熱愛和贊美之情,對于弘揚社會真、善、美亦有積極的作用。主旋律基調(diào)就貫穿了劉恒近期的影視劇作之中。《張思德》、《集結(jié)號》、《鐵人》等都有非常明顯的主旋律色彩。不同于以往的主旋律影片,劉恒以別樣新鮮的闡釋,剔除空洞的政治宣傳和說教,注重以情感人,強調(diào)了個體的生命價值。突破和創(chuàng)新顯而易見。
《張思德》讓我們看到了主旋律影片中個體生命價值的展現(xiàn)。以往的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人物傳記片,大都以黨和國家的領(lǐng)導人為表現(xiàn)對象,著力刻畫其在領(lǐng)導中國人民獲得解放過程中的豐功偉績、高尚情操和人格魅力。但《張思德》顯然有所不同,因為張思德既非黨和國家領(lǐng)導人,亦非曾活躍在中國政治、歷史舞臺上的重要人物,他僅僅是一名非常普通的八路軍戰(zhàn)士。很多觀眾對張思德的了解,僅僅是因為毛澤東那篇著名的《為人民服務(wù)》。換言之,在張思德這個“小人物”與“重大革命歷史題材”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但是,在這樣一部以“延安”、“八路軍”、“毛澤東”、“張思德”為關(guān)鍵詞的影片中,沒有對“整風運動”、“精兵簡政”、根據(jù)地建設(shè),以及敵后抗戰(zhàn)的正面描寫,觀眾看到的是生動的細節(jié)和感人的故事。“一滴水珠折射出了太陽的光輝”,“延安”和一個“小人物”形成了互相的輝映。劉恒圍繞張思德與其身邊人物的關(guān)系展開敘事,通過對細節(jié)的細膩刻畫,展現(xiàn)了一個立體的張思德。同時,突出了張思德的善良、樸實、隱忍、舍己為人的優(yōu)秀品質(zhì)以及為信仰而犧牲的精神,從而賦予了張思德強大的道德力量。經(jīng)過創(chuàng)作者的巧妙建構(gòu),張思德不再是一個抽象的政治符號或空洞的意識形態(tài)代碼,而是一個具有強大的精神感召力的個體。④
《集結(jié)號》是以國共內(nèi)戰(zhàn)、朝鮮戰(zhàn)爭及建國初期為題材的電影,改編自楊金遠的小說《官司》。影片傳達了社會巨變中的個人正義訴求。在社會大變遷時代,個人的命運包括其崇高的英雄壯舉本身也許終究顯得渺小,但是在《集結(jié)號》中,看起來渺小的個人卻可以憑借其不懈的義舉而贏得崇高美譽。從整體上看, 《集結(jié)號》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前一部分的主題是“犧牲”,后一部分的主題則是“正名”。如果影片僅僅描寫九連的官兵堅決執(zhí)行命令,不聽到集結(jié)號決不撤退的話, 那么它將與傳統(tǒng)的戰(zhàn)爭片無異。毫無疑問,影片的重點不在前半部分的“犧牲”, 而在后半部分的“正名”。處在故事內(nèi)核的那種“義”或“義氣”,從谷子地身上體現(xiàn)出來具有了真正動人心魄的神奇力量。同社會變遷相比,個體似乎算不了什么。但就個人生命價值的神圣性本身來說,這種小義其實也終究通向大義。⑤“每一個犧牲都永垂不朽”的口號肯定了普通戰(zhàn)士的個體生命價值,深化了影片的主題內(nèi)涵。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研究者指出, 《集結(jié)號》不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戰(zhàn)爭類型電影。顯然,創(chuàng)作者跳出了傳統(tǒng)戰(zhàn)爭片的框架,將當下中國的社會心理納入其中,并成功地把主流意識形態(tài)和主流社會心理縫合在一起。影片結(jié)尾處,谷子地在經(jīng)歷了一次次令人心酸的挫折和碰壁之后,終于為九連的弟兄們“正名”,九連的戰(zhàn)士獲得了本該屬于他們的榮譽和尊嚴。當集結(jié)號再次吹響時,觀眾渴望社會公平正義的心理也得到了有效的撫慰。尹鴻富有洞見地指出,《集結(jié)號》的成功在于它縫合了主流價值,出色地完成了個體價值與整體價值的重合。或許《集結(jié)號》帶給我們的最大啟示在于,只有當“主旋律”與人民的利益和人民對現(xiàn)實的基本認知相一致的時候,它才能引起人民的共鳴。
三.寫實精神
劉恒影視劇本中的寫實精神和平民視角與他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寫實風格是一脈相承的。筆下的主人公大都是再平凡不過的小人物,他不改造生活,而是復制和再現(xiàn)生活。小說《黑的雪》講述了一位從勞改所出來的年輕人李慧泉重新生活的快樂和絕望,穿插了他與女歌手的戀情及悲劇式的結(jié)局。剖析了在中國的經(jīng)濟改革大潮中,由主人公李慧泉悲劇的命運,折射出一代青年靈魂焦灼、無所依歸、無處尋覓的思想矛盾和精神掙扎。影片《本命年》的改編大體遵循了小說原有的故事情節(jié)和人物設(shè)置,強調(diào)了環(huán)境因素以及人自身性格對其命運的影響,同時也表達了對重建理想、重建全新富有凝聚力的民族精神的呼喚。
由同名小說改編的電視劇《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亦深刻詮釋了寫實的精神,故事圍繞張大民一家的喜怒哀樂,反映了普通民眾的情感與生活。對金錢匱乏、空間逼仄、精神壓抑的現(xiàn)實生活進行了真實描摹,點透了小人物“活著”的酸甜苦辣。影片雖然看起來詼諧輕松,卻充滿著諷刺與黑色幽默,將普通百姓的無奈刻畫得淋漓盡致。
四.人物形象與語言特點
由陳源斌小說《萬家訴訟》改編的電影《秋菊打官司》,放映后取得了很大成功。秋菊與村長形象的刻畫入木三分。編劇劉恒保留了原作中“民告官”的故事框架,其他內(nèi)容則增減重組。首先是對人物設(shè)置的改變,包括人名、人物數(shù)量、人物造型。劇本將主人公何碧秋改為秋菊,她丈夫萬善慶改為萬慶來,村長王長柱改為王善堂。增加了三個新的家庭成員,一個是萬慶來的奶奶六奶(影片中改成萬慶來的父親)、一個是慶來的叔伯弟兄(影片中改為慶來的妹妹)、一個是在影片結(jié)尾才出生的孩子。為增加秋菊的形象,突出倔強的性格和告狀的百折不撓,劉恒將秋菊設(shè)計為至少有六個月身孕的婦女,這為結(jié)尾秋菊生孩子村長幫忙以及內(nèi)涵升華打下伏筆。其二,將故事地點由江南水鄉(xiāng)搬到了陜西農(nóng)村,方言演繹更有滋有味,增加了賣辣子情節(jié),不僅畫面的美感得到提升,展現(xiàn)了陜西的民俗風情,也由辣子烘托出秋菊潑辣有沖勁的個性。其三,事情的起因由“種油種麥”變?yōu)樯w房,慶來罵村長沒兒子,村長打慶來并“往要命的地方踢”。這就上升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關(guān)乎傳宗接代的話題,文化內(nèi)涵深刻,使秋菊打官司的理由更加耐人尋味。其四,重塑了村長這一形象。與小說相比,劇本中的村長形象更加豐滿,也更具人情味。尤其是在除夕夜,秋菊難產(chǎn),村里人到鄰村看戲,村長不計前嫌騎車找人抬秋菊到醫(yī)院,救了秋菊一命。孩子滿月,兩家和好,村長卻被警車帶走,秋菊官司贏了,卻困惑了,奔跑追車,情節(jié)達到一個高潮。這樣改編,無疑比小說結(jié)尾一句空洞的“當時好好說就沒事了”更具戲劇性,也更發(fā)人深省。劇本絲絲入扣環(huán)環(huán)相接的敘事手法,使觀眾始終處在一種對于前因后果的不斷探詢與期待之中,吸引力大大增加。⑥好的題材、成功的改編、優(yōu)秀的導演,使《秋菊打官司》這部影片收獲了多項大獎,廣受好評。
語言簡潔精煉、話如其人也是劉恒影視劇本的一大特色。如《秋菊打官司》,秋菊委托吳律師辦理案子,秋菊的話不僅點明了她法律知識的缺乏,也生動的塑造了人物本身。“我自己的事情就不管了?鄉(xiāng)上、縣上、市里,我都跑了一冬天了,人家都沒給我個說法,那我到你這里來,你就能給我個說法了?”“哦,那就是說,你天天收人家的錢,天天給人家一個說法了?”《張思德》中語言既樸實又蘊涵哲理,如“走進革命隊伍是為了吃飽肚子,吃飽肚子長了覺悟,就該讓更多的人吃飽肚子。”“不管干啥子工作,都想著前線就在腳底下。”“馬掌是馬掌,你要是硬不成一塊鐵,想當馬掌還當不成哩!”《集結(jié)號》里谷子地向敵軍喊話:“你們已經(jīng)給圍死了,膩膩歪歪打下去誰都落不著好。我們給各位準備了兩樣好吃的,一樣是子彈,一樣是餃子。想打我們奉陪到底,覺得打夠了,把槍舉起來換雙筷子,九連陪著弟兄們吃餃子!”這樣的對白一開場就能吸引人。可見劉恒對日常豐富生活的積累和功力。
我們最初記住劉恒,是從他那聲粗魯而暢快的叫罵“狗日的糧食”開始的,他對生存困境的敘寫,讓我們記住了他的獨特。投身影視劇本創(chuàng)作之后,對生存和人性的探詢與展現(xiàn)依然存在,不僅深刻與尖銳地直指物質(zhì)層面,更觸及靈魂深處,并帶著歷史與文化的反思。作品里反映出來的思想與風格都將這些一一印證。
參考文獻
①周斌.劉恒論—以電影劇本創(chuàng)作為例[J].文藝爭鳴 2008(10)
②張力韻.金陵十三釵:劇本打動人心 凸顯人性光輝[N].東方網(wǎng)城市導報2011-12-19
③嚴歌苓.談《金陵十三釵》劇本,“妓女抗日”非虛構(gòu)[N].光明日報.2012-01-06
④蘇濤.主流意識形態(tài).藝術(shù).商業(yè)[J]. 浙江傳媒學院學報.2010(6)
⑤王一川.歷史影像再現(xiàn)中的價值取向[J].當代文壇.2012(1)
⑥鄧文倩.劉恒電影文學創(chuàng)作的“三級跳”[D].河北師范大學.2007年
(作者單位:西北師范大學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