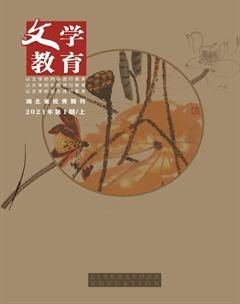《使女的故事》中的母性書寫
李察
內容摘要:加拿大女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很多作品均涉及母女關系問題和母性主題。本文基于生態女性主義視角,結合原型批評理論和作家分析,探求阿特伍德母性意識的源泉,解讀《使女的故事》中母性書寫的顛覆性話語以及母性主體的建構過程。
關鍵詞:《使女的故事》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母性書寫 母性主體 他者 原型
一.引言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小說《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1985)以美國馬薩諸塞州為敘事背景,向讀者展示了一個令人窒息的宗教集權統治下的政體。在這個國度中,女性被剝奪了經濟獨立權,并被分為了三六九等,其中大部分女性遭受著長期的洗腦和嚴苛的管束,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母性,即母親的內在性質,包括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兩個方面。母性的自然屬性是由女性的生理結構決定的,一旦成為母親,女性的整個機體結構為了適應物種存續自然地承擔起懷孕、生產、養育等職能。母性的社會屬性產生于形態各異的社會、歷史、文化的背景之下,承載著父權制對母親性別角色的界定,對處于這些環境中的女性的精神狀態和生存狀況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作用。母性書寫包括對母性主題的描寫和對母性內涵的挖掘,其目的在于打碎被父權制壓迫和奴役的母性刻板,重新建立母性話語和母性主體。在《使女的故事》中,女主人公既具有女兒的身份,又具有母親的身份,因此書中的母性書寫從兩個角度開展:第一,以女兒身份講述對自己母親的記憶;第二,以第一人稱的母親身份對自己為人母的經歷和回憶進行敘述。“生存”作為阿特伍德作品中反復出現的一大主題,同樣也出現在這部小說中。在為了獲得自身和孩子的生存權而斗爭的過程中,女主人公經歷了諸多劫難,也表現出了非凡的勇氣和忍耐力。
二.女性遭受到的身體禁錮和思想侵害
在基列國,生育能力較強的女性成為使女,她們被分配到大主教家中負責為其傳宗接代,在成為使女之前,這些女性先是被剝奪了工作和財產,接著被迫與家人分離,被抓到“紅色感化中心”接受嬤嬤們的訓誡和教導,同時接受“受精儀式”的專門訓練,以便提高受孕幾率,更好地發揮生育功能。她們被剝奪了原有的名字,一旦被分配到某位大主教家中服務,即被稱呼為“of”加上這位大主教的姓,表示從屬于這個大主教。使女被視為國有資源,在衣著上,她們身著代表性與生育的鮮紅色長袍。她們必須恪守健康飲食的原則,遠離任何不利于胎兒的食品。她們被要求清心寡欲,只能在規定的時間內才能外出進行日常采購,且一言一行都受到嚴密的監視。使女只是生育的工具,因此她們不需要具備知識,她們不可以閱讀,就連說話都受到限制;她們不可以打扮,因為外表對她們來說無關緊要;當她們有逾矩行為、被用刑時,往往手腳最先被折磨得血肉模糊,只要適宜生育的身體內部機能不受到損傷就行。波伏瓦指出,“任何國家從來都不敢強制性交……所能做的是,把她禁閉在某種處境中,懷孕對她來說是唯一的出路。”[1]81-82這就是基列國使女的命運,只有成功為大主教誕下孩子的使女才能免于永久放逐,等到孩子生下來之后,她又被送到另一位大主教家,為其繁衍子嗣。
小說中,奧芙弗雷德從母親的話語中汲取了抵抗壓迫、逆境生存的力量,為什么她的母親能夠給她帶來如此強大的力量呢?根據奧芙弗雷德的描述,年輕時期的母親莊重美麗、剛硬勇猛,充滿斗志,擁有極強的女權意識,曾活躍于為女性爭取夜晚行動自由、生育自由、身體自由和就業權利的游行和集會,拒絕做生育工具和“賢妻良母”。雖然她三十七歲才生下奧芙弗雷德,但她對自己的體能充滿自信,拒絕被打上“高齡初產婦”的標簽。母親絕不屬于傳統意義上的家庭婦女,她經濟獨立,從不覺得男人比女人優越,反而認為男人遠不如女人優秀,在她看來,男人“除了十秒鐘制造嬰兒半成品的那一點點價值外,什么用也沒有”[2]139,因此她另可當單親母親,也不愿意委曲求全地與在她看來眼高手低的男人組成家庭。即使上了年紀,母親也仍然堅持鍛煉,像年輕人一般精力充沛,接受自己真實的年齡和相貌,不愿意多加修飾。正是在這樣一位自信、樂觀、充滿活力的母親的耳濡目染下,奧芙弗雷德才成長為一名獨立、機智的女性,不依附于男人而活,以自己的方式反抗著基列國的清規戒律。
三.母女分離背后的強大紐帶
《使女的故事》中,奧芙弗雷德的母親被流放到遍地核廢料的“隔離營”中做苦力,暴露在有毒物質的侵害中,至死才能獲得解脫,奧芙弗雷德對母親只能反復悼念。奧芙弗雷德曾和丈夫帶著五歲的女兒試圖逃離美國,但在逃亡的路上,女兒被士兵帶走,奧芙弗雷德也被抓走當了使女。從那之后,奧芙弗雷德的眼前常常出現女兒的幻影,女兒被強行帶走時的情景也在她的夢境中反復上演,讓她痛苦不已。這些創傷記憶具有“凝結于受創當時、又無法言說的特質”[3]33,以身體感官和影像方式儲存;而創傷夢境通常包含真實創傷事件中的片段,往往反復發生,“且有著宛如發生在當下的駭人臨場感”[3]35。奧芙弗雷德深感已漸漸將母親和女兒的樣子淡忘,但她不甘心自己就這么被女兒忘卻,唯有用回憶和敘述的方式抵御骨肉分離之痛,抵御遺忘,即使她知道追憶有可能會讓自己深陷于過去,無法自拔。
小說中母子分離的情節還體現在使女在為大主教誕下孩子之后,無法陪伴孩子成長,很快被安排為下一個大主教發揮生育職能。父權文化不僅將偷食禁果之原罪全盤推卸到女性身上,認為她們“必須在生產上得救”[2]256,宣揚女性理應履行安于家中、相夫教子的神圣義務,甚至割裂母親和孩子的血脈聯系,否定母性的正面價值,把孩子當作父系家族的專屬財產。基列國的統治階級為了維護其統治,對女性進行長期的精神洗腦和規誡迫害,企圖打壓女性的主體意識,使其將男權理念不斷內化為自我管理的準則,這不是某一代女性所要承受的悲劇,而將殃及世世代代的女性。在紅色感化中心,嬤嬤們日復一日地向使女們灌輸扭曲的價值觀,麗迪亞嬤嬤稱使女們為“過渡的一代”[2]135,對這些價值觀存有抵觸心理,但是她們的下一代將從出生起便以使女的方式生活,因而會欣然接受作為生育機器的使命。奧芙弗雷德參加了受勛天使軍士兵接受新娘的儀式,這些女孩從未擁有過自由、充實的童年和少女時代,沒有任何戀愛經歷,直接被包辦婚姻捆綁,只為了盡早履行生育義務,她們被要求保持沉靜、一味順從。奧芙弗雷德的母親曾希冀能夠建立一種女性文化,但絕不是這樣的女性文化。在這些女孩身上,奧芙弗雷德仿佛看到了女兒未來的樣子,如果女兒繼續待在基列國,必定會遭受這些扭曲思想的毒害,延續其母親的噩夢。母親生下孩子,卻注定承受骨肉分離的傷痛,母親無法參與到孩子的成長教育過程,孩子也無法感受母親的愛與呵護,這是怎樣的一種人間慘劇!對女兒未來命運的擔憂也促使奧芙弗雷德迅速成長,重新構建其母性主體,反抗父權統治。建構母性主體并不意味著放棄母親的職責,成為母親和成為自己兩者并不矛盾,那些通過自身努力和奮斗找到真正人生價值的女性反而能夠更好地將其對人生的感悟傳達給孩子。
即使在母女分離的表象下,母女之間的牢固紐帶仍然蘊藏著巨大的力量,奧芙弗雷德的母親以其強大的母性主體意識給奧芙弗雷德的成長及其女性主體的形成帶來了積極的影響;由于沒有書寫工具,奧芙弗雷德用講述代替書寫,把她的母性故事用磁帶的形式記錄,她的聲音作為珍貴的史料被留存了下來。她從未向父權統治妥協,而是以其母性第一視角的敘述“將同時代女性的人生命運鉤織成一段屬于女性的歷史語言”[4]125,重新構建了其母性主體,動搖了男性霸權話語的權威性,激發了人們對父權文化下歷史書寫真實性的反思。
四.結語
阿特伍德的母性書寫并非呼吁女性舍棄母親身份和職責,一味地成為自我,而是期冀搭建一個母女互成主體、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和諧關系。阿特伍德賦予奧芙弗雷德母性的聲音,使她以母性主體重新審視歷史,顛覆了父權體制中被他者化的母性話語。雖然母女被迫分離的傷疤仍不時地帶來鉆骨之痛,但是母女之間強韌的精神紐帶不會斷,也正是對女兒的這股熱愛反過來激發出母性的巨大能量,鼓勵母親們在男性霸權話語中逆風前行。
參考文獻
[1][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I[M].鄭克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9.
[2][加]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M].陳小慰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12.
[3][美]朱迪思·赫爾曼.創傷與復原[M].施宏達、陳文琪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5.7.
[4]郝靜迪.簡析《使女的故事》中女性反抗話語[J].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9期:125.
(作者單位:南京科技職業學院國際教育學院)